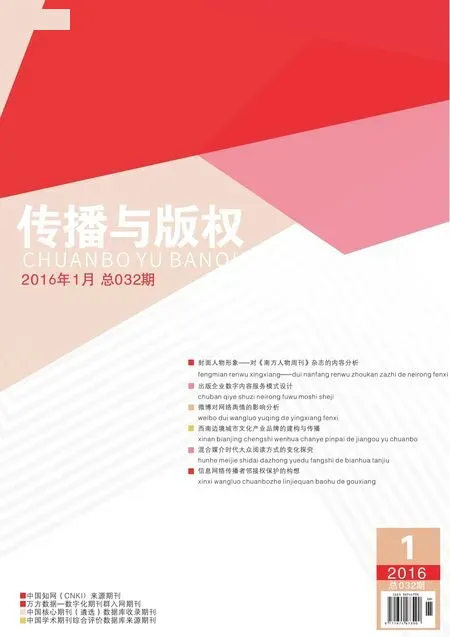大陆台湾青春电影价值取向比较研究
2016-03-28刘佳蓓孙绮薇
刘佳蓓 孙绮薇
大陆台湾青春电影价值取向比较研究
刘佳蓓 孙绮薇
[摘 要]主要探讨大陆、台湾青春电影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大陆青春电影表现出聚焦人与人的关系、世俗化的诉求以及结尾的和解;而台湾电影则更趋向于人与环境的探讨,小清新的叙事风格和悲鸣的结局。同时,探讨造成二者价值取向形成的政治、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综合原因。
[关键词]青春电影;大陆;台湾;价值取向
[作 者] 刘佳蓓、孙绮薇,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大陆、台湾均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然而大陆、台湾两岸的分治从1949年延续至今,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导致了两岸在青春电影价值取向方面的迥异。
一、人与人VS人与环境
在影片主题的着眼点上,大陆青春电影在叙事过程中着力于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台湾青春电影在讲述故事之外,更多地讲社会背景与生活状态融入电影中,或含蓄或直白地力图表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当下我们看到的大陆青春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大都被异化。现今为数不少的大陆青春电影中,主角往往无所事事却能够生活怡然快活,俊男靓女们挥霍着金钱,住着豪华别墅却喊着各式各样空洞无力的口号、追求着丝毫不接轨现实的“梦想”。①张红霞:《大陆偶像剧中的青年形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甚至有些剧情将时下校园不良现象加以放大,大肆渲染暴力、叛逆的青少年形象。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系列是描述女大学生间纷繁复杂关系纠葛的典型之一。席城和南湘反复背叛而又舍不下的互虐,顾里的心高气傲和两家的利益关系一直成为她与顾源感情路上的绊脚石,林萧终于和周崇光在一起却发现他患了重病。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人物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情感纠葛在四姐妹中步步升温。但也许正是这些让当下的年轻人在观影过程中找到那个在现实生活中无处安放的自我,影片中光鲜亮丽的角色们正过着大屏幕前观影者幻想中的偶像剧一般的生活,发泄着“我”想发泄的情绪。
苏有朋在2014年导演的电影《左耳》宣传期间说“这是一部没有堕胎的电影”②导演苏有朋在2015年专访中谈到电影《左耳》宣传期间说道。,引得众人唏嘘。由此可见这是当下大陆青春电影的常见桥段之一,而实际绝大多数人的青春时代并没有像这样骇人听闻。片中坏女孩黎吧啦因为爱上张漾而帮助他勾引许弋,左耳失聪的“小耳朵”李珥却暗恋许弋。大陆青春电影擅长将重点放在各种人物关系的纠葛上,仿佛暗示大众在一段青春里满满的都是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钩心斗角,并试图以此引起观众的共鸣。
观之台湾,台湾青春片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人与环境的层面加以探讨,通过影片讲述故事本身之外,其还承担了呈现社会显示的“多面镜”角色,戏里戏外从不同角度呈现台湾的社会背景与生存环境。以《海角七号》为例,影片在叙事过程中试图从多方位折射出台湾的时代背景。《海角七号》将视线聚焦在故事的发生地恒春上,此时恒春就如同台湾的缩影,因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而形成了不同社会成员共存的局面,在恒春舞台上展现出的不同群体的矛盾与碰撞、理解与融合,则可以理解为台湾的微缩景观。《海角七号》除了讲述阿嘉与友子的主线剧情,还多层次地展示了恒春这样一个背景杂糅的台湾小镇,不单纯讲述阿嘉的追梦故事,同时还跨越了老一辈与年轻一代人。在《海角七号》中,恒春成为一个意向、一个符号,它代表着台湾岛:一方面保持着传统,一方面又吸引着外来人驻足停留。恒春的居民则又代表着台湾的居民,发生在恒春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代年轻人的青春,更是整个台湾岛的缩影。
二、世俗化VS小清新
青春类电影往往以不同的视角来向大众传达视觉的唯美,大陆电影擅长将景观从奇幻的场景移植到现实生活中并且通过增加画面的华丽感来模糊现实生活中的粗糙细节。③杨红菊:《中国青春偶像剧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精致炫目的奢华景观配以现代的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无形中引导人们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以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为例,其第一部第三部没有具体连贯的故事情节,取而代之的是四位主角不断变化的衣着、华丽的衣帽间,展示的是一个个精致的场景和人物,而在现实生活中当观众看到这些时,他们往往被这样炫目光辉的假象所迷惑而沉醉于表象中。观众的初衷是要收获情节思想主旨而不是接受扑面而来的似电影散文般华丽的零碎画面。《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戏剧冲突的焦点放在女主角郑微感情上的反反复复与女二号阮莞的被他人背叛之上。陈孝正口口声声说郑微是他唯一爱过的人,但当面临未来转折时却轻易抛弃对方。影片中处处表达着为了各自所谓的成功名利都能放弃爱人。
同样是经历波折的过程,近期炒得火热的台湾校园青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便广受好评,当然不单单是因为它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整个影片的叙事平淡却胜在张弛有度的节奏和台湾电影的本土化实践。从我们熟知娇嗔的“台湾腔”倒并不为人熟知不那么漂亮的演员,这些向大众展示的就是最真实的台湾,所有人都经历过的青春,大众观影时也不会觉得声音的做作或是讨论演员的演技。细腻、真诚、朴实是它的特点,用心去生活和爱别人是电影的主旨。将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放在青葱校园,也是属于很多人的故事。曾经女主林真心无比崇拜刘德华,多年以后,男主徐太宇成了刘德华的助手,让刘德华将“真心爱你”的演唱会唱给了林真心。台湾电影能向观众传达出一份好的愿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平凡的叙事让大众深深感动,有经历的会投射往日旧时光的回忆;没经历的会遗憾年少的苍白。面对岁月,面对过往青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怀念,无论是谁无论哪种情形都足以催泪。
而台湾青春系列电影在取景方面,着力于将整个影片镜头几乎都放在校园中,这样的取景决定了电影校园小清新的整体基调。台湾电影总能从细节上体现出大多数人最真实的青春,让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2011年,由九把刀自导自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沈佳宜坐在柯景腾后面,每次喊柯景腾时,沈佳宜都用笔从背后戳他;沈佳宜和柯景腾打赌谁能考第一名的时候,柯景腾提的是要沈佳宜扎一个月的马尾……每个女孩的青春里都用笔戳过前排那个搞笑的男生,每个男生的青春都有曾被那个坐在自己后面可爱的女生戳过的美好回忆。这些细节总能引起你我在不同时候的共鸣,这也是大多数人在青春年少时青涩而最真实的校园生活。
三、和解VS悲鸣
在影片结局的设置上,大陆青春电影倾向于和解的结局,所有的波折、误会终在影片结尾化解,人物最终实现与彼此、与社会的和解释怀。在《小时代》系列中,纵然各个角色在不同的友情、爱情与利益之间纠缠不休,看似无可挽回的所有波折都在《小时代》系列的最后一部——《小时代:灵魂尽头》中得到和解:顾里与顾源的爱情危机最终化解、四位闺蜜“时代姐妹花”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宫洺与崇光之间放下家庭利益的纠葛寻回亲情、反面角色席城在片中死亡的结局亦代表着某种意义上与现实的和解。《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尽管故事过程中剧情波折不断,主角们在各自的故事中历经悲欢离合,故事的最后:步入社会打拼多年的郑微与陈孝正再次相遇,在彼此的交谈过程中放下了过往种种。同样在《左耳》中,四位主角在高中时代经历了感情与友情的欺骗、背叛,同时承受着自我迷茫与自我找寻的过程,故事以黎吧啦的死亡为转折,主角李珥对张漾的感情由当初的憎恨到结局时的理解;张漾在最终幡然醒悟并开始赎罪;李珥最终放下对许弋的感情期许。无论《左耳》的过程如何曲折悲伤,其最后的结局亦没有跨出达成和解的范畴。
台湾青春电影在结局的安排上则更加强调“悲鸣”,表达着对青春时代的遗憾与对现状的不甘。电影《海角七号》的结局是典型的“悲鸣”范例,影片结局处,主角阿嘉对友子说“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看似开放的结局其实是悲剧的暗示,因为无论是“留下来”还是“跟你走”都不符合现实的可能性。六十年前另一对情人的分开同样暗指着他们的结局,曾经的分离因为战争,而现在的分离却因为现实的变故,如此结局实则暗含浓浓的不甘,充满悲鸣的色彩。无独有偶,《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结局亦如此,女主角沈佳宜最终没有和任何一个追过她的人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另一个与她的青春无关的人,男主角柯景腾最后在婚礼上的幼稚行为,其实是内心不甘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达。那些年追过的女孩已然不是眼前人,即使还爱着对方,美好的回忆还存在,但现实中青春已逝,只空留“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无奈伤感。
大陆、台湾青春电影在结局处理上的迥异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样的。对于大陆而言主要因素有二:其一,大陆观众普遍倾向于“合家欢”式的大团圆结局,一个相对温情的结局更符合观众的心理期许,亦更适合当下的大陆电影市场;其二,以“和解”为结局,更加符合当下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更加符合大陆当下的电影审查制度。台湾则是:其一,处于岛屿的独特地理位置造成的不安定感从侧面影响着编剧与观众对结局的偏好;其二,大陆、台湾长期分离,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相对复杂的情绪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