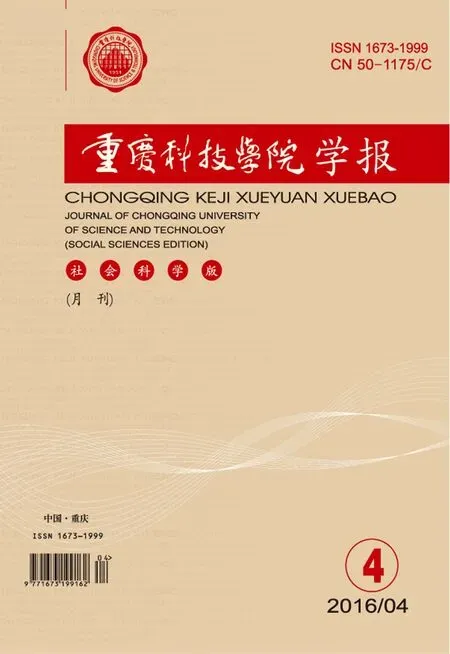毛泽东诗论的对立与统一
2016-03-25魏铭
魏铭
毛泽东诗论的对立与统一
魏铭
摘要:毛泽东的诗词理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用诗词创作给中国诗歌带来了极大影响,而且以他的诗论深刻阐明了诗歌的本质及创作规律,为中国诗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毛泽东的诗歌理论中,有许多观点都呈现出对立与统一的特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毛泽东本人针对当时诗歌发展特点提出的科学而不矛盾的、有利于诗歌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更好作用的创见。
关键词:毛泽东诗论;对立与统一;新与旧;内容与形式;雅与俗
毛泽东诗论主要见于毛泽东的几封谈诗的信件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从这几封信件及《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大致的诗论主张:
第一,他从诗的方法论和鉴赏论出发,阐明诗要用形象思维,即运用想象和联想来创作诗。他从唐诗与宋词的比较中,得出形象思维是诗人不能违背的艺术规律。这是他在给陈毅的信中提到的观点,他认为还应该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第二,他从诗体论出发,阐明了当代诗人应该怎样写“今诗”[1]3。他指出今天的诗人写传统诗词就要写今人的生活,表达今人的思想感情及其矛盾和斗争。新体诗和旧体诗都是他所说的“今诗”。他还提出:“新诗应该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吸取养料。”[2]170
第三,他指出“诗,当以新诗为主体”[3]57,认为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旧体诗不容易学,同时束缚人的思想。
第四,他主张把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以及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从诗歌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出发的。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的批评标准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2]56,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这是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出发对文学理论提出的建议。
第五,他提出写诗要有“诗意”和“诗味”。如果仅仅突出主题而没有诗意,强调诗意则远离生活,那么就与主题相背离。要解决主题与诗意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艺术上多下工夫,运用形象思维,通过使用意象,运用联想和想象,诗意和诗味便自然流露出来了。
从毛泽东诗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一些诗论观点是对立矛盾的,但同时又是相互统一的,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新”与“旧”的对立统一
自“五·四”运动以来,新体诗与旧体诗是明显的对立关系。在新体诗中,以胡适为主的自由体派提倡用白话写诗,反对一切古典诗歌。以闻一多为主的格律派主张“带着镣铐跳舞”,提倡格律,但也提倡以白话文入诗。旧体诗虽然跟古典诗歌有很大不同,但从形式到内容仍然有古典诗歌的痕迹。毛泽东所写的诗词都是旧体诗,但他的旧体诗又不同于以往的旧体诗,其诗词内容都是反映现实生活或者是革命战争等重大事件。他很少写新诗,可见他对古典诗歌的喜爱,但是他却觉得作诗应当以新诗为主。这个观点看似与他的实际创作自相矛盾,其实是有其原因的:毛泽东认为新诗一方面太过散漫,另一方面不易被大众读懂。如果能够对新诗加以改造,那么新诗势必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毛泽东曾指出新诗应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吸取养料,借以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在这里,从传统的古典诗歌中吸收养分是毛泽东想让新体诗借鉴旧体诗的形式以及风格,如用韵、对豪放和婉约诗风的继承、诗歌的形象思维,以及赋、比、兴等传统手法的运用,从而使新体诗在对优秀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借鉴方面与旧体诗达到内在的统一。
同时,毛泽东对旧体诗词不是全盘肯定,他对旧体诗词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旧体诗词是“谬种”,但他也认为“旧体诗词要革新,一万年也打不倒”[3]130。指出旧体诗完全可以吸收借鉴新体诗中的优秀元素,从而摆脱原有的束缚,呈现“新”的面貌。新体诗与旧体诗在毛泽东这里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关系,新体诗与旧体诗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毛泽东为旧体诗词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用他的作品展示了旧体诗词在表现新的时代风云与革命热情方面的特点,唤起了读者的审美兴趣。他在维护新体诗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从中国诗歌发展的深度和高度上,明确指出了旧体诗词存在的条件和价值,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
中国是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旧体诗词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到唐宋诗词、元代散曲,几千年来虽几经变革,但多以文言为诗,形式与格律逐渐趋于僵化,到晚清之际已很难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不但提倡新的文学思潮和价值观念,还批评正统诗坛传统诗派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主张诗体解放,提倡“新派诗”,以白话口语入诗。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突破了旧诗的格律形式,以白话自由表达情思的新体诗终于风靡文坛。胡适认为当时中国的新诗运动是一次“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崇高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才能跑到诗里去。他认为旧体诗不能真正表达诗人内心的真实情绪,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表达出崇高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可见,他也认识到新体诗的产生不仅是诗体形式的革新,因为形式是从属于内容的,新诗形式的嬗变深深根源于社会历史的变化之中,因此是表现人们日益丰富和复杂的现代意识的需要。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新诗的出路时指出,“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3]95。他主张要从民歌和古典诗歌中吸取养料,内容应该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形式要用形象思维,采用赋、比、兴的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法。毛泽东认为新诗过于散漫,如果能将古典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运用其中,通过用韵或者限制诗歌文体等,势必会改变新诗散漫的缺陷,使新诗精炼、大致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那么,这就给新诗蒙上了一层古典诗歌的外衣,内容是新的,形式却是旧的。这一新一旧从表面上看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毛泽东是想借古典诗歌的优秀创作传统来弥补新诗形式方面的不足,毕竟新诗还太“年轻”,这种借鉴并不会使新诗“不古不今”,相反,它会让新诗在新的时代下体现出一种贯古通今的思想艺术魅力。借旧体诗的形式,能让新诗的内容更加饱满。新诗的内容与形式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完全统一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诗应该是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划分文艺标准时,他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2]58的观点。一般看来,革命的政治内容都是严肃、严谨、具有鲜明时代革命色彩的,它与完美的艺术形式是相互对立的,要突出政治性,势必会削减甚至失去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其实,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的政治内容”是指革命的时代精神、革命的人物形象以及积极奋斗的劳动热情。所谓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是指浓郁的民族风格,能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时代特色。对于这样一种以写实为主的政治内容来说,要做到“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看似不可能,但是毛泽东将这两个概念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进行了重新定义,使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可以统一于革命新诗之中。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读毛泽东的诗词,首先能看出有明显的古典诗歌的形式美。细读其内容,则都是当时描写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等反映现实内容的题材,既有古典诗歌的厚重、严谨之美,又具有现代气息的新鲜之美,而不是古典诗歌的陈腐和老旧。如他创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111这首七言律诗不仅沿用了古典诗歌的创作方法,而且延续了律诗传统的押韵风格,但其内容是反映当时红军在国民党大围剿时期,跋山涉水,不畏艰辛踏上长征之路,最后三军汇合的历史事件。这种用古典诗歌的创作方式来展现现代生活面貌的诗歌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特色。
三、诗歌内容本身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主张诗歌内容应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统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无论是从思潮角度还是创作方法上,其关系都是极为对立的。它们正如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革命的现实要求必须真实地表现革命现状,如实记录革命进程;而革命的浪漫主义则是脱离革命现实,去寻求一种矛盾弱化,甚至带有盲目乐观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依旧是毛泽东从当时的现实需要出发,而不是毛泽东专门针对诗歌自身发展规律而提出来的。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内容本身的对立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革命是残酷现实的,战争中有不断的流血和死亡;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取得革命胜利抱有希望,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不断激励他们前进和战斗。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诗歌当时承担了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重任。内容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其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结合,既要求诗人扎根于生活现实,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和源泉,又要求诗人高于生活现实,用革命理想去照亮现实,从现实出发,展望美好,创造出比现实更加美好的诗歌世界。
毛泽东强调诗歌创作应该关注现实,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诗更富情感因素,更具浪漫气息,所以,不应该破坏诗歌自身的艺术美感。如他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117既写出了红军在行程两万里到达六盘山这一历史事件,同时又表达了豪迈的气概以及对未来革命胜利的信心。
四、雅与俗、古与今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认为民歌和古典诗歌分别是新的出路。民歌与古典诗歌,一个来自于民间,是大众化、口语化的;一个来自于文人,是精致化、贵族化的。民歌与古典诗歌在古代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毛泽东则认为这两者皆是新诗的出路。民歌具有生动、朴实、便于理解的优点,倘若新诗能吸取这些优点,则能避免僵化、教条化的缺点。古典诗歌具有韵律美和古典美,新诗也可以采纳。民歌与古典诗歌并不是对立的,两者都是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与其一味照搬西方诗歌的模式,不如从民族自身传统中寻找新诗的出路。当然,这并不是说会摒弃外国优秀的诗歌传统。要想让大众关心诗歌,诗歌就不应该脱离大众,而是应该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特点。
毛泽东的诗词中不乏既雅又俗的作品。一方面他注重写大众能懂的诗,另一方面他又十分看重诗意、诗味。写诗过于直白,虽然读者能轻易读懂,但却丧失了诗味。毛泽东十分注重提炼诗意和营造诗美。如他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1]163形象的诗意既写出了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情景,又不晦涩难懂。
总之,毛泽东诗论是毛泽东把诗歌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对立统一的特点。毛泽东的文艺生涯,自始至终都在诠释对立与统一:他既具有革命的热情和理想,又拥有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既写《沁园春·雪》这类豪放词,也写《虞美人》这类婉约词;他一方面强调诗歌的政治功用,另一方面又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审美;他肯定新诗的地位,但又从不写新诗;他发表旧体诗词,但又说旧体诗词是“谬种”,不建议让青年阅读。笔者认为,诗歌应该远离政治,一旦诗歌为政治服务,最终都会沦为政治的附庸,诗歌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做战斗工具的。然而,诗人毛泽东在特定的时代,将诗歌的文学性和政治性相结合,用诗记录了他的革命生涯,用诗鼓舞了千百万革命群众,用革命的最终胜利实现了文学与政治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周正举,阎纲.毛泽东诗话[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2]毛泽东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陈德述,苏文聪.毛泽东诗词与新体诗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编辑:文汝)
收稿日期:2016-02-25
作者简介:魏铭(1990-),女,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4)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4-00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