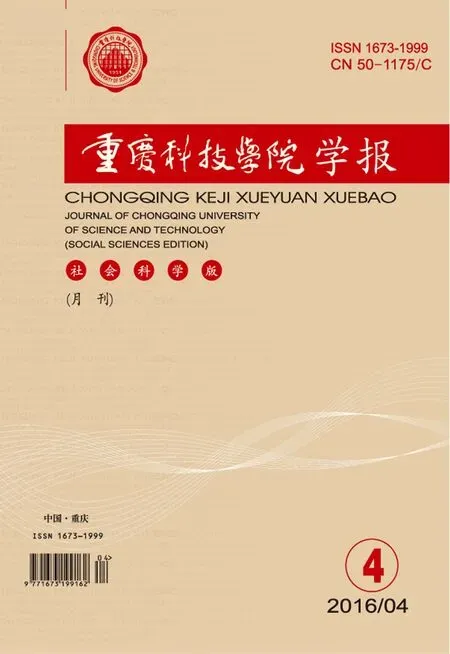新世纪甘肃乡土小说创作的精神特征
2016-03-25慕芳刘敬伟
慕芳,刘敬伟
新世纪甘肃乡土小说创作的精神特征
慕芳,刘敬伟
摘要:新世纪以来,甘肃乡土小说创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较大的突破,备受当代文坛关注。甘肃乡土小说呈现出较为独特的精神特征,展示了甘肃小说创作的文化品位,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格局。受作家自身因素和地域因素的影响,甘肃乡土作家需要进一步提升创作水平,促进乡土小说创作新的发展。
关键词:甘肃;乡土小说;精神特征;文化;人性
新世纪以来,甘肃的乡土作家深情关注着生活在这方古老土地上的农民的生存境况,创作的乡土小说呈现出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多发表在国内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并多次荣获大奖,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雪漠的《大漠祭》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猎原》2005年获得“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王新军的《民教小香》获“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2011年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马步升的《青白盐》2008年出版,被新浪网、搜狐网等新媒体推广宣传,并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
这些成就的取得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甘肃小说的边缘化地位,但因作品反映的西部地域风土人情在较大程度上整体提升了甘肃乡土小说创作在文坛的地位,以独特的精神特征展示了西部乡土小说的文化品位,改变了文学理论批评家对甘肃乡土小说的批评视野和审美期待,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苦难生存下西部农民的韧性与无奈
甘肃地处西北,自然生态环境复杂恶劣,土地较为贫瘠,农村经济发展严重迟缓,农民的生存状态相当艰难。为维持基本的生存,少部分人选择了外出打工,更多的人不得不留守乡土,从土地、山川、沙漠中寻求一切可以获取的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本来就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日益恶化,同时也加剧了农民的生存危机。
面对生存的困境,农民们并没有绝望,没有退缩,而是世代因袭的坚韧、顽强、勤奋使他们咬紧牙关,不断地寻求生存之路,展示了一幅充满韧性的生存图景。雪漠的《大漠祭》以深情的笔触描写了腾格里沙漠边缘沙湾村的农民老顺一家和其他村民的日常生活,“其构件不过就是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药、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1]14这些原生态的日常琐事详实生动,具有浓郁的西北生活风情,集中呈现了特定时代下西部农民的人生境况。作品中的老顺勤劳勇敢,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面对大儿子憨头的重病,面对女儿兰兰的不幸婚事,面对为儿子娶亲的巨额彩礼,他顽强地承担着生存和生活的重压,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他常说“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既饱含了朴素而又深沉的人生哲理,也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坚韧。
与老一代农民的默忍顺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虎关》中年轻一代农民兰兰、莹儿、猛子为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拼命地与现实和命运抗争,展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但也弥漫着无法释怀的忧伤。兰兰和莹儿作为换亲的等价物,婚姻不幸,在追求个人心灵安宁的征途上二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兰兰最终遁入宗教修行,莹儿则在再嫁之际口服鸦片美丽而悲伤地死去。青年农民猛子的身上不乏乡野陋习,他想方设法挣脱经济困顿的魔魇,其生命历程中透露出一种西北男子汉顽强的韧性,最终也没能实现梦想。这其中蕴含的悲凉与窒闷让人深刻体味到西北乡土青年冲破命运牢笼的艰辛,在这些交织的生存百态中充满了“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1]14。
唐达天的《沙尘暴》以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红沙窝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为主线,生动而悲情地描绘了以老奎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和以石头、锁阳、天旺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面对恶劣生态环境带领村民谋求生存发展的曲折历程。就现实生存而言,改革开放以前,红沙窝村农民面对沙尘暴曾经被迫背井离乡,但在村支书老奎的阻拦下又顽强地重建家园,他们打井抗旱、治沙理田、兴修水利,终于攻克难关,找到了生存之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老奎倍感无能为力,主动让贤,退伍军人石头成为新的村支书。石头年轻有为,开荒种田,发展特色产业,改变农村的生活方式,向外取经成立工程队,由锁阳组织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这些措施的实施逐步解决了村民的经济问题,并向致富之路前进。天旺利用在沿海学到的一技之长回村开办了农产品加工厂,在个人致富的同时也解决了乡亲们的就业问题。新世纪以来,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红沙窝村脆弱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们的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在心理层面,面对着肆虐的沙尘暴,当地农民内心深处往往更加痛苦、无助和无奈。改革开放前大批村民被迫逃离家园的苦闷悲凉,老奎因沙尘暴失去女儿叶叶的悲痛愤懑,杨二宝面对已开发土地沙化的无助悲哀,新世纪部分村民移民新疆的无奈悲情,等等。这些因为沙尘暴而产生的负面情感让人深思和感怀。“西部乡土小说中的悲情和无常感的产生,却更多属于生存的无常和命运的不可知,这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冲突和相互改造的结果。”[2]28作品中的西部农民顽强地与沙尘暴抗衡,竭力寻求生存之路和维护生命尊严,体现了新时代西部农民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而当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和危害超出了人力的抗争时,这种情不自禁的苦痛和酸辛便油然而生,表现为一种无言的伤感和悲凉。
二、西部传统文化的痴情与眷恋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西北地区的文化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共同性的同时,也因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自身的独特魅力。“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3]10甘肃乡土作家植根于西北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吸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作品中对西北独特的风土人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折射出作家对西北文化的无限眷恋,为现代语境下的甘肃乡土小说贴上了具有地域气息的文化标签。
出于对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精研,加之人生的波折经历,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白虎关》《猎原》)表现出一种浓郁的佛教文化情结。《大漠祭》中对于沙漠月夜的空明静寂的艺术呈现荡涤着人们的疯狂物欲;对乱葬岗子的描绘氤氲着“万法皆空”的佛理哲思,“无论强的、弱的、打人的、挨打的,最终的结局仅仅是一堆骨头。无谓的争斗,有啥意义呢?”[4]33《白虎关》中莹儿和兰兰为挣脱婚姻枷锁而去沙漠腹地贩盐,但途中遇险,莹儿陷入生命的绝望,“她想原来那永恒,并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没办法,人既然是来受苦的,当然得有好多制造苦的母体。”[5]292话语背后蕴含的佛教人生观让人深思。《猎原》中对凉州南山的牧民瘸阿卡、老阿妈、拉姆的虔诚向佛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对喇嘛、活佛的寺院生活也进行了细腻刻画。同时,作家也在有意识地渲染一种佛教气氛,“这就是世界,死的死,生的生,乐的乐,悲的悲”[6]51。
源于对这方土地深沉的爱,甘肃乡土作家在作品中对民俗文化也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摹,展现了特定时代陇原乡土儿女的生活热情和对土地敬畏的精神风貌。李学辉的乡土小说《麦女》用细腻写实的笔触营造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河西巴子营世界,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巴子营的选“麦女”习俗。《麦婚》则是用温情的笔调叙述了农民王世厚为儿子王奋发和儿媳赵金莲隆重举行“麦婚”的婚礼场面,展示出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长篇力作《末代紧皮手》展示了浓郁的西北风情,精心描写了余土地入选“紧皮手”的复杂程序,并以深情的语调描绘了巴子营的乡民请末代紧皮手余土地给土地“紧皮”的仪式,体现了乡民对土地敬畏崇拜的民间信仰。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民族的情感和文明的积淀。甘肃部分作家对这一领域的挖掘提升到了人性和生命哲学的层面,展示了甘肃习武之人追求侠义正气、光明磊落、修身养性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品格。马步升的《哈一刀》中的哈一刀坚守江湖道义,因追杀刀客马五用了第二刀,心甘情愿地为死者家属当牛做马,直至身死。《一点江湖》中的徒弟凡夫子通过文谏方式夺取了师父红狐大侠的武林盟主地位,之后便自满自大,不久便葬身于西路驼道。而红狐大侠却苦练文功,终于文武双全,成为了隐形刀坛盟主。
三、乡土牧歌中的挚情与哀愁
与传统乡土文学中的苦难书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新军以其深厚的生活经历和对乡土的细致关照,为读者呈现出了温情朴实的乡土恋歌和草原牧歌,尽管并不那么清新,甚至带有一定的感伤情调。但是,这样的书写在整体意义上拓展了甘肃乡土小说的发展格局,以真挚的情感和清新的笔调提升了乡土小说的审美格调,为甘肃文学的发展增添了一种诗意氛围。
西北乡村的生活是极为平静的,人们在鸡鸣、狗吠、牛叫中耕耘劳作,生儿育女,表现出了生命的本真,感悟着岁月的流逝。同时,乡土世界中的农民并非与世无争,邻里之间也并非没有争吵和矛盾。王新军以农家动物牛、鸡、狗、毛驴为写作切入点,对乡民的人性弱点进行了隐含式的思考,具有淡淡的伤感情怀。这样的诗意境界和隐忧情怀深深体现在“大地上的村庄”系列小说《村庄的开始》《闲话沙洼洼》《吹过村庄的风》《与村庄有关的一头牛》《两窝鸡》《两个男人和两头毛驴》《两条狗》《七彩山鸡》等作品中。在《与村庄有关的一头牛》中,作家以一头老牛最后的生命历程为书写主线,穿插了老主人和小主人对牛的不同情感,然而当人与牛终将老去的时候,作家的感慨油然而生:“所有这一切是早就注定好了的,生,死,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头牛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所有的贵贵贱贱在这一刻,在时间面前都将归于平等”[7]28。作品平静而又略带感伤地表达出了对人与动物生命平等关系的深沉思索,折射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生命哲学意识。
河西走廊地区的自然风貌较为复杂,绿洲和草原这样珍贵的自然存在为西部儿女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种沁人心脾的绿意,而这样的生活状态在王新军的创作中经过独特的艺术化处理体现得更加朦胧,体现了独特的诗意。结合自己早年放牧的经历,王新军将自己对草原的感悟融入写作,将草原开阔、美丽的自然景色和牧民豁达、自由、宽厚的生活情怀生动而传神地描摹了出来,展现了牧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在《吉祥的白云》中,阿妈和阿爸为一头名为嘎达姆的牦牛举行了一场充满神性的宗教葬礼,连吉达活佛也因之诵经祈祝草原吉祥,表达了他们对草原一切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作者也由衷地赞美他们充满神性的信仰。
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草原牧民的生活更多地成为了时代的定格。王新军笔下的草原书写也弥漫着一种哀伤的气氛,作家无限留恋并赞美草原的美丽和牧民的原生态生活,却也无可奈何地折射出对一种即将逝去的生活样态的惋惜和哀叹。《八个家》在尾声部分非常明显地传达出这种情怀:“悠远而苍凉的西部牧歌,它的欢乐它的忧戚,都将在游牧方式消失的那一天完全消亡。而且它们,正在迅速地走向消亡的结局。在这一切就要到来的时候,我再唱一曲游牧者悲伤的歌谣。”[8]173
四、地域历史书写中的人生与人性
西部历史波澜壮阔而又亘古绵长,在岁月的长河中西部儿女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更多的成为了尘封的历史,成为一种逝去的记忆。甘肃部分乡土作家注重从历史中发掘独特珍贵的创作资源,“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9]309,书写西部乡土儿女曾经的生活样式和人生百味,从而展现出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复杂和波折,在一定程度上以历史的眼光折射了人生的复杂性、偶然性和人性的多面性、普遍性。
西部乡土作家的新世纪历史书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对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小说的延续和创新,拓展了新历史小说的发展格局,丰富了文学图谱。马步升的《青白盐》以陇东黄土高原为自然生态背景,以马家几代人的家族发展和生死变迁为主线,以马家后代“我”作为小说的叙事主体,展现了马家、年家、铁家、海家历时百年的家族历史和复杂的恩怨情仇。作家褪去了政治色彩对陇东日常生活百态的干涉,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陇东儿女的生活本真和原生态。作家的生活积淀异常丰厚,语言运用娴熟自如,文白相间,口语、书面语交织,俚语、俗语、方言穿插运用,在一种亦庄亦谐的语言环境中运用传统描写和现代技巧塑造了马正天、马登月、泡泡、六两、乏驴、叶儿、铁徒手等众多既栩栩如生又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一幅陇东儿女的生存和情感画卷,揭示了生生不息的生命韧性和百味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北儿女人生和人性的复杂写照。
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融风俗描写、历史书写和人性书写为一体,以最后一位土地“紧皮手”余土地的生命历程为主线,深情地描绘了解放前至文革结束期间巴子营的乡民对土地的敬畏、崇拜之情,展现了历史风云变幻中不同阶层对于传统习俗鲜明的差异性认知,也表达出作家对传统风土人情的深情眷恋和悲情讴歌,带有明显的文化色彩和对历史的哲思。
张存学的《轻柔之手》以文革作为叙事的历史背景,用魔幻现实主义笔法讲述了史成延一家的苦难悲痛,揭示了特定年代人性的复杂和丑恶。在群魔乱舞的年代,儿子史凌霄被残暴地批斗致死,儿媳程红樱不堪批斗者的人身蹂躏而跳河自尽,大孙子史克不忍目睹人间惨相而逃离拉池城,十年后归来疯狂报复恶人,小孙子史雷也变得游移不定,等等。面对亲人的惨景,史成延不断杀鸡对抗死亡和亲人的亡
灵,却一再失败,心衰力竭。史克的复仇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灵的安慰,相反却坠入了绝望和虚无的境地。而史雷在母亲亡灵化作的“白光”中感受到母亲“轻柔之手”的抚摸,内心逐渐得到安慰。作品在一种荒诞怪异的叙述中,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生活认知和人性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拷问,并努力寻找让人感受温暖、回到平静的轻柔之手。
新世纪甘肃乡土小说取得的成就为当代文坛所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地域限制,影响着当代小说的发展格局。放眼全国,甘肃乡土小说的创作之路还不够开阔和延伸,多重制约因素仍然存在并影响着乡土文学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一直关注甘肃文学发展的雷达认为,苦难是甘肃乡土小说叙述的核心。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笔下,对于苦难的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但苦难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笼罩着甘肃的乡土作家,并最终成为甘肃作家的桎梏。因此,只有超越苦难才有可能走出甘肃[10]65。我们期待甘肃乡土作家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拓宽知识视野,超越苦难的核心表达,深刻发掘陇原大地上的真、善、美,以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审美范式展现甘肃乡土小说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雪漠.从“名人”谈起(原序)[M]∥雪漠.大漠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雪漠.大漠祭[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5]雪漠.白虎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6]雪漠.猎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7]王新军.与村庄有关的一头牛[M]∥王新军的小说.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
[8]王新军.八个家[M]∥王新军的小说.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
[9]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0]雷达.新时期以来的甘肃乡土小说[J].小说评论,2010(3).
(编辑:文汝)
基金项目:2014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多元视角下的新世纪甘肃小说创作研究”(14YB065)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6-01-12
作者简介:慕芳(1981-),女,硕士,兰州财经大学(甘肃兰州730020)商务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部文学及女性文学;刘敬伟(1983-),男,硕士,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4-005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