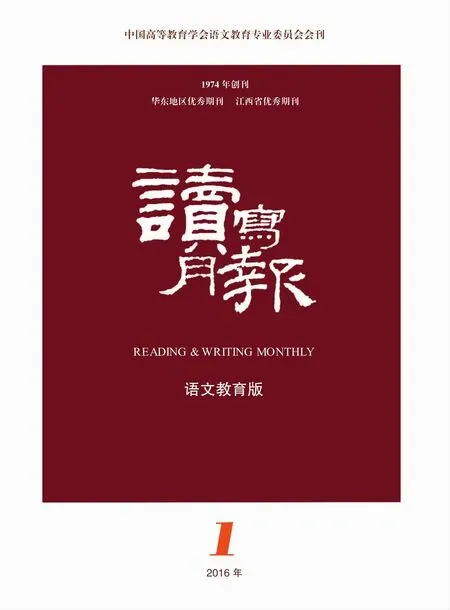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位语文教师杏坛三十抒怀
2016-03-20赵成昌
赵成昌
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位语文教师杏坛三十抒怀
赵成昌
新年伊始,翻开日历,无意中发现自己站讲台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因此,我不禁感慨万千,忧喜丛生。
做官与做事
我是在南方一个偏僻的农村长大的。读书的时候,我不仅寄托着父母、家族的希望,也寄托着全村人的希望。他们一致盼着我好好读书,能考上大学,将来做个大官,光宗耀祖,惠及乡里——“学而优则仕”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可是那年考大学,我不幸被一所师范院校录取。这意味着,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当老师的命。父母和乡亲对我的失望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上大学的时候,家里也请了客放了鞭炮,乡亲们也都来为我送行,但他们内在的失望是不言而喻的。好在我当时还年小,不怎么懂事,并没有顾及许多。
我走上教师岗位时也仅仅19岁,很多方面都不成熟。不过,自幼养成的自尊秉性时刻提醒着我: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把它做好;我的教师职业既然是命运安排好的,那就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不能让人背后耻笑。因此,工作起来我处处小心谨慎,且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让当时的校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是一个东北汉子,年岁比我父亲还大,说话常常直言不讳。有次,我们几个小年青聚会,他也来凑热闹;席间,他专门对我说,你很有前途,等你工作几年成熟后,提拔你当个主任。我当时耳朵就一热。是啊,学校也有当官的,主任大小也是一个官;能当上主任什么的,回家多有荣光!
此后,我的工作更加努力。当然更多的是为了讨好校长。东北校长也确实没有食言,仅仅两年之后就把我推上教导主任的位子。家里和乡亲听说我在学校“当官”了,都为我高兴,常引以为自豪;我当时也确实趾高气扬了一阵子。但是好景不长,还没干到一个学年我就感到特别的不适应特别的烦累。教导工作事无巨细,千头万绪,大到传达上面指示精神,小到分发学生作业本;加上本人一向性格直爽,安排工作从不知道拐弯抹角,往往顾此失彼,不能周全,领导和同事都有不少的得罪。最重要的是,我几乎没有时间在教育教学上花功夫了——身在其位,应酬难免,常常被灌得酩酊大醉,何谈什么教书育人?等清醒过来,我想想就后怕:长此以往,事业荒废那是肯定的。
说句可能让人不理解的话,自从干了教师这一行,我渐渐从中找到了一些乐趣,也渐渐爱上了这一行。但自从当了“官”,我就觉得跟事业渐行渐远。于是,在当官和做事之间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抉择。抉择结果,我还是选择后者,因为我考虑:与其在官场上虚度时光,倒不如踏踏实实做点事。当我把辞职报告递给那位东北校长时,他惊讶得目瞪口呆:“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干。”这一关还好过,最怕的是每年回家省亲——家人和乡亲早把我的官路铺设好了,我一回去总是问什么时候当校长什么时候当局长。当他们得知我辞官的实情时,没有不变脸色的。特别是我的一个族叔,说话尖刻得不得了:“人家花钱请客送礼都当不了,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呢?真是家门不幸啊!”
我无话可说,只能隐忍透心彻骨的悲凉,权当“秀才遇上兵”吧。只有回到学校,我才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当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我就显得格外的宁静与安然,仿佛一切烦恼和杂念灰飞烟灭。这时候的我,确实变成一个真正充实快乐的自己。为了教书育人,我不断看书学习,钻研教材,摸索探究;并且从理性的角度,经常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总结。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几年时间,我在工作方面就取得突出的成绩,成果丰硕,连连考评为“优”;同时,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比如“骨干教师”、“优秀工作者”。另外,在教育教学理论方面,我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发表了不少有价值有力度的论文。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被主管部门从一所县级普通中学,上调到一所省级示范中学工作。
所有这一切,当然和我“弃官从教”的决定分不开。我越来越感觉到,弃官从教是我教书生涯中一次最重要的抉择,也是一次最美丽的转身;不仅不后悔,还万分庆幸。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有一篇教育随笔在《中国青年报》“教育”专栏发表了,本来这是非常平常的事,不想被《人民日报》驻安徽的记者何聪先生注意到了,他要来采访我——我们这地方,向来山高皇帝远,极少有什么高层往来;这下,我等于丢下一枚重磅炸弹,在当地引起剧烈震荡。校长在第一时间就找到我——这是后来的校长,很年轻,跟我差不多大年龄;平常,我们无话不谈,但是朋友同时也是“敌人”,因为说话常常不怎么客气;私底下我曾经戏谑他“不学无术”,因为连高考作文也写不到500字。但是,我又不能不佩服他能说会道,左右逢源,是块“官”料;从教研组长到教导主任,没用几年时间就一路狂奔到校长宝座。刚刚坐上还没几天,就遇到这样的“大考”,紧张、无措是很自然的事。
他几乎是发疯一样的跟我说:“老兄,你写什么狗屁文章,把《人民日报》记者都要弄来?假如曝了什么光,我这校长还能当吗?你有所不知,我就是上头人的鼻涕,想什么时候擤就什么时候擤!”我这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又想,何聪先生来,无非跟我谈教育教学的问题,能曝什么光?所以尽量安慰他。校长这才渐渐平静下来,一再交代我到时一定要挑好话说。何聪来的那天,一幅壮观景象连我都吃惊:操场上彩旗飘扬,人山人海,并停满了大小车辆。县长、教育局长、宣传部长、电视台长,各首脑人物都粉墨登场——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被这么多的父母官接见,真有点受宠若惊。访谈中,他们也一律陪坐,让我跟何聪先生无法交流。我跟何聪商量,能不能让他们回避一下?何聪就示意他们走开,县长这才带着一帮头头脑脑点头哈腰地离开了。但校长不久又折回来跟我耳语:“县长大人陪坐,就是怕你乱说;拜托你,一定要遵守我俩的约定!”访谈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确实没曝光什么,上下官员们才如释重负。校长私下对我说:“这事真让我虚惊一场!你老兄以后别写什么鸟文了,有瘾就在家里写日记吧!”
我听了瞠目结舌,真想跟他红脸,但冷静之后也理解到校长的难处。不过这事真让我感慨万分,特别是对那些在台上做官的,深表同情甚至可怜:他们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这辈子不知要打多少保卫战,几乎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反过来我很庆幸自己就没有这种折磨——无官一身轻嘛!如果不是那次“转身”,我可能也摆脱不了如今校长的这副尴尬和可怜相!
至此,我还想到历史上的两个伟大人物:李白和杜甫,他们也都深受做官之害。李白四十二岁时因吴筠的推荐,终于被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抒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无奈和愤慨。杜甫漂泊西南十多年,为了朝廷一个郎官的职位而抱病离蜀:“通籍恨多病,为郎忝薄游”,结果事与愿违,客死在行程的一条破船上。现在看来,这些不能不说是他们人生中的一大遗憾。是的,中国很早就有奖励读书人的先例: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能去做官。所以,中国的政治总是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就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得既难看而又危险。当然,这不是一件好事,但又总是扭转不过来。
教学与教改
身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曾经有过一段浪漫想象。我想象中的语文是精彩纷呈,山花烂漫,处处充满诗情画意。我理想中的语文教学也一样缤纷五彩,生动活泼,课堂洒满春天般温暖的阳光,师生都情趣盎然,无不陶醉于语言和文学的美妙艺术之中。语文课堂,老师不仅仅是让学生摇头晃脑读名著,而更是像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一样,引导和帮助学生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语文课堂,老师奉献给学生的,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语文的外延跟生活同等——生活中处处有“语文”;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兼容的最大文化载体。我一直以为,既然社会选择你担当语文老师,那就是你的莫大荣幸!
所以,自在教学岗位上渐渐成熟之后,我就积极投身于课堂教学改革的洪流中。率先打破先生讲学生听的传统“满堂灌”教学模式,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全新的教学思想,进行教育教学摸索和实践。课堂上,我通过不断与学生交流、合作、探究,试图打造出一个陶冶学生情操的圣殿、活跃学生思想的孵化器。为了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我开动脑筋,灵活多变,不断改变教育策略和教学方法,让学生时时刻刻感受到课堂的新鲜与有趣。说话、演讲、辩论、表演等,成了学生课堂的家常便饭。为扩大学生的视野,我努力将课堂社会化,社会课堂化。比如:上《边城》,我会让学生讲讲家乡特有的风俗人情;天下雪了,我会跟学生说“走,到雪地作文去”;发现街道门牌有错别字,我会带着学生挨家纠正……
然而,这一切都面临着应试教育的严峻挑战。应试教育的课堂,死气沉沉,一点活力都没有;有的只是做题答卷的沙沙声,以及老师的埋怨和学生的叹息。“上课讲试卷,下课排名位,外出开考会”,这是应试教育的一贯模式。宗旨就是以考分为统帅,以考试为中心,以提高升学率为己任。特别是到了高三,学生读的全不是书,而是升学资料;教师教的也全不是书,而是考试试题。那些书商,看准时机,无孔不入,成天出入校园,目的就是推销那些高考复习资料。校园四周,书店林立,但也基本没有什么正规书出售,有的就是这“学王”那“考霸”。有时明知道这些铜臭味浓厚的试卷乌七八糟,错误百出,你还必须耐着性子自圆其说,牵强附会;你必须经常性地拿出你的考试法宝,在学生面前炫耀你的出卷、改卷、析卷之能事。教师之间围绕考分,常常斤斤计较,争风吃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长此以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一个尽头。
为此,我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无奈之下,只有振臂一呼:《我为什么无力反抗呆板的教学》,发表于《中国青年报》。没想到会掀起一番波澜,出现了前文我所不愿看到的那一幕。但事后还是感觉到了文章的力量,因为何聪先生的采访,使我在当地有了不小的知名度;采访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引起全国很多老师和专家的注意与讨论。这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方面的启迪:我不能一个人战斗,因为这不是一个学科的教学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教育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以身体力行的方式,经常上教改示范课,试图影响身边的人;又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经常与年青人研讨教改问题,试图感化后来者。与此同时,我不断著文立说,宣传推广,先后在《上海教育》《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班主任》《中小学管理》《名作欣赏》等知名刊物,发表我的教育理念和教改实践文章。考虑到目前高考的强大导向作用,针对语文考试的弊端,前不久又在《中国青年报》撰文呼吁增设听力测试,我觉得语文考听力既有必要也很可行。
总之,语文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无论刀山火海,我还将踽踽前行。
教书与写作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不与外人道也的爱好,那就是写作。因为业余时间经常写作,使我的生活很充实,心态非常好,精神一直饱满愉悦,显得越活越年轻。这让不少同事既惊讶又羡慕。当然,也有不理解和分歧的时候。有一次,和一位同事闲聊,听他说:“下辈子做头猪,也不愿去教书。”我问:“此话怎讲?”他答:“这还用解释?你整天累死累活,永远也就是个温饱;如果做头猪,不用干活,还被养得肥头大耳!”另有个同事,我与他闲聊,他说:“前世杀了人,这辈子教语文。”我问:“此话怎讲?”他答:“这还用解释?语文教得再好,学生也不重视,社会还常诟病;你难道一点也不闹心?”
然而,我对此都不以为然。我真的很感谢这辈子教书,尤其是教语文。因为教书,我经常读书研究书;因为教语文,我经常写作研究语文。写作,渐渐成了我放不下的习惯和业余最大的爱好。这种习惯和爱好,究竟是如何养成的,现在叫我说,还真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记得早在读初中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老先生,叫徐伯超;他曾是国民党一位高干的秘书,解放后留在大陆做了一名老师——他学问深得很,眼睛高度近视,上课几乎是脸贴着书的;对我作文尤为器重,每次都拿到班上范读。我的写作兴趣不知是不是被徐先生激发的。
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大学校报上。其实那也不算什么真正的作品,校报要开辟一个实习专栏,我作为前方的一个实习生,即时将实习情况如实记录下来而已。没想到交给老师,老师带回学校就把它发表了。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我还是很兴奋的,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从此,我就疯狂地写小说。当时,小说非常时兴,可是我很少有收获。慢慢地,就失去了写小说的兴趣,甚至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块写作的料。恰好,此时的我正倾心于教育教学改革,在教改上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了一些思考,于是立即转舵,改写论文和随笔,期望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那篇发在《中国青年报》上引起很大反响的文章,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炉的。由于我经常发表教改文章,包括谈高考改革问题的论文,后来又招来不少省市媒体记者的采访。有关我的一些作品或采访文章曾被各大网站疯转。不过这时候,我们的校长已经司空见惯了,不再有什么激烈反应。
当然,闲暇之余我也涉足一些其他体裁的写作,比如纪实文学。有一天收到一笔2000元的稿费,我以为是杂志社搞错了,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是真的,因为作品在读者评刊中获头奖。这让我心下窃喜。不过,这是我仅有的一笔“高收入”,更多的是“毛毛雨”,时常遭有些人的冷遇甚至嘲笑。有一次我握好几张稿费单去邮局,偶遇一个老熟人,他是办公司的,刚从邮局取了一皮包红彤彤百元大钞;翻翻我的稿费单,最低的就20元,最高的也不过100元——这些都是学术性很强的专业刊物发的,稿费当然很低。他无限感慨地说:“这要牺牲多少脑细胞,就给这点钱?不值得!这么吧,我用一张换你一张!”我立即就有一种屈辱感,毫不客气地反击说:“道不同不相与谋。我才不稀罕你的呢!你以为你那一张,就比我这一张值钱?”在别人眼里,也许认为我这是一种阿Q精神,但我觉得当时回答得特别痛快,特别豪壮!
还有一次,我们县忽然下发通知,要求在各行各业评选“学科带头人”,并以奖励。我本认为这是当局难得做的一项英明举措。所以,学校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和出色成绩,推举我参评,我欣然接受。我根据要求,在家认真挑选最有代表性的教研成果和证明材料,整整装了一大书包。可是没想到,送到有关方面之后就杳无音讯;直到几个月后才有消息:我名落孙山,而一个个工作平平、成果全无的人却榜上有名!据一个掌握内情的人告诉我,这都是暗箱操作的结果,事先打电话递条子的不知多少!更让我气愤的是,他们把我用心血凝成的一篇篇发表的教研论文当成垃圾,丢进废纸篓准备处理,多亏我赶得快才免遭一劫。从此,我对各种“评选”嗤之以鼻!
尽管如此,也没有改变我对写作的追求。长期以来,我一如既往,依然故我,乐此不疲,而且一往情深;或论述或随笔或文学,兴趣所至,必诉诸笔端。写作,不仅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精神生活的重要寄托。虽然也扛着省市作协的招牌,但我更以“校园作家”自居。我总觉得,写作与教学是能够兼容并顾的,而且还会相得益彰。我常常把我的写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并且不厌其烦地辅导学生写作。多年来,经过我的手已经有几百篇学生作品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我还主导创办了校园文学社团,定期出版《萌生》杂志。所以,我早已把写作与教书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有时我把得意之作拿到班上跟学生“共赏”时,看到学生那种近乎虔诚的眼神,既让我充满自豪感,又相信会给学生带来许多启蒙和教益。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
编辑:朝卿
责任编辑:周建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