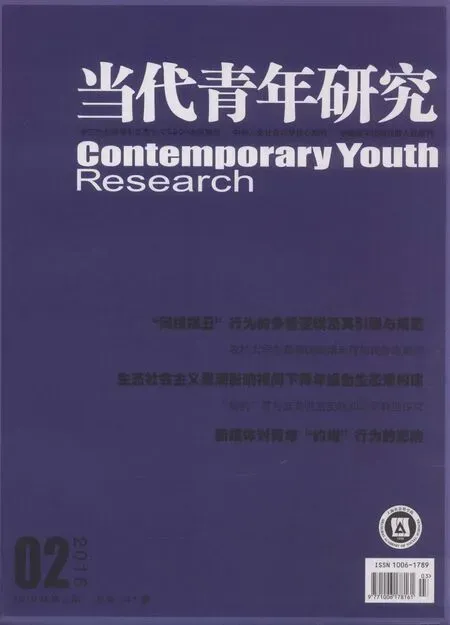当“超我”成为“上帝”
——农村大学生基督徒皈依历程的民族志研究
2016-03-19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程 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当“超我”成为“上帝”
——农村大学生基督徒皈依历程的民族志研究
程 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以往对大学生基督徒的研究多关注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因,缺乏对农村大学生基督徒的专门研究,也缺少对皈依历程中内在心理机制的探索。通过对农村大学生为主体的“约瑟”团契和“天使”教会进行的参与观察和后续访谈发现,“祷告”仪式对信仰的发生及维系起着关键作用。皈依即是人格结构中的“超我”逐步转变为上帝的过程。同时,基督教信仰中的平等、关爱等理念对农村大学生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帮助他们在大学场域之外融入有相似经济社会地位的同辈群体,免于由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匮乏而面临的社会排斥。通过教会,他们融入了一种联合生活,获得了归属感、秩序感和安全感。
农村大学生基督徒;参与观察;祷告;超我
一、研究背景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国内外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据中外学界都比较认可的数据,目前,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7%-2.9%。”[1]但事实上的基督教信徒人数很可能超过这一数字。于建嵘认为,“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人左右”。[2]不管实际的人数如何,几千万中国人选择了信仰基督教,这一事实令人深思。中国人长期游离在一神教之外,有自己的儒家哲学和功利主义的多神崇拜倾向,“是实利取向的而不是虔敬的,是入世的而不是超验的”,[3]是追求“和谐实用”[4]的。可以说,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基督教的要义是不太能相容的。偶然机会参与了一个以农村大学生为主体的团契之后,笔者惊奇地发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经历多年无神论思想浸染的年轻人居然最终也选择了符合西方文化脉络的基督教,虔诚地委身于上帝。笔者本人也出身于农村,与这些虔诚的基督徒在同一个时空下成长,经历了共同的时代变迁,也有许多共通的记忆,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最终在最为关键的信仰层面上发生了重大差异,这让笔者从内心感到讶异。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意义世界有着不同的模板,其中根本性的不同是上帝在心中的位置和意义。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汀(Aurelius Augustinus)主张“因信称义”,但对于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称义”之后才可有信的可能。那么农村大学生基督徒是如何将上帝植根于内心的?他们精神世界转变的心理机制和社会结构动因究竟是什么?
二、对已有研究视角的反思
对于人们为什么会委身于神这一问题,神学界与科学界有着历久弥新的争论。神学家奥古斯汀(Aurelius Augustinus)主张“因信称义”,德尔图良(Tertullianus)则提出了“因为荒谬,我才相信”的观察。神学家认为宗教高于理性,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则无法认同。涂尔干(Emile Durkheim)坚持把社会看作是宗教的起源,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认为上帝或神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的无助感,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认为宗教能够给人一种“大海般的永恒感”。[5]但这些断言并没有从微观层面揭示出委身于神的内在心理机制。
在这些解释之中,弗洛伊德的解释很有趣,他认为基督教“起源于人的无助感”。那么农村大学生选择基督教信仰的原因真的由于“无助”吗?这种解释虽然契合人们对农村大学生经济资本匮乏这一事实的想象,但经济资本的匮乏并不一定带来“无助感”。而且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可以推论越是无助和弱势的大学生越是容易加入基督教。左鹏通过对北京某教堂大学生基督徒的调查发现,“大学生基督徒在总体上并无弱势者的特征”[6],这一结论的来源是调查问卷表明大学生基督徒“生源地、月均生活费用及学习成绩”几项与大学生总体水平并无太大差异。这一结论虽一定程度上推翻了农村大学生是弱势者的刻板印象,但弱势与强势之分依赖于情境,弱势的生存现状未必带来精神上的弱势,学习上的弱势也并不就因此而成为弱势者。因而仅仅由这样几项数据而否认农村大学生在特定情境中的弱势地位又显得证据不足。究竟社会结构性因素,如原生家庭、阶层、性别等因素,对大学生信徒,特别是农村大学生信徒在皈依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亟待解答。苏杭通过参与观察近一年的大学生聚会,比较完整地展现出北京市一个大学生聚会点的常规活动和组织运行情况。他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7]但问题在于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有诸多实现路径,为什么大学生们选择了委身于上帝?这一问题在文章中并没有得到有效解释。
王晨丽对青年教会进行了实地研究,她强调了范丽珠曾经提出的观点:“实践中的中国宗教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发展轨迹,有些特征是西方宗教理论从根本上就忽视的,比如中国人对于信仰不强调形式上的宗教皈依。”[8]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青年家庭教会作为一种弱组织形式所具有的成员构成的同质性、组织活动的灵活性、对个体成员的关注性、成员关系的亲密性等一系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迎合了当前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个体宗教性建构的去制度化趋势和中国人宗教信仰私人化的惯习”[9]。她强调的中国人宗教信仰私人化的惯习,实质是符合中国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脉络。华桦在对上海8所高校25名大学生的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认为,“大学生信仰基督教是在遭遇危机、认知探索和人际网络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10],这种观点虽然比较有效地解释了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外在影响因素,但没有从微观的个体心理维度揭示大学生信仰转变的精神建构过程。
综上,以往的对大学生基督徒的研究多关注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因,缺乏对农村大学生基督徒的专门研究,也缺少对皈依背后的内在心理机制的探索。
三、研究田野与方法
在于建嵘教授的研究里,淮河流域是一个基督教教会非常活跃的地区,而笔者的家乡正是在淮河流域。寒假期间,在家乡一个农村教会的介绍下笔者参加了一个由安徽各地的农村大学生为主体的“约瑟”①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此处“约瑟”以一个讲道人自称的名字命名。团契②所谓团契,是基督教新教的名词。相应的英文为Fellowship,指教徒之间的团结和契合。团契的称谓源于拉丁词汇的koinonia,指的是有着“同一的心、共同的灵”。在这个层面上,团契就是指一群“在生活态度上彼此认同、相互激励的精神团体”。而实际上,团契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团体,还是一种实体的组织。教会常见的有“妇女团契”“青年团契”等。,接触了较高学历①约瑟团契中的大部分信徒学历都在大专及以上,也有个别的研究生。的大学生信徒,进行了为期5天的参与观察。约瑟团契中总共有近50名大学生,女生近40名。参与团契的基本上都是在读的农村大学生,也有个别已经工作。在“约瑟”团契里,除了笔者和另外一人以外基本上都是信徒。在回归校园之后,经由一个老乡介绍我以“慕道友”的身份参加了北京一个以两所重点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天使”(化名)家庭教会。教会的信徒有70多人,每次主日活动都有30多人参加,其中女大学生有20多人。笔者参与观察了他们日常的主日敬拜、布道以及日常通过微信的网络互动,与他们聊天、吃饭、一起做活动。每次参与活动笔者都会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进行或长或短的非正式访谈。在研究后期,积累了大量参与观察手记和访谈资料后,开始有意识地将农村大学生信徒精神世界转变相关的体验串联起来,连接理论资源进行可能的解释。
四、对农村大学生团契的民族志纪实
(一)团契氛围
到达团契之后很快开始了晚饭。先是饭前祷告,之后大家都互相帮忙盛饭和夹菜,互相关爱的气氛会让人很受感染。虽然笔者不是信徒,但在一个基督徒群体中生活还是与世俗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弟兄”“姊妹”的叫法无形中就缩短了大家之间的距离。同时,帮助他人已经是群体的风气,生活在里面会让人觉得温暖和安全。
这个团契已经举办了10次,每年2次,也就是5年了,所以大家都比较熟,三五成群地在交谈。起初我和其他人都不熟,所以就静静地在一旁观察。房间里总共有50多人,男女各占一半左右,都很年轻,基本上都是在读的大学生,也有个别已经工作。他们聊天的内容与现代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并无太大区别,很少有人直接谈到信仰。有意思的是我听到信徒Y-1②为保护被访者隐私,对文中出现的信徒按以下方式编码。其中“约瑟”团契的信徒编码为Y+序号,“天使”教会的信徒编码为T+序号。在说到他喜欢的一个女孩时,自己会经常向主祷告,希望“让那个姊妹了解他的心”,这时我才感受到这是一群有信仰的年轻人。团契是一个加固信仰的组织活动形式,所以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比较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者。后来了解到,只有Y-3不是信徒,但已经来参加过几次。他的理由是自己喜欢和基督徒在一起,并非是上帝,而是信仰上帝的人吸引他来到这里。晚上20多人共在一个大盆里洗脚,一起在不到30平方米的房间打地铺,自然也就使得每个人心理上距离都靠近了不少。
(二)祷告
因为非信徒的身份,先前几乎没有参加过基督教相关的活动,所以不管是祷告还是唱圣歌,都得滥竽充数。特别是祷告,无论是饭前、课前、课后抑或是课间都要祷告好多次。这让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笔者很尴尬。当一屋子的人都在很大声很虔诚地祷告的时候,笔者只能闭上眼睛听着。开始这让笔者有种异类的不安全感,后来也就适应了。但在第二天的一次祷告中,当地家庭教会的一位负责人带领大家祷告,提出在场的要把一生献给主的就站起来祷告,接下来,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站立起来虔诚祷告。只有笔者还是坐着,那时的感觉真是如坐针毡。没有任何人说什么,但那种环境给予的压迫感让人窒息。
(三)传道人
在每天的“讲课”中,带领祷告和唱圣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几乎每天都会很多次的祷告和唱圣歌。下面抄录一首歌词,以便让读者有直观的了解。歌词是这样的:“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心中。夜里有时会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这段歌词朗朗上口,即使不是在这种场合唱也并无不妥,而且内容并不是强调上帝,而是强调了信徒之间的感情。祷告极为频繁,内容各人各异。一般程序是先怀念主为信徒牺牲自己的恩德,再开始说自己的祈求,之后再是对自己的过错向主忏悔,最后是会以“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作为结尾。
讲道人所讲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约瑟这个人物;不受时空限制的爱;时代与人才。这三部分分别由三位传道人讲授。第一位传道人自称为“约瑟”,告诉大家以后就这么称呼他。也正是“约瑟”带领我们做了不少小组游戏,在很大程度上让整个团契气氛融洽了许多。他主要从《圣经》记载的关于约瑟的故事出发去教导大家要向约瑟学习,抵御自己心中的欲望,做一个合格的基督选民。而另一位女传道人主要从耶稣被定十字架来讲述耶稣对人类的爱,同时教导大家要怎么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运行的团契。主要原则就是要活在基督里,同心合意地敬拜神,不结党,谦卑,关心他人,以耶稣为榜样谦卑地在团契中生活。第三位传道人主要讲述了时代和人才,渲染了这个时代的罪恶,在这个任意而行的时代基督徒要活在神面前,以传福音为荣耀。
(四)离别前的聚会
很快,5天的团契即将结束。最后一天晚上包括负责为我们做饭的三位中年女信徒都一同来到了我们平时讲课的地方。这是最后的聚会,很多人都发了言,表达了自己在这次团契中的感受。其中有位城市来的信徒提到刚来的时候看到房间这么拥挤,厕所还是破旧的旱厕,都快被吓坏了。之后一个阿姨被大家请出来讲话,她一直在推脱自己讲不好,但后来还是被怂恿着站起来讲了一些。她说:“你们来这儿我很高兴,见到这么多大学生都为主的荣耀团结在一起,我很感动。刚刚听那位大学生讲这儿的厕所他都不敢进,我确实很惭愧,我们没有做好接待工作,让大家受委屈了。我们几个年纪大的也没什么知识,讲不好也做不好,只能来服侍你们,把荣耀主的重任放在你们身上了。但我们没服侍好你们,让你们受屈了。”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接着很多人都哭了。我当时也被这种信仰生发出来的感情所触动。
虽然只是短短的5天,但这次团契的经历让我有机会以“在场”的方式体验和理解基督教信仰者的生活。关于农村大学生皈依的社会结构动因、基督徒独特的意义世界、祷告在家庭教会仪轨体系中的重要意义等都逐渐浮现在脑海中。
五、皈依的社会结构动因
农村大学生基督徒精神世界的转变不是在想象中完成的,而是在特定情境通过特定的生活实践而逐步发生的。教会和团契是皈依发生的重要场所。在前面所描述的团契中,参与人群以农村大学生为主,地点也在农村,因而宗教与阶层之间的隐秘关系就被遮蔽了。但在后面“天使”教会信徒的访谈中,阶层的因素开始凸显在皈依历程之中。在“天使”教会的访谈中,一位信徒述说了他的皈依经历:“之前高中只知道学习,每天都好晚睡,宿舍熄灯了还搬桌子到公共厕所里学。考上大学之后以为终于解决了,其实心里过得并不开心。宿舍里有几个家境好的,好烟好酒往这里带,经常叫大家出去聚会,去一次两次还行,次数多了我自己吃不消就没再去。一不参加集体活动,感觉距离就远了,大家也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好,嘴上不说但心里已经不带你玩了。班里也不像高中时候的班级,大家天天一起学什么的,大家很分散,看自己兴趣什么的。我又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特长,交不到知心的朋友,很苦闷。后来一天晚上自己太憋得慌了,就在校园里转,遇到一个女孩子问我看没看过《圣经》,我就回答没看过,她就带我去了教会。我以前听说过,知道是基督教。但自己实在无聊,觉得去去也无妨。去那里发现大家对你很热情,不会因为你的家境什么的歧视你,反而会很关心你。后来才知道其实大家差不多,很少有特别有钱的,即使个别家境不错,也不会炫耀。和他们在一起很舒服,因为大家都诚心信主,关系很平等。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在教会交的……我感觉大学其实在精神上没给我什么,反而是教会让我在精神上不再空虚,每次要来教会之前心情都变好了。”(T-2)
当进入大学之门以后,出身于寒门的农村大学生似乎终于拥有了和城市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同等的人生起点,但进入大学只是农村大学生通过教育的阶梯实现阶层流动的第一步。在一个不再以成绩论英雄的大学之门,虽然农村大学生已经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独立,但钱依然是阻碍他们拓展人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经济的原因使得他们更容易在大学的五彩斑斓中感受到孤单、边缘和游离。同时,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跨入大学之门后的学习成长则不可避免地真正经受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中产阶级文化的洗礼。从人际交往的隐藏法则到穿着打扮、购物与流行文化,处处都需要重新学习。大学的文化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更像是一个“异文化”。跨入大学之门的寒门子弟需要不断面对所在场域的文化与自己原生家庭文化的疏离,在矛盾和冲突之中面对和融入城市中上阶层文化。一旦在融入过程中受挫,很容易心理失衡,陷入迷茫和精神上的苦痛之中。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平等、关爱等理念这时就对于农村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践行这些理念的教会和信徒更是给了农村大学生亲近感和归属感。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成了疏离的沙漠,教会成了自己的精神绿洲。
访谈中,农村大学生信徒们在谈到自己的信主历程时一般会谈到类似于 “家人是信徒”“同学朋友是信徒”“偶遇传教”“对基督教好奇”等原因。这些是吸引他们第一次走进教会的直接原因,但走进教会不等同于信仰发生。信仰的转变与教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教会究竟对一个只是对基督教“好奇”的大学生具有何种意义呢?下面是“天使”教会2位大学后才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信徒的皈依经历。“原先我也是好奇才跟着同学去教会,最开始就跟着唱唱歌,我也不是经常去。后来有一次分享上听到一个美国传教士讲自己的信教经历。有一次他在一个大森林里露营,突然感到很孤独。于是他就坐下来祷告,突然一头很小的麋鹿就从树林里露出头来,于是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不知怎么的,我听到的时候突然就很受感动。从那之后我就变得挺想去教会的。最开始自己其实有时也半信半疑,但即使怀疑的时候也希望能和弟兄姊妹见面,要不然不安心。”(T-5)大学的时候经常感觉很迷茫,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我们宿舍好几个同学都信,我开始也不太信,毕竟上这么多年学了。后来她们每次周日去敬拜的时候我也没什么事情就跟着去了,跟着祷告,看着她们做见证,唱赞美诗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真的是把自己献给了主。我也受到很大的感染,感觉好像主就在眼前一样。(T-7)
这些个人体验的发生是在“听”“观看”和参与教会活动中生成的。这也就意味着神圣性的宗教体验与世俗的社会关系紧密连接,不可分割。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对工人阶级子弟,也就是“家伙们(lads)”的文化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成为‘家伙们’的关键是融进这个圈子。自己不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一个人没法制造乐趣、气氛以及社会身份。”[11]“天使”教会在每次新成员加入时都有一个欢迎仪式,大家会一起唱歌,互相握手,寒暄,说“主喜欢你,祝福你”。每个人都要跟所有人握手并保持微笑,友善地打招呼。天使教会还会在每周日主日活动时玩一次“天使”和“小羊”的游戏。抓到“天使”的人要默默地关心自己的“小羊”一个星期。“小羊”不知道自己的天使是谁,只有到了下一次主日活动时才能够揭晓。而在“约瑟”团契,自称为约瑟的传道人带领大家分组做了一些破冰游戏,比如解开千千结和名字接龙,让大家很快熟悉起来。在团契中,大家每个人都互称对方“姊妹”“弟兄”。团契里还形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每次聚会吃饭时都自觉地互相为附近的人拿筷子、端饭等。
教会作为一个不同于大学校园的非正式组织营造了特殊的文化和氛围,也为每一个进入教会的大学生持续地制造乐趣、气氛和社会身份。在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里,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是否能顺畅地建立,否则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坠落至孤独的泥沼。与其说孤独是对他人的渴望,不如说孤独是对情境、气氛和文化的渴望。家庭教会正是提供了一个群体边界明显、内聚力较强且互动较为亲密的聚会场所,给予了“弟兄”及“姊妹”的同质化身份,营造了一种容易建立亲密关系,缓解青年期孤独的气氛和文化。
教会作为一个较为封闭的人际关系强互动场域,不仅让农村大学生们获得了神圣性的精神支撑,而且给了他们在大学校园里不易获得的友谊和人际支持。比如天使教会的信徒们经常有聚会活动,吃饭、烧烤、唱歌等。在微信群里,当信徒或者慕道友在面临考试、困难、同学或家庭矛盾和困惑时,他们都会在群里分享,互相支持,为对方祷告。
对话1(2015.2.10)
T-3:“这学期一个同学让我英语平时测验帮她作弊,没答应,结果她考了及格分,就没再理我了。”
T-6:你做得对!
T-8:帮她作弊其实是害了她。
由上式可知,在[0,1]区间上,度量ρπ和度量d(a,b)=|a-b|是等价的,因此关于ρπ的Cauchy-列就是关于d的Cauchy-列。d是[0,1]上的通常度量,[0,1]关于d是完备的,因此Cauchy-列{xn}关于d是收敛的。设{xn}关于d收敛到A,由于度量ρπ和度量d(a,b)=|a-b|是等价的,因此{xn}关于ρπ收敛,且收敛到A。
对话2(2014.5.10)
T9:“明天要考GRE,求代祷。”
T-2:“为你祷告,靠着主刚强壮胆一无挂率。”
在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团体中生活,互相关爱的气氛会让人很受感染。在持续的现实和网络互动中,孤独的个体不断与他人建立基于共同信仰的关系网络。起初并不信仰上帝的大学生们也会被教会营造的气氛和文化所吸引,被人和人的关系所牵绊,被自己抵抗孤独的渴望所拉扯。大学生信徒们在教会里寻找伙伴,互相倾诉,解答困惑,相互支持。在“天使”教会,如果某一次教会活动有人没来,大家还会四处打听,打电话询问情况,关心信徒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大学校园里松散的班集体组织反而都不容易在群体内部建立起这样的亲密关系。但如果经常不去教会,繁忙的大学生活中就会很难独自坚持信仰。
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教会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信仰的孵化器和稳定器,是一个抵抗孤独的有力场所。基督教信仰中的平等、关爱等理念对农村籍大学生基督徒有格外的吸引力,帮助他们在大学场域之外融入有相似经济社会地位的同辈群体,免于由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匮乏而面临的社会排斥。通过教会,他们融入了一种联合生活,获得了归属感、秩序感和安全感。
六、“超我”转变为上帝
对于农村大学生皈依基督教的事实当然可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但如果单纯沉浸在这种分析之中我们就始终不能深入个体的心灵,体悟把心奉献给上帝的心理转变过程。
单单是走进教会并不能让一个人真正地相信并选择委身于上帝,如同“约瑟”团契中信徒Y-3显然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精神世界被教会吸引,但却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没有在内心建构出上帝。涂尔干认为,“宗教是人建构起来的一种理想,而膜拜在所有宗教中都占有重要地位”。[12]在天使教会的主日活动以及“约瑟”团契的日常活动中,各种仪式轮番出场,无一不涉及对上帝的膜拜。那么在这些诸如唱福音、做见证、洗礼、布道、祷告等活动中,究竟何种仪式最为关键?
在“天使”教会2015年3月的一次主日活动中,大家都在小声地祷告,介绍笔者去的老乡T-1突然大声地祷告起来,说到自己对父母的恨是多么的不该,说到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多么愧对主赐予他的生命,希望主不要抛弃自己,说着说着就痛哭流涕。其他信徒也受到感染,纷纷大声起来,述说自己对主的忏悔。在场的信徒们都闭着眼睛,似乎人人都在与一个外在于人内心的尽善尽美的上帝进行着神圣性的对话,希望主能够原谅自己,让自己重获新生。
后来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很好奇上午祷告会上他为什么会那样激动,他告诉了我一段自己的故事。“我之前在外地大学那几年过得非常颓废,没什么交际,也没什么人关注我。和父母的关系也特别差,总是没来由地怨恨他们。有一次在亲戚家喝完酒就爆发了,把盘子都摔了。为什么恨他们?他们在我小时候总是吵架,吵个不停,长大了也总感觉对我不是那么喜欢,不像别的父母爱孩子那样爱我。但是我接触主以后,我每天都祷告,无数次地向主诉说曾经的那些恨。慢慢我就原谅了他们,每个人都有罪,他们也是,需要主来解救。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女朋友,手机里、电脑里都存了好多色情的东西,控制不住。特别痛恨自己但又戒不掉。后来信主之后我就还是祷告,每次想放纵自己的时候都求主帮助,慢慢地就不那么依赖那些东西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好了很多。”(T-1)
在T-1的皈依经历中,祷告似乎是不同寻常的一种关键仪式。它是信徒不仅在教会,也是在各种场合都可以自主完成的一种仪式。在信徒那里,祷告不仅是处理自我困惑的一种仪式,而且还是感受到主的存在与力量的一种有力手段。“约瑟”团契中一位男性信徒Y-5曾告诉我自己经历过的一次神奇的祷告。“因为家里一直有人信,但我其实不怎么信。大学时候我非常自卑,从来不太敢在公众场合发言。有一次逼着自己去参加演讲比赛,在讲之前一点都没准备。在台底下的时候,特别紧张。我没有办法就只好向主祷告,求主帮助。祷告之后好像就不那么紧张了,上台之后竟讲得非常流利。之后我就完全信了,上帝就在那里,你祷告他是看得见的。”
无论是在教会日常礼拜活动中还是在大学生团契中,同一时段进行次数最多的活动就是祷告。“天使”教会的牧师告诉我说,“祷告其实就是和上帝对话”。有研究者就认为祷告在实质上是一种交流[13],这里对祷告的理解似乎还是不够深入,究竟在这种对话和交流中,信徒的心理发生着怎样潜移默化的转变呢?这里需要对祷告的形式和步骤进行考察。祷告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形式,饭前和睡前祷告就有所不同,祷告的内容也因人而异。但最常见的包括忏悔祷告和祈求祷告。这两种祷告都包括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赞美主的恩德,其次是表现自己的信心①信心是基督教信徒经常使用的话语,指的是信徒对于上帝的虔诚程度,越有信心就意味着对上帝越虔诚。,最后是希望主帮助自己或他人克服什么困难或忏悔自己犯下的不讨主喜乐的罪并求主帮助自己改变,求主谅解。上面提到的信徒Y-5在面临上台前紧张这一问题时的祷告就是祈求祷告。在组成祷告的三个部分之中,第一部分“赞美主的恩德”通常是固定不变的,第二部分表现自己对主的虔诚也是简单几句话构成,第三部分忏悔或祈求的事情则根据信徒的生活境遇而定。
祷告里最激荡内心的是忏悔祷告。忏悔在基督教里究竟有何意味呢?忏悔首先来源于人的原罪,即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同时,基督教戒律里有许多道德准则,其中的不要妒忌、发怒等几乎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容易触犯的。祷告是与上帝发生联系的方式,越是向上帝忏悔,上帝就越真实地存在信徒心中。通过无数次这样的忏悔祷告,一旦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违背主定下的戒律的罪,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主对自己的谴责,内心极度不安,又会不断重复地祷告。这样一个仪式化的循环就使得上帝越来越真实地存在信徒的内心之中。这一点在和一位信徒Y-10的交谈中也得到印证。进入教会1年多了,她总是觉得自己信心不足。当问到她“那你平时祷告吗?”她说她“不像别人那样会祷告”,“不知道该怎么说”。没有祷告也就没有与上帝的对话,也就无法在内心中分离出具有神圣性和道德性的上帝。
弗洛伊德认为,“对父亲的向往是宗教需要的根基”[14],宗教起源于人类面对外部自然力量和他自身的本能力量时的无能为力。宗教是孩提时代经历的重演,他像依赖父亲一样去依赖上帝。他可以依赖他认为具有超人智慧和力量的父亲而感到安全,通过服从父亲的命令,避免违反他的禁令,从而为他赢得爱和保护。无论是向上帝祈祷还是向上帝忏悔都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像幼时依赖父亲一样依赖上帝。重复性的祷告就是重复性的依赖。
那么在内心建构起上帝的过程就仅仅是通过祷告分离进而依赖上帝的过程吗?或者说这种分离和依赖究竟带来了内心人格结构怎样的变化?在“约瑟”团契和信徒Y-7交谈时他谈到了一次自己的体验。他说有一次他在大街上要往垃圾桶扔一团废纸,结果扔的时候没扔准,纸团掉在了垃圾桶旁边。然后,他见周围没人就走了。可是走着走着,他心中就不断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要回去把纸团捡起来,你这样做是有罪的。于是他又跑回去把纸团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心里马上就很舒畅了。于是,他把内心的这种声音归于上帝的启示,认为主拣选了他,让他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
在基督教教义里,上帝是全知全能、自有永有的存在,能分辨一切善恶,决定一切事物与秩序。上帝在人内心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理论提出的人格结构中的超我部分有某种相通之处。在心理动力学中,本我、自我与超我是人格结构的三大部分。“本我”(完全潜意识)代表欲望,受意识遏抑;“自我”(大部分有意识)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超我”(部分有意识)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在Y-7的这段体验里,这种内心被谴责的心理过程对于世俗的人也是存在的,只是强度不同而已。世俗大众可以归结为道德或良心的谴责,弗洛伊德会解释为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在压制自我和本我。而在基督徒的精神世界里,他就会把这种谴责的来源归结为上帝。
综上所述,如果说教会提供了一个以上帝之名相互关爱、抵抗孤独的人际互动场所,祷告则是信仰发生的秘密武器。通过教会的共同生活和祷告,以《圣经》为主要依据的一系列戒律逐步替代了信徒们心中原有的道德和伦理守则,良心或者良知的判定者由原先人格结构中的超我转变成了上帝。信仰逻辑建立或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约束自我和本我的超我转变为上帝的过程。当超我成为上帝,上帝就真实地存在于信徒心中,却被视为异己的神圣性力量而存在。通过祷告从上帝那里汲取力量其实最终是从人的内心寻找力量,上帝的神圣性也是在人的内心才得以展现。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农村大学生皈依基督教的心理机制即是“超我”转变为上帝的过程。
七、进一步讨论
本文结合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从心理机制和社会结构动因两种路径试图理解当代农村大学生委身于上帝的选择。研究发现,教会满足了农村大学生们抵抗孤独的心理需求,皈依上帝的过程也是人格结构中的“超我”逐步转变为上帝的过程。对这一研究结论的解释力的讨论还可以衍生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农村大学生信仰基督教,融入教会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产生何种影响?第二,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每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都有超我的部分,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上帝植根于内心。那么哪些人更容易把心灵奉献给上帝?有人会把信仰基督的人看作是软弱和逃避现实困境的人,但实质上从这群信仰基督的农村大学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在自己的内心寻找力量,在接纳上帝的过程中也在制造自己的上帝。不管怎样,他们都试图在一个自我迷失的世界关怀自己的精神生活。第三,“超我”转变为上帝的心理机制是否可以适用于其他基督徒群体,抑或是应用于对其他宗教皈依的解释?这是一个更为宏大和需要研究者们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也许不依赖超自然的上帝,更直接地面对和依靠我们自己才更能体现渺小的人作为“能思想的苇草”[15]可能绽放的精神力量。
[1]人民网.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06/c1001-25409597. html.2015.
[2]于建嵘.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EB/OL].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8/12/1696.html.2015.
[3]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教新群体为例[J].社会学研究, 2005(01):21.
[4]李四龙.略论“中国宗教的两个思想基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 5):30.
[5]陆丽青.弗洛伊德的宗教思想[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80.
[6]左鹏.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学生基督教信仰状况调查[J].青年研究, 2004(05):18.
[7]苏杭.北京市大学生基督徒聚会点个案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07:21.
[8]范丽珠.西方宗教理论下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J].南京大学学报, 2009(02):101.
[9]王晨丽.青年家庭教会弱组织形式初探——基于上海某高校圈青年家庭教会的考察[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2010: 4.
[10]华桦.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与路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 2010(11):80.
[11]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秘舒、凌旻华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2013:2.
[12]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中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出版社, 2011: 578.
[13]张亚月.跨入上帝之门:基督教意义系统的建构与重构[D].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2003:6.
[14]西蒙格·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M] .严志军、张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45.
[15]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思想录[M]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157-158.
Abstraacctt:: Previous studies on undergraduate Christian lack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undergraduate Christian and the exploring of their inne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for they were mostly focused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impetus. This study tried to explore why rur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ommitment to god from both sides, which was the inner psychological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mpetus approach. The method here was participant observing in a rural house church fellowship whose members were mainly rural undergraduates. Pra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the Christian belief, which is also the process that transferring superego to god. Meanwhile, the equality and caring idea in Christian belief had great attraction to rur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helped them fit in with peer group where people had sam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instead of social exclusion for the lack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They fit in a kind of united life and feel belonging,sense of order and safety through the involving of house church.
When Superego Becomes God ——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Rural 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Cheng Meng
(Fa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dss:: Rural Undergraduate Christia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Pray;Superego
D432.6
A
1006-1789(2016)02-0030-08
责任编辑 杨毅
2015-12-27
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