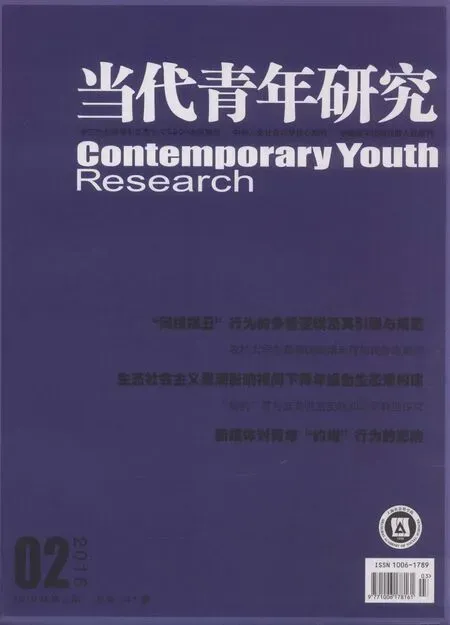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在微信同乡群中自我身份的建构
2016-03-19郭旭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郭旭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生代农民工在微信同乡群中自我身份的建构
郭旭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手机是新生代农民工连接乡土社会与城市身份的一种重要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微信同乡群进行深入访谈的研究发现,在同地熟悉群与异地熟悉群之间没有本质差异,实际上是原先农村社会秩序和农村人身份的网络迁移;而同地不熟悉群的日常交往,则强调城市现代的平等观念,凸显城市里的功利性交往。相对而言,前者容易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抱团意识,后者则可能更容易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微信同乡群;自我身份
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官网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一半左右,而且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增加,但初中文化程度仍然占到2/3左右。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劳动力大军中的主体,并将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较,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1]: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都高于父辈;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城市,基本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验;主要通过大众媒介和通讯技术了解外面世界,成为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他们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处于边缘,在城市中也处于边缘,具有双边缘人的现实处境;他们主观上具有较强的融入城市愿望。牛凤瑞等主编的“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指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8%,2030年将达到70%左右。“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全面进入城市型社会,城镇化也从速度为主转向速度与质量并重的新阶段。[2]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城镇化的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也将会如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城镇化阶段,新生代农民工能否积极融入城市社会就成为发展的关键环节。仅就他们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变迁而言,他们能否成功实现城市融合主要是指他们的城市身份能否实现成功转变。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情况调查显示,手机媒介在他们的城市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通过手机媒介的日常使用考察他们自我身份的建构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本文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微信群的日常使用,探讨对他们自我身份建构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较早探讨媒介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研究,当属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两位研究者将文化身份认同的概念划分为三个阶段:启蒙时期主体、社会学主体和后现代主体。霍尔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身份是在语篇内部而非外部得以建构,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它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及特殊的制度下产生的,而且是在特别特殊的散发形态和实践中产生,靠特别的阐释清晰的策略产生。[4]
美国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在《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中指出,三种社会中存在三类差异化的认同形式:在传统社会中,人的认同性是固定的,既坚实又稳定,不成其为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认同则变得颇为动态、多重化、个人化和具有自我反省的性质,同时还受到变异和革新因素的影响,然而认同仍然是来自一个限定性的角色和规范系列,因此认同性依然是先天的和本质的;在后现代社会中,认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越来越脆弱了,自我组织的个体正在分崩离析,认同性已经成为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观念。他认为,事实上个人的认同性是一种构建,是由个人的生命-情境中的材料所组成,但也与一种需要意志、行动、承诺、智慧和创造性工作有关。凯尔纳认为,在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形塑中,媒体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提供构建认同性的资源和材料。[5]
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从人际传播,如袁靖华在田野调查与抽样调查基础上,从新生代农民工交往意愿、交往行动、交往中的情绪心理效果等方面切入,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人际关系的显著符号因素与媒介因素。[6]洪婧茹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北京地铁建筑劳工的人际传播及其社会关系展开研究,认为他们建立的新的人际关系既非乡土社会式的复制,又不能与城市原有的社会空间接轨,从而产生了秩序上的混乱。[7]另外,从与人际传播相关的方言角度切入探讨方言符号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身份转换中的作用,折射他们在城市中尴尬的生存现状。[8]
也有学者从媒介技术扩散角度,探讨媒介对身份建构的影响,如丁未等学者,他们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手机等新媒介技术,在农民工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介技术的赋权作用,是嵌入在农民工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之中,同时也促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变迁。[9]雷蔚真研究了手机媒介在北京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44位农民工的深度访谈,重点探讨个体对信息传播技术的采纳过程,进而分析农民工个体在城市融合过程中,信息传播技术对其现代性身份形塑的作用。[10]李红艳认为手机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关系密切,手机不仅是一个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农民工利用手机拓展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11]还有学者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消费情况探讨他们的城市身份形塑,如杨嫚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对手机的消费情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手机的消费虽然能给新生代农民工表达自我身份以主动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重塑他们的社会身份。[12]另外,也有学者从QQ聊天群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媒介构建网络社区的过程,认为他们的网络社区主要是基于地缘的同乡关系网络。在QQ同乡群的日常交往中,也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个人与群体的身份建构与认同过程。[13]
从上面的文献可以看出,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际传播和媒介技术赋权等视角:前者重点关注人际传播,忽视传播技术本身的影响;后者侧重于考察新媒介技术赋权,忽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因素,所以得出技术决定论的乐观结果。笔者认为,媒介技术赋权绝非意味着机会均等,即使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也是如此。本文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中持续高频率接触的微信使用入手,考察他们在微信同乡群交往中,如何与他们自我身份进行协商,从而探讨乡土观念与城市处境对他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法。因为研究对象文化水平较低,平均文化程度是初中,为了提高调研数据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深度访谈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深度访谈法是以人为主体,允许受访者通过身体描述和言语解释,来表达其所见所闻所感的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虽然在调查中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但其长于揭示媒介文化对受众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影响,适合探讨在生活世界中受众对媒介文化的体验与意义等微观问题,而得到研究者的广泛使用。此次研究的访谈对象为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考虑到外出打工时间过短,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阅历和经验可能相对更少一些,所以将这个群体外出打工时间最低限定在半年以上。
考虑到农民工居住地分散,随机抽样难以操作,所以本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形式。在访谈一名农民工之后,让其推荐另外两到三名打工者,然后依此类推。在推荐的基础上,研究者也有筛选:选择不同县区的农民工,从而尽可能保证该群体的多样性。同时,鉴于研究的资金问题,本次访谈对象选取45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深度访谈对象:北京25名;长治20名。主要是基于:这访谈对象大多是山西省长治市户籍的打工者,只是有的人在北京打工,有的人则在长治打工,故在两地各选一定的访谈对象。
二、进城后的第一部手机:连接乡土和城市身份
手机是真正日常性的媒介,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仅是打电话的工具。手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仅是一种工具和技术资源,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格罗斯伯格认为,对很多人来说,网络是每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其他媒介或叠加或连接,或干脆替代其他媒介的信息传播。[14]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网络的覆盖,已经使得手机媒介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传播工具。
虽然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手机,比如在他们的中学学习阶段,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访谈中的80后,他们大部分还是进城后才拥有自己的首部手机。访谈对象C7讲道:“2003年9月来的长治,给人送煤球,一天有20-30元,也没什么买卖。后来挣了钱就用600元买了康佳蓝屏手机,主要是为了给家里打电话方便。后来觉得这个手机真是买对了!许多要煤球的都是通过手机联系到我们,生意好多了。”C11讲道:“刚来长治那年,就买了1千多元的摩托罗拉手机,主要是工作方便,与同事打电话,或者与顾客联系。不过还是给家里打电话多一些。”B18讲道:“第一部手机是小灵通,那时已经来了北京,主要是跟家里打电话。那时候我住的是地下室,信号不好,后来就用了天语手机,2006年买的。”C18说:“手机是在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家人给买的,我爸妈在城里打工,联系起来比较方便。”
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手机虽然是他们在城市中联系工作业务,进而开拓崭新社会资源的重要工具,但与家乡亲人保持日常联系,仍然是他们在城市日常生活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基于现实的交往需要而购买手机之外,也有一些人将手机当作城市现代人的身份,作为与人攀比的一种符号象征。C9说:“手机是自己在进城后第三年有的。当时在影楼上班,身边的人都有了手机,自己怕被人瞧不起。其实现在的孩子、大人都有攀比心理。别人家有的,我觉得自己也得有,至少不能被人瞧不起,说咱是村里的什么也买不起。我现在有手机,家里也有电脑。”B18说:“2006年,这个天语手机很先进,1千多元买的,周围人都没有,屏幕大、性能好,感觉特别牛。2009年是诺基亚N81,当时谁都在用,觉得自己不买都不好意思。”C14说:“第一部手机是2006年买的,诺基亚的,1500元,用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呢!当时(这个手机)既先进也拿得出手。同事们都有手机了,自己看他们玩得很好,自己也买了一部,其实那会除了跟家人联系外,基本没有什么其他联系。”
将手机作为现代城市人的基本标准,如C9所言:“在农村生活就要像农村人的生活要求自己,现在来了城市就要按照城里人的标准追求自己的生活,反正就是不能被人瞧不起。”对他们而言,手机不只是它的实用功能,也有它的符号资本或象征价值。从这种心理中,我们也可看出商品消费文化已经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这种消费文化的积极层面看,它建构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现代文化的身份协商与认同。这种身份协商是伴随着他们从农村逐渐适应城市工作与生活的整个过程,其中涉及既有与家乡人之间信息和情感的连接所产生的乡土观念,也包括信息产品中蕴含的现代气息的城市身份。
三、微信同乡群日常交往中的自我身份建构
聊天是新生代农民工日常闲暇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访谈对象表示每天工作之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登录微信。有的人微信和QQ都登录。在这些聊天工具里,几乎所有人都在不同的群,如同乡群(包括同村群、同地群、同省群)、同学群、同事工作群、专业群等,还有非群中的好友。访谈中,他们都对微信同乡群谈得很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同乡群中,有的人还经常发言。笔者以他们的微信同乡群为重点展开分析。与高崇等学者研究的QQ同乡群不同,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北京打工的同乡群,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远不止这么简单。笔者根据两个因素,即同地打工与否、相互熟悉与否,将打工同乡群分为四种类型,即同地熟悉群、异地熟悉群、同地不熟悉群、异地不熟悉群。
分别是:源自一个地方(主要是同一个村或同一个乡镇)并且在同一个城市打工的同地熟人同乡群;源自同一个地方但不在同一个城市打工的异地熟人同乡群。两种外群体群体:在同城打工,但原本不太熟悉,通过中间人认识而加入的混合同乡群(这个群里有的人已经不再是农民工);身处异地同时也互相不太熟悉的同乡群。在访谈中,前三个类型在访谈对象的微信群中都存在,但异地不熟悉类型没有出现。之所以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农民工本身拥有的资源有限,组建异地不熟悉群比较困难;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组建这种群对他们日常生活没有实际作用。就入群而言,同一个人可以加入不同性质的群,不同性质的同乡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交往也存在不同的情形。本部分主要对同城不太熟悉的同乡群外群体交际网络和异地打工的熟人建立的同乡群群体内交际网络的日常交往展开分析。因为这两种类型不但经常被提到,而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
(一)同城不太熟悉者建立的同乡群中的自我身份建构
访谈对象B18谈了她是怎样找见老乡,并加入同乡群以及在同乡群中的交往细节:“我在原来单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对外界什么也不知道。偶尔听到有一个说家乡话的人,觉得北京还能碰见老乡,感到特别的亲切。后来换了单位,又参加过一次老乡会,我认识了很多老乡,大家相互留下联系方式和QQ号码。我们自己组群,那会还是QQ群,后来有了微信,直接加入微信群,QQ就不聊了。现在这个群,每年都有年会。群里人很多,如果有需要一说话,肯定有人帮忙,我发现对我的工作也有帮助。我现在每周末爬山,如果一个人不想去时,在群里喊几句,就会有人响应。老乡之间一回生二回熟,有家乡情谊在那里,所以容易交往。这个老乡群里的话题,都是正能量的,每天晚上11点准时闭群。这个群目前500人,处于满员状态,如果有一人退群,立马会有人补进来。在这个由微信媒介搭建的空中家园,在一定意义上也延续了传统老乡的情谊,让她能够身处异乡还能感受到一种乡情。然而,这个同乡群并非一种原初乡土情感的网络复现,只是一种近似乡土交往的网络构建。
这个老乡群实际上是一个由外群体人际交往构成的老乡群,在其中不仅只有打工者,还有非打工者,他们只是由于都是山西籍的老乡,所以在城市中抱成团相互帮助,互相利用各自的资源。这种群体外的交际网络,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诸多资源,为社会流动提供可能。访谈中,B18对这个同乡群表示非常满意,经常面带笑容。在这个同乡群中,虽然同样也有群主作为管理中心,但没有中心与边缘的纵向社会网络结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重视个体的个性特征,这是一种扁平的社会交往结构。这种结构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群内资源共享、网络纽带的联结以及线上线下社会行动提供了新的交往平台。总之,笔者认为这个同乡群的日常交往,是将城市中的功利性交往运用到同乡群交往当中。在这个同乡群交往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具有一种乡土和城市身份建构的混合状态。
然而也有另外的情形,山西长治人在北京有另外一个老乡会“潞京会”,其中有很多名人,该会在微信里也建立了老乡群,目前人数也是满员500人。B4与B18、B19就是通过这个同乡会微信群认识的,现在经常线下聚会。与B18谈到的老乡会相比,B4所在的老乡会中有不少是在京的名人,虽然同属长治老乡,但现实社会阶层的差异无法忽视;B18的同乡会则没有这种社会阶层的显著差异。B4谈到:““潞京会”年会,要收大家每人300元,就是吃一次饭(而B18谈到他们的同乡会才花100元),明显就是想通过这个会来赚钱嘛,我就不去了。”
线下的不平等,在微信日常交往中也有反映。如B4经常在群里讲些荤段子,让大家开心,有一些资格较老的人指责B4这种行为,并声称让其退出该群。而B4也予以还击,并在群中获得了一些其他老乡的支持,如B19的声援。目前B4还在群中,但已经不再传播那样的内容。他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彼此熟悉的打工者同乡群。在这个新群里每个人可以畅所欲言,谈论的话题都是大家感兴趣的,B4获得了小团队的精神支持。然而,他在新群里发言时,也更加考虑现实中大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免引起熟人之间的误会。这个熟悉的同乡群,可以说组成了一个新的小集团,它可以增进了彼此认同,凝聚成新的力量。从B4的“叛逆”经历可以再次看出,这种外群体的同乡群交往,突出的是现代交往中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强调的是个体的个性特征。一旦这种城市现代交往的观念被破坏,势必与外群体的交往不欢而散或缄口不言。
通过B18和B4两人在微信同乡群中日常交往实践的比较,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交往中他们更加重视现代平等交往观念,即使是在同乡群体的交往也是如此,这种平等交往的观念不容破坏,否则要么奋起反抗要么改变日常交往的方式。在同城不太熟悉者建立的同乡群中,折射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建构了一种城市平等的交往身份,显示了城市现实生活对他们现代观念的影响。
(二)异地打工的相互熟悉者建立的同乡群中的自我身份建构
在访谈中,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参与同城包括打工者在内的群体外交往群,还另组建了异城熟人的打工者群。他们从一个村庄或同乡走出来,大家并没有在同一个城市里打工,但原本彼此熟悉的关系,借用手机这个媒介,在微信、QQ等社交媒介中得以维持和延续。这个网络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同样非常重要。C7说:“接触网络一开始是QQ,后来主要是微信,现在有100多位好友,都是认识的人。有40个经常联系,是一个村的。除了加入村里的两个群以外,我跟同村的8个同辈的人,也组建了“姐妹群”,这里面有一个是外省打工,一个是村里,经常说话的就是在长治的我们2个人。”B14说:“我们一个地方出来的人,建立了微信老乡群,闲的时候就上来看一看。看看大家在哪里赚钱,有没有好的路子。主要还是了解一下别人发展得怎么样,看看自己与人家的差距。我们这些出来打工的,许多年龄差不多的,有的人已经买上车了,看到这些压力就特别大。攀比也是好事,能让自己发现差距,更加努力工作,但压力太大的话,自己也承受不了,总怕父母在家里抬不起头来。”C6说:“自己加入了老家朋友的群,都是一个村的,群名叫“交天下好友,接受正能量”,群里都是老乡(40多人),另外还有一个群是“抢红包”群。每天一个村的老乡都在这里自娱自乐。我现在许多关于村里的最新信息,都是从这里首先知道的。”B21说:“微信里有70-80个朋友,也有老乡群,叫“南鲍小孩”“南鲍小女”群①当地方言:“孩”专指男孩,“女”则指女孩。,里面都是同龄的人。有在外面打工的,也有在村里的,每天都聊,抢红包。抢红包很开心,尽管没有多少钱。这个群里在外面打工的,还介绍城里的工作机会。我就是从这个群里到现在单位的。”这些内群体的同乡群的人际交往,原来在乡村时大家相互之间就是熟人。这种同乡群其实是复制了原来乡土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说前文中的外群体老乡群是“拟现实社区”,[15]那么这里的老乡群就是现实乡土社会的网络迁移。如C7重建了同村在同辈之间的姐妹情谊;C6从中获知村里的最新变动情况;B14在群里看到同村伙伴比自己发展得更好,产生了攀比和嫉妒心理;B21通过这个熟人网络社群找到了现在的工作,而且男女区分的乡村社会秩序在该群中得以重现。在群体内的网络中,原来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得以重现。B5告诉笔者,他正是因为原来的老乡群里有很多属于同村中的晚辈,称呼他“叔叔”,所以不敢随便乱说话,怕影响了自己在乡土社会中的辈分格局,进而对他产生负面印象,最终他才选择在同辈之间建立了一个新微信群。
由此看来,基于原初大家彼此熟识的内群体同乡群是一种乡土情谊的网络复现,与外群体同乡群交往中强调人人平等的观念不同,它本身不强调平等性,而更重视相互之间的情感维系。正如B9提到:“老乡和城里人交往相比较,更喜欢与前者交往。尽管前者更不容易交往,因为大家不在一个地方打工,而且干的活也不一样,基本上共同语言很少,但这些人以后肯定能用得上。父母都在老家,一旦家里有事,远水解不了近渴,老家的朋友都能相互帮上忙。”尽管这里的交往我们也能看出,也会考虑到交往中的现实功用,但支持这些功用的背后是大家熟识的彼此情谊,所以这种功用与城市中人际交往的功用是有区别的。
四、结论与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城市身份融入中发生了由被动性适应转向半主动性适应和建构型适应。[16]在半主动适应和建构型适应中,他们深受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乡土与城市的矛盾现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是借助于零碎的、从媒体信息流中获取的信息来构建个人神话,并把它转换成我们赖之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资源。”[17]各种传播媒介作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资源,参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建构。
从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手机媒介的使用中具有较强的能动性,然而他们中不同的个体从手机媒介中并非都能获得平等的机会。具体在微信媒介使用中,虽然媒介都为他们重新搭建了同乡交际网络,但主要存在内群体和外群体两种交际网络:前者主要基于传统理性乡土社会中熟人交往的网络迁移;后者主要基于工具理性在城市社会中“同乡身份”的陌生人之间的拟乡土交际网络。两者中凸显的交往观念明显不同:前者突出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后者是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如果说前者侧重于重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身份,那么后者则侧重于彰显他们的城市身份。
总之,在新生代农民工微信中搭建的同地熟悉群与异地熟悉群之间没有本质差异,其折射的是原先农村社会秩序和农村人身份的网络迁移;而同地不熟悉群的日常交往,则强调城市现代的平等观念,凸显城市里的功利性交往。相对而言,前者容易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抱团意识,后者则更容易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自我身份界限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即使在两种交际网络中身份仍然是模糊的,经常混合了农村与城市的复合身份。这种矛盾的身份处境,既有助于他们身份融入城市的一面,也有不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的一面。当他们不想再回到农村然而又融入不了城市时,他们的身份矛盾性,可能会导致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最终可能无法实现顺利融入城市。
[1]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2-7.
[2]蓝皮书:中国城镇化率达54.8% ,2030年将达70%左右[EB/OL]. http://news.163.com/api/15/0929/09/B4M1FNPE00014JB6. html.2015-09-29.
[3]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 2011(02):145-150.
[4] Hall Stuart & Gay Paul Du (edt.).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6: 4-5.
[5]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41-442.
[6]袁靖华.关系障碍:人际传播视角下的边缘身份融入——基于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05):58-72.
[7] 洪婧茹.建筑业流动劳工的社会空间、人际传播与关系重构[J].新闻大学, 2014(01):125-132.
[8]方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J].新闻大学, 2015(2):88-91.
[9]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61-70.
[10]雷蔚真.信息传播技术采纳在北京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探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02):88-98
[11]李红艳.手机:信息交流中社会关系的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 2011(05):60-64.
[12]杨嫚.消费与身份构建:一项关于武汉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06):65-74.
[13][15]高崇、杨伯溆.新生代农民工的同乡社会网络特征分析——基于“SZ人在北京”QQ群组的虚拟民族志研究[J].青年研究, 2013(04):28-39.
[14]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M].祁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6]朱力,等. “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04):4-10. [17]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31.
Abstrraacctt:: Using“ depth interview” method, this paper wants to explore how WeChat group to construct self identity in daily life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Mobile is an important media linking rural social and urban identity for the group.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WeChat groups, and the paper focuses on two categories. It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remote WeChat groups, and in fact, it reflects the identity of rural people and the original rural network migrating to network; but that not familiar WeChat groups emphasize the modern city of equality ideas, and highlight the city’s utilitarian nature. In contrast, the former promotes Baotuan aware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he latter is more likely to promot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WeChat Groupp
Guo Xuku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ds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WeChat Groups; Self-identity
G206.2
A
1006-1789(2016)02-0024-06
责任编辑 曾燕波
2016-01-25
郭旭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