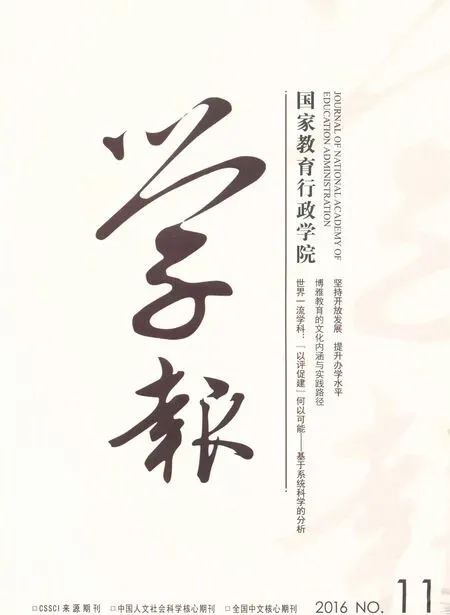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与路径
2016-03-19程孝良
程孝良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 611756)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与路径
程孝良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 611756)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具有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实力,是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力量。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应立足自身的现实基础和可能条件,借鉴美国一流大学特色发展、集群发展、均衡发展、协同发展的学科发展模式与经验,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以中国特色为统领,坚持内涵发展,强化“四大建设”,即以队伍建设为重点、本科教育为根本、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一流大学文化为灵魂;实施“三项改革”,即学科管理模式、资源配置、评价体系改革,破除功利的竞争与排名意识,努力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特色发展;科技创新能力
学科建设是高校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的龙头和先导,是其办学特色和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建成一流学科是创建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当前,我国正着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若干所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已经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学科冲击的实力。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与路径应如何抉择?全面考察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特征,深入剖析和透视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学科建设的模式和理路,不仅有利于解读世界一流学科形成与发展机理,也可以为我国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提供可资借鉴的启迪。历史与现实地看,不同的世界一流大学有着各具特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方略,但彼此也具有共同的基本理路,即学科建设坚持内涵发展、特色取胜、集群发展、协同发展等。
一、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必要性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是指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前以与行业联系紧密的学科为特色、隶属于国务院某个部委的单科性高校,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与发展,这类高校发展为具有显著行业办学特点、学科特色突出、适度综合的高校。为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分类推进”,既支持建设综合性大学,也支持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大学。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与高校获得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既要保证若干所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还要使一批优势学科能首先达到“世界一流”,就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就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
特色学科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形成的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秀的学科,是大学特色的标志。特色学科的形成源于某学科知识体系中的知识的创新和知识的重新组合,源于某学科中科研课题所取得的新突破和新进展,处于“人无我有”的态势。一个新发现或一项新发明或一种新理论的提出以及一种科技的新应用,往往使某学科独具特色。当今世界,特色已成为一种发展理念和战略思维为大学所接受。任何大学,包括是世界一流大学都不可以拒绝走特色发展之路,放弃培育和打造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品牌。世界一流大学除了整体学科水平高之外,一般都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如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古典文学,剑桥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哈佛大学的商业管理、政治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电子工程、植物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语言学、物理、生物等。因此,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是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力量。
(二)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现实基础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在原服务的行业领域具有突出的优势,拥有一批重点和前沿学科,引领相关学科的方向,体现出鲜明的行业特色。在长期为行业部门培养人才和科学技术研究的过程中,行业特色高校面向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行业特点设置应用性学科专业,形成了与该行业有关的较为集中的特色学科体系。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业特色高校的核心竞争力。[1]如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以电子、信息学科为特色,西南交通大学(原唐山铁道学院)以轨道交通为特色,西南财经大学以经济、金融为特色,成都理工大学(原成都地质学院)以地质、石油、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为特色。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和积淀,行业特色高校的这些传统学科都确立了在国内高校相应学科专业中的优势地位,并形成了所在高校的特色和优势。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据统计,在39所国家“985工程”院校中,行业特色大学约占1/2;在112所国家“211工程”院校中,近50所学校为行业特色大学。相关数据显示,部分行业特色大学的一批学科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如在第三轮(2012年)全国学科评估中,共有50所高校拥有全国排名第一的学科,其中有35所是行业特色大学,占70%;共有115个全国排名第一的学科(含并列),其中行业特色大学拥有62个,占53.9%。另外,有164所中国内地高校拥有进入ESI前1%的学科,其中行业特色大学有100所;有26所中国内地高校的48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其中包括7所行业特色大学的10个学科。这是我国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瞄准世界一流目标不断努力的结果,也表明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具备争创世界一流学科的坚实基础。
二、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
学科是大学最基本的单位,是凝聚学术力量培养人才、进行知识创新、为社会服务的依托和核心,大学学科建设的核心是学科建设模式的选择和构建。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不同高校的办学历史、学科背景与学科发展理念决定了不同的战略目标,进而造就了多元化的学科建设模式,呈现出异质化的特质,彰显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一)特色发展模式
强化学科建设特色,在学科定位、学科方向的选择与聚焦、建设资源的集中等方面,强调特色和重点,坚持扶优扶强,重点突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2]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曾说,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若干学科是一流的,但是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如哈佛大学偏重基础学科以及主要以人文为基础的应用学科和职业学科,主干学科为法学、教育学、医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麻省理工学院以理工为主,工学居上,工学、理学和建筑为其主干学科;普林斯顿大学偏重理工,以理为主,主干学科除理学和工学外,还有文学、社会科学、公共政策等;普林斯顿大学虽然规模小,学科也不齐全,但却连续八年雄踞《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美国大学排行榜榜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其坚持“小而精”的学科定位与特色发展道路,在纷杂的情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赶时髦,不贪大求全。正如普林斯顿现任校长雪莉·蒂尔曼所说:“小就是美!正因为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情,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都做到了极致。”[3]今天,你也许会因为在普林斯顿找不到在其他一流大学中非常普遍的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而惊奇,然而这正是其学科发展的特色。以创造“硅谷”财富神话而闻名的斯坦福大学只有短短100多年的历史,何以比肩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哈佛、耶鲁?缘于其在学科发展模式上选择了重点突破的特色发展模式。“二战”后的斯坦福大学作为一所私立二流院校,地理位置偏僻,师资流失严重,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极为困难。面对这一困局,时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特曼大胆地提出了“学术顶尖”的构想,决定采取特殊措施,重点发展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学科,经过重点建设,三个学科尤其是物理与电子工程学科成绩斐然。1952年,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标志着斯坦福大学进入一流大学的行列。在电子工程学科领域,特曼依靠出租学校的土地,建立高科技工业园,不仅使该地区成为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集散地(被人们称为“硅谷”),而且还极大地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吸引了人才,为电子工程学教学、科研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科与“硅谷”一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水平大学进行学科建设的一个样板。[4]
(二)集群发展模式
集群发展是指注重学科交叉,在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发展学科群,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大而全”。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指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到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知识虽划分为各种不同的学科,但看似各不相同的学科之间却并非孤立与绝对割裂,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大学学科“由点到线进而由线到面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学科的繁衍能力。数学与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及技术科学在知识的渗透、学科的交叉、门类的杂交中,犹如一张正在编织的大网,走向科学整体”。当今科技发展不仅需要同一门类的学科之间打破壁垒和障碍,进行交流与合作,而且需要不同门类的学科进行跨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呈现集成化的趋势。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间相互渗透,理科与工科、农医等不同门类间相互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相互交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方向,新技术与工艺以及新的理论体系,催生新的学科。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几乎都经历了一个由单科性、多科性甚至综合性的发展过程。闻名世界的私立大学、享有“小联合国”美誉的芝加哥大学选择了与普林斯顿不同的学科发展模式——综合集群发展模式(芝加哥大学囊括了人类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物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神学等等学科专业)。自建校伊始,芝加哥大学始终坚持兼收并蓄,秉承全面发展的理念,朝着哈珀校长的理想目标——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
(三)均衡发展模式
普林斯顿大学在学科建设上既坚持少而精,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科间的均衡发展。学校管理和决策部门从宏观上对各学科的发展进行有效调控与干预,注重学科间、学科与学校整体的联系,使学科间始终保持一种均衡发展的态势。不同于美国其他一流大学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不仅规模较小(在校生规模不过7000余人),学科也不齐全(普林斯顿没有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但这却并不妨碍甚至可能还促进了它的龙头地位。另外,普林斯顿非常注重保持各系科之间的有机联系,从学科专业的设置,研究内容和方向的厘定到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制定,绝不游离于整体之外,巧妙地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保持整体的平衡,维持学科发展的生态。因此,即使是一些特别热门的科研项目,社会需求量大,资金充裕,学校也不允许其无限制地发展。而对那些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发展滞后,较少或基本不能获得外界经费资助的学科专业,学校却进行最大限度的扶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坚持全面发展,各学科齐头并进,其主干学科主要有人文社会科学、工学、理学、管理、法学等,农林、教育等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四)协同发展模式
坚持协同发展模式就是注重强势学科之间相互支撑,互为基础和条件,通过强强联合,形成一个错综复杂互为支撑的学科网络。享誉海外的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被誉为“全球理工科大学之最”。然而MIT始终坚持理工与人文交叉、协同发展。考察MIT的学科建设历史,我们发现MIT并不只有强大的理工科,而且有雄冠天下的经济学科。它不仅拥有享誉世界的工程分院、自然科学分院和管理分院,在宇宙科学、原子科学、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具有独特的领先优势和特色,还通过学科交叉、协同,充分发挥理工科对人文学科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培植与工程、科学直接相关的学科”,形成了“语言学与心理学携手并进,经济学与工业管理学紧密结合,政治学和电子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发展态势,建成了一流的建筑与规划分院、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院。麻省理工学院拥有不容撼动的工学,不仅由于有一个由航空航天工程、材料工程、电气/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工程、核工程、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组成的学科群,还有其他学校不能望其项背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强大支撑。而它之所以拥有雄冠天下的经济学,则得益于它拥有一个由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公共财政学和工业组织组成的学科支撑网。特殊的发展模式,造就了MIT与众不同的人文学科内涵,成就了其人文学科不输于其他学校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正是通过文理交叉、相互渗透,协同发展,才使得MIT的理工类学科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5]
“条条道路通罗马”,学科发展模式本无所谓优劣,所谓优劣只在于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找到与学校自身优势和特色高度契合、恰切协调的学科建设模式与路径,并坚定不移地朝着设定的目标前进,最终形成我国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学科建设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谐共生、各具特色。
三、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主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就是要明确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措施,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路线图及支持保障条件。能否为各行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流的技术与服务、培养一流人才、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是衡量一所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因此,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应立足自身的现实基础和可能条件,坚持内涵发展,强化“师资队伍、本科教育、科技创新能力、一流大学文化”四大建设,实施“管理模式、资源配置、评价体系”三项改革,扎实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一)实施三项改革
1.管理模式改革
学科组织是学科布局的载体,学科发展必须以学科组织为依托。我国大学的学科组织由于受1952年院系调整的影响和改革开放后的自我建构、相互模仿,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院设置过多,院系并存,导致学科壁垒,分割严重。二是院系设置没有层次,不能反映不同性质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是对所有院系统一要求,违背了不同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影响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而且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的盲目攀比、恶性竞争。相比之下,国外一流大学的学院设置不仅数量普遍较少,而且注重学院之间的层次与布局分工,通过相互支撑促进学科发展。
美国大学采用科层组织与矩阵结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为了适应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科技发展趋势,美国一流大学采取了科层组织与矩阵结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一方面继续保持按学科分化要求建立起来的院系科层式学科建制的传统,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另一方面又根据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组织,以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如麻省理工学院,除设有建筑和城市规划分院,工程分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分院,斯隆管理分院,科学分院,怀特卡保健科学、技术与管理分院等6个学院,下属22个学系以外,还设有人工智能实验室、贝特斯直线加速器、生物技术处理工程中心等44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
英国大学坚持小而全的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式。英国大学坚持学校中央架构与独立的学院架构并存,其学科建设注重并强调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发展。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等著名大学的组织架构均实行学院制,但与其他国家大学按学科设置学院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学院坚持小而全,鼓励文理交叉,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并重。独特的学院制体制以及学科的混合为师生提供了跨学科合作研究及与其他部门加强学术联系和合作的机会。如牛津大学生命环境学部不仅包括生物化学、植物科学和动物学及其综合科学,也拥有文科方面的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和环境学等系科,充分体现了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特点。伦敦大学注重打破系科界限,设立综合性的地区研究、发展研究和教育研究等研究中心,同时实施研究生跨学科学习计划。
日本大学创造了学科学术学群、学系制。如筑波大学吸收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针对“讲座制”造成的学科间人事交流缺乏、宗派主义严重、割裂学科发展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等弊端,大胆废除了旧式的“讲座制”,建立起了新的“学群、学系制”,使不同学科领域的教育、研究得以交流与协作。东京大学学科管理先后经历了从“学院学系—研究所—研究中心”模式的嬗变。“学院学系”模式完全打破了老学科的旧框架,对老学科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和重组,进一步拓展了本来就较宽的学科口径。面向工业的“研究所”模式有利于解决综合领域的问题,在学科的划分上体现了学科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发展规律。“研究中心”模式则在“研究所”模式的基础上更加体现出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
2.资源配置改革
学科资源配置是学科建设的“牛鼻子”。在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在工业经济时代,大学逐步走近经济社会而处于边缘;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必将日益走进经济社会中心,“巨型大学”已经成为“知识产业的中心”,成为国家发展的焦点。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要遵循学科建设规律,以成本责任为导向,改革学科资源配置机制,建立与学校发展阶段及发展目标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模式。针对资源配置中较少考虑绩效,缺乏成本意识和责任约束,存在盲目扩张资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现象,制定综合考虑各学科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获取资源能力为基础的学科资源配置评估机制,使各个学科成为成本责任中心,引导学科逐步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责、权、利统一的实体。优化外部资源配置以释放活力。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突出重点发展方向,相对集中配置资源,形成若干学科高地和优势创新团队。优化校内资源配置以增强动力。明确校院两级学科建设责任,扩大学院学科资源自主统筹使用权,充分调动学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评价体系改革
学科评价是学科建设的“指挥棒”和重要手段。当前,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使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由“求全”向“求强”转变。2015年4月以来,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相继对其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教育相关机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或撤裁。学科的正常调整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行为如果演变成一阵风,那么过分的竞争、简单的裁撤则必然破坏大学学科发展的生态。高校这种不约而同的裁撤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反映了我国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在学科建设上的功利化意识与价值逻辑。[6]有趣的是,这些被裁撤的教育机构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由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加之我国高校追求“大而全”的学科建设格局的内在冲动而设置,现在开始打造一流学科,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强势学科,由“求全”转变为“求强”,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哈耶克告诫的那般:“当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学校不要仅仅根据学科排名来考虑学科去留的问题,应该统筹考虑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学科结构,撤销还是要经过论证和民主科学的程序制定决策。”对高校而言,学科评估的目的在于通过评估发现问题,持续改进,以保证学科建设的质量,即通过持续不断的学科评估,监测学科建设的成效和发展水平,为学校提供一把自我审核与比较评价的尺子,同时为社会监督学校办学提供一种参考。[7]如果将学科评估结果与一流学科建设紧密挂钩或简单套用学科评估结果进行资源配置,那么各学科为了争取学科建设资源,必将扭曲学科评估的目的,迎评和被评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非正常现象,学科评估的真正目标将被弃置一边。[8]
(二)强化四大建设
1.建设一流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是学科建设的主体。一流学科必然有一流的教师队伍且结构合理,并形成若干学术团队/共同体,聚焦若干学科方向或学术前沿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学术传承依靠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薪火相传,而不可能通过具体的某一代人来完成。通过学术共同体内的传帮带、老中青形成良好的人才结构与梯队,构建金字塔型的人才队伍是理想的学术共同体模型。塔尖由学科内顶尖的科学家比如院士做学科带头人,同时是学科/平台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中间由若干个研究团队构成,每个研究团队由一名一流的中青年科学家做学术带头人压阵、以若干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和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为骨干组成,每个团队围绕一个研究方向持续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塔基由若干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组成,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特长,分别加入一个固定的研究团队。如此则可在老中青的学术队伍中形成如梅贻琦所描述的,“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其次,要遵循“顶天”、“立地”的原则,确立若干个具体的学科方向。“顶天”,就是要深入到学科的前沿,学科方向的前沿性,决定了学科建设的时效性;“立地”,就是要考虑学科方向建设的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再好的学科方向也没有实际意义。
2.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学科的根本。大学以培养学术造诣高深、道德高尚的人才为宗旨。作为师生共同体,大学的第一功能是人才培养,其他功能则由人才培养延展而来。如果没有对探索真理和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追求,大学就会脱离其本源,更无法成为一流。学科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起始源头。学科是专业发展的基础,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基地。专业的发展离不开学科水平的提高,任何一个专业都有其构成这一专业知识的主干学科作为自己的支撑。专业以学科为依托,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教育也发展到何种程度,人才培养的质量,取决于学科水平。同时,也只有学科的分化和综合达到一定高度,才有相应的高新技术专业的出现。学科的人才培养功能是以课程为依托实现的。学科知识是构成课程的元素,学科为课程源源不断地提供构建材料,课程是按教育学规律对学科知识的传播、改造和拓展,学科要根据课程要求加强学科研究方向。
3.建设一流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流学科的核心。科技创新能力构成学科、大学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按国际通用的评价准则还是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一流学科的科研在本质上是科技创新能力。什么是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其创新成果主要体现为高水平论文和论文的引用;对于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服务于社会的项目,其创新成果主要体现为发明专利和专利的转让、成果的转化应用。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科技开发的生力军和应用研究的重要力量。美国赠地学院运动与范·海斯在1904年提出的“威斯康辛计划”,开辟了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先河。此后社会服务逐渐成为美国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学理念。西方大学的共同理念就是把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这种服务的最终结果是培养高素质的国民,并使这些人才用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同时,也生产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使国家在各个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此外,建设一流科技创新能力,还要建立包容创新的体制和鼓励创新的文化与环境,形成激发每一位教师的学术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创新文化氛围。
4.建设一流的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是一流学科的灵魂,是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学术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精神气质和氛围的总和,是大学思想、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一种过程和氛围。大学文化包括校园建筑、景观设施等呈现的物态文化,教学科研学术思想及对大学精神、校训的认同感体现出的精神文化,管理制度彰显的思想与制度文化,以及师生的人际交往、行为举止等反映的行为文化。对创建一流学科而言,一流的大学文化包括崇真尚实的科学精神、自由独立的民主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等时代内涵。当前我国大学在学科建设中存在着过分功利化的趋向,究其原因,在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下,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消费主义所滋生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迎合了一部分人追求眼前、局部物质利益,快速改善生活水平、一夜暴富的诉求和渴望,从而使一部分人陷入了对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极端崇拜之中,产生了“商品拜物教”。一方面导致了崇尚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念,实用化、功利化西方社会价值观受到一部分人的推崇;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语境和实践中,过去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失去了原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在社会生活快速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无法在短期内给人提供各种社会生活和行为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导致价值信仰危机,使得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崇尚价值理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信仰体系和思想方式面临被日益消解的危险。高校在市场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商业标签中迷失了作为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价值目标,出现了功利化趋向。为此,亟待建设一流的大学文化,找回大学精神,补足现代大学精神上的“钙”。
[1]程孝良.行业特色高校学科发展模式:美国一流大学的启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0-83.
[2]晋浩天.从“大者通吃”走向“特色取胜”[N].光明日报,2016-06-30(10).
[3]陈翠荣,王坤庆.小而精:普林斯顿大学办学特色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4):105-109.
[4]翟亚军,王战军.理念与模式: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解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17-21.
[5]许迈进,杜利平.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发展战略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5,(4):76-77.
[6]钟焦平.学科调整不能急功近利[N].中国教育报,2016-08-11.
[7]杨兴林.“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须预防四大误区[J].现代教育管理,2016,(8):14-19.
[8]韩琨.教育学科遭遇裁撤:功利or理性[N].中国科学报,2016-07-21.
(责任编辑田晓苗)
The Mode and Path for Industry Leader Universities to Build World-class Disciplines
Cheng Xiaoliang
The industry leader universities and high-level specialty universities have the conditions and strength to build world-class disciplines and they should b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is trend.Such universities should draw on their advantages and the environment,learn from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with their domestic peers for a more balanced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at emphasizes the Chinese reality and quality.In this process,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four fundamental dimensions,namely,team building,undergraduate education,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university culture.The universities should conduct reforms in discipline management,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valuation.Also,they need avoid overemphasizing competition and ranking that tend to be too utilitarian.
industry leader universities;world class disciplines;specialized developmen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G649.7
A
1672-4038(2016)11-0069-07
2016-10-05
程孝良,男,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成都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