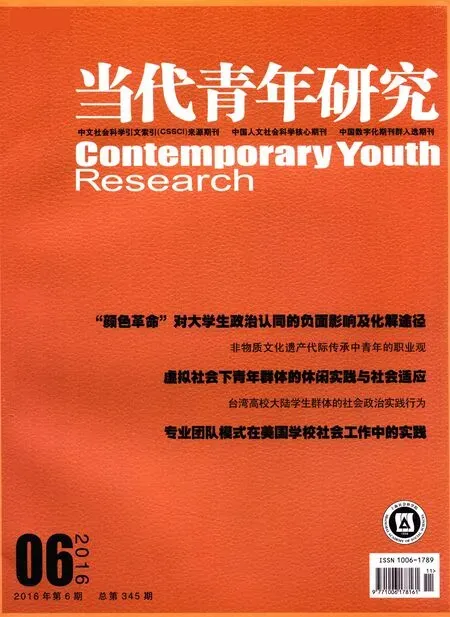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对我国工读教育的启示
2016-03-19石军
石 军
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对我国工读教育的启示
石 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日本问题儿童救助机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883年的“感化院”,经历了“慈善性”的儿童救助、“青少年教护院”到“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的历史发展与变革。历史的积淀形成了当前日本本土的、鲜明的和成熟的教育治理问题儿童的矫治模式——“自立支援”模式,在此基础上,对比中国工读教育的发展情况,得到“五点”启示:儿童本位,制度保障的基本理念;系统立法,给予充分的社会保障;家庭中心:重视归属与爱的需求;多元支持,健全的儿童保障体系;渐进发展,走出别样的制度模式。
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中国工读教育;启示
一、日本问题儿童救助的历史发展与变革
日本问题儿童救助机构历史悠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经历了“感化院”的儿童救助到“青少年教护院”到如今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的历史发展与变革过程。感化院因为相关法律的修改而不断更名,收容未满14周岁的非行少年,1947年,因儿童福利法的制定,少年教护院更名为教护院,1997年,教护院更名为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其内容在教护院的基础上新设了走读的功能,日本问题儿童救助虽然名称经历历史变更,但是感化院时代树立的教育理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
感化院在日本的教育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首先,感化院具有“民间性”。最初的感化院并非是政府倡导的,早在1883年,神道教的神职人员池上雪枝就在大阪开设了一所名为“雪枝”的感化院,开始着手对不良少年的保护和教育,将一些陷入不良状态、没有保护人和监护人的少年少女收留在自家宅院里进行适当的教育,采取了家庭式的收容方式,通过家庭夫妇与孩子们共同生活,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给予孩子们关怀、照顾与指导,开创了日本最初的少年感化院,1885年高赖真卿创立“东京感化院”,从此民间感化事业开始普及。但是,后期由于私立感化院的管理不善,随着专业矫治人员的减少,少年逃跑现象过多,于是日本出台相关法令禁止私立感化院而改为公立,结束了民间办学的历史。[2]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间感化院在日本问题儿童救助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奠基之意义。其次,日本感化院具有“慈善性”的儿童救济的性质,他是作为自由民权论者的民间感化事业家倡导的,倡导对儿童实行“感化”制度,来反对对儿童实行“惩戒”的惩治场制度,惩治场形同监狱,把不良行为的青少年与接收刑法入监的少年在惩治场杂居,容易导致交叉感染,导致行为的恶化,尽管惩治场制度开创了日本少年矫治体系保护主义思想的先河,但当时的少年刑事政策的主体仍然是刑罚主义,惩治主义最多仅仅起到补充作用。[3]为此,建立独立的、适合青少年不良行为的专门教育矫治机构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直到1900年,日本政府借鉴了英美等国家先进的经验,出台了《感化法》,并在全国设置了感化院,至此,感化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体制也被广泛地利用在日本感化事业。公立感化院的诞生,标志着少年保护从慈善性和福利性的民间感化事业领域开始向担负预防不良少年犯罪的国家刑事政策的领域发展。[4]
教护院是日本教育矫正问题青少年的专设机构,其主要负责矫正被家庭裁判所判处保护(限制自由)处分,根据少年法的规定应当在少年教护院中进行教育矫治的人员为不良行为或可能发生不良行为的少年儿童,入院人员根据家庭裁判所的裁定解送。其中主要是盗窃犯,其次是流浪儿童和有蛮横、恫吓行为的少年,主要负责年龄段在14-20岁之间的男性青少年(日本宪法的规定,年满20岁才能成为日本公民)。据研究统计,在被矫正的青少年中盗窃的占45%,违法反取缔兴奋剂犯罪的占35%,校内暴力的占5%,家庭暴力等占3%,被矫正的少年中,80%为第一次入院,20%为第二次或第三次入院。被矫正的少年在教护院矫正的平均时间为1年,入院的少年当中有40%的父母离婚,37%来自单亲家庭,16%跟父亲在一起生活,7%参加过校内暴力团伙,另外有2%的少年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教护院的目标是能够对问题青少年进行教育矫治,使得这些儿童能够主动地适应生活与社会,习得一技之长,做一个守法的社会公民,为此,日本青少年教护院,对入院的儿童实行正常的义务教育,教护院从普通中学聘请一些学科老师,对于应当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青少年,日本教护院也按照普通高中的教育大纲和教材对少年进行学历教育,表现好的学员,在被矫正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取得大学入学考试的资格。在管理方式上,日本很多青少年教护院采取晋级式管理方法,根据每个被矫正少年的具体表现评定矫正的级别,通常被评为1级以上的少年可以获得假释。在日常的教育矫治的过程中,教护院实行小房间制,职员与矫治青少年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对他们进行日常生活的养成指导,职业教育培训训练和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此外,日本教护院每月会组织被矫正的问题青少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在教护院内举办运动会、文艺演出等活动,还会邀请被矫正青少年的父母一起参加孩子的比赛,同时,被矫正少年的亲属每月可以到教护院探视一次,以改善不良的亲子关系,以形成家院教育合力。被矫正的少年从少年教护院退院时,要参加由教护院组织的出院仪式,仪式相对比较正式而庄严,并在父母的面前宣誓:从此以后一定做一个自食其力、为社会服务的合格的社会公民。
儿童自立支援机构是主要针对实行了不良行为或有实行不良行为倾向的儿童和“虞犯”少年进行教育矫治的福利机构,旨在帮助家庭环境恶劣的初中毕业儿童,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确保儿童健康发育、促进儿童利益最大化,维护儿童权益,通过系统的支援,促进儿童向好的方面变化,最终走向自立。儿童自立支援设施针对的主要是是失教的“虞犯”少年,所谓“虞犯”就是对可能涉及犯罪的青少年的某种行为所进行的规定。少年虞犯行为包括经常与有犯罪习性之人交往者,经常出入少年不当进入之场所者,经常逃学逃家者,参加不良组织者,无正当理由携带刀械者,有违警习性或经常于深夜在外游荡者,吸食或施打烟毒以外之麻醉或迷幻物品者。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有58所,其中国立和私立各2所,地方政府50所,市立2所,从数据看,日本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1961年到1987年,全国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的入园率一直维持在50%,自1988年至今,入所率一直保持在40%,所以,从全国范围看,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的收容总体呈现低迷状态,从儿童的入所经历看,59.7%的儿童有过被虐待经历,有根据《少年法》经由家庭决定作为保护处分的有28.7%,有注意欠缺多动症障碍的占7.5%。[5]自立支援设施根据其个性特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接收有不良行为或有这种可能性或家庭环境等原因需要进行生活指导的儿童进入该设施,保护者根据儿童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指导,帮助其实现自立,对退所的儿童实行谈话咨询或者进行其他援助。自立支援设施属于家庭式、开放式或非强制性的教育矫治机构,是主要矫治儿童其不良行为发生的专门机构。
二、自立支援:日本教育治理问题青少年的矫治模式
日本教育矫治问题儿童在多年历史的积淀的基础上,形成了当前鲜明的、本土的、有特色、成熟的教育治理“问题少年”的矫治模式——“自立支援”模式,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如自立援助之家)有公立与民间之分,分布较为广泛。
第一,在办学理念上,强调“共同—共生”的理念,共同成为教育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与儿童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和共同成长,强调集体教育,可以在设施内过集体生活并从事集体劳动。通过有效的监护,强调在教职员与学生之间建立广泛的接触关系、信赖关系和强烈的依恋关系,形成尊重他人、和他人共同成长、获得共生的力量。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没有把孩子作为“惩戒”的对象,而是强调:“儿童应该是被治的、被引导的、被教育的和被爱的对象,强调把儿童作为儿童进行教育的理念,实行民主主义,附加职业教育、家庭教育和基督教教育的教育方针。”[6]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强调教职员给予孩子父母般的爱的“同一性教育”,给予孩子家庭式的温暖氛围,通过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来教育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在自然环境的教育中,形成一种有节律的生活,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给予孩子们日常生活指导、日常学业指导和未来就业指导支援,形成“三位一体”的指导模式,让孩子能够真正从内心接触社会规范,培养规范意识,同时,满足孩子们充分的安全、归属和爱的需求,通过系统的照顾、教育、支援和治疗,最终帮助儿童走向自立的道路。
第二,在办学模式上,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主要采取两种办学形式:第一种办学模式采用“夫妇小舍制”的办学模式,顾名思义,就是作为职员的夫妇入住小舍,与数名虞犯儿童共同生活,虞犯儿童大多数是因为家庭问题导致的问题儿童,所以,希望通过弥补和完善家庭功能来影响和矫治孩子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家庭这样一个小集体生活,创设一种家庭氛围,给予孩子家的温暖。在小舍中,夫妇共同承担儿童的教育和监护任务,但是,单纯地采用“夫妇小舍制”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对教育矫治儿童的力量有限,导致现在采取这种形式的办学模式数量急剧下降,孕育着第二种办学模式的产生。第二种办学模式采用“倒班制”的办学模式,所谓“倒班制”,是指数名职员通过轮班工作,分时分段对虞犯儿童进行指导的办学模式,倒班制按照办学规模的不同,可以分为小舍、中舍和大舍。倒班制有利于改变“夫妇小舍制”人员不足、力量薄弱的弱势,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在教育矫治儿童的指导方针上可以集思广益,发挥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倒班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轮班值班导致儿童与职员之间接触有限,对儿童了解不深,容易导致儿童情绪竞争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立儿童支援设施一般都采用“倒班制”的“大舍”办学模式,学校采用寄宿制,收容数量较多的虞犯儿童,有数量较多的专职人员进行专业化的监护、管理和教育。此外,儿童自立支援设施还要对相关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与儿童商谈所的合作与交流,包括人事交流和联合研修,还强调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与家庭裁判所和警察的合作,交流和互换信息,加强相互理解和共同认识,共同建构合作协助体制与力量,为整个社会的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支援和援助。
第三,儿童自立支援设施面临的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生源不足。虽然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问题青少年案件也在不断增加,儿童问题日益严重,社会上广泛存在各种类型的问题青少年群体,如行为和情绪障碍、拒绝上学、夜不归宿、逃学、甚至社会上儿童虐待现象严重,社会对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的需求量增大,但是,儿童自立自由设施入所的儿童数量减少的倾向依然严重,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儿童自立设施属于福利设施,入所需要征求父母的同意,但是,真正能够得到父母理解和同意并积极配合的为数不多,这是生源减少的主要原因。二是传统的家庭式的小舍夫妇制在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倒班制,倒班制在配置中缺乏有经验的专业职员,在教育手段和矫治模式上还需要亟待提升,难以确保“支援内心具有深刻问题的儿童自立的专业性”。三是《少年法》的修订,将本来属于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管辖的未满14周岁的违法儿童,扩大为少年院处遇的对象,减少了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的生源来源路径。
三、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对中国工读教育的启示
(一)儿童本位:制度保障的基本理念
受欧美教育思潮的影响,日本教育界非常重视儿童,提倡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即使在特殊教育领域,日本的儿童自立支援设施也高度重视“儿童本位”的基本理念,坚持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权益为中心,从儿童的实际出发,为儿童争取利益最大化,着眼于每个特殊儿童健康地、快乐地发展,主要体现在教育矫治的过程,职员要充分考虑儿童的个性特征,使每个儿童都能发展他们的潜能,尊重儿童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摒弃剥夺儿童自我活动的余地,实施强制的、非民主的、充满“规训”色彩、有抽象主义倾向的教育矫治模式。通观日本当今的《儿童福利法》,法律规定对各种残障儿童包括智力的、肢体的、重症身心的、精神情绪的、盲聋哑、行为障碍儿童等,除了提供保护、治疗外,进行日常社会生活指导和授予知识技能则是重心,日本的残障儿童福利已经从“医疗保护对象”的时代进入了“教育对象”的时代。[7]正如日本儿童自立援助设施,儿童福利是要帮助这些行为和情绪障碍的儿童获得生活自立,是要保证这些儿童享有尊严与人格的权利,有正常的社会生活能力,有享受幸福人生的愿景,即便在“虞犯儿童”这样的特殊教育领域,日本“儿童为本位”的基本理念可以在各个层面和多处细节之处体现出来,处处彰显出“以人文本”、以“儿童文本”、以“教育为本”的教育矫治理念。
(二)家庭中心:重视归属与爱的需求
日本和我国一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亚洲国家,重视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力,在儿童福利等多方面体现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特点,这点有别于传统欧美等发达国家以“政府”为主体的福利模式。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发展历史悠久。日本政府把“养育、抚育儿童家庭的支援”和“儿童权利的保障”作为今后日本儿童福利的目标和基本方针。为此,日本政府在教育矫治“问题儿童”的过程中,特别钟情于家庭式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特别重视以“夫妇小舍制”为单位的家庭式办学模式,强调在办学的过程中,给予孩子家的感觉,满足孩子充分的安全、归属和爱的需求,这种家庭式的办学模式在日本教育史上持续时间较长,也是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的最大支柱,在教育矫治问题儿童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建立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支援体系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吸取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训。发达国家的儿童支援体系主要有政府财政支出,国家或政府经济的丧失就是福利的丧失,日本吸收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了“家庭中心”的儿童支援模式,所以日本制定福利政策的出发点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自立,避免让国民对国家的过度依赖。[8]第二,日本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日本学界普遍认为,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最高的学府,重视父母在教育儿童上的义务与责任,同时,日本政府对于家庭、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上发挥重大作用也有着非常高的期待。
(三)系统立法:给予充分的社会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形成和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儿童社会保障制度,日本为了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状况,为了促进儿童的更好发展,基于保护和发展儿童的立场上,系统地加强立法,给予儿童充分的社会福利保障。1945年,日本政府面对战后儿童的救助,日本颁布“战祸孤儿等保护等对策纲领”,依此纲领设置社会局。1946年相继颁布了《生活保护法》和《实施流浪儿童与其他儿童保护等紧急措施》的行政命令;1947年,日本颁布了关于儿童福利的第一部基本法《儿童福利法》。该法规定:“儿童”的定义为20周岁以下的年轻人,规定只要是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9]中央政府厚生省设立“儿童局”。1951年,日本政府又制定“儿童节”和《儿童宪章》。1961年,日本政府实施了《儿童抚养津贴法》,地方政府广泛兴建儿童福利机构,如儿童之家等。1964年,厚生省“儿童局”改为“儿童家庭局”,实行《母子福利法》,设立支持性的儿童商谈法,首开地方区域的儿童咨询、商谈与辅导机构。[10]1970—1971年,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儿童津贴制度》和《儿童津贴法》,进一步完善了儿童的社会保障制度。1997年,日本政府对《儿童福利法》进行了修订,并规定:为有儿童的家庭建立“儿童家庭支援中心”与“儿童咨询所”,在各地区为儿童养育提供多种形式的建议、指导与支持。[11]1998年6月,日本中央社会福利审议会、省社会援助局向公众提出了《有关社会福利基础结构变革》的报告,该报告特别强调不仅仅强调日本的儿童福利主要是对残障儿童、孤儿、单亲儿童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特殊儿童”实行特别支援的政策。[12]还要求为“虞犯”儿童,以及其他一般家庭的儿童的更好发展,创造良好教育环境,给予儿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日本又制定了《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以加强对各类儿童的系统支援。近年来,随着日本社会“虐童”现象的迅速增加,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2000年制定了《儿童虐待防止法》,并于2004年、2007年分别进行了修订。[13]综观上述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对儿童的系统立法,立法多,涉及范围广,并且随时代的变化对法律不断地加以修订,以实现与时俱进,形成了一套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从我国工读教育60年来的发展和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看,工读教育的政策法规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法律,但是,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工读教育的长远发展,这还远远不够,所以,应该吸收日本的经验,加大立法力度,甚至单独立法,明确其特殊性质,引起社会关注,提高社会影响力是非常必要的。[14]
(四)多元支持:健全的儿童保障体系
日本政府建立了多方面参与的社会犯罪预防体系,从政府到民间,从家庭到社区,加强对问题青少年给予有效的监护,给予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第一,在政府层面,日本政府已经采取了综合性的推进措施,如设立预防青少年犯罪日,通过各种调研、活动组织、研究宣传等多方面的手段,健全儿童保障体系。例如,日本文部省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全国性青少年问题的大型调查,如青少年行为与心理问题、校园与家庭暴力、学生逃学与离家出走等主题;法务省每年也组织各种活动如街头游行、张贴海报、辩论比赛、体育比赛、作文比赛、居民集会、座谈会、观看电影等活动方式对青少年问题进行有效的干预。[15]第二,在家庭层面,日本政府重视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为此,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福利体系,在坚持以“家庭”为中心进行教育矫治的同时,也强调与社会的相互协作与支持,以实现教育矫治体系的家庭化和社会化协作。第三,在社区层面,日本政府重视对问题儿童的社区矫治,社区是链接家庭和学校的重要桥梁,在教育矫治中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为此,日本政府在社区成立了“社区儿童养育中心”,并建立了绿色网站“儿童教育网”,社区重视加强与问题学生家长的联系,并对家长的教育提出教育孩子的建议和方法,对家长进行有效指导,以减少家长错误的教养方式对孩子造成的影响。第四,在办学层面上,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采用公私互助,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问题学生的教育矫治,推进社会服务多样化,给全社会的问题儿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总之,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对其问题儿童的多元支持,希望通过建立完整的、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教育矫治问题儿童,以减少青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现象。
中国工读教育经历了初创和起步阶段(1955—1966)、破坏和复办阶段(1966—1982)、调整与改革阶段(1982—1992)和改革与发展阶段(1992—2015)。[17]其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历史原因,全国工读学校一度停办,即便当前的中国工读学校现状也令人堪忧,其形势亦不容乐观, 全国工读学校数量每年以3%-4%的速度下降。同时,工读学校的分布和发展也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重庆等20 多个大中城市,一些省、区尚未建立工读学校,工读学校整体力量薄弱。[18]为此,中国工读教育的发展要坚守工读学校“立足教育,挽救孩子,科学育人,造就人才”的价值取向,借鉴日本儿童自立支援的发展模式,采用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加强历史文化积淀,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变革,加强对中国工读领域的宏观制度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在全社会树立“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尊重和保护儿童的尊严,保障儿童的基本权益的实现;加强对中国工读教育的系统立法,把工读学校的日常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给予儿童和工读教育充分的社会法律保障,使得工读学校各方面适应法制社会的需求,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最终实现中国工读教育的法制化;尝试与社会各部门建立协同共育机制,开放办学,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加强“现实互动”,通过多元的系统支持,健全儿童的保障体系,多角度、多层面地促进中国工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1][5] 鞠青.中国工读教育研究报告[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223-224.
[2] 程捷.日本少年矫治体系的历史嬗变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02):42-47.
[3] 尹 琳.日本少年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4-15.
[4] 重松一义.少年法的思想与发展[M].株式会社信山社,2002:85.
[6] 赤羽忠之.思考虞犯与教育[M].北树出版社,1984:112-113.
[7][10] 龚婷婷.法国、美国和日本儿童福利的发展及其启示[J].教育导刊,2010(03): 88-92.
[8][9][13][16] 王晓燕.日本儿童福利政策的特色与发展变革[J].中国青年研究,2009(02):10-15.
[11] 邹明明.日本的儿童福利制度[J].社会福利,2010(01):53-54.
[12] 陈作章.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及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J].日本研究,2001(02):39-46.
[14] 石军.中国工读教育政策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代意义[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01):64-70.
[15] 罗建河.日本青少年犯罪的防治措施及其启示[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03):61-66.
[17] 石军.中国工读教育政策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代意义[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01):64-70.
[18] 李玉非.工读教育发展问题探讨[J].教育史研究,2009(06):7-10.
The Revelation of Japanese Stand on Its Own Support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on Chinese Reform Education
Shi Jun
(Moral Education Institut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apan’s problem child aid agency has a long history, dating back to 1883 “rehab”, and experienced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harity save the children”, “youth teaching widely” to“stand on its own support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istory has formed the current Japanese bright, mature treatments of the problem of children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l -“autonomy support”.This paper compar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form situation, proposed the “five” revelation: children’s standard, the basic idea of system security; the social security legislation system;family center,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needs of belonging and love;multiple support, improving the children’s security system; and gradual development, out of the different system modes, hoping to provide th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form education.
Japan; Stand on Its Own Support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Chinese Reform Education; Revelation
C913.5
A
1006-1789(2016)06-0117-06
责任编辑 杨 毅
2016-10-0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CSH023;广东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重点课题“中国工读教育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WT041。
石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工读教育、基础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