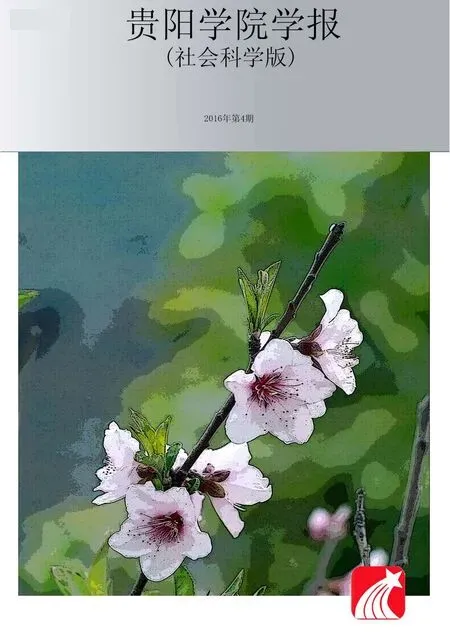汉晋士人个体自觉与生命之累
2016-03-18郑兴中
郑兴中
(肇庆学院 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广东 肇庆 526000)
汉晋士人个体自觉与生命之累
郑兴中
(肇庆学院 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广东 肇庆 526000)
汉晋之际,士人冲破礼教的束缚,个体进一步自觉。与士人个体自觉相同时的,是士人对于生命之累的特殊体验。此种生命之累,表现为生死之累、情累、所遇之累及物累等方面。对于生命之累的体验和面对,是理解汉晋文学、艺术及思想转变的重要视角。
汉晋士人;个体自觉;生命之累
汉晋之际,是士人个体自觉的时代,此种自觉,在余英时的名著《士与中国文化》中有充分的论述。士人个体自觉的表现,如士人之崇尚名节、人物评价、重容貌与谈论、珍视个体之生命与精神等。[1]269-279
士人个体的自觉、对于个体生命的深入体会,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个体对于“生命之累”的关注与重视。所谓生命之累,即是士人个体在独自面对生命之时所遭遇的困惑与烦累。个体愈自觉,其对于“生命之累”的体验也愈深刻。生命之累,并非汉晋之际士人所独有,但却在此时表现得更为突出,从当时留存下来的文献,对此有大量的讨论,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直接与士人个体自觉相关。
笔者根据郭象《庄子注》的论述,将生命之累概括为生死之累、“情”累、“所遇之累”及物累四个方面。生死,是每个自觉士人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情累,则是个体内在生命所时刻体验的;“所遇之累”,也即外在的命运之累;物累,即是应物之累。
一、生死之累
如何面对生死,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对此问题,儒家的基本态度是《论语》中所讲的“未知生焉知死”,将此一问题搁置起来。其实,在传统儒家提倡的宗族的生活方式之中,生死的问题,基本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并非突出的问题。但当士人从礼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享受个人自由的同时,生死的问题却突显出来。
此一问题表现最突出的是反映在诗歌上。汉晋之际留存的诗歌中,有大量对于生命无常易灭的感慨。如汉末的诗歌集《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这首诗是对生命无常最直接的感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短暂,但忧愁却漫长。面对短暂的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纵情娱乐;“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夜以继日地享乐,因为成仙等,不是常人所能够达到的。此种生命苦短,当纵情享乐的思想,也反映在《列子》一书中,其中以《杨朱》一篇最具代表性,张湛注:
“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而复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自枯槁于当年,求余名于后世者,是不达生生之趣也。”[2]192
凡此种种,都是对于生命无常、当及时享乐的感慨。但是,此种娱乐也不能克服生死之累。
又《古诗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该诗的作者游戏宛洛,看到洛中的繁华、王侯的宴乐,不可谓不享尽荣华富贵。但越是如此,作者却越发生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样人生苦短的感慨。即便纵情享受人生,也难逃死亡的“戚戚何所迫”。
汉晋士人对于生死之累的体会,也反映在其对于时间流逝的特殊体会上。正如杨立华老师在《郭象<庄子注>研究》中所述,对于《论语》“子在川上”一句的解释,汉代以前通行的理解是“为对水所象征的勉力进德之象的赞叹”,“将‘子在川上’读解为对流逝的岁月的慨叹,是魏晋士人的新见解”[3]158。这种对于时间流逝的慨叹,根源还在于对于生死问题的忧虑。
二、“情”累
情累是生命之累的一个重要方面。情,包括情感、情欲等方面,最根本的还是个体对于生命、际遇等的主观感受。汉晋之际,随着士人的自觉,其对于情也进一步重视,士人追求“称情而直往”、“任情不羁”,并进一步要求“缘情制礼”[1]371-383。
关于“情”的讨论,在魏晋玄学初期就出现了。圣人有情,“这正是当时个性解放的士大夫生活中的一个中心问题”[3]374。王弼提出“圣人有情”的观点。《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的《王弼传》: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汉魏之际,认为圣人无情,是当时普遍的观点,因为在传统汉儒语境中,性阳情阴、性善情恶。王弼则独出己见,主张圣人有情。其主要论点在于,人具有情和神明两个方面。圣人在情的方面与凡人相同,而在神明方面则超越于凡人。同时,圣人必须是“应物”的,也即接触世间事务、处理世间事务,这主要是从圣人所承担的政治责任讲的。圣人承担政治责任,但不会被这些政治事务所困累,也即“应物而无累于物”。所以,王弼讲圣人有情,主要是从圣人应当承担政治责任角度讲的。王弼认为,圣人有情,但却无累,原因即在于圣人神明的独特智慧。何晏、钟会等人,认为圣人无情,所以无累;而王弼则认为圣人有情,同时也是无累的。两者相同的都是认为圣人无累,不同的是,一则认为圣人无情故无累;一则认为,圣人即情而无累。
自觉的士人对于情累,是有深刻体验的,并进一步认为,有情,是士人区别于普通民众的重要标识。《世说新语·伤逝》: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4]552
圣人忘情,最下层的普通民众则达不到情,而最钟情的,则是士人。由此可知,具备“情”,是当时士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所谓“最下不及情”,原因即在于下层民众并未自觉。
正因为士人所具有的丰富的情感体验,其受情之累也是最深的。这也是郭象所说的“遁天之刑”。郭象注《庄子》“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一句:“感物大深,不止于当,遁天者也。将驰骛于忧乐之境,虽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郭象认为,感物太深,驰骛于忧乐之境,放纵自身的情感,这些都是遁天之刑。
三、所遇之累
“所遇”,即际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命运。人生的命运际遇,充满了不确定性及无可奈何的因素。特别是在汉晋之际,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如何面对命运的累害,是士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于人生的命运际遇,随着士大夫的进一步自觉,相关的讨论也随之而增加。如东汉王充的《论衡》。该书对汉晋思想的影响,如余英时先生所述“汉魏士大夫如蔡邕、王朗之流皆宝秘其书以为谈论之资,而卒得流传,则仲任(王充)思想影响及于汉魏之际之思想变迁者必至为深微”[1]182。我们考察《论衡》一书,便可以理解其原因。该书首篇即是“逢遇第一”“累害第二”“命禄第三”“气寿第四”“幸遇第五”“命义第六”等,其讨论的主题即是个人生命的际遇、累害、寿命等,这也正是当时士人自觉之表现。
王充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人生的际遇之累,如其所讲的人生的三累三害,《论衡·累害第二》:
“何谓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择友,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恚,毁伤其行,二累也。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疏远,疏远怨恨,毁伤其行,三累也。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增加傅致,将昧不明,然纳其言,一害也。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二害也。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於将,三害也。夫未进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5]
此种人生际遇的累害,是即便如孔丘、墨翟那样的圣人也难以避免。对于人生的命运之累,王充将其归结为命运之偶然,与人的贤愚、善恶没有什么关系,是没有原因的,也是无可奈何的。
对于人生际遇之累,《庄子》中有深刻的讨论,郭象对此也有精彩的阐发,如《庄子·德充符》“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一句,郭象解释:
“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为彀中。夫利害相攻,则天下皆羿也。自不遗身忘知、与物同波者,皆游于羿之彀中耳。虽张毅之出,单豹之处,犹未免于中地,则中与不中,唯在命耳。而区区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尔。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而横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6]110
凡是涉及到利害关系,每个人都成为羿那样的射手,每个人都是处在其射程范围之内。被射中与否,完全都是命运,所以,未射中,不必欢喜;射中,也不必忧伤。郭象进一步讲,人生百年之中,“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也即人生的际遇,都不是我能够把握的,都只是自然之理,自然如此的。
四、物累
所谓物累,即“应物”之累,字面意思即是应对外物而产生的烦累。士人要面对、处理外在的事物而产生相应的烦累。其中政治事务之累是最主要的。如《庄子·秋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在庄子看来,政治事务即是一种物累。前文讲到“情累”,王弼主张圣人有情,其重要的理由是,圣人是“应物”的,也即,圣人是承担政治责任的,同时,圣人也是无累的。此一观点,在郭象那里被进一步地强调。郭象注《庄子》“藐姑射之山”一句:
“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绋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6]15
圣王处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即圣人在承担政治责任、处理国家政务的同时,享受心灵的自由。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郭象那样认为外物不足以“缨绋其心”的,如阮孚“避难渡江,元帝以为安车将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7]1364。又阮修,“性简任,不修人事,绝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7]1366。阮孚、阮修,都是晋代的名士,他们的态度,也代表了士人对于世俗事物之累的厌弃。
五、结论
汉晋之际的士人,冲破礼教的束缚,进入自由精神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达到完满的状态,毋宁说是个体精神被完全暴露于生命之累之下。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生命对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如上文所论述的生死之累、情累、命运之累等。汉晋之际士人对生命之累的敏锐体验、对生命之累的正视与面对,促使其在诗歌、音乐、书法、绘画等领域展现出绚烂夺目的光彩。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所以能够展现如此高的艺术境界,也是由当时士人整体情怀所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即是个体生命的自觉及对于生命之累的感慨,正如《兰亭集序》中所述:“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同时,如何面对生命之累,也是我们理解汉晋之际中国学术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视角。为了应对生命之累,士人创造了玄学。玄学与礼教的根本区别,一者为个体信仰,一者为族群信仰。所谓族群信仰,正如徐清祥老师指出的,“信仰者与信仰对象(神)的关系,是以族群(或种族)为单位,而非以个人为单位。具体地说,我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与神发生关系,而是作为族群的一员,以族群的名义与神发生关系”[8]。作为族群信仰的礼教,其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族群的问题,包括种族问题、政治问题;而个体生命的问题,则不在其关注范围内,也无法解决个体生命之累的问题。因此,自觉的士人,由礼教转向玄学与佛学。玄学与佛学,都是个体信仰,以个体生命所要面对的问题为核心,并对士人个体的生命之累提出了自己的解答。
[1]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2]杨伯峻. 列子集释[M].北京: 中华书局, 2012:192.
[3]杨立华. 郭象《庄子注》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4]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5]黄晖. 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 2007:11.
[6]郭象, 成玄英, 曹础基, 等. 庄子注疏[M].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7]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8]徐清祥. 从族群信仰到个体信仰——兼论两晋士族信仰之变迁[J].哲学研究,2005(7).
责任编辑 何志玉
The Individual Awakening and Tiredness for Life of Scholars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ZHENG Xing-zhong
(Institute of Xijiang History and Culture,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00, Guangdong, China )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the scholars broke through the bondage of Confucian and made themselves awakened.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awakening, they simultaneously have a special experience of tiredness for life including the tiredness for death, emotion, destiny, material and so on. Experiencing and facing the tiredness for life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literature, art and thoughts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the scholars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individual awakening; tiredness for life
2016-06-10
郑兴中(1986-),男,浙江建德人,肇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唐佛学。
K23;B222
A
1673-6133(2016)04-01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