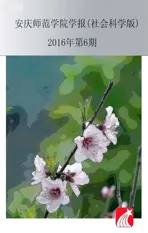王宠惠关于民初宪法体制的构想
2016-03-18李超
李超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王宠惠关于民初宪法体制的构想
李超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在中央政体模式和司法诉讼体制上,王宠惠主张照搬英国传统的内阁制和“一元制”,而在地方制度上却主张承继清末以来的制度遗产,并充分融入古代中国的历史传统,采取一种折中式的改良主义方案。即便该方案违背当时两大政治势力的制宪理论以及自身所属政治立场,他仍明确提出了这一构想,并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王宠惠关于民初宪法体制的构想既存在基于自身政治立场考量的特征,也拥有个人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的痕迹,还包含有针对民初制宪问题比较分析的深刻思考。
王宠惠;民国初年;宪法体制
一
王宠惠(1881—1958)是民国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担任过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和国务总理等职务,也是中国新式大学文凭的首位获得者,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首位中国人,有“民国第一法律家”之美誉,其宪法学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的宪政发展史产生过深远影响,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王宠惠的研究成果已颇丰富,主要有:段彩华《民国第一位法学家:王宠惠传》、余伟雄《王宠惠与近代中国》(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刘宝东《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祝曙光《法官外交家王宠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许章润《乱世中的第一代法学家——〈王宠惠文集〉评析》(氏著《说法活法立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生《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3期)等。此外,肖延丽、孙守明、范小渝、谷传波和王文慧的硕士学位论文也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该王宠惠的宪法学思想。不过从民初制宪之争的时代背景出发,对于其关于民初宪法体制构想之探讨分析仍然鲜见,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1911年4月,身在英国的王宠惠接到清政府电召,要求回国参与宪法修订。9月他回到中国后并未赴京就职,而是加入了同盟会,先在广州担任军政府的司法部长,后到上海担任陈其美的顾问。12月以南方代表伍廷芳参赞的身份,在上海参与了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3月袁世凯政府成立后,则被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6月与蔡元培等同盟会内阁成员一起辞职,改任外交部的顾问,后赴上海担任中华书局英文编辑部的主任。1913年3月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同时开展宪法学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宪法平议》《宪法危言》和《比较宪法》等著作,围绕民初制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宪法当议》中,设计了一套较完整的宪法草案。该草案可看作是其宪法学思想初步形成的一大标志,也是民初制宪理论“百家争鸣”之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宪法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最初刊发在1913年3月的《民立报》上,共上下两篇。上篇“宪法要义”,又分为“绪论”“宪法之性质”“宪法之内容”等9节内容;下篇“宪法草案”,即所谓“王宠惠宪草”,共8章100条。在当时大量涌现的“私拟宪草”之中,不论从内容上还是结构上,该宪草均称得上是相当详细而完整的一份。身为国民党高层的王宠惠,所提出的制宪观点并未完全站在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上,在一些问题上与国民党“官方”的制宪主张存在明显冲突,不仅引起各方舆论哗然,还遭到了国民党派人士的抨击。于是他于同年6月在《民立报》上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答客难》一文,以回应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评。
二
以《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为主要依据,结合《宪法平议》和《宪法危言》等其他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出王宠惠关于民初宪法体制之构想,主要体现为“政体模式”“司法诉讼体制”以及“地方制度”这三大主干部分,具体内容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政体模式上采取内阁制度。他主张设置内阁及内阁总理,负责具体施政,总理人选由国会决定,而其他内阁人选则由总理决定。换言之,内阁的组建权掌握在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手上,采取的是法国那种国会政府主义,行政权实际上受制于立法权。
在该政体模式构想下,行政权由大总统和内阁共同拥有,分别行使。大总统人选必须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35岁,任期4年,可连任1次,主要职权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军事统帅权、人事任免权、赦宥权、戒严权、接见外国特使、大使和公使的权力、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的外交权、公布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提起法案的权力等。
除此以外的行政权,则由内阁负责行使,而且内阁主要对国会的众议院负责,并承担施政成功与否的政治责任,因为内阁的组建和任免受制于众议院。制约的权力还体现为国会的弹劾权,国会采取参众两院制模式,众议院拥有对内阁弹劾案的提起权,参议院拥有相应的审判权。可见,国会对于行政权方面,拥有相当程度的操控力。此外,国会关于立法方面的职权主要有:提议及议决法律案的权力,议决政府预算及决算案的权力,议决公债募集及国库有负担契约的权力,答复政府咨询事件的权力,受理国民请愿书的权力,向政府提意见和质问书的权力等。
第二,司法诉讼体制上采取“一元制”模式。他主张司法权归法院所有,实行薪酬法定和法官职业终身制,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不受外界干预等。当时各政治势力其实已就这些内容达成了共识,但在“一元制”还是“二元制”的诉讼模式问题选择上,各方意见不一。王宠惠是“一元制”模式的坚定提倡者,认为不论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均应归属普通法院管辖,反对设立所谓“平政院”的行政法院制度,甚至他还反对“行政法”这样一门法律单独存在的合理性。“总之,实行民权之国,其人民与官吏于法律上为平等,即应受同一法律之支配,乃宪法上之一原则。而凡反乎此原则者,皆应排斥之……行政法者即官吏于人民于法律上为不平等也,其反乎上宪法之原则孰甚焉。而况以行政上言之,其所谓利弊者,仅利及于一部分之官吏而已。而其弊之多,则普及于国家人民,利弊多少轻重之比较为奚如耶。故吾国不应采取行政法派,可不待再计而决之。”[1]14-15
第三,地方制度上保留省制,采取中央监督下的地方自治制度。王宠惠认为,地方制度的构想只适用于22个行政省,蒙古、西藏和青海等边疆地域的制度另行规定。可以说在民初的制宪之争中,该地方制度构想堪称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格外引人注目。具体而言,该构想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管辖事务的权限范围,包括地方税、省内公债之募集、市政工程、交通事业和卫生事业等完全归地方政府管辖的事务,以及各级学校、公立银行、警察、监狱和外债募集等必须征询中央政府同意或授权的,部分归地方政府管辖的事务。二是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组织运作的模式。他主张地方和中央在政府组织运作上保持“政体模式”的一致性,即均采取内阁制的政体模式。所谓“省议会”,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不仅拥有地方上的立法权,还拥有对所谓“省内阁”的组建权和任免权,如果说中央或国家层面的权力配置模式上,实行“国会至上”原则,那么在地方层面则称得上是“省议会至上”原则。
王宠惠关于地方制度的构想,实际上是兼取“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一种折中方案。“夫绝对主张集权而排斥分权,与夫绝对主张分权而排斥集权者,同为昧于政治之原理均无有是处也……一国之政治,有集权之趋势焉,有分权之趋势焉。此二趋势者,或进步或保守,一张而一弛,一阖而一辟。国家以此而强盛,地方以此而发达,政治以此而进化,人民以此而振兴,是二者亦相需而行,不可须臾离也。是故世界各国,无论何种政体,其实行集权者,必同时而有分权之事。其实行分权者,亦必同时而有集权之事。若夫绝对集权及绝对分权,则断断乎不可。”[1]24他还是“省制入宪”的倡导者:“吾国各省,于政治上有莫大之关系,规定于宪法,即所以使之处乎巩固之地位,若仅以法律规定之,恐吾国政党主张不同,此党胜则存省制,彼党胜则废省制,一起一仆,而各省乃时时变动而不已,则非但不能谋地方之发达,且不能保国家之巩固,此省制之所以宜规定于宪法也。”[1]25-26
三
王宠惠发表《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等文的1913年春夏之际,正值民初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制宪权及宪法问题开展激烈角逐之时。民初这场制宪之争,大致可分为两大战场:一个是在国会官方制宪过程中产生的争论,另一个则是围绕制宪问题的各种理论与主张在社会舆论上之碰撞,而其中的显著表现,堪称当时大量涌现的“私拟宪草”,仅《宪法新闻》这份专门刊物所刊载的“私拟宪草”,即达15份之多。
1913年的“私拟宪草”是民初制宪理论潮流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外知识精英对民初宪法体制构想的一个缩影。尽管这些作者们提出的观点与主张,在政治上的立场及利益等因素的考量下,必然会对各自所属或所支持政治势力的制宪理念有所呼应,但事实上也并未完全一致。这些“私拟宪草”,首先应看作草拟者的个人观点,然后才是草拟者的政治背景;所以不少“私拟宪草”体现的宪法体制构想与作者所属政治势力的制宪理念存在冲突,而“王宠惠宪草”便是一个突出例证。“对私拟宪草者的政治背景乃至政党背景进行考察虽是必要,但实不可将拟宪者标签化,更不宜将他们所起草的宪法草案与他们的政治立场划等号。”[2]对比其他“私拟宪草”,王宠惠关于民初宪法体制的构想大致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在政体模式上,王宠惠的构想几乎照搬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内阁制度,缺乏对内阁制政体的具体内容或形式进行调整。而在其余14份“私拟宪草”之中,虽然除了古德诺和巴鲁这两位外籍宪法顾问主张采取总统制政体,其他12位中外知识精英均不约而同地主张采取内阁制政体,但他们无一不对内阁制政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或改变,根本目的在于使代表行政权的大总统和代表立法权的国会这两大国家权力主体“势均力敌”。可见,当时大多数知识或政治精英们,并非愿意简单照搬美国式或法国式等其他共和宪政国家现有的政体模式,而是“脚踏实地”地将民初国情等现实因素作为制宪考量因素,试图“创造性”地设计一种更合适的政体模式。对于发源自英国的内阁制度这种政体模式,他们的构想均是适度增强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制约,同时适度削弱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王宠惠的构想则是采取“原汁原味”的“国会至上主义”之内阁制政体,这也许与他身为国民党高层的个人政治背景,以及常年留学英美国家、深受英美法系熏陶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在司法诉讼体制上,王宠惠选择英美法系“一元制”的主张在所有“私拟宪草”之中堪称“独树一帜”。前文已述,他不仅明确主张采取“一元制”,而且对行政诉讼及行政法的合理存在持消极反对态度。正如李秀请教授所论:“王宠惠和章士钊反对设立行政法院,实质上是否认行政法的独立存在。这一时期主张实行英美法系体制者的理由与上述两位的主张基本一致,只是其他人大多一方面承认行政法的存在,但同时又结合当时中国国情,认为不应效法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3]也就是说,虽然在民初的制宪之争中,关于司法诉讼体制存在“一元制”还是“二元制”的争论,而当时的“私拟宪草”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边倒”现象,均不同程度地支持“二元制”,但唯独王宠惠坚定地站在“一元制”论者的阵营里,这与国民党的制宪理念也是吻合的,后来出台的“天坛宪草”也是将《临时约法》的“二元制”规定改为了“一元制”。同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以将其主张看作是与他个人身为国民党高层的政治背景,以及常年留学英美国家、深受英美法系熏陶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在地方制度问题上,王宠惠的构想仍与其他绝大多数“私拟宪草”不一样,提倡的是一种兼取“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折衷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不仅与国民党官方的制宪理论存在明显冲突,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政治势力之观点也相差甚远。在当时发表的“私拟宪草”之中,涉及地方制度构想的不足一半,而其中主张保留省制的更少,除了王宠惠之外,便是袁世凯的两位法律顾问——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和英籍顾问毕葛德。可以说,在该问题上,王宠惠、有贺长雄和毕葛德三人的构想拥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尤其是王和有贺的构想,堪称两位中外知识精英关于民初地方制度构想理论上的一次“不谋而合”,均主张在现有省制的基础上开展改革,对地方权限范围内的事务采取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以谋求地方之发达,而在地方政体模式上采取“议会至上”的内阁制度,并遵循古代中国行省之历史传统,采取一种由中央监督下的地方自治制度。
可见,王宠惠在前述中央政体模式和司法诉讼体制上,主张照搬英国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内阁制度和“一元制”,而在地方制度问题上却主张承继清末预备立宪以来的制度遗产,并充分融入古代中国的历史传统及现实条件,采取折中式的改良主义方案,即便这样一种方案明显违背当时两大政治势力的制宪理论以及自身所属政治立场,仍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构想,并对质疑者予以反驳,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综上所述,王宠惠关于民初宪法体制的构想,既存在明显基于自身政治立场考量的特征,也拥有个人教育背景和留学经历的痕迹,还包含有针对民初宪政事业建设的比较分析的深刻思考。他于1913年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宪法平议》和《宪法危言》等著作,是运用近代西方法学理论来审视民初的制宪问题之典型,也成为近代中国宪法学说史的构成部分。张生教授总结道:“作为学者官员,王宠惠为民国政府的法律改革奉献了第一流的比较法知识,竭尽所能地完成了政府的各项法律任务,时人已无可附加;但他以比较法构建法治国的理想在中国大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在比较法学界,其开风气之先的地位是毫无争议的,却因困于西学,更无传世之作。”[4]笔者认为,审视王宠惠针对民初中国所设计的宪法体制构想及所提出的问题,有值得我们重视和挖掘的地方,这也是他作为“民国第一法律家”给后世留下的思想遗产。
[1]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M]//张仁善.王宠惠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夏新华,刘鄂.民初私拟宪草研究[J].中外法学,2007(3).
[3]李秀清.所谓宪政:清末民初立宪理论论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82.
[4]张生.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J].比较法研究,2009(3).
责任编校:徐希军
WANG Chong-hui’s Conce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Chao
(Law School,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In the central regime model and the judicial procedure system,WANG Chong-hui insisted on imitating the British cabinet system and the“unified system”.However,in the design of local systems,he claimed to inherit the political legacy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and advocat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adoption of an eclecticism plan for improvement.Although this plan wa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al theory of the two political powers as well as his own political stand,he still proposed and stuck to his opinion.His conce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based on his consideration of his own political stand and revealed the trace of his personal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including his in-depth analysis of drawing up a constitution then.
WANG Chong-hui;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constitutional system
D921;K258
A
:1003-4730(2016)06-0042-04
时间:2017-1-20 15:3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70120.1533.009.html
2016-01-28
李超,男,福建宁德人,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商学院讲师。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