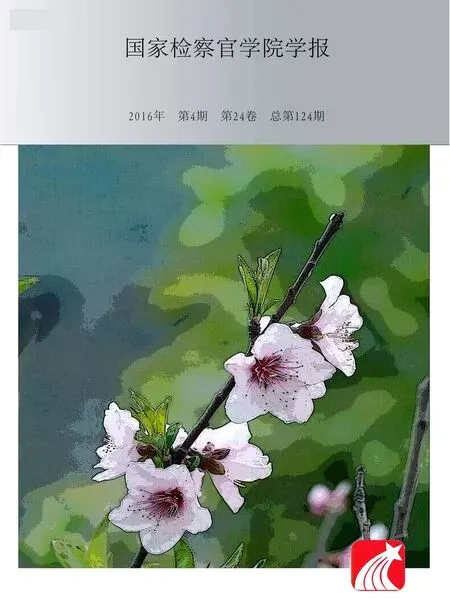日本欺骗侦查所获同意与正当程序
2016-03-17白取祐司
[日]白取祐司 著 倪 润 译
(神奈川大学 大学院 法学研究科,日本;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域外法治
日本欺骗侦查所获同意与正当程序
[日]白取祐司著倪润译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日本;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北京100088)
摘要:侦查人员欺骗侦查不同于“诱惑侦查”之处在于,欺骗侦查并非是国家在制造犯罪,而是侦查人员为了方便侦破犯罪,在证据收集等侦查过程中使用欺骗手段。这些欺骗手段的共同特点是违法程度较轻,但做法欠缺公正性。在强制侦查(处分)和任意侦查(处分)中都存在侦查人员欺骗侦查的情形,欺骗侦查原则上是违法的,但是,这种违法是否直接导致证据排除的后果则至少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欺骗是否导致本来应当实施的合法的强制处分或任意处分未实施,欺骗的性质、程度是否达到了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大程度,因欺骗所受侵害的法益是否重大等。
关键词:正当程序认识错误任意处分强制处分
引言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欺骗受处分人,或者利用其不知情对其实施“任意处分”的例子并不罕见。〔1〕比如,侦查人员隐瞒进行酒精和兴奋剂检查的目的,采用欺骗的手法,获取已有尿意的犯罪嫌疑人的尿液进行尿检。这种侦查方法对人权侵害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比根据强制采尿令状强行插入采尿管的采尿行为要小。尽管如此,这种通过欺骗被处分人达到侦查目的的做法是否违反正当程序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执行“强制处分”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侦查人员以违反《兴奋剂取缔法》的嫌疑为由获得了搜查扣押令状,在搜查犯罪嫌疑人家时,为了防止其销毁证据,侦查人员伪装成了快递人员让其打开了房门。*大阪高判1994年4月20日高刑集第47卷1号第1页以下。大阪高等法院认为,该行为属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11条所规定的为了执行令状所实施的“必要处分”*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在执行查封证或搜查证时,可以开锁、启封以及其他必要的处分。上述处分,对扣押物也可以实施。——译者注。,具有合法性。但问题是,使用欺骗手段让犯罪嫌疑人打开房门真的属于“必要处分”吗?这种侦查方法完全没有问题吗?
很多情况下,侦查机关都会尽可能隐藏侦查目的和方向,隐瞒自己的意图,使被处分人陷入认识错误,从而达成侦查目的。当然,这些做法并非都违法。但是,侦查人员使用欺骗和计谋,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并无异议。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计谋和欺骗的侦查方法又不违法呢?界限和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本文拟讨论的问题是:首先,在侦查过程中,被处分人可能确有同意的意思表示,但因为侦查人员的欺骗和计谋使其意思表示有瑕疵,这样的侦查手段在令状主义下存在问题吗?如果存在问题,问题在哪里?《刑事诉讼法》的什么价值和利益受到了损害?本文拟通过判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具体分析下列4种判例类型:第一,令状执行时使用计谋达成了侦查目的的情形;第二,隐瞒真正的目的让犯罪嫌疑人“任意同行”的情形*“任意同行”是指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的规定,在实施犯罪侦查且有必要时,对未拘留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要求其到场进行调查。被调查人可以拒绝到场,或到场后随时退出。——译者注。;第三,隐瞒兴奋剂或酒精鉴定的目的进行采尿的情形;第四,假装令状已经签发而进行任意侦查的情形。本文拟将讨论的焦点放在被处分人的“意思”和“强制”的关系上。
一、使用计谋以及欺骗的侦查方法的判例
(一)使用计谋执行令状
首先,第一种类型的典型判例为判例一(前述的大阪高判1994年4月20日判决)。基本案情如下:侦查人员以犯罪嫌疑人违反《兴奋剂取缔法》的嫌疑为由获得了搜查扣押令状,为了防止其销毁证据,在搜查犯罪嫌疑人家时侦查人员伪装成快递人员让其打开了房门。此时,本来侦查人员应当在门口告知犯罪嫌疑人自己是警察,然后让其开门。如果被处分人拒绝开门,侦查人员可以采取“必要的处分”——使用万能钥匙,或者破门而入也是被认可的。但是,由于在毒品犯罪中,作为扣押对象的兴奋剂很容易通过水冲就被销毁掉了,故侦查人员使用计谋让犯罪嫌疑人主动打开了房门。
大阪高等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侦查人员伪装成快递人员让犯罪嫌疑人打开房门的行为,虽然使用了有形力,但是并未像把门锁弄坏一样导致房屋所有人和居住者财产上的损害,这是一种和平的、非常稳妥的方法,在方法上并不欠缺社会共识上的相当性。”该案辩护人反驳道:《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的“必要的处分”要求侦查人员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来访的目的和令状已签发的事实再要求其开门,只有对方表示明确拒绝且有隐匿罪证的具体行为时,才能采取“必要的处分”。但是,大阪高等法院并未认同该主张。
此外,该类型的先例还有判例二。*东京高判1983年3月29日和刑月第15卷3号第247页。该案基本案情与判例一类似,侦查人员以犯罪嫌疑人违反《兴奋剂取缔法》的嫌疑为由获得了搜查扣押令状,在搜查犯罪嫌疑人家里的时候,为了顺利地进入其家中,谎称自己是佐藤让犯罪嫌疑人打开了房门。东京高等法院并未将“侦查人员谎称自己是佐藤让犯罪嫌疑人打开了房门”这一点作为一个直接争议点,且在结论上认定了侦查人员的行为合法。
(二)隐瞒目的的任意同行
根据日本《警察职务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侦查人员在进行“职务询问”*“职务询问”是指日本《警察职务法》第2条的规定,警察根据异常的举动以及周围其他情况进行合理判断,对于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可能犯有或将要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可以让其停住并对其进行询问。——译者注。后,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任意同行。问题是,要求其任意同行的时候,侦查人员有必要告知犯罪嫌疑人其所受到的怀疑吗?判例三专门讨论了该问题,结论是“没有必要告知”。*东京高判1986年1月29日和刑月第18卷1-2号第7页。基本案情如下:侦查人员在对违法停车的司机进行职务询问中,发现其有兴奋剂使用或持有的嫌疑,为了弄清该嫌疑,侦查人员告知其任意同行到警察局,理由是要继续调查其违法停车的事情,其间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兴奋剂的问题。东京高等法院认为:“从整个任意同行的过程来看,警察并没有对被处分人施加任何直接的有形力和心理强制,故该任意同行不能被认定为违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警察确实并未如实告知被处分人有关兴奋剂的嫌疑。对此,我们应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分析,当时警察并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可以证明该嫌疑,这仅仅是其主观猜测而已。与此不同,在违法停车这件事情上,被处分人是现行犯,证据确凿,警察以此为由要求被处分人任意同行是可以被认可的。综上分析,认为警察的侦查行为中存在计谋和欺骗的观点不成立。”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通过使犯罪嫌疑人产生误解(认识错误),让其任意同行到警察局的情形。判例四判决该行为违法,但肯定了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最判1986年4月25日刑集第40卷3号第215页。基本案情如下:巡警ABC三人从多名群众处得知犯罪嫌疑人X正在使用兴奋剂,于是着便服到X家,在门口处说道:“我们是某钱庄来收利息的,有问题要问你,可以进来吗?”尽管没有得到犯罪嫌疑人的明确同意,ABC三人还是进了犯罪嫌疑人的住宅。之后,A要求X与他们一起走,X以为他们是来收利息的,同意与其一同前往。ABC三人让X坐进了事先停好的车中,然后出发了。此时,虽然X心里在琢磨这三人有可能是警察,但还是没有反抗。到了警察局1小时以后,X承认了自己在使用兴奋剂,同意采尿。审判中,本案的焦点是:从任意同行到采尿,程序是否具有合法性?日本最高法院认为,“采尿程序之前的一系列程序,诸如巡警ABC三人未得到同意就进入犯罪嫌疑人X家;从X家中出发的任意同行也未得到X的明确同意;没有答应X要离开警察局的要求强行将其留置在了警察局等,存在脱离了任意侦查范围的违法,故后续的采尿程序也应当评价为带有违法性质。但是,巡警ABC三人从进入X家中开始就没有擅自进入的意图,在X任意同行时也没有使用任何有形力,此外,X在途中发现ABC三人可能是警察后也未提出异议仍然跟随其一同前往警察局。综上可见,巡警ABC三人违法的程度不能算是重大,本案中尿液鉴定书的证据能力不应当被否定。”
不难发现,判例四和判例三的区别在于,X在和警察一起上车出发前,对被警察实施任意同行这件事情本身产生了误解(认识错误),没有意识到。此外,在判断任意同行是否具有违法性时,还有判决认为,仅仅告知犯罪嫌疑人到警察局来,却没有告知到警察局是要接受讯问,也是判断任意同行是否具有违法性的一个重要判断因素。*神户地判1968年7月9日下刑集第10卷7号第801页;秋田地决1969年5月14日刑月第2卷9号资料编第13页。
(三)侦查人员在采尿时实施计谋
第三种判例类型涉及酒精检查和兴奋剂检查,其问题在于,对于醉酒驾车嫌疑人或兴奋剂使用嫌疑人,可否隐瞒为了检测其是否摄入酒精或兴奋剂及其摄入量而进行采尿?
判例五是一个肯定判决。*东京高判1973年12月10日判时728号第107页。基本案情如下:犯罪嫌疑人A因为醉酒驾车被作为现行犯拘留,但是A拒绝呼气检查。在警察局呆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6点A告知警察其有尿意,请求警察带其去厕所。警察隐瞒了要对其尿液进行酒精检查的意图,让其使用房内放置的桶。在法庭上,A的辩护人主张对使用上述方法获得的尿液进行鉴定所得的鉴定书属于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东京高等法院认为,“本案中,警察并未违背犯罪嫌疑人A的意志对其强制采尿。而且,警察对有醉酒驾车嫌疑的人实施呼气检查测定酒精浓度,这是警察的职权所在。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应当要按照交通法规对其实施制裁。加之,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2款的规定,侦查人员根据犯罪侦查的必要性,采集人身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脚型等并不需要令状。使用上述方法对犯罪嫌疑人A进行尿检,并没有对其身体造成伤害,没有违法性。”
与判例五不同,类似案情的判例六却是一个否定判决。*东京地判1974年1月17日判时727号第29页。在该案中,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本案的采尿行为从收集过程上来看,首先是采取了让犯罪嫌疑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手段,侵害了其个人尊严和基本人权,也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正和正义的理念;其次是违背了令状主义,属于违反宪法的重大违法行为。本案中的尿及其鉴定书都不能作为事实认定的证据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判例六中,警察告知犯罪嫌疑人负责侦查该案的侦查人员不在场,所以不能带其去厕所,只能使用房间里放置的桶。对这种积极的欺骗行为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院的判决。但是,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却被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了(参见判例七)*东京高判1974年11月26日高刑集第27卷7号第653页。。判决理由如下:从社会常识来看,尿是基于权利放弃意思下的排泄物;采尿行为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2款所列举的行为(比如采集指纹、脚型等)类似,侦查机关没有义务征求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进行酒精检查。
此后,值得关注的判例还有大津地方法院的判决。*大津地判1977年11月14日判时884号第128页。在该案中,有兴奋剂使用嫌疑的犯罪嫌疑人到警察局来更新驾照,警察并没有将采尿的意图告知,让其在警察局滞留4小时,提供茶和果汁让其饮用,使之排尿。大津地方法院认为,本案中的采尿行为并非基于犯罪嫌疑人的真意以及明示的同意(存在强制的因素),否定了尿液鉴定书的证据能力。可以看出,本案和判例五、判例六在任意性判断的问题上,都十分重视犯罪嫌疑人是否知道警察有采尿目的,在这一点上具有共通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津地方法院作出了否定判决,但还是被大阪高等法院驳回了。*大阪高判1978年9月13日判时917号第141页。大阪高等法院对采尿行为的事实进行了重新认定,认为从案情经过分析,犯罪嫌疑人毫无疑问知道警察具有采尿的意图。
(四)假装令状已经签发而进行任意侦查
第四种类型判例的案情与判例五和判例六类似,但是存在更多的欺骗行为。判例八将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的尿的鉴定书认定为违法收集的证据。*东京地判1987年11月25日判时1261号第138页。基本案情如下: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Y违反《兴奋剂取缔法》的犯罪事实,警察F部长在9月14日申请到了搜查Y住所的搜查扣押令状,正在寻找实施搜查的时机。4天后,Y因为盗窃被警察E拘留至警察局。警察F部长获知了该情况,在得知Y有尿意时,故意隐瞒了持有的对其住所的搜查扣押令状,携带着采尿容器和手续材料对Y实施了采尿。随后,Y在任意采尿同意书和所有权放弃书上签了字。东京地方法院认为,“在该案中,采尿程序违背了日本《宪法》第3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的令状主义,属于重大违法。如果允许采尿鉴定书作为证据使用,对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是不适当的。本案中的侦查人员利用已经签发了的对住所的搜查扣押令状,欺骗犯罪嫌疑人使其误以为侦查人员具有采尿的令状,从而让其配合实施了尿检,该鉴定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笔者认为,欺骗被处分人,利用其认识错误让其“任意提出”尿液、配合尿检的行为是违法的,可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认定为无罪,但是为什么本案将欺骗直接认定为违法?这还需要更充分的理由。
类似的扣押程序是否违法受到争议的案件还有判例九。*名古屋高金沢支部1981年3月12日判时1026号第140页。基本案情如下:警察N持搜查扣押令状(扣押对象写明是凶器),赴黑社会组织办公室搜查伤害案件中的凶器,在此过程中,发现现场的黑社会组织人员Q可能持有兴奋剂。N多次要求Q出示其所持物品,Q显得很紧张,反复说到要去厕所。N告知Q持有搜查扣押令状,可以搜查其所持物品,让Q将所持的所有物品拿出来接受检查。Q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检查。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沢支部判决认为,“在本案中,虽然对于所持物品的检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Q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检查,警察N没有搜查兴奋剂的令状,却告知Q将所持的所有物品拿出来接受检查。随后,又将Q以现行犯实施拘留,对兴奋剂予以扣押。从案情来看,可以说警察N对Q隐私的侵害程度大,很难认为其行为是适当的。”尽管如此,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沢支部又引用最高法院1978年创造的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即重大违法排除,*最判1978年9月7日刑集第32卷6号第1672页。认为从比较考量的角度,本案没有达到排除证据需要的重大违法,推翻了原审的无罪判决。
二、判例分析
(一)令状执行过程中使用计谋
首先来讨论第一种判例类型。判例一的判决对于侦查机关谎称身份进入住宅的行为,并没有说明理由,从结论上直接就认定为属于社会共识认可的适当的方法。多数判例评释赞成该判决,认为“该侦查方法使用欺骗是存在问题,但是该行为不同于破坏门和锁的行为,可以评价为社会共识上认可的稳妥方法”,*山室惠:《令状による捜索(2)》,《别册ジュリスト·刑事诉讼法判例百选》(第7版),1998年,第51页。“该案中,证据又很可能、很容易被销毁,故支持本判决结论。”*宫城啓子:《捜索差押許可状による住居立入り方法の適否》,《ジュリスト》1068号(1995年),第171页。但是,笔者认为,用计谋获取有瑕疵的同意(意思表示)从而进入住宅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了侵入住宅罪,这是否可以轻描淡写地认定为“社会共识上认可的稳妥方法”还值得慎重检讨。此外,在判例一中,判决认为侦查人员伪装成快递人员进入住宅的行为,属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11条所允许的“必要处分”。但是,从条文所处的位置来看,这里的“必要处分”应当限定为在“出示令状后”实施。如此一来,就不能援用《刑事诉讼法》第111条来为使用计谋进入住宅的行为开脱了。
值得注意的是,该类型的特征是搜查扣押令状已经正式颁布,不存在第二种判例类型的那种违反令状主义的问题。在判例一中,侦查人员本来可以在门口告知犯罪嫌疑人自己持有搜查令状,如果遇到抵抗,使用万能钥匙打开房门也可以执行令状,但侦查人员却使用了欺骗手法。如果说使用欺骗手法是为了省时省力,那么对程序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影响也确实要比其他类型小。但是,不执行令状,未经过同意便进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为什么被允许?我们不得不说问题又再次回到原点。
(二)隐瞒真正目的的“任意同行”
接下来来讨论第二种判例类型。判例三判决侦查人员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兴奋剂使用或持有的嫌疑,直接以违法停车的理由让其任意同行到警察局的行为是合法的。此处的欺骗,并不是直接针对任意同行。
这里,需要注意“认识错误”,在该点上判例三和判例四并不相同。在判例三中,被处分人对任意同行表示了同意。在接受“任意同行”上,被处分人并不存在认识错误,而仅仅是对自己到底受到何种嫌疑产生了认识错误。当然,若严格考察,此处并未根据兴奋剂使用的嫌疑实施任意同行,“同意”是有瑕疵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违反了令状主义。但是,即使嫌疑人的具体嫌疑并不明确,也可以进行职务询问。在职务询问中可以不告知嫌疑人其存在嫌疑。即,警察没有义务告知嫌疑人具体嫌疑,而且警察即使未告知也并不违法(或属于欺骗)。但是,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实施“任意同行”的前提是要确保任意性。为此,至少应当告知嫌疑存在,且嫌疑人通过告知内容要能够决定“是否愿意同行”。*名和振平:《任意同行の目的の告知》,《别册判例タイムズ11号·警察実務判例解説》(1990年),第44页。
在判例四中,犯罪嫌疑人X将着便装的3人误认为是收高利贷利息的人,随他们一起上了车。X在意识到3人是警察之前,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被“任意同行”。即,在接受“任意同行”上,X存在认识错误。如果说X推定的意思是拒绝同行的话,可以说侦查人员利用了X的认识错误。虽然不知道侦查人员是否有欺骗的意图,但是在X认识发生错误期间,侦查人员在未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违法执行了“任意同行”,该案中的侦查人员应当有消除嫌疑人错误认识的义务。
(三)使用计谋或利用错误的采尿行为
下面来讨论第三种判例类型——侦查人员隐藏鉴定兴奋剂或酒精的目的进行采尿的判例。判例可以分为两类:违法类和合法类。有观点认为,与第四种判例类型不同,第三种判例类型的判例并没有积极地欺骗犯罪嫌疑人令状已经颁发,而且被鉴定的客体也仅是尿这种排泄物,所以利用被处分人的认识错误实施采尿行为的违法性相对较弱。*认为尿属于无价值物,即使通过欺骗实施采尿行为也不违法的观点可参见:河上和雄:《排尿の検査のための採取をめぐる若干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捜査研究》271号(1974年),第52页;伊藤栄樹:《鑑定資料とすることを秘してとった尿と鑑定書の証拠能力》,《警察学論集》27卷5号(1974年)第14页。但是,笔者认为,在该类型判例中,被处分人是否存在认识错误较容易判断,但是侦查人员是否存在欺骗却不容易认定。
在判例五中,判决认为侦查人员隐瞒检查酒精含量的目的实施采尿行为不属于“违背被处分人意思的强制行为”,且“采尿方法也未丝毫伤害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属于合法行为。不难发现,该判决是从侦查人员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并未将被处分人的意思作为考虑对象。
在判例六中,判决认为,“该案的采尿行为使用了让犯罪嫌疑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手段,侵害了其个人尊严和基本人权,也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正和正义价值理念,违反了令状主义,属于违反宪法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同于判例五,判例六论及了被处分人的个人尊严,着眼点从侦查人员转移到了被处分人上。判决认为侦查人员通过计谋和欺骗损害了被处分人的个人尊严(人格权)。*熊本典央:《尿の採取と憲法31条·35条》,《判例評論》185号(1974年),第37页。
(四)关于是否持有令状的欺骗和错误
最后来讨论第四种判例类型——侦查人员使用计谋和欺骗,假装令状已经签发而进行任意侦查的判例。在判例八中,侦查人员明明没有获得令状(搜查扣押令状存在,但是没有强制采尿令状),却假装有令状。侦查人员存在积极的欺骗,使被处分人陷入认识错误,达到了扣押目的。在判例九中,警察隐瞒了令状所允许的搜查扣押范围,得到了被处分人不情愿的同意,对所持物品的检查在事实上也超出了搜查扣押令状所允许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中,虽然被处分人的同意存在瑕疵,但是法院并没有直接将之认定为违法,判决使用了利益权衡的方法,根据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得出了违法的结论。
这两个判例都属于明明令状没有颁发却假装已颁发,从而实施扣押或所持物品检查的情况,违反了令状主义。在判例八中,侦查人员本来没有获得令状的可预见性,却利用其他令状达到其目的,该行为属于重大违法。侦查人员如果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则可以不考虑被处分人的意思以及被侵害的同意权限,直接认定证据不可采。这从判例八中没有论及被处分人的意思以及被侵害的同意权限也可窥见一斑。
三、被处分人的意思与强制处分或任意处分
(一)被处分人的意思
被处分人的意思在判断强制处分和任意处分是否合法时具有重要意义。违背被处分人的意思,可导致强制处分和任意处分违法。判断强制处分是否合法的先例性判决(1976年)明确写道,“对于压制个人意思,对身体、住宅、财产等加以制约而实现侦查目的的行为,如果没有特别规定,不允许实施。”*最决1976年3月16日刑集第30卷2号第187页。可见,该判决把“意思的压制”和“对身体等诸权利的制约”作为强制侦查的要件,为通说(法益侵害说)所支持。关于“意思的压制”,比如在窃听案中,侵害行为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如果本人知道后会当然反对,这就属于“意思的压制”,并不需要现实的“意思压制”。*井上正仁:《任意捜査と強制捜査の区別》,《ジュリスト増刊·刑事訴訟法の争点》(第3版),2002年,第48页。又如,对于昏迷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有鉴定处分许可状的情况下对其实施采血的行为,违背了令状主义,同样也是基于类似的判决理由。*仙台高判1972年1月25日刑月第4卷1号第14页。如此,可以总结出,强制处分是违背被处分人的意思或推定意思的法益侵害行为。同样,违背被处分人的意思,换言之,侵害被处分人意思决定自由的侦查行为,只要不满足法定要件,也不能作为任意侦查(处分)被允许。
(二)强制处分和被处分人的意思
在前述第一种类型判例中,因为强制处分的执行过程中存在欺骗,所以被处分人的意思自由存在问题。当然,在强制处分中,即使违背了被处分人意思也能实施法益侵害,正因为如此,强制处分才是“强制”的。但是,这也并非是说强制处分可以完全无视被处分人的主观因素。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10条、第222条第1款的规定,在强制处分中侦查人员有出示令状并进行告知的义务。被逮捕人、被搜查人、被扣押人虽然应当忍受强制处分,但法律保护其知道令状内容的权利。又根据日本《宪法》第34条的规定,在逮捕令状中应当明确记载因何种犯罪被捕(即逮捕理由)。这里的“逮捕理由”,从权力行使一方来看,是正当行使特定权力的根据;从公民一方来看,是说明其为什么必须要忍受权力行使的理由。将逮捕理由向被处分人出示是正当程序和令状主义的核心要求。
奥平康弘教授认为,通过出示令状向被处分人明确告知强制处分的理由是尊重权力服从者人格的体现。*奥平康弘:《憲法Ⅲ》,有斐阁,1993年,第314页。令状主义与要求尊重个人人格尊严的正当程序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即使是执行强制处分,也应当向被处分人出示强制处分的理由和根据。可见,被处分人决定是否要抵抗侦查机关的机会和权利受到保护。侦查人员利用计谋和欺骗进行侦查侵犯了被处分人的人格尊严。判例八的判决中多次提及被处分人的人格尊严,也是遵从了该观点。
(三)任意处分和被处分人的意思
在任意处分中,如果没有发生违背被处分人意思的法益侵害,就不需要令状,法律对其具体实施过程也没有任何强制性规定。对于“任意处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对“任意”(“自发性”)的判断和侦查时对“任意性”的判断并未完全一致。有观点认为,对“任意”的界定并不仅限于本人自发主动的情形,也包括内心不情愿但勉强去做的情形。从社会常识来看,只要不是因为身体受束缚或强烈的心理压迫而导致的自由被拘束的情形,就都可以被认定为是“任意”的。*熊谷弘:《任意同行と逮捕の限界》,《捜査法大系》,日本評論社,1972年,第49页。但是,在前述第二种类型的判例中,在使用或持有兴奋剂的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隐蔽实施的“任意同行”(目的的不告知)就不属于“任意”。根据日本《犯罪侦查规范》第102条第1款有关“任意到场”的规定,侦查人员在实施任意处分时,必须向被处分人说明到场的日期、时间、地点、原因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其中,告知到场原因是任意性得以保证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从与被处分人的意思自由的关系来看,要做出自由的意思决定,就必须给予意思决定人必要且充分的信息。如果隐瞒信息,就当然不能作出任意的意思决定。侦查人员使用计谋和欺骗并不仅仅是隐瞒了进行意思决定的信息,而且也积极地提供了错误信息。被处分人根据所提供的错误信息不能进行自由的意思决定,所以其意思或同意就是有瑕疵的意思或同意,即使是任意处分也是不允许的。
(四)对侦查人员的计谋和欺骗的评价
以上内容从被处分人的意思决定自由的角度,对强制处分和任意处分进行了分别考察。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应当如何评价被处分人的认识错误,以及造成被处分人认识错误的计谋和欺骗。如果把侦查人员看作是在侦查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斗争的另一方当事人,那么某些计谋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实施。原田国男法官认为,“犯罪侦查是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智力比赛,是一个激烈的战场。双方都应承受这种风险,犯罪嫌疑人有时候会因疏忽大意被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所欺骗,不能因此就完全判定该行为违法。”*原田国男:《採尿検査をめぐる問題点》,《警察学論集》27卷5号,1974年,第36-37页。同样,臼井滋夫检察官认为,“确实,我们都希望侦查能够公正合法地进行。但是,因为侦查是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之间虚与实的较量,所以,为了击破犯罪嫌疑人的各种防御手段,发现实体真实,在一些情形下也只能使用某些类似于计谋之类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臼井检察官也明确表示不赞同那种将此类侦查行为认定为违反正当程序,且将以此获得的所有证据排除的“正当程序至上”的思考方法。*臼井滋夫:《尿の無断採取行為の適法性》,《研修》311号,1974年,第129页。
但是,侦查人员中也有人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侦查人员只能使用被允许的方法收集证据。如果犯罪嫌疑人陷入认识错误,侦查人员有纠正的义务。并不是所有的计谋都允许侦查人员实施,比如对拒绝采尿的犯罪嫌疑人,通过谎言(‘不检查尿,只是将之扔掉’)实现了尿检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是存在问题的。”*荒川洋二:《アルコール含有量を測定する意図を秘して被疑者から尿を採取することの適否に関する二つの裁判例》,《捜査研究》272号(1974年),第52页。也有观点根据不同计谋在欺骗内容和程度上的不同,将之区分,从而进行具体的合理性考察。笔者认为,这种思考方法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如果认为积极的欺骗是不对的,那么利用被处分人的认识错误达到侦查目的的行为在程度上也与前者一样,是不对的。问题分析到此,我们需要问一下为什么侦查人员的计谋和欺骗是不对的?笔者认为,根据日本《宪法》第31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侦查权力,有遵守正当程序的义务。侦查机关应当公正合法地行使权力,通过计谋和欺骗的手段达到侦查目的,原则上应当是不允许的(参照判例六),这不仅仅是因为侦查机关违反了正当程序的遵守义务,而且对于计谋和欺骗的实施对象——公民而言,这种行为侵害了其作为人的尊严,剥夺了被处分人意思或自主决定的自由。因此,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计谋和欺骗手段原则上是违法的。但是,这种违法是否直接导致证据排除的后果则至少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欺骗是否导致本来应当实施的合法的强制处分或任意处分未实施,欺骗的性质、程度是否达到了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大程度,因欺骗所受侵害的法益是否重大等。
结语
对于侦查人员使用计谋和欺骗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作为侦查对象的公民的意思表示是否有瑕疵;二是使用计谋和欺骗的侦查手段是否违法。对于前者,可以从“侵害被处分人意思决定的自由以及自主决定”这个角度进行讨论;对于后者,可以从“使用计谋和欺骗的侦查手段违反正当程序,属于违法,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这个角度进行讨论。
最近,在刑事司法中有引入诸如和解、交易等民事上作法的趋势。但是,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绝不是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正因为如此,侦查人员有义务遵守正当程序的相关规定。其实,法律已经授权给了侦查人员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人员应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若舞弄计策欺骗犯罪嫌疑人、被处分人,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许可就当然是不允许的,这很明确,不属于立法应当探讨的问题。
(责任编辑:郭欣阳)
作者简介:白取祐司,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日本法和心理学会理事长。 倪润,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28(2016)04-0162-10
*本文原载白取祐司:《刑事诉讼法の理论と实务》,日本评论社2012年12月版。本译文受“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新入校青年教师科研启动资助计划”资助。
〔 1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7条第1款规定,“关于侦查,为了达到其目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但是,如果本法律没有特别的规定,就不得采用强制处分。”根据该法条的规定,在日本,侦查时实施的处分区分为强制处分和任意处分。强制处分是侵害个人重要利益的处分,需要遵循令状主义原则。强制处分只限定在法律有规定的领域,比如逮捕、查封、搜查、强制采尿等。任意处分不需要遵循令状主义原则,常见的任意处分有:任意同行(嫌疑人同意被带走)、职务询问(警察令行为可疑者停下接受质问)、任意采尿(嫌疑人自愿提交尿液)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