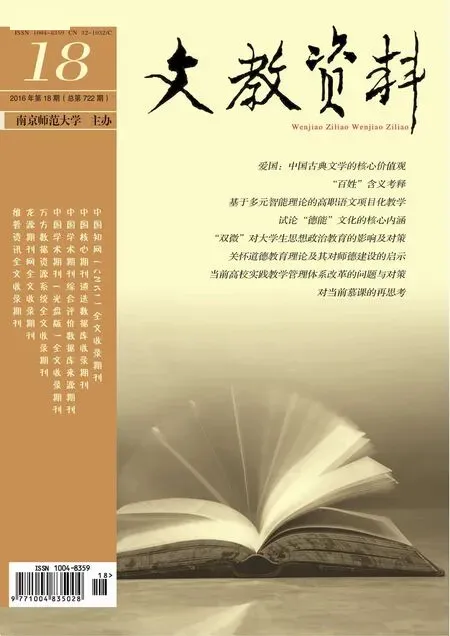钱穆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2016-03-16黄和谦
黄和谦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北京 100872)
钱穆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黄和谦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北京100872)
通过分析经钱穆晚年整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书的内容,揭示了钱穆学术的变化轨迹,即从早年偏嗜王阳明心学到晚年认同程朱理学的转变。在做学问方面,钱穆主张,观念层面上要能够对诸家观念调和一致、融会贯通;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坚持义理与考据二者并重,不能偏颇。此外,在史学方面,钱穆主张史学家要善于发现自己国家民族独特的内在特质。
学术思想融会贯通中国文化民族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以下简称《论丛》)是钱穆晚年整理其有关中国学术思想散篇文章的结集,作为对前期著作的观点和论证的补充。全书共八册,自上古迄先秦为上编,秦汉迄唐五代为中编,宋以下至民国为下编,共三编。尽管某些学者在自己的文章中经常引用《论丛》的观点,但是从已刊的论文数量上看,目前学界对《论丛》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①。诚然,笔者亦无力对《论丛》全书展开学术评述。因此,笔者尝试以《论丛》为中心,探讨钱穆学术志趣转变与学术观念转移的过程,揭示其中变与不变的因素。
钱穆曾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一书中表露心声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我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1]
钱穆出生于1895年,那一年正好是泱泱大国遭到东洋小国羞辱的一年。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殆尽,堂堂大国,不齿于邻邦。战败直接导致清政府需要为此支付2.3亿两白银的赔款,高昂的赔偿金额不得不让普通百姓去承受,造成上下失序,内外失调。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冲击,促使中国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比对中西方文明,寻求自强之道。钱穆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要比对两方孰优孰劣,就先要对中国文化,以及对西方文化有一番全面、系统、透彻的了解。钱穆一生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之精神,探源溯流,为“故国招魂”。
据余英时《钱穆与儒家》一文所载,钱穆早年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及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后来遍读诸家全集,有感于韩愈因文见道的主张。于是转治宋明理学,上溯五经、先秦诸子,下逮清儒考订训诂。此是钱穆的主要学术经历。《论丛》(七)序文:“余治宋明理学,首读《近思录》及《传习录》,于后书亦尤爱好,乃读黄、全两学案,亦更好黄氏。因此于理学各家中,乃偏嗜阳明。一九三O年春,特为商务印书馆万有书库编撰《王守仁》一册,此为余于理学家妄有撰述之第一书……然余于此二十年中,思想逐有变。一九三七年在南岳,多读宋明各家专集,于王龙溪罗念庵两集深有感。余于程朱,亦素不敢存菲薄意……乃知朱子之深允……余不喜门户之见……虽此六十年来,迭经丧乱,而古人书本,迄未放弃。尤于宋明理学家言,是非得失,始终未敢掉以轻心。”[2]
此条紧要,当作数条说明。其一,可证钱穆学术思想由王向朱的转变。1916年~1917年钱穆在鸿模小学执教,在暑假陪伴学生考试期间他只带了《王守仁》一书在考场外细细研读。他于1930年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写作《王阳明》②一书,认为以传统的考据训诂方法研究王阳明的义理之学不能得其要领,而且携门户之见也无助于对王阳明思想的理解。他说:“读者须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自透大义,反向内心,则自无不豁然解悟。”[3]但是从1930年到1960年钱穆承认“乃知朱子之深允”,前后跨度达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间,钱穆沉潜反复,泛览百家,最终才将一瓣学术香心归于朱熹。
其二,钱氏晚年,深允朱子之学。《朱子学术述评》载:“若说到朱子的思想,则他的最大贡献,不在其自己创辟,而在能把他的理想中的儒学传统,上自五经四书,下乃宋代周张二程完全融成一气,互相发明。在朱子的见解上,真是‘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他在中国思想史里独尊儒家,在儒家中又为制成一系统,把他系统下的各时代各家派,一切异说,融会贯通,调和一致。”
又说:“以整个中国学术史观之,若谓孔子乃上古集大成者,则朱子乃中古之集大成者。”[4]朱熹的学术地位几乎与孔子并列,都是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钱氏对朱子极为推崇。
但是钱氏推尊朱子,却不盲从。在观念层面上,他继承朱子融会贯通、调和一致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上,自然对朱子学说有所取舍。在《辨性》一文中,他总结道:“大抵晦翁讲宇宙方面,思路较完密,但其所谓理,则规范的意味重,推动的力量薄,平铺没劲,落到人生方面,使人感到一种拘检与散漫疲弱无从奋力之感。”在总结朱子个人思想的薄弱处后,又转而指出朱学流弊,即“以读书来代替穷理”,“以研究字义来代替研究物理”,最后“转到章句与训诂”上。在《辨性》一文的结尾处,钱氏进一步指出:“自晚明以下,中国儒学衰竭,亦竟无大气魄人能将孟子《中庸》晦翁阳明四家和会融通,打并归一。其有调和折中与夫入主出奴,皆未能深入此四家中而超乎此四家外来熔铸一新的天地。”[5]可见钱氏推崇朱子,又不惟朱子是尊,他试图绾合各家各说,和会融通,开创儒学复兴的新局面。
其三,可证钱氏议论小心,不喜门户之见。其实,钱氏为学,不惟不喜门户之见,也深恶持论片面、惨刻,甚至妄议古人。读《钱竹汀学述》一文,钱穆在摘录钱竹汀(钱大昕)关于抨击为学者好非议古人的文字后,作评注:“观于上引,竹汀为学,主于持论执中,实事求是,绝不愿见学术界有轻肆诋毁菲薄前人之风,更不愿有门户出入主奴之私争。此在当时学术界中,洵可谓一特立独出之人物。”[6]钱穆称誉钱大昕,褒扬他为当时学界中特立独出的人物,不仅不妄议古人,而且也无门户的偏见。但是,钱穆在文中如此褒扬钱大昕背后是否隐藏着其他动机?如果将这篇文章跟《〈崔东壁遗书〉序》一文结合着读,或许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个疑惑。
《〈崔东壁遗书〉序》一文说:“今既谓见于六经,传于儒家,其说未必绝不信,亦岂得谓六经不载,儒书不传,即尽为无稽不根之说耶!”粗一看,此语似乎只是特针对那些为疑而疑,持论片面者而言。但是行文不久,钱穆话锋一转,说:“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岐出益迷。彼以为儒术之与经义,此我之所吐弃不屑道者;然‘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琐琐之疑,节节之辨,岂所谓能疑辨者耶!”
又言:“以古拟古,我未见绌;以今准今,我乃实逊。我不自负责而巧卸其罪于古人,古人宁受之耶!然则尊古固失之,谴古亦乌得为是哉!”[7]这可能是针对过度地疑古思潮而发的。早在1930年顾氏曾力荐钱穆去燕京大学任教,可谓有恩于钱氏,然而学术讨论贵在自由且有所创见,而不是私立门户,互相标榜。钱氏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点,应该立足时代、敞开胸襟,研读古人书籍,要知人论世,更要融会贯通、调和一致;既不能惟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又不要为疑而疑、妄议古人,进而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以致妄自菲薄。这样的学术观念在钱氏的学术生涯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今举《讲学札记》中札记一条以互相发明:“陈澧兰甫谓为学可以有宗主,但不可有门户之见;世有所谓截断众流之说。如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迨孟子之死而不得其传。今世持此单传之浅见者,比比皆是。余喜前者而恶后说,盖狭隘门户陋见,非儒者为学之态度也。”[8]有门户之见,就容易因为主观的偏私而对学术成就产生不客观、不公正的判断。不过,钱穆没有门户之见,并不是主张乡愿之学,模糊是非,没有主见。相反,他在对各家思想作一番系统介绍后,旁征博引,往往有取舍,有创见。
在《〈大学〉格物新释》一文,钱氏指出:“明代人曾谓《大学》格物两字释义,共有七十二家之多,此不过极言此一语义解之纷繁。若论其至关重要者,在当时,则仍只朱子与阳明两派而已。”进而又剖析朱子“格物”之弊,“将使人穷老尽气,终不得门以入”。接着,他又将矛头指向王阳明的“格物”观点,认为王氏的看法“此只可谓阳明自发议论,与《大学》原义无涉”。于是,钱氏从《大学》、《乐记》、《孟子》、《小戴记》,旁涉《易》、《诗》,考据“物”的本义;其引“《小戴记·投壶》注,相间去如射物”,又摘取“《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以及《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则”。然后总结:“此皆物与则并言同义,犹言法则、准则。以今语说之,犹云榜样或标准。”因此“人性之明德,人事之至善”,即《大学》格物“物”字义”[9]。观钱氏为文,先祖述诸家“格物”字义,一一剖解,征于文献,训诂明义,最后力求融会贯通,生发创见。
钱氏追求融会贯通,不存门户之见,落到为学的方法论上,则主张考据、义理二者并重。《论姚立方《礼记通论》》说:“有清初叶,学者疑古辨伪之风骤张,而钱塘姚际恒立方尤推巨擘。独为《九经通论》,惜不尽传,其《礼记通论》则散见于杭世骏所编《续礼记集说》中。其书于《小戴》所收诸篇,逐一考其著作之先后,辨析其思想议论之所以来,若者为儒,若者为墨,若者为者,而第其高下,判其是非得失。虽不尽当,要异于拘常守规之见也。”[10]清初,学术界掀起疑古辨伪思潮,不过清儒大多溺于考据,少能申明义理。姚际恒讲义理之学,立足《小戴礼记》考据各家学说,“判其是非得失”,以训诂申明义理。钱氏赞赏姚氏这样的做法,所以他指出姚氏的研究成果虽然并不是全都得当,但是相比同时代常规(溺于考据,疏于义理)的做法还是有所创见的。
在由其学生整理的《讲学札记》中,钱氏的意见就更浅显。他说:“讲义理之学,不可一概避开考据不谈。如姚际恒作《礼记通论》,将《小戴记》四十七篇一一找出证据,是其精细处。此即义理与考据并重也。”[11]
既然钱氏主考据与义理二者并重,不可支离,那么专于考据、唯务雕虫的清儒自然为钱氏所不取。他说:“清儒研经之外,亦治史学,但他们的治史,也像他们的研经,他们只研究古代史,不研究现代史。他们只敢研究到明代为止,当身现实则存而不论。他们的治史,亦只为史书做校勘整理工作,却不注意史书里面所记载的,真实而严重的人事问题。清代学风,总之是逃避学风的。”学术的内在规律往往是“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而且“清儒到道、咸以下,学术走入歧道,早无前程”,所以他们不足应学术、时代之变,迎学术、时代之新[12]。
此外,钱氏论史主张,史学家需要发现自己国家民族独特的内在特质。钱穆说:“历史本身有内容、有生命,有主体,有个性。如说儒学史与禅学史,便各有其内在之生命与个性为之作主体。”基于此,钱氏在该文中说胡适,对中国禅学“并无内在了解,先不识慧能神会与其思想之内在相异,一意从外在事象来讲禅学史”,是其病痛所在。并进一步批评胡氏,“其讲全部中国思想史,几乎全犯此病”;对于中国儒学,钱氏又指摘胡氏,“先未深求孔子思想内在的大体系”,亦“未对所谓中国帝皇专制的内在政体深求”,所以“思想与制度,双方落空,无内容,无实情,便搭配来讲历史,那只是形式的、虚无的,非其历史”[13]。
注释:
①仅见于徐雁平先生在《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为例》
一文,该文主要就《论丛》第八册展开论述,梳犁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钱穆“每转益进”说的确立。
②该书后来被台湾联经出版社收录于 《钱宾四先生全集》,并改名为《阳明学述要》。
[1]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20.
[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序[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0册)阳明学述要[M].联经出版社,1998:3.
[4][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71-194.229-281.
[6][7][10][1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80.318-329.184-204.1-12.
[8][11]钱穆口述.叶龙整理.讲学札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50.5.
[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03-118.344.
[1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1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