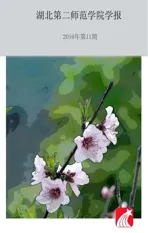在翻译伦理关照下:重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2016-03-16吴秀群
吴秀群
(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00)
在翻译伦理关照下:重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吴秀群
(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00)
文学翻译是一种翻译实践,与翻译文学有着本质区别,不应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混为一谈,建议对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进行区分,并重新对其进行定义。从翻译伦理角度论证文学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翻译伦理;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文学翻译;翻译文学
创造性叛逆自提出之日起,各种质疑声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是其概念模糊不清。本文指出,文学翻译是一种翻译实践,与翻译文学有着本质区别,而谢天振引入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向文学翻译成品,也就是翻译文学,因此不能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混为一谈,建议对其重新定义,进而从翻译伦理的角度论证了文学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一、研究背景
“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在其论文《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的关键》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埃斯卡皮所说的叛逆主要指语言层面的叛逆,而且还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文学价值。谢天振于上世纪90年代初将其引入国内,并在其上世纪末出版的《译介学》中给予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创造性叛逆”引入国内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中国知网上,以“创造性叛逆”为主题进行搜索,截止2016年9月底,已多达1000多条题录。除了大量期刊文章外,其中不乏博士论文和相关专著,如刘小刚(2006)的博士论文和董明(2006)的专著《翻译:创造性叛逆》,分别以哲学阐释学和描述翻译学为理论基础,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且均对创造性叛逆给予了充分肯定。可见,“创造性叛逆”研究热度之高。
但创造性叛逆自提出之日起,既有肯定之声,也有质疑之声,并由此产生了“忠实派”与“叛逆派”之争。质疑者首先对创造性叛逆的定义和表现形式提出了质疑。谢天振在《译介学》中关于创造性叛逆有这样一段阐述:“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2]137质疑者认为此概念非常模糊,需进一步澄清。段俊晖[3]以创造与叛逆的关系为基点,将创造性叛逆分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吴雨泽[4]认为创造性叛逆具有一定的理据,但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应始终以“忠实”标准加以规约,并认为创造性叛逆并非变相和单纯的“叛逆”,而是基于创造性深层意义上的“忠实”;王向远[5]认为,所谓 “翻译总是创造性的叛逆”,只是一种印象性概括,并不是严格的科学论断,并指出了叛逆的两面性,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的消极面“破坏性叛逆”。由此可见,对创造性叛逆的质疑大多源于其概念的模糊性,因此,有必要对创造性叛逆进行重新定义。从上述文献追踪可以看到,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但也不是尽善尽美。
二、创造性叛逆概念的重新界定
从上文文献综述可以得知,谢天振并未对创造性叛逆进行明确定义,但从他对创造性叛逆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再强调译者的主观努力和主观愿望,在此可以理解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译者来讲,他的主观愿望还是要尽量去接近原文,也即忠实于原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导致最后的背叛。他还归纳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包括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三个方面。其中译者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又可分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谢天振认为绝大多数的误译和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既然是无意识型的,那么实际上是与译者的主观愿望相悖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概念与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其中争议较大的是误译,而误译在翻译中又是无法回避的。正如日本学者河盛好藏说:“没有误译的译文是根本不存在的。”误译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无意误译主要是由于译者翻译时的疏忽大意、外语功底的不深和对译语文化缺乏了解造成的。这一类的误译,作为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译者应尽量避免。王向远[5]指出,不能将译者出于无知、疏忽等翻译水平与翻译态度上引发的误译,称之为 “创造性叛逆”。也就是谢天振先生所说的“无意误译”,在王向远看来是一种“破坏性叛逆”。本人也认为这种“无意误译”与“创造性叛逆”有着本质区别,不应将其归在“创造性叛逆”之下。另外,“漏译”也值得商榷。孙致礼[6]虽然肯定叛逆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认为由于误解、疏漏或翻译策略把握不当而引起的叛逆,属于无意义性叛逆,往往是不合理的,应尽力加以避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谢天振先生虽对“创造性叛逆”归纳较为全面,但对创造性叛逆缺乏明确的定义,以致于将所有所谓的“不忠实原文”的翻译文学都称之为“创造性叛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导致忠实派对其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使“创造性叛逆”的盲目崇拜者大力鼓吹之,导致了翻译中的胡译、乱译,从而导致了翻译质量的下降。这也是部分翻译学者对“创造性叛逆”持质疑态度的重要原因。鉴于部分学者和译者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有必要澄清“创造性叛逆”的实质,对“创造性叛逆”进行明确定义。创造性是指个体产生新奇独特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能力或特性,也称为创造力。如孙建昌认为,“创造性叛逆应该是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行为”[7]。总之,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结果,是对译者主体性的肯定,是对译者功劳的认可,若将“无意误译”、“漏译”等因为译者素质和态度因素造成对原文的不忠称之为“创造性叛逆”,实为对译者的一种贬斥。
为什么学者会对创造性叛逆有如此多的质疑声呢?谢天振[8]在其《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中,对此前的研究进行了批评指正,并再三强调“创造性叛逆”是对客观现象的描述,不是用来指导翻译实践的。由此可见,谢天振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创造性叛逆的,而译介学侧重于文学与文化研究,正如贾植芳在《译介学》序一中所言,译介学研究“与其说是翻译研究,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学研究,一种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出发点就不同,当然会引发诸多争议。同时也提醒我们,应将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与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区别开来,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谢天振看来,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只是对文学翻译成品的一种客观描述,因此他将所有有悖于原文的译文甚至由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所导致的不同理解统统归为创造性叛逆,它只是一种描述性研究,并不涉及到对译文的价值判断。正如王向远所指出的,谢天振是把“创造性叛逆”置于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立场的,研究的着眼点是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的价值,强调的是译者的主体性、译入国读者的阅读主体性。许钧在深入剖析埃斯卡皮的那段至理名言的基础上,指出埃斯卡皮所说的创造性叛逆已经突破了语言层面的界限,而延伸到了作品的生成与传播。而谢天振引入国内的“创造性叛逆”更是直接指向文学翻译成品。但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侧重于研究如何翻译,怎样翻译更好,其中涉及到的就是对译文的价值判断。而且,文学翻译实际上一种翻译实践,并不直接指向翻译成品。由此可见,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与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存在着根本冲突,故而不能将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直接搬到翻译实践中。当然这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只是研究出发点不同而已,谢天振提出的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更确切地讲是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那究竟什么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呢?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原文所指的艺术空间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追求深层意义上的“忠实”而采取的一种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是译者翻译水平的体现。孙致礼曾将叛逆划分为五种表现形式,他认为“纯语言”层面的叛逆,是翻译中难度最大的叛逆,这样的叛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为译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创造空间[6]。若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考查创造性叛逆,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些学者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要“创而有度”的观点。所谓“创而有度”就是译者的创造性要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比如吴雨泽提出的运用忠实标准对创造性叛逆加以理性规约。若将创造性叛逆分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也将使我们跳出“忠实”和“叛逆”之争的怪圈。下文我们将从翻译伦理的视角,来探讨文学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三、翻译伦理关照下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大多数学者对创造性叛逆的质疑实际上源于译文对原文的“忠”与“不忠”,然而正如王东风[9]所说,忠实只是一种错觉,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伦理判断。而何谓翻译伦理?王大智认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也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10]。而翻译行为的主体又是谁呢?
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包括译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主要反映在翻译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刘小刚[11]认为,接受者是创造性叛逆无可非议的主体,而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区分是主体研究的深化。许钧[12]则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场最中心的位置,相对于作者、读者来说,译者主体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对《译介学》将媒介者、接受者与接受环境都列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表示怀疑,认为“接受环境并不构成‘主体’,而是对‘主体’构成制约作用的一个因素”。袁莉也认为译者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本文认为,就文学翻译实践而言,译者是创造性叛逆当之无愧的主体。
黄玲,钟琳认为,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不可分割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最鲜明的体现。[13]创造性叛逆实际上是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使译者的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那么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不是可以信马由缰,毫无限制呢?下文我们将谈一谈翻译伦理和译者主体性的关系。
刘新建,刘著妍[14]指出,翻译伦理的作用体现在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上,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片面的。本人在《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现身》中,通过对西方翻译伦理主要思想的考查,曾提出与国内以“规范”为导向的翻译伦理不同,西方翻译伦理表面上制约了译者主体性,实际上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15]。无论是贝尔曼的迎向异质的翻译伦理、韦努蒂的存异伦理、皮姆的文化间性中的译者伦理,还是切斯特曼基于价值的翻译伦理,一方面规范了译者翻译行为,另一方面使译者的身份得到了很好的彰显,因此我们应看到翻译伦理的两面性。
1. 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的认可
首先,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它是一种艺术再创造,如何在译入语中更好地再现原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离不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而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诗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又决定了译者不可能对原文亦步亦趋,因此古往今来一直就有“译者即叛逆者”之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种有意识行为,是对译者主体性的认可,而翻译伦理尤其是皮姆的译者伦理,认为译者至少要在原文作者、读者、客户、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五个方面选择自己“首要忠诚”的对象,对忠诚对象的选择涉及到译者的价值取向,而译者的价值取向又关系到翻译策略的选择,整个过程都离不开译者这一行为主体的参与。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还是翻译伦理,实际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即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还有学者提出,翻译伦理将翻译关注的重点转向人而不是文本,是对翻译中人的关怀,即对译者的人文关怀,与我们当今提倡人文关怀的社会不谋而合。
2. 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身份是多重的,译者身份的多重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伦理约束的多向性[16]。如切斯特曼一人就提出了五大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显然译者不可能同时遵守五种伦理,而每一种伦理都是对译者翻译行为的一种制约。其中,再现伦理认为译文应准确再现原文或原文作者的意图,不能任意对原文进行增减及篡改,必须再现原文特征。也就是,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再现。王莉娜[17]对切斯特曼的前四种模式进行了解析,认为不同模式适用于不同文本的翻译,其中再现模式尤其适用于文学翻译。
在翻译实践中,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主要体现在,译者必须使译文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如贝尔曼的迎向异质的翻译伦理、韦努蒂的存异伦理,均要求把他者当作他者来认可。另一方面,翻译伦理所要求的“忠实”并不是否定译者主体性的客观存在,而是在更高层次上要求译者提高发挥主体性的能力,去不断追求译文在更深层次上忠实于原文。从此意义上来讲,创造性叛逆实为更为深层的忠实。正如许钧所说,“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18]276
在翻译伦理关照下,“叛逆”与“忠实”这一矛盾,看似相互对立,不可调和,实际上是相生相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有共时和历时的特点。我们都知道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者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看似叛逆的作品在另一时期却是忠实的,反之亦然。
四、结语
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对文学翻译成品的一种描述,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而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的一种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因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翻译伦理关照下,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性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又受到翻译伦理的制约。翻译伦理和译者主体性的关系,就好比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一样,在翻译伦理的框架下,译者既可以享受一定的自主权,但又不能肆意而为。在翻译伦理关照下,创造性叛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1] Escarpit, R. “Creative Treason” as a Key to Literatur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1961,(1):16-21.
[2]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 段俊晖. 重新定义创造性叛逆——以庞德汉诗英译为个案[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4): 117-121.
[4] 吴雨泽. 在“忠实”标准的观照下:重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4): 123-126.
[5] 王向远.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J]. 广东社会科学,2014,(3): 141-148.
[6] 孙致礼. 翻译与叛逆[J]. 中国翻译,2001,(4):18-22.
[7] 孙建昌. 试论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 理论学刊,2001,(4):118-120.
[8] 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J]. 中国比较文学, 2012,(2): 33-40.
[9] 王东风.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 中国翻译,2004,(6): 5-11.
[10] 王大智. “翻译伦理”概念试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12): 61-63.
[11] 刘小刚. 释义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J]. 中国比较文学, 2006,(1): 129-140.
[12]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2003,(1):6-11.
[13] 黄玲,钟琳. 从翻译过程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J]. 长春大学学报, 2015,(6): 118-121.
[14] 刘新建,刘著妍. 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制约关系探究[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4,(4): 84-87.
[15] 吴秀群. 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现身[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1):35-39.
[16] 郝军. 翻译伦理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孙致礼《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3,(2): 76-78.
[17] 王莉娜. 析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J]. 外语研究, 2008,(6): 84-88.
[18] 许钧. 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郑诗锋
Redefine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Under Translation Ethics
WU Xiu-q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Anhui 244000, China)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type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different from translated literature.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reative treason in translated literature are not the same, which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Therefore, creative treason should be redefined.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inevit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creative treas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thics.
ethics of translation; creative treas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ed literature
2016-09-13
吴秀群(1979- ),女,湖北钟祥人,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及外语教学。
H059
A
1674-344X(2016)11-01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