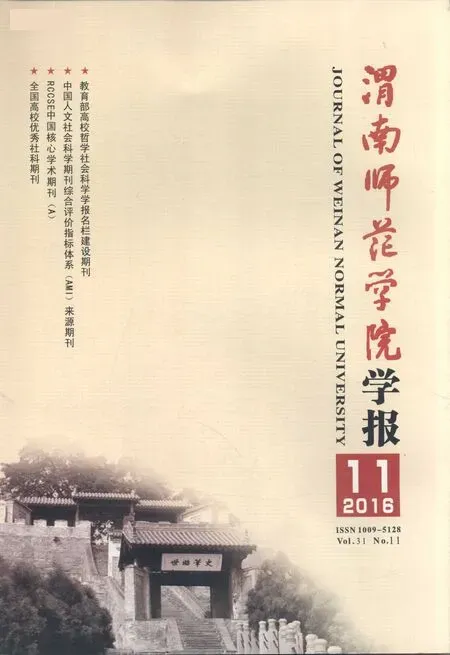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再认识
2016-03-16王玉洁
王玉洁,满 鹏
(1.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 710016;2.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西安 710016)
刑事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再认识
王玉洁1,满鹏2
(1.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 710016;2.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西安 710016)
摘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赋予了刑事法官享有庭外调查权。文章对现行规定予以剖析,使读者明确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前提是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产生质疑,难以判别真伪。同时,庭外调查权行使的路径有先后顺序,只有当举证责任主体穷尽手段仍无法证明证据真伪性时,法官才能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
关键词:法官庭外调查权;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
何为刑事法官庭外证据调查权?很多人对此进行了解释,如有论者认为是在刑事案件中,“法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在法庭以外所进行的调查核实活动”[1]237;也有论者认为是“法院审判活动中,审判法官及其他法院工作人员对有关证据,依职权开展调查收集的诉讼活动”[2]2。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在休庭后对证据进行的调查核实,是法官履行其案件事实查证责任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其审判权的积极运用”[3]380-381。这一解释立足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称最高院《解释》)第220条也规定:“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如何正确理解上述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规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何为有疑问的证据
应该注意的是,在《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和最高院《解释》第220条中均提到了“有疑问的”证据。那么,何为有疑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认为,主要是指合议庭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认为公诉人、辩护人提出的主要证据是清楚、充分的,但某一证据或证据的某一方面存在不足或相互矛盾,如对同一法律事实、公诉人、辩护人各有不同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或鉴定结论等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疑问,就会影响定罪或判刑,但是,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法庭无法及时判定真伪,很有必要先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4]183从该条解释上我们可以看出,对证据有疑问需要调查核实的前提是案件主要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合议庭仅是对某一部分证据有疑问,这种疑问虽然不能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后果,但其程度必须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程度可能会对定罪量刑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0条明确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据此,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更加深入地解析“何为有疑问的证据”,即一方面是对证据的证据能力有疑问,另一方面是对证据的证明力有疑问。
首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证据的证据能力,即证据能够呈上法庭,成为审判者定案依据的资格问题。对证据能力的判断其实质是对证据三性的判断,即法官是否对提交法庭的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产生疑问。
第一,关联性。关联性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即用来证明要证事实的证据必须限于与双方争议的事实有关联,否则不能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一般情况下,法官对于提交至法庭的证据是不是能够用来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比较容易判断,通常很少产生疑惑。
第二,客观性。客观性指证据在社会中实际发生,或是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受主观性推测、主观想象或者人们捏造的东西。[5]164证据具有客观性的主旨在于强调证据的真实性,即证据必须是真实的,而不能是虚假的、伪造的。证据的客观性包括证据形式的客观性、证据内容的客观性和证据所证内容的客观性。(1)证据形式的客观性,就是承载证据内容的载体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司法工作人员能够使用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最基本前提,法官通常对此不会产生疑问。(2)证据内容的客观性,就是证据中所蕴含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于此点,法官通常亦很少产生质疑。例如,辩护律师二审期间将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的退补提纲作为新证据向法庭提交,意图证明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不足。由于该退补提纲并非是案件发生过程中留存下来的客观存在,而是案件已经发生后,承办案件的工作人员在案件的审查起诉过程中对需要完善部分制作的文书,故法官最终以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为由不予采信。(3)对于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是否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否是与案件事实完全相符的,就需要通过人的认识活动进行探知。因为客观的印记、痕迹形式和留存的案件信息在其产生的时候是存在于未知领域的,尚未被人们的主观性所掌握,此时这些证据是潜在的,未显露出来的,只有通过人的认识活动,这些证据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证明作用。例如凶案现场遗留的几枚烟头,在未经过法医鉴定之前,它并不能证明什么,法官也不会将它作为审查对象,因为大家并不知道烟头是否是被害人所留,是否是犯罪嫌疑人所留,这些都需要人们予以发现和确认。而当人们为了证明案件事实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和认识这种印记和痕迹与案件事实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客观的、内在的联系从而得出证据事实的时候,人的主观性便不可避免地介入到了证据之中,使证据成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混合物。比如,被害人由于对犯罪嫌疑人的痛恨,其陈述就有可能夸大部分事实、某一证人由于系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其证言就有可能避重就轻或存在虚假的情况。若此时,控方提交的某位证人的证言与辩方提交的另一位证人的证言所证实的内容正好相反或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往往就会导致法官对控方所提交的指控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人证言产生疑问,究其实质是法官对某一证据所证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4)当然,法官对证据客观性的判断通常不是分裂开的,其对证据所证内容客观性的判断需要证据形式客观、完整的辅佐。《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6条、27条、29条就是对此判断方式的体现。即第26条规定:“勘验、检查笔录存在勘验检查没有见证人的,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没有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人员违反回避规定的等情形,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又如在实际工作中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其供述是否真实时,法官通常会结合该讯问笔录记载是否完整,是否记载了讯问的起始时间,笔录是否由两名侦查人员签名,笔录记载的讯问地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等因素,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进行判断。若法官在审查判断某份讯问笔录所载内容的客观性时,从笔录记载的供述内容看犯罪嫌疑人供述完整、翔实、逻辑性强,但讯问笔录记载的讯问地点不是在看守所而是在办案单位讯问室等其他地点,此时辩护人又提交了证实某份讯问笔录系在刑讯逼供情形下做出的证据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会对该份笔录所证内容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第三,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的收集和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一般包括主体的合格性、程序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实践中,对于刑事案件证据的收集主体是否合格各方通常均不会产生质疑。对于证据形式的合法性问题,法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亦很容易作出判断。而对于证据是否依据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收集,控辩双方经常会产生诸多争议,例如从犯罪嫌疑人处查获的毒品是否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了封存拍照,毒品是否受到了污染等等。
分析完证据的三个属性,我们接下来分析第二个方面——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于案件事实有误证明作用及证明作用如何。证明力即证据资料在诉讼证明中的价值,也就是指证据资料在审判者心目中产生相信与否的力量和程度,其实质是证据在审判者心目中的可信程度。
法律预先明文规定证据证明力的为“法定证据制度”。这一制度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中运用证据,只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规则,这样就能够发现真实。这种规定有利于约束法官,防止法官专权,但这种机械的做法只会窒息法官对案件的理性判断,难以作出符合案件真实的裁决。与之相反,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预先不作规定,允许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自由加以判断的证据制度,称为“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也就是证据的证明力是靠审判者内心来感知的,其是由审判者凭借事实与经验作出判断。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的制度顺应了诉讼证据本身的复杂性,可以使法官对证据进行理性的自由判断,是现代各国普遍实行的证据制度。
可以说证明力是证据本身固有的属性。如果证据具有客观性并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就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但不同的证据,因各自的特性和与案件待证事实的关系不同,对于待证事实往往具有不同的证据价值,发挥着不同程度的证明作用。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是基于两大点:第一,基于不同种类的证据具有的不同特性;第二,基于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对于不同种类证据的不同特性,例如物证更直观,更容易把握,书证的证明力较强,对确认案件事实一般具有重要作用。对这些不同特性的判断法官很容易进行判别。那么,法官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内心判断其实质可以说仍是基于该证据的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及其本身的客观性来进行的。因此,对法官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质疑归根结底其实是对证据关联性和客观性的质疑。前文已经对证据关联性和客观性进行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根据上述从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两个方面的剖析可以看出,法庭对证据有疑问通常发生最多的情况就是对证据所证内容的客观性,也就是对证据所证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无法对某一事实形成内心确信,进而需要对该证据所证的事实进行补充证明。
二、补充证明的路径
从《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和最高院《解释》第220条的规定中,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法官对证据有疑问时,应当如何进行补充证明,即补充证明的路径是什么?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有两条路径可以解决,一是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及有关人员补充,一是可以自行调查核实。
第一,上述这两条路径是否有先后顺序呢?笔者认为,这两条补充证明的路径是有先后顺序的,即第一条路径在先,只有当第一条路径不能完成此任务时,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选择第二条路径。也就是说,当法官对某一证据有疑问是,应当首先要求举证责任主体补充提出证据,只有当举证责任主体穷尽手段仍无法证明证据真伪性时,法官才能行使庭外调查核实权。即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行使具有一定的补充性。这一原则实际在诸多法律条文均给予了体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8条规定:“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出庭检察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补充证据或作出说明;确有核实必要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最高院《解释》第108条第2款规定:“对到案经过、抓获经过或者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第110条第2款规定:“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坦白、立功的事实和理由,有关机关未予认定,或者有关机关提出被告人有自首、坦白、立功表现,但证据材料不全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第二,法官庭外调查核实的方法和对象。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庭外调查核实的方法,包括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那么,法官庭外调查核实的方法是否仅限于如上7种方式,能否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等手段呢? 对此,学界观点不一 。有观点认为,法官庭外调查仅限于如上七种手段[6]226-227,也有学者认为法官庭外调查不应限于上述6种手段[7]。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时仅能采用法律明确规定的7种手段。首先,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程序法定原则。其次,法官庭外调查权是一种补充性的调查核实权。只有在证据真伪不明而控辩双方无法或不愿举证时,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法官不得已才采取的调查核实方法,并非是常态性的调查核实方法。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调查核实手段还是在法庭上调查核实,只有在法庭上无法解决时,才使用庭外调查核实权。这也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从法条列举的这几项调查核实手段来看,反映出了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这种必要性原则。因为,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查询和冻结都必须在庭外进行,在法庭上都无法解决。而对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基本上都是可以在庭审中予以调查核实的,并非必须在庭外进行。 因此,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方法应限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手段 但是,法官庭外调查的对象则不限于通过上述7种手段获得的证据,也包括有疑问的证人证言、被告人辩解和供述等。但对某些种类的证据,法律也限制了法官庭外调查的方式。如《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4条第2款规定:“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由其出具相关说明,也可以依法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27条第2款规定:“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第三,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参与人。为了避免法官庭外调查核实权行使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参与不足,使得庭外调查权行使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不足,有必要强化该程序控辩双方的参与度。故最高院《解释》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核实证据,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到场。上述人员未到场的,应当记录在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亦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即第38条规定:“法庭进行庭外调查时,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到场的,法庭记录在案。”控辩双方参与法官庭外调查,不仅可以有效消除控辩双方对法官取证过程的担心,也有利于法官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防止法官形成偏见 。
需要注意的是最高院《解释》第66条第2款“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时,发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新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告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提取,并及时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查阅、摘抄、复制”的规定,不属于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的范畴,因为这里发现的新证据系对案件事实认定有重要作用的证据材料,不符合前述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前提需是案件主要证据确实充分,仅对部分证据存有疑问。因此,在此情况下,法官应当告知举证责任的控辩双方收集、提取该证据。或者必要时,法官可以先直接提取,随后及时通知举证责任的控辩双方查阅、摘抄、复制。
参考文献:
[1]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孙云康.论法官庭外调查制度[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
[3] 龙宗智.刑事审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5] 程蓉斌.中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6]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7] 李奋飞.刑事诉讼中的法官庭外调查权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1):35-36.
【责任编辑刘蓉】
Re-recognition of Judge’s Right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ut of Court
WANG Yu-jie1, MAN Peng2
(1.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Shannxi Province, Xi’an 710016, China;2.Xi’an Public Security Bureau Baqiao branch, Xi’an 710016, China)
Abstract:China’s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give judges the right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ut of cour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making the reader clear that the premise of exercising the judge’s right of investigation out of court is that authenticity of part of the evidence is suspected, which is difficult to tell the truth. And, there is a sequence of paths to exercise the judge’s power of investigation out of court. Only when the subject of the burden of proof who is using all kinds of means is still unable to 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vidence, the judge can exercise the investigation out of court.
Key words:judge’s power of investigation out of court; relevance; objectivity; legality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11-0049-04
收稿日期:2016-05-05
作者简介:王玉洁(1984—),女,陕西渭南人,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员,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满鹏(1984—),男,山东滕州人,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民警,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社会与法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