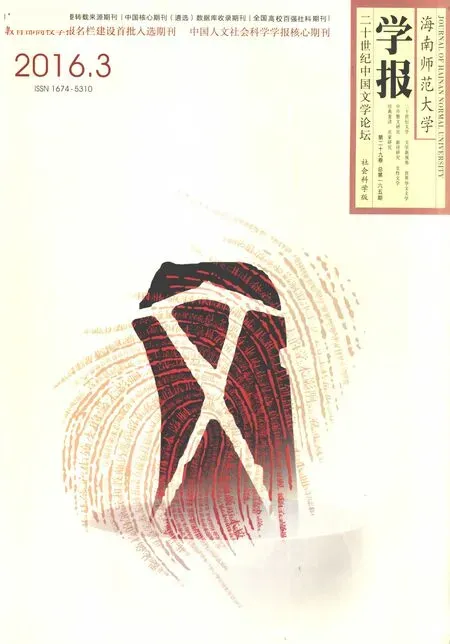文艺批评的底气、勇气与地气
——评熊元义《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
2016-03-16曾庆江
曾庆江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文艺批评的底气、勇气与地气
——评熊元义《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
曾庆江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这些年文艺界呈现出非常奇怪的现象。比如,一方面是创作数量屡创新高,“著名作家”、“杰出诗人”、“知名画家”等遍地开花,但是精品力作却少得很,即便是获得国内外大奖,被受众认可的层面也相对有限,文艺接受市场的低落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文艺批评家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式批评性的文字出现在各大报刊杂志网站上,蔚为壮观,甚至口水骂战而形成传媒热点的也不见少数。从本质上讲,文艺批评理所当然属于文艺接受的重要范畴,并且应当有利于文艺创作。文艺创作、文艺接受和文艺批评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文艺批评已经变成少数人自说自话,玩票的专利了。人们在责难文艺批评“失语”和“缺位”的同时,也呼唤真正透彻的文艺批评。在这一语境中,依然有批评家在坚守,在关注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关系的同时,努力破解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症结。熊元义博士的《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理论反思》。凡出自本书的引文,不再特别说明,只在正文中注明页码。就是这样一部值得关注的文艺批评著作。这部著作没有对文艺批评进行元话语的构建,也没有对经典文艺批评理论做进一步的阐释,少有宏观叙事,而是立足于文艺批评实际,在把握相关文艺批评家的风格特征以及文艺创作现状的同时,对文艺批评的发展瓶颈、理论构建以及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体现了文艺批评的底气和勇气,并且与地气相接,对当下的文艺批评建设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一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创作的发展繁荣,文艺批评也随之迅速发展,它们在引导文艺创作,推动文艺理论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正由于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的极大影响,逐步导致了文艺批评的异化。文艺批评变成了某些批评家的“登龙术”,大致体现为两种趋向:“歌德派”和“酷评派”。“歌德派”的做法是对作品进行歌功颂德,极尽褒扬吹捧之能,当下比较流行的“红包批评”、“交换批评”即是如此;“酷评派”的做法则一律采用“骂杀”的方法,看似气势磅礴,其实多偏颇之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歌德派”常常是异常活跃,逢请必到,穿梭于各种创作研讨会。“酷评派”也往往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因为他们时常有惊人之语,成为各大媒体谈论的焦点。正因为如此,文艺批评成为一个门槛极低的行业,似乎能码字儿敢说话的都可以成为批评家,而这也推动了文艺批评学术泡沫的形成。
但是,真正的文艺批评家绝不是写几篇批评性文字,出席几场研讨会就可以打造的,而是需要深厚的文艺理论作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从事文艺批评是需要扎实的文艺理论作为底气的。熊元义的文艺批评即是如此。他自己经过大学中文系的科班训练,攻读了文艺学的博士学位,熟读了古今中外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作,体现出对理论的偏好,出版了《回到中国悲剧》《拒绝妥协》《眩惑与真美》《当代文艺思潮的走向》《中国悲剧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多部文艺理论著作,这为他深入地进行圆熟的文艺批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部《理论反思》中,他系统地分析了鲁迅、朱光潜、陈涌、姚雪垠、刘再复、陆梅林、仲呈祥等诸位大家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特色,体现出良好的理论素养。这是进行文艺批评的底气。例如,在《自觉地推动当代文艺思想的解放》一文中,作者系统分析了姚雪垠的文艺思想。姚雪垠由于小说创作的影响,使得人们对其文艺理论的关注度并不很高。熊元义认为,“姚雪垠不但在文学创作上开辟了一条历史小说创作的新路,而且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长篇历史小说美学上也做出了独特贡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第242页)他在系统解剖姚雪垠文艺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姚雪垠等人“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思想的解放运动中是相当积极和自觉的”(第249页),这具体体现在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深入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深入两个方面。但是作者并没有神话姚雪垠的文艺思想,在正确认识其文艺理论贡献的同时,熊元义也客观地评价道,“姚雪垠的文艺思想过于偏重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而轻视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甚至在有些方面还贬斥浪漫主义文学观。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坛流行浪漫主义文学观时,姚雪垠包括他的文学创作就难免遭到排斥和轻视。姚雪垠的这种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曲折发展。”(第256页)如果不详细了解其文艺理论的全貌,是没有底气做出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结论的。相比当下不少文艺批评家断章取义式的批评,熊元义的底气是值得赞赏的,也是值得同行学习的。在文艺批评的经世致用和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学术泡沫愈演愈烈,熊元义从理论文本出发的底气,让我们看到未来文艺批评的发展方向。
正因为有着文艺理论的底气,才能正视当代文艺批评的困境。在熊元义看来,当下文艺批评陷入了“缺位”和“缺信”的双重困境。“所谓‘缺位’,就是有些文艺批评对优秀作品弘扬不够,对不良倾向抵制不力,对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个案艺术品探讨艺术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等研究不深。所谓‘缺信’,就是有些文艺批评的社会公信力下降。”(第10页)可以说是戳住了当下文艺批评的痛处。熊元义对当下文艺批评的理论构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学的发展严重脱离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应当立足于反思和总结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惟有如此,才能构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学的真正生长点。打铁也需自身硬,正因为有着坚实的文艺理论底气,才能够说出掷地有声的话来。
二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光有文艺理论的底气是远远不够的。当下,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不在少数,但是做一个饱学之士容易,做一个有良知的饱学之士则实属不易。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艺批评家,就需要在相关底气的基础上敢于担当,正道直言。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但是,敢于正道直言并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建构在一定的底气基础之上的。所谓“无知者无畏”是指那些虽然敢说话,但是由于不怎么读书,将常理当作真理甚至将谬误当作真理而夸夸其谈。这种做法不但无补于文艺批评,反而助长浅薄、浮躁的风气。当下不少热衷于出席各种文艺创作研讨会的“会油子”或者倚马可待的批评家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型。只有建构在文艺理论底气基础之上的正道直言,才能击中文艺批评的要害,进而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因此,要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不仅需要底气,更需要建构在底气基础之上的勇气,道人所未道,道人所未敢道。
文艺批评的勇气要求我们能够直面当下批评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引导文艺批评良性有序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推动文艺创作发展。例如在《喜剧理论的阙如与喜剧批评的迷失》一文中,熊元义从关于中国喜剧艺术领军人物赵本山的相关批评说起,认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批评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时应该遵循喜剧艺术规律,全面地把握赵本山的喜剧艺术,准确地认识赵本山的喜剧艺术在世界喜剧艺术发展史上的位置,极力避免简单的捧杀与棒杀”。(第50—51页)他接着说,“中国当代有些喜剧作品往往容易混淆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这两个范畴”,“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该深入地解剖赵本山的喜剧艺术,即充分肯定赵本山在喜剧艺术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不掩饰其局限并深入地分析这种局限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而不是一味地责备赵本山的一些喜剧作品的媚俗。否则,这是难以服人的。”在指出问题的同时,熊元义也为批评开出了相应的药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批评赵本山的喜剧艺术时应该积极开展喜剧艺术批评,而不仅是文化批评。……这种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戏剧艺术批评的基础上,是戏剧艺术批评的丰富、补充和延伸……有些文艺批评家却不是把找本身主演的喜剧作品看作喜剧艺术,而是仅仅看作一种文化现象。”(第53页)作者的观点是要从文艺本身自身的特点进行文艺批评,这样才能抓住对象实质,真正意义上引导文艺创作。
文艺批评的勇气要求我们能够透过文艺批评繁盛的表象击中其实质性问题,让人警醒,真正意义上引导文艺批评向前发展。例如,有些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熊元义认为这种判断“没有抓住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要害”。他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作家并不缺乏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而是在于“有些作家放弃了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推崇一种只认强弱、不辨是非的粗鄙实用主义文化,既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第24页),这可以说是击中了当下文学创作“缺失”之要害,自然发人深省。针对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的看法,熊元义认为是“没有正确地区分狭隘的文艺的批判精神与科学的文艺的批判精神”。(第25页)他进而指出:“科学的文艺的批判精神不是以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来彻底否定现实生活,而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而是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批判现实生活。总之,这种科学的文艺的批判精神是艺术家批评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第25页)这种辩证客观的观点贯穿整部著作始终。作者并不是“矮子看戏”式的人云亦云,即便是一些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批评,他也结合相关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实际进行细致的思考,缜密的判断,从而得出更加客观真实的结论,这种结论无疑是更有利于当下文艺创作的,更有利于当下文艺批评话语构建的。
文艺批评的勇气要求我们能够理性客观地对待前人的文艺理论成果,以发展的眼光来解读先贤的相关思想,并指向当下的文艺批评。以《朱光潜在中国悲剧把握上的理论失误》为例进行简单分析。众所周知,朱光潜是我国著名美学家,在构建我国现当代文论体系方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众多青年批评家来说,除了极少数“无知无畏”者以简单粗暴方式“否定一切”式的姿态对其不屑一顾外,大多数批评家是对其膜拜有加,往往将其奉为理论的圭臬反复引用以证明自身观点的合理性。熊元义立足于中国悲剧产生的语境和自身特点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有着明显的不同,即“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这样,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就无法把握中国悲剧的真正内涵。究其实质,熊元义认为是朱光潜“强调了艺术创造,而忽视了艺术的反映”,因此造成了理论失误。而朱光潜的理论失误对当下应当产生某种启示,那就是,“理论的贫困仍然制约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瓶颈所在。”(第62页)作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朱光潜,而是从朱光潜的若干失误来反思当下文艺批评的相关问题,视野开阔,立论精准,既体现了文艺理论的扎实性,又彰显了文艺批评家为文艺创作负责的良知,勇气可嘉。
三
但是,我们还要说,有文艺理论的底气,有文艺批评的勇气,也未必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批评家。如果操作不当,极有可能陷入堂吉诃德和风车作战的尴尬。堂吉诃德勇猛地和风车进行战斗,体现了他嫉恶如仇、维护正义的心理动机,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由于所选取对象为虚幻的风车,只能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堂吉诃德在骑士小说的熏染下,成为思想上的智者,这是他行走天下的底气。他和风车进行战斗,体现了他捍卫理想的勇气。但是底气和勇气加起来仍然不免身陷尴尬的局面,这表明,对象是非常重要的。是选择“无物之阵”进行摇旗呐喊,还是有的放矢真刀实枪地进行战斗,结果是大不一样的。熊元义的文艺批评就是有的放矢真刀实枪地战斗。只有接地气的文艺批评才能摆脱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尴尬,才能真正意义上促成文艺批评话语的构建,推动文艺创作的良性发展。
19世纪时的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经历表明了接地气的文艺批评是多么地重要。1835年,果戈里的《密尔格拉得》等问世后,由于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受到了反动批评家们的围攻。当果戈里感到徨惑不安的时候,别林斯基凭借他锐敏的文学感觉,写了著名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分析了果戈里作品的意义和特点,以巨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气势,充分肯定了果戈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对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的迫切意义。这不仅大大地鼓舞了果戈里,促使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写出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与果戈里同时代的一批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在《理论反思》这部著作中,熊元义并没有集中关注某个文艺创作家的创作,也没有单一地指向某一批评家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很难断定他的文艺批评对哪一个文艺创作家或者批评家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是,由于他的批评始终立足于当下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发展实际,应当属于“类属批评”,可以对相当多的文艺创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产生相应的启迪,从而彰显文艺批评的现实功用。
在《深情创作与矫情创作》一文中,熊元义在评析了文艺批评家王学海相关研究著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延伸解读与思考,他认为,“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不是在已有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前进,而是在断裂中反腐和‘折腾’。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不能在承前启后正前进,不是在接力中发展,而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习气严重。中国当代优秀文艺批评在这种反复和‘折腾’中很难形成合力,更难形成浩浩荡荡的潮流。因而,中国当代不少优秀的文艺批评往往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既不能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形成持续影响,也不能引导中国当代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第277页)这种接地气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了当下文艺批评的症结点,对不少批评家应当是一种警醒式的批评,正所谓响鼓宜用重锤,其振聋发聩的效果可以想象的。在《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及理论解决》中,作者评述了文艺理论家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等文艺思想,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对照陈涌、姚雪垠等人的文艺思想,认为“中国当代有些文艺理论家在遇到文艺理论批评不是本着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追求真理,认真辨别这些文艺理论批评的对与错,而是追逐特殊利益,放弃是非判断”,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丧失别林斯基追求真理的勇气,“要在健康而深入地开展文艺理论争鸣的过程中促成对立的双方在更高的层次上超越彼此的局限,形成新的共识,达到新的团结。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第296页)
在《理论反思》一书中的第三辑“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中,多单个文艺创作者或者作品专论,这些文字正是作者接地气的批评。例如在《回归正义与民族精神的传承》一文中,作者集中笔墨分析了陈凯歌电影《赵氏孤儿》。熊元义认为,《赵氏孤儿》深刻地揭示了小人物“复仇”的困境即小人物在遭受戕害后很难找回公道,“具有某种令当代人纠结的悲剧意味”,但是“在人性的深度开掘上却没有与时俱进,而是深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风靡一时的‘人物性格组合论’的影响,严重地陷入了抽象人性论的误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第368页)这种接地气的论述公正而客观,是可以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产生相应启迪的。诚然,每个文艺创作者的作品虽然各具形态,但是其优劣点也是明显的。熊元义在对这些文艺创作者进行评析时,一方面公正客观分析其优劣得失,另一方面又结合具体文本,刻意抽象出能对当下创作产生启迪的思想、观念以及做法,从而彰显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的引导功能。例如对忽培元的散文就重点强调其对“民族精神的重铸”,因此产生“一股向上牵引的力量”;对刘上洋的散文则强调其“独到的眼光与思辨的力量”,从而“具有感荡心灵的思想力量”;对于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田禾的乡土诗创作,熊元义认为是“没有任何伪饰和美化,而是质朴和袒露的”,而这正折射出当下不少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出现的精神背叛”;对于郑局廷的小说创作,熊元义重点肯定其“有力地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论述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一己之见,但是由于较好地从作品出发,又能与当下的文艺创作实际对接起来,有着明显的地气,从而对现实创作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文艺批评的接地气,也要求批评家走出书斋,走出就作品说作品的狭隘视角,抓住社会热点问题与敏感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得出发人深省的结论。例如旭日阳光一炮走红之后,得到社会的强势关注,有人对其成功的秘诀进行分析,也有人不无担忧其未来发展,虽然各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切中这一文化现象的实质。熊元义认为,精英化道路并不适用于旭日阳刚,因为这“偏离了艺术的真谛”,“旭日阳刚既然成于他俩与基层民众的血肉联系,而衰也只能是他俩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血肉联系”,可以说是点中了当下文艺创作的死穴,既是对当下文艺创作不良倾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今后文艺创作的精辟预言,因此是极具参考性的。又例如,针对新世纪以来大家热议的“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这一问题,熊元义不是简单回答是与否,而是通过社会上是与否的回答来细致剖析其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从而抽象出令人深思的结论:“中国当代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无根’和‘失语’状态在目前愈来愈严重,其症结恐怕就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本来出身社会底层,但是他们不是维护中国基层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抒写中国基层人民的深层苦难,而是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阶级,跻进了异己阶级……”这种结论虽然不能说是高见,但是却是接地气的,有勇气的,彰显了文艺批评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
总体而言,熊元义的《理论反思》以坚实的文艺理论为底气,以敢说真话、实话为勇气,最终能够与文艺创作于文艺批评的底气相接,发挥了较好的社会功能,因为他始终认可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的一句话:“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好的呢?”
(责任编辑:毕光明)
A Review of Xiong Yuanyi’sReflectionsonTheoriesofLiteraryandArtCriticism
ZENG Qing-jiang
(SchoolofLiberalArts,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68-05
作者简介:曾庆江(1976-),男,湖北随州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8
基金项目:2012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国当代文学传播机制研究”(项目编号:HNSK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