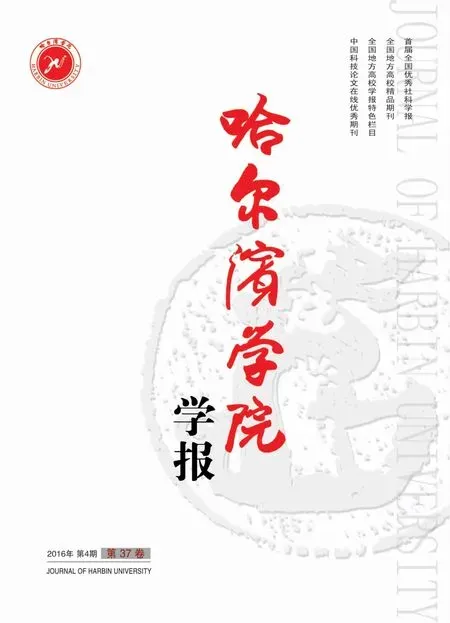唐朝和亲公主的悲剧性研究
2016-03-16陈宁波
陈宁波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唐朝和亲公主的悲剧性研究
陈宁波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
[摘要]和亲在历朝历代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唐王朝同样如此。在唐王朝辉煌的历史与文化中,远嫁的公主们用悲凉的和亲之音演绎了遥远的和亲历程。和亲之功不可磨灭,和亲之悲同样值得思考。和亲公主的悲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与影响。
[关键词]唐朝;和亲公主;悲剧性
一、血泪夹杂的和亲历程
(一)血泪和亲路
唐朝是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同其他王朝一样。和亲也是唐王朝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在唐王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中,曾经有多位公主为了国家的安定而踏上了漫长而又遥远的和亲之路。漫长的历史画卷书写着和亲公主们的贡献与其辛酸的历程。
汉高祖与匈奴大战,被围白登,无奈之下其采用美人计而解白登之围。这也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和亲作为外交工具的先河。和亲虽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民族的团结,但它所牺牲的则是和亲公主的青春年华与独立人格。而和亲的历程也往往是漫长而充满各种艰险的。昭君的事迹至今仍被人所称道,但辉煌事迹的背后却是用艰难困苦堆积而成的。张文琮的《昭君怨》写道:“戎图飞万里,回首望三秦。忽见天上雪,还疑上苑春。玉痕垂泪粉,陇首望沙塵。唯有孤明月,犹能远送人。”[1](P504)在路途中,昭君不断回首,眼泪沾湿了脸上的脂粉。当一切已成定局之时,她感叹道:“唯有孤明月,犹能远送人。”唐太宗时,唐与吐蕃烽烟再起,作为和亲主角的文成公主踏上了其漫长而又充满艰险的和亲历程。
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最终到达遥远的拉萨,她所经历的不仅是路途的遥远,更有自然的艰险与人为的磨难。从藏族人民咏叹的民歌中便能看出文成公主历程的艰辛,“不要怕过宽大的草原,那里有一百匹好马欢迎您!不要怕过高大的雪山,有一百匹驯良的牦牛来欢迎你!不要怕过涉深深的大河,有一百只马头船来欢迎你!”[2](P8)藏族民歌饱含了人民对文成公主的爱戴。但从其内容不难看出其和亲的艰辛历程。李道宗与侯君集于公元635年追击吐谷浑时来过此地,其“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马秣雪。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3](P6226)仅从其中所经历的一段路程便可以想象到其和亲历程之艰辛。
文成公主的泪水见证了其历程的艰辛。《西藏王统记》中写道:“因念唐时遭受诸种留难,遂使公主上下人等,无人服侍,几近一月。公主从人皆出怨言,谓藏地号称俄鬼之乡,真实不虚,饮食服用亦将不继矣,公主闻之心中实难忍受。”[4](P75)在各种艰难困苦中,文成公主以坚韧的性格为大唐的安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文成公主的青春年华最终在唐与吐蕃人民的心中开出了灿烂的花朵。静乐公主和宜芳公主的和亲历程却是短暂而令人惋惜的。出嫁契丹的静乐公主还没有在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便将生命永远的留在了契丹。《资治通鉴》卷215载:“三月,壬申,以上外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嫁契丹李怀节;甥杨氏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宠……九月,癸未……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5](P6864-6868)静乐公主与宜芳公主可以说是唐朝和亲公主中最为短命的两位。她们的生命仅仅在和亲的国家中存在了半年。和亲的路途一定程度来说是一条不归之路,尽管也曾有公主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但回到故土的公主有的也只是落寞的心灵与空虚的躯壳。
(二)悲凉异国音
静乐公主与宜芳公主的死亡,留下的是深深的惋惜与深沉的思考,华丽的和亲仪式背后则是一种血泪夹杂的悲凉旅程。文成公主于贞观十五年(641)[3](P6074)出嫁吐蕃,而卒于永隆元年(680)[3](P6078)文成公主没有子嗣,《西藏王统记》中记载:“彼时汉妃与尼妃俱无子嗣。”[4](P94)母以子贵,而文成公主则是深有体会的。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漫长的四十年最终去世,她心中不仅充满了对故国的思念,而且充满了无尽的孤独感。而弘化公主嫁给了吐谷浑的诺曷钵可汗,吐谷浑的国力在当时是难与吐蕃和大唐相比的,所以当受到吐蕃进攻之时,吐谷浑唯有依附大唐。《新唐书》载:“吐蕃出兵,捣虚,破其众黄河上,诺曷钵不支,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3](P6227)高贵的公主们本是千金之躯,高高在上,但在和亲的旅程上,她们成了一个个远去而又终不得归的悲凉形象。
唐朝和亲公主能够最终回归故土的是极少的,太和公主便是其中的一位。太和公主的一生充满了动荡、无奈、悲凉,她在回纥先后做了三位可汗的可敦,而当黠戛斯攻破回纥后,她便有了回归故土的希望,但不幸的是她又被乌介可汗所劫。此刻她已经不再是唐王朝眼中的和亲使者,而是唐王朝出兵的障碍。“会昌三年(843),回纥大掠云、朔北边,唐武宗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6](P4235)正因如此,当她回归故土时,各种斥责和责备扑面而来。和亲仅仅是阻止战争的一个手段,并非是最好的方法。作为工具的公主,能做的只有在艰险中发挥她们的功用。帝王家的公主本是高贵的,但在和亲的历程中她们却是悲凉而又无可奈何的。李商隐在《马嵬》中写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7](P604)远嫁边塞的公主在异国独居时,更多的是向往平民的生活,因为平民至少能够在故土了此余生。作为太和公主的前任,咸安公主为唐与回纥的发展与稳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白居易诗云:“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1](P4705)咸安公主先后做过几位可汗的可敦,在回纥生活了二十一年后,咸安公主永远的留在了回纥,但她的内心却是对故国充满了无尽的思念。白居易在《祭咸安公主》中写道:“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远陈薄酹,庶鉴悲怀。呜呼!尚飨。”[8](P6961)命虽不在,魂牵故国,在浮沉的一生中,公主们用血泪谱写了赞歌与悲歌两种不同的曲调。
二、多重身份下的命运悲凉
(一)和平友好的使者
唐王朝的和亲公主最为主要的身份便是和平友好的使者。她们身上所承载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了骁勇的大将与善战的军队。
文成公主嫁入吐蕃,不仅维护了唐王朝边疆的稳定,也促进了吐蕃的经济及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作为和平的使者,文成公主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唐王朝获得了吐蕃在军事上的支持,《新唐书》载:“二十二年,右卫率长史王玄策使回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虏。”[3](P6074)而吐蕃则是获得了大唐先进的文化,《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带去吐蕃的物品就有“经史典籍三百六,还有种种金玉饰。诸种食物烹调法,工巧技艺制造术”等。[4](P68)《资治通鉴》卷196载:“其国人皆以赭涂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亦渐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5](P6164-6165)弘化公主与文成公主共同维护唐王朝的稳定。吐蕃与吐谷浑为世仇,两国连年交战。在弘化公主与文成公主的努力下,双方和平交往。一方面稳定了大唐的边疆,另一方面,也是保证了人民的安居乐业。和亲虽然不能长时间的维护唐王朝的边疆稳定,但它却在短时间内发挥了军队难以达到的效果。唐朝诗人胡曾在《汉宫》中写道:“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9](P65)又如汪遵在《昭君》中写道:“猛将谋臣徒自责,娥眉一笑塞尘清。”[9](P64)和亲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战争的发生,为百姓赢得稳定的生活环境。金城公主作为和平的使者,出色的完成了她的使命。在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后,唐与吐蕃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但每次金城公主都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避免了双方更大的损失。《新唐书》载:“金城公主上书求听脩好,且言赞普君臣欲与天子共署誓刻。”[3](P6082)在一次次的调停中,金城公主从两国的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唐蕃两国在赤岭立碑后,双方维持了一定时间的和平。《新唐书》载:“自今二国和好,无相侵暴。”[3](P6085)
然而,作为和平使者的唐朝公主,她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未能完成任务而不被重视,甚至是责备。静乐公主与宜芳公主是中国和亲史上最为悲剧的两位公主,因为她们的生命在和亲后仅存活半年。她们的功绩是难与文成公主等令人敬仰的公主相比的,但她们的努力却是值得肯定的。而她们用鲜血给统治者敲醒了警钟,和亲不是一条坦途,也不是完美处理边疆问题的策略。太和公主因没有完成保证边疆平安无事的任务,而受到了唐武宗的责备。她一生动荡不定,当回到故里时得到的却是无情的责备。《资治通鉴》卷246载:“上遣使赐太和公主衣,命李德裕为书赐公主,略曰:‘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国家……为其国母,足得指挥;若回鹘不能禀告命,则是弃绝姻好。今日以后,不得以姑为词!’”[5](P7968)太和公主任务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让她一人承担实在是不公。由此可见,和亲公主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帝王手中。异国命运悲凉,回国后却也是同样的命运。安化公主从唐王朝答应和亲至其出嫁,前后持续六年之久。而公主的青春年华也在这六年的等待中渐渐散去。
(二)漂泊的异邦国母
当公主们嫁入异国的那一刻起,便由公主的身份转为了异邦的国母。作为异国的国母,她所面对的既有后宫妃嫔的挑战,又有延续子嗣的压力,也有不断漂泊的无奈。
文成公主嫁入吐蕃之时,便受到了赤尊公主的挑战。《西藏王臣记》载:“见文成公主暨从人抵达汉地。于是心生妒嫉,故设障难,使公主与赞普不能相见……于是,举行相见庆会,受享之福,可与天帝相竞。席间,赤尊言曰:‘汉主文成汝,辛苦婚使迎,虽来此藏地,然我先为大’。如是语已。公主言曰:无心作较量,汝言赛谁强,先越户限大,庙堂建湖上。”[10](P26)文成公主用出色的语言艺术与行动回应了赤尊公主,但这也反映了异国国母的生存压力。文成公主很好的处理了与赞普身边的女子关系,但她却没能给松赞干布生育子嗣。《西藏王统记》载:“彼时汉妃与尼妃俱无子嗣。”[4](P94)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彼此相爱,但松赞干布更需要的则是王朝的延续与子嗣的繁盛。文成公主的爱情并没有长久的持续下去,在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最终在孤独与对故国的思念中悲凉的离世。
金城公主虽然为赞普赤德祖赞生有一子,但她与儿子的相认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西藏王统记》载:“汉公主于阳金马年在札玛生产赞普赤松德赞。那囊萨至公主前,伪为亲昵,竟将公主之子夺去,诈言此乃我所生者。公主以乳示之,涕泣哀求,悲伤号呼,仍不授与其子。”[4](P117)金城公主虽最终与自己的儿子相认,但她也是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煎熬。而与儿子没有相处多久,金城公主便永远的与儿子分离。《西藏王统记》载:“殆王子五岁时,母后即逝。”[4](P118)
宁国公主因回纥的丧葬风俗而差点性命难保。《新唐书》载:“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3](P6117)经过一番论争后,宁国公主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但宁国公主也是没有子嗣。《新唐书》载:“后以无子,得还。”[3](P6117)宁国公主回到长安后,最终孤独的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小宁国公主虽有子嗣,但她的两个儿子都被天亲可汗所杀。小宁国公主陷入到失去儿子的苦痛中,在回纥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孤独的死去,她所遭受的是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
公主们嫁入的政权并非是稳定的,因此作为国母的公主们也要做好漂泊的准备。燕郡公主因契丹内部纷争而漂泊,《新唐书》载:“郁于死。弟吐于嗣,与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携公主来奔,封辽阳郡王,留宿卫。”[3](P6170)东华公主则因丈夫被杀而不得不漂泊入唐,寻求庇护。《新唐书》载:“后三年,可突于杀固,立屈烈为王,胁奚众共降突厥,公主走平卢军。”[3](P6171)东光公主夫妇因契丹的强大而不得不离国漂泊。《新唐书》载:“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胁奚众并附突厥,鲁苏不能制,奔榆关,公主奔平卢。”[3](P6175)
(三)悲凉和亲史的抒写者
和亲一方面促进了民族间各方面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和亲双方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公主们在和亲中的悲凉命运以及和亲所起的实际作用也是值得深思的。
和亲对于战争而言只能起到暂时停止的作用,因此当一次次和亲完成后,烽火依旧燃起,剑戟再次出击。刘敬之策解了高祖平成之围,但他的设想却没能实现。《史记·刘敬传》载:“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以无战以渐臣也。”[11](P2719)但汉匈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因为和亲而停止脚步,远嫁的公主们换取的只是短暂和平。吐蕃在松赞干布去世后,便与唐王朝展开了战争,而此时的文成公主却是无能为力,她能做的只有默默的祈祷,最终孤独的在吐蕃香消玉殒,魂归故国。
白居易肯定了咸安公主在和亲中所做的贡献,他在诗中写道:“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1](P4705)但他同样看到了和亲辉煌背后的公主命运的悲凉。因此他在《祭咸安公主》一文中写道:“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远陈薄酹,庶鉴悲怀。呜呼!尚飨。”[8](P6961)在漫长的和亲史上,应该铭记的不仅仅是那些显赫的战功与辉煌的成就,值得深思的是和亲公主们悲凉的命运与悲凉的和亲历程。
三、和亲之音的聆听与思考
关于和亲之音,古往今来都有人在聆听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引发一次次的思考。在对待匈奴问题上,汉朝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而缙绅之儒士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12](P3830)而班固对于和亲之音的聆听则比较客观,思考也比较深刻,“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13](P1374)和亲之策只是国策的组成部分,因此,统治者对于和亲应该慎重和深思熟虑,后世也应该对于和亲之音给予客观的评价。
细君公主在乌孙谱写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心归故乡”[14](P94)的悲凉之音。杜甫在《咏怀古迹》中写道:“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15](P1502)和亲之音中,幽怨之音也是其中重要的音符。杜甫笔下的昭君怨音,更多的是和亲公主们幽怨之音的代表。因咸阳公主之功,白居易写下了“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1](P4705)而在《祭咸安公主文》中他写道:“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远陈薄酹,庶鉴悲怀。”[8](P6961)和亲之功不可忘记,和亲中的悲凉之音更值得深深品味与思考。
[参考文献]
[1]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万绳楠.文成公主[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索南坚赞.刘立千.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司马光.胡三省.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刘煦,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李商隐.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董浩,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鲁歌,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10]五世达赖.刘立千.西藏王臣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1]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3]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王嵘.西域文化的回声[M].新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
[15]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责任编辑:张庆
The Princesses as the Victims of Heqin in Tang Dynasty
CHEN Ning-bo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nzhou 730030,China)
Abstract:To marry princesses to the ruler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d been a very important way for Chinese emperors in all dynasties to exchange frontier peace. Tang Dynasty was no exception. The “heqin” princesses contributed to the gloriou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Tang with their tears and sadness. As we think about the contribution of heqin,the pessimism is also worth considering,which make effect on the later times.
Key words:Tang Dynasty;princess of marriage;tragedy of character
[收稿日期]2015-06-17
[作者简介]陈宁波(1989-),男,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4—0069—04
[中图分类号]I207.22;K2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