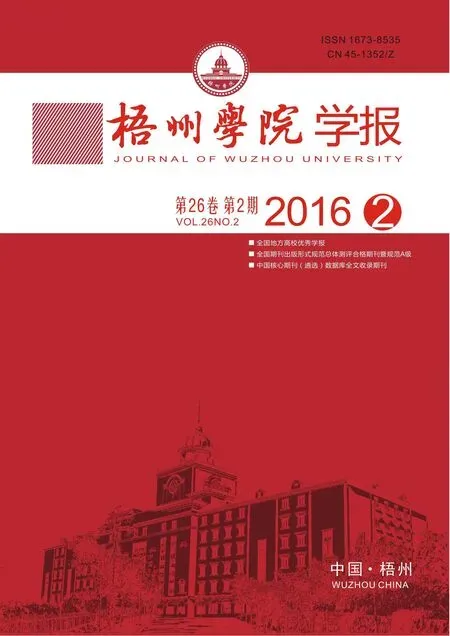互文、反讽视域中的莫言小说《酒国》
2016-03-16徐学斌
徐学斌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互文、反讽视域中的莫言小说《酒国》
徐学斌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国民性批判和现代化追求一直是新文学发展史上相互缠绕的命题,至今不衰。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呈现了一个奇特的寓言化世界,深刻地醒思了“酒国”丑恶的人性、野蛮的“食婴”恶习,以及权利和资本共谋的腐败风气。从互文和反讽视角解读《酒国》,笔者发现小说文本极具寓言性和本体性,浓缩了莫言对于历史和现实、物质和精神、国民性和现代化的多重思考。
[关键词]莫言;《酒国》;互文;反讽;寓言化
1993年《酒国》出版,莫言认为这部小说是“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长篇”,“是我美丽刁蛮的情人。”[1]但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批评界却一片沉寂,并没有引起莫言所预期的反响,“此书出版后无声无息,一向喜欢喋喋不休的评论家全部都沉默了。”[2]2001年,《酒国》荣获“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此书才逐渐得到批评家的重视。究其原因,《酒国》之所以迟迟才得到评价,不仅与其复杂的文本形式、深邃的主题思想有关,还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历史语境息息相关。80年代末期沉闷的文学场域,以及文本触及到的政治腐败问题,愈发让批评界“敏感”,“这部小说是90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评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国内的很多的批评家畏畏缩缩的不敢来评它,就是因为这部小说的锋芒太尖锐,有很多话他们不敢说明白。”[3]所幸的是,20多年过去,创作(作家)和批评(批评家)的话语权愈益走向常态化、多元化和自由化,文本所指与能指在阅读、阐释、接受过程中也不再停留于单一粗暴的批判层面。
细读小说《酒国》,不难发现莫言在形式结构上的用心,人物形象、叙事模式、主题内蕴上的互文共生关系和反讽的寓言化表达,使得荒诞的故事情节充满张力,现实和虚构的缝隙被不断扩大又不断弥合,历史和现实也在支离破碎中得到重整。同时,小说对人性的贪婪和欲望、酒国残忍的“食婴”恶习、官商勾结的腐败风气、野蛮嗜血的劣根性的反讽式刻画,呈现出作者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深刻醒思。
一、互文:叙事的冲突与文本的张力
一切历史内容、精神实质的表达都离不开形式结构的支撑,“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更具有历史性。”[4]《酒国》文本呈现的思想内蕴和历史内容之所以如此纷繁复杂,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它独特的互文结构。
一是文本之内的互文。《酒国》文本交织并行着三个叙事,三者之间互为对照、补充、阐释,构成了互文阅读。叙事一:叙述省侦查员丁钩儿前往酒国市调查肉孩事件的始末。叙事二:叙述李一斗的小说创作。叙事三:叙述酒国酿造大学博士李一斗与作家“莫言”关于文学创作的通信对话。在最后一章,通过“莫言”的酒国访问,则巧妙地弥合三个叙事的缝隙。
颇为吊诡的是,叙事一中作为调查人员的丁钩儿进入酒国“无物之阵”后左奔右突,至死也没有确定“食婴案件”的真实性,而在叙事二中则赤裸裸地近乎自然主义地呈现金元宝卖婴、李一斗岳母烹婴、酒国人食婴的真实细节,酒国人的累累罪行昭然若揭;叙事一中阴险狡诈的无耻政客金刚钻,在叙事二中却是酒国人崇拜的精神偶像;叙事一中因杀婴而内心忏悔以至于精神分裂的李一斗岳母,在叙事二中既是温婉美丽的女性形象,又是残酷的杀婴不眨眼的恶魔形象;叙事一中被丁钩儿妒杀的酒店经理余一尺,最终却复活在作家“莫言”的现实生活中,并和“莫言”相见交谈;至于披着红衣的婴孩,则在三个叙事之间穿插出入,忽而是率众反抗的小妖精,忽而是骑驴独闯为民除害的侠客,忽而成为庸俗丑陋的侏儒余一尺的自称,忽而变为一尺酒店的伙计。三个叙事之间生成的叙事冲突,仿佛一个叙事“圈套”,使得人物面孔变得不可确定,人物形象变得复杂颠倒,人物行为变得荒诞不经。然而正是在这互文性叙述冲突之中,小说的故事情节爆发出一股似真似幻、大开大合的过剩能量,在文本之中故作颠覆,考验着读者的审美和领悟能力。
二是文本之外的互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酒国》文本都关联到诸多的名家作品。文体形式上,对民间传奇、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元小说进行的戏仿,使得小说风格多样,众“体”互生;主题内容上,“潜文本”隐现着纷繁复杂的精神交流和对话,甚至解构与颠覆,使得小说的阅读快感和阐释难度奇妙扭结,众“声”喧哗。这正是莫言“结构就是政治”[5]以及思想“密度”的自觉追求,使文本变得复杂多义,“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5]
在此,笔者试着通过着重分析小说主题内容上的互文来考量《酒国》文本的张力。显然,酒国的“吃人”主题正是对鲁迅“吃人”主题的借用和掘进。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吃人”多被理解为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对自由人性的戕害,而酒国的“吃人”则着意批判利益驱使下人性的残忍、官僚的腐败和权力的异化对于个体人的吞噬。“这部作品里有戏仿,有敬仿,比如对《药》的敬仿……我的本意并不是去说中国有食人现象,而是一种象征,用这个极端的意象,来揭露人性中的丑恶和社会的残酷……作品中对肉孩和婴儿筵席的描写是继承了先贤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继承得好还是坏那是另外的事情,但主观上是在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6]在鲁迅“吃人”主题的关照下,酒国的“吃人”更显出时代况味,在人性“审丑”中走得更远。
除此之外,《酒国》与卡夫卡《城堡》的互文也值得分析。首先是人物形象上,主人公都是孤独的“跋涉者”,行走在孤独的旅程中,摆脱不了欲望的泥淖,个体价值的沦落,幻想着征服世界却被世界征服;他们都是外人进入新的却一成不变的超稳定的异化结构,比如官僚机制、政治结构,要想破坏它是不可能的,其结果都是有去无回。有所区别的是,丁钩儿最先是作为“正义”的化身出现的,其在“权色酒肉”的诱惑下堕落成社会渣滓的遭遇,更凸显出在一个政治理想终结、英雄失势的时代下变革社会的艰辛。其次是共通的隐喻,“酒国”“城堡”都象征着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这样的“酒国”“城堡”,有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一个黑洞一般,任何异质性的因素进入,都会被同化以至消灭。这种神秘的力量,更像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残酷与无情,是为“无极”。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无极”的存在,然而无论人做出怎样的主观行动,命运都不可自控,都无法走出这样的困局。因而,读者看到,丁钩儿左冲右突,依然无法逃脱“便衣”的侦缉(第八章)。同时,处在泛人类意义的高点上俯视丁钩儿和K的遭遇,让我们更能够看清个体人选择的脆弱性和有限性,人的反抗变得可有可无。
二、反讽:历史与现实的寓言化言说
谈及反讽,克尔凯郭尔指出,“想象力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为描绘形形色色的图画保留着无边无际的自由空间;活泼的场景随意攀绕在一起,奇形怪状的线条互相缠绕,构成调皮的笑声,缤纷错杂的穿过松散的织物,讽喻把一般说来极为局限的形状朦朦胧胧地扩展开来,其间讽刺模仿式的玩笑肆无忌惮地把一切颠来倒去。”[7]可以说,这种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酒国》文本世界的写照。莫言通过对酒国“食婴”事件颠来覆去的描绘,对食、色、性夸张缛丽的铺陈,借用民间传奇故事,用冗杂繁复的狂欢性话语,绘声绘色地上演丁钩儿、李一斗、余一尺等人的滑稽戏,叙写着一系列诸如人的生存、社会制度、人类文明等宏大主题,营造了一个荒诞的寓言化世界。这个寓言化世界是在三个交错叙事的时空里展开的,叙事一是作家“莫言”的创作时空,叙事二是虚拟时空,叙事三是“莫言”与李一斗生活的现实(虽然此现实依然是虚构的)时空。假若以“莫言”和李一斗生活的现实性为衡量标准,按照虚构程度对三叙事进行排序的话,笔者姑且得出“虚构性:叙事一>叙事二>叙事三”的结论。然而众多人物的在三个叙事之间的时空“穿越”,制造了真幻难辨的假象,于是,历史陷落,现实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变得暧昧不清,而人性和世界的本质却在混沌中崭露头角。无怪乎,张旭东认为,“在莫言的世界中,现象的世界(the phenomenological reality)很少得到再现,而是被‘形式——叙述’空间所吞没,并由一种无情的虚构逻辑转化为寓言性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颠倒的反而成为真实的。”[8]
在这种颠倒的叙述中,莫言往往把“真假美丑崇高鄙陋”的事物并置,反差对照达到反讽式观照的效果。动物的反刍、肛肠的蠕动、令人作呕的腐败、背景的阴沉晦暗等描述常常倾泻笔端,间或也有人性温情和社会和谐的流露,然而总体给人以末日腐烂颓败的气息——道德堕落,精神沉沦。“但小说对严肃性内容的讲述和表达,却并非疾言厉色的控诉与批判,而是凭借一种立足于民间伦理的欢乐力量对抗着强大的体制话语和政治伦理。裹挟着反讽、诙谐、幽默等民间性因素的叙述语流,喷薄而出,难以遏制,庄严、肃穆、神圣、崇高崩裂成荒诞、怪异的碎片,七零八落,不成阵势。”[9]某种程度上说,莫言正是用反讽式、狂欢化的“叙述语流”来摆脱主流话语的宰制。读者可以看到,李一斗对酒国驴街“美味”的描述就充满了这种“反讽、诙谐、幽默”的“叙述语流”,通过冗长的、高昂的、颂词般的话语堆砌与挤压来解构他的整个话语体系:
这几年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要吃肉提高人种质量,驴街又大大繁荣。“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驴肉香、驴肉美、驴肉是人间美味。读者看官,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三揩油喂了麻汁”,“蜜斯特蜜斯”,什么“吃在广州”,纯属造谣惑众!听我说,说什么?说说咱酒国的名吃,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请多多包涵。站在驴街,放眼酒国,真正是美吃如云,目不暇接:驴街杀驴,鹿街杀鹿,牛街宰牛,羊巷宰羊,猪厂杀猪马胡同杀马,狗集猫市杀狗宰猫……数不胜数,令人心烦意乱唇干舌燥,总之,举凡山珍海味飞禽走兽鱼鳞虫介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在咱酒国都能吃到。外地有的咱有,外地没有的咱还有。不但有而且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最了不起的是有特色有风格有历史有传统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听起来好像吹牛皮实际不是吹牛皮。在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致富高潮中,咱酒国市领导人独具慧眼、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道路[10]135。
显然,这种“叙述语流”表面上高尚、振奋人心,实际上却充斥着无尽的野蛮和虚弱,在陈词滥调、胡言乱语中,一切庄重崇高都变得虚假怪异。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反讽有意地回避和丑陋的现实针锋相对,而用“调皮的笑声”来调和激愤和不满,以反讽之“轻”对抗现实之“重”,乃至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意图博取读者的会意。因此,文本中繁冗甚或累赘的空话、套话、废话、口号、叫嚣形成的话语狂欢,主体形象被颠覆,历史与现实被解构,主观情感被夸大,在醉话连篇中却看到事实真相,在无尽戏谑里却看出人性残忍,在浑浊不清中却看到价值判断。在“假大空”的陈词滥调中,过剩的能量溢出,游离了主流话语。这种言说的“失败”,却正彰显出话语的剩余价值。它撕裂了历史的缝隙,揭开了现实的伪装:话语的繁衍成为反讽的开始,最终抵达寓言化的想象与言说。正如李一斗的信里所说:“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我的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10]54-55在这样的一个话语幻景中,那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面繁荣掩盖之下的欲望、功利、诱惑、残忍、淫荡、贿赂、阴谋、野蛮、颓废、沉沦倾巢出动,在一个依“法”办事、心照不宣的世界里极尽狂欢。在这里,所谓的“英雄”(丁钩儿)死了,真正的“渣滓”(余一尺、金刚钻一流)却还活着,尚留着凡庸市侩的大众(李一斗、“莫言”)在苟活,光明和希望也一齐葬送在“大茅坑”里,“那里稀汤薄水地发酵着酒国人呕出来的酒肉和屙出来的酒肉,漂浮着一些鼓胀的避孕套等等一切可以想象的脏东西。那里是各种病毒、细菌、微生物生长的乐土,是苍蝇的天国、生蛆的乐园”[10]309,就连同“抗议”也被活埋。
作为故事的“看客”,读者看到的人物几乎都带着神经质的癫狂。丁钩儿到最后直接成了神经错乱的疯子;其他如女司机的阴晴不定的话语;肉孩首领的阴鸷的目光;余一尺时静时怒、亢奋的叫嚣;袁双鱼对酒的执迷;唯一的带着一线光明的美丽女性——李一斗的岳母——也被折磨成疯子。一个个疯狂的人物,演绎的正是一个令人疯狂的世界。虽则每个人都在承受着无法言喻的压抑,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反抗成功,最终都沦为无助的个体,难以获得拯救。在猿酒节将要开幕的狂欢前夕,读者却见证着丁钩儿的死亡——狂欢和死亡同在,热闹和冷寂并存,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效应。他的死亡,是否寓示着英雄的瓦解、没落和世俗欲望的胜利?是否意味着拥有反抗因子的个体最终都向无孔不入的欲望诱惑和压抑人性的官僚机器屈服?是否揭示出纵酒以及滥酒文化作为万恶的渊薮对人性和道德的戕害?是否在检点社会上盛行的丑陋饮食文化与尚未褪尽的嗜血根性?是否在忧虑着人性沦丧的道德危机和共同体坍塌的社会困境?是否在反思着国民性重造的艰辛和现代化追求的曲折?作者真实的复杂的意图,任何读者可能都一言难尽。但正如文本所营造的寓言化的荒诞世界所指涉的那样:历史在晦暗的背景中失落,英雄不复存在,群魔则登台狂欢乱舞;现实在颠倒的话语中混沌不清,个体历经人格分裂式的阵痛,犹疑不决的价值判断跟随着金钱和欲望狼奔豕突。也正是在这历史的陷落和现实的混沌中,作者反讽的触角延伸到了当今社会和官场的诸多丑恶现象。
三、醒思:国民性批判与现代化追求
个体的生命是生活,社会的生命是历史,某种程度上说,两者分别对应着国民性批判与现代化追求的主题。如果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现场,中国刚从“文革”的历史创伤中走出不久,“改革开放”的篇章已然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作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地改写着个体生活和社会历史。与此同时,个体价值和历史理性却被市场经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诸种意识形态所召唤,被抛出了既定的历史轨道。在追求现代化的宏大命题的指引之下,前所未有的欲望和能力被释放出来,社会面临着道德滑坡、人性沦丧的精神危机。许多学者都对此有过讨论,刘再复认为:“中国社会产生了千年之裂变: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开始了一个被称作‘现代化’也可称为‘全球化’的急速城市化历史裂变时期。国家精英转入城市,工商业空前兴盛,整个时代的主题是‘发展’两字。但是‘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则是‘道德’的崩溃。”[11]《酒国》指涉的官僚腐败、人性贪婪与权钱合谋,正是面对时代“发展”逻辑背后“道德”崩溃的社会现象,恰如其时地在“寻根”之后作出的深刻省思。
面对时代创伤和弊病,莫言反讽的超脱不同于禅宗的超脱,它游戏历史,戏谑现实,却并不消灭历史,无视现实。反讽的逻辑背后始终有一个“我”,这个“我”解构一切表层的、深沉的、生理的、精神的现象,突入到附着在个体上的“国民性”和附着在社会上的“现代化”的“病症”里,以寻找改造个体生命、变革社会进程的契机。如果回溯从《红高粱》到《酒国》的创作脉络,莫言关于“纯种”理念的探讨就一直缠绕着国民性批判与现代化追求这两大主题。只是,《红高粱》展现的原始野性、蓬勃生命力的本色英雄到了《酒国》这里却彻底蜕化萎缩成欲望横流的酒囊饭袋。如此,烈士陵园的老革命对于丁钩儿的鄙视就不足为奇,“瞧你这点出息……我们播下了虎狼种,收获了一群鼻涕虫。”[10]235如果再把对比的视野扩展到90年代初的“颓废”批判和“欲望”书写,那么同时期的社会颓废、历史堕落和精神沉沦就被烛照得更为清晰,贾平凹的伪古典爱情《废都》(1993年)与梁晓声的政治寓言小说《浮城》(1992年),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只是《酒国》严肃的批判理性更带着含混的表达方式,它依然在形式上成为“先锋小说”,有着深沉的末日气息和伤感格调,但却没有彻底地沉溺于历史的虚无而指向无意义的狂欢,“英雄”无法逃避悲剧结尾却依然喊出了一声:“我要抗议……”这可能是肉体走向毁灭发出的无奈心声,却也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那就是重建历史的激情和渴望。这一声音被鲁迅、巴金那代学人彷徨呐喊了许久,至今还未中断,文学的启蒙和反抗的幽魂依然游荡在历史的天空。
莫言正是借助文学的形式对历史、现实、道德、文化和文学的整体性颓败多方出击,喷涌、宣泄着不可抑制的愤怒——即使这样的反抗又有着挥之不去的历史挫败感和虚无感。这让我们想到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沉痛和感叹,对《酒国》的价值判断在认同与审视之间举棋不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指出“国民性”的全部,给出完整的“现代化”的方案,在一个历史终结、“后”学盛行的时代,回避未来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因而,《酒国》只能走向混沌和终结,假使我们能看到绝望者背后哪怕渺若微芒的希望,能洞见沉沦者哪怕一丝丝的抗争,能觉察暴虐者哪怕偶有的人性复苏,那么它的历史也必然不会如此残酷无情,让见证者也难以安心——
在国民性重造、现代化追求的道路上,“我要抗议……”这是反抗的开始,它从未停止,更不会终结。
参考文献:
[1]莫言.我变成了小说的奴隶[N].文学报,2000-03-23(3).
[2]莫言.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M]∥莫言.莫言讲演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26.
[3]莫言.我的文学经验——2007年12月在山东理工大学的讲演[M]∥莫言.莫言讲演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63.
[4]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282-283.
[5]莫言.捍卫长篇小说而尊严——代序言[M]∥莫言.酒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6]姜异新.莫言孙郁对话录[J].鲁迅研究月刊,2012(10).
[7](丹)克尔凯郭尔.论反讽的概念[M].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47.
[8]张旭东.“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莫言《酒国》中的语言游戏、自然史与社会寓言[J].学术前沿,2012(14).
[9]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从《狂人日记》到《酒国》[J].文艺研究,2014(4).
[10]莫言.酒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1]刘再复.“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酒国》、《受活》、《兄弟》三部小说的批判指向[J].当代作家评论,2011(6).
(责任编辑:孔文静)
On Mo Yan’s The Republic of Wine from thePerspective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Irony
Xu Xueb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Up to now, national-charactered criticism and modern pursuit have always been a intertwine pro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Mo Yan's novel, The Republic of Wine, presents a peculiar and allegorical world, thinks profoundly about the ugly humanity and the savage habits of “eating babies”, as well as the corruption ethos due to the collusion of power and capital. By interpreting this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irony,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literary text of this novel is fully embodied with the nature of allegory and ontology, which consists of Mo Yan's multiple thoughts about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material and spirit, the national-charactered criticism and modern pursuit.
Key words:Mo Yan; The Republic of Wine; Intertextuality; Irony; Allegorical.
收稿日期:2016-01-11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35(2016)02-0043-06
[作者简介]徐学斌(1993-),男,江西赣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