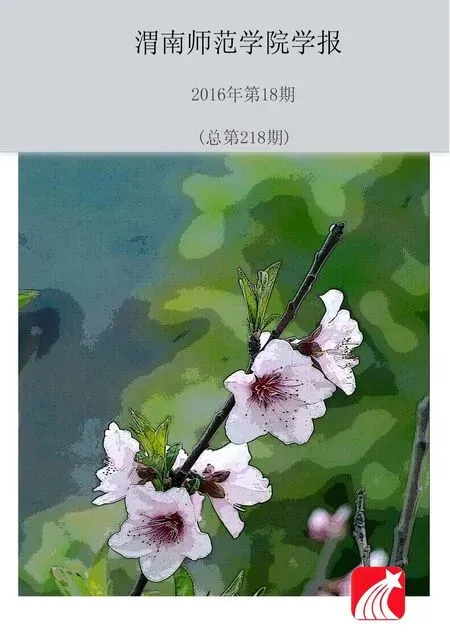从传播到传真的接力与博弈:《史记》外文译本述评
2016-03-16高风平
高 风 平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研究】
从传播到传真的接力与博弈:《史记》外文译本述评
高 风 平
(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随着“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典籍译介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势头不俗。《史记》既是一部中国历史的不朽巨著,也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旷世经典,集史学研究价值与文学艺术价值于一身,是人类文明的精髓与财富。文字记载的简捷性、语言风格的艺术性和叙事结构的独特性构成《史记》的重要文本特性,也是对外译介过程中译者必须谨慎处理的元素,译者常常因为不得不游走于忠于原著与迎合读者之间而陷入两难境遇。因此,对现存译本的对比性探析和客观理性分析对《史记》翻译或新译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导向功能。
《史记》;翻译策略;杨宪益;华兹生;倪豪士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发展的异军突起,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渐提升,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多地走入国际视野,并开始引起世界瞩目。中国“文化走出去”迎来了不可多得的大好机遇 。加大对外宣传中国异彩纷呈的历史和文化的力度,让世界尽快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当今国际形势的迫切需求。[1]要做好中国历史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讲好中国故事”,自然离不开典籍译介,如何对承载着浓郁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的典籍进行合理译介,探索一条既利于有效传播,又保障忠实再现的途径,是摆在广大翻译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中国典籍的代表作品和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是《二十四史》,了解中国历史从了解《二十四史》开始。《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个朝代所编撰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等 。[2]
《二十四史》源起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550年)至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计3 213卷,约4 000万字,编写体例为本纪、列传两种纪传体。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著作《史记》。《史记》共130篇,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总计52万余字。《史记》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开篇,直至汉武帝天汉年间,跨越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文化等领域,内容丰富详实,可谓包罗万象,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同样重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首创了“纪传体”。这是一种新的史学编纂模式,被历代史家所推崇并沿用,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其《通志》中曾赞誉道:“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3]鲁迅先生也曾不禁慨叹,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4]。
《史记》既是一部中国历史巨著,也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不朽之作,集史学研究价值与文学艺术价值于一身。文字记载的简捷性、语言风格的艺术性和叙事结构的独特性构成《史记》对外译介中必须谨慎处理的重要特性,也是常常将译者推向两难境遇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这一特殊文本的相关翻译研究意义重大,且在一定程度上将拓展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维度。
自1872年以来,不同国家的汉学家或译者曾经陆续尝试翻译《史记》《汉书》《左传》等,但多为节译或选译,也仅占全套《二十四史》文本的很小比例。 概括起来,其中英译本为:《左传》全译本,《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节译本,以及《晋书》《隋书》《三国志》等史籍中某些篇章的英译本。可与西方经典相媲美的《史记》 英文全译工程虽已启动,但仍处于期待之中。[5]
随着“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典籍英译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展势头不俗。目前尽管《史记》已有多个外文译本,但全译本仍在期待中。因而,对《史记》进行翻译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梳理、分析、比较和研究探索,将对《史记》及同类文本的翻译起到指导作用。同时,对现存译本的横向对比、纵向对比、中外译本对比以及相关的深度探究与求证,将对史记翻译或新译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引领功能。
二、史记译介的诉求与现状
(一)《史记》译介的诉求
1.传真中国文化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流传下来的史书典籍存量巨大。然而,由于中西方史学思想和传统的差异,西方世界对中国史学一直存有偏见,甚至误解。一些史学大家曾经将中国史学定义为“原始的史学”,这种轻视和鄙夷的态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将中华文明作为历史研究对象兴趣索然,不置可否。所以即使在当代,也有很多国外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或只知皮毛,或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这种管中窥豹的现状使西方世界一些对中国史学孤陋寡闻、闭门谢客的学者依旧无法跨越无视或慢待中国史学的怪圈,从而无缘接触、欣赏到传统中国社会的精彩和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精髓。如此戴着有色眼镜的史学研究注定了其局限性和片面性。
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全书展示了黄帝以来中国古代社会近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和数十个王朝的兴衰轨迹,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正统观念与时代精神,它是研究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古代文化最具权威性的资料宝库。不读《二十四史》,何谈研究中国历史。所以中国历史文化“走出去”,必须高度重视《二十四史》的全面译介,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
中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以其迅猛的发展态势走进了国际视野,中国历史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外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专家学者,也包括普通百姓,开始对承载了绚丽多姿的中华文明的《二十四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汉学家德效骞曾由衷地说:世界上最大的历史资料库可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找到。对于今天的汉学家来说,《二十四史》翻译是汉学界最为宏大,而又最为令人期待的工作。[6]为了让各国史学家对人类文明主要发源地的东亚有更全面、客观的了解和认识,进而架构理性、真实、科学的“全球史”,《二十四史》整体英译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国外汉学、史学界翘首以盼的工程,也是中国译界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开篇,《二十四史》整体英译必然始于《史记》英译,一个公正、忠实、权威、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兼具的《史记》全译本必须紧急列入我们的近期目标,从而为后续典籍译介扫除障碍,并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因为,无论是刻意模仿还是潜移默化的隐性影响,先入为主的《史记》外译本都将很可能成为绕不开的模板,从而有意无意中成为《二十四史》英译的范本。故无论是对《史记》译介的严谨缜密的实践态度、合理求真的策略定位,还是对现存外译本的梳理、求证、科学评价和理性分析,不仅意义重大,而且迫在眉睫。它将直接影响到同类译本的策略走向、文本风格和传播成效。
2.扭转文化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满足国人打开窗户看世界的需求,大量有关异域文化,特别是西方历史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史学著作的汉译本大量涌现,有效填补了国人对异域文化的认知缺失,加深了了解程度,在某些层面甚至可以说几乎达到了大众化普及。比如,中国人通过汉语译本,对国外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基本达到了通盘的了解,一些重要事件几乎妇孺皆知,一些研究成果甚至超过了目的语本土国家或地区的专家学者。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化,包括史学著作“走出去”的程度却相对滞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历史仍然知之甚少,感觉遥远而陌生,更谈不上家喻户晓。如,中国传统史学著作、现当代史学著作,能够译成外语“走出去”的可谓屈指可数,中国本土译者领衔的大型典籍译介项目更是凤毛麟角,出现了严重不对称现象。这种局面导致的后果是,国人对外国史学的认识与外国人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出现严重的失衡状态。 要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就必须疏通渠道,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这样才能为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领域争得实至名归的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更是广大本土翻译工作者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周一平教授曾呼吁:要把中国的《二十四史》尽快英译推向世界,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史书,让全世界史学家了解中国的史书,这不仅有助于让全世界人民、全世界史学家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有助于“全球史”的编纂,也有助于全世界人民、全世界史学家全面了解什么是历史记载、什么是史书、什么是史学,从而推动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7]
(二)《史记》译介面临的困难
1.底本理解的分歧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语言之一,两种语言都是联合国工作语言,在当今“中国热”日渐盛行的环境下,汉语和英语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可谓平分秋色。但两种语言差异巨大。中国人的祖先居住在亚洲东部北温带,气候相对温和,少有飓风、台风、海啸那样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半封闭的大陆型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他们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心理文化必然会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中,以意统形,强调意义的连贯,但不看重形式标记,形成了“意和”句法特征和“隐性”语法特征。汉语为高语境文化,在语境轴上仅次于日本,几乎处于语境依赖的最高点,表现为词语意思的确定强烈依赖语境,信息传递主要靠心领神会,重意会而轻言传。表述中用词好重复,青睐简单句,不排斥流水式句式,多用以人称为主语的主动句;而英国人的祖先主要生活在海岸区域,年复一年受到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侵扰,自然灾害不可预测,人与自然力量悬殊,长此以往,人们形成了冷静、理性的思维习惯。善于观察自然,分析自然,了解自然,从而适应或控制自然。如此心理文化表现在语言中形成了英语的“显性”语法特征和“形和”的句法特征。语序自由、构词灵活,句子结构层次弹性很大,常常跳跃式处理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 英语用词以替代规避重复,善用复合句,被动语态使用频率很高,常用物称作主语。[8]
汉语和英语这些心理文化影响下的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差异形成汉译英过程中的重重障碍,译者必须处处谨慎,充分调动各种知识储备,认真查阅求证,方能准确揣测、理解源语文本作者意图。正确的翻译是建立在准确理解基础上的,理解是翻译的前提。而汉语的文言文本是一种浓缩式简捷概括表述风格,个中解读、理解之困难可想而知。正如郭著章所说,文言虽和白话一样也是汉语,但在阅读文言时,就连文言方面的专家有时也会感到棘手。因此查证所译文言的意思,应该是翻译文言的首要环节。[9]1
语言高度概括、凝练,是汉语文言文本的重要特征。司马迁《史记》为文言文本,其中既有浅显易懂、一目了然的章节,也有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的语句,容易产生歧义或误读,那么误译也必定在所难免。
所谓误译主要有两类,即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语言层面产生的误译主要由汉英语言的结构差异、文言与白话的错位对接,以及汉语内部的隐性因素或语义演变导致;文化层面的误译则是由两种文化的心理程序差异、思维方式差异或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但对于《史记》而言,除了来自语言和文化层面的误译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困难——因为译者选择了不同的底本而造成理解差异,从而导致误译。而且这种误译对于译者来说是很难察觉的。如果不对相关平行文本作深入细致的筛查式研究和专业化、学术性求证或论证,要意识到此类误译几乎毫无机会。而这样的研究、求证工程浩大,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耗时耗力,开展起来谈何容易。如:
(1)华兹生与《史记》翻译
美国著名翻译家华兹生选择的底本为1934年东京出版的由泷川资言注解的《史记会注考证》,同时也参考了百衲本《史记》及《汉书》中对应的章节。
华兹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启动《史记》英译项目。华译《史记》是基于战后美国文化构建工程的需要,以文学资源的功能进入美国社会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工程之子项目,卡耐基基金会资助了此项目,并要求译本要面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将其定义为普及性经典文学读物。
华兹生在日本花了3年多时间完成了《史记》的选译。受到当时国际环境所限,他没有机会获取中国本土和欧洲大陆的相关研究资料。他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打算在《史记》的歧义考证上有所突破,而“只是按照中国及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对《史记》的一般性理解”解读、翻译了《史记》。[10]因此华译《史记》版本中既有源于他个人解读、查证失误导致的误译,也有因忽略了歧义考证环节而导致的“重蹈覆辙”式误译。
另外,华兹生不仅刻意省略了对秦朝和秦朝以前历史的英译,而且回避了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论题的讨论。华兹生为了“可读性”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忠实性”,引来众多汉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华译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应有的“学术性”。但同时大家对华兹生在《史记》研究和英译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也予以充分肯定。
(2)倪豪士与《史记》翻译
同为美国汉学家的倪豪士和其团队是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启动《史记》英译项目的,主要底本为中华书局1959年和1982年版《史记》,也参考了监本和百衲本《史记》,以及中国台湾王叔岷、日本泷川资言等的译文或相关研究和评述。这是美国的第二次大规模《史记》英译,也可以说是《史记》新译,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倪豪士博士担纲,台湾文建会资助了这次《史记》新译。该项目运行3年之后,又陆续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等给予的各种资助。
1994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倪豪士主编,郑再发、吕宗力、倪豪士、罗伯特·雷诺兹等英译的《史记》第1卷《史记·汉以前的本纪》(TheGrandScribe’sRecords:Vol.1TheBasicAnnalsofPre-Han.China),以及第7卷《史记·汉以前的列传》(Vol.7TheMemoirsofPre.HanChina)。2002年和2006年,该社又出版了倪豪士等英译的《史记》第2卷《史记·汉本纪》(Vol.2TheBasicAnnalsofHanChina),及第5卷(上册)《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GrandScribe’sRecords:TheHereditaryHousesofPre-HanChina,PartI)。
倪豪士团队阵容强大,资金丰厚,目标宏伟,工程浩大,旨在全译《史记》,将主要读者对象定位为国外汉学、史学专家学者,要求尽量做到忠实原文,注解详细,可读性强,前后连贯,且具有专业学术价值。倪译《史记》 属于协同式集体合作运作项目,同时还获得很多中外《史记》研究专家学者的大力帮助、指点和引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兆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吴树平以及西方汉学家吉德炜、顾传习、韩禄伯、鲁惟一(M.Loewe)、班大为、高德耀、梅维恒等都提出过建设性的宝贵意见。[11]
倪豪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均远优于华兹生,他的资源优势得以让他具备审慎考证、多方查询的条件,因此他对底本的解读相对更为精准,误译相对较少。
(3)杨宪益与《史记》翻译
我国翻译大家杨宪益早年留学欧洲,1941年携夫人戴乃迭回国。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拿来主义盛行,西方著作汉译本甚嚣尘上,而中国本土著作外译本却寥寥无几。1952年,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刘尊棋向归国不久的杨宪益夫妇谈到了一个要译介古典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把中国的文化推进国际视野、加速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宏伟计划,这次谈话鼓舞了杨宪益夫妇,于是他们立即付诸行动,陆续推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译作。随后《史记选》英译很快提上议程 ,他们共选译了18卷,其中包括本纪1卷、世家3卷和列传14卷,主要为文学性和艺术性较高的篇章。[12]
作为本土译者,杨宪益无论是在底本资料资源,还是相关平行参阅、研究资料的资源占有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不但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更便捷的信息渠道,而且可获取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总体而言,杨译本对《史记》的解读更权威、精确,语言再现更贴切、忠实,信度更高,更注重原汁原味的传真效果。
以上这些《史记》英译项目可谓实力雄厚,阵容强大,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能完全规避误译。所以,典籍翻译一定要选择学术界认可度高的权威底本,同时查阅、研究相关平行文本资料和学术研究资料,参阅求证,严谨求真,才能做出信度高、有学术价值的译本。
而在文本新译时,要认真查证已有译法是否达意;比较同一句子的不同处理方法;敏锐发现、捕捉那些形神兼备的经典美译,兼收并蓄,灵活变通,既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精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提升,进而让新译本得到升华。
2.策略选择的分歧
长期以来,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都曾尝试翻译《史记》,希望中国的文化精髓能够走进国际视野,使不同文化间能够更好地分享、互动和交流。尽管如此,直至20世纪50年代,《史记》翻译始终没有出现真正可称为成规模的项目, 在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并不理想。20世纪50年代,几乎是同期启动的中国译界巨匠杨宪益夫妇的《史记》英译和美国学者伯顿·华兹生的英译本可谓开疆拓土之作,成为《史记》英译的里程碑。至此国内外各种节译、选译作品不断呈现,但这些译作除了规模不同、篇幅各异之外,语言风格也各具特色。翻译策略的迥然不同可能导致译语读者的解读困惑,有时甚至可能引起误解。
翻译作品的最终呈现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主要包括源语文本类型、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翻译主体对源语文本的态度、翻译主体的翻译目的以及译语读者的需求期待等。翻译是选择的艺术。 翻译既要忠于作者意图,又需迎合读者诉求,加之源语和译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两难选择。译者常常纠结于是更多地关照读者“舒适度”,尽量将源语文化纳入译文读者熟知的知识范围和文化价值观背景,让作者意图迁就读者期待,即采用归化策略,还是更多地坚守原作的“异质性”,尽量传真源语语言文化的原汁原味,让读者努力靠近作者,即采用异化策略。
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包括译者的主观因素,也包括文化差异、社会环境、国际局势及文本类型等客观因素 。
同时,译者主体性也会影响到策略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影响译文最终如何呈现的根本性因素。而且,当关注不同的读者群体、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且受制于不同的时代或社会环境时,译者主体性又往往会随之表现出动态变化,导致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可能会对同一源语文本有不同的阐释。同时译者主体性也会受到一些偶然性、突发性因素的影响,所以翻译界有一种普遍共识,即“只有永恒的原作,没有永恒的译作”。
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关乎译本的归宿,不同的策略成就不同的译本效果,这也是我们现存史记译本风格迥异的原因。不同的源语文本类型、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环境,面对不同层次的译语读者和读者需求,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译者会选择迥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即便是同一译者针对同一源语文本,当其他因素发生改变时,也可能重新定位策略选择和文本处理方式,因此也产生了旧本新译的必要性。况且语言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有时仅仅是出于与变化中的语言与时俱进的需要,译本也是要不断修订,甚至是推翻重译的。
翻译策略选择影响因子的复杂性,导致《史记》译本翻译策略和语言风格的多样性,强制性的策略统一不可能,也不合理。但是文本风格差异太大无疑会导致译语读者的困惑,而要找到一种两全之策又谈何容易。
三、现存《史记》外译本概况
(一)《史记》不同语种译本
1.《史记》的东亚译本
《史记》在东亚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在《史记》传播过程中,天然的地理优势,使他们对《史记》的研究和翻译更为关注和深入。
2.《史记》的德文译本
1.2.1 教学方法 针对《儿童护理学》中“住院儿童的护理”章节采用PBL案例教学法,教师以临床病例为引导,提出问题。课前一周将病例相关资料发给护生,护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图书馆、网络等方式查阅相关资料,寻求问题答案;课堂上护生讨论,对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最后由教师归纳点评。学期结束后采用CTDI-CV评价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
19世纪中期,奥地利汉学家先驱菲茨迈耶将《史记》24卷译成德语,发表于《维也纳科学院会议报告》,这是《史记》的最早德文译本 。1951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尼诗发表了《公元前209年陈涉起义》的德文译文;1962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战国时代的出现:司马迁〈史记〉译文》,包括《史记》卷75至78,被《东方文化论丛》收录;1965年,其译著《信陵君:〈战国策〉和〈史记〉中的记载》由斯图加特、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 包括《史记》卷70、77、87和88。1956年,《史记》研究名家弗雷兹·杰格的《史记》卷82德译本被莱比锡《中日研究:安德烈·韦德迈尔诞生80周年纪念文集》收录。
3.《史记》的法文译本
在法国,最早大规模译介《史记》的是汉学家沙畹博士。1889年,沙畹随法国使团来到北京,得益于清末驻法使馆参赞唐复礼的帮助,来华一年后即完成 《史记·封禅书》法文译本,由北京北堂图书馆出版。1895—1905年期间,沙畹译注的 5卷本《史记》译本由巴黎拉鲁斯出版社出版,包括《史记》卷1至47 。 1969年,巴黎梅森内夫出版社再版沙畹的《史记》译本时,增加了1卷,新版译本涵盖《史记》卷1至52,收入了沙畹去世后留下的3篇译文——《史记》卷48、49、50,以及康德谟翻译的第51、52卷,还附有戴密微撰写的导言,1个总索引和1个由鲍格洛撰写的自1905年以来的《〈史记〉译文目录》。该书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沙畹尚未注解的《史记》法译初稿,现存于法国纪梅博物馆。
1972年,巴黎法兰西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吴德明的《〈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译注》,该译本附有整套专业性注释、书目、索引及泷川资言注解的《史记会注考证》的汉语原文和注释,是公认的面向专家的学术性译介与研究的翻译典范,注重不同释义的对比、考证,吸收了中国传统注疏、文学和语文学研究的成果。译风严谨,译语华贵,措辞缜密,既有优美的旋律感,又具浓郁的诗歌美,被《法国高等汉学研究所文丛》收录。[13]
4.《史记》的主要英译本
在《史记》外译本中,英译本是最全面且普及程度最高的译本。
20世纪50年代,美国汉学家华兹生在其著作《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的第二章中,翻译了史记中的主要章节内容,用流畅自然的语言风格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成为古老中国的史学文化和英语西方世界读者之间的纽带。
还有几乎与华译本同期且影响力较大的是我国杨宪益先生的英译本,这位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与夫人戴乃迭以“中西合璧”、强强联手的组合形式,合作完成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典籍的英译。其《史记》译本可谓现有《史记》译本中的经典,并被《大中华文库》收录 。
还有一位译坛重将是美国的倪豪士,倪译本《史记》,以严谨、细腻、学术性强著称,主要针对专家学者类读者群体,同时也注重可读性。
《史记》的其他英译版本还包括:艾伦于1894年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上发表的 《史记卷1:五帝的起源》和于1895年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上发表的 《殷朝》。1917年,夏德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发表了《张骞的故事,中国在西亚的开拓者:〈史记〉卷123英译》。1947年,德弗朗西斯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了《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英译本。1962年,鲁道在《远东》上发表了《史记·伍子胥传》的译文。1974年,英国爱丁堡南边出版社出版了杜为廉和约翰·司考特合作编译的《司马迁笔下的军阀及其他人物》。1994年,牛津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雷蒙·道森译注的《司马迁〈史记〉》,该译本被“世界经典系列丛书”收录。[14]
(二)《史记》主要英译本比较
1.华译本:以普及为目的的迎合
美国曾启动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史记》英译项目。分别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华兹生《史记》选译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运作的倪豪士团队《史记》全译。两者无论是在底本选择、读者对象、对底本的解读、研究资料的来源和可供查阅求证的平行文本资源占有量上,还是在语言文化差异、文本叙事结构的具体处理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华译本主要针对普通读者,强调可读性和接受度,为了保证译本通俗易懂,华兹生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注释和介绍性材料,回避了当时美国读者感觉陌生的专业术语和人物称号,替换了对于叙事意义影响不大的汉语度量衡单位。同一人物的姓名、头衔始终锁定同一形式(刘邦是唯一的例外)。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提升可读性,华译《史记》有时甚至以牺牲严格意义上的忠实性为代价。显然,华译《史记》的侧重点在于《史记》的文学价值。华译本在叙事结构上也做了大尺度调整,与原司马迁《史记》相去甚远。
因为西方史学沿袭了古希腊罗马的叙事风格,严格按照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编排叙事顺序,而且习惯于加入个人观点。 为了迎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和文本期待,华兹生按照典型的西方历史的叙事结构模式,调整了《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的体例,并根据历史事件推进、发展的自然进程,重新排列了人物的出场顺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易读易懂的译本对读者的吸引力远大于那些较多保留异质文化特点,给读者带来陌生感的译本,归化策略无疑会增加译本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
尽管华兹生的策略选择受到他所处时代特点的限制,但彼时彼地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他刻意迎合读者的做法既达到了尽量占有更多读者群体的目的,也保障了他的主要赞助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创收计划。
另一方面,尽管华译本在对《史记》的忠实性上打了折扣,但无疑也开启了《史记》大范围走近西方普通民众的先河。没有华兹生煞费苦心的引荐和不遗余力争取到的基础读者群,《史记》在西方世界的认知度不会如此快速提升。可以说,是华译本为后来倪豪士重译《史记》奠定了基础,也为他选择新的译介策略做了很好的铺垫和准备。正是因为有了华兹生这样的巨人肩膀,倪译本才可能有今天的高起点,所以,华译本在《史记》推介的进程中可谓功不可没。
2.倪译本:基于学术性的全译尝试
倪豪士是受到华译本的启发和影响才萌发了重译《史记》的想法,他是华兹生的忠实读者和铁杆粉丝。他坦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新一代《史记》学者就是受到了华译《史记》的影响而开始他们的研究的。倪豪士的设想是:采用与华译不同的翻译策略——异化为主;既定读者群为史学、汉学专业人士;项目目标为注重学术性、突出忠实性的史记全译本。但目前为止这一令人期待的宏伟工程还只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全译仍是未尽计划。
倪豪士团队的《史记》英译项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思路逐渐转变,开始关注基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轨迹的中国史研究。中美关系改善之后,美国学者得以多渠道获取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资源。倪豪士团队全译《史记》的重大翻译工程正是在这种全球化与多元共生的语境中启动的,华译曾无缘采用的异化策略在倪豪士时代可谓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倪译本刻意保留了《史记》原文本纪、世家、列传等的排列顺序,附有纪年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中所遇问题或质疑点的相关评注和说明,现存相关外文译本书目和研究成果,参考文献目录,包含汉语拼音、汉字及官职英文译文的索引,春秋战国图、秦帝国图、项羽与刘邦战役图等,并且在脚注中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及资料依据、词汇对照表等。倪译本出于对古老中国文化的敬畏和尊重,为读者呈现的缜密的考证、详尽的注释以及科学的解读都切合了时代的诉求。
倪译《史记》将重心放在《史记》的文化价值上,追求客观、忠实,更多保留了中国文化异域特色,更注重译本的信度。这大幅度提升了译本的学术价值,也成就了倪译《史记》特定的可读性。这与当初华译《史记》旨在迎合读者所追求的可读性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史记》华译本体现了处于强势地位的译语文化对外来文本的强制性同化,那么,倪译《史记》则反映了源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主动接受度的提升。
3.杨译本:追求原汁原味的传真效果
杨宪益夫妇供职的外文局是中央所属事业单位,承担着中国文化对外宣传的任务,处理的文本具有官方权威性。英译《史记》是杨宪益供职期间的常规工作,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必然遵守源语社会文化系统的主流规范和译本处理的规则。“因此可供译者自由发挥的余地有限,通常的做法是对源语亦步亦趋。”[15]224
杨宪益作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对国家利益有强烈的责任感。输出中国历史文化是其翻译《史记》的目的,在这个主导思想下,他的翻译理念是非常明确的,即最大限度忠实于原文。他大胆采用音译、直译来处理一些语义空缺词和文化负载词;同时,即便是英汉语言系统中能够转换或变通的词汇,他也会不辞辛苦,审慎对待,认真拿捏,尽量观照文化含义,保留文化特色,可谓将固守原汁原味的再现做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对于司马迁极具中国特色的史书编撰结构,杨戴夫妇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和认同,他们对这种以封建等级排序的叙事风格并不陌生,所以译本中无不表现出司马迁对《史记》编撰体例的尊重和捍卫。
杨宪益作为中国文化宿儒,古文功底深厚,对中国史学著作的简洁风格接受度很高。因此,杨宪益的翻译策略更多地趋向于真实再现,比较贴近原文。其显著特点是译笔简洁爽直,几乎是复制了《史记》雄健、刚毅、大气的风格。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表现了作为国家喉舌的权威机构对自己民族经典史学著作的尊重和保护。杨译在20世纪50年代业已完成,但直到1974年才在香港首次出版,1979年由外文出版社在大陆出版。
四、结语
《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16]23全译《史记》工程浩大,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此类长篇巨作,通常的翻译运作轨迹都是由节译到全译,由选译到系统翻译,由随性的编译到严格的亦步亦趋;再由势单力薄的单兵作战到优势互补的团队合作,由单一项目运作到大规模系统工程,由区域化行为到跨国乃至国际化联手协作。截至目前,真正具有史学专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史记》全译本仍处于策划、探索、进行阶段,修成正果尚需时日。
现存译本中,华译本尽管有很强的译者主体性参与痕迹,但依旧是迄今为止译界公认的影响力最深远的译本,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接触中国史学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杨宪益和戴乃迭所译的《史记选》(SelectionsfromRecordsoftheHistorian),则被公认为忠于原文视角下比较权威的译著。杨戴夫妇是我国才华横溢、绝无仅有的中西合璧式夫妻翻译大家,是可遇不可求的强强联手,也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介到西方世界的先锋人物。作为源语文化的本土译者,他的资料、信息资源之丰富,对原文理解的透彻性、默契度都是同时代的华兹生所望尘莫及的。杨译本不仅致力于对源语史学信息的忠实再现,而且尽量保留司马迁史记的叙事风格,而这正是华译本的最大短板。同时,在《史记》译文中,杨译本也并没有忽略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尝试将原文中的大量默认值进行了显化,显著提高了译文接受度,使得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源语文化,有利于汉语典籍文化对外传播。
倪豪士组织开展的《史记》全译,是一个团队的集体行为,且阵容之强大前所未有,其中不乏中国本土的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这样大规模的合作翻译,实际运作之难、成本投入之大、工作任务之艰巨,足以让早期的译者望而却步。幸运的是倪豪士赶上了好时代,在这个追求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下,美国学界对待异质文化传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倪豪士领衔的《史记》全译工程得到了众多机构的资助,以再现异域文化为特色的异化翻译策略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保留《史记》原文的文化特质,做出详尽的文化与学术注解,这既是倪豪士团队对当时文化情境和文化氛围审时度势的明智选择,也符合所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目标读者的期待,契合时代的需要。
从华兹生到倪豪士,我们看到了翻译策略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看到了西方文化战略和文化心态的变迁和随着这种变迁出现的对文化差异以礼相待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多元文化共生的包容态度,以及对古老人类文明精髓的敬畏。
华兹生以争取读者关注为目的的翻译策略,在对《史记》认知度的荒蛮阶段,无疑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让西方世界接触、了解、认知,进而主动探求遥远东方的古老文化瑰宝。对传播《史记》精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之后倪豪士的接力创造了关键性条件,使倪豪士能够在读者认知度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得以践行以忠实再现原汁原味的《史记》为目的的异化翻译策略,从而在传真中国文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振奋人心的一大步,有效释放出《史记》作为史学巨著、文学经典的冲击波,完成了《史记》翻译从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传播到理直气壮、大刀阔斧的传真的华丽转身。
从迎合读者到忠于原著的历程中,不同时期的译者都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在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都可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也是彼时彼地的最佳策略选择。正是他们知难而进、永不言弃的长期努力和惺惺相惜、承前启后的智慧接力,《史记》翻译才有了今天良好的读者基础和开放的互动环境,在《史记》英译策略的博弈中,忠实的“异化”终于得以施展魅力,释放能量。
目前,倪豪士团队全译《史记》的重大翻译工程及所采取的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标志着《史记》英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语境中人类对异质文化的渴望与尊重。
我们在期待倪豪士全译本早日面世的同时,也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必须强化中国本土译者队伍的建设,提升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大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规范出版机构的计划性和系统性,主动出击,争取早日启动我国自己的史记全译,乃至《二十四史》全译项目,为人类文明的共享添上一笔浓墨重彩,为国际社会互动呈现一桌饕餮大餐。
[1] 高风平.中国文化“走出去”:机遇与挑战[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11):127-132.
[2] 吴松林.“中国梦”下的《二十四史》整体英译决策思考[J].绥化学院学报,2013,(9):80-84 .
[3] 黄春燕.同归而殊途——论司马迁与郑樵史学思想之“通”[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78-82.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吴原元.略述二十四史在美国的译介及其意义[J].历史教学问题,2011,(5):94-100.
[6] Homer H. Dubs: The Reality of Chinese Histories[J].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46,(6):23.
[7] 周一平.中国二十四史:尽快英译,推向世界[J].探索与争鸣,2008,(12):27-30.
[8]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9] 郭著章.文言英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0] Watson Burdon. TheShiJiand I[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1995,(17):202-203,205-206.
[11] 吴涛.西方汉学家批评视角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2-98.
[12] 赵桦.20世纪50年代史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转折点[J].大家,2010,(8):126-127.
[13] 李秀英.《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6,(4):303-308.
[14] 李秀英.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25-129.
[15] 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6]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贺晴】
A Review on the Transl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Home and Abroad
GAO Feng-p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Historical Records is a monumental historical work written by Sima Qian, the famous Chinese historian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and has been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accurate history, lofty style and vivid image, depicting up the scene of people’ social life in three thousand years before Han Dynasty.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various languages and each version has its unique way of representation when the translator picked up different strategies. The reasons for translator’s adjustments may include social particularities of his time, the main purpose he was to achieve and how well the readers have been prepared. Thus,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are of high importance to make the later job more reasonable, better acceptable and more professional, so as to efficiently help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ll over the world.
Historical Record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Yang Xianyi; Burton Watson; Nienhauser
H319
A
1009-5128(2016)18-0058-09
2016-06-28
渭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基于中华文化推介的直译策略研究——以渭南为例(13SKZD004);渭南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基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任务型”立体交互式英语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JG201308)
高风平(1961—),女,山东济南人,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与文化比较、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