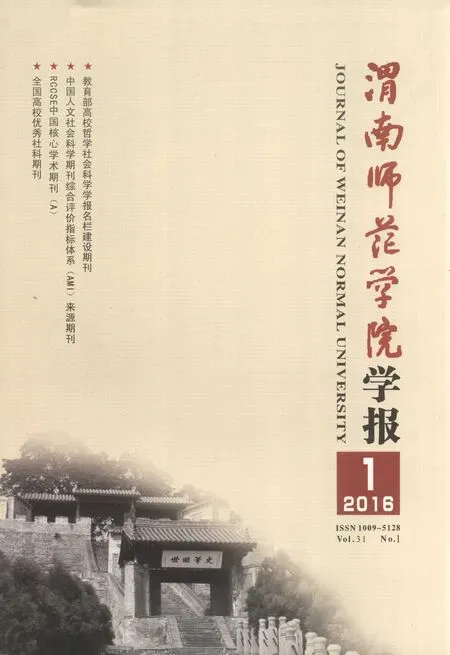《史记》与丝绸文化
2016-03-16刘宏伟
刘 宏 伟
(韩城市司马迁学会,陕西 韩城 715405)
《史记》与丝绸文化
刘 宏 伟
(韩城市司马迁学会,陕西 韩城 715405)
摘要:司马迁在传世巨著《史记》中,对于丝绸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作了大量细致的记述,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研究丝绸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关注并挖掘《史记》中所蕴含的丝绸文化元素和历史文化信息,正确评价司马迁在丝绸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对于更进一步理解国家新的战略部署、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更加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史记》;丝绸;丝绸之路;文化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不仅为人类发展贡献了四大发明和瓷器,而且早在原始社会,就以另一种代表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丝绸,而对推进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追逐“两个百年”伟大梦想的征程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访问中亚各国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1]“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它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面向欧亚大陆开放的新战略,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带”概念,体现的是经济带上各城市集中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却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史记》与丝绸文化的关系,深入挖掘史圣司马迁笔下留给我们的丰富丝绸文化遗产,对于更进一步理解国家新的战略部署、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更加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丝绸”不仅是中外商业交流的商品,而且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表征着“丝绸”本身在丝路沿线国家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文化上的多元与融合,因此,丝绸之路、丝绸文化都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笔者认为司马迁对丝绸文化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记述了丝绸的发明与发现;二是详细记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史实与凿通丝绸之路的伟大贡献;三是记录了上古至汉朝初期人们使用、流通、交换丝绸的各种情况,是研究丝绸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一、《史记》对丝绸发明人嫘祖的记述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索隐》引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世本·帝系》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2]10戴德《大戴礼记》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山海经·海内经》明言:“黄帝妻雷祖。”[3]117-118
其他文献也有类似记载,且多言嫘祖与养蚕业有关。如《淮南子》所引《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这是对蚕桑丝绸起源于黄帝时代的明确记载。《通鉴外纪》云:“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路史·后纪》云:“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之先蚕。”《隋书·礼仪志》引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弋、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北周以后,嫘被祀为“先蚕”(蚕神)。唐代著名韬略家、《长短经》作者、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所题唐《嫘祖圣地》碑文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明代文学家徐道在《历代神仙通鉴·仙真衍派》说:“(黄)帝初闻西陵氏女嫘祖,聪明温顺,聘娶为妃。常来游河滨,见树上都有白团,似鸟卵,而欲掰视,中有虫女指,询之土人,云龙与马交,遗精所化,嫘祖取置于器,越日出蛾,雌雄相配,自辰亥始解,生子无数。嫘祖藏之来春,皆生小虫,采桑嫩叶饲之。摘而挪沸汤缫之,绎而为丝。法天象经书莫言之义,造机抒,织成币帛,可以衣体,至是遂为人用。复以草木之华,染化五采文章,为衣服之美,而天下不患皴瘃。”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将嫘祖养蚕、育种、采桑、治丝、纺织、织帛、制衣体以及染色增美等事业,都作了系统的描述,与宋朝《织部·祀谢》中的画幅内容十分吻合,使人不得不承认嫘祖是我国上古时代养蚕治丝之始祖。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织部·祀谢》画幅内,就刻有宋朝绍兴县令楼王寿五言诗八句,内容是:“春前作蚕市,盛事传西蜀,此邦享先蚕,再拜丝满目,马革裹玉肌,能神不为辱,此事虽眇茫,解为民为福。”并涉及“蜀女化蚕”,成为“蚕女马头娘”的典故。康熙为此画题七绝诗云:“劳劳拜族祭神桑,喜得丝成愿已偿,自是西陵功德盛,万年衣被泽无疆。”清代史学家吴乘权在《纲鉴易知录》中称:“西陵氏之女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故后世祀为先蚕。”[4]39-40
总之,司马迁笔下记载的嫘祖“养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而被后人奉为神灵,世世代代享受着人们对她的隆重祭祀,与炎帝、黄帝共同成为了华夏民族的肇始者。
由于先秦文献并未确指嫘祖西陵氏位于何地,《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也只是称“西陵”为“国名”,致使有关嫘祖故里的地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围绕嫘祖故里展开争论,较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是湖北的黄冈说、浠水说、宜昌说、远安说和四川盐亭说、茂县说以及河南西平说、山西夏县说、陕西黄陵说、山东费县说等等,不一而足。不管哪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历史上确有嫘祖其人其事。正是有她“教民养蚕”、“织丝茧以供衣服”,才产生了丝绸,也才有了丝绸文化。所以说,嫘祖确为中国丝绸之祖。
二、《史记》之前典籍中对丝绸的记述
祭祀先蚕之礼早在西周就已开始。《月令·西周》云:“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归,而藏诸庙中;天子藏诸于明堂,每月告朔朝庙,出而行之。”至今北京北海公园还有先蚕坛。这表明,祭祀先蚕是代代相承,循而未改,以先秦时代人们既知嫘祖始蚕而言,西周所祭先蚕,就是嫘祖。再以西周王室出自黄帝之后而论,其祭先蚕,也是祭祀嫘祖。南北朝也仿西周制度,祭祀先蚕西陵氏神。
传世文献中对中国丝绸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书中提到了当时生产蚕丝和丝织品的地区。《禹贡》的记载进一步表明,早在中国文明兴起的初期,中国丝织品已经形成了许多种类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国丝绸最早传到古希腊,希腊称中国为“支那”,即希腊文“丝绸之国”的含义。这充分证明了丝绸的起源在我们中国,中国丝绸的起源是在黄帝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礼记》《战国策》等文化典籍中,多处记载了蚕、桑、蚕丝和丝织品的生产、制作、工艺、使用情况,《战国策》还明确记载了罗、纨、绮、锦、绣等丝织品种。例如,《礼记·昏义》载:“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左传·隐公四年传》中,隐公向大臣众仲问道:“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5]689
虽然这些有关的文字比较零碎、不成体系,但却真实地反映丝绸早在那个时代已经十分普及了。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述采桑、养蚕、制丝的诗歌就更多了。据统计,《诗经》305篇,其中涉及丝绸文化的诗歌就有二三十首之多,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东周早期、春秋战国时期劳动人民植桑、养蚕、制丝、纺织的生动画面,内容极其丰富。譬如《卫风·氓》就通过男主人公氓抱着布匹来换取农家女的真丝的爱情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蚕丝和真丝织品的贸易情况。《魏风·十亩之间》尽管只有短短几句,却生动地描写了采桑人在紧张劳动结束时呼唤同伴返回的愉快心情。《周颂·闵予小子之什·丝衣》描写周王祭祀神灵后设宴饮酒的隆重场面,前五句写了助祭的人们穿着洁净的丝绸祭服,恭恭敬敬地戴着黑色的爵冠,忙忙碌碌、非常认真地从庙堂到庙门,一样一样地检查着羊牛之类牺牲和大鼎小鼎盛放的各类祭品。从这里可以看出,丝绸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另外,《秦风·终南》《郑风·丰》《曹风·鸤鸠》《鄘风·干旄》《卫风·硕人》《唐风·扬之水》均写出了当时丝绸服饰的华丽与珍贵。
《诗经》中描写蚕桑丝绸生产过程最完整的当数《豳风·七月》了。这首诗根据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逐月展示农业生产的各个场景。从第二章到第七章,完整地记录下了蚕桑丝绸的生产过程。“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秋风渐起,“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开始纺绩,染成黑色及黄色的扮线;“我朱孔阳,为公子裳”[6]60-61,最后用鲜亮的红色扮织品,来为公子制作衣裳。这首纯朴古老的农事歌,同时也反映出底层劳动人民繁重的劳动情形和辛苦的生活。
三、《史记》篇章对丝绸的记述
距今五千年的时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丝绸,商周丝绸业已较发达。战国、秦汉时代经济大发展,丝绸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公元前126年,在汉武帝西进政策下,大量国内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向西运输。经过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丝绸发生了很大变化,既继承传统又兼容外来技术、纹样的优点。宋元时代随着古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丝绸技术的大发展,品种风格有了创新,丝绸生产中心也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至明清江南苏杭一带成为最重要的丝绸产地。
《史记》中,除前文提及的嫘祖以外,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关于丝绸的记述文字。
1.禹甸九州即有丝
《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把天下分为九州,规定了各地的贡品赋税,指给了各地朝贡的方便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划定了五服界域,使得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众河朝宗于大海,万方朝宗于天子的统一、安定和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从下面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许多地方,都出产丝,并且作为贡品向朝廷进献。
济、河维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于济、漯,通于河。[2]54
在兖州,“其贡漆丝,其篚织文”,这一地区进贡的物品是漆、丝,还有用竹筐盛着的有花纹的锦绣。
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潍、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酓丝。浮于汶,通于济。[2]55
在青州,“莱夷为牧,其篚酓丝”,意即除了进贡畜牧产品,还要进贡用筐盛着用来作琴弦的柞蚕丝。
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大野既都,东原底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臮鱼,其篚玄纤缟。浮于淮、泗,通于河。[2]56
在徐州,“其篚玄纤缟”,就是要进贡用竹筐盛着的纤细洁净的黑白丝绸。
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2]58
在扬州,要进贡象牙、皮革、羽毛、旄牛尾和岛夷人穿的花草编结的服饰,还有用竹筐盛着的有贝形花纺的锦缎。
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梦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维箘簬、楛,三国致贡其名,包匦菁茅,其篚玄纁玑组,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汉,逾于雒,至于南河。[2]60-61
玄纁指彩色的帛。玑是珠子之类。组是丝带。在荆州,除进贡其他丰富的物品之外,还要进贡用竹筐盛着的彩色布帛,以及穿珠子用的丝带。
荆河惟豫州:伊、雒、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絺、纻,其篚纤絮,锡贡磬错。浮于雒,达于河。[2]62
豫州要进贡的是漆、丝、细葛布、麻,以及用竹筐盛着的细丝絮,还有治玉磬用的石头。
《夏本纪》的文字,揭示出华夏大地上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了丝织品,而且各地的丝织品并不相同,种类繁多,各有特点,与当地的地理、气候、自然条件息息相关。
2.争桑之战
周敬王元年(前519),吴楚两国因争夺边界桑田,曾发生大规模的“争桑之战”。这个史实在《史记》的《吴太伯世家》中有记载:“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2]1462
《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述与《吴太伯世家》大同小异:“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2]1714
“争桑之战”,充分说明了蚕桑之利在当时经济上所占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3.蜀国的帛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2]2994-2995这说明,在春秋以前,蜀国的帛便以品质优良而运销秦地和越地,秦蜀两地的丝织品——缯帛和蜀布已经开始流通、交换。另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司马相如所做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等名篇佳作。这些汉大赋运用华丽的辞藻、铺排的句式、宏大的结构、富丽的气氛,展示了西汉王朝物产丰饶、欣欣向荣的社会面貌,其中不乏丝绸的影子。
4.《货殖列传》反映出丝绸是一种珍贵商品
司马迁两千多年前撰写的《货殖列传》一文,是一篇经济学的宏文巨篇,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多处谈到丝绸。如在讲述各个地方出产的物品时,就指出:“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2]3253“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2]3265“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2]3270讲到商业奇才白圭的创业史,则有“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2]3258-3259。意思是说,他通过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
5. 其他篇章中有关丝绸的记述
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开篇一段,有娄敬与虞将军很有意思的对话,原文是这样的:“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原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2]2715娄敬想面见刘邦,但不愿意换新衣裳,还对同乡虞将军说:“我穿着丝绸衣服来,就穿着丝绸衣服去拜见;穿着粗布短衣来,就穿着粗布短衣去拜见:我是决不会换衣服的。”在《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好几处都提到丝绸。一处是每逢乳母入朝,汉武帝都要派宠爱的侍臣马游卿拿五十匹绸绢赏给乳母,并备饮食供养乳母。另一处是汉武帝宠爱的郎官东方朔在宫中吃完饭后,便把剩下的肉全都揣在怀里带走,把衣服都弄脏了。皇上屡次赐给他绸绢,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他专用这些赐来的钱财绸绢,娶长安城中年轻漂亮的女子为妻。从此可见,当时丝绸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了。
《史记》中提到丝绸的地方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罗列。
四、张骞凿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丝绸之路”
尽管丝绸之路是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一条贯通欧亚北部的商路,可是“丝绸之路”一词最先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来的。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1877—1912)一书中,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近两个半世纪开辟的,经西域将中国与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地区以及印度连接起来的丝绸贸易道路命名为Seidenstrassen,英文名为The silk road[7]5-6。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承认。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打击匈奴,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带领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向西进发,不料在途中被匈奴俘虏,“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2]3157。就这样,张骞在匈奴度过了长达十余年的软禁生活。后来,他们找机会逃出匈奴,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康居。公元前126年,张骞和堂邑父两个人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张骞的首次西行,被史学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后,地处远东的西汉王朝抓住机遇,倾尽国力向西拓展,通过丝路的交流与贸易,在印度、东南亚、锡兰岛、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源源不断地流行于欧亚非三洲的各个国家,大陆之间的贸易沟通变得规则有序。
公元前119年,张骞时任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历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变成了“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2]3166的强烈愿望。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汉朝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西汉末年,由张骞西行开辟的丝绸之路被荒废。到了东汉时期,公元73年,汉明帝派大臣班超再次出使西域,重新打通了隔绝58年的西域。班超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到达波斯湾。由此,班超首次将丝绸之路延伸打通到了欧洲,到了欧洲的罗马帝国,罗马也顺着丝绸之路首次来到中国,到了当时的东汉京师洛阳,这是目前丝绸之路的完整路线,即东端由洛阳出发,西端从西亚延伸到了欧洲(罗马),这条完整的丝绸之路从西汉首次开辟到东汉而定型完整。公元166年,大秦(罗马)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同中国的首次直接交往。同时埃及和中国最早的官方沟通也是在这一时期。
五、从《史记》看丝绸文化发展及其贡献
如上所述,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传世巨著《史记》中,用如椽之笔记述了嫘祖养蚕、发明丝织的滥觞之举;又在书中多处记述了华夏各国广泛使用丝绸的史实。更重要的是,他翔实地记叙了张骞出使西域各国、传播、交换丝织品的贸易过程,使丝绸之路由商贸之路变成了政治经济交流的大通道,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杰出贡献。
正是由于司马迁用不朽的文字翔实地记录下了张骞出使西域、开凿丝绸之路的历史史实,后人才知道了西域丰富的物产和资源,才了解了丝绸之路沿线众多的国家和风土人情,才明白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拓丝绸之路、加强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战略眼光。
丝绸,一个生活日用品,最后演变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它的产生、小范围使用,一直传到欧亚各国,在史圣笔下脉络清晰,栩栩如生,不啻勾勒出了丝绸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为后世了解、研究丝绸和丝绸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就是《史记》对丝绸文化的最大贡献。我们在谈到丝绸、重铸丝路辉煌时,不能忘记张骞、班固,更不能忘记史圣司马迁。如果没有太史公的《五帝本纪》《大宛列传》和散落在《史记》全书中对于丝绸的点滴记述,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会黯然许多。
参考文献:
[1] 暨佩娟,崔悦. 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N].人民日报,2013-09-16.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晋]郭璞.山海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 段渝. 黄帝、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J].成都:中华文化论坛,1996.
[5] 四书五经[M].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
[6] [宋]朱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张燕.长安与丝绸文化[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朱正平】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ilk Culture
LIU Hong-wei
(Sima Qian Society of Hancheng, Hancheng 715405, China)
Abstract:Sima Qian handed down his masterpiece Historical Records. For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silk, he made a lot of detailed description, which is the firsthand document about China’s ancient classics study of silk culture. It’s far-reaching significan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ilk cultural elements and its historical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its exploration, and correctly evaluate the Sima Qian’s enormous contribution to silk culture. It is for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ntry’s new strategic plan, to promote “One Road One Belt” construc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 silk; Silk Road; culture
作者简介:刘宏伟(1968—),男,陕西岐山人,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理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司马迁与《史记》、周文化与吴文化及文学、史学评论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03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1-0047-06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