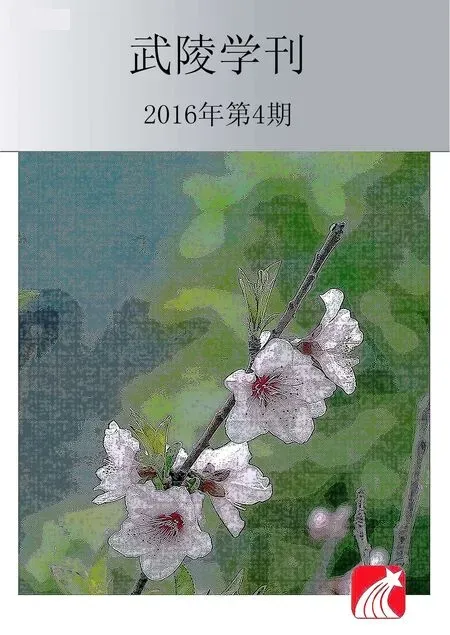“凭心而言,不遵矩矱”
——学习《林默涵文论》的文格
2016-03-16涂武生
涂武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凭心而言,不遵矩矱”
——学习《林默涵文论》的文格
涂武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林默涵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教育家,曾长期在宣传、文化部门任领导工作。不久前出版的《林默涵文论》,集中体现出他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辩证思维、一分为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丹心铁骨、高风亮节的人格和文格。
《林默涵文论》;林默涵;人格;文格
我与默涵同志最初相识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我从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参加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参编人员集中住在中央高级党校。周扬和林默涵当时是负责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领导,他们几次到住地看望编写组成员和召开座谈会。同时,林老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也多次到文学所出席过各种不同的活动。“文革”爆发,10余年间天各一方,我们相互都不通音讯。直到1977年8月4日,在八宝山何其芳的追悼大会上,默涵同志从江西流放地专程赶回北京参加这次活动,我才重新见到他。关于个人接触和了解的默涵同志的一些往事,我已经写过两篇短文。一是《美的爱慕和追寻——默涵同志与美学》,它在收入《大江搏浪一飞舟——林默涵60年文艺生涯纪念集》(重庆出版社1994年出版)前,曾专送林老亲自审读过。二是在他去世后,我写的《“人入暮年志未销”——记与默涵老人的一次交谈》,追忆了他与我倾心长谈他参加抗日战争和奔赴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经历(发表于《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往事历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心底。
这本刚刚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新出版的《林默涵文论》,我收到后立即从头至尾翻阅了两遍,感到特别亲切,非常感动。书中选进的许多文章,我之前都在他赠送的《林默涵劫后文集》和《心言散集》中读过。这次重读,再一次深深感到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林老的风范和贡献。人有人格,文有文格。他在书中说的“凭心而言,不遵矩矱”,就集中地体现出他的人格和文格。在我看来,它们的要点至少可以概括和归纳为: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辩证思维、一分为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丹心铁骨、高风亮节。这些方面,都真实地表露和揭示出他为文为人的崇高风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崇敬。
一、实事求是,联系实际
默涵同志1938年由武汉奔赴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自聆听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此后,他便终身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定悍卫者、宣讲者和继承者。《林默涵文论》中的首篇文章,就是195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在这篇文论中,他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结合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卓越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党的原则”,同时,还肯定“这个讲话不仅对于文艺工作的前进和发展,有其伟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前进和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这是一部关于革命文艺的、也是关于革命的思想工作的辉煌的科学著作”[1]3。这个评价,符合实际,对建国后深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曾经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默涵同志按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首先肯定了“在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下,文艺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1]3。同时,又不回避文艺界存在着思想混乱的情况,它们一方面“表现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追求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追求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在虚伪的化装下,宣传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以至反动思想”;另一方面,“和上述倾向看来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便是文艺创造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1]5。作者认为,上述两种倾向的表现虽然并不相同,但是,就其根源和结果来说,却是具有共同的特征。他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首先肯定在《讲话》指引下我国文艺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又不讳言存在的缺点;而在指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时,同样又有两方面不同的表现形态。这就是紧密联系实际,对《讲话》的全面理解、研究和贯彻。
相隔30多年后,林老死里逃生,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仍然忠心耿耿、情有独钟。在1983年毛泽东诞辰90周年之际,林老又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引导我们继续前进》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毛泽东的一生“是在中国社会最激荡、斗争最尖锐、变化最剧烈的时候度过的。在这漫长的、无比艰苦的战斗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在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丰功伟绩将永留史册”。作者再次强调,《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426。
面对当时有人散布的《讲话》“过时论”,说什么它“是针对延安当时的情况讲的,只适用于延安特殊的时间地点,全国解放后就不适用了”,林老依据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以普遍性和特殊性、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驳斥了这种错误认识。他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确实是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延安文艺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是有历史原因的,“跟整个新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由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缺点是分不开的,延安文艺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全国革命文艺界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当时虽然是一些小块地区,然而是新兴的、光明的、向上发展的,它们是新中国的雏形”;“适合于延安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也是适合于解放后的全中国”。同时,他又强调“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明确表示也不能用凝固不变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并非‘句句是真理’。事实上,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主观认识的逐步深入,思想或理论总是要不断地补充或修正。”[2]428应当说,经过十年“文革”的思想理论混乱,在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上,林老是起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的。
记得有一次我去林老家中,他对我谈起某些人对“解放思想”的不正确理解,表示一定不能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对立起来。解放思想决不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与实事求是恰恰是相违背的。在《林默涵文论》中,他围绕对《讲话》的认识分歧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写道:“思想解放的实质,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一个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主要就看它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思想不符合客观实际,是产生一切错误的根源。落后于客观实际或者超过客观实际,都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或者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3]339他再三强调:“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辩证法去认识和研究客观实际,去研究客观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发现新事物的新规律,找到新的解决办法”[3]339;对待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其他许多著作,都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此后,他还围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话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和讲话;而《林默涵文论》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团结奋斗 繁荣文艺》,恰恰就是作者1992年在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里,他又特别强调“文艺界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4]。从1952年到1992年,相隔整整40年,林老的大半生都坚守实事求是、联系实际的精神,坚持、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他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坚定的捍卫者、积极的宣传者和杰出的阐释者。
二、辩证思维,一分为二
唯物辩证法是符合客观真理的科学思维,是与形而上学片面的、僵化的、死板的、孤立的思维方式对立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必须用“一分为二”的维度和视角,来看待文艺作品和现象。鲁迅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5]他还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6]默涵同志的文论,就是一贯遵循这种科学的辩证思维,来看待、研究文艺家和文艺作品的。
20世纪50年代中,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下,《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作品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评论界对于这篇作品也发表了各种不同的和相反的意见。那么,默涵同志又是怎样来看待这场争议呢?他在《人民日报》1957年3 月12日发表的《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中首先肯定:“对于一篇作品有分歧的看法,原是很平常的事情。而经过不同意见的互相争辩和商讨,我们就能逐渐地得出正确的结论。”接着,他便对有的人因为小说批评的是党委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这样一个尖锐的主题,而全盘抹煞这篇作品,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王蒙是怀着同旧的事物斗争的热情来写这篇小说的。“有的人甚至怀疑作者的动机,认为这篇作品是对于我们党的机关的有意诽谤。这种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不能帮助作者克服缺点,而只会打击作者的创作情绪,同时在读者中间引起思想混乱。”[7]40由此,他提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文艺批评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他认为,这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对文艺创作的发展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默涵同志又细致地分析了作品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个性,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作品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小说作者是抱了一种热情来描写生活中的新旧斗争的,并且直接批评了党的机关中的消极现象。可是,由于作者在理解生活和描写生活方面都存在着缺点,他虽然比较深刻地写出了消极的事物,却没有写出真正能够战胜旧事物的积极力量,因而作品给人一种不健康的灰暗感觉。”[7]48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王蒙时年22岁,初出茅庐、意气风发,初露锋芒、才多识寡,无论是捧杀还是骂杀,对他都是诱惑或打压。默涵同志从作品的实际出发,真正做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独具慧眼、鞭辟入里,于作者和读者均有深刻的启迪和教益。至于作家不久后便遭遇“黑云迷雾、凄风苦雨”,那是包括默涵同志在内的许多人均未料到、也左右不了的。
新时期开始的80年代,在所谓“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展开了对电影剧本《苦恋》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个作品“艺术性很好,有创新”,“作者很有才华”。而默涵同志就站出来反对这样的论调。照他看来,“艺术性不能离开思想内容。艺术性主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而《苦恋》根本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作品,不但不符合历史真实,在生活细节上也很不真实,那样,还怎么谈得上“有很高的艺术性”呢?他相信:“《苦恋》的作者白桦同志是有才华的”,可是,作者确实写出了一个“有严重错误的剧本。可见光有才华并不能保证作品的成功”。针对作品中的具体情节,例如画家的女儿对父亲说:“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林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反驳:“我以为这样提问题就是根本错误的。爱祖国,这是每一个人的天职和义务,我们对祖国的爱不应该有什么交换条件,不能说我爱不爱祖国要看祖国是不是爱我。”他认为,正是这些不真实的细节,“给本来就不大了解我们国家历史的许多青年看了的话,绝不能加强他们的爱国主义,只会使他们感到中国不好”[8]。把握辩证思维,对具体作品和作家进行具体的、细致的分析,这就是默涵同志一贯遵从的准则和作风。
与以上相联系,林老的人格和品性,还表现在他实事求是地努力接受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力求避免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尽可能防止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也就是说:“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例如,20世纪50年代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刚刚提出时,就有人出来“纠偏”,认为“天下大乱”“大势不好”。默涵同志及时地指出:这些都是因为旧的“习惯势力”作怪,有些人的习惯的想法和做法还变不过来。“他们对这个新的方针就采取了明显的或不明显的怀疑、抗拒的态度。”他以个人的认识转变,真诚地、耐心地劝说这些同志要“很好地理解这个方针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明确地表示:“在我们文艺界,今天到底存在着什么倾向呢?‘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都存在。但是,目前主要的危险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因此,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必须坚决地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20多年后,进入到新时期,他重提“左”和右的问题,并且进一步分析说:“事物是复杂的,什么时候都要看到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有时候,‘左’可以走到右,有时候,‘左’右是可以汇合起来共同反对正确的革命的东西的。但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主要倾向。”他告诉大家:“我的意见是应当实事求是,有什么不好的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有‘左’纠‘左’,有右纠右,‘左’比右好不对,右比‘左’好也不对。过去就是一反右就看不到‘左’,现在不要反过来,一反‘左’又看不到右,这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的看法和做法,是使我们吃了大亏的,我们不应该重犯这个毛病。”[10]事实证明,默涵同志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适时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绝对主义、教条主义,研究新情况,找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才能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达兴旺、繁荣昌盛。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林默涵文论》中收录的44篇文章中,有一篇题目就是《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这是作者1982年4月29日在文化部文艺理论学习班上的发言。在毛泽东《讲话》发表40周年之际,林老对这篇经典著作再次进行了全面、完整的阐释。他奉行的基本原则是:“真理要坚持,错误要修正。”在讲话中林老直截了当地、实诚地表示:“我们并不认为《讲话》‘句句是真理’,它的次要的、个别的提法或论述不当之处,无须加以掩盖。”[11]林老赞同当时有的同志的提法: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要坚持、运用、发展。坚持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如果不去运用,坚持它做什么?同时也只有在运用中才能有所发展,如果束之高阁,不运用而放言发展,那只是空谈而已。将坚持、运用、发展三者结合和统一起来,是林老学习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态度和科学方法。
林老对待自己过去的言行和文论,一贯就是抱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来反思、反省的。他将这种态度概述为:“一、不掩盖自己的观点,怎么想就怎么讲,错了,就改,如果有错误而自己还没有认识到,就保留自己的观点,但对于组织上的决定,在行动上一定要服从、执行。二、对别人的意见要实事求是,不要加以歪曲。人家怎么说的就是怎么说的,如果你认为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要把别人的意见歪曲,然后当作靶子来攻击。这是起码的道德。”从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林老的文格和人格、文德和人德,都严格地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准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明明白白、坦坦荡荡,没有文过饰非、缄辞闭口,更没有强辞夺理、以伪乱真。
默涵同志言行一致、身体力行,说到做到、说一不二。他在晚年不止一次地公开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掩耳盗铃、颠倒是非。他总结自己“十七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时便承认:“在正确路线下,工作上也会犯错误。事实上正是这样。我们在过去‘十七年’中是有严重错误的。‘十七年’中,我有十四年做文艺工作(我是1952年调到中宣部做文艺工作的),既有‘左’的错误,也有右的错误,但更多的是‘左’的错误,主要是由于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低,脱离群众,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作风严重,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训。”[3]330他不仅口头和文字上坦承和反思错误,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在工作上、行动上力求避免和重犯过去的错误,并且真诚地规劝和希望所有人都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细心地读过《林默涵文论》的人也许都会发现,书中有一条长注,那就是关于文艺工作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问题的注释。在这条几乎占了半页篇幅的注解中,作者回顾了自己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过程,表示拥护“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同时,又对过去赞同和宣传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检讨为“都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而且特别声明:“为了保持我这次讲话的本来面貌,我对当时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意见,未作改动。我认为,一个人的认识是可以改变的,但当时怎么认识就是怎么认识,不应该偷偷地修改自己说过的话,那样做不是老实态度。”[3]341林老深深地懂得毛泽东说过的:“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12]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和法宝之一。为了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自觉地、主动地、虚心地听取来自党内外的批评,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检查和剖析,并及时改正。毛泽东早就向全党提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13]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加强修养、自我反思,才能不断地提高和前进。默涵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言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榜样。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默涵同志是不同意某些人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什么“忏悔”“宽恕”“谢罪”之类的东西混为一谈的。他郑重声称:“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14]党内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和加强自身建设,与宗教所谓免除“因果报应”而“悔罪”“忏其前愆”“悔其后过”等等,风马牛不相及,绝不能混淆在一起。关于这样的话题,我曾亲自听他重复过多次。他毕生言而有信、身体力行,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光明磊落、不愧不怍,不矜不伐、不亢不卑。
四、丹心铁骨,高风亮节
在《林默涵〈劫后文集〉题记》中,作者写道:“因为工作的需要,时常要发表些意见,对所见所闻又不能做到心如槁木、毫无感触,积久了就有了这么些篇,虽然芜杂而零碎,却也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化思想方面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显然存在着分歧。我的意见不过是其中之一种,错误肯定是会有的,然而‘凭心而言,不遵矩矱’,怎么想就怎么说,决无看风向、赶浪头之意。所以,即使错了,也错得明明白白,决不含糊其词,让人摸不着头脑,也使反对我的意见的人容易抓到毛病,便于进行批评,只要批评得对的,我都接受。”[15]274这段自白,的确如《林默涵文论》编者“前言”所说:“寥寥数语,表达了林默涵同志坚定的原则性、社会责任感及理论勇气。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谦虚谨慎、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和与时俱进的真诚愿望。”[16]
从以上概括的《林默涵文论》的要点中,我们不难看到,“凭心而言,不遵矩矱”可以说是林老毕生遵从的人生准则,是他的人格和文格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为自己作的真实自画像。如果说,《林默涵文论》中充溢着一股生气勃勃的“内功”,我体会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融为一体。作者心系人民,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这简明扼要的“凭心而论,不遵矩矱”8个字中,我们深深领会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论家的丹心铁骨、高风亮节,光明正大、高瞻远瞩。
“凭心而言,不遵矩矱”,坦率地表白的是做人做文的基本准则:言为心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说假话,不当两面派,不做墙头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首先要对自己红彤彤的良心忠诚,心中想的什么和文章写的什么基本一致,没有人格分裂。“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在默涵同志的文论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字里行间的“自然而然的流露”,真心实意、真知灼见,实实在在、实话实说。
“凭心而言,不遵矩矱”,说明一个人写的文字,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意见,独行其是、言必己出,独具一格、独辟蹊径;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被繁文缛节所限制;更不会人云亦云、唯唯诺诺,模棱两可、是非不分。林老的文论,是与“洋八股”和“党八股”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既没有教条主义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也看不到形式主义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它们不拘一格、洞若观火,言近旨远、言简意赅。在林老的文论中,我们很难找到“槽床过竹春泉句,他日人云吾亦云”。
“凭心而言,不遵矩矱”,展示的是人格和文格的高度结合与统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文过饰非、矛盾百出。林老直白地说:“我以为,对于复杂纷纭的事象,谁也不可能没有看错的时候,随着认识的深入而改变原来的主张,这种事是毫不足怪的;但改变主张总要说明改变的理由。有的人昨天那样说,今天看看风头不对,抹抹嘴巴,却又这样说了,而绝口不提所以变化的理由,仿佛昨天的话根本不是他说的。”[15]274的确,有的人虽然千遍万遍地声称“要讲真话”“不说违心之言”,可实际上这不过是个遮羞布和谎言,为的是掩盖和粉饰自己言行中处处都有的连篇假话、套话、废话;更有不少“风派”“新派”“潮派”,一天一个“新论”“新体系”,全是东拼西凑、东拉西扯,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可仍强词夺理、自鸣得意。林老文论中的许多篇章,都坦然地、直言不讳地、明明白白地表示出“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的态度。
“凭心而言,不遵矩矱”,是一种品性和风骨。古人倡导的是“德之不立,无以立言”,有了高尚的人品,才会有真正超凡的文品。“以文观人,自古所难”。纵观古今中外名家,人格与文格固然不少人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可也有某些人不一致、不统一,甚至于反差明显、大相径庭,口蜜腹剑、两面三刀,旁门左道、嘴甜心毒,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者大有人在。文格的魅力来自于人格的闪亮,高风亮节自然而然地带来笔底生花。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7]旗帜鲜明、丹心铁骨、敦厚谦和、质朴厚道的林老,“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文品即人品”“文格即人格”的榜样和楷模。《林默涵文论》的书香,带来了浓浓的红色岁月记忆和海阔天空的温馨。1982年11月,林老在伦敦拜谒马克思墓后写过一首“述怀”诗:“平生不善稻粱谋,/逆水行船棹未休。/岂情微躯投鳄鼈,/甘为孺子作驹牛。/接传天外真知火,/化却人间冻馁忧。/莫道春日花事尽,夕阳红叶耀高秋。”[18]这是对“凭心而言,不遵矩矱”的诗性解读,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崇高理想的歌颂!
[1]林默涵.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2]林默涵.毛泽东文艺思想引导我们继续前进 [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3]林默涵.关于文艺工作的过去和现在[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4]林默涵.团结奋斗 繁荣文艺[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535.
[5]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鲁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395.
[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M]//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344.
[7]林默涵.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社,2016.
[8]林默涵.文艺与党的关系及其他[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368.
[9]林默涵.什么是危险?什么是障碍?[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51-52.
[10]林默涵.我对所谓“三、四、‘左’、右”问题的看法[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93.
[11]林默涵.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402.
[12]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44.
[13]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32.
[14]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495.
[15]林默涵.林默涵《劫后文集》题记[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16]编者.前言[M]//林默涵文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2.
[17]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408.
[18]林默涵.六九述怀[M]//林默涵.心言散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366.
(责任编辑:田皓)
Study of Literary Theory of Lin Mohan
TU Wusheng
(Chinese Institute of Arts Research,Beijing 100029,China)
Lin Mohan is a famous literary theorist,writer and educator in China and has been a leader for a long time in China’s propaganda and cultural departments.Literary Theory of Lin Mohan published recently shows his noble literary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such a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connecting with reality,sticking to truth,correcting errors and so on.
Literary Theory of Lin Mohan;Lin Mohan;personality;literary character
I206.7
A
1674-9014(2016)04-0087-06
2016-05-08
涂武生,男,湖北武穴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学和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