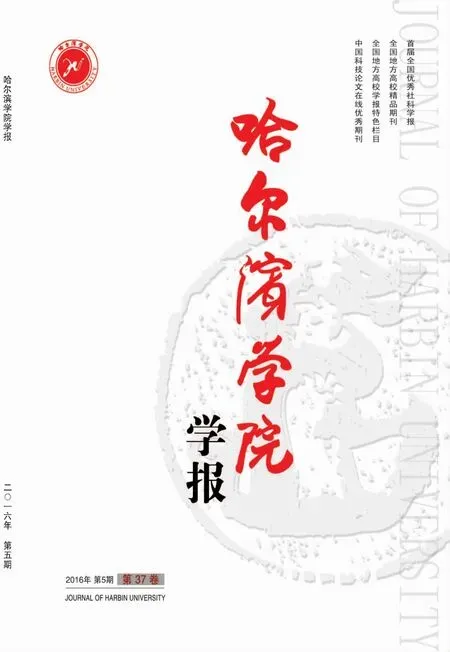从《宋书·隐逸传》看隐逸文化的发展
2016-03-16杨志娟
杨志娟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从《宋书·隐逸传》看隐逸文化的发展
杨志娟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摘要]《宋书·隐逸传》是史书隐逸列传在刘宋的继承和发展。追溯《宋书》之前正史中的隐逸传,可以看出隐逸文化的线条性发展。探究隐逸的思想基础,更能了解隐者的心态。隐士们或笃守隐逸之志,或亦宦亦隐,均离不开守志保身这两大出发点。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无法隔绝的是其臣民身份。
[关键词]《宋书》;隐逸传;隐逸文化
《宋书·隐逸传》记载了20位隐士,他们为了守志保身而选择隐居山林。他们读书识礼,崇尚自由,个性冷漠,是一批“耿介”之士。隐士们追求避世远害,修身自保。但这群隐士并没有清晰地分割开“仕”与“隐”的关系,或笃守隐逸之志,隐居山林,但作为一朝臣子,他们又无可避免地要接受任命入朝为官,然其心中秉着笃守其志的追求,无法拒绝的君臣关系,让他们徘徊于仕与隐之间,呈现出亦宦亦隐的状态。
一、对史书“隐逸传”的追溯
《宋书·隐逸传》并不是最早专门为隐士设传的史书,二十四史中,《史记》最早有对隐士的记录,然最早为隐士设传的是《后汉书·逸民列传》,接下来就从刘宋之前正史中看隐逸传的线条性发展。
《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没有单独为隐士设传,但列传的第一篇就是《伯夷列传》,可见司马迁已然关注到隐士的生存问题。在追述了许由、夏、卞随、务光这几位隐士之后,借孔子“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世用希”[1](P2122)的评价,引出伯夷叔齐为让位而竞相逃离。恰逢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对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1](P2123)的行为不齿,隐到首阳山,饿死不食周粟。如果说史书中最早的隐者是伯夷叔齐的话,那么他们的隐逸是为了坚守心中的“义”,是对统治者不守仁义的反抗。其后《汉书》中,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的前半部分实际上就是隐逸传,以伯夷叔齐之事开启论述,加之孔孟二人对伯夷叔齐的褒奖,列举出园公、绮里季、夏皇公等人“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2](P3056)避身山林,等待天下太平。这些人“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2](P3058)班固认为,逸民的行为可以抑制贪婪,劝勉良好的世俗,跟古代的隐士很相似。
之后,史书中较正式记载隐士的是范晔的《后汉书》,专门设有“逸民传”。范晔在序文中讲到隐士隐居的目的:“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庇物以激其清。”[3](P2755)这段话涵盖了两种隐居动机,一是遵从内心而隐居“隐居求志,静己镇躁,庇物激情”,二是不得已而为之“回避全道,去危图安”。该逸民列传记载18位隐士,重点讲述隐士的守志和修志。紧接其后是《晋书·隐逸传》,载隐士38人,传序概括了隐士的生活状态“古先智士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寝巢而韬其耀,良画以符其志,绝机以虚其心。玉辉冰洁,川渟岳峙,修至乐之道,固无疆之休……修身自保,悔吝弗生”。[4](P2425)隐士多是耿介之士,平素有着浩然正气,他们藏身江海,销声匿迹,隐藏才华,读良书,体会人生之至乐,但最为重要的是“自保自身”,可见隐逸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守志和保身。
《宋书·隐逸传》载隐士18人,序文沈约先用《周易》《论语》对世道不行,贤人隐居的论断,引出他自己的概述:“及逸民隐居,皆独往之称,虽复汉阴之氏不传,河上之名不显,莫不激贪厉俗,秉自异之姿,犹负揭日月,鸣建鼓而趋也。”[5](P2276)沈约认为隐士均为独往之人,隐逸是他们偏介的表现,如果“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5](P2297)如果他们逢上清明的社会,又怎会选择放情江海之上?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表现。之后史书如《南齐书·高逸传》《梁书·处世传》《魏书·逸士传》等专门为隐士列传,其名虽殊,但均是对隐士这一群体关注的体现。某一朝代隐士的人数、隐居的原因,与这一时期社会的清明与否有直接关系。
通过对唐前史书中隐士的追溯,无论是否专门为隐士列传,都可以看到史家对隐士耿介正直人格的关注。这些隐士有着浩然正气,高尚操守,重要的是,他们的出现与社会政治的清明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政治清明与腐败的晴雨表。
二、“隐逸”的思想基础
隐逸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中都有对隐逸的论述,都在相当程度上探讨过隐逸现象。
儒家思想是维护中央集权制体系的,以孔孟为代表,提倡文士积极入仕,但孔子的言论著作《论语》中也有对隐逸的赘述。《公冶长》篇多有对世道混乱,贤人获罪现象的披露。孔子给出的应对措施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6](P41)“道不行,乘浮游于海”,[6](P49)“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6](P49)可见,孔子将出仕与入仕的标准归为社会政治的有道与无道,社会的清明直接影响士人的进取心。继孔子之后的孟子,也讲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7](P358-359)有机会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要“志泽于民,兼济天下”,不得志的时候要独善其身,同时出仕、入仕也要与社会的“道”相一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7](P370)世道清明时,为道奉献出自己的才智,社会黑暗时,不屈就于混乱的世道,坚守处世的准则。孔孟所谈的隐逸是与“道”密切联系的道隐。
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主流是崇尚入仕的,那么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则是与隐逸异曲同工的。司马迁曾这样评价老子“老子,隐君子也”,[1](P2142)老子不仅主张“清静无为”,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隐士的行为规范,“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1](P2141)庄子生活在诸侯争霸白热化的战国时期,为在乱世中自保,他隐居以求其志,他厌恶求名用智的行为,他认为“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两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8](P120)《庄子·天地》中提到尧治天下时,伯成子高立为诸侯。而当禹治天下时,伯成子高就辞职归隐山村种田去了,禹问原因,伯成子高这么回答“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8](P334)也说明了因为政治的不清明自由,所以士人选择隐逸。
到了魏晋时代,玄学成为主导,它在《庄子》《老子》《周易》的基础上形成。在大动乱的年代,儒家正统观念失去约束力,士人的情趣和追求发生变化,他们任情纵欲,回归到本真的生命状态。玄学从以“无”为本的正始玄学,到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学;再到西晋,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名教与自然”合一;再到东晋,玄学不仅与名教合一,并融入佛教思想。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9](P368)不错,隐逸本身需要选择安静的环境,多数隐士居住在山林崖壁之中。这与佛教的修身养性观念一致,东晋不少僧人隐居名山,《宋书》中多次出现的名僧慧远、法崇、支僧纳均为这类隐士。“晋宋时代,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不安之中,佛教的出世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被更多的文人所兼纳,于是清谈佛老成风。不少人高蹈遨游,啸傲于山水之中,通过山水体玄味道。”[10]关于西晋儒道合流的情况,段春杨博士已在其论文中进行了分析。[11]《宋书》中的隐士更为特别的行为之一就是与名僧交好,《宋书》中的隐士不同于之前史书中隐士的行为之一就是与名僧交好,如戴颙擅长画佛像,宗炳、周续之、孙淳之、沈道虔、雷次宗、关康之等的人物传记中均可看到其与名僧的联系。这不仅可以反映出佛教在魏晋的大发展,而且显现了不论玄学还是佛学,在追求自由与清净这一点上是异曲同工的。
儒、道、玄、佛各家思想,其追求与侧重虽不同,但在世道荒乱、社会黑暗的背景下,均讲求自身的清净与自保。就隐逸这一主题而言,各家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追求远害、保身。
三、隐逸与政治的关系
《宋书·隐逸传》详细记载了18位隐士,他们或居住在会稽名山,或笃学好文艺,或与名僧交好,其引人关注的一个特点便是,其中有不少亦隐亦宦的隐士。
亦宦亦隐,即为仕与隐交叉进行,界限不明显。为什么隐士与政治生活藕断丝连呢?原因有二,其一便是统治者。《宋书》中所载的隐者,均有记述皇帝、藩王邀请其出山为官的事例,这些隐士也是多次“不就”“不省”“并不就”。就统治者而言,一是这些隐士有着更强大的济世之才,有着良好的品德操守,邀其出山更能够协助自己的政治统治。二是邀请隐士更能彰显出统治者亲和力,以及对隐士的尊重,皇帝对隐者的出手相助与支持便能体现这一点。宋世祖刘裕对隐者很敬重,多次给予隐士物质、资金的支持。如周继之,高祖“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月余,复还山”,[5](P2280)“高祖北伐,还镇彭城,遣史迎之,礼赐甚厚”,[5](P2281)高祖称他为“真高士”,可见高祖对周继之的隐居生活是不断干预的,他的隐居生活并不纯粹。还有解职后再为官,之后再解职的阮万龄,他的隐居是在解职的夹缝中,如果时机成熟,他可能还会选择为官。还有贫困的沈道虔,武康县令支助他办学教徒,被太祖听说后,“赐钱三万,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5](P2292)“太祖敕郡县令随时资给”,[5](P2292)可见,太祖对隐士生活的关心和慷慨。同样,还有隐退不交事务的雷次宗,他的《与子书》讲道:“但愿守全所志,以保令终耳。”[5](P2293)他隐居是为了守志保身,但面对皇帝的征召,他也只能屈从“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5](P2294)他的进和退都是为了保身。隐士为什么与社会藕断丝连呢?王瑶先生这样分析,“因为他们并没有反抗或不满的意图。如果可以征他们出仕的话,是可以表明当局的搜扬仄陋的苦心,如果他们还坚持想作‘草莽臣’而不愿屈节的话,当局也不妨成其情,这是与唐虞盛德媲美的。一个时代有这样多的清高逸民,且表示了统治者的仁德广施,泽被天下的治债。”[12](P199)这是从统治者的角度看,统治者对隐士生活的资助或提携,不仅反映出统治者的慷慨,更能衬托出当局的高尚品德。
其二是隐士自身和他不可避免的社会关系。就隐士自身而言,作为一代臣子,他们又很关注社会生活。王瑶先生讲,“隐士如果完全是遗世的,那就应该没有什么事迹流传下来;正因为他们对现实不满,才有了逃避的意图,但‘不满’本身不就表示他们对现实的关心吗?真正遗世的人对现实应该是无所谓‘满’与‘不满’。因为不满才隐逸的人,实际上倒是很关注世情的人,所以‘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并不是一件可怪的事情。”[11](P197)因为隐士看不惯世态人情所以选择隐逸,而这份看不惯不正表明他对世态的关心吗?还有,隐士不可避免的亲属关系、君臣关系,这些在君主专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动摇的。从亲属的角度看,隐居需要物质基础,虽然也有像翟法赐这种居于原始人状态的隐士,但毕竟是少数。戴颙的哥哥生病,戴颙无奈之下“乃告时求海虞令”[5](P2277)来解决哥哥无药医治的问题。周续之对高祖命令其讲授“礼教”也无法推辞。同样还有雷次宗,徘徊于仕与隐之间,“仕”是听命于皇帝,接受其物质、资金扶持;“隐”是为了守志,两者的目的均是为了保身,就连“隐逸之宗”陶渊明也无可避免地为了生计而做官“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5](P2287)“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5](P2287)他做官是为了解决生计,为疾病求得医药费,但他实在无可忍受官场与内心所守原则的冲突,于是甘于贫困的他归隐南山,种篱修菊,秉清高之心,怡心中之志。
这些隐士,为坚守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而选择隐逸,但为了保身,他们又无奈地徘徊在仕和隐之间。不论仕还是隐,他们都是政治清明与否的晴雨表,因为隐士的身份,让他们无法割断政治生活。所以在对“隐逸”的坚守中,他们呈现出徘徊摇摆的状态。
综上,《宋书·隐逸传》在继承前代正史隐逸传的基础上,反映出刘宋时期隐士亦隐亦宦的特点。了解这群隐士不仅可以反映出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且可以关照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动向。隐与仕在中央集权制环境下是不可避免,也是历久弥新的话题。不论是先仕后隐,亦隐亦宦,还是先隐后仕再隐,都是为了更好地保全自己,更好地坚守内心原则。由此看出,隐与仕是处在一个易于变换的尺度内的。隐士的身份是避世的,其根源是关心时政的,所以《宋书》中亦宦亦隐的隐者,是隐士与政治不可分割的表现,也是恪守内心准则与修身自保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沈约.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宗白华.美学散步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李亮伟.隐逸与古代山水文学[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3).
[11]段春杨.徘徊儒道之间——西晋作家的思想及文学发展趋向[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11).
[1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责任编辑:张庆
Development of Hermit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ng Annals·Hermits”
YANG Zhi-juan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Song Annals·Hermits”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y record about hermits in Song period. The previous history books tell the linear development trace of hermit culture. To explore the philosophy of reclusion can understand the hermit’s ideas. They,either as officials or hermits,were out of the purpose of sticking to their philosophy and saving their own lives. Although there were special they still could not cut themselves from the feudal ruler.
Key words:“Song Annals”;Biography of the Hermits;hermit culture
[收稿日期]2015-06-08
[作者简介]杨志娟(1992-),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5—0046—0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5.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