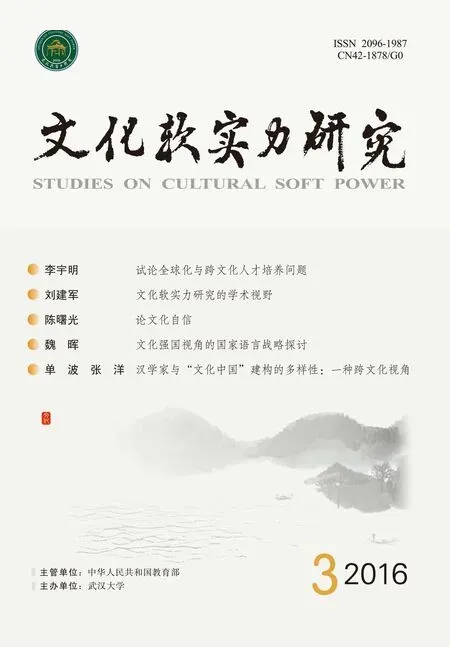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世嬗变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文化滋养
2016-03-16吕惠东
吕惠东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世嬗变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文化滋养
吕惠东
近世以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困境与新生的嬗变过程,表现为从“中体西用”到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和从“诸子学复兴”到现代新儒学的兴起。留存创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关于世界观与本体论、科学辩证法、人类未来社会理想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 近世嬗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 文化滋养
笔者认为,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以下阶段:“五四”及建党初期,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萌芽酝酿期;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中期是其初步形成时期;延安中后期是其基本形成时期;新中国成立后17年是其研究深入并不断政治化时期;“文革”十年是其遭受挫折甚至中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是其融合中国改革实践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学术新生时期。具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各种主义、思潮、学术流派竞相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亮相,几千年内生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和西学冲击,经历了自我解体、嬗变与新生。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正经历由选择性应用到学术性研究的跨越,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体系的初步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良好的历史契机,并使其深深根植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之中。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世困境:从“中体西用”到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学为主流,与诸子学、佛学共同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自董仲舒始,儒学就始终处于主流、主导、独尊的地位。在世界相继进入工业文明后,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统治的理论根基,却成为制约中国步入世界工业文明大潮最主要的伦理束缚。近世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和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下,儒学已没有主动选择的自由,要么革新自我,融入世界潮流;要么抱残守缺,走向历史的殉葬场。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步伐与中华民族遭受民族危机的程度是同步的、成正比的。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西学思潮”的双重冲击下,古老的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同时,维系中华古老文明的精神文化——儒学的命运开始告急。儒学面临两千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中学”与“西学”自此展开了长达百年的较量。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及影响
首先,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人,他们既想维系传统的伦理道德,又希冀通过改革来达到挽救日益衰微的晚清帝国的目的。他们吸取了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观念,人为地将西方文化分为“体”与“用”两个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取其“用”,而遗其“体”,这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西学”只是“夷学”,是不能跟融合了“儒、释、道”于一体的中国文化相提并论的。中国传统的“夷夏观”无疑还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但他们毕竟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
其次,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认识中西关系上更向前进了一步。1861年,早期改良派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的论点。此说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所接受,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其本质上是以中国传统的“器变道不变”为依据,提出以西方器物技艺之用,维护中国纲常名教之体。李鸿章曾说:“顾经国之路,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认为西学乃“偏端”、“异学”、“仿习机器”,只能“治标”,唯有中学能“培养国本”,“中国文物制度”才是“郅治保邦”的根本。早期维新派的郑观应也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盛世危言·凡例》。。这表明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皆认为中学是治国之根本,西学只是奇技淫巧,是治国之末端。
一直到张之洞等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才有了较之“中学”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张之洞之前,沈寿康、孙家鼐等都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行了初步的阐发,但赋予“中体西用”说理论形态、系统阐发的则是张之洞的《劝学篇》。张之洞以“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主线,强调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主张以孔孟之道、纲常名教来“务本”、“正人心”,以办“洋务”、设“五学”来“务通”、“开风气”。表面上是中学西学各司其职各有所得,其实质上仍是在维护封建统治根基的伦理纲常。在张之洞看来,大清即是国家,“保清”就是“保国”,他强调“三纲五常”乃“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他极力抨击民权学说以及父子、男女平等的理论。这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一个特点。
“中体西用”之说在学理上有诸多不通的地方,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是应对民族危机下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一个折中纲领。但“中体西用”论仍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主流学术思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起着决定作用。其融合中西的主张,相对前人本身就是一种进步,顺应了西学东渐、学新自强的时代潮流,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自“中体西用”口号提出并逐渐官方化后,在中国就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的热潮。其一,洋务派兴办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式学堂。例如开设同文馆,开设学习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的专业学校,学习外文、工程技术和近代军事技术以及自然课程等。其二,派遣幼童留学欧美。洋务运动期间,官费留学生达二百余人。其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为中国铺设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甲午海战著名将领邓世昌、刘步蟾,以及近代传播西学思潮的严复等等。他们通过应用西方的技术和管理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三,翻译和出版西学书籍。在洋务派主持下,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书籍,涵盖外交、军事、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医学等近代各门学科,不仅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为中国学术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思想史发展中古代与近现代的一道分水岭,是学术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由古代迈向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此为起点,维新改良思潮得以高涨,革命思想得以酝酿萌芽,顽固保守思想则渐渐沉默以至衰竭。它的合法化,不仅凸显了西学的价值,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打破了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国落后、封闭和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从此“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变革,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它的合法化起到了强化民族整合的作用。“中体西用”内在地包含着团结爱国的民族意识,既是民族危机下的一种方法论选择,又在中国现代化、世界化进程中注重自身的民族特色的保存。例如,不能否认康有为的“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与“中体西用”的口号是存在一定历史关联的。因此“中体”是中国在“西化”过程中联结中华文明的一条精神“纽带”。*参见薛其林:《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7页。
随着历史潮流的涌动,“中体”所固守的一些文化阵地逐渐被“西学”所代表的现代化、世界化潮流所蚕食。从西方器技的引进到学理的引进,从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到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进而到倡言变法鼓动革命,再到文化伦理的自我西化等等,都是在“中体西用”这块招牌下进行的。“中体西用”的口号可以看作“西学思潮”初起时在融入中国文化学术所遭到的第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儒学这一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国主流学术思想对日益强大的“西学”的最后抵抗。这道障碍逐渐扫除之后,儒学独尊的地位逐渐不复存在,“西学思潮”开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大踏步前进。
(二)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
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文化,在近世西学思潮的冲击下,其文化主导地位逐渐丧失,成为封建遗旧的代表。民国初期,在受到西学新文化进一步批判和打击的情况下,儒学独尊的地位最终终结。
1.辛亥革命后儒学地位的变化
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其政治功能亦宣告终结。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临时约法》的制定,首次在制度上宣告了儒学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终结。
中华民国的成立,还结束了儒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垄断地位。忠君、尊孔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学的宗旨和方针。1912年2月,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参见高叔平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主张废除清朝的封建主义教育宗旨,代之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教育杂志》第4卷第7号,1912年10月10日。。1912年10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取消经科,将其并入文科,要求大学应以研究教授高深学术,养成国家需要的硕学闳材为宗旨。*《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载《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1913年1月10日。同时要求小学废除读经科,初等小学男女同校。这样,在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中,儒学及其典籍彻底丧失了其在中国教育系统的主导地位,这对儒学的传播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转折点,自此儒学的社会影响力大大削弱。
当然,儒学思想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社会影响力已深入两千多年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中,不可能因为一场政治风暴就土崩瓦解。政治系统中的封建复辟流、文化领域中的顽固保守流,在某个历史节点上就会跳出来打着儒家封建伦理的幌子招摇过市。从1913年下半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打着“尊孔”的旗号,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封建复辟的逆流。康有为、严复等人也对“废止读经”的规定竭力反对,哀叹民国成立后,政体答辩,礼教不存。加之后来的张勋复辟等等,一幕幕的民国闹剧不断上演。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自由、平等、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和时代趋势,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交锋中,儒学逐渐败下阵来。当然,中国社会文化走向民主科学的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
2.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
如果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国家制度、法律层面终结了儒学独尊的地位,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从文化思想和学理层面对儒学做了历史性的时代判决。
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吴虞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学人,不约而同地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整体性的进攻。尤其是《新青年》周围的一批学者,毅然举起了“打倒孔家店”*关于“打倒孔家店”一词的来源,彭明、杜圣修等考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及学人论著中均未发现“打倒孔家店 ”的记载。宋仲福考证最早使用“打倒孔家店”概念的是“全盘西化”派学者,1924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刊登了《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认为“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全盘西化”派的主要代表陈序经在30年代亦提出了“提倡打倒拥护专制政治的孔家店”的号召(参见宋仲福:《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考察》,《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这使后人从不同意义上把“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礼教的代名词。的旗号,以批判儒家封建礼教为切入点,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新文化运动。
(1)新文化运动对儒学所宣扬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儒学自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以来,历朝历代,不论是封建君主还是官宦文人,都依着维护封建统治的名义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修饰,使其成为封建礼教的核心基础。新文化运动的成员大多从礼教层面或对儒学的内核展开激烈的批判,他们第一次以明确的文化批判立场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化历史。
面对民国初年封建遗老“尊孔读经”、“维护礼教”的吵吵嚷嚷,陈独秀率先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进而开辟了一个文化的新时代。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大声疾呼:“举凡残民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5页。号召青年以“民主”与“科学”两大武器向腐败的封建意识战斗。在《一九一六》一文中,陈独秀批判了儒家思想的“三纲”核心说,指出其使两千多年来的国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他号召全国男女青年,“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一九一六》,《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针对袁世凯打着“尊孔”旗号的复辟,将“孔教”写入宪法,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陈独秀以“孔教”为民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障碍进行了集中批判。“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封建社会把孔教作为唯一国教使国人全面信奉。“蔑视他宗,独尊一孔,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陈独秀:《宪法与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4页。“今乃专横跋扈,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国家,独尊祀孔氏,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去化民善俗之效也远矣”。*陈独秀:《宪法与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5页。“故今所讨论者,非孔教是否宗教问题,且非但孔教可否定入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也。此根本问题,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不得不急图解决者也。”*陈独秀:《宪法与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6页。
在猛烈批判“孔教”的基础上,陈独秀指出了中国儒教现代化以及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出路:“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宪法与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8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无疑是批判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最为猛烈的斗士之一,也是传播西学思潮以唤醒国民产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旗手李大钊,也对孔教儒学、封建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李大钊针对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一荒诞的事件,指出:“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入之宪法”;“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孔子是国民中一部分人的圣人,宪法是全体国民共同遵守的律例;孔子之道含混,宪法之义,效力极强。*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59页。李大钊认为二者无论是范围、效力、理念、适用对象等皆不可混杂在一起,要施行现代之民主政治,必须将孔教踢出国家政治生活。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时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184页。
此外,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形式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刻、无情的批判,他深入思考中国国民性这一深刻的主题,直面黑暗的社会、麻木的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指出这都是封建“吃人的礼教”造成的可怕后果。鲁迅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令国人窒息的礼教的“铁屋子”,给中国一个光明的未来。吴虞在《吃人与礼教》等系列批判儒学封建礼教的作品中,抨击了礼教对社会的危害,指出“孝”是孔子伦理学说的起点,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上述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现实造成的危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之一,其深刻性至今仍影响较大。
(2)在中西学术与文化对比的社会现实和学理依据的基础上,优劣已显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陈独秀大力倡言:“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页。他在《新青年》撰文明确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页。吴虞也指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他还把儒学利于专制、不利于共和的弊端概括为三:尊先祖与隆君师并称,尊君尤甚;持宠固位,取媚于上,同于妾妇,去公仆之义绝远;实行愚民政策,不开民智。新文化运动的学人认为,儒教与共和是绝不相容之物,提倡孔教必背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学。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代表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心声。因此,他们批判儒学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在中国提倡西学,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
(3)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虽有偏激,但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儒学、打倒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学人对儒学及传统文化的批判,只有极少数是绝对的偏激派,例如钱玄同,他主张“废除汉字而代以罗马字母”,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钱玄同认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并断言:“二千多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是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但钱玄同毕竟只是代表了一小部分学人,大部分人对儒学的批判虽有偏激,但并不是全面否定,我们应该结合具体语境作深入分析。例如陈独秀,在1916年以前,他对儒学的批判并不激烈。1916年以后,他才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学说。但综观陈氏一生,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儒学,对孔子本人,也有具体的评述。他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陈独秀:《孔教研究》,《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2页。李大钊也声明:“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人批判儒学,主要是批判其中与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相悖逆的东西,批判与封建专制主义相一致的东西,而不是要彻底打倒儒学、否定儒学,更不是要“全盘反传统”。
经过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不适于现代政治观、学术潮流的内容进行的批判,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后一道障碍,也是最大的一道障碍基本清除,伴随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同时而来的是西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这为中国学术体系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萌生和初步形成的基本学术要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困境中的新生:从“诸子学复兴”到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一)“诸子学复兴”
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诞生了包括儒、墨、道、法、名等众多学派在内的诸子学。汉代董仲舒倡言“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其他的学派只能成为附庸,在中国近两千年的社会文化发展中缓慢前行,但也未中断。民国初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和对学术自由的倡导,诸子学获得了发展的有利契机。其研究逐渐繁荣,出现了被称为“诸子学复兴”的局面。
晚清尤其是民国以来,随着封建主义在政治上走向瓦解,孔子和儒学逐渐从正统独尊的神殿上跌落下来,重新评价儒学和非儒学派的思想价值和文化地位就成为历史的必然。1916年11月,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指出:“孔教乃中华之国粹。然旧教九流。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陈独秀:《宪法与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5页。这就从学理上阐明了中国传统学术独尊儒学之一家,对中国文化多元遗毒甚深,必须打破这种一家之言的局面。
正是在民国旧学解体、新学创建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诸子学借助这一潮流,结合新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现实,获得了新生,出现了创作的热潮。*参见郑大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民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35页。
(1)关于民国时期的道家研究。首先是有关老子年代的考证问题,胡适、张煦等人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老子生于周灵王初年,早于孔子;梁启超以及后来的顾颉刚、张寿林、罗根泽等“疑古派”认为老子其人其书成于战国末年,在孔子之后;钱穆、冯友兰等则认为《老子》晚于《庄子》,孔子问礼者与《老子》作者系两人。这是当时对道家学说研究的一个热点。其次是大量著作对道家经典与人物进行了考证。例如马其昶的《老子故》、奚桐的《老子集解》、陈柱的《老子集训》、蒋锡昌的《老子校诂》、严灵峰的《老子章句新编》、高亨的《老子正诂》、杨树达的《老子古义》、钱基博的《老子〈道德经〉解题及读法》、吕思勉的《经子解题》等著作,或从校勘、训诂的角度,或从史实考订的角度,对老子及其学说进行了研究。关于《庄子》的注释、整理相对逊色,但也有一些著作。例如,马其昶的《庄子故》、支伟成的《庄子校释》、胡远濬的《庄子诠诘》、朱文熊的《庄子新义》、马叙伦的《庄子义证》、刘文典的《庄子补正》、顾实的《庄子天下篇讲疏》等。再次是关于道家学说的现代新解。主要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部分内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部分内容、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的部分内容、王力的《老子研究》、郎擎霄的《老子学案》、《庄子学案》、蒋锡昌的《庄子哲学》等等。
(2)关于民国时期的法家研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开以法理学参酌法家学说的风气。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较早系统地把法家学说作为政治思想史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杨鸿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其中对先秦法家学说的研究集前人研究之大成。
(3)关于民国时期的墨家研究。首先是校注考证《墨子》及其作者。代表作有梁启超的《墨子学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尹桐阳的《墨子新释》、叶瀚的《墨经诂义》、张之锐的《新考证墨经注》、张纯一的《墨子集解》、于省吾的《墨子新证》等等。其次是阐释墨家思想学说。代表作有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墨经校释》,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的方法,从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和伦理学等方面阐释了《墨子学说》;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把现代西方学术规范运用于墨学研究,推动了墨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进程。此外还有陈顾远的《墨子政治哲学》、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张纯一的《墨学分科》、郎擎霄的《墨子哲学》、钱穆的《墨子》等等,皆用现代学术思想对墨子学说进行了新的阐释。再次是《墨辩》之研究。“《墨辩》复兴是民国墨学复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郑大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民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梁启超的《墨经校释》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此研究的先河。此后的代表作有伍非百的《墨辩解故》、邓高镜的《墨经新释》、郭湛波的《先秦墨学辩》、栾调甫的《墨辩讨论》、鲁大东的《墨辩新注》等等。民国时期对墨学的研究,无疑是繁荣的,其中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校勘、考证、注解等研究,还有用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结合现实的当代阐释,给墨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时代特色。
(二)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在儒学独尊地位终结后,一部分服膺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末期的儒家学说,在坚持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做了现代性的阐释,进而使儒学在现代学术思想系统中获得了新生。学界一般将其称为“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
一般认为,儒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先秦儒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二是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三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现代新儒学,它是对“五四”以来激烈反传统倾向的一种保守回应,是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抗。方克立认为,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主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依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构建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实出路的一种学术思潮流派。它主要是指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社会政治的内容。*方克立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90多年来,现代新儒学已经过三四代人的薪火相传,第一代主要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50—70年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为第二代代表;80年代至今,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等为第三代代表。本文主要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表现。
梁漱溟(1893—1988),是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也是两千多年来儒家传统的最后守护者之一。美国学者Guy Alitto(艾恺)称他为“最后的儒家”。在“五四”儒家思想遭到严重挑战的时候,在“打到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在“全盘西化”的社会迷离中,梁漱溟以儒者风范和勇者的魄力,对处于末路的儒学进行了大胆的提倡,并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其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及《人心与人生》等。梁漱溟的哲学汇合了中西印三方的思想,并以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现代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其思想中非理性主义倾向与理性主义的矛盾,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斗争的一个侧面。梁漱溟继承了儒家哲学中的性善论传统,接受了儒家哲学中注重反省内求的认识路线,并同柏格森哲学的直觉主义结合起来,构成其认识论的基础,进而构建其唯心主义宇宙观的生命哲学。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以全新的角度解释了中西文化之异的原因。他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分为以西方、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三种文化形式,并提出了对待他们的不同态度。梁漱溟对于时代问题和精神的把握极为精当,他不仅注重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阐扬,更注重对儒家当下的困境及儒学未来前景的展望。这既使梁氏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先驱,也是在各种文化流派中现代新儒家迅速崛起的原因。梁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切关注,对人类文化未来命运的思考,也使得现代新儒家能够在学术思潮激荡的时代迅速崛起。他对东西文化的把握,成为几十年来后人研究的主题。
熊十力(1885—1968),现代心性儒学的奠基者。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代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儒佛学说的恢复及新释这一重要倾向。它不但把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等熔于一炉,而且使辩证法思想贯穿于体系的始终。“新唯识论”体系既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凸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现当代价值,同时也解决了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境遇下,传统文化的出路和前途问题。熊十力也因此被称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现代新儒学的精神象征。
冯友兰(1895—1990),其创立的“新理学”代表了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的儒家方向,它尽可能消解道德生命过程中的虚妄成分,尽可能挖掘道德实践过程中的理性地位。冯友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著“贞元六书”形成其“新理学”哲学体系。新理学是现代中国哲学家自创哲学体系的一个典范,它吸收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和新实在论哲学,来表达传统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基本精神。新理学根植于现代学术意识,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具有清晰的形成系统的哲学体系,同时试图以现代理性精神来阐明和改造传统哲学。从儒学的角度看,新理学悬搁了道德形上学,使道德从“天地”回到“人间”,尝试由理性、理想解释道德,而不是由宇宙精神来解释道德。这一努力使儒学不再以神秘的、独断的宇宙本原为起点,它真正面对宇宙人生的客观性、现实性和复杂性,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形而上学之建构*参见陈鹏著:《现代新儒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94页。。
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君劢、贺麟、钱穆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开辟了儒学在20世纪的发展方向,使儒家思想及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他们的成就,在于能够吸收儒学之外的文化资源,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既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坚持本民族的特色,又不排斥现代文明的成果和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这也使现代新儒学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与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马克思主义鼎立于中国思想界的三大学术思潮之一。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也是带有欧洲的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性的学说。使这样一个同时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学说应用到中国,必然要实现其在中国的“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诸子学复兴”以及现代新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阐释、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术体系的中国化,提供了优质的传统文化资源。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毛泽东在讲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学习时也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这无疑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创作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有效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思想资源提供了方向指导。
(一)世界观和本体论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缺乏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春秋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经战国中期宋妍、尹文的“精气说”、荀子的“自然之天”,到汉代王充明确提出物质性的“气一元论”,再到王船山对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等等,中国本土文化中一直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物质观。另外,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也极为丰富,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王充的无神论、范缜的“神灭论”等等。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流派和精神之一。可见,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及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有诸多共通之处。这使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便捷地从学理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又更好地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借鉴和吸收,使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更具学理性,并深深根植于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土壤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辩证法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而辩证法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源远流长,李约瑟曾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页。。中国古代的“八卦”、“太极”的核心是阴阳观念。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先后提出了“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和实万物,同则不继”,“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长短相随”,“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进行继承发展之后,欧洲的辩证法思想才得以新生。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具有融通相似之处。这使得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时,具有了文化上的先入性。正如李约瑟所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这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3、67页。郭沫若在1925年《马克思进文庙》小品文中写道:“马克思到此才感叹起来: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孔子,引者注)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是一致的”。*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168页。这种东西辩证思维的共通性,使得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便捷、科学全面地学习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风靡全国”的现象,进而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初步形成提供了辩证法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三)关于未来社会理想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有着诸多共通之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这尤其体现在儒家的“大同”思想中。《礼记》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者有所终,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妇。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4页。近世以来,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台,康有为著《大同书》,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并在《礼运注》中说:“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这里的“大同”社会,“太平世”便是中国古人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自古至今,“大同”社会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所追求建立的一个人人平等、友爱、和谐的社会对中国的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这恰恰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建立财产公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你(马克思,引者注)这个理想社会和我(孔子,引者注)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正因为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学说作为底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和认知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时并未显得有太大的心理障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乘着社会主义的船舶来到了中国。这种文化共通性也使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好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学说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和方向的学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社会学学术体系的初步建立提供了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近世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国家民族境遇中,在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资源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样,无可避免地面临全面崩溃与瓦解的命运。此种情形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包容的文化态度、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与向往,使得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经历痛苦的自我革命后,获得了自我超越与新生。经过创新并留存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Modern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Cultural Nourishment of Chinese Marxism Academia
LvHuido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China)
Ever since modern times,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ism has gone through evolution of dilemma and rebirth manifested by Chinese essence and Western utility towards the end of Confucius status as the primary as well as the revival of the Philosophers’ school towards the rise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oth preserved and innovated has nourished the cultural 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academia while providing it with world outlook ontology and dialectics of science beside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 about human beings’ social ideal for the fu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Modern Evolution;Chinese Marxism;Cultural Nourishment
10.19468/j.cnki.2096-1987.2016.03.008
吕惠东,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党的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评价体系建构研究”(CCNU16A0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