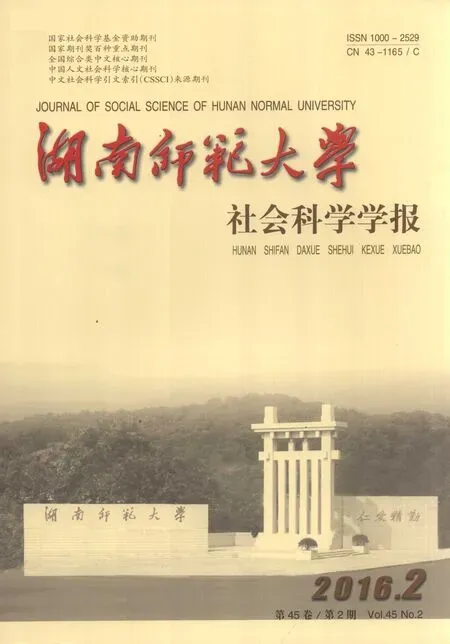福山转变问题:治理挑战视野下的中美政制比较
2016-03-16李风华赵会龙
李风华,赵会龙
福山转变问题:治理挑战视野下的中美政制比较
李风华,赵会龙
摘要:福山的转变意味着政制比较应当采取针对国家治理的动态比较分析。国家治理活动中天然内含着双重治理价值取向,一方面既要充分照顾到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又要在必要时实现迅速集中以满足对效率的需求。而在治理挑战之下,对及时有效性地追求似乎更加迫切。中美两国的政制在面临治理挑战时,显然强调民主集中的中国政制更有可能及时完成对民意的筛选,实现资源和力量的集中,以应对治理挑战,这也正是中国政制的优势所在。
关键词:治理挑战;中美政制;治理价值;优越性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英国、美国和苏联虽然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大体上都可以算作是有效能的国家范畴。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的创建相对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变革,致使新兴的社会势力无法在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内表达自己的利益关切。因此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力量只能游离于软弱而低劣的政治制度之外,以暴力、游行示威等极端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对现行的政治秩序形成巨大的冲击。并由此总结道:“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①。那么现代性国家会出现亨氏所言的政治衰败吗?同样,现代化中的国家会出现政治繁荣吗?
一、从历史终结到政治衰败:福山转变问题蕴含的治理价值
事实上,个别意识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检讨美国政制的根本问题了,这就是当年极力鼓吹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10月,福山撰写《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文章尖锐地指出美国政制过度强调民主制衡,致使其自缚手脚无法灵活运转,并据此认为美国政治体制正日渐僵化,走向腐朽。应该注意到,福山转变问题的价值不在于其结论,甚至也不在于其看问题的具体方法,而在于比较政治学重心的悄然位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罗伯特·达尔、林德布洛姆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全力以赴地证明资本主义政制与社会主义政制的优势。这种抽象出政制的特征进行静态比较的研究路径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达到顶点,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进程似乎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胜利。然而,社会主义并未如他们所期望的那般覆灭,而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焕发了新的活力,并且展现出一种强力追赶和超越的势头。眼看美国面临中国的崛起而仍然束手无策之际,极富历史趋势敏感的福山提出了美国政治衰败论,其真正的意蕴在于,静态抽象的政制比较路径的破产。
福山并不承认之前的历史终结的错误,仍然认为自由民主为历史终结。只不过在手段上更加强调国家建设,但事实上他所讲的手段变化本质上改变了其之前鼓吹的历史终结。而福山所以这样做,其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的崛起,使他看到中国政制在治理方面的巨大成果,相反,原来作为自由民主样板的美国,反而在社会治理方面举步维艰。因此,福山转变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政制应付社会治理的能力。自然,在社会治理方面,美国宪政体制下的治理结构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无论是横向层面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还是纵向层面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主权分立与制约以及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节制,这些都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的广泛参与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针对具体治理内容的公共政策要想实现预设的目标偏好,只保证其参与的广泛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保证公共政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忽视民主性可能会使公共政策失真,而忽视及时有效性则可能会使公共政策久拖不决。因此,本文认为国家治理活动面临着双重价值倾向,即民主参与性和及时有效性。在常规的治理活动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充分满足对民主参与性的价值追求。时效性同样是国家治理活动中追求的价值之一,而且在治理挑战下对它的需求则会更加显性化,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极可能会从民主参与性上转移到政府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化解矛盾上来。而且,我们确信随着社会治理挑战程度的加大,能否保证及时有效性往往决定着事态的发展。因此,福山所谓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理应从治理价值失衡算起,即过度强调民主制衡而忽视治理时效性,这种失衡在挑战治理面前更加表露无遗。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治理挑战,社会主义中国同样无法独善其身,它同样时刻面临着社会风险、长期变迁以及激烈国际竞争等治理挑战的冲击。本文以治理挑战为切入点,来比较分析中美两国宪政体制下治理利弊。本文将治理挑战概括为社会风险、社会变迁以及国际竞争。
二、社会风险视野中的政制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西达·斯考克波、彼得·埃文斯等为代表的“回归国家学派”强调国家自主性以及国家能力建设在政治革新、民族经济发展等广泛领域内不可替代的作用。《找回国家》一书指出虽然在特定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地缘政治等外交政策方面,美国政府能够相对“绝缘”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影响,但由于“没有从前工业化和前民主化时代所继承的中央集权式官僚政府形式,而且,联邦体制形成的权威分散、主权在全国性政府各个部门间的划分”②,使得其整体上缺乏自主性所需的结构性基础。福山所讨论地美国政制的衰败,同样基于特定国内制度安排下的结构性基础。然而,政治结构特征塑造出的治理价值倾向深刻地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绩效,这一点却并非是“国家自主性”一词所能意达的。美国由治理价值失衡所引起的功能性障碍,在面对社会风险等治理挑战时更加显性化。社会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跨区域性以及短时间内巨大破坏性等特点,它对治理时效性这层价值要求非常高。在面对具有如此特征的治理挑战时,以政制为支撑的国家治理活动要想取得相对良好的治理绩效,必然需要相应的具备以下方面的比较优势,即应急反应能力、快速区域协调整合能力以及短时间内组织动员能力。因此在应对社会风险这类治理挑战时,中美两国究竟谁更有优势,就要看国家治理背后的政治制度因素谁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为以上三种能力。
第一,应急反应能力比较。突发的自然灾害是对一国应急反应能力的巨大考验,同时应急反应能力的强弱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的绩效。而本文认为应急反应能力又主要考验的是问题意识和效率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一国政府能否对事关民众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始终保持高度的灵敏性,也只有将人民的利益、群众的安危浸入一国执政的根基、治理的肌理,才能始终保持警觉性和灵敏性。所谓效率意识是指面对治理挑战时不仅要有问题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及时高效地将强烈意愿付诸实践的能力。只有问题意识和效率意识相结合才能构成相对强大的应急反应能力。
问题意识的塑造,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一国政权的性质。虽则如此,现实的政治运行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扭曲、再造问题意识。例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也早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也总是教导“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③。然而政治运行的现实却使我们认识到,“向人民负责”、“向人民服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约束,“向上级负责”、“向领导负责”却是不折不扣的现实。反观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成熟的市民社会,发达的政党政治,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政治运作的现实。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论证说,“任何一个人,当他自己能够并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时,他的权利和利益才能确保不被漠视。”并由此认为,“让所有的人去分享国家主权才是最可想望的”④,而多层次宽领域的选举政治为民众“分享国家主权”提供了可操作化的渠道。所以美国民众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公共权力,发达的民主选举制度也为执政者倾听民意提供了巨大的动机。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问题意识上,“向下负责”的美国至少是不比“向上负责”的中国差的。
然而,问题意识的强弱仅仅是应急反应的单一层面,要甄别应急反应能力,对效率意识的考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在“向上负责”的中国,“中央的权力范围不受中级或地方所保留的权力或责任的限制,中央干预省级甚至地方和基层事务的事情相当普遍,下级的任何重要行动都要向中央报告”。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结构的组织原则。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决策之前应当是完全民主的,而在执行时就是完全的集中主义”⑤。这就充分保障了党委统一领导,议行合一,避免了相互牵扯,而这恰恰为救灾赢得了宝贵时间,使灾害的危害面降至最低。虽然决策前的民主程序尚有待完善,但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高效性却是美国无法望其项背的。须知,在灾害面前,我们的治理价值在于“效率优先兼顾民主”。
第二,区域协调能力比较。自然灾害不仅具有突发性特点,而且它们的发生往往是跨区域的。常规的国家治理活动,一般是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进行的,而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影响面大,涉及不同的行政区域。因此,要想有效地应对治理挑战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区域协调能力。单一制下的中央选择性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是中国现实的国家结构模式,执行中央的政策法令是地方政府应尽的职责。因此在应急治理过程中就可以“做到既有统一领导,也有有效沟通与协调的多方协作治理,从而大大提高应急的及时性、动员的有力性和救灾的有效性”⑥。
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在这种国家结构下,“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两种政府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⑦。“两种政府相互控制”的前提是州政府享有足以对抗联邦中央政府制度化的自主权力,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治理活动侧重于强调州级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这套治理模式在常规的治理活动中自有它的优势,例如,由于美国的治理结构强调责任主体的相对下移和治理服务外包,在行政成本上可能要比中国低。但是,在面临自然灾害这类治理挑战时,这套治理模式却可能面临着协调性差的困境。联邦政府并不像中国中央政府那样拥有制度化的区域协调的渠道,它更多依靠的是联邦中央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漫长的讨价还价。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完成一定范围内区域协调,中国的效率可能会更高。
第三,组织动员能力比较。自然灾害的发生,除了具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特点外,往往还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的灾难。这就意味着单靠某一受灾区域自身的资源和力量是难以有效应对的,因此这也就必然要求有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来填补受灾区域资源和力量的缺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生态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不仅有着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的组织体系,并且对每位党员都有着严格的纪律管制。党组织内部的组织动员活动往往具有政治任务的性质,而且由于党组织深植于基层,党内的组织动员对全社会往往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同时中国的组织动员能力还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即政府层面、政治性社团层面和社会层面得以保障和强化。政府层面,中央政府可以以法令政策的形式向下级政府进行政治动员,例如汶川地震发生后,就共动员了19个省级单位参与对地震灾区的对口支援;政治性社团层面,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政治性社团(工、青、妇等),在规模上都是全国性的,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动员自身成员来支持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层面,汶川地震后,有9万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灾区重建工作;23个省市12 355个灾区青少年心理康复援助专家志愿团,496名心理专家参与灾区心理援助,辅导个案3 417个。
美国政党内部没有严格的政党纪律,党员对党的领袖、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也并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与中国相比,美国政党内部的组织动员更多依靠的是规劝。而且民主党与共和党,都缺乏有凝聚力的全国性组织。两党全国性松散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产生于州一级的党组织,而州一级的党组织则成为各自为政的权力中心。同时,党派之间现实的利益纷争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对峙,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后才能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完成组织动员活动。因此,在组织动员面前,缺少纷争且有着严格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动员显然比简单的劝说式动员更加有效。
在治理自然灾害这类社会风险时,显然,强调民主集中原则的中国政制比强调民主制衡的美国政制更有利于实现“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治理价值。
三、社会变迁视野中的政制比较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文使我们认识到,过渡型国家由于没有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新崛起的社会力量只能游走于体制之外,对现行脆弱而低效的政治制度造成巨大冲击,政治衰败因此而来。当然对于现代性国家而言,政治制度相对来说高度发达,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不仅高度复杂且获得了全社会高度的认同,它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集团提供了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它所能容纳的社会活动范围也极大的膨胀。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任何“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便会发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⑧。美国就是其中的典型。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做出一定调整,迟早都会面临治理结构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窘境。因此长远地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社会变迁的治理挑战,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政制下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做出制度变更。要想使政治制度对社会变迁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并能够随之做出一定革新则至少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政治势力的非均衡化;其二,优势政治势力应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一国政治生态中,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势均力敌只会导致社会分裂,只有存在相对优势的政治力量才能起到一种整合作用,才有可能在社会变迁中起到引领时代进步的作用。同时,占据相对优势的政治势力还必须有着足够的智慧以辨识环境的变迁,进而承担起历史责任的重担。接下来,本文将从以上两个层面来对比分析中美政制在面临长期社会变迁时的优劣。
第一,政治势力力量的对比。欧洲民族国家的创建有赖于封建王朝权威的相对加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经济的崛起建立在威权体制基础之上;拉美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摆脱亨廷顿所谓的“普力夺”社会,就是因为军事政变剔除了各政治团体的相互倾轧,使得政治秩序得以重建。同样,要想有效应对长期社会变迁这类治理挑战,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权力的集中仍是不可或缺的因子。中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在法理上,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中国共产党享有绝对的权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国政治版图中居于绝对超脱的地位。在中央层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国家结构上的单一制也使得中央的绝对权威较少受到来自地方的威胁。在中国,政治势力的非均衡化是政治现实。
继承中世纪英伦遗风,美国1787年宪法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分权制衡体制。国会内部参议院与众议院之间,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联邦与州之间,从整体上看均被赋予势均力敌的公共权威。这是因为美国制宪者们认为“只要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置于同一机关手中,不管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许多人,不管是世袭的、自行委派的,还是选举的,我们都可以公正地断言,这就是暴政。”⑨出于防止“暴政”的现实考虑,“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的制衡逻辑赋予了政治势力势均力敌的力量。而宪政结构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尖锐对立,等于在宪政结构上的权力对立外叠加了第二层的党派对立,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因而更加强化。
中国政治势力的非均衡化既是政制结构设计使然,更是政治生态中的基本事实。相较于中国,美国政制结构的设计更多考虑的是公共权威配置的均衡化,现实的政治运作更是如此。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能够顺利推进每隔五年一次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奥巴马政府单单是推动一个医疗体制革新就困难重重。当然政治势力的非均衡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确实给中国造成过巨大的悲剧,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但请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种可能性,即面对社会变迁这类治理挑战时谁更有可能有效地应对。
第二,政治势力历史责任感的对比。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地变化发展,要想实现及时有效性地推动体制机制革新,仅仅拥有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探究这股力量的性质。如果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在社会变迁面前不能克服眼前的和局部的利益诱惑,甚至说不能克服一己之私,承担起应有的历史重任。那么,我们虽不能武断地认定它必将是“恶水之源”,至少也是与治理挑战无益的。在美国,多元主义、多元参与是其政治制度之所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石。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借用“派系”一词对利益集团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所谓派系,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中的多数还是少数,受某种共同激情或利益所驱使的,联合起来公然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长久与总体利益”⑩。而之所以会出现“派系”利益与“社会长久与总体利益”相冲突,在奥尔森教授《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有着详尽地论述。奥尔森认为,在增进集团利益的路径选择上,利益集团往往倾向于在既有社会总利益存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自身所占“蛋糕”的份额,而不是努力增进社会整体福利。这是因为相比之下,前一种路径选择成本巨大,而且本集团所占社会总收益的份额微乎其微。由此,为实现特殊利益,利益集团必然会侵入政治领域,渗透政治决策过程。他们“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此之故,用分蛋糕来比喻社会收益的重分配还不够恰当,更近似的比喻是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还会同时打破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⑪。在西方选举政治的前提下,为了迎合选举的需要,政治势力也往往具有主动接近为强大利益集团所裹挟的“民意”。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到治理的时效性,更严重的是利益集团对政治生活的渗透、把控,不可避免会使政治机器与社会整体变迁产生“隔绝效应”,使其无法及时有效应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治理挑战。“隔绝效应”一旦产生,历史责任感就无从谈起。历史责任感意识淡薄,伴随社会变迁,适时高效推进政制革新更是空中楼阁。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社会正开始经历着由单一的社会构成向多元型社会转变。利益格局剧烈地变动,使社会中能够参与和影响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利益团体逐步形成。更有甚者,中国已经出现足可抗拒全面深化改革,危害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中美两国利益集团本身及利益集团与政治机器间的关系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服务于本文目的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如果说美国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多元主义”之上,那么中国式利益集团则更倾向于是建立在“法团主义”之上。著名法团主义理论家施密特认为,法团主义是指社团“被国家承认或由国家同意(如果不是创立的话)而建立,并在各自的领域内被特意授予代表的垄断权,作为交换,其领导人的选择、要求和支持的表达,要受到国家的某种控制”⑫。如中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社会团体必须挂靠一个行政部门,并接受其监督和领导,这一点与自由结社的美国是根本不同的。“多元主义”基础之上的利益集团与政治机器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单向度运行模式;而“法团主义”基础之上的利益集团与政治机器之间的关系则更多的是一种“上下互动”的模式。其二,多元民主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石,更是其合法性的根基。而利益集团的存在则是其多元民主的具体表现之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多样化利益集团的存在就是其合法性的根基。这也正是美国政治机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特殊利益集团“痼疾”的根源所在。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则建立在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其合法性的重心则逐渐转移到推动经济社会迅速现代化上。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强大到可以妨碍经济社会发展时,政治机器就可以以重构其合法性为强大动力机制,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遏。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⑬。而在美国,利益集团却恰恰是其政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由此显而易见的是,第一个层次的差异,使得在面对社会变迁治理挑战时,中国政制更有力度;第二层次的差异,使得中国政制在面临社会变迁治理挑战时更有动力。
社会变迁此类治理挑战,同样需要一国政制能够提供及时有效性的治理价值。只有如此才能在社会变迁中不误时机,与时俱进。虽然中美两国在社会治理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科”现象。但在社会变迁等治理挑战面前,治理价值客观上要求侧重于及时有效性,与美国相比,显然中国政制更有利于提供这层需要。
四、国际竞争视野中的政制比较
历史上,国家综合国力的生成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自发模式;一类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为模式。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如英、美等国依靠市场的力量,通过对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等原则的运用,成就过不可一世的帝国力量。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如德、日等国则直接依靠国家的力量强力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告诉我们它应该属于第二类国家。进入21世纪,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白热化的国家竞争同样是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面对这类治理挑战,主权国家首先必须具备及时有效地完成自身力量的整合,即有能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和力量加以统一调配和运用以形成合力的潜能。如果自身整合能力不强或很弱的话,国将不国,就更不要谈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了。其次,还必须具备将合力转化为连贯且持久的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只有主权国家能够有效地实现自身力量的整合,并且有强烈的意愿将之转化为落实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的动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由此,中美两国在应对国际竞争这类治理挑战时的对比就转化为两种模式之间的比较,即市场主导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在生成国家整合能力和推进国家发展战略能力方面的对比。
第一,国家整合能力的比较。国际竞争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以主权国家为计量单位的,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往往以单位国家的整体实力来衡量。因此,一国内部整合能力的强弱是国际竞争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历来是美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最大共识。这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就是多元民主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群体的利益是高度分化的。麦迪逊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造成派系之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⑭。应当鼓励基于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通过组织化的力量进入政治领域,争取自身利益。由此,政治成为经济领域中高度多元化市场主体之间自由竞争以争夺利益的另一个舞台。“政治本身构成了一个市场,而政党与政客则构成了这个政治市场上的掮客,为各种社会力量代言。”⑮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美国政治仅仅是为社会资源和力量的配置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资源和力量的分割则主要依靠的是多元化社会力量之间的讨价还价。政治市场化的治理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政治稳定,因为政治是向社会力量开放的,任何势力都可以自由进出。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该治理模式则无力提供积极的支持。由此,美国国家整合能力的形成主要依靠的是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实现资源和力量的整合,政府或曰政治力量并不主动承担国家整合的义务,它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进程中自发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能够实现最优化的政治稳定,但每一次利益的重新组合,每一步前进的取得都要经过原子化的市场主体之间漫长地讨价还价过程。然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效率、及时有效性的追求却有着独特的偏好。这是美国政制下,治理价值失衡的又一明例。然而在中国,政治绝非仅仅是作为市场主体竞争的舞台而存在。国家不再仅仅是多元社会力量利益交换的平台,相反,它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国家资源和力量的整合过程中充斥着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是以公共权威为主导的有意识的自为行为,而不是历史过程中自发性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中国有一个整体利益型政党,它不代表某些个人、团体、党派的局部的、狭隘的利益,它能够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而实现国家迅速有效地整合,增进全体人民福祉存量,打造一流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所在,更是巩固其执政合法性所必须。这一点从根本上区别于美国的多元民主理论及实践。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特定的国际竞争领域,如航空航天领域,中国取得同样的成绩往往要比美国耗费更短时间的原因。
第二,推进国家发展战略能力的比较。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极强的内向倾向性,其政党往往迫于迎合内部的民意,而不能做长远考虑。一旦内部政治市场上出现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左的所谓“民意”时,资本主义选举式民主往往会迫使后者让位于前者。内部民意市场对国家发展战略产生巨大影响的例子,在美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中更是屡见不鲜。2013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因无法达成政府新财政年度的预算案,非核心政府部门被迫关门达16天。而奥巴马总统也迫于处理国内政治僵局而缺席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当然因国内政治原因缺席国际会议本来也无伤大雅,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国家发展战略地推行,但至少国家形象还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的。更有甚者是美国竞争性的两党政治,这使得国家发展战略总免不了受五年或十年一次的政治局势摇摆的影响。比如在国内政策上,共和党偏向于对富人减税、减少财政支出等,而民主党则主张向富人征税、扩大财政支出等;在国外政策上,如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时期奉行单边主义,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国际事务中则积极推进多边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健全,市场在社会主义中国得以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相对单一的社会阶层开始重新分化组合,市场主体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相应的,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利益诉求者。但是与美国根本不同的一点就在于,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的多元化,都是建立在有主导性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多元化。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领域这种结构体现得则更加明显,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总之,它始终存在着一个掌舵者。同时,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决定了掌舵者与参与者在根本利益上是高度一致的。这当然是实现民主基础上集中的保障,而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则能有效满足治理活动中对及时有效性价值追求的需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破除层层羁绊连贯推进良好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集中力量,从1953年即开始的“五年计划”则是最好的例证。
五、结语:政制比较必须持动态视野
福山转变问题近年来在中文政治学界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议。有的学者热诚地欢迎他的转变,认为他抛弃了原有的“历史终结”论;有的为福山感到失望,认为他的学术取向从来都跟随时势变化;还有的检索福山的前后论述,认为中国学界的高兴其实是一种误读,福山的民主立场并未发生实质性动摇。对于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福山本人的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转变从客观上反映了传统上对于政制的静态比较研究存在着本质性的缺陷。无论福山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当他把美国的政治衰败归咎于美国的政制本身的时候,传统上比较政治分析中往往为众多学者所暗暗接受的政制楷模——美国政制——已经不再那么光彩照人。
政制研究中,中国和美国无疑是人们必然拿来进行比较的对象。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着的治理挑战显然要远远超过美国。事实上,由于中国所面临的极大困难以及传统政治学所认为的中国僵化政制,使得“中国崩溃论”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非常流行。然而,尽管中国存在着远比美国更多的政治问题,其政制本身尚处在一个不断改革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但是人们都不难看到,中国政制在应付治理挑战方面要远远比美国做得更成功。
治理挑战当然需要民众的大智慧、需要多重力量的参与,与美国相比,尚处于完善中的中国政制在该方面也存在着不小的“偏科”。同样应该得以明示的是,在国家治理活动中民主参与性与及时有效性也并非是非此即彼、根本对立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设计更有利于实现治理角色间的转换——从民众广泛参与的引导者到及时高效的政策制定者。显然,缺乏“集中性”力量的美国政治结构使得国家治理活动在角色转换上出现了制度性障碍,而这样的不足在治理挑战面前更加凸显。相比之下,中国的政制建立在民主集中制之上,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虽然民主性基础尚处于薄弱环节,但“弱民主”比“弱集中”在治理挑战面前的优势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政制正处于变革、发展及完善之中,说它在政治上全面繁荣有点名不副实,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中国政制的基本结构在社会治理,尤其是挑战治理面前却有可圈可点之处。想必福山应同样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感慨美国政治衰败,否则的话,与世界上众多的失败国家或者衰落的日本、欧洲发达国家,美国不但没有政治衰败,反而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相当的成功。
我们认为,福山转变问题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观点,甚至也不在于其所引用的具体事实,而在于方法上的启示:传统的静态比较分析已经不再适宜。采取动态视野来进行两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比较,并进而把握两者的政制优缺点,这应当是比较政治分析所应当采取的路径。本文在中美政制比较研究方面,较多地对中国政制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中国政制的不足和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在反腐败、民权保护、基层政府结构等许多方面,美国仍然还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动态比较分析的理由。本文所提出的治理挑战只是动态视野的一个初步尝试,在这个方向,我们期待有更多学者的努力和批评。
注释:
①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②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页。
④John Stuart 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Liberal Arts Press,1958,pp.43.
⑤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⑥彭宗超:《政治制度对应急管理体系及其运行绩效的影响——中美比较的视角》,《新视野》2014年第2期。
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64-266页。
⑧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⑨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9页,第44页。
⑪(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1页。
⑫Philippe C 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In Frede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 eds,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 in the Iberian World,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 Press,1974,pp.85-130.
⑬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8页。
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7页。
⑮王浦劬、李风华:《中国治理模式导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The Issues of Fukuyama’s Conversion:A Comparis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Facing Governance Challenges
LI Fenghua,ZHAO Huilong
Abstract:Fukuyama’s conversion indicates that we should adopt the method of dynamically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erm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ctivitie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naturally contain double value orientations. On the one hand it should abundantly take consideration of the universalit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needs to centralize the power rapidly to meet the needs of sufficiency. Indeed,promptness and effectiveness seem more important under the context of governance challenges. China’s political institution,which apparently stresses democratic centralism,is more likely to screen out the popular will timely and effectively,centralize resources and powers so that it can cope with governance challenges better.
Key words:governance challenges;comparison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value orientations of governance;superiority
作者简介:李风华,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赵会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责任编校: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