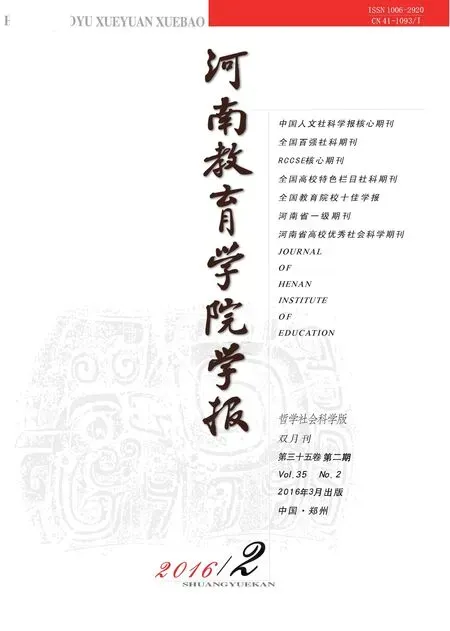非遗传承中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与身份呈现——以郓城县鲁西南鼓吹乐为例
2016-03-16张宗建
张宗建
非遗传承中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与身份呈现
——以郓城县鲁西南鼓吹乐为例
张宗建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其变迁发展有着以“人”为主体的传承特点。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体系之外,民间依然生存着非代表性传承人的非遗传承边缘群体。这类群体虽然生存于政府传承人体系之外,却在一定程度上因其淳朴的乡土气息,与民间受众群体联系最为密切。对郓城县鲁西南鼓吹乐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案调查,为我们呈现出边缘群体在传统民间文化行为中的生存现状及受众群体对其身份的基本认同。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边缘群体;生存状况;身份呈现;鲁西南鼓吹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不同于其他类文化遗产,其保护主体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是实际存在于物质空间中的实物遗存,而是某一特定区域内,部分群体或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及各种实践活动。这一传承特质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并非静态的“物”,而是活态的“人”,其传承方式基本上以口传心授为主。21世纪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政府及地方群体的重视,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诸多相关法规及制度,基本形成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并突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地位,形成了四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2008年5月14日,文化部出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方法》,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申请方式及传承人义务等。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相关非遗项目的核心内容,是非遗项目发展传承的代表性精英群体,在一些亟待抢救保护的非遗项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对代表性传承人基本上是作为某一项目的精英人才进行保护的,这种保护方式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濒危类非遗的发展传承提供一个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但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的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群体的社会角色亦会被突出,从而具有了身份定位,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来“匠人”“手艺人”的身份定位。但是,作为集体性创作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就并非是一个人所能传承发展的,因此作为掌握非遗相关技艺、知识、实践的非代表性传承人群体,即便其不具备政府认定传承人的代表性,依然是非遗传承主体的重要部分,需要我们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加以重视。
一、边缘群体在非遗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
进入非遗保护时代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突出了保护的中心环节,即“人”的作用凸显,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确立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明确了工作重心,也为民间代表性艺人的传承活动提供了经济与地位保障。当前的中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汲取了近几十年日、韩“民间国宝”制度的经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很好地切合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笔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除部分濒危非遗项目,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承发展群体仍具有较大基数,而在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政府认定的各级传承人往往只有一位或两位代表性人物,比例较小。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在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过于重视一两位传承人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从事该项目的民间群众的作用。其二,其他从事该项目的民间群众多数并不了解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国家的政策导向并不能调动非遗基层传播的积极性。在这里,我们把从事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民间群众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边缘群体。
(一)边缘群体区别于传承人群体的特征
较之于政府部门认定的传承人群体,边缘群体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与目前边缘群体的生存现状密切相关。
1.边缘化特质
边缘化特质是边缘群体这一概念的一个显著特点,可分为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边缘群体作为并未受政府保护的民间群体,在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中有着政策边缘化的特点。其次,在地位上,相较于国家认定的传承人群体,边缘群体依然是普通大众,非遗的展示传播行为,多数是在农忙及工作之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具有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再次,在技艺传承上具有边缘化特征,政府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具有某一项目技艺上的代表性与权威性,而边缘群体在技艺上可能不如代表性传承人群体凝练与深化。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空间中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单单是纯粹技艺的实践,而应当在其所处文化环境中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出现,是文化空间内资源整合的产物。边缘群体正在文化空间中实践着这种文化行为,显然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部分。
2.与受众联系紧密
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确立,为部分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群体提供了生活、传承保障,同时部分优秀传承人的社会地位随之上升。这也使得部分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群体与民间受众群体逐渐疏远,如部分民间手工艺、民间音乐及民间舞蹈等表现形式,在传统农耕社会多数是附属于所处文化空间,作为文化仪式的一部分出现,而目前,这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多被作为精英人才置于舞台进行表演,失去了原生的文化环境,失去了原生的受众群体。边缘群体由于其地位的边缘化,依然与民间受众联系紧密,在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的作用便因此凸显出来。
3.原生态特质
边缘群体由于所处文化空间的原生态,自身亦形成了原生态的特质。边缘群体的传承有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及后期自学等,由于各方面原因,这类群体并未成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精英人才,由于没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其传承特点、技艺表现特点及生存特点都具有原生态的特质。
4.经费缺乏保障
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确立,为传承人提供了传承经费,使其在传承保护及日常生活中有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作为民间普通群众的边缘群体,依靠该项技艺所获得的经济收入是有限的。多数边缘群体成员由于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经济上无保障,仅仅将非遗传承作为其谋生的辅助选择。
(二)边缘群体的社会地位与作用
1.当代文化环境下边缘群体的社会地位
当代文化生态环境与传统的农耕文化相比较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较强的农耕社会色彩,受传统社会群体性文化活动的影响,掌握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传人,在地区文化环境中往往有着特殊的地位。
从社会地位的认同上来讲,边缘群体的社会地位主要由两部分群体的认知决定,首先是受众群体的认知,其次是边缘群体对自己的认知。
从受众群体来讲,非代表性传承人所在区域的受众群体,对于边缘群体有着与生产生活相切合的需求。如面塑技艺。农耕社会时期,民间群众捏制面花乞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以及祭祀神鬼祖先,这一诉求传承至今,现在民间群众举行祭祀仪式时,依然会请当地面塑边缘群体艺人制作“花供”“面花”以示仪式的庄重。这也证明了民间受众群体对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边缘群体有着深刻的历史、情感认知与认可。然而,受我国民间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在旧中国、旧时代,传承民间文学艺术,传承民间知识、手工技艺和民俗的民间艺人,均处于社会的底层,是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不仅不被上层文化所重视,其传承活动还常常受到误解并因此受到批判和处罚,其社会地位极为低下”[1]。民间受众群体虽然与这类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却因观念问题并不给予其相对体面的身份,而是以“戏子”“工匠”“要饭行当”等称呼。21世纪以来,虽然传统农耕社会体系已逐渐解体,但旧观念依然影响着民间受众群体对于边缘群体的身份认知。认可其技艺实践,但在身份上只有模糊的定位,是目前边缘群体身份呈现与定位的一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部分边缘群体的技艺传承与发展。
从边缘群体自身的认知方面讲,由于传统观念中受众群体对于民间手工艺人的认知行为相对比较模糊,对其身份定位较低,导致这类边缘群体虽有技艺,却不得不接受较低的社会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以来,政府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较高的身份地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及技艺传承的代表性等问题,边缘群体很难得到政策上的照顾与政府的身份认同,部分边缘群体陷入了身份定位更为模糊的状态。
边缘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开来的,不管从受众群体讲,还是从边缘群体本身来看,虽对其身份价值有一定的认同,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从农耕时期到当代社会,并未有显著的提升。相对于这一群体在文化活动中重要的仪式作用、实用意义等,其社会地位的高下是影响非遗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边缘群体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这里的“人”不能单指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者的民间受众群体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受众群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行为、认知态度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原生文化空间中的存活状态。在目前的非遗保护体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会地位上升,部分代表性传承人已不再具备以往原生态的生存环境,而是主要参与政府展演、会场展示等商业化实践。边缘群体成为与消费群体联系最为密切,也最能满足受众群体文化需求的传承者。
非遗技艺在边缘群体中的传承,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空间内的自然衍变。这类群体没有形成强烈的传承使命感与责任感,其技艺实践是一个顺其自然发展的过程。代表性传承人群体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与自身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使命感,其中传承发展有一定的人为色彩。边缘群体的存在可以为我们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发展的脉络,以及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原生态创新的过程,引导我们更科学地研究传承保护。
二、鲁西南鼓吹乐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
笔者在边缘群体研究过程中,采用鲁西南鼓吹乐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个案。“鲁西南鼓吹乐是流行于山东鲁西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鼓吹乐种。该乐种从古至今十分繁盛,是中国境内唯一保持着以方笙作为定律乐器的北方鼓吹乐种,在民间信仰仪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2]目前,鲁西南鼓吹乐在民间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济宁市嘉祥县、梁山县,菏泽市郓城县、巨野县、鄄城县等地最为兴盛。鲁西南鼓吹乐沿袭了历史上的文化作用,即在祭祀、丧葬、嫁娶、节日等场合使用,具有极强的仪式功能。在鲁西南地区,鲁西南鼓吹乐一般被当地民众称为“响器”,由四至六人组成的乐队则被称为“响器班”。一个乐队主要由吹管乐器与打击乐器两类组成,吹管乐器主要唢呐(当地多称之为大笛)、笙、竹笛等,打击乐器则有梆子、铜板、锣等。2006年,鲁西南鼓吹乐被文化部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主要以菏泽市郓城县响器班的发展现状为对象。此地区处于非代表性传承人所在区域,边缘群体的自然衍变状况良好。调查发现,目前在此区域平均每个乡镇有10—20人专职及兼职从事响器班工作,区域内的红白喜事一般情况下均由这些人负责礼乐。“鼓吹乐为什么会在这片田野大地上繁衍昌盛这么多年?正是礼俗承载,才得以世代传承。尽管传承是个动态的过程,但礼俗的积淀与其静态的特点,使传统在变与不变中延续。”[3]随着祭祀仪式、节日庆祝的相对减少,鲁西南鼓吹乐在此地区主要承担结婚喜庆及丧葬哀悼的礼俗功能,另外还承担商铺开业时烘托气氛等世俗功能。郓城县鲁西南鼓吹乐有两大传承群体,一是家族式传承群体,二是靠兴趣学习鼓吹乐群体。在当代文化环境视野下,由于传承人生活方式、身体状况、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不同,郓城县鲁西南鼓吹乐传承边缘群体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况。
(一)家族传承群体的生存状况
1.部分家族传承群体退出鼓吹乐及原因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非遗项目之所以出现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界文化环境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人因效益问题不愿传承等因素。其主要原因集中于经济收入。从事某项非遗传承如果不能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将很难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支出。作为边缘群体的响器班首先要解决生活问题,其次才能谈及技艺的创新演进。调查发现,一般情况下,婚丧嫁娶主事方会请来四至六人不等的响器班(一般情况下为四人)。响器班负责一天的礼乐,一般为早晨8点左右至中午(丧葬仪式则稍微延长至下午),收入一般为一人100元左右,且主事家准备午餐,并发放香烟若干盒。对于婚嫁这类仪式,一般集中于春节前几天及“五一”“十一”等节庆日间,这段时间也是边缘群体最为忙碌的时期;丧葬仪式则具有日期的不确定性。但仅靠婚丧嫁娶礼俗仪式的收入,完全不能够贴补日常家用。这也使得部分家族传承式的边缘群体放弃了鼓吹乐这一家传“手艺”,从而导致了传统鼓吹乐技艺逐渐失传。
20世纪,郓城县汉石桥村李家班响器是郓城南部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个鼓吹乐班子。笔者在调查走访时发现,李家班传人,50岁的李富银近两年不再从事响器班的工作,而是在本村从事理发行业。提到“李家班”现在不再进行婚丧嫁娶的礼仪吹奏时,李富银说:“为啥俺这班子人都不干了?都打工去了。俺家老三,以前他领着班子,这又打工去了,为啥?两个男孩,一个孩子一订婚就是四五十万。老百姓能弄多少钱?所以都不干了,都出去打工去了,下面小孩也跟着打工。一直玩这个(指鼓吹乐),你玩不起啊,到孩子订婚的时候没钱不行啊。为什么这样?就是这个弄不到钱,怪热闹,吃点喝点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主要指日常生活)。”*田野调查时间:2015年8月13日;地点:山东省郓城县汉石桥村;调查者:张宗建;调查对象:李富银。从李富银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技艺传承过程中,边缘群体并非主观上愿意抛弃技艺,而往往由于经济因素放弃技艺传承。在之后的调查中,我们得知李富银已经与县剧团合作,继续兼职从事唢呐吹奏,只不过他的舞台从或庄重或热闹的婚丧嫁娶场合转变为更多艺术表现的镁光灯舞台。李家班成员也并没有完全退出鼓吹乐行当,李富银的弟弟与侄子目前仍在兼职从事此工作,这也体现出了家族传承具有惯性前行的特点,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后来,我们问及李富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认识,从其回答中我们发现,作为当地有名的吹奏世家的传人,他对非遗保护、国家政策及代表性传承人申请知之甚少,并很难将这类信息联系到自己身上。
李家班响器作为家族式传承的代表,其兴盛衰败的过程凸显了边缘群体在当代文化经济新潮中尴尬且无奈的生存状态。由于政策导向尚未遍及边缘群体,地位尚待提升、经济收入无保障、家庭支出的压力,均成为造成尴尬状况的因素。“挣不到钱”“玩不起”是笔者调查时最常听到的话。他们逐渐退出礼乐舞台,也正代表了目前多数家族式传承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
2.部分家族式传承因创新得以继续发展
家族式传承群体作为代代传承的“老班子”,所生存的文化空间更为纯粹,能够长期得到民众的认可,其在演奏形式、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能力较强,比靠兴趣学习鼓吹乐群体有着较大的存活优势。
目前表演形式的创新,主要是在鼓吹乐之外增加戏曲演唱、鼻子吹唢呐、魔术小品、杂技表演等娱乐节目。以郓城县吕月屯村“王家班”为例,作为历史上附近区域较大的响器班,现在王氏家族从事此工作的人数已相对减少,领头人王长征便邀请临近村庄响器工作者,组成了一个有十几人的响器班,王家班已不再是纯粹的家族式班子。他们改装了一辆舞台车,配置了多台音响设施,不断改善自己的演出条件,逐渐走向了专业的发展道路。同时,鲁西南地区的丧葬仪式上往往会使用民间艺人扎制的纸人、纸马等来祭祀,王家班便在“响器”的基础上,制作这类产品,满足了整场文化仪式的物品需求。近年来,王长征依靠这种多元化发展方式,占领了部分消费市场。近年来,通过这种表演创新形式的发展,有一定家族传承优势的班子发展迅速。
“我对于小孩子上学是什么想法呢?还是唢呐。老辈干这个,我也不能丢掉它。其实干这个以后也有发展前途,就怕你吹不好。唢呐吹好了,也能吃香。”*田野调查时间:2015年8月13日;地点:山东省郓城县吕月屯村;调查者:张宗建;调查对象:王长征。通过王长征的话,我们看到,他通过转变观念获得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对后代的前途产生了文化传承上的信心。这为鲁西南鼓吹乐的发展和边缘群体的民间传承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二)靠兴趣学习鼓吹乐群体的生存状态
鲁西南鼓吹乐边缘群体除在家族式传承之外,另有一部分群体是出于对音乐的兴趣而拜师于各“响器班子”。这部分群体没有家族式传承的学习环境,受教年龄也大都晚于家族式传承群体,故除少数人群可以在吹打技艺上有所造诣,多数群体从艺术水平上讲可以说是边缘群体中的边缘群体。这类群体人员并没有太过强烈的家族传承使命感,多是将其作为一种兴趣或谋生工具。家族式传承祖祖辈辈均以鼓吹乐为主要收入来源,而靠兴趣学习的群体父辈多以务农或民间商业等为主要收入来源。至今,鲁西南仍有家族班子以响器班为主要营生工具,而靠兴趣学习的群体大多则是以此为兼职,作为农忙之外的额外收入。因此在参与与退出的行为选择上,后者更为自由且没有传承祖辈手艺的压力。但他们作为边缘群体的一部分,在民间文化活动中的作用也应当受到重视。
1.靠兴趣学习鼓吹乐群体退出鼓吹乐的各种原因
这类群体的退出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经济因素。在后期学习的这类边缘群体中,依然存在如上所述因经济收入退出的因素,这一点与家族式相同,不再赘述。第二,年龄及身体因素。一般婚丧仪式提供的餐食较之日常生活要丰盛得多,因此难免有部分成员因油类、肉类及烟酒类摄入过多导致疾病及衰老,只能逐渐放弃这一工作。第三,响器班成员之间的矛盾。一般情况下,四人的响器班由一副大笛(唢呐)、一对笙及一人专司打击乐器组成,三个吹奏者(一副大笛,一对笙)要比打击乐乐手演出更为费力,而薪水则是四人相同。由于那些由后期学习者组成的响器班中并没有历史传承意义上的“班主”(大笛的吹奏者均被默认为一个班子的“班主”),在没有权威“班主”调和的情况下,各个成员便会逐渐产生心理不平衡。另外,主事家赠送香烟的数量往往也会引起响器班成员分发不平等的矛盾。诸多矛盾的累积导致部分响器班解体,甚至成员不再从事此工作。
2.靠兴趣学习鼓吹乐群体往往附属于家族式传承的响器班
此次调查发现,在边缘群体的家族传承与后来学习者群体的人数上,家族传承群体依然占据较大比例。家族式传承的响器班依然是民间受众群体在婚丧嫁娶时的第一选择。例如在郓城县谭庄的一家响器班子,其成员均是后来学习而非家族传承,成员间完全是凭借兴趣爱好组成了一个团体,没有“班号”“班名”,因此,民众只有在联系家族式响器班未果后,才会迫不得已地礼乐活动中选择他们。即便他们在技艺上可以与家族式传承的班子相提并论,但在群众的观念中,依然是礼乐传统深厚的家族式响器班更能给自己的文化活动“撑起场面”。
作为边缘群体中的边缘群体,在经济收入、民众认可等方面,后学者自己组建“响器班子”并不是最佳选择。因此,多数后学者以依附于家族式传承的“响器班子”(如吹笙、打击乐器等配角或为人员替补)为主要模式。这类群体,一般以务农、外出打工为主,参与鼓吹乐的礼乐行为完全属于兼职活动。据调查,这也是多数凭兴趣学习者的主要生存状态。他们不需要关注技艺的传承,其后代继续从事该职业的比例也非常小。在这一系列文化活动中,他们关注的首先是在一场礼乐活动中可以赚取多少钱,其次则为排练过程、演奏过程是否能够满足自己对于鼓吹乐的兴趣。
这类群体多数是在20世纪鲁西南鼓吹乐门派意识逐渐弱化后出现的,他们可能没有代表性传承人吹奏技艺的精湛,但作为一场完整文化仪式中的成员,这类群体是随文化环境变化而自然衍生出的一类群体。在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他们起到了维系民众与展演者关系的作用。
三、边缘群体在其文化环境内部的身份呈现
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导向来看,目前民众关于非遗保护的关注点多在政府认定的传承人、政府组织的文化展演活动等方向,而忽略非遗正存活于自己身边的事实。“由于文化的多样,国家无法将所有的文化事象纳入到保护体系,那些未被纳入保护体系的文化以及游离于体制外的文化持有者,有可能因为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而忽视了其存在的价值。”[4]这就涉及边缘群体的身份呈现问题。以鲁西南鼓吹乐为例,边缘群体的身份呈现,主要可分为在原生文化环境中的社会身份呈现及国家政策导向下的身份呈现。
(一)原生文化环境中的社会身份呈现
从历史沿革来看,鲁西南鼓吹乐艺人在传统农耕社会由于传统观念问题身份较为低下。受众群体对其评价的关注点并不在技艺的高超或文化仪式的功能作用,而往往将其与自己的身份进行对比,认为艺人不主要从事农耕活动,因此是“下三流”“要饭的”。笔者调查发现,由于各行各业的兴盛发展及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对于这类群体的身份评价,民间群众多不再进行公开议论,并且多数人已认可边缘群体对这种文化行为的选择。但仍有部分年长者及受教育程度较低民众对此群体有偏见,反映到具体的文化活动中,如在进行一项婚嫁仪式的间歇时段,会有部分群众因对响器班的休息不满而起哄,“怎么这么懒,也不使劲吹”,“你们再给我吹个戏呗”。从这种言辞依然可以看出部分民众对于这类群体的轻视。因此,边缘群体在受众认知中呈现为文化活动的辅助参与者、服务者。但从文化行为角度讲,这类群体却是民间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群体,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紧密联系着民众与文化活动本身。
(二)国家政策导向下的身份呈现
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的受保护群体,主要是以国家政府认定为主的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国家政府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承人以往生存的原生文化空间,重构了其传承的文化内质及相关技艺。在身份呈现上,代表性传承人群体在国家认定后,迅速脱离非代表性传承人的边缘群体,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成为国家体制内群体。但国家政策中没有保护民间边缘群体的相关规定,在政府视野下没有对其社会身份的具体认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国家认证体系影响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关系,代表性传承人与边缘群体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四、结语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体系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相对科学的发展路径。但不可否认,在文化变迁迅速的当代社会,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类别较为复杂且受众群体基数庞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在研究上依然有待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文化行为,其自身原生的发展过程是自然演进的,与代表性传承人相比,边缘群体更接近民间受众,在文化生态意义上具有文化活动的原生态特质。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代表性传承人体系下,进一步深入田野调查,对边缘群体进行深入的跟踪研究工作,对于更好地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锡诚.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方式[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8.
[2]杨红.民族音乐学田野中的音乐形态研究:鲁西南鼓吹乐的音乐文化风格探析[J].中国音乐,2007(1):92-102.
[3]李卫.鲁西南丧葬礼俗与鼓吹乐[J].中国音乐学,2006(4):37-41.
[4]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思想战线,2012(6):53-60.
(责任编辑周军伟)
Living Conditions and Status Presentation of Marginal Population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 Case Study of Lu Southwest Wind Music in Yuncheng County
ZHANG Zongjian
(ArtInstitute,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331,China)
Abstract:As a part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s the main heritage fea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s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there are still non-representative inheritors, which are marginal population. Such groups live outside the protection system, but to some extent, they contact with civil audience most closely because of the simplicity and local flavor. To study the Lu southwest wind music,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uncheng County, may show the marginal group’s living conditions and status present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rginal population; living conditions; status presentation; Lu southwest wind music
作者简介:张宗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硕士研究生(重庆 400331)。
doi:10.13892/j.cnki.cn41-1093/i.2016.02.004
文章编号:1006-2920(2016)02-0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