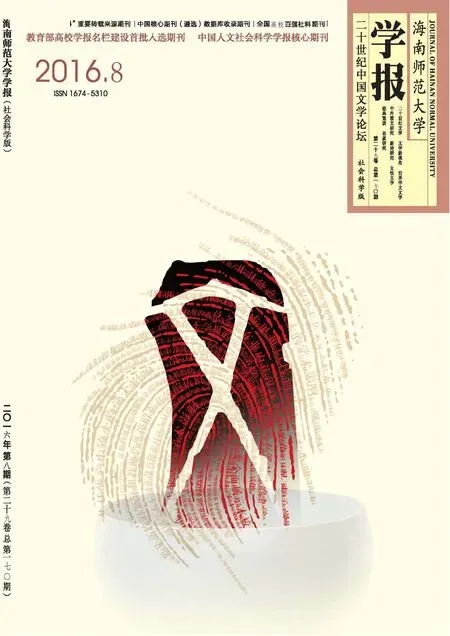跨向新时代的丁玲之困
2016-03-16李丹
李 丹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跨向新时代的丁玲之困
李丹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40到50年代转折之际,丁玲及其作品得到了权力话语体系的高度认可。然而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 却可窥见“个人主义”对她情感、认知的影响并非彻底销匿,其中对自我情感和形象的关注,与主流话语所要求的“集体”情感观念间存有裂隙,于是形成在同一问题上“公”“私”呈现双重态度的情况。公开表达中的言说困境,显示出丁玲自觉的身份认同以及以丁玲为个例的40年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国情怀。
丁玲;言说困境;转折时期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丁玲在关键部门的任职,对其政治身份的认可和作品的高度评价,都显示出“公开”的丁玲在体制内的重要地位。但葛兰西提示我们,关注作家在“私人”领域的表现,恰可鉴别“霸权统识”是否真正完全建立、无缝覆盖。①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葛兰西分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统识时,认为家庭、教堂、工会、学校等看似具有私人性选择的机构,正是阶级意识形态的所在位置。尽管丁玲曾将革命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声称她走向革命的过程就是取消“时隐时现”的个人主义走向“集体的英雄主义”的过程(《〈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然而通过对丁玲在40至50年代之交的作品、言论与信件、日记综合考察,不难发现,“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影响已经内化在丁玲的情感结构中,甚至在集体话语统识程度颇高的1948年前后,依旧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可察其社会身份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缝隙。但由于职是之故,在公开场合中又显示出对矛盾思想的调和。本文即以“私人写作”为切入点,以“个人主义”的影响因素作为参照,观察身处权力顶峰的“宠儿”丁玲,迈步走向新中国之际,在内化党的文艺政策对“个人主义”提出的严格要求时,所表现出的同构和异质,跳脱“断裂”、“接受/反抗”的解读模式,为还原丁玲生动的面貌做一点努力。
以往的研究不论谈丁玲的“政治化”倾向,或反之谈她对“个性”的坚守,其中关于“个人主义”对丁玲的持续影响均表示否定或是讳莫如深。“个人主义”一词从晚清传入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其内涵一直处在被构建的过程中,并不适于给出一个本质化的解释。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20世纪20年代晚期,大多数的作家已放弃了个人主义,将写作重心逐渐从狭窄的个人经验转移到更宽广的社会现实中去。这当中包括丁玲,但她的情形却有些特殊。
关于丁玲早期创作中的“个人主义”特征,茅盾、冯雪峰等都一早做出了一致判断,成为经典论述而延续至今。同时,“个人主义”也是丁玲在政治风波中的重要“罪状”。通过发现“个人主义”的影响在私下场合的保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丁玲的心境,还原一个“不变”的丁玲。
对“本我”的专注是“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核心精神,包含了人类对自我重要性的强烈关切,以及对现实的个人看法。我所关注的是丁玲在建国前后这段时间的写作中,“个人主义”的影响因素是如何存在的,这个影响主要指向“自我意识”,其中又包含“对自我的关注”和“自我情感的表达”。
一、自我情感的压抑与流露
第一,在小说与家书中,“革命”与“恋爱”的不同选择。丁玲在私人写作时显露出的情感与主流话语多少存在偏离之处,贺桂梅曾论证丁玲身上留存的旧话语与主流话语之间形成的“难以弥合的缝隙”*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第279—281页。贺桂梅对比了丁玲的信件日记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关于黑妮爱情的叙述之间的反差,论证了丁玲身上留存的旧话语与主流话语之间形成的难以弥合的缝隙。小说中,黑妮与程仁之间的爱情要为阶级界线让路,爱情的位置相较于革命而言是低一等的。然而,在私人生活中对爱情的依恋,与同期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之间构成一种分裂。丁玲1947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到她对丈夫陈明的感情,觉得为他的健康、生命的存在而劳苦是她的幸福,又意识到也许这就是毫无意义的话。然而就是这样看似毫无意义的流露却反映出真实的个体的欲望。。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以颇为收敛的方式书写爱情。钱义将参军离家,丁玲对顾二姑娘的心理活动作了如是描写:“也不是为的舍不开男人,只觉得有些委屈。”*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或许“儿女情长”容易被指责为爱情至上的个人主义,这在冯雪峰等人的批评中丁玲早有所领教,也或许丁玲自觉地避开了私密的情感。不愿意让丈夫离开的“委屈”,是来自可怕的公公钱文贵,在正义的革命事业面前,“爱情”怎可成其阻碍。然而类似的情况却发生在了丁玲和陈明之间。1947年陈明去了前线(西战团)后,丁玲在信中说:“当你没有走之前,当然我曾有过一些顾虑,如你的身体,等……但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的,亦是人性的。”*丁玲:《致陈明(1947年3月19日)》,《丁玲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页。革命的逻辑是舍小我成大我,私下的丁玲却直白地表达出自然的“顾虑”。并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丁玲对个人主义的自我情感是保持警觉的,但她又认为这种情感是属于人性的,自然的。1948年初,丁玲又连续写下五封家书希望陈明可以回到她身边一起工作。“可是我很想你,我觉得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人可以更谈得来了。”*丁玲:《致陈明(1948年6月17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62页。身为干部的她,理应与群众和其他干部“谈得来”,并投入火热的工作中,但现实却令她寂寞。在私人的写作中,处处显示出她对于“应该删去的”那部分情感的执着,透露出“个人主义”在丁玲身上的印记。
董桂花、周月英这两个形象,同丁玲一样有着女性干部的身份,她们都面临着革命与家庭关系的矛盾。在斗争钱文贵之前,羊倌因谋生而“一年四季也看不到个影子”,使得他老婆周月英成了一个尖酸的怨妇。董桂花也因为李之祥对她工作的反感和家里欠下的债务而痛苦煎熬。斗争钱文贵时,周月英“死劲”打了钱文贵后,“平时的愤怒减少了很多。她对羊倌发脾气少了,温柔增多了,羊倌惦着分地的事,在家日子也多,她对人也就不那么尖利了。”*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98页。斗争的任务一日未尽,她就无法享受到属于她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至于董桂花,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交代她后来的际遇,或许也如她期待,通过斗争地主,把“窟窿填上”了罢。但是,与小说中的斗争优先不同,私下的丁玲在革命与幸福的冲突中,选择后者。她写道:“离开你,并非生活的幸福,只是生活的奋斗,我需要奋斗,可是更需要幸福!”*丁玲:《致陈明(1948年6月17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62页。丁玲和董桂花不但对于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如出一辙,相较于干部工作更眷顾个人幸福,甚至可以将工作放在次等这一点上,二人的态度也形成呼应。
第二,杂文、随笔、发言稿中言说困境的线索。1948年丁玲在一篇日记中记载下了与陈明重逢的片段。她说:“我们又有了我们的天地,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们都有一种舒适的感觉”,还说“身体健康就是两个人惟一的希望,并且都会这样去做,享受属于两个人的幸福”*丁玲:《日记(1948年6月26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44页。。即使是在革命工作中,她精神的满足更多的还是来源于个人家庭生活的温馨。1949年10月丁玲受命率团访苏,陈明的离开使她“一点事也不能做,如丧魂失魄一样”,她觉得自己“很软弱”,是“外强中干”*丁玲:《致陈明(1949年10月19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94页。。如果“外强”是在政治生活中的坚定,“中干”恐怕就是个人精神世界中爱情的空虚,但是带着“软弱”一面的她,才是个完整的个体。
作为干部的丁玲,在公开场合自觉传达着新政权所要求的意志,要求大家,同时也是要求自己,须通过鞭策自己,理性地了解并努力去喜欢上“新”的事物,进而“跨到新的时代来”。丁玲认为当前的文艺,正是抛弃了个人情感的小圈子,而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本质,高于过去的作品。对于被归于旧时代的“小圈子”的情感,是绝对要摒弃的。她批评莎菲式的女性之绝望:将其归因于“受到历史社会条件和创作条件的限制”*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1950) 》,《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逐渐重塑自己的形象地位。过去别人评价她早期创作中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第8页。,而现在她批评巴金的作品“那种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丁玲:《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丁玲全集》第7卷,第119页。。她认为现在应该看“家庭中”的人物进入部队、农村、工厂后的情况。相较于宽广的社会生活,属于“家庭”的关系、情感就被降低了位置,这与日记中透露出的对家庭情感的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
日记中的丁玲享受于家庭生活的幸福、平和,她说:“我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别的希望,生活只是一种和谐,和谐是一种最难忘的日子呵!”*丁玲:《日记(1948年6月26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44页。和谐如此珍贵,但作为公众人物时,她却强调战斗的作用,认为不论是文学创作者甚至是阅读者都需要接受和融入战斗的气氛中,“必须参加群众的斗争生活,理解他们新鲜的、战斗的、热情的感觉才能启发自己的感情有所变化”,*丁玲:《谈文学的修养》,《丁玲全集》第7卷,第151页。但她自己的情感又何尝能轻易变化呢?
在一次讲话中,她提起一个在农村“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共产党给她分了土地,“如果她要求自己的儿子在家好好种地,养活一家子,过两天好日子,那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位老大娘却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当兵。”*丁玲:《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丁玲全集》第7卷,第126页。老大娘的高觉悟与丁玲日记中对孩子的不舍之间,却可见革命逻辑和丁玲自我情感的差异。“麟儿进了航空学校,心中很难受”*丁玲:《日记(1948年6月17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40页。(后来又在给蒋祖慧的信里问起他到底是去学造飞机还是学驾飞机,如果是驾飞机恐怕更是增添担心了),加之据说组织已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她从未得知,所以心中有“说不出心中的苦闷”。在私下,作为母亲的丁玲,表达出对儿子天然的保护欲,尤其被动接受组织的决定,更是增添了无从抱怨的抱怨。这些细微体验,对于个体而言正是主体性得以确立的真实欲望。然而诸如上述属于“小圈子”的感情只可见于日记、信件,在公开言论中又明确反对,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言说困境。
二 自我关注与集体观念的裂缝
在小说中,下乡干部斗争热情高涨,大公无私。形象高大光辉的干部章品,对艰苦的革命工作甘之如饴,达到“忘我”的境地。他“在冬天的夜晚他就住在那看园的小屋里,或者一个土坎坎里,左手拿一个冰冻的窝窝,右手拿一个冰冻的咸萝卜,睡一会儿又跳一会儿,为的不让脚给冻僵了”*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22页。。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丁玲去河北中部参加土改,当时的一篇日记最后写道:“闻明天须走七十里,心颇动摇,但已骑在虎背,无法反悔……惟通宵臭虫似蚂蚁,浑身被咬得起了许多疙瘩。”*丁玲:《日记(1947年5月16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31页。尽管土改工作应属革命大义,苦难当前的丁玲却有骑虎难下的勉强情绪。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可贵但也痛苦,生活质量降低,精神和身体的自由受限制,首先要战胜的就是自己。游走于“集体”之外的孤独感受,和工作困苦前的自怜,可见作家对自我的关注,也说明为主流话语所不容的个人主义因素的留存带给她的矛盾挣扎。
另一位深入农村的干部文采,感到“这里有一种最淳朴的感情,使他的冷静的理智,融汇在群众的热烈的浪潮之中,使他感觉到充实和力量”*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58-59页。。经过土改的历练,“他的确已经在逐渐修改自己,可以和人相处了”,*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97页。全然一派融入群众的满足和热闹气氛。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过程中,丁玲曾有过两次停笔,在其中一次停顿期间写下的日记中提到:“这里很热闹,夹杂在里面不舒服,不群众化,不随俗,是始终没有改变,我喜欢的人与人的关系现在才觉得很不现实……大家都在学浅薄的低级的趣味。”*丁玲:《日记(1947年5月29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297页。在集体与个人的对立中,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放弃“为自己”的一点东西?来自亭子间的文人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找得到内心世界与民众结合的切入口。1947年春节,丁玲给儿子信中也提到,年过得很寂寞,村子上就两家人,是公家人,没什么来往,只有妹妹不那么寂寞,她和老百姓的娃娃们玩得很好,*丁玲:《致蒋祖林(1947年1月27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27页。足见她与当地百姓的关系生疏,并不能像文采那样在群众中找到充实,而是感到“自我”的与众不同、不合。
丁玲在1950年写的《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一文中,把“容易寂寞、找不到朋友的感情”称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寂寞病”。这些人“总觉得自己心里还有一些话找不到人说,闷得慌”,内心期盼有旧友能来谈谈心,其实是还没能“与群众生活联系起来”*丁玲:《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丁玲全集》第7卷,第199页。。可在此前不久的一篇日记中,她提起陈学昭,说个人“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她写到与立波谈起此人时的一段对话,“他说:为什么是一个人奋斗呀,现在革命的队伍这样大?我说,队伍大,但各人必须走各人的路……”末了还加一句:“他并不希望了解这些问题”,感叹“怎么懂得道理的人这样少!”*丁玲:《日记(1949年3月14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68页。透露出她的诉说不被倾听、不被理解的孤独感。丁玲没有对陈学昭在革命热潮如火如荼时选择出国的行为加以批判,而是认同她走“各人的路”的独行,同时感到无法与周围人沟通的痛苦和孤单。这种孤独感和集体观念的松动与她公开的言辞又一次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身为党的干部,丁玲穿梭于大小会议之间,忙于《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一些文艺创作者对“赶任务”对写作的影响感到头疼,丁玲教育他们:“今天蓬蓬勃勃的在搞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经济建设等伟大运动”,不应该自己做文章的规划,“而是把自己投入到火热的战斗中”。并在文中批评了希望脱离工作岗位到文学研究所去学习的同志,劝其“应该乐于接受在工作中很好的经验”*丁玲:《谈谈文艺创作问题》,《丁玲全集》第7卷,第252-253页。。又批评了读者不喜欢书中“老是开会,自我批评,谈话,反省……”*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1950)》,《丁玲全集》第7卷,第201-202页。的情绪。殊不知,她的内心多么渴望安安静静地创作。1949年5月访苏归来,回想起一年“四处奔波,成绩很少”,丁玲不禁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不学无术之作家”*丁玲:《日记(1949年5月24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79页。。她致信陈明,说工作很忙,希望自己要“抓紧时间写点文章”*丁玲:《致陈明(1950年10月4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99页。。在通信中可以看到她对干部工作压抑创作的焦虑和无奈。她多次流露出对“没完没了”的会议的厌恶。“老是开会做什么呢?已经有那么多人了,我就不必去……让人家骂我去吧。我愿意躲在这里”,*丁玲:《日记(1949年3月14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68页。又说:“好吧,再开两个月会吧,以后不要再开了!让我能有两三年的写作时间!”*丁玲:《日记(1949年5月24日)》,《丁玲全集》第11卷,第379页。
干部工作与个人创作的矛盾并没有解决,随着“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丁玲身上隐含的双重状态在政治漩涡和人事争斗中越来越显性,最终被认定为在话语纯粹度方面的失败者而遭到淘汰。被派往北大荒之前,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找丁玲谈话,“谈话之中,丁玲突然间喃喃说出:‘姚蓬子、冯雪峰管我叫冰之,左联同志都叫我丁玲。’这种忆旧让刘白羽诧异不已,最后说了‘要读党报社论,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战士’几句就草草结束了谈话。”*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前后中国文坛纪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24页。两种称呼背后是时代呼啸而过,当时过境迁,那个呼喊着跨到新的时代来的丁玲却不能对旧的记忆挥洒自如。1950年的丁玲曾说,“描写知识分子转变是少的……但这也的确因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动荡的时代中的一些摇摆,一些斗争,比起工农兵的战斗来,的确是显得淡薄无力得多……假如有一个真真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作家们又把他当一个干部,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来出现了。”*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1950) 》,《丁玲全集》第7卷,第207页。这仿佛恰巧印证了丁玲自己身份的仓促建构过程,她原本就是她口中所说的那种“漂亮多情又无路可走的倜傥情调的知识分子”*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1950) 》,《丁玲全集》第7卷,第207页。,但极少目光关注她作为那个“旧”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而是直接把她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战士来看待和要求,便忽略了很多关于一个真实的人的细节。
言说困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丁玲的表现是虚伪的。公开场合的丁玲毋宁说是她的社会身份,是她对自己思想矛盾的调和,丁玲对革命话语自发自觉的认同是不容忽视的。兴亡之际的社会责任感已经融入40年代知识分子的血液,乱世的孤独体验又催生出强烈的归属需求。当一切曾经指导过他们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希望”的火光终于在旷野上燃烧时,黑夜与光明中,出于本能选择后者。于是“到陕北(或北方)去”成了这一时期流亡者文学里光明与希望的前景目标。历经千辛才寻找到了希望的作家们,将这个精神“归宿”,“虚化和夸大成没有矛盾、缺陷的绝对存在”,将集体的事业高度神圣化,并且去追求这种“神性”,在当时形成一种“时尚”*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3-35页。。在融入集体而将“我”消融,进而在得到成为“新人”的认可的孜孜追求中,对个人情感、欲望的眷顾,必然是受到否定的,是被认为“过时”的。
认识到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认同心理,就不难理解公开场合的丁玲自觉清除旧话语的痕迹、协调内心矛盾的用心。纵使有时她认为一些情绪、思想是“属于个人的,亦是人性的”,但却绕不过内心为革命事业树立起的光辉丰碑,所以即使私人信件中,提及个人情感后还不忘加上“也许这就是毫无意义的话”*丁玲:《致逯斐》,《丁玲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或许正是上述心理发挥作用。丁玲真心认同她所认定的事业,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80年代复出以后,当没有什么阻力让她沉默的时候,为何她也没有像巴金一样再创作出反思性的作品或者向过去她批评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和忏悔。
同丁玲一样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鲁迅作为同路人在公开场合对于革命的支持和私下言谈中的疑虑也随着史料的公开而被揭示出来。*葛飞:《1936:鲁迅的左翼身份与言说困境》,《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但还存在一些也许同样典型性的作家和他们所能被揭示的问题,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的转变问题,是否能够以简单的个性丧失来一笔涵盖和解释?公开与私下场合会出现双重状态原本是人的自然表现,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意识形态高压的情境之下,言说困境的浮现使作家与时代浪潮的龃龉清晰可感。多重历史和现实的视野也将帮助我们从非此即彼的表态模式中解脱出来,从而勾画出更为生动的历史图景,拓展出新的研究可能。
(责任编辑:毕光明)
Ding Ling’s Plight in Her Transition to a New Era
LI Dan
(SchoolofLiteratureandCommunication,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t the turn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50s, Ding Ling and her works were highly regarded by the power discourse system. However, from Ding Ling’s diaries and letters can be discerned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ism” on her emotion and cognition, of which the concern with self-emotion and image is somewhat incongruous with the “collective” emotion concept required by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thereby forming both the “collective” and “private” attitudes on the same issue. The publicly expressed discourse plight is reflective of Ding Ling’s conscious idenity recognition and the strong family-country sentiment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with Ding Ling being a case in point.
Ding Ling; discourse plight; the transition period
2016-03-01
李丹(1989- ),女,土族,青海乐都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6
A
1674-5310(2016)-08-0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