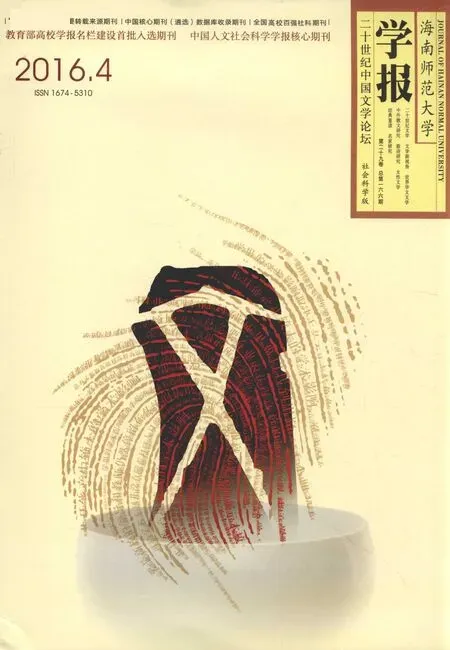驱逐、辩护还是监督
——柏拉图《理想国》诗学思想管窥
2016-03-16汪韶军
汪韶军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驱逐、辩护还是监督
——柏拉图《理想国》诗学思想管窥
汪韶军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围绕柏拉图对诗的态度,学界存在两种对立观点:驱逐说与辩护说。但实际上,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贯的,并不存在矛盾之处。驱逐说固然未能揭示柏拉图诗学思想的真面目,“辩护”却也不至于,称“监督”则比较合适。柏拉图要做的是本着真善美三位一体,对诗歌进行“纯净化”。这是其以哲学指导政治之思路的延伸。
关键词:柏拉图诗学;驱逐说;辩护说;监督说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严厉指责了诗歌,也对诗人下过逐客令,这使他成为诗学史上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长期以来,人们一再征引卷三中的那段驱逐令,将柏拉图诗学的这一面放大再放大,以至偏离了事实。近来有学者对柏拉图诗学做了进一步研究,如国外埃利阿斯(Julius A. Elias)著有《柏拉图对诗的辩护》(Plato’sDefenseofPoetry)一书,国内王柯平先生亦作有《柏拉图如何为诗辩护?》一文。面对同一文本,人们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诠释:驱逐与辩护。到底哪种看法更接近柏拉图诗学思想的真面目?抑或是两种看法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以为,柏拉图固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诗人都驱逐出去,却也不存在为诗辩护的问题,谈不上什么直接辩护与间接辩护、强势辩护与弱势辩护。应该说,他对诗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之处。柏拉图只是想通过对诗的“纯净化”,使诗服务于理想国的建构,这可以说是他用哲学来指导政治的延伸。
一、作为诗人哲学家的柏拉图
柏拉图是古今少有的诗人哲学家。哲学史家梯利(Frank Thilly)惊叹道:“柏拉图是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也是哲学家和论辩学家。他以罕见的程度把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象和深邃的神秘感情结合起来。”*[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1页。这一评价非常恰切。柏拉图熟谙古希腊神话、史诗和悲剧,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经常从中旁征博引。埃利阿斯曾做过统计,柏拉图对话集中共引用荷马史诗142处、赫西俄德史诗32处、品达颂诗13处,此外还有对埃斯库罗斯等其他诗人的多处引用。*参见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荷马史诗也经常信手拈来,证明他对诗的惊人的熟悉程度。
柏拉图早年喜爱诗歌和剧作,自己也写过悲剧和诗歌。水建馥先生所译《古希腊抒情诗选》中收录了3首柏拉图的诗作。20岁时,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投身哲学,将此前自己创作的剧本付之一炬。柏拉图是出于一种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试图通过哲学来改造政治,为全体公民谋求最大幸福,引领人们走出洞穴得见光明。这种对政治和道德的关注,使得对文学的创作和本体研究不再成为他的核心关切。他宁愿做诗人所赞颂的英雄,也不愿做赞颂英雄的诗人,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说他从此以后不爱诗。事实上,诗已经浸入到他的骨子里,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以另一种形态延续着。
作为一名诗人哲学家,柏拉图并不拒斥诗歌,他从未想过要压抑自己的诗才。尽管在当时有一场诗与哲学之争,柏拉图站在哲学一边对诗和诗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实际上,诗与哲学在他那里并非死敌,相反,他在深层次上将两者融汇了起来。其对话体不仅是一流的哲学著作,也是一流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哲学与诗的奇妙化合体,达到了人所不及的境地。后世曾有人(如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模仿此体裁,但远不如柏拉图的精彩。赵敦华先生评价道:“柏拉图的对话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对话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对话充满情趣,严密的论证配以优美的语言,行云流水的雄辩夹杂着隽永的格言,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高度统一。”*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2页。读过柏拉图对话录的人,都会被那诗化的表述方式所感染。他喜欢引用和编造故事,善于用具体事例和象征、借喻的方式来说明抽象的、难以表述清楚的哲学理论。《理想国》中的日喻、线喻、洞喻、床喻,《会饮篇》、《斐德罗篇》中爱的故事,《斐德罗篇》中的灵魂马车,这样的例子在其著作中俯拾即是,所有这些都是那么引人入胜。《理想国》卷五中的“三个浪头”,真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掀起了一次次的论辩高潮。当然,柏拉图并未采用诗的体裁、诗的格律,他是使诗为我所用,服务于哲学的表述,服务于理想国的建构。
二、柏拉图对诗的监督
柏拉图对诗的魔力有着深切感受,《伊安篇》533D-533E中的磁石说就是对此做出的生动描述*参见[古希腊]柏拉图:《伊安篇》,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他认为,在诗歌的长期熏染下,人们会逐渐形成一种习惯,而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它会影响到人的一言一行,影响到人的言谈思想方法。既然如此,一首“好”诗就有益于塑造美好的心灵,而一首“坏”诗也就会爆发出可怕的破坏力量。柏拉图明白诗对心灵与性格塑造的重要性,所以他非常强调诗乐教育,把它列为“七科”之一,并时刻警惕着“坏”诗的负面效应。
(一)卷三的“逐客令”
《理想国》卷三写道:“假定有人靠他一点聪明,能够模仿一切,扮什么,像什么,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以为我们会向他拜倒致敬,称他是神圣的,了不起的,大受欢迎的人物了。与他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城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他到别的城邦去。至于我们,为了对自己有益,要作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3卷,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2页。这就是人们一再征引的“逐客令”,我们可以从中抽绎出两点。
其一,柏拉图驱逐的只是某一类外来诗人,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把城邦里的所有诗人都扫除出去。柏拉图认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然禀赋,都应该按其天赋集中毕生精力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精益求精:“鞋匠总是鞋匠,并不在做鞋匠以外,还做舵工;农夫总是农夫,并不在做农夫以外,还做法官;兵士总是兵士,并不在做兵士以外,还做商人,如此类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3卷,第102页。如果一个人什么都干,结果将是没有一样能干好。具体到诗歌领域,柏拉图认为,一位诗人或诵诗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搞好两种模仿,哪怕是很相近的两种模仿,譬如悲剧与喜剧。而这里被驱逐诗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模仿一切,为了能够扮什么像什么,他们就得耍些小聪明以哗众取宠,而这是柏拉图无法接受的。
其二,尽管柏拉图一再贬低模仿,但诗人的模仿在他那里并非可有可无。柏拉图在禁绝前述诗人的同时,仍然强调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以模仿“好人”,导人向善。“逐客令”后面还有一大段类似的话:“我们要不要监督他们,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我们要不要同样地监督其他的艺人,阻止他们不论在绘画或雕刻作品里,还是建筑或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哪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否则我们的护卫者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嘴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便铸成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3卷,第107页。可以看出,柏拉图是要斩除腐蚀性的“毒草”,禁绝一切“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东西,而留用追随真善美的“鲜花”。正如梯利所言,柏拉图“敌视一切卑下和庸俗的东西”*[美]梯利:《西方哲学史》,第61页。。“写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但是可耻地或邪恶地讲话和写作,而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去讲话和写作,我想这才是可耻的。”*[古希腊]柏拉图:《斐德罗篇》,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3-174页。笔者认为,《斐德罗篇》中的这段话道出了柏拉图对诗的真实态度,即:他并不反对诗歌本身,而只是要求诗人尽其为人师的职责,“为灵魂而歌唱”(《法律篇》),为理想国服务;他并不反对模仿本身,而只是反对模仿和宣扬非理性的东西。
(二)柏拉图对诗歌的全面审查
由于“诗歌有三个组成部分——词,和声,节奏”*[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3卷,第103页。,柏拉图便从内容到形式,从讲什么到怎么讲,对诗歌进行了全面审查:对过去的诗作进行了删削,对未来的诗作提出了一系列的规范。
怎么讲?那种挽歌式、哭哭啼啼的调子和甜腻的、软绵绵的靡靡之音,如伊奥尼亚调、吕底亚调,必须彻底废弃,因为它们会使人变得萎靡不振、软弱消沉。而一刚一柔、模仿勇敢与节制的声音,如多利亚调和弗里基亚调,被留用了下来。
讲什么?“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页。评判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呢?著名美学家塔塔科维兹(Wladyslaw Tatarkiewicz)曾指出:“柏拉图是著名的三位一体‘真、善、美’的创造者,它集中概括了最高的人类价值。”*[波兰]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柏拉图正是本着真善美三位一体,要求美同时必须是真、善。以此为标准,他对诗歌做出了取舍,凡是不真、不善的东西,都坚决舍弃。
其一,诗必须真。
柏拉图在本体论高度上,断定“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10卷,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1页。。在《理想国》卷十中,他通过“床喻”贬低了诗的模仿,认为诗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与真实隔着两层。诗人制造的只是可感事物的影像,不能给人以真理和知识,诗人所用的想象处于认识的最低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肯定下来: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它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10卷,第396页。可以说,柏拉图在这里彻底否定了诗与真的联系。在他看来,诗人貌似无所不知,实则一无所知。他指责诗人只是“影像的模仿者”,而未做出一些实际的事务,如救死扶伤、发明创造、指挥作战、治理城邦、教育公民等等。他质问荷马:“有哪一个城邦是因为你而被治理好了的,像斯巴达因为有莱库古,别的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邦因为有别的立法者那样?有哪一个城邦把自己的大治说成是因为你是他们的优秀立法者,是你给他们造福的?”*[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10卷,第394-395页。这是柏拉图反复申说的一个道理,在《伊安篇》中,他曾以驾车、治病、占卜等为例,说明一个圈子的事情只有圈内人士最在行,诗人或诵诗人不可能知道一切。在《斐德罗篇》中,他又根据灵魂观照到“真实存在”的多少,将城邦公民分为九类:第一类是“智慧或美的追求者”或“缪斯的追随者和热爱者”,而“诗人或其他模仿性的艺术家”则屈居第六类。*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斐德罗篇 》,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163页。然而,第六类是否囊括了所有诗人?“缪斯的追随者和热爱者”中是否有诗人?这些都是问题。第六类中的诗人无疑是模仿性的、技艺性的诗人,但据柏拉图的迷狂说来看,这些诗人并非诗人的全部。柏拉图似乎对模仿性的诗和诗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对迷狂的诗和诗人却是非常推崇。陈中梅先生认为:“并非每一位诗人都是两度(或三度)离异于真理的卑劣的摹仿者”*陈中梅:《诗与哲学的结合》,《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第119页。,笔者以为,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
尽管如此,柏拉图在论述时很少做这种区分,从而给人一种全称判断的错觉。他认为,诗不仅不能给人以真理,而且撒谎。柏拉图一再强调,神只是好事物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好事物的原因只能是神。至于坏事物的原因,我们必须到别处去找,不能在神那儿找。”*[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2卷,第75页。这与他矢口否认卑贱物、污秽物有相应的理念是一个道理。柏拉图认为神如同理念,是尽善尽美的,永远自身同一的。可当时的诗歌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在他看来,许多诗句亵渎了神明,没有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实本性,反而把他们描写得丑恶不堪,比如说他们明争暗斗,贪财恋色,受情感的支使,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大哭大笑,全然没有神的尊严。而这是非常糟糕的,它们既不真也不善,非但不能使人敬畏神明,以之为楷模,反而给人们以托辞,以为既然神与英雄都这样,凡人作恶又有什么要紧?柏拉图在此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对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神谱》等诗作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中所包含的古希腊神话的批判,而不是针对诗本身,其目的是要将一切拟人的成分从神性中驱除出去,以便为现实人生树立一个个典范。我们知道,古希腊神话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即神具有与人相似的形体和七情六欲,也会干出偷盗、奸淫、尔虞我诈之类的丑行。如果说柏拉图之前的爱利亚派哲学家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着重批判了神人同形观,那么,柏拉图就着重批判了神人同性观。
其二,诗必须善。
如果说诗对知识的获得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那么,它对德性的培养却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柏拉图对其作用的讨论涉及到他的灵魂学说和正义说。
柏拉图把灵魂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按照他的“马车之喻”,理性就是那个居于领导地位的驾车人,而激情和欲望则分别是拖着马车跑的良马和野马,处于被领导地位。如果理性能发挥其作用,欲望简单而有分寸,领导着的领导着,被领导的被领导着,就能产生灵魂的四种德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相反,如果本应俯首贴耳的部分起来造反,企图在灵魂内部取得生来就不属于它的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僭越就将导致乱套、不正义。
柏拉图对灵魂的三分无非是想把人性分为神性的和动物性的两个部分。他鄙视一切与感官、感性、肉体、欲望相关的东西,在他看来,无论什么,只要一沾上感性,就变得不完美、不纯粹而更为低级了。肉体对于灵魂来说,是一种障碍;灵魂附着肉体,就像河蚌困在蚌壳里一般。柏拉图崇尚一种理智主义的幸福观,认为用理性指导一切行动方为至善之道。他要求人们永远走向上的路,用灵魂的高贵部分统率低贱的部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要成为情感、欲望的奴隶。也就是说,城邦的所有公民(包括统治者)都要挣脱肉体的蒙蔽,禁绝肉体的快乐,转而去追求心灵的快乐,去观照理念世界的至善纯美。在笔者看来,《理想国》卷三末尾金银铜铁的故事主要也不是为了论证人间的等级秩序,而是通过譬喻,强调用理性来统率国家。他所说的“上等人”、“下等人”,并不是从权势地位上来区分的,而是就一个人身上理性成分的多少而言。柏拉图强调服从统治者,实际上是服从理性的另一种说法,即用理智和正确信念来指导情感和欲望。
柏拉图将其灵魂学说和正义说贯彻到了诗学领域,认为悲剧满足了人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喜剧的插科打诨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变得像个小丑。总之,诗歌把灵魂的低劣成分激发、培育起来,从而导致理性部分的毁灭:“在我们应当让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在我们应当统治它们,以便我们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可悲时,诗歌却让它们确立起了对我们的统治。”*[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10卷,第406页。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应该时刻用理性克制自己,保持心灵的平静。那些刺激性的、挠人心志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是不相宜的,都是必须摈弃的。
柏拉图对诗的内容和形式不仅定出了几条原则性的东西,还做了许多细节规定,如要求诗人称赞地狱生活,不要把阴间描绘得那么阴森凄惨,以免使人产生恐惧怕死之情,以为好死不如赖活。柏拉图认为,这一点对城邦保卫者的教育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三)“理想国”中留用的诗作
可以这么说,柏拉图的删诗和逐客令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他对诗歌功能的特别关注,因而笼统地说柏拉图驱逐诗人是有失偏颇的。与其使用“驱逐”一词使人产生误解,不如改用“监督”更为确切。以荷马史诗为例,尽管柏拉图对它进行了大力删削,但他同时也承认,荷马史诗中有许多东西值得赞美。《理想国》卷十称“我从小就对荷马怀有一定的敬爱之心”*[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10卷,第387页。,在《伊安篇》中尊荷马为“最伟大,最神圣的诗人”*[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页。。事实上,柏拉图认为,德才兼备的诗人不仅不应离开城邦,而且应该积极参与到城邦的道德教育中去,成为民众的良师益友。诗歌作为一种“技艺”,与其它技艺一样,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着它自己的位置,只不过它要服从哲学的指导,否则又将导致“不正义”。
经过柏拉图的删削,理想国中只剩歌颂神明和赞美好人的颂歌。正如柏拉图心目中的“统治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治者,他所留用的那些颂诗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诗作。归根结底,这类诗作歌颂的是理性和由它带来的四种德性。那么,这些留用的诗歌是否纯是味同嚼蜡的道德说教,还是同时兼具极高的审美价值?“如果他们能说明诗歌不仅能令人愉快而且也有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诗于我们是有利的了。”*[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10卷,第408页。可见,柏拉图对诗的审美价值也没有完全否定,诗歌给予人的审美愉悦在一定范围内还是被许可的。当然,柏拉图的主要标准还是“有益”。
三、结语
总体说来,柏拉图对诗歌的态度是主张对其加以监督;传统的“驱逐说”不符合事实,后来的“辩护说”也未能得其真。柏拉图不是要“翻天”,而是要“补天”。他并不反对诗歌本身,他反对的是诗人忘却自己的职责,宣扬一些不真亦不善的东西。柏拉图的诗学主张在根本上是为其理想国中的道德教育服务的,他要求诗担当起责任和使命,起到一种有益于城邦管理与社会生活的教化作用。
应该说,柏拉图诗学中的认识论原则和道德理想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对诗歌的存在也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这种思想原则无疑会减少空洞无物和藏污纳垢之什。柏拉图的偏颇之处在于,在他那里,诗与哲学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他强调哲学君临于诗之上,用哲学来统摄诗,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导致哲学对诗的吞并。真善美本是相互独立的三大价值,但柏拉图再三再四地强调诗必须真、诗必须善,却很少提及诗必须美,美于是成了真与善的附庸和工具,诗歌本身的审美特性被冷落了。
(责任编辑:王学振)
An Analysis of the Poetics Idea in Plato’sTheRepublic
WANG Sha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There exist two contradictory viewpoints on Plato’s attitude towards poetry—Banishment and Defense. In fact, Plato’s attitude in this aspect has been consistent rather than contradictory. Neither Banishment nor Defense can reveal the truth of Plato’s poetics idea which can be more properly referred to as “supervision”. What Plato really wants to do is to purify poetry based on the tri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which is an extension of his idea of directing politics through philosophy.
Key words:Plato’s poetics; banishment; defense; supervision
基金项目:海南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子项目“海南文化软实力科研创新团队”(编号:01J1N10005003)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汪韶军(1973-),男,浙江淳安人,哲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老庄哲学、魏晋玄学、禅宗、美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4-0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