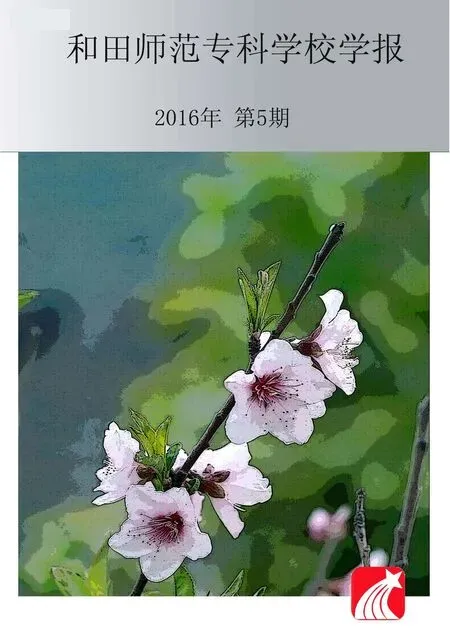班第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武功述略
2016-03-16吴学轩
吴学轩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班第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武功述略
吴学轩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班第两次随乾隆帝征讨准噶尔,授定北将军,擒获达瓦齐,功拜一等诚勇公。大军撤回,唯留班第印信,予五百兵驻守伊犁,阿睦尔撒纳不轨,班第察觉,多次请奏缉拿。最终,寡不敌众,在崆吉斯被围自尽。论文集中对班第在第一次平定准噶尔中的功绩、与阿睦尔撒纳反叛的关系,以及兵败自杀对乾隆帝平准、治准政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做一个深入研究。
班第;征讨准噶尔;武功述略
17世纪初,准噶尔在巴图尔洪台吉的统领下,统一了天山北路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张。噶尔丹自立后,于1680年,攻灭叶尔羌汗国,控制了整个新疆,对清朝的威胁越来越大。1688年,噶尔丹直接进攻了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使清朝北部屏藩尽失。1690年,康熙帝亲征准噶尔,自此,准噶尔和清朝开始了对青海和硕特与漠北喀尔喀控制权的长期争夺。雍正九年,清军在和通泊战役中惨败,准噶尔一度占据优势。直到在光显寺之战中,喀尔喀额驸策凌出奇制胜,大败准噶尔,双方才不得不划界议和,维持了近30年的和平。但对清朝而言,“准噶尔一日不灭,则蒙古一日不安,边境一日不宁,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1]乾隆十年,很有威望和才能的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逝世,准噶尔内部因争夺汗位发生内乱,噶尔丹策零的三个儿子在这场内乱中都被杀死。最终,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夺得了汗位。不久,在这场内乱中失势的准噶尔达什达瓦部宰桑萨喇尔、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等先后降清,阿睦尔撒纳恃功骄横肆意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引起达瓦齐不满,被打败,也投降了清朝。这对早已下定决心要完成“皇祖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憲皇帝筹办未竟之绪”[2]的乾隆来说是机不容失。
一、领兵出征
统帅在战争中至关重要。乾隆帝最初选择了舒赫德、策楞。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与班珠尔纳默库率部众来降时,乾隆帝派尚书舒赫德及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去接应安置,奏请“俟阿睦尔撒纳到军营日,谕以照车凌等初到接济口粮之例,分给骒马牛羊,挑其可用之兵,将阿睦尔撒纳等大台吉,一并留在军营候旨。其老少子女,俱令携带接机口粮,移至所指地方。”[3]乾隆帝下旨:“策楞等办理此事,甚属错谬!……全无勇往办事之心,一味畏葸怯懦,必欲坏国家大事,其居心尚可问耶!”[4]二人被撤职。最终,由“以尚书班第代往。”[5]临战换将,被委以重任,班第必然有他突出的才能。
在第一次平定准噶尔叛乱中,乾隆任命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马木特为北路参赞大臣、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并且,让他们统领先锋部队。三人都是由准噶尔降清,乾隆帝看重的是他们在准噶尔部落中的威望,希望他们能够招抚旧部,减少平定准噶尔的阻力。可以说舒赫德、策楞就是因为没有理解乾隆帝的这层用意,才被撤职。从第一次平定准噶尔的顺利进军来看,乾隆帝的这层用意是得到实现的。但从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日后的反叛来看,也是有很高风险的。因此,这支军队的统帅,不但要要善于处理民族关系,而且要战功卓著。
班第(?-1755),康熙五十七年,出任理藩院堂主事。雍正三年,打箭炉外裹塘巴塘乍了察了察木多及云南之中缅归附,鲁隆宗诸部归达赖喇嘛管辖。班第奉命赴西藏宣谕。回到京城后,升任理藩院侍郎。乾隆四年,由兵部侍郎,兼理藩院侍郎。到乾隆八年,已经是兵部尚书,兼议政大臣的班第,仍然要兼管理藩院事。可见,班第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是受到康雍乾三帝肯定的。从武功上看,在班第任湖广总督期间,就曾以两个月的时间镇压湖南筸永绥苗人起义,而受到乾隆的嘉奖。在清军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中,班第以内大臣的身份附金川军营办理粮饷,被加封太子少保。乾隆十五年,又赴西藏平定罗布藏丹经等人叛乱,诛杀罗卜藏扎什等。乾隆十八年,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又缉获增城东莞奸民王亮臣等。可以说,在雍正、乾隆年间的重大军事活动中,班第都担任过要职。虽然,在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中,班第任四川巡抚,办理粮运,因 “见军机未能速竣工,不肯任其事,唯请另派大臣经理,……于张广泗之罪直陈无隐,而一字不及讷亲。”[6]被罢免兵部尚书,降为侍郎。但这是班第为数不多的降职。可以看出,班第性格稳重、谨慎,作战经验丰富,而且善于筹办粮运,很少犯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班第确实没有辜负乾隆帝对他的期望。
二、妥善布置,轻松平定达瓦齐
达瓦齐虽然坐上了汗位,但他本身才智平庸,贪图享乐,清军距伊犁还有百余里时,他仍然“日纵酒为乐,不设备。”[7]被擒至北京封为亲王,赐第宝禅寺街后,“不耐中国风俗,日惟向大池驱鹅鸭浴其中,以为乐。”[8]因此,准噶尔部人心离散,在第一次平定准噶尔叛乱过程中,清军几乎没有遇到大规模抵抗。《圣武记》中“所致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绎络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9]的说法,虽有夸张之处,但也不是没有依据。最终,在达瓦齐逃至格登山后,侍卫阿玉锡等二十五骑发起突袭,达瓦齐仅带数百骑逃至南疆,最终,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所擒获,献给清军。总体来看,班第在第一次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并没有突出贡献,但实际上每个关键环节都有班第的精心部署。
首先,在进军时间上。乾隆帝原本担心“未深知达瓦齐情形”[10]令班第、永常在博拉塔拉河会合,四月内进军。但班第,在“收获包沁扎哈沁等众谍哈萨克掠达瓦齐牧准噶尔生计蹙”[11]的信息后,立即奏请二月内先后进剿。四月,行军至博拉塔拉时,“得达瓦齐所遣征兵使者,知伊犁无备。班第谋约西路军锐进。”[12]战争中,战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班第能够在乾隆已经有明确旨意时,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果断进军,确实体现出了他作为统帅的一种决断力。其次,在指挥军队上。统率一支由阿睦尔撒纳、萨喇勒为先锋的军队,就意味着不止要与达瓦齐作战,更要留心他们二人。同时,清军将领中也有一些掣肘之事,征西将军永常就“自受事以来刚欲自用……更沾沾以接济兵粮为必不可绥之事,足以见己之长,独不思按月接济粮。”[13]乾隆帝下旨“从前永常不识事体,数请运米,军营兵丁,军所稔闻,日久未见支领,不无悬望希冀情事,现在正系军行紧要之时,不得不为忧虑,班第升任将军,西北两路,事同一体。”[14]其三,持重进军。班第手握大权,但从不居功自傲、贪功冒进,即使在已经得知达瓦齐逃至额密勒初,也是一面让阿睦尔撒纳领兵先行,一面上奏乾隆“臣思大兵现在深入,臣等所领兵马,休养数日,益觉饱腾,现选兵八百名,令马木特、阿兰泰带领先行,会同阿睦尔撒纳等,一并迸发,尚余兵八百名,臣班第随后带领。”[15]关于达瓦齐的擒获,更多被人们所熟知的是由霍吉斯将其擒获,但在《清代通史》中就说到:“城主霍吉斯,虽故与达瓦齐善,以已得班第檄……献于军前。”[16]《啸亭杂录》和《圣武记》中也说“阿克苏伯克霍迪斯,已得班第军中檄,即执之以献。”“而霍吉斯已承我将军檄。”[17]“后承班公檄,献于军门。”[18]可见,班第对此是有提前部署的。
三、阿睦尔撒纳反叛与班第的关系
在乾隆帝《御制双烈诗》的前言中指责班第、鄂容安:“观望疑虑,以致兔脱。”[19]后世著作中,也多认为班第没有及时擒拿阿睦尔撒纳。但在对《清实录》等史料对比分析后,发现这一说法并不够全面客观。
“阿逆出身微贱,而狡黠凶狠迥异。”[20]投奔清朝的目的就在于借清军的力量,统一准噶尔,并做大汗。但乾隆在开始并没有认识到阿睦尔撒纳的野心,并且非常看重他。仅在《西域图志》中,就收录了乾隆帝《御制准噶尔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归诚信至诗以纪事》、《御制赐宴辉特部亲王阿睦尔撒纳》等多首为阿睦尔撒纳所做的诗文。在达瓦齐擒获后,前锦州副都统纳兰图奏言:“阿睦尔撒纳等,系被达瓦齐逼迫来降之人。不可深信,应加意防范”[21]等语。乾隆帝称:“此奏,甚属懦怯不堪之至!……阿睦尔撒纳有勇有谋,且感激朕恩,常思报效”[22]将纳兰图革职拿问。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的过分信任,为阿睦尔撒纳最终的反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基本平定达瓦齐之后,乾隆帝打算“仍众建而分其力”[23]复设四卫特拉。但“阿睦尔撒纳之乞进兵也,本欲假手大兵灭准喝尔,以己为珲台吉,总辖四卫拉特。”[24]请求清廷“于伊亲戚中,不论何姓,则其众心诚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举,奏请皇王施恩,裨领其众。”[25]野心毕露无遗。对此,班第早有觉察,在阿睦尔撒纳等过扎哈沁,私将人口带往时,就意识到了阿睦尔撒纳的不轨,将此事上奏了乾隆,但乾隆的批复是“朕以非大事,不必过于约束。”[26]在班第奏称“带兵前往额尔齐斯之西喇托辉地方,已阿睦尔撒纳前队会合等语。”[27]乾隆帝错误的认为是班第怕阿睦尔撒纳抢功,批复到“大兵进剿,自宜略分先后,经朕屡降谕旨,令班第计阿睦尔撒纳行程,约离数日,相继前进,……前因永常急遽进兵,其意惟恐萨喇勒首先成功,伊不得同邀爵赏,朕已降旨训饬,班第若祈存此意,即属器量狭小,岂朕委任之意。”[28]在军队行进至塔木集赛后,班第奏言阿睦尔撒纳:“攫取牲只,又妄自夸张,调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及入伊犁,益无忌惮,纵属下人肆行掠夺,不行禁止,及得达瓦齐游牧,所牧牲只财物,多方隐匿,驼马各千余,羊至二万余,又素性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众心怨恨,遂恩拥自卫,不愿撤兵,臣等时为催促,推诿观望,且云巴里坤、额尔齐斯二处,仍须各留精兵五千驻防,明系仗我师力,威服准夷,以遂私计,至奉晓谕哈萨克敕书时,阿睦尔撒纳故意犹豫,欲先自行遣使,臣等力指其非,始令侍卫顺德讷同往。……再阿睦尔撒纳扬言此处喇嘛等谋叛,请将济隆呼图克图速行遣往,令其宣谕众庶,安辑人心,阿睦尔撒纳久居此处,致伊等猜疑,必至生变,或因欲实其言,潜行鬼蜮,故生事端,俱不可不先事预防。”[29]可以说将阿睦尔撒纳反叛的意图讲的非常清楚。但乾隆帝的批复“初览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详闻,仍系阿睦尔撒纳希图徼幸,贪得只什物耳,并无图占准噶尔确据,阿睦尔撒纳自投诚以来,叠受朕恩,事事出于望外,至朕办理庶政,一惟秉公执法之处,伊未经身试,是以志气骄盈,希图徼幸,亦事所必有。……亦不必过于苛求”[30]在班第密奏:“阿睦尔撒纳私用图记,调兵九千,防守哈萨克,布鲁特等”时,乾隆的批复仍然是“阿睦尔撒纳,擅行派兵防守,班第等理宜阻止,但既经遣派亦可,朕前降旨,令阿睦尔撒纳入觐,如已起程来京,此事可不必置问。”[31]在萨拉勒、鄂容安等多次密奏后,乾隆才意识到:“阿睦尔撒纳意欲占据准噶尔种种僭越佞行,情蹟系著一摺。……种种不法之处,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岂必待其生变。”[32]阿睦尔撒纳佯装赴热河觐见,同时,加紧煽动纳噶察告称阿巴噶斯乌克图与喇嘛等议:“有若不令阿睦尔撒纳统领准噶尔,伊等宁剖腹而死等语。”[33]乾隆传谕班第、萨喇勒、鄂容安:“阿巴噶斯是为阿睦尔撒纳威力协制,情系可原”[34]在班第密奏,阿睦尔撒纳将所赏皇带孔省翎置而不用,并不将已经内附受恩之处,告知厄鲁特人众等语时,乾隆才真正下决心除掉阿睦尔撒纳,密旨班第:“今览班第等所奏,阿睦尔撒纳不惟不知感激朕恩,且将内附受恩之处,欺瞒厄鲁特人众,即此一节,应当明正典刑,其余悖逆之事,更无足问矣。班第等如奉到前月二十八日所降谕防已将阿睦尔撒纳擒治甚属妥协如尚未办理伊起程前来朕必将伊拏问班第等诸事务宜密之又密不得稍有泄漏”[35]但阿睦尔撒纳已有了一定的准备,而清军大军早已撤回,班第仅有索伦兵三百,喀尔喀兵两百,不敢轻易动手。身为定边右副将军的萨喇尔更是向班第、鄂容安进言:“阿睦尔撒纳智勇兼备,不可撄其锋,不如覆命天子,将准部界之,其祸可立解也。”[37]遭到了班第、鄂容安的严词拒绝后叛逃。此时,定西将军永常驻军木垒,仍有劲兵数千,不但没有及时出兵相救,反而退守巴里坤,军务大臣刘统勋奏请退回哈密。一再贻误军机,被乾隆帝革职拿问。相反,之前,因奏请分置阿睦尔撒纳家属而获罪的舒赫德,在“闻班忠烈公第(班)密劾阿逆之事,日:阿逆叛志已决,不可使得其家属傅虎以翼,……乃部署士卒,围其营帐。其夜阿逆众至,……阿知有备,乃踉跄遁去。”因此,阿睦尔撒纳的反叛,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倘若乾隆帝能够早下决心,不多次对缉拿阿睦尔撒纳留有余地,或者,永常等及时出兵相救,班第的牺牲和第二次准噶尔战争都是有可能避免的。
四、班第之死的影响
在策楞奏言:“班第等陷贼之信后”,乾隆帝“深为悯恻”“每一思之,不胜愤懑。”著扎拉丰阿、玉保、策楞等,设法通信,传谕班第等,“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办事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义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兵。”[38]足见,乾隆帝对班第的爱惜。最终,班第寡不敌众,无法突围,自杀殉国。之后乾隆帝的平准、治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以“天下共主”“不喜穷兵黩武”自居的乾隆帝,在第一次平定准噶尔用兵中以怀柔政策为主,即使在阿睦尔撒纳反叛之初,仍然下旨:“阿睦尔撒纳虽有罪应诛,其游牧人众,毋庸掠拢,诚恐明噶特等,肆意抢掠,非所以示体恤,仍遵前旨传谕伊游牧人众,照旧安居,……并严禁抢掠。”[39]但在班第等自杀后,乾隆帝便认为“厄鲁特人皆不可德怀”[40]以赐死额林沁多尔济为例,乾隆帝很清楚,额林沁多尔济虽才智平庸,放走了阿睦尔撒纳,但他毕竟是喀尔喀大活佛呼图克图的兄弟,赐死他,很可能会引起喀尔喀的动乱,但乾隆帝坚持了这一做法。结果,原本就与阿睦尔撒纳有勾结的喀尔喀贵族青滚杂卜利趁机发动叛乱,“自军营私行逃归,遂将伊卡伦,台站兵丁尽行撤回,……多方煽惑喀尔喀人等”[41]引发了准部更大的叛乱。
乾隆帝的这一转变,对之后指挥平准的将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班第之后,主持西征的策楞、玉保、达尔当阿等都屡次错失良机,让阿睦尔撒纳轻易逃走,被革职拿问。虽然兆惠“以寡击众,战守甚力。”[42]清军最终能够再次平定准噶尔,他功不可没,但兆惠的军队“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可渔猎资身之地,皆搜剔不遗,……呼走壮丁,以次骈戮,妇孺驱入内地,多死于途。”[43]巴里坤大臣,雅尔哈善更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纵兵“乘夜雪袭杀巴雅尔全部四千余人。”[44]反观班第,早在出任两广总督时,他就奏言:“广东贮炮械皆多。皆前荡平藩逆及海寇时所缴。日就朽坏,可惜,请将完好者修整,余悉熔铁备用。”[45]可见,班第是比较爱惜民力的。在第一次平定准噶尔过程中,乾隆帝也称赞到:“班第自到军营以来,办理诸事,俱合时宜,奋勇果断,……收厄鲁特兵一百五十余名,我兵并未伤损一人。此皆班第实心奋勉,调遣合宜所致,深属可嘉!”[46]并且他多次约束军队,不得滋扰民众。与之相比,清军第二次平定准噶尔和兆惠等人的功绩,就充溢着一种血腥。这种“由阿睦尔撒纳服叛而导致的乾隆治准政策的改变,终于给准噶尔人带来了无情的灭族之灾。”[47]班第之死,是促使这一改变的重要原因。
此外,班第之死,对清朝最终对准噶尔设官置守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初定准噶尔后,乾隆帝原本令班第“于准噶尔归大宰桑之子孙,或已革宰桑内,择其诚实者,拣选八九人,带领家属,移居察哈尔地方,令其巡查,并资差遣”。[48]但最终,清朝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正如松筠所言:“准噶尔之平,实启自阿睦尔撒纳忽叛忽降,兵端由此起,即疆舆由此定”。[49]
[1] 清世宗实录(卷105)[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383.
[2][21][22] 清高宗实录(卷489)[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737、14754、14754.
[3][4] 清高宗实录(卷469)[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481、14481.
[5][16][36][42][43]
[44] 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88、90、92、94、94、95.
[6] 吴忠匡等校订.满汉名臣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1284.
[7](清)李元度著,易孟醇点校.国朝先正事略[M].长沙:岳麓书社.1991:610.
[8][17][20][37](清)昭琏著.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76、76、75、99-107.
[9][18][23][40](清)魏源著.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6、152、152、155.
[10][11][45] 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中)[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822、822、822.
[12] 赵尔巽著.清史稿(卷三百十二. 列传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661.
[13][14][25](清)傅恒等撰.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2辑)[M].《平定准噶尔方略 1-4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1175、1150-1151、1202.
[15] 清高宗实录(卷487)[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14708.
[19]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24] 包文汉整理.清朝蕃部要略稿本(厄鲁特要略四)[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204.
[26] 清高宗实录(卷485)[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14677.
[27][28] 清高宗实录(卷486)[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14694、14694.
[29][30]
[31] 清高宗实录(卷491)[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14778-14779、14779、14782.
[32] 清高宗实录(卷492)[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14782.
[33][34] 清高宗实录(卷494)[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14814、14815.
[35](清)傅桓.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五)[M].北京:全国图书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1215.
[38] 清高宗实录(卷499)[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14889.
[39] 清高宗实录(卷495)[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14821.
[41](清)傅桓.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三)[M].北京:全国图书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1519.
[46] 清高宗实录(卷475)[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145421.
[47] 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19.
[48] 清高宗实录(卷490)[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14767.
[49] (清)汪廷楷,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一).《初定伊犁记事》[M].北京:中国书店,2010:12.
2016-09-10
吴学轩(1991-),男(汉族),甘肃张掖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