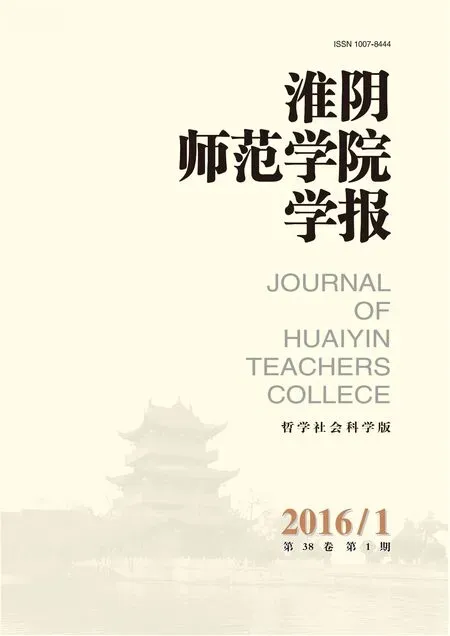网络时代全球化的时空转变
2016-03-16黄少华
黄少华
(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网络时代全球化的时空转变
黄少华
(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结构性转变。在时空层面,这种结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分离、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二元交织、流动和弹性成为全球化的主导逻辑。
关键词:全球化;网络社会;时间;空间
一、时空视域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作为伴随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而逐渐兴起的一股浪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的动力机制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随着以互联网崛起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全球化已然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作为对这一结构性转变的理论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词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正如沃特斯(M.Waters)所说:“就像后现代主义是19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19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借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转换的关键概念。”[1]在社会学界,哈维(D.Harvey)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吉登斯(A.Giddens)的“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卡斯特(M.Castells)的“网络社会”,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和贝克(U.Beck)的“风险社会”等理论概念,都尝试对全球化作出新的解释。相比于经典社会学的社会决定论视角,今天社会学家对全球化的讨论,已经开始转向一个多元的视界。在这种多元视界中,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切入对全球化结构转型的分析,尤其引人注目。
吉登斯认为,时空特性是认识社会的重要维度。忽视时空特性,必然导致社会学以简单、粗疏的方式研究社会。在传统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空间常常只是被简单地视为社会行动的环境或舞台,并不假思索地接受视时间和空间为一种可以客观地加以数学测量的观念[2],而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构社会理论。与此不同,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空间越来越被视为相对的,并被认为是渗透于社会行动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像吉登斯、卡斯特、鲍曼(Z.Bauman)等社会学家,都十分强调时间、空间与社会行为和社会过程的内在关联,甚至强调“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3]。在吉登斯看来,时空结构是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它参与形成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建构了形形色色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他强调,在今天,现代性与全球化联手改变了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因此理解和把握时间空间延伸和分离的实质,是理解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关键。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仅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空间与场所也相互分离。由于邮件通讯、电报电话、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场东西的直接作用正越来越被在时空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换言之,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延伸,导致社会被不断地重组。所以他强调:“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延伸的基本方面的表达……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4]不过,与吉登斯强调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时空延伸不同,像鲍曼和哈维这些学者强调的是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例如鲍曼认为,“‘时空压缩’概括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人类状况参数的多层面改变”[5]1。哈维同样用“时空压缩”来概括现代性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哈维认为,现代性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表现形式,并进而改变了我们经历与理解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现代主义促进了时间与空间的压缩,而且这个过程在后现代时期以被大大加速,从而导致时空压缩的强化阶段。“强大的发明潮流,集中聚焦在加快和快速的周转时间上。决策的时间范域(现在已经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分秒必争)缩短了,而且生活方式的风尚变换迅速。这一切伴随了空间关系的激烈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理形势的浮现。这些事件,引发了强烈的时空压缩的感受,影响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每个面向”[6]。
卡斯特提出“流动空间(flow space)”和“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概念,作为分析网络时代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在众多从时空关系讨论全球化实质的当代社会学家中颇为引人注目。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是指“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在网络化社会中,社会事件与社会关系围绕“流动”而建构,包括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组织性流动、象征流动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空间(local space),流动空间以空间与地点脱离为特征。在流动空间中,不在场的事件影响甚至决定着在场事件。而无时间之时间则解构了时钟时间的概念,在以光速传播信息的网络社会中,空间的流动性导致以地域为标识的时间虚拟化,时间成为穿梭在全球信息回路,“混合了横越邻里的现场报导”,呈现为“前所未有的时间立即性(immediacy)”[7]561。卡斯特强调,信息技术范式是推动这种新的时空结构凸显的核心机制,“资本脱离时间以及文化逃离时钟都受到新信息技术决定性的促动,并且嵌入网络社会的结构里”[7]505。信息技术所塑造的“以电子为基础的沟通系统”,已经“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物质向度:时间和空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向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地方空间。当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可以在同一则信息里被预先设定而彼此互动时,时间也在这个新沟通系统里被取消了”。[7]561其结果是,流动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构成了新的全球化社会的物质基础。
二、全球化的时空转变
网络时代全球化的时空转变,首先体现在作为人类生活之基本物质向度的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分离。卡斯特认为,空间(space)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空间就是社会,它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结构的动态所塑造。”[7]505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空间和地点是同一的,人们通常通过“场所”理解“地点”,场所作为人们展开社会生活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界性界限之内的地域(locale)”[8]。而地点的涵义在于,它必须能够承载物理实体于其上并且意味着边界的存在。因此,在网络社会出现以前,人类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一种地域性活动,表现为“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受‘在场(present)’的支配”。而在网络时代,空间则日益与地点相分离,社会活动不再局限在给定的共同场境中面对面展开,人们置身的物理地点与其展开社会活动的社会空间已全然不是一回事了。社会空间“有不同凡响的即时传播的特性。从此,人们不再被物质的障碍和时间的阻隔分离。随着电脑终端和录像监测的结合,这儿和那儿的区分不再有任何意义”[5]16。在这种情形下,场所常常被远距的社会事件穿透并重建。“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7]530。
网络时代全球化时空转变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二元交织。在工业时代,全球化意味着地方或个人从地方性物理空间中剥离,而融入全球性的资本和市场逻辑体系之中;相反,地方化则是对地方性特征的强调与保留,并在此基础上对带有侵略性质的全球逻辑体系的拒绝。在网络化时代,这种工业时代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已完全被颠覆,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二元交织关系。全球化意味着在时间延展下,“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结构……全球化本质上是指这个延伸过程”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5]56。在网络时代,全球化意味着决定地方性事件的,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是本地的事件与情境,而是全球层面的互动形塑着地方性事件的性质和进程。“在网络空间,地方只有在全球化的流动过程中才能获得意义”[8]同时,远距事件还参与着地方认同的建构。在网络时代,个人认同与地方认同的建构,常常与全球化相联系甚至借助全球化才得以实现。互联网作为全球互动平台的形成,打破和超越了物理时空对社会时空的限制,使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二元交织在今天成为现实,这种“二元交织”体现了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全球化中地方与全球的关系,全球化和地方化已不再彼此分离排斥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定义。
网络时代全球化的时空转变,还体现在全球化主导逻辑的改变。网络社会的崛起,导致全球化的主导逻辑,由先前的稳定和固化转变为流动和弹性。鲍曼在其《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中强调:“在后现代社会中,流动性成了最有力、最令人垂涎的划分社会阶层的因素;每天,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阶层不断地形成和重建,其依据就是流动性。”[5]9卡斯特也强调,新信息技术范式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其重新构造的能力,这在以不断变化与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里是一种决定性的特征[7]84。信息技术范式的弹性与流动性特质,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固定的物理空间,在一个水平网络里由不同节点的任意组合构造社会生活。高度的信息复制组合能力,导致资本在全球回路中运作的高效并从根本上改变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形态,传统的金字塔型科层制组织逐渐转向扁平化的鱼网式组织,“从而使组织虚拟化,成为一张没有控制中心、由节点相互沟通编织而成的弹性的鱼网”[8]。在这种流动和弹性的网络结构中,流动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时空延伸和时空压缩的二元交织,构成了网络时代全球化的时空结构。
参考文献:
[1]Waters M.Globalization[M].London:Routledge,1995:1.
[2]黄少华.哈维论后现代社会的时空转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3).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5.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3.
[5]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M]//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92.
[7]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J].兰州大学学报,2003(3).
责任编辑:张超
“网络与人文研究”征稿启事
本栏目选题范围包括网络与哲学政治问题、网络与社会经济问题、网络与道德法律问题、网络与语言文学问题等,要求论题新颖独到,理论性强,论述透辟,避免通篇一般叙述。来稿字数请控制在8000字以内,行文格式符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排规范,请打印并附寄磁盘文件(或发送电子邮件,E-mail:zhchao053@163.com)。
本刊编辑部
作者简介:黄少华(1963-),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宁波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合作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的宁波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1-0123-03
收稿日期:2015-11-25
【网络与人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