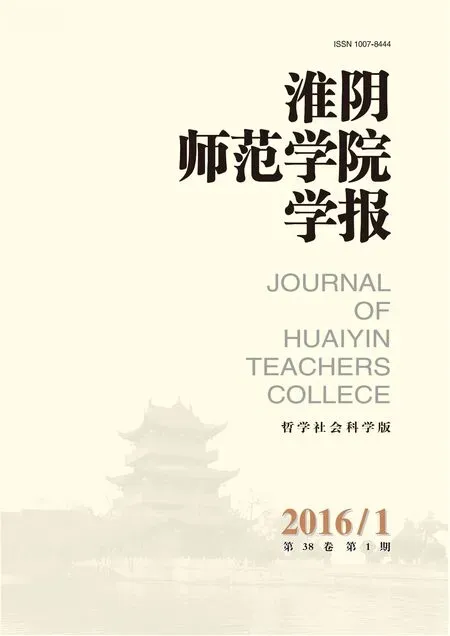明代精英文人与民歌传播——以李梦阳、何景明、李开先和冯梦龙为例
2016-03-16徐文翔
徐文翔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00)
明代精英文人与民歌传播
——以李梦阳、何景明、李开先和冯梦龙为例
徐文翔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00)
摘要:明代中后期,以李梦阳、李开先、冯梦龙等为代表的精英文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民歌的传播中。他们或利用自身在文坛上的影响力促进某些曲牌的流传,或亲自搜集、整理、刊刻民歌集,对民歌的传播以及民歌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反映出雅俗互动的文化背景下文人与民间的深入交流。
关键词:明代;精英文人;雅俗互动;民歌传播
明代民歌是市民文化的产物,属于典型的市民文学。此类文学的发生、发展,通常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律,即所谓的“民间机制”。但部分精英文人对民歌的染指,在客观上对它的传播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处所说的“精英文人”,指自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文学地位,并通过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文人,比如李梦阳、何景明、冯梦龙等。。明代(尤其是中晚明)的精英文人,他们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经常是兼及雅俗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民歌的传播不会如此迅速地融入雅俗互动中。更何况,有些文人本身在民间就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他们对某些曲牌的推崇,必然导致其流行程度的增加。对精英文人与民歌传播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能够更好地理解明代文化的雅俗互动,进而更准确地把握文学发展的脉络。
一、李梦阳、何景明与《锁南枝》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载:“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1]中原,也就是河南及其周边地区。而在成、弘年间,文坛的两位领袖人物李梦阳、何景明也长期居住在河南,与当地流行的民歌有着密切的接触。按照李梦阳《诗集自序》中的说法,他一开始并不欣赏民歌,认为“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词靡靡”,完全不符合其审美标准。在其友人王叔武的一番开导下,梦阳方改变了对民歌的印象。王叔武为山东曹县人,从地理位置上说,曹县与河南交界,也属于中原地区,因此其地所流行的民歌,应当也不出《万历野获编》所说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那么,叔武所称赏民歌的“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差不多也就指以上几种曲牌而言。
从现存资料来看,梦阳在对民歌的印象改观之后,尤其推崇的是《锁南枝》。比梦阳稍晚的李开先,在其《词谑·时调》中有如下记载:
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请问其详。崆峒告以:“不能悉记也,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越数日,果闻之,喜跃如获重宝,即至崆峒处谢曰:“诚如尊教。”何大复继至汴省,亦酷爱之。曰:“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每唱一遍,则进一杯酒。终席唱数十遍,酒数亦如之,更不及他词而散。……词录于后:以竢识者鉴裁:“傻酸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2]1276
开先之生活年代仅比梦阳稍晚,此则材料在细节方面或有虚构,但大体上应当是真实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中的记载,可以与此相参照:
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
可见,李、何二人所称赏的那首《锁南枝》,就是《万历野获编》中所说的《泥捏人》。据传这首《泥捏人》本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所作,名为《我侬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3]
后流衍为民歌,直到晚明尚且风行,只不过曲牌换作了《挂枝儿》。冯梦龙《挂枝儿》“私部”一卷《泥人》曰:
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捻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他来糅合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
下并有评语曰:“此赵承旨赠管夫人语,增添数字,便成绝调。赵云:‘我泥里有你,你泥里有我。’此改‘身上’二字,可谓青出于蓝矣。”[4]230
此为《泥捏人》之流衍过程,而我们关注的是,成、弘年间李梦阳与何景明对这首民歌的传播所起的推动作用。继李东阳之后,李、何二人领袖文坛,《明史·文苑传序》曰:“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此一变。”[5]《何先生传》亦称:“于是明兴诗文,足起千载之衰,而何、李最为大家。今学士家称曰‘何、李’,或称曰‘李、何’,屹然为一代山斗云。”[6]《锁南枝》本为市井之徒所熟稔,一般文人学士可能对此并不感兴趣,其一,依照传统观念,流行民歌不入其法眼,因此亦不关注;其二,或有接触,但像李梦阳早期那样,存有偏见。但梦阳以如此尊崇之地位,居然去肯定流行民歌这种“下里巴人”的东西,并对学诗文者说“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这对天下文人无疑会产生一种指向性的影响。也许不排除这种情况:有许多文人本对这首《锁南枝》并不熟悉,但因梦阳此语,或许会特意去了解、学习,这在客观上对《锁南枝》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又或许,因为《锁南枝》,文人又会对其他曲牌的民歌有所了解。文人在接触这些民歌后的反应,可能并不总如那个“学诗文者”般“喜跃如获重宝”,但因此而促使文人去接触民歌、加深对民歌的了解,对民歌的传播而言无疑是有益的。再如何景明,同样对这首《锁南枝》,景明称之为“时调中状元也”,并“每唱一遍,则进一杯酒。终席唱数十遍,酒数亦如之,更不及他词而散”。以何之地位,这则风流轶事无疑会对他的仰慕者起到很大的影响。抛开文学层面的作用不说,李、何二人对《锁南枝》的推崇,势必会影响大量文人仿效之;而文人群体对民歌的关注和肯定,又会极大地提高它在雅俗文化互动中的地位。
二、李开先与《市井艳词》
李开先是“嘉靖八才子”之一,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然而他的仕途却并不顺利。他曾在朝中任职十三年,官至吏部郎中、太常寺少卿,却由于性格刚直而身陷党争之中,终于在嘉靖二十年(1541)被罢官。此后的27年,他都闲居于故乡章丘,广置田产,怡情享乐,以排解忧愁。开先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是这长达27年的闲居时间,却也造就了他在文学上——尤其是戏曲上的卓越成就。据他自述,这段时期,“有时注书,有时摛文,有时对客调笑,聚童放歌;而编捏南北词曲,则时时有之”。除了在戏曲上的成就外,开先对民歌也颇用心,集中表现在对《市井艳词》的编辑和为之所作的四篇序言上。
李开先因长期闲居乡里,所以能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民间流行的民歌。在《市井艳词序》中,开先说:
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一则商调,一则越调……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
开先所述,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民歌流行情况颇有帮助。沈德符称“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而开先称在章丘地区“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虽然两种曲牌的流行时间并不一致,但正德和嘉靖都属于“自宣正至成弘后”,因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山坡羊》和《锁南枝》在当时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流行。“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这句话虽略有夸张,却说明了这两种民歌在市井中是何等地风靡。开先在这首序中接着叙述自己改写和仿作这两种民歌的情形:
尝有一狂客凂予仿其体,以极一时谑笑。随命笔并改窜传歌未当者,积成一百以三。不应弦,令小仆合唱,市井闻之响应,真一未断俗缘也。[2]469
“尝有一狂客”云云,不必一定当真,笔者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开先找的一个托词,实际上是他自己难以按捺住对民歌的兴趣。“命笔并改窜”,是说开先对流行民歌(即《山坡羊》和《锁南枝》)进行了改写,但也不排除其中有拟作的成分。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先这本《市井艳词》编出来后,民间的反应是“市井闻之响应”,也就是说在民间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市井艳词又序》中,开先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反响:
词出一时狂兴,聊以应客侑觞,不意邑人有录之者,有欲刊之者,又有欲焚之者……然录者百人而有九十人焉,刊者多半,焚者无几。
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人对《市井艳词》是肯定和接受的,仅有个别之人加以反对。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精英文人与民间文化通过民歌进行互动的例子。这一百余首《市井艳词》虽然已经亡佚了,但我们可以肯定,开先虽然对流行民歌中“淫艳亵狎”的成分进行了删改,但总体风格上仍然是很“俗”的,不然市井之人也就不会“闻之响应”了。之前的李梦阳、何景明是利用自己在文坛的影响力对《锁南枝》进行推崇,从而推动了它的传播;而开先则更进一步,他不仅在理论上肯定民歌,更亲身参与民歌的传播中。在《又序》中,开先还论述了自己对于通俗文学传播的看法:
俗以渐加,而文随俗远。至于《市井艳词》,鄙俚甚矣,而予安之,远近传之。米南宫尝谓东坡:“世皆以某为狂,请质之。”东坡笑曰:“吾从众。”予之狂于词,其亦从众者欤![2]470
“俗以渐加,而文随俗远”,是开先长期与民间文化接触而得来的经验。与李、何二人不同的是,开先因其经历,而更具民间视野,这是他从事民歌实践工作的前提。而从效果上看,这种实践是非常成功的。由此可见,即便是上层文人,只要充分认识到通俗文学的性质和传播规律,也能很好地促进它的传播和雅俗文化的互动。李开先编辑《市井艳词》而推动了《山坡羊》《锁南枝》两种民歌的传播,便是很好的例子。
三、冯梦龙与《挂枝儿》《山歌》
无论是在对民歌的认识上,还是对民歌传播所作出的贡献上,冯梦龙都堪称明代第一人*关于冯梦龙的民歌观念及对民歌整理所做出的贡献,可参看拙文《冯梦龙〈叙山歌〉解读》(《名作欣赏》2013年8月刊)、《论冯梦龙的民歌观念》(《南方论丛》2015年第1期)以及《冯梦龙的民歌编纂》(《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梦龙的民歌观念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点,便是他赋予民歌以一种独立的文体地位。在此基础上,他对民歌的辑录、整理才能依照民歌的“本来意义”进行。
冯梦龙一生主要编辑了两部民歌集,即《挂枝儿》和《山歌》。《挂枝儿》是梦龙编辑的第一部民歌集,共收录《挂枝儿》曲牌的民歌420首*这其中含有冯梦龙及其友人的数首拟作,梦龙在集中都有详细说明。详见周玉波、陈书录编:《明代民歌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梦龙本人并没有为《挂枝儿》这部民歌集作序,其好友俞琬纶有一篇《〈打枣竿〉小引》,因为《打枣竿》即《挂枝儿》,而且根据序中的内容,可以判断这篇序文就是与俞纶为梦龙的《挂枝儿》所作的序。在序中,俞氏说:
街市歌头耳,何须手为编辑,更付善梓,若欲不朽者,可谓童痴。吾亦素作此兴,尝为琵琶妇陆兰卿集二百余首,间用改窜。不谓犹龙已早为之,掌录甚富,点缀甚工。而兰卿所得者,可废去已。[7]
从“尝为琵琶妇陆兰卿集二百余首,间用改窜。不谓犹龙已早为之”这句话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即梦龙所辑录的《挂枝儿》,其中一个来源渠道就是从歌妓那里得来的,而梦龙在年轻时确有一段时光曾流连于歌台妓馆,并与一位名妓侯慧卿相恋。在《挂枝儿》集的最后,梦龙以一首自作结尾,词曰:
纂下的《挂枝儿》委的奇妙,或新兴或改旧费劲推敲,娇滴滴好喉咙唱出多波俏。那个唱得完这一本,赏你个大元宝。啧啧,好一本新词也,可惜知音的人儿少。[4]293
其中的“或新兴或改旧费劲推敲”这一句颇耐人寻味。“新兴”指的是当前正在流行的民歌,这毫无疑问;那么“改旧”怎么理解呢?笔者以为,这说明梦龙自早年间便已经收集了一些《挂枝儿》民歌,当时或许并非有意要编纂一本《挂枝儿》民歌集,而只是单纯出于对歌词的喜爱。梦龙后来编纂此集时,以前收集的那些旧作也拿出来进行了整理,“改”的原因或许是新兴的《挂枝儿》已经和旧歌在体式上略有不同,或许有其他原因。在末尾,梦龙又说“好一本新词也,可惜知音的人儿少”,似乎是说所编的这本《挂枝儿》并没有得到世人很好的反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这首拟作本就是集中的一首,写完之后全集才开始刊行,那么在传播之前,梦龙怎么会知道缺少“知音”呢?除非这首是全集传播之后,梦龙又后期加入的,而这种可能性极小。何况梦龙在中间说“那个唱得完这一本,赏你个大元宝”,对所编的这本集子似乎颇为自得。那么,他这么说便可能是出于一种“广告”的心理。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揣测,幸识者有以教我。
关于《挂枝儿》的实际传播效果,清初文人钮琇在《觚剩续编·人觚》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试卷皆亲自批阅……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局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8]
“浮薄子弟,靡然倾动”与“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说得很明显——梦龙所编辑的《挂枝儿》,实际上是大受民众欢迎的。当然因此也引起了一些负面效应,但这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挂枝儿》的传播之广。另外,王骥德《曲律·杂论》也记载这样一件事:
昨毛允遂贻我吴中新刻一帙,中如《喷嚏》《枕头》等曲,皆吴人所拟,即韵稍出入,然措意俊妙,虽北人无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远也。[9]
王骥德大约与梦龙同时,毛允遂送他的“吴中新刻一帙”,里面的《喷嚏》《枕头》,也正是梦龙所辑《挂枝儿》中其好友的拟作。因此可以肯定,友人送给王骥德的,正是梦龙的《挂枝儿》。通过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挂枝儿》不但大受“浮薄子弟”欢迎,也流传于文人群体中。这正印证了熊廷弼所说的“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这句话。
《挂枝儿》成书之后,梦龙又编辑了第二部民歌集《山歌》。与《挂枝儿》只收同一曲牌的民歌不同,《山歌》并不是一种曲牌的名字,而是吴中地区流行的“吴歌体”民歌的统称。此外,《山歌》中除了“山歌”之外,还收录了一些当时传播于吴中地区的《桐城时兴歌》。《山歌》的成书时间是在《挂枝儿》之后,但梦龙对集中民歌的搜集时间,似也可上溯到其青年时期。在《山歌》卷五“杂歌四句”中一首《乡下人》的注释中,梦龙说:
莫道乡下人定愚,有极聪明处。余犹记丙申年间,一乡人棹小船放歌而回,暮夜误触某节推舟。节推曰:“汝能即事作歌当释汝。”乡人放声歌曰:“天昏日落黑湫湫,小船头砰子大船头。小人是乡下麦嘴弗知世事了撞子个样无头祸,求个青天爷爷千万没落子我个头。”节推大喜,更以壶酒劳而遣之。此节推亦不俗。[4]322
丙申年间,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是年梦龙二十三岁。我们假设梦龙从这时便开始留意身边的“山歌”,那么至其成书,其过程也长达二十余年。可见,在其前半生,梦龙几乎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和民歌发生着关系。在《山歌》的篇首,有梦龙所写的序言《叙〈山歌〉》。在序中,梦龙说“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这句话
说明当时所流行的民歌基本上都是情歌。另外,梦龙宣称“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儿》而次及《山歌》”,明确指出其编辑《山歌》的目的与《挂枝儿》一样,都是为了弘扬民歌中真挚的男女之情,揭露那些封建卫道士借“名教”之名而戕害人性的行径。将民歌的功能上升到思想武器的地位,在梦龙之前是没有过的。梦龙能有此认识,与他将民歌当作一种独立的文体有关。
从民歌传播上来说,冯梦龙所编辑的《挂枝儿》和《山歌》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吴中民歌在海内的流行。并且梦龙不仅仅是为传播而传播,他还赋予这两本民歌集以思想意义。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明代民歌丰富多彩的面目,很大的功劳要归于梦龙。从这个意义上说,梦龙编辑这两本民歌集,不仅功在当时,更利在千秋。
结语
到了明代,尤其是中晚明,部分文人一反传统,开始对“雅”文学的审美风格进行“俗”的追求,他们与民歌之结缘呈现出一种迥异于中古色调的群体自觉,达到了“从雅到俗”“以俗为雅”的雅俗之间较为平等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部分精英文人依靠其社会地位、文学地位的影响力,极大地推动了民歌的传播。在与民歌接触的过程中,这些精英文人也对民歌的“真”“情”等核心审美要素进行了理论上的接受,进而影响了其创作,促进了明中后期雅文学的世俗化。
参考文献: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47.
[2]李开先.李开先全集[M].卜键,笺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3]蒋一葵.尧山堂外纪[M].明刻本.
[4]周玉波,陈书录.明代民歌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07.
[6]何景明.大复集[M].明嘉靖刻本.
[7]冯梦龙.冯梦龙集笺注[M].高洪钧,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48.
[8]钮琇,觚剩[M].南炳文,傅贵久,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5.
[9]王骥德,王骥德曲律[M].陈多,叶长海,注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72
责任编辑:刘海宁
The Elite Intellectuals of Ming Dynasty and Folk-Songs’ Propagation—Take Li Mengyang, He Jingming, Li Kaixian and Feng Menglong for Examples
XU Wen-x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000; China )
Abstract:In the late of Ming Dynasty, the elite intellectuals such as Li Mengyang, Li Kkaixian and Feng Menglong , worked to the propagation of folk songs with great enthusiasm . They used their own influences in the literary world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some tunes, or in person to collect, inscribe, and sort out folk songs. It not only played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songs and folk art, but also reflect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iterary intellectuals and the civil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refined literature and the popular ones.
Key words:Ming Dynasty; the elite intellectuals; interaction of the refined literature and the popular ones; the spread of folk-songs
作者简介:徐文翔(1986-),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1-0106-04
收稿日期:2015-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