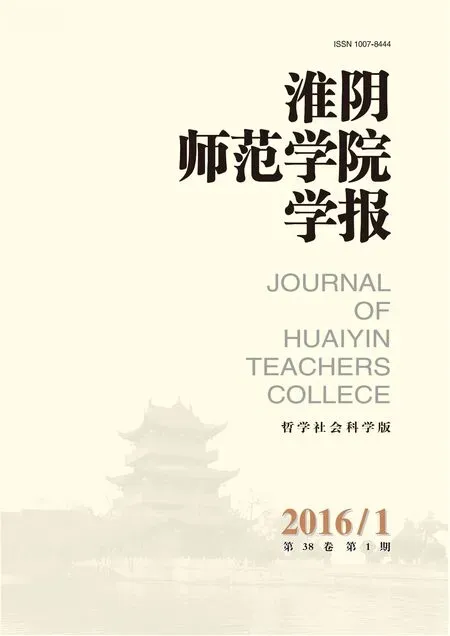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
2016-03-16乔治忠
乔治忠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
乔治忠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史学史学科具有评论以往历史学发展状况的内在功能,面对复杂多样的研讨对象,需要将思维突破本专业的界限,即具备很强的学术穿透力,才能完成其学术研究的任务。中国历史学在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不少偏差和扭曲,需要中国史学史学科在总结与评判中予以纠正。中国史学史的学术穿透力,还可以表现为在一般历史问题的探索中,发现和提出其他史学专业未能达到的思路,得出创新的论断。因此,加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学术穿透力;史学史;史学评论;逻辑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要取得较深层次的开拓和创新,应当具备相当的学术穿透力,但迄今学界对此探讨不多,因而对于思维的“穿透力”的理解,还往往是浮泛的。所谓“穿透力”,一般指研究问题周密、敏捷,直击核心,切入准、层面深,即具有透彻的思维和表达能力。这里显然没有讲明思维和研究“穿透”可以达到多大的范围,是否可以由此及彼、跨越个案,成为跨越本专业的穿透。本文即对此予以讨论,以与史学界同仁商榷。
一、史学史研究必当具备学术穿透力
史学史研究应当和必须具备较强的学术穿透力,这是由其学科的性质和内容所决定的。这里所谓的学术穿透力,主要是指突破本身专业范围,扩展到整个历史学甚至越出历史学界限而作出的评判。不言而喻,学术穿透的广度也必然包含着学术的深度。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担负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学术任务。中国史学史就是把演进范围大体规定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清理我们祖国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有规律。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内容,可以按分类方式归结为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等八个方面。[1]4-8很明显,“阐明史学演进过程”的任务,表明了史学史学科应该具有对以往史学发展状况予以系统总结的功能;“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导致史学史研究向史学理论思维的层次迈进。而总结性、理论性的学科,需要具备更强的学术穿透力,否则不能很好地完成其学科任务。
史学史研究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以往诸多史家、史书展开分析和评论,因此史学评论乃是史学史学科的内在功能。史学史面对历史学中不同的研讨对象,势不能对于以往史家及史书涉及的各种内容懵懂无知。因此史学史研究做出的史学评论,需要在更宽广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才能使思维穿透具体专业的界限,达到深刻、中肯和准确。
史学评论,并不仅仅属于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各个专业的学术讨论,都不缺少史学评论的内容。每个历史个案的研究都会出现不同意见的分歧,论者申述自己的主张,或支持相同、相近的学术见解,或对不同意见予以批评,自然就包含着史学评论,这种史学评论十分及时,你来我往,形成学术论辩,对学术的发展很有促进力度,十分宝贵。例如1950年代评价历史人物曹操,讨论就十分热烈,学者平等争鸣,基本没有来自学术之外的干预,也不顾忌论敌身份、地位等种种因素,仅以观点、论据的是非曲直发表评论、进行分析。这样的学术讨论事例还有一些,但未能保持和继续发扬,非学术因素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论辩的主导力量,给历史学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后虽则经历了观念和认识的拨乱反正,史学批评却一直没有恢复到完全正常的学术氛围,一方面是大面积的无原则吹捧,另一方面是仍然不时地出现非学术性的党同伐异。有鉴于此,凸现了需要从史学史角度进行总结性史学评论的迫切性。
史学史角度的史学评论,一般要迟于同一专业内的评论,其好处在于可以等到矛盾现象充分展开,背景原因更多显现,因而能够观察得更加全面,对于历史学较大问题应当并且可以追求最终的裁决水平。缺点是其往往滞后,难以尽快地支持正确见解、尽快反对错误主张。因此,在某些专业内历史问题出现主流上的大的偏差,或是学术讨论不很正常的氛围下,更应当提倡和较早地启动史学史角度的史学评论,这就要求史学史的研究者具备较强的学术穿透力,即有能力审视各个断代史中论说的偏差讹误,以纠正之。
迄今为止,历史学在发展进程中出现和积累了不少偏差、讹误和颠倒是非的扭曲性观念,需要从史学史研究的机制上予以纠正。偏差和扭曲的观念表现多端,试举例如下:
其一,缺乏史学史的学术意识,以断代史的“史料”眼光考察问题,容易出现偏差。例如关于《史记》取材问题的论述,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2]卷六二这其实是说《史记》的资料来源,有班固所见到的《世本》《战国策》二书中的内容,从“史料”角度来看并无大碍,但从史学史角度考察,班固的说法不确切,因为司马迁在世时根本不存在《世本》《战国策》这两种史籍,《世本》和《战国策》都是汉成帝时刘向(约公元前79—前7)整理图书时将零散资料汇总编辑,拟定书名而成,此时司马迁早已逝世几十年之久。司马迁在世时并未见到过《世本》《战国策》,但确实利用了后来被编入此二书中的文献资料。刘向编辑多种资料命名为《世本》一书,至宋代亦已佚失,故其书内容、体例难以尽知。经清代学者辑佚,采用了不同编排方式,是为今日所见之本。著名先秦史家陈梦家《〈世本〉考略》[3]根据书中“今王迁”一语,判断《世本》撰于战国赵王迁时期,不少人接受这种观点,遂使谬说流行。实际上书中的内容不能作为判断成书时间的依据,《全唐文》中的内容都属于唐代,但该书却是清朝官方所修,其理甚明。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4],在唐代史学部分讲述清末发现敦煌文献的事件,将清朝官方纂修的《明史》放在明代史学中论述,民国时期撰成的《清史稿》也置于清代史学中评论,都是缺失史学史的学术意识,误把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当成了断代史研究的史料。
其二,接受上方任务观念及其强制求成的学风,是造成判断谬误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导致整体方向性的重大失误。最典型的事例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克商年代问题的设定,其立论过程动用了复杂而专业性的天文运算,但全部推算却是建立在伪文献史料与铭文之错误解说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今本《国语·周语下》有一段文字:“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5]138早有学者指出这是西汉末投靠王莽的刘歆所伪造羼入*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指出:“《国语》所见有关春秋时代之岁星纪年,均出刘歆伪托,据是,所谓‘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者,踵其踪迹,亦是刘歆羼入之文。”。西周时不可能有“岁星”的概念,更没有“鹑火”等星次的名称,这一点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连承担武王伐纣之天文运算的学者们也心知肚明。但青铜器《利簋》有32字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关于《利簋》的释读,有多种分歧的见解,参见《文物》1978年第6期《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这里的关键是解读“岁鼎”二字,郭沫若、王宇信等不少专家将之解释为战前的祭祀兼占测*参见《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载黄盛璋、王宇信之说。,“利”是占测者之人,因此被赐以金,遂用这些金制作了利簋。也有人将之解说为“岁星当空”,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赐有事利金”,而且木星称之“岁星”,最早也是战国时期的观念,因此明显讹误。但断代工程的决策者,偏偏采取伪造的文献和对《利簋》的错误解释,让二者互为指证,这好比一个案件的审判官指使造伪者与说谎人互相串供作证,于是就依此断案。推其动机,乃是为了完成工程任务而“特事特办”,强制求成,舍此便走投无路。将学术问题视为行政任务来执行,是完全不可取的,强制求成,所“成”者大多荒谬。
其三,逻辑混乱而导致论据与论断之间全不搭界,这尤其体现在一些信古、佞古学者之论断中。例如关于《尚书·禹贡》的撰成年代,古代传统说法认为其为大禹治水之后。近现代史学界的信古派,虽然不好意思坚持古代旧说,但将其成文时间尽量提前的主观意愿极其强烈。顾颉刚先生不仅从《禹贡》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整体水平上论证其成文于战国时期,将天下划为“九州”,即为战国时期才可能具备的文化意识,而且还举出地理、水道、物产等方面五大具体证据,指出《禹贡》成文不可能早于战国,如其中“华阳黑水惟梁州”的内容,应当表明是在战国之时秦国打开对四川地区交通之后的信息。这个结论,早被许多学术大家认同。
但是,受过考古学科教育的邵望平女士,1987年发表《〈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6],认为《禹贡》中的九州,既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乃是“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随之不厌其烦地引述考古发现的上古三千年以来各地的山川、田野、物产以及人类的遗迹,比附于《禹贡》对九州的描述,于是认定“九州”反映了公元前1千多年的中国实况,反对将《禹贡》的撰著时间定为战国时期,实际上是主张《禹贡》撰于殷商或西周之初。其实,对于《禹贡》和其中“九州”的描述,论辩的问题是何时人们才可能具有这种地理划分的观念,而邵先生下笔两万言,离题百光年,顶多是说明了“九州”言及的那些地区和物产早就在地球上存在,很久以前就有过人迹,至于人们什么时候把几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看成九个州,其文是一丁点儿也不沾边的。所谓“九州”不是行政区划而是“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的说法,乃是企图逃避辩驳,但终归是逃不脱的。地球上自然有“自然形成”的地理区系,例如“七大洲”“四大洋”,几万年前人类就散布在除南极洲之外的各大陆地,也面对着各大海洋。但将这种自然的地理状况总括成为清晰的认识,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多年才达到的水平。中国的状况一样,战国之前,根本不会对几十万平方公里大地做出“地理区系”的准确划分,《禹贡》“九州”的描述是一种宏观地理架构内的具体考察,越与实际地理状况靠谱,就越成文较晚,相反,凭借想象发挥的观念,倒可以早些形成,例如《山海经》内最荒唐的地理故事即是。然而,自邵氏之文面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鼓噪,许多大牌学人不仅吹捧邵文,而且肆意发挥,连顾颉刚的学生辈也被卷入,这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项耻辱,而且至今仍未洗刷。检索相关的学术论断,只有陈立柱先生的《考古资料如何证说古文献的成书时代?》《〈禹贡〉著作时代评议》两篇论文[7],对邵文以及相关的文章做出系统、深入的批驳,堪称杰作。但陷入信古迷狂的一些人对此视而不见,继续重复和扩大邵文的逻辑错误与史料穿凿,谬论百出,不胜枚举,需要在史学史研究的总结中予以严厉批判。著名先秦史学家王玉哲既不疑古也不反对疑古,绝无半点结派偏私之习,治史唯求真、求是,他对“九州”之说探本溯源地考证,指出春秋时期之前“九州”“九有”“九域”“九土”“厹由”,等等,都是一地,乃是“今山西境内之一小地名”,这里“九”字纯为声符,而不是数目。[8]那些信古大家们,在考索“九州”这一概念的形成源流上毫无作为,只是东摘几句文献、西列几处考古,横竖穿凿,就得出毫无逻辑的结论,把王国维之本来就不科学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堕落为“二重游荡法”,是否应该觉得有些自惭呢?
其四,因某种利益驱动或随声附和而失却了学术理性,主要表现于学界兴起吹吹拍拍的不良学风,这种现象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但犹当注意的是些集体性甚至有组织的横加夸饰,影响广泛而恶劣,典型实例之一就是近十几年对雷海宗的肆意吹捧。雷海宗先生信奉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史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这是一种以主观臆想构建的历史循环论。雷先生因为受荒唐历史观的指导,所有历史见解皆处于根本性错误的状态,不仅如此,他对于历史事实也多所曲解或随意摘取,因而在学术上乏善可陈。如备受热捧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讲述汉代至南北朝的官制、改朝换代、人口与治乱等,杂糅最表层的中国历史知识、斯宾格勒的历史理念、道听途说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等,避而不言汉代权势极大的军事长官大司马、大将军,浑然不知《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上百部兵书,连曹操注释《孙子兵法》也不提一字,于是断言中国属于“无兵的文化”。而谈到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家族制度等,大加赞扬秦始皇的暴政,咒骂推翻秦朝者是“反动的势力”,1935年前后就预定全世界各国政治都应当走向独裁。笔者曾著文对雷海宗的所有庞杂古代予以全面评判,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但可注意的是,出于利益驱动和随声附和的夸饰风气,常常积重难返,以至于学术理性渐至流失。把见识平庸并且充满谬误的学人捧为大师,会使整个学术史严重扭曲,使人觉得“学术明星”乃可以随意打造,其恶劣影响既深且远,不可忽视。
史学史的研究内容之一是史学评论,或称之为史学批评,史学史研究以往的史家、史书、史学状况,离不开史学评论的手段。而当代人的史学活动和历史著述,在其完成之时就开始进入史学史的视野,因此当代史学评论实际仍是史学史研讨的延续。进行史学评论者并非都是史学史学科的从业人士,史学评论的文本也并非都具有史学史研究的性质,但史学史角度的史学评论,是将评论对象置于史学发展的整体线索中进行定性和定位分析,评论的眼光是长时段的、广视野的,这明显地具有学术优长之处。当前历史学的各种评价机制,大多是短期的、狭窄的,一部史书被部分人赞扬,或获得很高评奖,但一旦放到史学发展史内评议,其论点是否禁得起检验?究竟有没有学术上的创新?是否值得今后的史学史著述写上一笔?在史学史上是值得肯定还是无足称道抑或应当指责批判?这才是最终的审判。
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史学评论方面有很重的学术责任,应为历史学的发展把住最后的学术关卡,这就要求研治史学史的学者也需要关注、了解和审视一般历史研究中的大问题、关键问题、一时还说不清的问题、争论激烈的问题、论述模糊且证据薄弱的问题、名家定调而人云亦云的问题、非学术因素扰动的问题,等等,特别是当这类问题涉及史学史学科的内容时,更不能现成地接受其他专业提供的结论,一定要重新审视。史学史是在历史研究中后续的、等待历史学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启动的研讨活动,可以在矛盾充分展开、事实显露清晰之时进行,具有后发的优势。史学史研究具有对史学总体状况及其社会背景进行综合考察的特点,因而较容易做到个案研究的全面性。史学史学科具备理论思维的品格,与史学理论的研究密切联系。所有这些优点,可以促进史学评论深入、确切,为历史学强化学术性和端正学风作出长远的贡献。此即史学史学科的学术穿透力之一。
二、史学史学术穿透力的一些体验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历史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我反思,而史学史则是对历史学的总结性反思,即人类自我反思的进一步展开,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史学史研究以“反思之反思”的特点通过对历史学整体的把握,穿透历史学而关注一般历史问题的探讨,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为了评判已有的历史研究,更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史学史研究不能局促于本专业知识的范围之内,即使为了史学史本身课题的研究,也必须了解、领会、探索一般的通史、断代史问题。至于审视和评论其他历史著述,就应当真正了解该书内容所涉及的知识与技能。更有进者,史学史既然是比历史学高一层次的反思,那么其思维方法穿透到一般历史问题,就完全可以提出和发现其他史学专业未能达到的思路、得出其未能得出的正确论断。如白寿彝先生在《司马迁与班固》[9]一文中,论述从西汉到东汉的史学演变,对于刘向、刘歆父子做了研究,指出这父子之间在政治观点、五行相生相克理念、学术思想上都有很大不同,与前人并论“向、歆父子”的见解大为不同而理据充分,已经从史学史穿透到其他史学领域。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以穿透到一般历史问题的探讨,笔者也略有体验,谨此举出三例。
1.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学、大学的历史课程均有讲述,多种中国古代史、通史著述中也列为专题,但发生民族大融合的原因是什么?却都含糊其辞。
民族融合主要依靠文化认同而形成凝聚力,在中国古代,整体性的文化认同是从史学开始的。政治的清明、经济的昌盛对民族融合有可能起到推动作用,但如果缺乏文化认同,一旦政治变动或经济衰败,很容易导致民族分离,世界从古至今的无数史实足以为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传统史学的认同,就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凝聚力。传统史学所先导的古代民族凝聚与民族融合,上层统治者的作用不容低估。在华夏、汉族方面,统治政权崇尚“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推行“用夏变夷”的文化传布;在少数民族方面,虽然也存在抗拒“汉化”的势力,但历史的主流是各族政权向慕中华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模仿传统的官方修史体制。这种现象始于西晋末年的十六国时期,例如后赵石勒(羯族)称王之后,即命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10]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氐族前秦苻坚政权设“著作郎”等史官之职,赵渊、车敬、梁熙、韦谭记录起居注等史书[10]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南燕政权,皆设置史官并且实际进行了记史、修史活动,《史通·古今正史》称:“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南燕有王景晖在慕容德、慕容超时任官,“撰二主起居注”,后来仍撰写《南燕录》六卷。[11]卷十二《古今正史》鲜卑族南凉秃发部君主乌孤“初定霸基(按约387年),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11]卷十一《史官建置》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11]卷十一《史官建置》,后来虽有波折,但北魏最后确立了比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更为健全的修史制度,从而导致全面的文化认同。这种状况,在秦汉时期的匈奴政权以及更早的其他民族政权不曾有过,而在十六国、北朝及其之后,则相当普遍,这是因为东汉确立的官方不仅记载史事,而且纂修成品著述性的史书,使统治者的业绩正面地记述。修史书可使统治者的功业垂于后世,可使许多人物青史留名,也可使撰史者立言传世,不仅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极大的文化魅力。由仿从修史而接受华夏的历史观念,更将自己说成与汉人有共同的祖先,因而“认祖归宗”,如匈奴族的赫连勃勃,自称是“大禹之后”,鲜卑族政权自称为黄帝之苗裔等,即形成民族融合之强大而稳定的因素[12]。不立足于对史学史的深入研讨,是不能发现与解决这项历史课题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清朝将传统文化遗产加以大规模总结与提炼,是显著的范例。在世界历史上,很难见到中国古代这样经常的由异族上层迅速、全盘、系统、主动地接受另一民族文化的现象,原因在于唯中国具备这种包含官方修史的独特繁荣的传统史学。以往人们总是把中国民族融合的积极因素归结于下层民众,往往将上层统治者说成民族融合的阻碍力量、消极因素,是缺乏史实依据的。世界许多地区、民族(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尽管经过长期杂居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仍然离民族融合的距离甚远。因此,各族下层民众如果缺乏整体文化的趋同,仅在杂居与生活中的融合,总是缓慢与不稳定的。
十六国、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北方多种民族相继勃兴,纷纷建立政权,甚至间或形成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强盛国家。这时期民族关系、民族文化如何发展,应当说很有变数。但是恰恰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记史、修史的官方史学活动,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甚至出现北魏孝文帝时期全面、主动的“汉化”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史学引导了历史、改变了历史。
2.关于康熙帝与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系,清朝官方书史描绘得温情脉脉,这被清史研究者的许多史学著作认同,歌颂孝庄后的论述颇多,文学艺术作品就更加绘声绘色。然而史实真的如此吗?孝庄后是在顺治朝与康熙初期很有政治裁决大权的人,因此不能不联系顺治末与康熙初的朝廷大政来考察。顺治帝后期与其母孝庄后极其不和,甚至长年不去探望问安,说明矛盾已经公开化。顺治帝逝世,辅政大臣拟定的所谓“遗诏”,有如一件认罪书,特别是检讨了“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13]卷二:顺治十八年三月甲子的过错。接着,清廷大肆改变顺治朝“汉化”了的政权机构与制度,宣布“率循祖制,咸复旧章”[13]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同时兴起“哭庙案”“江南奏销案”“庄氏史狱”等,皆为对南方汉人士绅的打击。这一系列做法,均靠孝庄后坐阵才可施行,连守旧满洲贵族四位辅政大臣的任用,也必然是由孝庄后所决定。
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亲政,继承其父政治制度“汉化”的方针,第一个大的举动是下诏纂修《清世祖实录》,在谕旨中指示:“卿等督率各官,敬慎纂修,速竣大典,表彰谟烈,以副朕继述显扬先德之意。”[13]卷二四:康熙六年九月丙午为此还特别撰写了“孝陵神功圣德碑”文,将顺治帝“遗诏”几乎逐条否定,标志着向守旧势力发起反击。但是,纂修实录工作也受到守旧大臣鳌拜之党羽、实录馆总裁官班布尔善的抵制,僵持不下。此间,康熙帝每隔几日就到孝庄后住处问安,一则表示亲热,二则防备守旧势力离间,三则窥探孝庄后的行为打算,似乎关系融洽,其实乃是政治博弈的手段。与此同时,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出手搏击。康熙八年(1669)五月,康熙帝以召鳌拜入宫议事为由,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擒拿鳌拜,随之捉拿其党羽班布尔善等人。这次断然举措,事先是瞒着孝庄后的,据白新良教授考证,擒拿鳌拜实在康熙八年五月十日。[14]至十二日拟定《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局面已经有效控制。同日,康熙帝再次向孝庄后“问安”,实际是一次摊牌,孝庄后即使不快,却也无计可施,而康熙帝举出鳌拜欺君、专权的罪状,对孝庄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最后,首犯鳌拜免死监禁,而党羽班布尔善等人却被处以死刑,这个不正常的结案,应是孝庄后与康熙帝达成的妥协。随后,康熙朝逐步采取政治体制和文化建设“汉化”的措施。为推行这种政治方针,瞒着孝庄后擒拿鳌拜,是一项政治豪赌,但康熙帝赌赢的把握是充分具备的,因为孝庄后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嫡系儿孙坐稳帝位,此乃最大的政治利益,况且康熙帝又多年表现得十分恭顺。这里,对孝庄后的评论,对康熙帝与孝庄后关系的判断,对顺治末到康熙初清廷政治的论述,都需要做出重大的改变,而所有这些,是对康熙朝纂修《清世祖实录》进程细致研究发现的,可见史学史研究可以穿越到历史探讨,而且可以取得独到的创见。
3.王国维1925年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史学方法命题,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5]2-3
这得到非常普遍、非常赞誉的评价,至今视为研究先秦史的重要手段。从断代史家撰文立论的角度出发,运用“二重证据法”真是十分便利,但将之置于史学史中考察,则在肯定其推动了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利用于历史研究之外,弊端立见,而颇多负面效应。
首先,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乃针对顾颉刚等的疑古思想,试图阻止“古史辨”这一史学革命思潮。“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断言,反映出强烈的信古观念。后来推崇“二重证据法”的学者,基本都是要以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来“印证”古书记叙,将上古传说和神话坐实为可信历史,造成先秦史研究整体主流方向的迷失。其实,考古发现的文献和遗迹,有些当然可以印证古文献的记述,但大多数考古发现是会否定古文献、古传说的内容,例如偃师二里头发现的所谓“夏文化”遗址,既无文字,又无明显超越其他地区的社会先进性特征,实际宣示了夏朝历史传言的崩溃,即历史上也许有过“夏”这个酋邦或方国,但并无所谓“夏代”,那么一丁点儿地方,又不能证明周边部族是受其统领,有什么资格可以代表中国上古的一个朝代?又如山西陶寺遗址的发现,据说时间、地点都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但遗址反映出人类残酷的大屠杀、大毁灭现象,既毫无权位禅让的祥和气息,也不是宫廷政变的样态,而是种族灭绝之类的战争。于是,关于尧、舜的历史传说彻底破产,因为再没有其存在的时间和空间。
其次,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依靠他利用甲骨文对殷商世系的考订,成果体现于其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但这种考证算不上“二重证据”,因为都是文字资料,甲骨文与藏于档案馆的秘档,文献性质并无实质区别。考订清朝历史,若利用清内阁档案算不算“二重证据法”?如果再加以满文资料,算不算“三重证据法”?再加上蒙古文资料是“四重证据”吗?加上英文资料、日文资料、法文资料、俄文资料……呢?其实都是一种,即文字史料而已。后来考古资料的利用,这倒是有别于文献的另类证据,但不同体系的资料强行比附,甚至以古文献所记述为主体的“印证”性穿凿,造成极大的混乱,每一考古发现,皆与文献连接为“二重”,论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可见其中并无科学性。更糟糕的是:某些考古学者也致力于将考古材料穿凿于神话传说,把考古的发现装入陈旧的上古史体系的框架,使本应居于科学高度的考古学,变成信古思潮的下等婢女,甚至连基本的逻辑思维也弄得混乱不堪,如上述关于《禹贡》“九州”的鼓噪,败坏学术,莫此为甚。
第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守旧的信古观念为出发点,因而存在很严重的逻辑谬误,例如他谈到《史记》的记载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15]52-53姑且不论《史记》所述“殷周世系”是否真的“确实”,仅就其根据殷周世系“确实”就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就是十分明显的荒谬逻辑。《史记》一书,有大量确实的记载,也有许多失实的记述,纷纭斑驳,甚至同一史事叙述得自相矛盾,此为自古以来的学界所共知,岂能因为一项记载可信就推想其他记载也同样确实?王国维此说,在逻辑上几乎可以视为弱智,但至今史学界仍有人每每引证此说或模仿此说发论,真是匪夷所思,莫非信古观念真能令人变傻并且具有传染性?
以上事例足以显见“二重证据法”的纰缪与造成的流弊,但因其可以给先秦史家提供随意撰文的方便,故将之当作铁饭碗一样地护惜。而以此种方法撰写的文章多如飘风落叶,却极难寻见出学术的科学性和确定性,史学史学科理应对之予以审视、剖析和评判。
三、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新思考
史学史学科以历史学的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而中国历史学积累的问题之多,给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以很大的挑战,需要做出突破常规的新思考。简要言之,有以下三端尤其值得倡导和推动。
第一,史学史学科一般被认为是历史学之中的一个分支专史,从上述史学史的学术任务来看,这种定义是远远不够的。史学史虽然是从历史学中纵割分出,但一旦独立并且形成体系,就要与史学理论紧密结合而凌驾于整个历史学之上,起到审视、总结、评判与纠偏的作用。当前,历史学界的学科结构轻重失衡,中国历史仍然偏重于断代史,此乃几千年以来陈旧历史学模式的延续,总体上造成学术眼光短浅,理论思维贫困。历史学必须通过反思,清理自身的演进历程,才能更为成熟,梁启超说:“凡一种学问经过历史的硏究,自然一不会笼统,二不会偏执”[16]然而十分遗憾:史学界恰恰正是对历史学最缺乏“历史的研究”。白寿彝先生曾经说:“史学史的研究状况,很不正常。学哲学的人都知道,必须要学哲学史。学文学的人也知道文学史很重要。但学历史的人,偏偏不重视史学史的研究。……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史学工作水平之不足,也为史学的发展带来损失。”[17]57近年情况稍许改善,但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学术队伍还是格外薄弱,依然属于“很不正常”,需要大力扩充,否则难以很好地总结和审视历史学的发展状况。
第二,改变历史学的学科结构,是需要从高校教学抓起的工作。先进高校历史学的课程以中外“通史”课程占去绝大多数课时,而所谓“中国通史”,实际不过几段断代史的拼凑,并无通史意旨。这样,断代史不断复制,形成持续循环。白寿彝先生早就指出:
我们历史系的课程,几十年来主要是开设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课程,每一门课程都包含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都教4年。我们把这两门课程叫做“八大块”,这“八大块”的设置,是从苏联学来的,我们授课时数比苏联已经消减不少。但分量还是很大,为开设别的课程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两门课程,主要是靠课堂上讲,课堂下看讲义,很少有阅读参考书的机会。而且,一门课搞了4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是“通史”不“通”……[17]55
因此,白先生主张通史就讲一年,提纲挈领,腾出课时安排其他各种专史、读书与研讨,特别要抓史学史与史学概论。这是多年教学与研究得出的体会,上升为教学改革的设想,应该下最大的决心予以施行。
第三,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不仅要求学术队伍的扩大,更需要专业人员学术素质的提高。提高本专业学术素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知识结构的扩展和研究技能的掌握,二是理论思维能力的增强。历史学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史学史专业学者的整体知识结构必须优于断代史专家,在一些特殊知识技能方面也需要有所作为。例如先秦史专业往往辨识和利用甲骨文、金文资料,史学史专业之中也应具有相应的内行人员,才能做出审视和评判。理论思维对于史学史研究尤为关键,在方法论上的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为发现问题、破解问题的利器。一项研讨历史的议论,如果逻辑上已经悖谬,再多的资料罗列也无济于事,许多错误观点常常是在理论和逻辑上失足的,这样的失足比史料的缺陷更为严重,往往一被揭示,就再难以站立。史学史专业的学者,掌握渊博的知识与多方面的研究技能,练就敏锐的理论思维,就会在学术研究中发挥强劲的学术穿透力,从而为历史学的健康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乔治忠.中国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8.
[2]班固.汉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陈梦家.西周年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刘节.中国史学史稿[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5]国语: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J].九州学刊(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编辑出版),1987,2(1):9.
[7]陈立柱.考古资料如何证说古文献的成书时代?[J].文史哲,2009(3);禹贡著作时代评议[J].古代文明,2010(1).
[8]王玉哲.中华民族早期源流[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245,248.
[9]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4).
[10]房玄龄,等.晋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刘知幾.史通[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乔治忠.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J].学术研究,2010(12).
[13]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白新良.康熙擒鳌拜时间考[J].满族研究,2005(3).
[15]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1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中国文库》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66.
[17]白寿彝.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M].白寿彝文集·历史教育·序跋·评论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仇海燕
责任编辑电子信箱
张超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专栏、周恩来研究专栏、网络与人文研究专栏
E-mail: zhchao053@163.com
王荣江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专栏
E-mail:wrj6363@163.com
刘海宁文学、艺术、语言文字
E-mail:hysylhn@163.com
杨春龙世界史、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翔宇论坛
E-mail:chunlongh@sina.com
仇海燕现当代学人研究专栏、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栏、中国史、社会、旅游
E-mail:hysyqhy@163.com
孙义清文化产业研究专栏、新闻与传播、教育与教学
E-mail:yiqing202@163.com
Academic Penetr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QIAO Zhi-zho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The discipline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has its internal function to comment the past state of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studies. Facing to the complicated and volatile research objects, we need to break our thinking patterns through our own major boundaries, that is to have a strong academic penetration, in order to finish the task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accumulate quite a few of errors and deviations, which is needed to be corrected by the summ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discipli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rough discovering and proposing some train of thoughts which are not to be found by the other major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studies, the academic penet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n draw a creative conclusion in exploring the general history problems. Because of thes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academic penetratio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comment on the history studies; logic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1-0003-08
收稿日期:2015-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