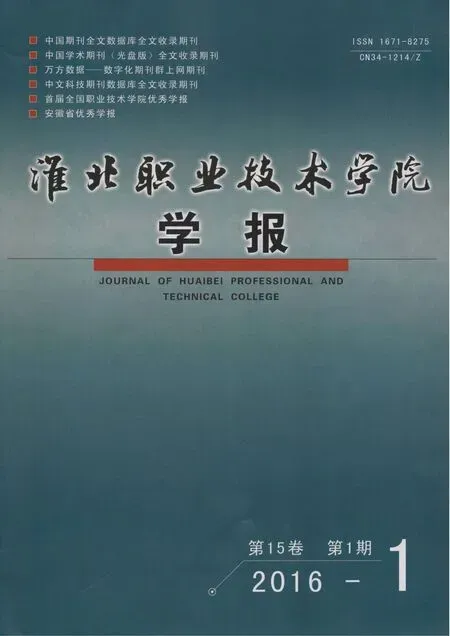狱门边绽放的野玫瑰
——《红字》中珠儿的镜像解读
2016-03-15段红
段 红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狱门边绽放的野玫瑰
——《红字》中珠儿的镜像解读
段红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摘要: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是一部经典之作, 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品主要人物之一珠儿的心理发展恰好完整印证了拉康的镜像理论。在成长过程中,其身心历经了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阶段,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个体。
关键词:《红字》;镜像理论;主体认同
纳撒尼尔·霍桑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以深遂的思想和独特的创作手法享誉世界文坛。其代表作《红字》“是一部包含着心酸眼泪的文学作品,它倾注了作者的一腔真情,令人读罢眼热、心酸,总有一丝丝忧伤在脑际萦回”。[1]23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红字》具有世界级水平,是出自美国人之手的第一部本土小说。[2]76近年来对《红字》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诸如从道德观、主题思想、艺术手法、心理分析等方面,而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视角来研究该部作品的,则多聚焦于作品的主要人物丁梅斯代儿、海丝特和齐灵沃斯,极少提及珠儿。事实上,珠儿的心路历程恰好完整印证了拉康的镜像(the mirror stage)理论,其心理历经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阶段,完成了镜像阶段的全部过程,最后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个体。
一、拉康的镜像理论
拉康的镜像理论是基于对人的心理发展过程的认识,也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生成的理论。拉康认为:婴儿6到18个月时,便进入镜像阶段,也是其心理发育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婴儿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了完整的自我映像。这一镜中影像给了他对自我的全面印象,使他得以将昔日零碎的片段组织成一个整体,由感性映像联合体上升为经验、自成的身体。经过镜像阶段, 儿童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他已能将外界的客体与自我的身份相区别, 这源于他已认出镜子中的自我映像,这是通向自我意识的最具决定性的一步。虽然如此,并不意味着他已经产生了自我意识。经过镜像阶段后,他由最初的欲望客体渐变为无意识中的欲望轴心,最后上升为文化意义上的角色。这样,儿童逐渐成长为有外部形象的人的形式。总结镜像阶段,拉康认为“其功能是幻想功能的一个特例,旨在建立有机体与现实间的联系”,[3]193拉康的镜像阶段分为符号级、想象级和现实级三个等级。
二、珠儿的镜像分析
珠儿是《红字》中主体自我意识体现的典型人物,珠儿心理成长过程始于小说开端。珠儿第一次出场是在刑台上,被母亲海丝特抱着,倾听台下丁梅斯代尔的劝诫。襁褓中的珠儿,一反被动的常态,对丁梅斯代尔的声音做出了回应。珠儿回应的不仅仅是词语,更是声音本身所代表父亲的文化权威。“这位年轻牧师,声音甜美、圆润,饱含深情,感人至深,足以引起共鸣,博得人们的同情。就连襁褓中不谙世事的婴儿也被感染了、感动了, 她用清纯的眼神凝望着这位年轻的牧师,抬起小手,发出亦悲亦喜的嗫嚅声”。[4]206珠儿的反应充分显示了婴儿与自我和牧师关系的终极目标。
在拉康看来,儿童早期本应与父亲确立良好的关系,可是新生儿天然地会聚焦在母亲身上。特殊身份的珠儿自出生就与生父、甚至整个社会相互隔离,造就了母亲成为她最亲密、最为关注的人,尤其是母亲的音容笑貌,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据移置理论,母亲的形象常通过借代过程为其它形象所替代。母婴之间,密不可分, 母亲的乳房往往成为象征母婴亲密关系的标志。具体到珠儿,母亲身份的认证则由母亲的乳房迁移至海丝特胸部的红字。珠儿对这个象征物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她来到世间第一眼所见并非母亲的微笑,而是一件独特的东西,就是刻在母亲赫斯特胸前的那个红字!”[4]红字成为珠儿降生以来所见的第一个物象,一件象征母亲的物像。
也许,红字A起初的确象征母亲。然而,历经镜像阶段,珠儿渐渐地对母亲产生了不解,进而对代表母亲形象的红字也产生了疑惑,内心充满矛盾。在之后的行动中,珠儿清晰地表达出这种矛盾心情。作品在揭示想像级她在认证对她而言第一个有意义的形象为红字的同时,也对红字表现出攻击:“在一个夏日的上午,顽皮的珠儿把采来的野花一朵朵投向母亲的胸前,目标直指那个特殊的红字,每每击中目标,她便会像小精灵般地跳上跳下,欢欣鼓舞。”[4]这种矛盾心情的外露,清晰地传达了心理辨别的镜像阶段过程。这意味着它承认了孩童的他人意识,在自己和母亲之外。珠儿的关注力直接指向现实的父亲而不是想象中的父亲。“孩子举起她稚嫩的食指,好奇地去触摸那个红字。”[4]珠儿的行为暗示她不认可天父是其生父,最起码不是她现实中的父亲。这一举动暗示了她对父爱的渴望,也揭示了她想要的想像中的父亲与她必然的符号级的父亲内在的关联性,都源自同一个红字A背后。
红字A和牧师将手置于胸口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时常触痛海丝特的内心,她总是设法回避这个问题。毋庸置疑,珠儿只有通过字母A的意义才能知晓谁才是她真正的父亲,在找到符号性的父亲之后, 她才不会继续纠缠这个问题。拉康镜像阶段的论述中,公开揭示了俄狄普斯三角关系,剧场安排在树林中。此时,将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与珠儿隔开的小溪就充当了镜子。作品中,小溪被描绘成能够“可以看见水面反光”的物件,潺潺的小溪,于安然宁静中间杂着忧伤,宛如不谙世事的孩提,不知如何在伤感的情景中寻求快乐。在珠儿停下的地方,小溪适时地形成了一个平静的水潭,映现出孩子那娇小的身影,宛如仙境中的小仙女那样楚楚动人。最重要的是在镜像反射过程中出现了异化现象。在小溪的底端 映射出另一个孩子 ,当然也是同一个孩子。母女俩几乎同时关注到这种异化现象。“母亲似有感应孩子在疏远她,如同独自漫游林孩提,错失了方向, 茫然无措,无法回到原点,令她不安起来。”[4]在她看来,当下的珠儿已经不属于她,而是属于另一个人的世界 。
在完成镜像阶段的最后时刻,母亲在珠儿的逼迫下,不得不又一次戴上那个红字A。有意无意间,珠儿让牧师从镜子般分离她和母亲的小溪旁消失了。作品自始传达出珠儿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随心所欲,想得到的,她会无所顾忌地飞奔而去,直截了当,将其据为己有,毫不做作。要突破认同阶段,达到心理和文化上渐趋成熟,她就必须进入符号级,学会从外界接受社会价值。最终,在父亲的法权下珠儿获得了认同,却失去了原本的自由,失去了作为孩子应有的天性,与此同时,她则获得了文化定义中成为成熟的女人的能力。她将在人类社会的喜怒哀乐中成长起来,不再继续与世界争强,而要做一个正常的女性,像狱门边的野玫瑰自由绽放,吐露芬芳。
三、结论
作品中,珠儿的成长历程恰好符合并验证了拉康的镜像理论。她第一次出场是在监狱前的绞刑台上,襁褓中的珠儿对外界的感应完全靠听觉和视觉的刺激 。在镜像阶段前期,她发现了自居与对立的映像,在中后期,珠儿迈出了通过该阶段最关键的一环:经由想象级实现符号级的飞跃,归于父亲的本体和权威性。据此,可以推断《红字》远不止是揭示道德、文化与宗教主题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颇具精神分析学内涵,与意义的卓有见地的经典工作,这也是霍桑魅力经久不衰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谢林江,李芙蓉.傲雪盛开的寒梅:苔丝和海丝特之比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2).
[2]方文开.人性自然精神家园:霍桑及其现代性研究著[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3]尼·柯·波波娃.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M].李亚卿,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4]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方华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长河
收稿日期:2015-12-02
作者简介:段红(1978-),女,河南信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16)01-01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