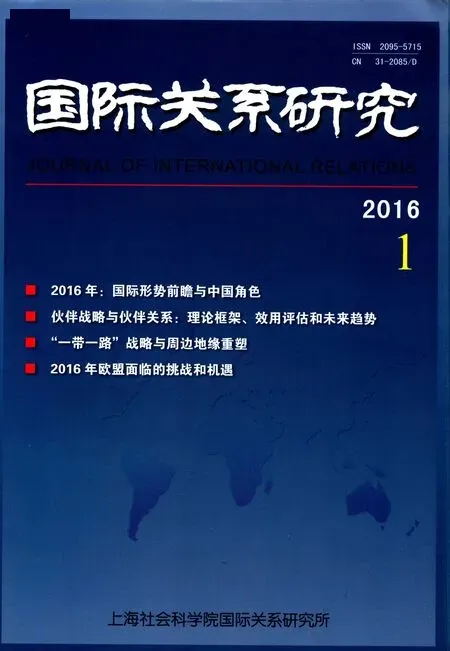“一带一路”场域中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关系辨析*
2016-03-15宫玉涛
宫玉涛
“一带一路”场域中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关系辨析*
宫玉涛
[内容摘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势力披着民族、宗教的外衣发展和活动,恐怖主义的存在被误导性地认为与一些特定民族、宗教有密切关联。虽然特定的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与特定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在特定条件下存在某种关联性,但不能人为地把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更不应把反对恐怖主义斗争单纯地定位为反对某一个民族、宗教。要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严峻的恐怖主义难题,要发挥沿线各国打击披着民族、宗教外衣进行活动的恐怖主义势力的合力,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的关系,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参与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恐怖主义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关系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提出的重大倡议,其沿线覆盖亚洲、欧洲大部分地区及非洲部分地区的广阔地带,美国是“一带一路”特殊而重要的相关方。“一带一路”沿线是民族因素、宗教因素众多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复杂且多变的地带,也是恐怖主义活动频繁、恐怖主义事件多发的地带,特别是在一些霸权国家主导或谋求主导的地区,例如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更为频繁,恐怖主义事件更为多发,“由某个霸权国家支配的国际秩序比多元的国际秩序更容易产生和发展恐怖主义”,*Brynjar Lia,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errorism:Patterns and Predic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16.在区域范围内同样如此,更何况某些地区还有复杂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的多重关系症结。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恐怖主义组织身上及发生的各类恐怖主义事件中,不少明显或隐约能看到民族、宗教的影子,即民族、宗教似乎已经成为一些恐怖主义势力生存、发展和频繁活动借助的外衣。在欧洲,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当伊斯兰背景的恐怖主义势力号召穆斯林移民向非穆斯林的异教徒进攻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忘却自己的国民身份和公民身份,而选择伊斯兰主义,进行向西方国家的异教徒基督徒发起恐怖主义式的进攻和复仇。*宋全成:《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3期,第108页。上述这些状况容易产生误导,使不少民众对当代复杂的恐怖主义形势作出简单而直观性的判断,即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生硬地关联在一起。而这种倾向使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混乱不堪,阻碍着人们正确而科学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制约着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合力打击,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对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科学的认识,是我们厘清恐怖主义现象和问题的根本,是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方有效限制、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特别是披着民族、宗教外衣发展和活动的恐怖主义势力的重要前提。
一、恐怖主义与民族因素、宗教因素的“特定关联性”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各主权国家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中,不少是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组织,也有不少是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性质的组织,它们可能在政治取向和目的性上有所区别,但在手段上普遍热衷于暴力恐怖袭击。从这方面说,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之间存在“特定的关联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特定的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在特定条件下存在某种关联性,特定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是导致特定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最强有力与最致命的根源之一”。*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在很多现实案例中,民族因素与宗教因素是交叉在一起发挥消极作用的,这在“一带一路”沿线表现得非常明显。
1.恐怖主义与民族因素的“特定关联性”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2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积淀,不同的民族普遍拥有各自不同的民族习俗、文化观念、价值信仰。从古至今,这些为数众多的民族在所在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作用,不少民族影响着所在国家的发展轨迹。当今世界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共同为同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分,例如法国的法兰西民族与科西嘉人等少数民族、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人与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俄罗斯的俄罗斯族与车臣族等少数民族、中国的汉族与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对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部分“人士”而言,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他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少数极端的激进人士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暴力恐怖袭击就是其惯用手段。法国的科西嘉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俄罗斯的车臣族、中国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都有一部分激进人士谋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并普遍建立了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分裂组织,如法国的“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西班牙的“埃塔”、俄罗斯的车臣反政府武装、中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为了达到自身的政治目标,这些组织及其追随者在这些国家制造了各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例如我国新疆等地区近年来的大多数暴力恐怖事件就是“东突”分裂组织及其追随者发动的。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分裂势力谋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行为与近代以来延续至今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对一个已经独立、合法的主权国家的分裂行为,而后者则是反对外来殖民者、侵略者、干涉者的自身解放运动。就参与者而言,前者局限于部分民族分裂势力,而后者则带有整体民族性的特点。就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而言,相对于前者,后者有相关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依据。国际社会对待民族解放运动,及现实中一些国家内部分裂势力谋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不同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广大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不仅有内部广大国民的支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给予理解、肯定和支持,甚至长期殖民、侵略、干涉这些国家的西方大国最终为了自身利益主动或不得不被动地允许、支持这些国家的解放和独立,这是这些国家能够实现解放和独立的根本原因。而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内部的分裂势力不仅没有在内部获得广泛支持,也没有获得外部的普遍理解、肯定和支持,这是这些分裂势力追求的政治目标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当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存在一些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围绕这一点的定性问题,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是有不同看法的。*余建华:《关于恐怖主义外延相关理论问题的论析》,《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6~119页。
民族主义从来不是纯粹的,它具有利己和排他的特性,这种特性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就容易形成民族分裂主义。长期以来,不少民族分裂势力为了实现分裂目的而不择手段,包括暴力恐怖的手段,这就是“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近代以来被广为演绎和应用的民族自决理论。但实际上,现实中的民族分裂主义者是在滥用民族自决理论。民族自决理论不是也不应是一个民族中的部分人无原则地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有分离的权利”,但“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9页。民族分裂主义者的行为是将民族自决理论庸俗化,而这将导致“民族自决权是国际生活的无序状态而不是有序状态的主要制造者”。*[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联合国1960年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在现实中,不管是法国的“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西班牙的“埃塔”,还是俄罗斯的车臣反政府武装、中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及东南亚的一些分裂势力,都存在打着“民族自决”的幌子忽悠、误导民众和外部支持者的现象。
“一带一路”沿线的民族分裂主义普遍持有“本民族第一”的思想,他们利用民众对本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心理、生活习俗等的高度认同,打着维护本民族整体利益的旗号,鼓吹政治疆界应与文化疆界和语言疆界吻合、少数民族被所谓的主体民族“统治”是不道德的等观点,煽动本民族民众对所在国的中央政府、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心理仇恨,并建立一定的政治军事组织,以便使他们实现目的获得硬性条件。这在我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疆独组织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从我国反恐部门查获、收缴的这些分裂组织对外宣扬主张的宣传物可以明显看到上述类似的带有强烈鼓动性的思想和观点。“一带一路”沿线不少民族分裂势力还得到一些外部势力的支持。由于国际社会目前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存在较大的模糊性,缺乏统一、权威的界定,也为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争取外部支持、或外部势力出于某种战略目的或意识形态思维而主动支持某些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借口。一些被某些国家甚至国际组织认定的民族分裂型的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不仅可能不被另一些国家“认同”,甚至可能得到外部国家或外部力量的政治保护和支持。我国的“东突”分裂势力就得到了某些外部力量的支持,例如,买买提明·艾孜来提等被中国公安部明确认定的恐怖主义分子甚至堂而皇之地在一些国家从事反华活动,甚至得到这些国家一些人士的公然资助。俄罗斯车臣的一些恐怖分子也公开在一些西方国家从事反俄活动而不被禁止,甚至得到一些西方人士的公然资助。
民族分裂势力从事的分裂行为,谋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是所有国家政府和主体民族难以接受并坚决反对的。为实现自身非正义性的目的,一些民族分裂势力选择暴力恐怖手段。恐怖主义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以一种无定形的方式进行战争,实施非对称的攻击,以损害并试图打败一个显然占优势的敌人。它尤其吸引着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民兵、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其他的在兵力和火力尚无法与‘压迫者’相对抗的少数派势力”。*[美]伊恩·莱塞等著,程克雄译:《反新恐怖主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民族分裂势力希望借此制造社会恐慌,引起国际关注,甚至直接寻求国际某些势力的支持或干预,对所在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作出让步,从而达到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现实中“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分裂组织的暴力恐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制造社会恐慌、引起国际关注的目的,引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干预,但其最终的政治目标却没有实现,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恐怖主义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无原则的畸形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对各国正常秩序和发展的反动,自然遭到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和坚决抵制,即使出于各种目的或私利对其表示理解和支持的外部势力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支持这样的政治目标。
2.恐怖主义与宗教因素的“特定关联性”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曾总结说,宗教在历史上既表现为维系世界的力量,又表现为动摇世界的力量,*转引自何锦熙、王建敏:《西方社会学说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这是对宗教的历史作用的精辟解析。并且,“由于宗教能够使人类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从而可能变成一种最强有力、最顽固的社会控制方式”,*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这也就意味着宗教因素具备了为极端组织及其暴力恐怖活动提供精神动力的条件。有西方学者认为,“暴力是宗教的本质因素,没有无宗教的暴力,也没有无暴力的宗教”,*Hent de Vries,Religion and Violence: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from Kant to Derrida,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这话有点绝对,但在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地区却有其合理性,“没有无暴力的宗教”同样有其合理性,每个宗教都有可能成为暴力的精神依托和动力。在现实中,在冲突和存在困难的地区,宗教更容易吸收民众。*Steven Hause,William Maltby,Western Civilization,Belmont,CA:West/Wadsworth,1999, p.157.宗教的这一特点也容易为从事恐怖主义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所利用,这也是存在冲突和发展困难的地区宗教极端组织活动频繁、恐怖主义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区域就属于类似地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宗教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存在,同时也存在具有较大区域性影响的宗教,可以说,这一地区是各种宗教并存、博弈、斗争的主要地区。这一地区也是各类宗教极端势力众多的地区,例如活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伊斯兰祈祷团”、活跃在菲律宾南部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等。
纵观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和宗教发展史,可以看出宗教矛盾和冲突是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之一,也是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西方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征(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战争)、基督教与新教、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曾引发较严重的战争和灾难。各类宗教的极端势力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或争取最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恐怖的暴力手段成为很多宗教极端势力的选择,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在内的重要宗教在世界各地都有以不同面目存在的极端组织或支持者。这些宗教极端势力用一种偏执、无限扩大化、极端片面、绝对化的观点来诠释自己的信仰体系,在现实中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二是宗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或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在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下,甚至出现了与国际主流社会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运行机制、道德原则,*Bruce Hoffman,Inside Terrorism,London:St.Andrew’s University Press,1998, p.87.在“一带一路”的部分区域已经出现了世俗化外的“宗教世界”,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充满暴力恐怖色彩,如“伊斯兰国”治下的区域就到处充斥着暴力恐怖的画面。极端化了的宗教因素所导致或激化的暴力冲突,不仅可以发生在不同宗教之间,在宗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也经常发生。例如,我国新疆地区就多次爆发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10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了40余年的宗教战争。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内部分裂为黑山派和白山派,两派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激烈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史见证》,《人民日报》2015年9月25日,第9版。历史上和现实中,伊斯兰教内部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也时常发生严重的教派冲突,这种冲突甚至成为引发国家之间对抗、战争的重要诱因,这在中东地区表现得淋漓尽致。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沙特等国家介入叙利亚内战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沙特等国家对也门内战的介入等都有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的争斗因素在发挥作用。
目前,激进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是遍及各主要宗教派别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宗教原教旨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恢复宗教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统治地位,建立神权高于一切的神权体系,“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原教旨主义一词最早源于基督教,用来称呼20世纪初的基督教清教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强调严格按照字面解释《圣经》,并以此作为教徒生活和教条的原则。按照这种宽泛的解释,可以说,原教旨主义几乎在世界上每种宗教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等,它们是“对各种宗教中要求返回原始教义的派别和主张的称谓”。*张步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演化及影响》,载许涛、何希泉主编:《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原教旨主义虽然发源于基督教,但在当今世界却是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影响最大。
需要指出的是,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并不能划等号,并不是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都是宗教极端主义者,更不能说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都是恐怖分子,也并不是所有原教旨主义组织都是恐怖组织,“致使这些组织变得危险的,不是他们的伊斯兰性质,而是它们的暴力手段和没有包容性的目标”。*Shibley Telhami,The Stakes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Boudler:Westview Press, 2002, p.26.在中东国家中有不少人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但现实中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仅不搞暴力恐怖活动,而且是坚定的暴力恐怖活动的反对者。实际上,原教旨主义中存在温和原教旨主义和激进原教旨主义的区别。温和原教旨主义主张开展合法、和平的运动,反对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实现目的,这是他们与激进原教旨主义的主要区别。例如,在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看来,真正对美国和西方安全构成威胁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伊斯兰教组织,而是假借伊斯兰教名义的宗教极端组织、恐怖主义组织。因此,他认为绝不能用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恐怖主义组织所宣扬的观点来看待伊斯兰教。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是为了把“和平天使”和“凶残恶魔”区别开来,即把正常、有益、合法的伊斯兰教社团与那些以伊斯兰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的宗教极端组织区别开来。*[美]J.L.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激进原教旨主义者通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不少势力热衷于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解决问题。客观地说,激进原教旨主义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体现,也是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渊源和土壤。
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具有交叉性,例如,活跃在菲律宾南部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在我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地区非常活跃的“东突”势力既是民族分裂组织,也是激进原教旨主义组织。民族和宗教成为这些极端组织经常使用的两大“武器”,这两大因素合流无疑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二、恐怖主义因素的民族性、宗教性分析
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一带一路”沿线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势力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或披着民族、宗教的外衣开展活动,体现出了特定的民族、宗教色彩,企图借助民族因素或宗教因素发展和活动,或者谋求为自身的暴力恐怖行为“正名”或获得“道义性”、“合法性”。我国的“东突”势力就是擅长借助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开展活动的典型,根据我国反恐部门的相关公告可以看出,“东突”势力在新疆大打民族牌、宗教牌,诱骗一些人同情它们,甚至加入它们的组织,或偷渡到境外加入所谓的“圣战”队伍。
民族分裂主义、激进原教旨主义是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温床,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一带一路”沿线恐怖主义势力的主要群体,也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重要群体。西班牙的“埃塔”、俄罗斯的车臣反政府武装、我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势力、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伊斯兰祈祷团”、菲律宾南部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等民族分裂组织或宗教极端组织毫无例外都有从事恐怖主义的经历。
因为特定的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与特定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在特定条件下存在某种关联性,这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容易误导一些人对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关系的认知,也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来为自身的战略和利益服务。“9·11”事件后,有些西方政客和学者就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一些将恐怖主义与某一个民族、宗教相关联的言论。例如,2001年9月16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将反恐战争比作“十字军”东征。2006年8月31日,小布什又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的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反恐战争说成为“反伊斯兰的战争”。*李景治、宫玉涛等:《反恐战争与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9·11”事件后一些美国学者公开声称,“只有伊斯兰恐怖主义在威胁美国”。*Jack Miles,“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urvival,Vol.46,No.1,Spring 2004,p.23.这些言论不应当仅仅被视为“口误”,至少反映了西方国家部分政客和学者内心思维中对待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关系的立场和态度,有些言论是为特定战略和利益服务的。这也就可以理解,虽然这些言论在现实中引发了争议,也招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穆斯林盟友的不满,但类似言论仍然不绝于耳的重要原因。因为长期的敌视、敌对,一些地区也存在个别组织和个人将恐怖主义与某一民族、宗教生硬关联的现象。例如在中东地区,以色列的一些民族极端组织、宗教极端组织和激进人士将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视为恐怖主义的化身,相应地,一些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极端组织、宗教极端组织和激进人士将犹太民族、犹太教视为恐怖主义的代表,彼此又经常用恐怖主义的手段袭击对方,这是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活动不断、双方敌视情绪长期无法化解的重要原因。不少民族或宗教极端组织也反对本国政府对外部“敌人”的妥协,甚至不惜用暴力恐怖手段对付对“敌人”妥协的本国政治领导人,1981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被刺杀、1995年以色列前总理拉宾被刺杀就有这样的因素,这是中东和平进程长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在“一带一路”沿线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中,以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为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无论从数量、规模和破坏性影响来看,都是相对突出的。这可能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倡导的“圣战”(Jihad)主张有一定关系。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教义,世界分为两部分: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地区和异教徒统治的地区。一些激进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主张,穆斯林应该通过不断的“圣战”,向全世界传播对真主的信仰,直至全世界都接受伊斯兰教为止。*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也就是说,他们要改造或消灭异教徒,实现全世界的伊斯兰化。此外,《古兰经》提出:“在捍卫信仰时可以使用暴力,并教导说,参加斗争者比不参加斗争者更有可能被接纳进乐园”。*[美]J.W.李普曼著,陆文岳、英珊译:《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部分教众,或被一些极端主义者用来误导教众跟随他们从事“圣战”乃至恐怖主义活动。
客观地说,如果主张“Jihad”仅仅是指一种恐怖主义式的、带有暴力恐怖色彩的“圣战”,这本身就是对“Jihad”的一种非常狭隘的解释。但“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极端组织和个人却“最大限度地将这一狭隘的解释发挥到了极致,并主张和实施极端形式的做法”。*[日]山内昌之:《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美国》,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理论探索》,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这些极端组织在所谓的“圣战”旗号下发展势力、开展活动,并为其暴力恐怖活动寻找理论依据,公开宣称:“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问题只能通过战斗来解决……除了‘吉哈德’之外别无他途。”“由于敌人已经深入到伊斯兰世界内部,‘吉哈德’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集体责任,而成了一种个人的神圣义务,每个穆斯林都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和方式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向伊斯兰的敌人发起进攻,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安拉奋斗”。*肖宪:《当代国际伊斯兰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39页。一些具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背景的极端组织或个人甚至“从恐怖袭击中获得一种虚幻的胜利和满足感,以维护其所追求的事业和信仰”。*叶青:《试析当代伊斯兰圣战观》,《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第17页。正是因为以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为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在“一带一路”沿线乃至世界范围内较高的活跃度,及以西方国家或西方利益为重要对象的攻击行为,使得西方某些人士制造出“恐怖主义威胁就是伊斯兰威胁,就是阿拉伯威胁”等误导性、敌视性言论。这种把一个民族、宗教整体视为恐怖主义的观点,是造成西方国家与阿拉伯民族等非西方民族国家,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产生矛盾和冲突的重要祸根,也是隔阂乃至仇恨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同时,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也不再纯粹地为本民族、本宗教的整体利益进行斗争。例如,不少宗教极端组织虽然打着为宗教利益而“圣战”的旗号,但是它们实现存在价值的方式已经游离于自己的宗教信念,分化成不同的专业性、职业化的恐怖主义组织。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少地区,很多所谓的“圣战者”事实上就已经成为只认金钱的雇佣兵,在车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冲突和战争中,不少所谓的“圣战者”事实上并不是无私的宗教卫道士,而是领取佣金的职业战士。在目前的“伊斯兰国”中就聚合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雇佣性质的“圣战者”。我国“东突”势力也有人员进入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据叙利亚驻中国大使伊马德·穆斯塔法披露的信息,至少有30名“东突”分子潜入叙利亚从事恐怖主义袭击行为,或参加针对叙利亚政府军的作战。*邱永峥等:《至少30名“东突”分子潜入叙利亚》,《环球时报》2013年7月2日,第3版。据中国反恐部门推测,在叙利亚的“东突”分子可能多达上百人。据有关媒体报告,“伊斯兰国”中还存在所谓的“东突营”,可见“东突”分子在“伊斯兰国”的规模。这些人并非都是雇佣军,有狂热的宗教信徒,但不少人具有雇佣军的身份嫌疑。
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披着民族或宗教外衣、打着民族或宗教旗号用暴力恐怖手段实现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已经成为部分恐怖主义势力的选择,这也给所在国的安全与稳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导致一些地区长期处于动荡、冲突之中,使所在国部分或整体的暴力冲突不断、社会治安恶化、政局动荡不安,也使所在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受到巨大威胁。我国是受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活动危害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长期遭受恐怖主义的危害。例如,在新疆地区,宗教极端极力鼓吹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对“异教”和“异教徒”的仇恨和仇视,不断破坏新疆各宗教和睦相处和民族团结。它们违背和歪曲伊斯兰教教义,以“圣战殉教进天堂”等歪理邪说蛊惑蒙骗穆斯林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把一些人变成完全受他们精神控制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频繁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残杀包括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在内的各族无辜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史见证》,《人民日报》2015年9月25日,第9版。这不仅对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也严重威胁着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此外,俄罗斯、法国、西班牙、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均不同程度地面临如是问题。特别是法国,近年来成为欧洲国家中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最多的国家。俄罗斯因为加大了在中东地区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招致“伊斯兰国”的疯狂报复,也成为受恐怖主义袭击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在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和袭击状况更为普遍和严重。在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存在和相关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叙利亚内战的复杂性和惨烈性,加大了叙利亚内战解决的难度。
三、解决恐怖主义难题的思路
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与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存在某种特定的关联性,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引发了各种类型的恐怖主义难题,这增加了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难度。但相应地,要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已经非常严峻的恐怖主义难题,特别是要发挥各国的合力打击披着民族、宗教外衣发展和活动的恐怖主义势力,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的关系,客观地认识和对待一些特定的民族、宗教及其教众,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民众、教众参与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必须认识到,就实质关系来说,虽然民族分裂主义、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是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温床,但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势力并不代表其所在民族的整体,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也并不代表其所信仰宗教信徒的整体,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宗教整体性地奉行或支持恐怖主义。现实中的各类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成为一类非理性的社会畸形团体,只是以某种标志或信念加以包装而已。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势力与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势力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意味着其所在的民族大众、所“代表”宗教的教众都奉行或支持恐怖主义。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任何一个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势力都没有得到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支持,任何一个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组织也都没有得到本宗教大多数教徒的支持,无论是激进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激进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还是激进的犹太教原教旨主义、激进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背景下的恐怖主义组织都没有得到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印度教大多数教众的支持。这些组织用暴力恐怖手段从事的行为反而受到越来越多本族人、本宗教教众的反对。例如,我国的“东突”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行为虽然得到了一小部分反汉族、反共产党、反中央政府或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甚至赞同、支持,但大部分维吾尔族群众认为,这些分裂势力并不代表全体维吾尔族人的意愿和利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恐怖主义行为的反对者,很多人甚至牺牲在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第一线。2014年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案发生后,11名维吾尔大学生公开发表《我们,不会再沉默》的公开信,对恐怖分子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呼吁“维吾尔同胞勇敢地站出来,抵制邪恶极端,与极端思想作斗争”。这在当时激起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共鸣,体现了一般的民众与恐怖分子的明晰界限。在中东国家,部分宗教、教派的民众多次上街游行反对恐怖主义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对当地恐怖主义行为的反对。对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必须宣传并多方面传递这些正能量,尽可能地减少负面因素对一般大众的影响。在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有必要尽可能地争取大多数,特别是那些有可能被恐怖主义势力争取过去的群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恐怖主义势力。要对各类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宣传,让广大民众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害,在恐怖主义势力与一般的民族大众、宗教教众之间确立一道隔离墙,减少恐怖主义势力对一般大众、教众的诱惑、误导和欺骗。
实质上,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宗教真正崇尚恐怖主义,在任何一个庞大的民族体系、宗教体系中既会有精华,也会有邪恶的病体,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恐怖主义已经严重损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形势下,如果将具有民族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相关民族的“代表”,或者将具有宗教背景的恐怖组织视为相关宗教的“代表”,将恐怖主义与某一民族或某一宗教的关系普遍化、绝对化,甚至为了自身利益以种种理由对一些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其结果只能是扩大恐怖主义势力的“群众基础”,助长恐怖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从而掩盖恐怖主义势力反人类、反社会的极端性性质和邪恶本质,甚至会变相地“帮助”恐怖主义势力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方乃至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着较大反恐压力的今天,要坚决反对把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的民族、宗教生硬地关联在一起的做法,更不应把反对恐怖主义斗争单纯地定位为反对某一个民族、宗教,不能无限夸大恐怖主义与民族因素、宗教因素的关系。这样做的后果,只会混淆恐怖主义和民族因素、宗教因素之间的关系,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冲突,扰乱各国合作对恐怖主义的打击,甚至会形成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激化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从而导致新的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对恐怖主义斗争过程中的偏颇做法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教训。
“一带一路”沿线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不少恐怖主义势力是在西方国家的纵容甚至支持下发展壮大的,典型的事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中情局在阿富汗对“基地”组织的支持。“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能说一点责任就没有。为了自身战略和利益,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已联合起来打击“伊斯兰国”,但现实的状况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打击效果非常不理想,“伊斯兰国”的实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实力不断壮大、控制范围不断扩大,西方国家及其中东盟友存在“出工不出力”、谋求祸水转移即借手“伊斯兰国”打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嫌疑。2015年10月以来,俄罗斯对“伊斯兰国”进行了多次空袭,短期内重创“伊斯兰国”,*[俄]谢尔盖·斯特罗坎、叶莲娜·切尔年科:《俄在叙问题上获得主动》,《环球时报》2015年10月17日,B1。这与此前美国等国家对“伊斯兰国”的联合打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上述嫌疑更为明显。正如有英国学者所说,“在美国,有时对颠覆性暴力行为大声谴责,有时却又拍手欢迎”。*[英]约翰·格里宾等著,朱善萍等译:《历史焦点》(上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他们在战略和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将恐怖主义与某一民族、宗教生硬地关联,也可以无视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本质及其恐怖主义行为而予以纵容甚至支持。毫无疑问,这不利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方在打击恐怖主义时应竭力避免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到了通力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了,美国、欧盟国家、俄罗斯、中国等大国之间应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通力合作。在大国合作的基础上,再联合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恐怖主义势力常年盘踞、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的国家以及受恐怖主义活动影响较大的周边国家,这样才有可能改变目前打击恐怖主义各自作为的不利局面,取得打击恐怖主义的空前效果。“伊斯兰国”的种种行为和对各国的安全、利益的威胁和侵害,为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大国及联合相关国家打造反恐合作机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如果各国能够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将是多赢的结果,不仅将给予“伊斯兰国”沉重打击,维护各国的安全与利益,也将帮助各大国及相关国家尝试构建处理共同威胁的机制,为将来解决其他共同威胁提供经验和借鉴。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恐怖主义的发展也出现了全球化的态势,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同样出现了全球发展的态势。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方需要在厘清恐怖主义与民族、宗教关系的前提下,单独或共同制定正确的反恐策略,坚决打击顽固者,有效分化动摇者,积极争取反对者,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也须摒弃对待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只有这样才能集合尽可能多的力量共同对恐怖主义进行有效的打击,从而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方的安全与稳定,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简介]宫玉涛,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东亚关系与边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恐怖主义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5MDQN08)、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团队建设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软实力与社会价值信仰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5MDTD07C)、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项目编号:YETP1307)、中央民族大学柏年康成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的建设性意见和帮助,文中错漏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