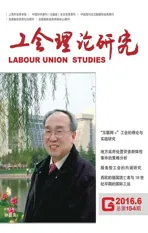西欧的德国流亡者与19世纪早期的国际工运
2016-03-15文丰
文 丰
(1.中共宜昌市委党校,湖北宜昌443000;2.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西欧的德国流亡者与19世纪早期的国际工运
文 丰1,2
(1.中共宜昌市委党校,湖北宜昌443000;2.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19世纪早期,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德国革命家流亡到西欧的法、英、瑞士等国,他们建立起一系列的政治组织,并广泛参与到各国的工人运动中。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的工运组织活动基本都是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进行,这使欧洲的工人运动在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国际主义色彩。德国流亡者参与的英法等国的工人运动,为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工人运动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国际工运;德国流亡者;社会主义
一、西欧的德国流亡者
17世纪三十年战争导致的严重创伤,对德意志民族国家来说,是一场十足的灾难,而这场灾难又为19世纪的普法战争埋下了伏笔。由于德国在近代前期的四分五裂,当别的民族国家开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之时,它仍然被视为西欧“先进”文明与落后野蛮的俄罗斯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这种相对落后表现为以普鲁士、奥地利为代表的德意志邦国在政治上封建性与专制主义并存;经济上,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建立,这严重阻碍了德意志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与之相应的则是德国的工人运动必须肩负起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一起反封建、反专制的历史任务。因此,至少在19世纪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社会主义运动。
同时,由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封建邦国的专制主义回潮,一批共产主义思想家和自由主义革命派流亡到西欧,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瑞士。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潮即通过这些政治流亡者在欧洲普遍传播开来。这一批流亡者在国际工运的深入发展中,逐步转向了共产主义,威廉·魏特林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一流亡群体成了早期工运的主要成员,在一份正义者同盟的供词中,提到的盟员大部分都是德国裁缝,而魏特林的职业也是裁缝。[1]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工人解放的学说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思想残余。但是相对于法国的布朗基而言,他极力主张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全阶级的共同奋斗,而不是通过一小群精英分子的秘密活动来实现突发性的社会革命。因此,他又是进步的。
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详尽的计划、超强的执行力和足够庞大的阶级力量,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或者关注工运的思想家们只能停留于“空想”阶段。19世纪上半期西欧工运的蓬勃发展并不能掩盖英、法、德等国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起义失败的事实。
因此,在后来盛行的暴力革命与议会斗争学说形成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之前,这些德国的流亡者们只能在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内,利用自己的哲学头脑,并大力挖掘自身的思辨能力,来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口头和纸面上的“劝说”“揭露”或“批判”。
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法两国的工运思想家则较早地发展出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并且在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先驱欧文那里得到了初步的尝试。虽然在现实中,欧文的实践失败了,但是对于幼年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潮来说,不啻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在法国,从布朗基起义到巴黎公社,法国一直被视为近代欧洲工运的中心。因而,可以看出,这批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的德国流亡者们,是在英法等国亲历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念的交锋和革命实践的洗礼后,再回流到德国。因此,研究早期的国际工运和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西欧社会主义思潮与德国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对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法国工运有一个简要的了解。
二、19世纪早期的法国工运
法国被认为拥有悠久的无产阶级革命传统,其起源可以上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虽然就性质而言那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毫无疑问,法国的无产阶级在其中显示了巨大的阶级力量。法国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祥地,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故乡,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法国诞生了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傅里叶、巴贝夫……,这个无限延续的名单足够撰写一部法国社会主义编年史。1830年代一系列的法国工人起义——1830 年7月的巴黎工人起义、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9年四季社起义——使法国无产阶级成为当时欧洲工运的典型代表,法国亦成为19世纪欧洲工运的中心和社会革命的温床。19世纪早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圣西门和傅里叶都是法国人,而巴贝夫和布朗基则前赴后继,直接将无产者的革命付诸行动。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早期工人运动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实素材和理论养分。
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早期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也暴露无遗,不堪忍受的工人们频繁发起自发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基本上都缺乏思想理论的指导。换言之,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初级形式,其本质在于为批判而批判,它只是针对当时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种较为理想化的对策,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及现实基础提出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斗争策略。“直至1830年,社会主义还仅仅接触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小团体。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无视工人的斗争便向空想社会主义进军。工人的队伍进行了一场英勇的、分散的和必定要失败的斗争,斗争没有学说指导,也就没有胜利的前景。”[2]马克思在回顾巴黎公社失败原因时也指出了相似的问题:“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3]马克思这里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英法等国的工人运动深受本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而这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来源于对英法资本主义形态的观察,这种观察的结果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它必然打上早期资本主义的烙印。这种理论源于近代早期,可以上溯到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和哈灵顿(《大洋国》)的观念。一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走一条温和的但是“突变”的道路,即避免激烈的社会内部冲突,依靠资本家的良知,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愿景。这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差别不是后天发生的,而是源于他们各自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但是同样要注意布朗基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通过少数革命者的暗杀活动,来动摇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至少是对其中的统治阶级产生震慑,从而使整个社会快速地进入共产主义。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并反映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中以及马克思对19世纪中后
期在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切且持久的期望中。
由于当时的欧洲同时面临封建残余势力的垂死挣扎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两股阶级力量的巨大张力,此起彼伏的社会思潮必然处于激烈的交锋和震荡中。没有哪个学说能够完全一统天下,各种思潮必然在涌现于世的那一天起,就打上无比清晰的阶级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法国近代工运的元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倡导者布朗基。
布朗基于1835年组织了工人革命组织“家族社”,其入社问答条目反映出了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工运领导人对他们所处时代阶级关系的一般看法。他们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阶级观念,对“贵族”和民众进行了区分:“谁是当今的贵族?(回答)大财主,银行家,商人,垄断者,大土地所有者,交易所经纪人,一句话,靠牺牲人民利益而发财的剥削者。……什么是人民?(回答)人民,这是从事劳动的公民的总和。”这里的“剥削者”显然不是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传统意义上的土地贵族,而是这个时代的“资本家”们。问答已经鲜明地指出了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方是“贵族”,另一方是“人民”,一边是剥削者,另一边是劳动者,而且指出了改变这种不公正社会状况的道路:社会革命。[4]当时的法国处于由金融贵族建立的七月王朝的腐朽统治下,巨大的贫富差距诱发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金融资本家政权引起了激进思想家的尖锐批评和法国社会的普遍反感。在法国当时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中,布朗基选择了直接走向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家族社于1836年被法国警察摧毁后,他又与战友巴尔贝斯在次年组织了四季社,他们在该社委员会1839年5月12日的宣言中,直接发出了战斗口号:“公民们,拿起武器来!压迫者灭亡的时刻到了……”[5]从他们的战斗口号中,我们显然听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遗响。
后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深刻揭示了布朗基社会主义观念的基本特征。然而,自布朗基起义到1848年革命再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失败,给包括法国在内的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以沉重的打击。经验表明,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在推翻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中,能够熟练地掌控或运用国家机器,尚不具备建立阶级专政的政治能力——这个问题要等到1917年才会解决。
三、德国流亡者的早期组织
1833年,流亡在法国的德国革命者和工人成立了“德国人民同盟”,这是一个带有共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组织。1834年,一部分政治流亡者和手工工匠从该同盟中分离出来,另立“流亡者同盟”。不久,这个组织就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流亡革命者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得这个组织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动摇不定。组织内部的无产者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矛盾迅速转化为理论上的激烈冲突。[6]
该同盟的政治主张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将是一个法治国家,而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人民主权,特别是维护人民自由这一项最为神圣的权利,这些观点显然是与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针锋相对的。他们所寻求的关于公民各种自由的权利,基本上是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的权利,但在封建邦国林立的德意志却告阙如的。由抽象的自由权利延伸出的集会、请愿、出版等权利则被视为公民自由的有效保障。在同盟章程中阐发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理论,特别是选举制度,显然是对英国宪政的一种简单模仿和对卢梭公共意志理论的继承。此外,关于财产权的限定,包括财产的共有性质,直接决定了占有者本身的社会地位,这被认为是公民独立的基础条件。由于财产是公有的,所以每个社会人便不再屈服于他人的权威或乞求他人的施舍,即不再依赖于他人而完全独立。拥有了可靠的财产权之后,公共教育就负责启迪民智,开发国家的智力资源,并在思想领域保持公民的独立思考能力,为自由、平等等信仰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而独立公民正是幸福国家的第一个
目标。[7]
上述思想属于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理论上的不成熟性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社会认识和现实的政治参照。这些早期的革命者不可能提出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科学学说,而马克思本人在其早期的研究中,也必然承续了这一类思想中的某些基本观点,并且可以看出这类观点一直延续到巴黎公社失败后,通过对其经验教训的总结才得以重新修正。
1836年,该同盟内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确实是一个无产者的政治组织,但却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作为一个由德国的政治流亡者成立的秘密组织,该同盟章程的第一章第一条明确提出:“德国正义者同盟由德国人组成。德国人就是指那些使用德语、保留德国风俗习惯的人。”其宗旨是:使德国从可知的压迫桎梏中获得解放,并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权和公民权。[8]正义者同盟属于国际工运早期的工人组织,其中保留了大量的神秘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残余。根据恩格斯在科伦共产党人事件后的回忆,正义者同盟“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决不排除准备适当时机在德国举行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的德国分支。”[9]
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正义者同盟接受了在当时法国工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布朗基主义,并参加了布朗基领导下的1839年5月的四季社起义。起义遭到了七月王朝的血腥镇压,路易·菲利普政府逮捕了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在内的正义者同盟中的积极分子。此二人皆于释放后流亡到伦敦,在那里参加了1840年2月由德国流亡工人建立的德意志教育协会这一秘密组织。不久,正义者同盟的中心由法国巴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而英国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给了国际工运极大的便利。随后,马克思流亡伦敦并与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一起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共同指导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6月于伦敦)和第一国际(1864年10月于伦敦)的成立工作,欧洲的国际工运由此脱离了早期的不成熟形态,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德国流亡者对欧洲工运的影响
德国流亡者几乎参与了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一开始是在法国和比利时,接着在英国。后来成为德国工运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沙佩尔还参加过马志尼领导的向萨瓦的进军,这都充分说明了同盟的国际主义性质。
同盟成员来源的多元性一方面使得早期的西欧工运带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化使得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际工人组织无法在短时期内建立,他们始终缺乏一个明确的、单一的、坚定的政治目标。这并非是由于早期工运理论的不成熟或是工运成员们的政治觉悟不高,而是国际工运在实践中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工人运动领导人必须主动适应各个国家千差万别的社会习惯、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乃至文化氛围。早期工运的领导者们早就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到了欧洲各国,但是一直未能产生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泛欧工人阶级的国际政党。这也是为何最早的工人阶级政党首先出现在德国(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1875年与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然后才在欧陆各国依次产生的原因。
此外,早期欧洲工运的国际主义特征带来的一个理论后果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多国同时发生。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在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后,各国之间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这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此外,大工业导致了文明发展程度相差不多的国家之内,社会必然分裂为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因此,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都必须在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10]虽然这一结论被列宁发展为在一国或数国首先爆发革命的观点,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而言,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和各国经济的联动性。这必然要求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各国工人阶级需要主动突破民族国家的狭隘界限,去寻找共同的普遍化的阶级利益,从而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目标。
再次,自卢梭开始,法国的思想家们不断地批判和揭露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揭露的结果之一,便是在19世纪前期,法国的社会平等状况要远远好于德意志各邦。然而,这种相对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丝毫缓解工人阶级的生活困苦,它只是在从七月王朝到第二帝国时期,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法国没有发展出一套能够充分指导本国工人运动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而这正有待于德国革命家在19世纪中后期的辛勤工作。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早期工人运动培育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而这些社会主义者(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推动了整个西欧工运的发展。这一互动过程使整个西欧工人阶级都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暂时性地克服了当时弥漫欧洲的民族主义狂热。
然而与上述结论相对应的是,在德国统一前,德国流亡者们希望通过国外的社会主义运动来促进本国工运的发展。由于本国强大封建保守势力的存在,近代以来在西欧各国已经充分发展的权利学说在德意志却无法付诸政治实践。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在自己的自由权利都无从谈起的时候,不可能与被剥削对象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因此,实现民族统一成了德国工运领导者的强烈诉求。由此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1871年的普法战争一方面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奥地利除外),但另一方面却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勃兴。普法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最具生命力的思想运动。欧洲工人阶级积极争取各项权利的同时,各国工人运动的民族属性逐渐超越阶级属性,这注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义无反顾地倒向本国统治阶级的这一历史结局。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1-45.
[2]克洛德·维拉尔.法国社会主义简史.曹松豪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5.
[3]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3.
[4]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69.
[5]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70.
[6]米·伊·米哈伊洛夫.共产主义者同盟,杨润千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6:23.
[7]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41-47.
[8]德国政治同盟章程,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Tit.509,Nr.47,Bd.2(副本).转引自: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0-11.
[9]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42.
[10]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68-369.
[编辑:韩 超]
D415.16
A
1008-7753 (2016) 06-0043-05
2016-10-11
文丰(1984-),男,湖北襄阳人,中共宜昌市委党校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