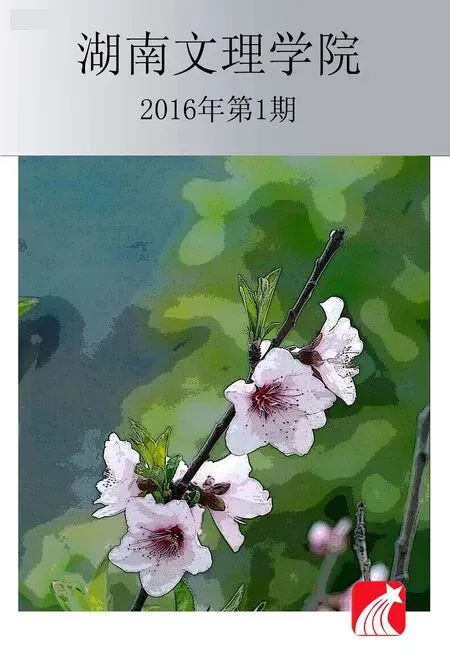伦理引导战争观念探析
2016-03-15丁雪枫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丁雪枫(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伦理引导战争观念探析
丁雪枫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摘要:伦理引导战争的观念由来已久,慎战取向的战争主体、人道性的战争手段、有限性的战争过程等对人的尊严的关切能够得到普遍认同,是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依据;世界和平、人类文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目的王国”的理想,是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目标;提升了战略威慑而非实战、推进了政治对话而非对抗、促进了武器智能化而非拼命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践,成为伦理引导战争观念的价值确证。
关键词:伦理;战争;引导;人的尊严
引导战争的因素复杂多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尤其关涉伦理道德,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研究尚显不足。加强伦理对战争的价值引导研究,对于实践强军目标[1]、促进世界和平、推进人类文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依据
作为一种理念,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合理性依据,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慎战取向的战争主体与普遍价值认同
相对而言,野蛮民族往往好战,文明民族往往慎战。随着人类越来越文明,慎战主体越来越多,其慎战思想也日益支配整个人类。在中国,慎战思想源远流长。春秋时期,老子就提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道德经·三十章》)认为“以兵强天下”就是“好战”,通过战争获得国土、权力是不道德的。相反,“不以兵强天下”就是“慎战”。当然,慎战并非不战,只在迫不得已时才选择采取战争的形式解决部族、国家间的争端,于是发展出“哀兵必胜”的思想。同时代的孔子明确提出了慎战思想:“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孔子主张把战争看作跟斋戒祭祀和对待疾病一样,要慎之又慎。即使作为兵家的孙武也主张慎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直至发展出孟子的“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的价值命题。中国传统如此,西方也一样。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尽管都把勇敢看作军人的必备美德,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都主张慎战,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发动战争。
慎战思想或主体的慎战取向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至少有两个依据:其一,节制战争。战争是由主体发动并参与的,主体的慎战倾向有利于限制战争,即使战争发生,也能把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努力减轻战争带来的伤害。其二,减少损害。战争对于参战的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三十章》)他认为战争常常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灾难,战争是消极的。总之,主体谨慎地发动战争、谨慎地参与战争,具有普遍的价值认同意义。
(二)人道性的战争手段与普遍价值认同
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尤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今世界尚不可能杜绝一切战争。但是如果主体在战争中通过人道的手段取得胜利,则会受到普遍认同。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合理性。
战争手段是指赢得战争的方式方法,人道性的战争手段就是赢得战争时采取人道的方式方法。人道性战争手段能够被普遍认同,依据至少有三个:其一,“人人都是目的”。康德指出:“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2]在康德看来,所有的人都有公平的人格尊严,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当然,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用作目的而不用作手段是不可能的,往往互为目的、互为手段,但是,康德认为,即便在把一个人当作手段时,也必须以其目的性作为前提条件。目的是永恒的,手段是暂时的。其二,“我”是目的。即战争中的我方军人和老百姓等都是目的,其生命、生活、尊严都应该得到保护和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战争的基本法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手段,保存自己是目的,保存自己就是尽可能保障己方人员的安全,否则就不应该发动战争。其三,“敌人”也是目的。战争中把自己当作目的并不难,难的是把敌人也当作目的。广义上,敌人包括参战的敌军和普通老百姓等。尽管交战是两国之间尤其两国军人之间的事,但是人们往往把敌国的一切人都当作对手加以轻蔑和消灭。事实上,即使直接参战的敌方军人也并非都是好战之徒、侵略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受其政府的蛊惑,被迫参战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好战者、侵略者只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才是应该被制服、消灭的对象。在敌方政府官员中,直接煽动战争的也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一般都是慎战的。敌方的百姓更是如此,他们比政府官员、军人更希望和平。所以战争中要尊重敌方的无辜百姓、厌战的政府官员和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的生命、生存、价值应该受到人道的对待;即使罪大恶极的敌方军人、政府官员,只要停止侵略,就可以成为人道主义的保护对象,否则就应该被消灭。手段为目的服务,人的目的性决定了人道性战争手段的合理性,人道性战争手段被普遍认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合理性。
(三)有限性的战争过程与普遍价值认同
有限性战争过程的价值合理性根据在于无限性战争过程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从伦理的角度看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社会财富的浪费。一般情况下,战争过程越长,耗费越多。社会财富是人民这一价值主体创造的,其目的是为了使自我过上更好的生活,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发展。然而,漫长的战线和战争过程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浪费了主体的劳动成果,因而是恶的。其二,人员的疲累。战争过程越长,参与战争的主体越多,战争主体越疲累。一方面,主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生命用在无限的战争中,显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无限延长的战争过程很可能无限否定主体的劳动和尊严,也无限否定主体的生活和价值,因而是不道德的。其三,对生命权的轻视。战争过程的延长,对敌我双方军人、民众的生命都是严峻的考验。我方力图消灭、制服敌方,敌方也想方设法消灭、制服我方,敌我双方军人、百姓都生活在恐怖、紧张之中,其精神必然高度紧张。尤其是,直接参与战争的人可能随时面临伤残甚至死亡的威胁。生命是臻于至善的基础,伤残或死亡是对至善的一种践踏;无限的伤残或死亡是对至善的无限贬低,因而是不道德的。
相反,有限性的战争过程具有价值合理性。当战争不可避免时,人们普遍认同有限战争,即速战速决,其伦理依据至少有三个:其一,节约资源。相对而言,战争过程越短,越能节约社会资源。将主体创造的财富用在自我身上,而非用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上,是最大的人道,因而是道德的。其二,减少伤亡。有战争就有伤亡,其伤亡的不仅有敌方军人、敌方百姓,也有我方军人、我方百姓。无论是谁伤亡,他们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因此是极为宝贵的,都值得敬畏。在战争中,战争过程越短,参战人员越少,受战争影响的人也就越少,他们的生命越能得到保护和保障。战争史表明,战争过程与人员伤亡成正比,战争过程越长,伤亡越大;反之,战争过程越短,伤亡越小。沃尔泽说:“把我们关于战争的观点理解为(虽然也可能有别的理解)承认和尊重个人权利及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的权利的努力是最充分的。”[3]序28-29“个人(对生命和自由的)权利构成了我们对战争作出的那些最重要判断的基础。”[3]62减少伤亡是道德的价值诉求。其三,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战争不是社会的常态,社会生活的常态应该是和平。战争时期,整个社会生活处于极端状态,一切为战争服务,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当然,这在正义战争中是不可避免的。无限的战争过程意味着无限地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无限地否定人的生命、生活和尊严;相反,有限的战争过程,能使人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过有价值的生活,因而是道德的。
二、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目标
阐明了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依据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回答伦理把战争引向何方,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目标是什么以及价值目标是否合理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依据更加具有说服力,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一)维护世界和平
诚然,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伴随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集团主体对狭隘利益的武装争夺。奉献、牺牲即主体利益的付出是道德的基础,然而,战争主体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得一己私利或狭隘集团的私利,不仅不能奉献或牺牲自我利益,而且强取豪夺他人的利益,满足自我或小集团的欲望。由此可见,战争在起源上具有不道德性。
人类自有战争始,就有了人们对和平的诉求。从常理来看,战争意味着惨烈的生存状态,和平意味着平静的生活状态,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的:战争就是冲突,和平就是无冲突;有战争就不能有和平,有和平就不能有战争。这种把战争与和平对立的观点是片面的。实际上,战争与和平是辩证的关系,这种辩证性表现为以战止战、以战争保障和平。《商君书·画策》指出:“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同时期的《司马法·仁本第一》中也强调:“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它们都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认为“以战止战、以战去战”具有合理性,以“去战”“止战”为目的的战争应该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战争在其产生时具有消极和不道德性,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战争又具有维护和平的价值。
所以战争的合理性取决于和平,而和平的价值依据在于其伦理性。人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生存、生活,才能配享人的尊严;相反,战争状态即惨烈的人类生存状态,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不是你伤就是我伤的情况下,人们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个参战者随时可能面临伤残和死亡,甚至伤及无辜和平民,因此战争状态不利于大多数人的生存、生活。沃尔泽认为,参战的军人只是工具,不是人,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和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不具有伦理性,而作为其对立面的和平就具有了价值合理性。罗尔斯也认为:“战争的目标是一种正义的和平,因此所使用的手段不应该破坏和平的可能性,或者鼓励对人类生命的轻蔑,这种轻蔑将使我们自己和人类的安全置于危险的境地。”[4]和平保障了人类的正常生活、生存和发展,其伦理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二)促进人类文明
伦理引导战争的第二个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类文明。首先,战争过程缔造人类文明。粗略地说,战争的发展也经历了野蛮和文明两个发展阶段,正义的战争可以促进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在野蛮时代,战争是你死我活的较量,使对方屈服的最好办法是消灭对方或大量消灭对方;为了消灭对方或使对方屈服,各种战争手段都可能被考虑。在人类历史上,从肉体上消灭对手,乃至灭族战争也时有发生,所以战争过程是残酷的、野蛮的。在文明时代,战争的目的虽然没有变,仍然是使对方屈服,战胜对方,但并不追求消灭对方的肉体。尽管在特殊情况下,需要通过消灭部分敌军肉体的方式才能使其屈服,但是战争的真正目的不再是毁灭,而是让对手放下武器,停止不正义的战争。这一思想渊源流长。在中国古代,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强调,战争的最合理状况是零损害。如果说战争过程的文明在社会发展处在较低阶段时多是美好的愿望的话,那么在社会发展进入较高阶段尤其是信息化时代这一良好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战争推动了军事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战争目标是人类文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卫人类文明,二是发展人类文明。就保卫人类文明而言,自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尽管有了文明的记载,尽管人类越来越文明,但是野蛮并没有消除,战争也没有消失。野蛮民族往往挑起战争,文明民族为了保护人类文明被迫还击。但也有这种情况,战争往往由文明国家发起,打击的对象是野蛮民族,究其原因在于,在野蛮面前,文明显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文明民族为了保护人类文明,防止文明遭到破坏,必需先下手为强,防止野蛮民族对文明的破坏。从逻辑上看,由文明国家发起的战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践上有可能走向极端而导致价值霸权。一些所谓的文明国家可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以“文明”的借口强加给其它国家和民族,进而征服它们,使其接受所谓的“文明”,这就不具有合理性。就发展人类文明而言,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具备较高的人员素质、较好的武器装备、较合理的战术战法,而提高作战人员的素质,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人员素质的提高;提升武器装备的水平,也带动了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战术战法的合理性程度,也带动了其他社会管理模式的更新和发展等等。所以在人类还不能消灭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的重要价值是保护和促进人类文明,这也是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目标。
(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伦理引导战争的第三个目标应是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鉴于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事实,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因此,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也应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人被异化的事实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被深刻异化。在经济上,资本家盘剥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工人劳动得越多,自己获取得越少,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工人反而越发穷困。在政治上,国家机器掌握在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手中,工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言论、集会等自由受到极大束缚。在文化领域,资本家掌握着舆论工具极力宣扬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实质是宣传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合理性,工人处于被检查、被压制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被异化,资本家也同样处在被异化的处境中,因为它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凭借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对工人进行政治压迫,凭借其话语权对工人实施文化霸权,最终激化了阶级矛盾,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革命和正义战争是改变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的根本途径。鉴于这种情形,马克思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理想,并强调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只要有一个人尚未自由,其他人也难以自由;人们只有相互帮助,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
作为政治的继续之战争,伦理引导所要达到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里有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就肯定的方面而言,合理的战争必须能够带来敌我双方乃至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表现为战争能够促使己方、敌方、第三方人民的解放、自由、独立。因此,民族独立、推翻殖民统治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战争也是正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民主、自由的新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发动的这些战争都是合理的正义的战争,它们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否定方面而言,任何战争的结局都不能导向奴役、专制、不自由和征服。一场战争如果没有促进敌我双方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具有不合理性;如果导致了敌我双方人民群众遭受剥削、奴役,就不具有合理性;如果导致己方自由、敌方不自由,也不具有合理性。敌方人民也是战争解放的对象。总之,奴役人的战争或使人陷入被奴役处境的战争都应该受到批判。
三、伦理引导战争的军事实践
伦理引导战争的实践对国际政治生态尤其军事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伦理引导现代战争最重要的价值理念。恰如孙子所言:“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一)提升了战略威慑而非实战
伦理引导战争,就是强调战争的价值合理性在于对人的关切,关注敌我双方人员尤其是无辜民众的生命、生活和尊严。为此,伦理引导战争就是强调威慑而非实战。
在信息化条件下,威慑是主要的军事形态。一般情况下,军事形态有三种:实战、和平与威慑。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战与和平是暂时的、有缺陷的,威慑是持久的、合理的。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实战的残酷性。战争实践表明,战争意味着伤亡和损失。在冷兵器时代是如此,在机械化战争时代甚至信息化战争时代也是如此。在实战中,在敌我双方的激烈较量中,不仅敌我双方军人的生命、生存得不到全面保障,而且敌我双方无辜民众的生命、生存也得不到全面保障,尤其可能造成敌我双方财产的巨大损失和浪费,“打仗就是打经济”。因此,伦理引导战争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甚至消灭实战。二是和平的不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大战、小战,世界性战争、局部性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世界上能够有100年时间和平的国家非常之少。绝对和平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望,是战争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伦理引导战争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战争,通过相对和平的实现而推进绝对和平。三是威慑的合理性。威慑成为当前国际军事形势的常态。军事威慑具有必然性,其存在具有伦理性,因而成为当前军事形势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核武器的使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的常规武器投入战场,更由于生化武器的实际存在,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越来越谨慎,因为一旦爆发世界性战争,就可能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实际存在使各国尤其大国之间都着眼于威慑、遏制而非实战。军事威慑的伦理性在于,保护人的生命、生活和尊严。尽管军事威慑的存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增添了人们的心理负担,但是对人们的伤害远远小于因战争炮火夺取他们的生命和伤废他们的肢体而造成的伤害。在威慑环境下,冷战中的敌我双方除了少许心理负担外,一般都能很好地生活。与实战相比,军事威慑更加尊重人,因而更具有合理性。于是,伦理引导战争就会使威慑日益突出,实战越来越少。
(二)推进了政治对话而非对抗
战争一般是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伦理引导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在于这种价值引导推动了分歧国家的协商而非冲突。协商意味着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认为,行为规范不能由统治者确定,也不能由少数人确定,甚至也不能由多数人确定,而应该由行为者坐在一起进行商谈,得出各方都认可的规范、制度,这样的规范才具有价值合理性。商谈伦理的合理性在于,各方承认自己为人,也尊重对方为人,自己与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承认对方需求的合理性,尽管需求是千差万别的。尊重每一个人,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扬弃了康德的目的王国的思想,值得肯定,但它也有缺陷。因为,社会规范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由于人口、地域的限制,许多情况下把所有社会成员召集在一起达成共识,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具有理想性。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商谈伦理认可了人与人的公平性。相反,冲突则意味着双方相互否定、互不尊重、不承认对方的合理存在和合理诉求。冲突的伦理困境就在于对自己肯定而对他人否定。冲突中的一方认为对方不配享有人格尊严、对方劣差一等,因而应该被消灭或被压制,对方也以同样的思维方式或价值观念看问题,可想而知,冲突的结局只能是战争。
有鉴于此,协商与冲突的伦理差异促进了在现代国家关系中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对话而非对抗。在国家之间的政治对话中,分歧的国家之间相互承认对方,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承认:国与国的平等、国民与国民的平等,人格尊严得到相互的认可。通过对话,分歧国家解决了争端,达成了共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互利,相得益彰。相反,对抗意味着分歧国家或分歧民族之间互不认可,一方力图征服另一方,一方力图毁灭另一方,都视对方为寇仇。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人民之间的相互仇视。因此,对抗不仅消解了国格的价值,而且消解了人格的价值,使人类命运共同体陷入瓦解。伦理引导战争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促进分歧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对话、平等协商解决争端,消解它们之间的对抗、冲突与战争。
(三)促进了武器智能化而非拼命
伦理引导战争理念促进了武器的发展。伦理引导战争的价值基础是对人的关切,这里的人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包括敌我双方的军人、平民、政府官员,各方都把对方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如前所述,伦理引导战争的首要价值是威慑而非实战,是对话而非对抗,即使发生战争,也要少伤亡或零伤亡,少损失或零损失,这是伦理引导战争的又一价值。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武器装备的研究与运用。
一方面,武器装备日益自动化和智能化。其依据主要在于对己方人和物的价值关切。众所周知,复杂、笨重、庞大的战争武器,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保障,而且影响作战效率,难以达到战争目的。正义战争既要考虑己方军人的生命、生活与尊严,又要考虑己方百姓的生命、生活与尊严,也要考虑财物的消耗与使用。武器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集成化、简单化、小型化,减少了实战时我方军人的劳动以及平时不必要的训练,同时还能提升战场效率,缩短战争进程。不仅如此,武器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集成化、简单化、小型化也减少了社会保障的负担,节约了资源。因为,庞大复杂的武器装备必然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民众为此也要付出不必要的牺牲。可见,武器装备日益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对人的充分尊重。
另一方面,武器装备日益精确化。其依据主要在于对敌方军人、百姓及财产的价值关切。敌军也是人,也配享人的尊严与价值。然而敌方军人并非全部罪大恶极,真正有罪的是少数人,是一些好战的军官或政府官员,有时甚至是个别人。这些人要么具有分裂的倾向,要么具有侵略的倾向,由他们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战争,而其他大多数人、其他军人往往受到战争机器的鼓动参与战争。武器装备日益精确化,其主要目的就是精确打击少数罪大恶极的战争贩子,消灭他们或迫使其屈服,最终结束战争,而非在肉体上全部消灭敌军,更不能消灭或危及普通平民。武器装备的精确化能减少对普通平民的误伤及其财产损失;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因而既符合伦理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未来战争武器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220.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6.
[3]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责任编辑:张群喜)
作者简介:丁雪枫,男,安徽霍邱人,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军事伦理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10&ZD072)。
收稿日期:2015-11-12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6)01-0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