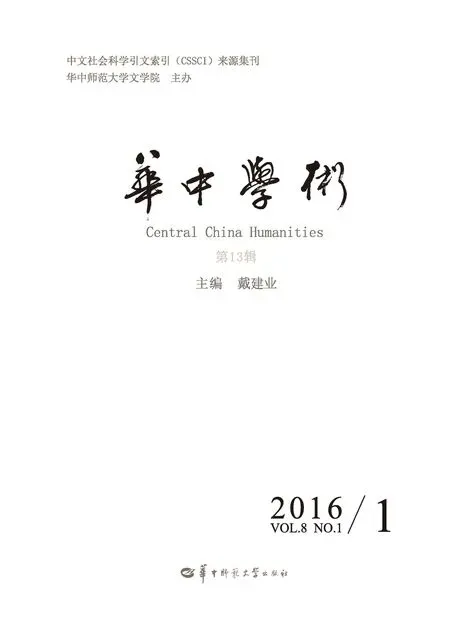《边城》悲剧的重审:由美而悲的结构性冲突
2016-03-15杨洁梅
杨洁梅
(中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边城》悲剧的重审:由美而悲的结构性冲突
杨洁梅
(中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摘要:《边城》的地理背景,叠映在《桃花源记》的美与和平的武陵山水之间。沈从文在风光优美、社会友爱的世外桃源中,引入了人类个体恋爱婚姻的情感冲突,导致美善世界出现爱情悲剧,刷新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田园牧歌的单一图式,使之更为接近人类生存的本真。作品由乐转哀的牧歌图式之下,潜藏着一个美与悲的二元结构:不同个体的某种美好追求一旦生成会聚,既可能基于价值认定的相同而美美并存,也可能基于价值认定的相异而美美冲克。美与悲的存在解释了作品悲剧的生成,边城也因美美冲克而不再是纯粹的人美、景美、情美、事美亦即完美无缺的人世天堂。作者虽然艺术上成功地描绘了美美冲克的情感景观,但意识中却不时吹动“命运”和“偶然”的神秘之雾飘入叙事场域。
关键词:《边城》;牧歌图式;悲美本质;结构性冲突
小说《边城》,曾被沈从文自我定性为“一分从我 ‘过去’负责的必然发生的悲剧”,希望通过这部“纯粹的诗”和“传奇”,“调整”、“排泄”、“弥补”内心郁积多年的情绪——“过去痛苦的挣扎”、“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让“生命得到平衡”。但那些“不幸故事”,必须以“温柔的笔调来写”[1],才能将痛苦、悲剧和爱情的憧憬,平衡为一种美的记忆与叙述。本文的努力,即在于寻找小说中美与悲的构成、美与美的冲突,以及悲剧的开演与落幕。
一、由乐转哀的牧歌图式
牧歌是民歌的一种,原意指牧人和牧童吟唱的歌谣,一般描绘理想化的牧人生活方式,流行于放牧民族或农业民族中的放牧人群,所以有时也描述田园风光。牧歌作为一个词语和歌曲形式,在中国很可能最早见于唐人元结的《五规·戏规》:“元子倚于云丘之巅,戏牧儿曰:‘尔为牧歌,当不责尔暴(践踏庄稼)。’牧儿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2]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术语来考察,牧歌(eclogue)的来源只能是西方文学,指的是以田园生活和牧人群为题材的一种短篇田园诗,把牧人群的田园生活描写为“一种自由的享受,即免遭比较文明的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和腐化堕落的折磨”[3]。牧歌除了抒写牧人们乐园生活的自由享受之外,还涉及牧人们在树荫下“倾诉他们的悲痛”[4],引起悲痛的原因往往是情人的离去,也可能是情人的死亡,这种哀乐并存的牧歌类型就涵盖了哀歌/挽歌的传统。
《边城》代表了中国这类作品的最高成就,被誉为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巅峰之作。沈从文明确以“哀乐”并存的“牧歌”定位《边城》[5],刘西渭赞誉《边城》为“一部idyllic(引者注:意为田园诗般的、牧歌的)杰作”[6],汪曾祺指出《边城》有“牧歌的调子”[7],夏志清评价《边城》是“牧歌式的文体”的“代表作”[8]。可见作者本人,乃至中外学术界,都曾长期将《边城》与西方的牧歌传统相联系,用以界定和阐释这部“诗小说”[9]的抒情特质。
《边城》的寓意,在于“用这个故事来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10],描写“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11]。翠翠的爱情故事,既是作者那种“哀乐”的精神投影,也是边城故事的中心结构。主要人物有5位:翠翠和她的(外)祖父老船夫、船总顺顺及其长子天保及次子傩送。叙述时间跨度为3个端午节。故事开端于两年前的“那个端午”,13岁的翠翠,黄昏时分在河边邂逅初长成的傩送,在“大鱼咬你”和“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的隐喻性青春对话中情窦初开。在这一阶段,诗画边城中的生活环境,以及翠翠和傩送之间朦胧、羞涩而纯美的初恋情感,给人留下的是舒缓、欢快、明媚、随性、温情、美好的边城乐园印象。发展到一年前的“上个端午”,故事的情感基调开始发生变化。在船总家,天保在父亲的授意下将节庆战利品——又肥又大的鸭子——送给单恋的意中人翠翠,船总顺顺与老船夫在此时达成天保配翠翠的默契,而翠翠的心却追随出门在外的傩送下了青浪滩。故事在“这个端午”错综复杂起来,一系列突发的情况与事件参与并改组了先前的故事结构:亲兄弟爱上同一个姑娘翠翠,而娇美的中寨团总小姐以城中一座崭新的碾坊为身价进城与傩送相亲。长辈在子女婚恋方面“美美相配”的原初意志,逐渐将乐园中人导向“哀”的处境与“悲”的结局。最终,祖父企图将孙女从类似翠翠之母的命运索套中解救出来,挽救并成全孙女的爱情,但他在垂老之年与命运的拼死搏击以失败告终,暴风雨之夜的终老显得绝望、悲壮而凄凉。他拼尽全力保护的唯一亲人孙女翠翠,并没有获得比她的母亲更好的命运,翠翠面临的是亲人的死亡、爱人的出走和无期的等待。《边城》中,爱情的失败往往伴随着人生的挫折和生命的消逝,由乐转哀的牧歌图式由此确立。
二、边城牧歌的悲美本质
《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之下,隐藏着一个美与悲的二元结构。
(一)乐园图景的美善本质
《边城》的乐园构想建立在美和善的基础之上,透过景象、物象、形象的描绘与塑造,投射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习俗、人际关系、民族心理、人物性格等各个层面。时间、地理和文化概念上的边城,是沈从文为人们阈定的一个理想化的人间乐土和精神家园。边城自然、人心、人事对美、善的自发追求中所生成的乐园景象,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独特的存在之一。
在涵蕴桃源文化与屈原文采的湘西世界,《边城》构筑了一个风景美、人情美、人性美和“一切充满了善”[12]的诗意边城,以此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边地茶峒凭水依山而筑,山是常年深翠,水是清澈透明,沿岸的泥墙乌瓦、河街的吊脚楼和城边的渡口与四周的环境“极其调和”。尽管茶峒位于“两省接壤处”,但十余年来“并无变故发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着边城人民所感到”,俨然承接着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外界的社会历史之“变”无法影响边城人性之“常”。这里的人事(社会习俗、风土人情、文化氛围)是“安静”、“淳朴”、真率、“自然”、非功利的。在这小城中生存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的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依循美和善的道德原则行为处世,于微细处、常态中浸润、沉淀出独特的边城性格。一如作者的好友刘西渭所言:“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14]
《边城》乐园图景的审美本质,在于沈从文寄予美好愿望而着意为之的至高境界:和谐与自然——“一切是和谐”,“一切准乎自然”,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15]。在这一文本意义层次,边城意象与桃源意象渐次混一。观照沈从文“乡下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他对腐化衰败、复杂功利、矫情失血的都市和现实一以贯之的批判姿态,《边城》牧歌的实质正是“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16]。从而,在理想化的边城之“美/善”与都市和现实之“丑/恶”的隐形对立结构中,获得整一效果和生成意义。
(二)哀歌/挽歌图式中的悲剧感
“自杀、猝死和时间不可避免地流逝,都让表面的田园事情变得暧昧起来。”[17]殉情而亡的翠父翠母、心力交瘁而亡的祖父老船夫、意外丧生激流的天保、自我流放离乡的傩送、大好青春空逝的翠翠,这些在历史与现实当中苦苦挣扎的生命情状,穿透“表面的田园事情”被一一表现、澄明。在翠母的悲情故事中,似乎还有一个“翠母之母”的影子故事:老船夫之妻的身世。她是不是也在翠母年幼时故去了?也许真是这样,翠翠母亲才会选择一定要生下一个新生命延续自己陪伴父亲的责任之后再自杀,完成自己对父亲的责任。翠翠祖父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分别陪伴与照顾三个唯一的至亲女性,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情感、全部寄托都在她们身上。当最后一个女性翠翠被“天意”笼罩而断定不能拥有明丽的天空之际,老船夫运行了70余年的精神系统终于彻底崩盘,在一个惊雷滚滚、风雨大作的夜晚无疾而终,以一种罕见的方式貌似波澜不惊地卸下了全部的人生责任。
作者的衣钵弟子汪曾祺透过《边城》表面的“温暖”,看到小说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18]。《边城》并非一个只有美、诗、乐而无悲的中国式桃花源镜像。在武陵桃花源中,田园景色宜人,外围环境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内部情景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源中人各司其职、关系融洽:“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没有社会冲突,没有爱情冲突,更没有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全然是永恒和谐。而在边城中,同样美的风景和人情,却存在因“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而发生的种种“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19]的冲突。边城尽管没有社会冲突,但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冲突(天保死于险滩激流),人与命运的冲突(翠翠的祖父、父亲和母亲对命运的抗争),尤其是爱情的冲突(翠翠、傩送、天保三人的情感纠葛),且均以悲结局。这些或许预示着作者想象中的乡土湘西——他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必然凋敝、没落,为作者所珍视的农业社会中的那些民族传统美德,将被现代物质文明挤压、替代而渐趋消失。作者后来在《〈长河〉题记》中就曾补充揭示:“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的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20]《边城》的创作,既有对故乡曾经的人性美善的赞美,也有对“崩溃了的乡村”[21]美善流逝的痛惜。对此,刘西渭在感慨中夹杂着疑惑、疑惑中夹杂着感慨:“何以和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22]
当时普通读者群对沈氏小说的阅读与欣赏尚停留在文本的表层,他们仅只看到了故事的美和文字的美,没有上升到评论家刘西渭、作家汪曾祺所能达到的认知层次。即使是刘西渭,沈从文因这位“极细心的朋友”[23]看到了作品是“用人心人事作曲”而授予他“最好读者”[24]的称号,也对他没能领悟自己“写它的意义”[25]而感到遗憾。对读者们没能领悟自己的创作意图或悟透作品的深曲之意,作者深表痛心:“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6]这种文本表层的清新、朴实与底层的热情、悲痛错落并置,将现实的认知层面与事物的喻象层面相连接,产生引譬连类的意义和造景生情的复杂能力,美与悲互为表里、共生互长,是一种共存与转化的关系。因此,沈从文提醒读者在欣赏《边城》时,要善于发掘被美的故事、美的文字所遮蔽的悲剧感,亦即小说的真意。
三、由美而悲的结构性冲突
边城悲剧的形成,可以从其特殊的悲美结构上获得解释。
(一)悲剧冲突的动力和内容
黑格尔认为“各种本身合理的伦理力量”是造成悲剧冲突的真正动力和内容,是构成悲剧人物性格的“优良品质”[27]。
在《边城》中,“各种本身合理的伦理力量”就是各种善的并存与竞争。沈从文说《边城》“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28]。所谓“素朴的良善”是与道德的善相对的概念[29]。道德的善遵循物质文明的一整套规约制造出“失血”的善乃至伪善,而“素朴的善”则是自然本真的善,指向边城与生俱来的人情美和人性美,遵循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道德”[30]——虽自在生长于民间,但又将民间世界的一切混浊丑恶予以澄清,是一种被净化、理想化了的体现人性、人世美好的淳朴道德。美和善这两个概念对沈从文而言是一体的,他说“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的一种象征”[31]。归根结底,素朴的善本身即是美的、自然的,是构建边城之美的元动力与核心要素。
但是,边城中善的个体、善的人性、善的动机、善的行为等这些美的因素,并没有将事件推向完满,反而促使悲剧形成,背离了作者的创作初衷[32]。对于这种矛盾作者也难以解释,只好归之于无所不在的“不凑巧”,是命运的悲剧。“不凑巧”(作者有时也表述为“凑巧”)亦即“偶然”[33],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定”[34]。他坦承:“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35]
沈从文在《爱与美》一文中,阐述了他对美、爱、神三者关系的看法:“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 ‘美’,亦即发现了 ‘神’。……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亦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简便那个 ‘人’。”[36]美指的是作品中“一切美物,美事,美行为,美观念”[37],以及由美而生的人。神则用造物者之手,或者说是命运之手,创造神迹,创造美以及爱的载体人,并且,从命运之手所创造的神迹中可以十分轻易地发现偶然的身影[38]。回归到传统文化语境,上文所说的“不凑巧”、“偶然”、“上帝造物之手”,等等,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亦即冥冥中无所不在的天意。
沈从文在善的世界中,引入命运之手的干预,作为催化剂,希望借此解释边城悲剧的形成原因。事实上,沈从文所谓命运之手的设计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知道:善与善之间可能产生新的善,也可能此善与彼善互不交集,不能产生新的善,甚至两种善或多种善互相冲突而导致悲剧!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家族、每个群体所理解、所认定、所祈盼、所索求的善,有相同也有差异,不可能完全重合。通常悲剧的结构效果来自“多组善恶对立的两两组合”[39],对《边城》这个“一切充满了善”的特殊空间来说,是多组善与善冲突,亦即美与美冲突的两两组合,“美的有时也令人不愉快”[40],不同个体的某种美好追求一旦生成会聚,既可能美美并存,也可能美美冲克,产生“美丽总令人忧愁”[41]的文本效果。
(二)悲剧冲突的路径和力量
《边城》中每个人物的内心愿望和行为选择(即沈从文所说的“单纯的希望”)都是合情合理的。无论是翠翠祖孙,还是船总父子,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对婚恋对象的选择以及对选择分歧的处理,都有充分的理由和尚美、向善的动机,各自本身都是一股合理的伦理力量,但不等于任何时候都能达成任何人希望达成的美好愿景。
翠翠是“自然之子”,是“没有沾染人世间的一切功利是非思想、与自然融为一体”[42]的生命现象,代表着边城之美的最高境界,是边城未婚男青年心中美好的超越世俗的一个梦:“美与爱的理想”[43],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天保和傩送这两个边城最优秀的青年男子兼兄弟的爱慕。两兄弟的父亲船总顺顺心里有个如意算盘,那就是天保配以渡船为陪嫁的渡口孤女,傩送配以碾坊为陪嫁的中寨富家女。表面看去,他对儿子们的这种婚姻安排似乎存有那么一点私心。然而,深究一下即可发现,与其说是做父亲的偏心偏爱、厚此薄彼,不如说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两个儿子能力的洞察、评判有关。船总顺顺当年白手起家,相较外貌和气质酷似妻子的次子而言,他更为信任“一切与自己相似”的长子的自立能力,因此,将碾坊安排给傩神送来的需要留在身边保护的次子,而十分放心地将渡船安排给长子,交给上天保佑,送到渡口去白手兴家。
在翠翠这个年纪,她所能看到的最远图景并不是婚姻,而是让人心动的眼缘和心缘,她的自然本性和少女的浪漫天性,决定了她必然会爱上外表俊美、性格诗意并且多有几面之交的傩送。而她的祖父老船夫已近天年,是自身悲情故事的亲历者和女儿爱情悲剧的见证者,对生活、对婚姻、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于情窦初开、未经世事的翠翠,他更看重的是家庭质量和婚姻生活。祖父的意中之选是长相粗糙、豁达实在的哥哥天保。而天保如果娶到翠翠,他的规划是在渡口兴家立业:“我应当接那老的手来划渡船。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岨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限上种大南竹,围着这一条小溪做我的砦子!”在这幅蓝图中,老有所养,家庭兴旺,人丁繁茂,生活富足,这不仅意味着天保可以给翠翠带来现世的安稳与幸福,也意味着祖父自己此生未能实现的家业梦想,将通过天保与翠翠的结合得以延续、实现。反之,傩送吸引翠翠的素质,则是漂亮,“能抓女人”,“诗人的性格”,恰恰对老船夫那种强调安全稳定、本分实在的内在需要构成了消解。
他们的愿望与选择分歧,源于年龄、性别、价值取向和生活阅历的差异,而非主观意图上的故意或恶意。做父亲的希望儿子们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做祖父的希望孙女能获得其母没有得到的婚姻幸福,翠翠、天保和傩送则希望得到自己的幸福。当他们一旦发现分歧的存在之后,做祖父的转而极力成全孙女;兄弟间则商量以不流血的诗意的方式(在渡口对岸的崖上竞歌,谁获得了翠翠的回应,谁就赢得追求翠翠的机会)化解冲突;在天保、翠翠的祖父相继死去之后,船总顺顺打消自己原先的念头,托人来渡口以傩送媳妇的身份将翠翠接进家门,翠翠则暂时不愿离开祖孙生活的熟悉环境,傩送也不忍独享这份幸福,驾船远走他乡,让时间来抚平心口的创伤。
在此一场域之中,每个人的愿望都是合理的、美的、善的,每个人也都在想使这件事变好、变美,似乎一切都是成人之美。但当这些本身合理的愿望与选择,在“追求某一种人类情致所决定的某一具体目的”[44]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导致此善与彼善因具体目的不同而对立与冲突。
天保想娶翠翠,托人去渡口探询老船夫的口风。老船夫听后“心里很高兴”,只是觉得提亲的形式不够正式,心下还想回去征求一下翠翠的意见,所以比较含糊地回了一番意味很足的话:“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如果)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如果)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按照船总顺顺的意思:天保的“车路”在渡船,傩送的“车路”在碾坊。老船夫这番回话给天保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认为有了双方家长的支持与认同,“事情弄好”的希望很大。“我不是竹雀,我不会唱歌”的天保选择走“车路”,无意中介入了翠翠和弟弟的情感空间。
当然,船总顺顺、天保、老船夫产生这些想法时,对另外两个当事人翠翠爱傩送不爱天保、傩送选渡船不选碾坊的想法是一无所知的,即使是翠翠和傩送两人之间,也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情感状态:虽心属对方,但并未挑明。尽管老船夫“隐隐约约”体会到“这事情在什么方面有个疙瘩,解除不去”,但仍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孙女所爱的人与自己中意的人并非同一人。多方力量的意外介入,使事情变得错综复杂,原有的和谐被打破。天保和傩送相互知晓了对方的心事之后,就面临了情感、道德、伦理的两难困境。在兄弟之情、情人之爱、尚美之意与公平竞争的内在需求之间形成了选择和冲突。此外,翠翠的自然本性、母爱教育的缺失以及自小远离女性群体独处渡口所带有的混沌特质,造成了翠翠不仅对情态发展失去应有的判断,就连爱情上的语言表达也具有相当的障碍,她不能及时告知老船夫自己的心思,也未能在傩送屡次寻求沟通时给予恰当的回应。这种懵懂加失语的无意为之的状态,自然也是翠翠爱情由美而悲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里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45]《边城》就是这样一个亦实亦虚、“一切都当美一些”的人间乐园,乐园中的男女主人公似乎理应拥有美好人生。意外的是,每个主人公都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掉入了作者所谓偶然的陷阱。为什么会有偶然的存在?偶然又是如何形成的?推动这一命运结局的神秘力量,超出了作者的理解,只好归之于冥冥中的天意。这个前人几乎忽略了的问题,正是源于《边城》文本的结构性冲突:并非各种美的意识、美的情感、美的初衷,都能时时刻刻、自始至终遵循着和谐的意志与路径,发展、共融于同一时空。相反,小说中的此美与彼美、自美与他美、独美与群美,每每在关键时候互相冲突,导引三位青年主人公的共同命运由美而悲,而类似世外桃源的边城,也因此不再是纯粹的人美、景美、情美、事美,亦即完美无缺的人世天堂。
注释:
[1]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0~111页。
[2]《全唐文》卷三八三(整理本第三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04页。
[3]《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国际中文版修订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526页。
[4][美]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王腊宝、张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5]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6]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35年6月。
[7]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
[9]郭纪金主编:《中国文学阅读与欣赏》,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10]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11]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国闻周报》第13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
[12]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13]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国闻周报》第13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
[14]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2卷3期,1935年6月。
[15]李健吾(刘西渭):《边城》,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16]刘洪涛:《〈边城〉与牧歌情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第74页。
[17][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571页。
[18]汪曾祺:《又读边城》,《汪曾祺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5页。
[19]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8日和12月10日。
[20]沈从文:《〈长河〉题记》,《重庆大公报·战线》1934年4月21日。
[21]沈从文:《〈边城〉题记》,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4月25日。
[22]刘西渭:《篱下集》,收入《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23]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24]“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8日和12月10日。
[25]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26]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国闻周报》第13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
[27][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84页。
[28]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29]“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住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接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不大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这是沈从文创造“素朴的善”所遵循的美学原则。沈从文:《自传·女难》,转引自《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3页。
[30]陈思和:《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边城〉》,《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31]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8日和12月10日。
[32]《边城》的故事结局背离了作者的初衷:“我读过许多故事,好些故事到末后,都结束于‘死亡’和一个‘走’字上,我却估想这不是我这个故事应有的结局。”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33]沈从文在《黑魇》一文中说:“分析人事中的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与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沈从文:《黑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34]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35]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36]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9页。
[37]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
[38]“耳目所及都若有神迹存乎其间,且从这一切都可发现有‘偶然’友谊的笑语和爱情芬芳。”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2~123页。
[39][美]约翰·克罗·兰色姆著:《新批评》,王腊宝、张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40]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41]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8日和12月10日。
[42]陈思和:《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边城〉》,《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43]陈思和:《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边城〉》,《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44]陈太胜:《理念与感性形象——黑格尔的艺术哲学》,《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45]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8日和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