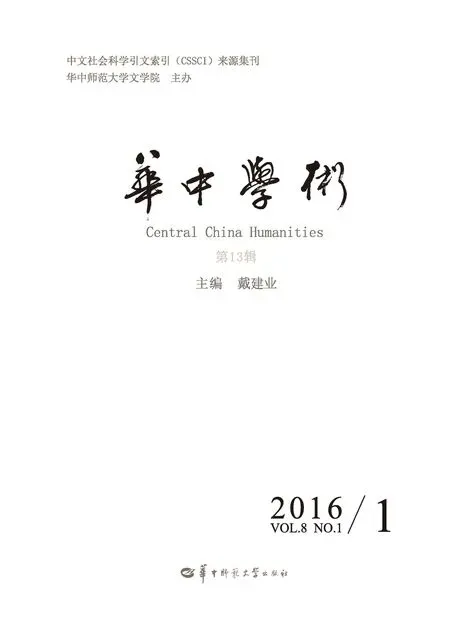阿寄事迹考论
2016-03-15张世敏
张世敏
(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阿寄事迹考论
张世敏
(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内容摘要:义仆阿寄的故事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按文献类别可分为文集、小说、史志三支,故事的源头不是宁稼雨在《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所说的文言小说《阿寄传》,而是《田叔禾小集》中的《阿寄》一文。阿寄故事正好发生、流传于明初禁奴与明末奴变之间,通过对文献进行解读,可知在禁奴与奴变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期,士大夫阶层一方面绕过禁奴政令,已默认了庶民蓄奴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主奴关系松动甚至主奴秩序颠倒时,士大夫希望通过树立道德榜样来维系奴仆忠于主人的关系。各种文献中的阿寄故事承载着士大夫们重构主仆关系的理想。
关键词:阿寄;田汝成;禁奴;奴变
阿寄是明代严州府淳安县徐家的奴仆,同时也是一位贩漆商人,五十多岁后,以十二两白银作为资本,为寡妇主母挣得巨万资产。从其身份来看,阿寄在明代是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这位小人物的传记被《明史》、《浙江通志》等史志文献与《田叔禾小集》、《明文海》、《焚书》等集部文献收录,故事在《续说郛》、《五朝小说大观》、《旧小说》、《醒世恒言》、《无声戏》等小说中广为传扬。一位小人物被明清两代士人普遍关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在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的社会背景下,阿寄具有奴仆与商人双重身份,是研究明代商品经济与封建政治相互冲突难得的样本。本文将对阿寄故事的源流进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阿寄故事这一独特视角,对明代社会中的奴仆现象进行论述。
一、阿寄事迹源流考
明清记录、敷演阿寄事迹的文献数量较多,文集、笔记小说、通俗小说、地方志、正史等文体均记述了其事迹,这些支流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其源头在哪里,各个支流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是需要我们探讨的两个问题。
(一)阿寄故事的源头
对于阿寄故事的源头,学界至今未做严密的考证,仅宁稼雨在《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中略有提及,该书介绍道:《阿寄传》,“明代传奇小说。未见著录。现有《续说郛》、《五朝小说大观》本等《明史》、《浙江通志》、《严州府志》等均据以立传”[1]。据此论述,阿寄传的源头是一部称为《阿寄传》的文言小说,且未见之前文献著录。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是持之有据的,乾隆《浙江通志》中阿寄本传开篇便交代传记资料来源于“田汝成《阿寄传》”[2]。明代《吴兴备志》施奶婆传后,有作者董斯张的按语云:“范蔚宗传李次公,近世田叔禾传阿寄。施奶婆者,不可为万世人臣法哉?”[3]李贽《焚书》在收录《阿寄传》时,也明确指出:“钱塘田豫阳汝成有《阿寄传》。”[4]这些文献都将阿寄故事的源头,指向田汝成的《阿寄传》。因此,宁氏关于《阿寄传》故事源头的结论还可商榷。
第一,从版本上看,《续说郛》中的《阿寄传》并非现在可见到的阿寄故事的最早版本。宁氏认为作为阿寄故事源头的文言小说《阿寄传》未见著录,最早见之于《续说郛》。《续说郛》的作者陶珽生于万历元年,主要生活于万历年间,因此,《说郛传》的成书当在万历或万历之后,离阿寄故事发生时的嘉靖已有较长时间。事实上,早在嘉靖年间,田汝成《田叔禾小集》便收录了阿寄传记,篇名为《阿寄》,与《续说郛》的阿寄故事内容高度一致,可视为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田叔禾小集》刊刻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是“汝成晚年令其子艺蘅所编,凡诗文三百六十九首,五十以后所作,均不在是焉”[5]。《田叔禾小集》在编定时作者还在世,且五十岁后的作品不收录,说明其中的《阿寄》相比其他能见到的版本要早。《田叔禾小集》是在田汝成授意之下,由其子编定的,因此,该集中所收《阿寄》当更加可靠。
第二,从文体与内容上看,记述阿寄故事的文章在明清时期一般都被视为散文而非小说。阿寄之文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题名为《阿寄》,另一个版本题名为《阿寄传》,通过比对可发现,两者之间内容高度一致,仅有细小差别。题名《阿寄》的版本最早见于《田叔禾小集》卷六,全文如下:
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二牛,季寡妇得阿寄。阿寄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老仆,乃费我藜羮!”阿寄叹曰:“噫!主谓我力不若牛马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银一十二两畀寄。寄则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既皆输粟为太学生,而寡妇则阜然财雄一邑矣。顷之,阿寄病且死,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衴中二楮,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可世守也。”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箧,无寸丝粒粟之储焉,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呜呼!阿寄之事,予盖闻之俞鸣和云。夫臣之于君也,有爵禄之荣;子之于父也,有骨肉之爱。然垂缨曳绶者,或不讳为盗臣五都之豪。为父行贾,匿良献苦否,且德色也。乃阿寄村鄙之民,衰迈之叟,相嫠人抚髫种而株守薄业,户祚彫落,沟壑在念,非素闻《诗》、《礼》之风,心激宠荣之慕也。乃肯毕心殚力,昌振镃基,公尔忘私,毙而后已。是岂寻常所可及哉!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以为常。见主母不睇视,女使虽幼,非传言不离立也。”若然,即缙绅读书明礼义者何以加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6]
此文收入《明文海》卷四百三,题名《阿寄》;收入《文章辨体汇选》卷五百三十七,题名《阿寄传》。还有《焚书》卷五所录《阿寄传》。各种文献中的《阿寄传》与《阿寄》之间的差异,仅在于“仲得二牛”作“仲得一牛”。明代各种阿寄传记之间虽然高度相似,但也存在规律性的差别,即题为《阿寄》者都作“仲得二牛”,题为《阿寄传》者都作“仲得一牛”。无论是《阿寄》还是《阿寄传》,都被收入别集或总集中,由此可知,阿寄的传记在明清时期大多被视为传记散文。即使阿寄故事后来被《续说郛》等小说集收录,题名《阿寄传》,然其内容也与之前作为散文存在的《阿寄传》完全一致。小说《阿寄传》完全可视为散文《阿寄传》变换文体之后的改头换面。
第三,从史志编撰原则上来看,正史与方志在修撰时一般不会取材于笔记小说。正史与地方志作为官修史书,特别注重内容的真实可信,即使是明清两代地方志良莠不齐,其真实性颇受怀疑,甚至被等同于笔记小说,被称为清言丛书[7],但很难找到正史与地方志取材于笔记小说的记录。而正史、地方志取材于文集的记述很是常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记道:“国史不得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8]“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铭金刻石,纪事摛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9]章学诚所论,说明文集记述、家乘谱牒、地方志、正史,都具有史的性质,材料可以相互为用。由此可见,即使内容完全一样,作为文人传记的《阿寄传》可以被正史与地方志采用,但作为笔记小说的《阿寄传》则不大可能被正史与地方志采用。
综上所述,阿寄故事的源头只能是田汝成为阿寄所作传记,宁氏所言《明史》与方志据小说为阿寄立传之说不确。
(二)阿寄故事的流别
记述、敷演阿寄故事的明清文献种类较多,导致阿寄故事形成了几个支流,有以文人传记为代表的文集一脉,有以笔记小说、通俗小说为代表的小说一脉,有以正史、地方志为代表的史志一脉。阿寄故事的不同的流别之间关系密切。
文集中的阿寄传记是其他各个流别的源头,是其他两类文献记述与敷演的基础。在田汝成《田叔禾小集》之后,李贽《焚书》收录了《阿寄传》并对故事做了评述,《明文海》、《文章辨体汇选》则分别收录了阿寄传记,这说明明清文人对阿寄故事有持久的关注。
笔记小说《阿寄传》,内容与散文《阿寄传》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只是文体归类时对文体的理解有分歧而已。通俗小说《醒世恒言》中的《徐老仆义愤成家》,与田汝成的《阿寄》之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徐老仆义愤成家》相对《阿寄》来说,故事更加具体,故事发生的地点具体到了村子,徐家三兄弟的姓名,寡妇的姓氏,以及阿寄经商的经过等,都有详细记载,但故事梗概却与《阿寄》完全一致,阿寄经商的本钱都是十二两。
《明史》、《浙江通志》以及《严州府志》等正史与地方志为阿寄所立之传,完全以田汝成《阿寄》作为底本缩略而成。以《明史·阿寄传》为例,传云:
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析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阿寄,时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老仆何益。”寄叹曰:“主谓我不若牛马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尽脱簪珥,得白金十二两畀寄。寄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致矣。”历二十年,积资巨万,为寡妇嫁三女,婚二子,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二子,输粟为太学生。自是,寡妇财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谓寡妇曰:“老奴牛马之报尽矣。”出枕中二籍,则家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可世守也。”既歿,或疑其有私,窃启其箧,无一金蓄,所遗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10]
通过对比可发现,《明史·阿寄传》除了做过将“阿寄年五十余矣”改成“时年五十余矣”等改动之外,相对于田汝成的《阿寄》,没有几个字是创作的,可以说是“缩而不作”。《浙江通志》与《严州府志》中的阿寄传也大抵类于《明史》。
通过对阿寄故事的流别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文集中的阿寄传记自成一脉,是小说、史志这两个流别的文献源头。小说中的阿寄故事是对文集传记的敷演,史志中的阿寄传记则是对文集传记的节录。文集中的阿寄传记通过小说的敷演成故事而在普通大众之间传播,通过史志的收录而被主流意识形态接受,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二、阿寄与明代奴仆
阿寄是一位典型的义仆,其故事在明清两代广为传扬,文集、笔记小说、通俗小说、正史、地方志等不同种类的文献,都记载了他的事迹,有的还对其事迹进行了评论,这为我们从不同视角审视阿寄形象提供了文献依据。在明代奴仆史上,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明代前期的禁奴,一是明代后期的奴变。田汝成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其文集《田叔禾小集》也成书于嘉靖年间,阿寄之事是田汝成耳闻之时事,据此可知《阿寄传》当作于嘉靖年间。从现存的众多文献可知,阿寄是士大夫阶层为了特定目的树立的义仆形象,故事又正好发生在明前期禁奴与明后期奴变的转折点上,因此,阿寄为我们研究明代奴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禁奴与士人对庶民蓄奴的接受
明朝建立后,下层出身的朱元璋在一定范围内推行了禁奴政策。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颁布诏令,规定“士庶之家毋收养阉竖,其功臣不在此例”[11]。蓄奴的特权被限定在功臣这一很小的范围内。洪武三十五年(1382)颁布的《大明律》也规定:“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12]按照《大明律》规定,蓄奴的资格稍稍放宽,只要是非庶民的一般官员,蓄奴也不违法,但朱元璋禁奴诏令的基本精神在《大明律》中得到了延续。上述诏令与法令,在明初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为此,牛建强论道:“朱元璋在推行各项政令的过程中,使用铁腕,令到即行。可以肯定,其限制庶民使用奴婢的政策在当时是产生了实际效果的。”[13]
与明初相比,明中期的禁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蓄奴法令在民间被全面突破,自弘治、正德开始,“追求奢华消费的取向已成为全国带有明显整体性特征的普遍现象”,“明代中后期奴仆现象的大量化和普遍化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4]。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即使是到了嘉靖年间,庶民蓄奴依然未被官方正式接受。嘉靖年间担任过刑部郎中的雷梦麟为限制庶民蓄奴,再次强调“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15]。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庶民蓄奴的普遍性与禁止庶民蓄奴的法令之间,已经存在矛盾冲突。相对于政府近乎顽固地维护《大明律》禁止庶民蓄奴的政令,夹在政府与庶民之间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态度更能代表当时社会对于庶民蓄奴的接受程度。
根据阿寄的故事资料,可知阿寄是庶民所蓄之奴。前面所引各类记述阿寄故事的传记、小说等都出自士大夫之手,从这些文献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士大夫对庶民蓄奴的态度。田汝诚《阿寄》一文在记述阿寄之事时,说阿寄是“淳安徐氏仆也”,阿寄临死之时说道:“老奴马牛之报尽矣。”文中直言阿寄的奴仆身份,与官方文件中所载明代士庶在买卖奴仆时,往往“皆不书为奴为婢,而曰义男义女”[16]有着很大的差别。不仅如此,田汝诚还把阿寄与主人的关系,比作君臣、父子关系,在传末发表议论,说道:“夫臣之于君也,有爵禄之荣;子之于父也,有骨肉之爱……移此心也以奉其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细味田汝诚之论,徐氏蓄奴,阿寄为主尽忠似与君臣、父子关系一样理所当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元明事类钞》以及冯梦龙《徐老仆义愤成家》等文献在记述阿寄之事时,同样也对阿寄的奴仆身份直言不讳。这说明在庶民蓄奴已成为常态的明代中晚期,士大夫已接受了这种现实,与政府维护《大明律》禁止庶民蓄奴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受文人传记的影响,《吴兴备志》、《浙江通志》、《严州府志》等史志在撰写阿寄的传记时,也对阿寄的奴仆身份直言不讳,这说明士大夫漠视《大明律》禁奴条款的心态,已蔓延到主流意识形态,明初的禁奴令,到了明中期之后,已成一纸具文。
(二)奴变与理想的主仆关系
蓄奴在明中期以后成为普遍现象,奴仆的人数便会积累达到一定的规模。按照民间的约定俗成,奴仆在卖身时,“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子孙累世,不得脱籍”[17]。在奴仆与主人矛盾的推动下,发生奴变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明代奴变,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谢国桢的《明季奴变考》,吴晗的《明代的奴隶和奴变》,傅衣凌的《明季奴变史料拾补》等。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可知,奴变在明代晚期频繁发生。
实际上,早在明中期,自上而下都发生了奴变,《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宫婢肆逆”条载:“嘉靖壬寅年,宫婢相结行弑,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18]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身陷奴变之险境。宫门之外,除了有奴变之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奴仆通过经商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因此,很多奴仆在经济上已能够与主人抗衡,或者在经济实力上凌驾于主人之上,原来奴仆依附于主人的关系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冲破。主要生活在嘉靖与万历年间的管志道对此现象曾有过激烈抨击,他说:“近乃有起家巨万之豪仆联姻士流,多挟富而欺其主;亦有奋迹贤科之义孙通名仕籍,则挟贵而卑其主。”[19]奴仆傲主到明末更是变本加厉,顾炎武曾言:仆人一旦得势,“则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于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甘于毁名丧节而不顾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20]。
在明中期以后自上到下奴仆钳制主人甚至发生奴变的社会大背景下,构建理想的主仆关系,是士大夫阶层必须面对与思考的问题。阿寄作为一名仆人,其故事在文集、小说、史志广为记述传扬,实际上承载着士大夫阶层重构主仆关系的理想。各类与阿寄故事相关的文献,大部分在讲述故事时会夹杂着对主仆关系的议论。例如:
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儿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顾复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则其天定者虽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虽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谓天性者,不过测度之语;所谓读书知孝弟者,不过一时无可奈何之辞耳。奴与主何亲也?奴于书何尝识一字也?是故吾独于奴焉三叹,是故不敢名之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视我正如奴矣。”[21]
冯梦龙曰:“为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伤伦。能为义仆是良民。盛衰无改节,史册可传神……劝谕那世间为奴仆的,也学这般尽心尽力帮家做活,传个美名;莫学那样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骂。”[22]
李渔曰:“我道单百顺所行之事,当与嘉靖年间之徐阿寄一样流芳。”[23]
前文所引田汝成《阿寄》及以上议论性文字说明,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把主仆之间的关系,与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相互比照,奴仆忠于主人,就像臣子忠于君王,子女孝顺父母一样,是理所当然之事。在奴仆“背恩反噬,尾大不掉”习以为常的明代中后期,对主人忠而忘私的阿寄,被士大夫们树立成践行奴仆道德的标杆,李贽说阿寄是自己“以上人”,“彼其视我正如奴”,不是要否定阿寄的奴仆身份,而是要从道德上将阿寄无限抬高。《严州府志》、《浙江通志》以及《明史》中的阿寄本传中,虽然未在传中对阿寄之事有所评议,但史志收录阿寄传记本身就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阿寄无言的肯定,也是最高的肯定。可以说,阿寄事迹之所以广为传扬,是因为奴变频发、奴仆傲主成为常态的明代中后期,亟须一位道德上的奴仆标杆。明清两代文人在书写阿寄故事时,实际上包含着文人们重构主仆关系的理想。
三、结语
阿寄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义仆,士大夫阶层以及史志的编撰者为树立典范,使得其故事在文集、小说以及史志中广为传扬,其故事在传播中相应地形成了文集、小说与史志三个分支。此前,小说领域的学者宁稼雨在编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阿寄”条目时,将史志中阿寄故事的源头追溯到文言小说《阿寄传》,不仅有违史志编撰传统,也与文献相抵牾。事实上,明清两代所有记述阿寄故事的文献,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田叔禾小集》中的《阿寄》一文。
阿寄故事发生在嘉靖前后,多种文献中的阿寄形象,实际上是士大夫树立的奴仆道德典范。在明代奴仆史上,明初的关键词是禁奴,明末的关键词是奴变。从阿寄故事这个视角来观察明代奴仆史,可知在禁奴与奴变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士大夫阶层一方面绕过禁奴政令,已默认庶民蓄奴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主奴关系松动甚至主奴秩序颠倒的社会大背景下,士大夫希望通过树立道德榜样来维系奴仆忠于主人的关系。各种文献中的阿寄故事承载着士大夫们重构主仆关系的理想。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文学商品化与明代传记文学新变研究”【14WX2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清)稽曾筠:《阿寄传》,乾隆《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九,《四库全书》本。
[3](明)董斯张:《笄祎徴第六》,《吴兴备志》卷十三,嘉业堂刊本。
[4](明)李贽:《阿寄传》,《焚书》卷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94页。
[5](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3页。
[6](明)田汝成:《阿寄》,《田叔禾小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清)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文史通义》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3页。
[8](清)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文史通义》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3页。
[9](清)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文史通义》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8页。
[10](清)张廷玉:《阿寄传》,《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15~7616页。
[11](明)夏原吉等:《明太祖实录》卷七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352页。
[12](清)薛允升:《立嫡子违法》,《唐明律合编》卷十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13]牛建强:《明代奴仆与社会》,《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第98~107页。
[14]牛建强:《明代奴仆与社会》,《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第98~107页。
[15](明)雷梦麟:《人户以籍为定》,《读律琐言》卷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16](清)薛允升:《良贱相殴》,《唐明律合编》卷二十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595~596页。
[17]佚名:《研堂见闻杂记》,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30页。
[18](明)沈德符:《宫婢肆逆》,《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69页。
[19](明)管志道:《分别官民家奴婢义男因以春秋之法正主仆议》,《从先维俗议》卷二,《太昆先哲遗书》本。
[20](明)顾炎武:《奴仆》,《日知录》卷十三,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67页。
[21](明)李贽:《阿寄传》,《焚书》卷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94~595页。
[22](明)冯梦龙:《徐老仆义愤成家》,《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22、726页。
[23](清)李渔:《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无声戏》第十一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0页。
主持人语 这里披载的四篇论文,都不是所谓的宏观研究,而是扎扎实实地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相当成就和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展开的研究。四篇论文所涉问题各不相同,论述风格也因人而异,其观点虽不能说都是可以让学界同仁认同或接受,但都能持之有据地成一家之言。这也许就是这四篇论文最可宝贵的品格。
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的《世纪焦虑与历史逻辑——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几点启示》一文,是陈教授提供给纪念林语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该论文以较为新颖和独到的视角——世纪焦虑与历史逻辑,着重论述了林语堂对于中国文化既批判又肯定的复杂内容,较为有力地辨析了林语堂以西方文化肯定中国文化的意义、价值以及所留存的缺憾。其观点,都是从材料而出,所以,具有相当强劲的说服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由此阐述了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启示性意义,从而拓展了自己对一个具体对象研究的意义,也当然显示了作者论文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作为青年学者的云南师大孙淑芳与中南民族大学杨洁梅的论文,则很直接地显示了青年研究者的风格——敢于尝试,勇于创新。孙淑芳的论文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较为繁难的跨艺术的格局来研究鲁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与戏剧的关系,其框架及格局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列举和分析的事例不仅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而且也较为新颖。可以说是为学界从戏剧的角度来透视鲁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问题提供了自己的一家之言。杨洁梅论沈从文《边城》的论文,其中的一些观点也许学界同仁不一定认为是作者的创建,但作者在论述问题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才气,却是不能否认的,至少作为主持人,我是很直观地感受到了的,也十分欣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欣然将该文在此披载的重要原因。
许祖华的论文是一篇细读经典的论文,其细读所选择的角度是话语与修辞,其中对鲁迅《伤逝》所采用的两种修辞手法的分析,虽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但也经受得起相应的推敲,有些观点虽为一家之言,但也言之成理。(许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