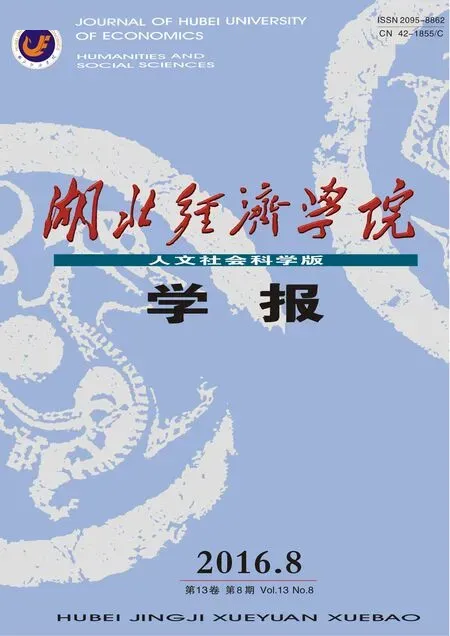文化话语权视阈下本土文化译介研究
2016-03-15张勇
张勇
(西华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南充637009)
文化话语权视阈下本土文化译介研究
张勇
(西华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南充637009)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迫切地需要走出去,并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自己的话语权。文化话语权构建离不开文化的译介。文化译介主体决定文化话语主导权,文化译介策略影响着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意识的建构,而译文的标准建立决定文化在国际上的解释力和传播效力。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译介主体、译介策略和译介标准等对于我们在全球话语环境中构建中国本土文化的话语空间、确立中国文化的话语地位等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话语权;译介主体;译介策略;译介标准
一、引言
法国思想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权决定了谈什么。掌握了对外话语权,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占据了对外交往的主动权”。[1]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权利,文化话语权的获取也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迫切地需要走出去,融入世界文化之林。然而,中国文化能走出去多远,很大程度取决于翻译的效果。[2]文化话语权在国际上的表达与阐释离不开翻译。[3]文化话语权关乎文化的实力和影响力,要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就离不开文化的译介和传播。文化译介是宣传和推广民族文化与民族价值的重要手段,是塑造国家形象,弘扬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话语权,构建异域他者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化译介就是要将中国文化翻译和推介出去,实现“文化走出去”,抵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宏伟的战略目标。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建构需要从文化译介的角度去研究。首先,构建中国文化话语权需要掌握话语主导权。在对外文化译介中,话语主导权掌握在译介主体身上,谁是译介主体,谁就控制了话语的主导权;其次,本土文化话语权的建构离不开自主文化意识的培养,在译介过程中采用怎样的译介策略更有利于文化意识的培养值得进一步探讨;另外,文化话语权的建构还必须考虑文化的传播力,接受力,加强译文的凝练,统一传播口径和翻译标准就势在必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译介主体、译介策略和译介标准等对于我们在全球话语环境中构建中国本土文化的话语空间、确立中国文化的话语地位等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二、文化译介主体与话语主导权
文化话语权的构建首先体现在文化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文化译介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掌握文化主导权有效途径之一,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译介主体地位一度旁落,纵观中国典籍译出历史,不难发现这一任务主要由外籍汉学家完成。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译介始于十六世纪末,盛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和传统经典的《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西方,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不可否认西方学者在译介中国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由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局限性或者由于译者主体立场的原因产生认识偏差,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曲解甚至歪曲,从而导致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产生偏见。要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让外国读者认识和尊重中国文化,中国学者理应承担译介中国文化的重任,只有成为文化译介的主体,才能拥有译介话语主导权。
西方人由于对非母语的文化、语言的理解很难做到全面、公正、深刻,就造成了这种总体概念的片面以至歪曲。这中间,有的是有意的,如美国某些人“妖魔化”中国,就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译介实现的,而译者在意什么,怎么译等方面有完全的决定权,中国文化的弘扬就不可能有自主权。[4]
在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然而遗憾的是,都是以外译汉为主,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推介力度远远落后于外国民族文化的汉译,中华文化在国际上一直处于话语弱势。
三、异化翻译策略与本土文化意识建构
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中,翻译起重要的作用,而翻译策略的运用将体现话语权,并对话语权的转变产生巨大的影响。[5]当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美国的Lawrence.Venuti为代表。他考察了十七世纪以来两百多年间译成英语的作品 (包括文学和非文学),认为最大问题就是过于 “流利”,“自然”、“透明”,而这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被殖民化。针对这种“归化”(domestication)的翻译策略,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一个翻译策略:“异化”(foreignisation)。他认为在英语中采用异化译法在今天特别必要,“它是对当今世界事务的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用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6]
在对外交流中,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7]在翻译实践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存在,比如中国译者将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译成中文时,采用异化策略,直译为“西风颂”,保留了西方文化中西风的文化底蕴,而在翻译许多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材料时却采用了归化策略,比如故将中国的“东风”译成“West Wind”,将中国的“济公”译成“Robin Hood”,这种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委曲求全的处理策略让中国文化丧失殆尽,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在西方文化强势霸权下,中国文化缺乏话语权的尴尬与无奈。通过文化译介,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这样才能逐渐消减西方文化霸权,打通一条由边缘向中心区扩张的通道,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对话,让东风还是东风。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一句“不折腾”的翻译引发了翻译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最初《中国日报》(英文版)将其译为“don't sway back and forth”,有趣的是后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现场直译为 “BU ZHE TENG”,而就是这个好笑的译文却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这一典型的“不折腾”翻译事例证明在对外译介时也可以“不折腾”,尽量采用直译加注的异译策略,这样在译文中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体现文化自主意识和文化自信。
为了更好地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在推介中国文化经典时,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未尝不是一种有效手段。有学者甚至认为可以在中国文化译介过程中构建能体现中国文化特性的中国英语,如果提升中国英语的水平,使之在使用规模、范围和效能上大致也相当于国际英语社会的一个正常成员,让中国英语也如同其他种类的英语,那么提高汉译英的质量、保持中国语言和文化特征、读者接受中国语言文化的宽容度也将会大幅度的提升。[8]
四、译文标准化与话语解释权
开放的中国,要实现与世界的全方位接轨,必须在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基础上,做好本民族文化的对外译介工作应系统规范翻译行为、统一翻译标准,统一对外宣传语言。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多学科人才的配合才能得以实现,但这种规范性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制定一套汉译外的规范标准,获得国际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强化本土文化术语表达的统一性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外学者对其解读也不尽相同,其译本也五花八门,数量众多。比如最能体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论语》其译本据统计多达50多种,李坤在对比了几个译本后发现其中“礼”、“善”、“德”、“信”、“贤”、“义”等核心概念词的译文也变化多样,就其“义”字而言,马歇曼译成“reason”;理雅各则为“propriety”;亚瑟.韦利则译成“ritual”,而我国学者辜鸿铭的译文则较为繁琐,他译成 “education and good manner”。[9]要构建文化话语权务必统一译文,过多的译文只会造成思维上的混乱,文化译介不畅,更何况有些译文歪曲原意,甚至诋毁中华文化。
译文标准的建立离不开翻译词典的建设。翻译词典编撰的意义在于统一译本,避免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惑。文化话语权的构建离不开翻译标准的制定,所谓制定翻译标准,指的是中文与世界各个语种之间的字、词、句的对译标准,即翻译辞典建设,这是中译外事业的基础工程,同时也涉及中文与世界主要语种之间的解释权问题,是中文在世界上话语权表现的核心部分。[10]辞典中的既是语言也是话语,而话语就是权力。[11]一般说来,双语翻译词典的编纂宗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务对象,也就是一部双语词典是为操哪一种语言的读者服务的;二是编纂目的,也就是编这样一部双语词典是干什么用的。[12]目前翻译词典多数为“内向型”双语词典,主要服务于国内读者英语学习之用。要构建中国文化话语权,就需要将中国文化译介出去,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翻译词典服务对象就不能局限于国内读者,同时也要面向海外读者。一部好的汉英词典除了提供人们学习和译介参考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我们在编撰汉英词典时应尽可能收录体现中华文化的词条。目前的翻译词典收录的词条偏少,尤其是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的收录更少,不能充分满足海内外读者学习和翻译的需要。
五、译文的凝练与文化传播效力
译文的凝练是指译文在无损意义的传递条件下用尽量少的信息符号提供准确的语义信息,做到简明扼要。比如金晓宏建议将《汉英词典(第三版)》中“相生相克”的译文“mutual enhancement and inhibition between the five elements(an ancient concept to explain natural phenomena,and later appli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etc.)”精炼为“mutual generation and restriction”,[13]不仅简化而且押韵,更有利语言文化的传播。
中华文化负载词因其概念丰富,译文表达往往繁琐冗长,但在构建中国文化话语权时,简单、凝练的译文更有利于文化传播,有必要加强文化符号的凝练,完善文化符号的表达系统。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文化话语权的构建,汉语拼音的音译词也能逐渐被世界熟悉和认可。比如将“仁”音译为“Ren”;“礼”音译为“Li”或者“Ly”,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华文化的译介和传播,促进中西文化交融。文化不是简单地将物质和精神叠加,它是基于物质和精神创造而形成的、不断传播着的符号系统。我们向来注重文化的创造而不注意文化符号的凝练,以至使文化传播缺乏明确而强烈的表达话语。没有简洁的符号,就没有强有力的表达;没有强有力的声音,就没有话语权。[14]
六、结语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实现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文化译介是必经阶段。文化译介主体决定文化译介的内容、观点和立场,文化译介策略影响着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意识的建构,而译文的标准建立决定文化在国际上的解释力和传播效力,由此,文化译事关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构建,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有必要从译者主体、译介策略、译文标准等方面加以深入研究。
[1]萨拉森.福柯[M].李红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5.
[2]李蓓,卢荣荣.中国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 急需迈过翻译坎[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08-14,(4).
[3]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
[4]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03,5(2):42.
[5]刘万生.从“不折腾”的英译看我国文化话语权的重建[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6):44-45.
[6]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History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1994.
[7]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1996,(2).
[8]傅惠生.《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英译文语言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23-29.
[9]李坤.《论语》英译困境及思考[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4):84-87.
[10]何明星.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60年[J].出版发行研究,2013,(6):31.
[11]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ColinGordoned.&trans.,Pantheon Books,1980.341-345.
[12]吴建平.双语翻译词典的编纂宗旨、释义和例证刍议[J].辞书研究,2009,(3):63.
[13]金晓宏,《汉英词典(第三版)》中汉语文化特色词汇处理不足评析[J].黑河学院学报,2015,(3):89-93.
[14]王保国.加强文化传播提升文化话语权[N].河南日报,2015-05-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