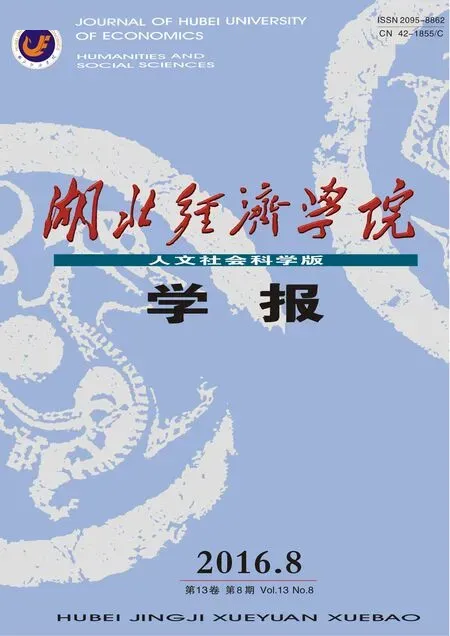爱伦坡作品中的女性空间表征
2016-03-15李望华
李望华
(广东东软学院 英语系,广东 佛山 528225)
爱伦坡作品中的女性空间表征
李望华
(广东东软学院 英语系,广东 佛山 528225)
空间从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容器,空间的中立性也只是幻觉。空间是权力、意识形态的生产对象。爱伦坡的作品中,男权社会的女性空间是脆弱的,危险的,女性对空间没有控制权;男性在空间表征为女性树立了美的标准,对女性产生压倒性的规训作用,凡不符合该标准的女性便受到男权无情的放逐;男权的压迫激起了女性的反抗,女性从身体的夺取,开始了空间的夺取,最终摧毁了象征整个男权的城堡。
爱伦坡;女性;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
19世纪初叶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为世界贡献了经典的侦探小说、悬疑恐怖小说,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很多处于死亡、恐怖的处境之中,带有鲜明的特色,显示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有研究者发现其作品中的女性集体失声,[1]很少能听到女性的对话;有研究者发现其不同的女性形象代表了不同的女性向度如:永恒的精神美的象征、被客体化女性和反抗抗争中的女性。[2]但显而易见,爱伦坡笔下女性的境遇是悲惨的,她们是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命运反映。本文运用空间理论,分析爱伦坡作品中女性与空间的关系,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空间占有、空间再现和为自身空间而做的抗争。
一、空间的生产
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代人文研究领域经历了“空间转向”。空间或空间性不再只属于几何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它变成了人文研究的热点。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斐伏尔和福柯为这次空间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列斐伏尔继承了传统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生存——实践论哲学和福柯的权力哲学关于空间的论断。结束了空间作为空洞的、中立的事件发生的容器的历史,挖掘了空间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传统认识论依据二分法把空间分为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使出现在研究者视域中的空间陷入容器化、空洞化和同质化。马克思主义通过确立人类实践的本源性宣告了作为天真自然的消亡,揭示了所有的自然都是“人化的自然”,[3]是人类实践的产物。福柯指出空间是权力角逐的场域,是权力显现的手段和权力生产的结果。
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辩证法。空间不再仅仅作为生产的空间,即不再仅作为各种物质和社会生产的容器而出现,空间自己成为被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权力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对象。他摒弃了传统认识论对空间分析的二元对立,因为简单的二元对立所确立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不能全面描述空间的复杂性,他辩证地引进了第三项,以消除空间研究中主客观等二元对立对空间的简单分割和处理。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空间被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实现了空间研究的主观和客观、物质性与精神性、感知与想象的统一。
空间实践强调空间既作为空间中的物质生产的容器,也作为生产实践的对象的空间。空间是社会生产、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产物。空间表征强调观念性和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空间。表征空间是实践主体在实践中生产出来的空间,它是物质性的空间、也是具有社会性的抽象空间、可以是被主体感知的心理空间,既是人类实际生存于其中的空间,也是体验性的、想象性的空间。[4](P38-39)
文学实践不可避免地生产了空间,在文学中同样可以发现三个层次的空间。文学所生产的空间充分显示了社会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对空间的生产。在爱伦坡的作品中,空间的生产与男权社会联系紧密,从这个视角出发,分析女性的空间占有称为可能。
二、女性的空间实践:失落的空间拥有
男权社会用法律和道德等手段规定了男性在选举权、经济权等方面的特权,女性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出现的。女性则被剥夺了选举权、财产权。在男权社会,在肯定男性特权的同时也赋予了男性对空间的无限掌控。马克思强调“自然的人化”已经使自然变成“人化的自然”,在爱伦坡小说中出现的自然景观、人文建筑等景观无不打上男权的烙印。
在爱伦坡的作品中,打上男权社会标志的男权空间是稳定的、坚固的、安全的。作为男权的空间出现的是诸如城堡、监狱等。城堡是一个一个的实体,体现的男权社会男性的主体间性,而没有给女性留下空间。城堡以对周边的池塘、道路的占有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如在《厄舍府的倒塌》中,厄舍府的形象极大地传染给了周遭的树林、池塘。厄舍府看起来是衰败的,树林和池塘也是颓败的;厄舍府是阴森的,它旁边的树林就不能是明媚的;厄舍府是冷酷的,它旁边的树林和草地就不能是温暖的。
同时,女性的空间就是变动的,脆弱的,危险的。在《莫格街杀人案》中,母女居住在四楼。虽然表面上是安全的——当侦探去查看现场时,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完好无损,但当真相大白时,才发现她们的空间很容易被侵入。一只黑猩猩爬上树梢就轻而易举地推开窗户,闯进了她们的生活空间,对她们实施了致命的袭击。女性空间的脆弱性可见一斑。
男权空间对女性身体实行圈限。女性作为财产的一部分是不允许其他男性侵犯的。其他人对女主人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看。在《人约黄昏后》中,就算女主人出了事故,非常悲伤,别人也不能走近去安慰;男青年走近女主人意在安慰也被认为是逾越礼仪的事,是大逆不道的事。城堡里的女主人没经过允许,是不可以走出城堡的。她只能通过极端的手段,如把让孩子掉进水里,来获得与心爱的人会面的机会。城堡对面是监狱。显然是宣示男权的存在。男权为了显示自己对空间的把控,必须把不利于自己的人关进监狱,以展示自己对权力的维护。而女主人的情人正是从监狱方向来的,他既是作为男权的敌人出现的,也表现了打破男权对女性的控制愿望。
男性对空间的绝对拥有和支配,使女性的空间局限在闺房。在爱伦坡的小说中,女性极少出现在空旷的自然,广场,集市中。女性被限定的社会角色不是在社会上为他人提供服务,因此她们只能委身在闺房,作为家族延续的工具。而对于男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空间——闺房,女性也没有掌控权力。如在《丽姬娅》中,罗维娜的婚房设计装饰都是丈夫来负责,都是装饰城丈夫喜欢的样子,不管她喜不喜欢。女性对空间拥有实现不了。为了获得男性的肯定,莉姬亚要进入男性空间——丈夫的书房用她甜美的嗓音来愉悦自己的丈夫——向男性献媚,来获得男性的肯定。
男权用对空间的分配,确立的物件位置来管理自己的领域,显示自己的权威。女性也被当作物件,被分配了位置,在从生到死的时间序列里,都有明确的位置,以便于男性的管理。如《厄舍府的倒塌》中,“我”虽然进入了城堡,但轻易看不到主人的妹妹,只有经过主人的允许,才有可能看到女性从自己的房间出来。她基本不出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就是便于男权凝视观察的对象。而她死后,被放入早就建好地窖,这里曾经是地牢,体现着权力的管控。位置,赋予了男性和女性观察和被观察的关系,监视和被监视的关系。男性可以在任意观看女性,而女性则不行,她处于被观察的中心。在爱伦坡的小说中如《丽姬娅》中的罗维娜、《厄舍府的倒塌》中的玛德琳,女性经常会被放置于棺木中,成为献给男权的祭品。女性死后的空间都处于男权的掌控与规划中,棺木就是祭坛,女性的身体被置于祭坛,作为向男权献媚的最后物件存在。
三、男权对女性的空间表征:压迫的源头
男权对女性的空间表征指男性对女性的想象空间。在爱伦坡作品中很少出现对女性自己的想象的描写,这本身即是男权社会压迫的表征之一。有分析指出女性在其作品中很少发声,或者发了声,也会因其对男权的忤逆而遭到男性的报复。如在《黑猫》中,妻子因指出黑猫胸口的白色毛像十字架,提醒丈夫因杀死第一只猫而带来的罪恶感,最后竟被丈夫“无意”锤杀。发声尚不可能,女性的想象就只能沉默在历史的角落,连进入文学描写的可能都没有。
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的空间表征中只存在符号化的女性。被符号化的女性,即按照男性的审美标准塑造的女性。如在《莉姬娅》中,莉姬娅被比喻成塞壬海妖[5]一样,她具有塞壬海妖的美貌和智慧、具有超越世人无所不至的能力,但完美的女性只是符号化的女性,只能存在于神话中,完美女性作为符号弥散在男权社会。从存在意义上,具有生命多维度特征的真实女性消亡了。
作为整体的女性只是作为男性凝视和观看的目标存在于男性的空间表征中,即男性的想象空间中,以满足男性凝视和观看的欲望。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的爱好、需求都不在男性的关注之中,男性关注的是他们想象空间中的女性。如在《椭圆形画像》中,作为丈夫的画家关注的是画布上的美女,对作为模特的妻子的反而视而不见。作为模特的妻子只能被作为个体的男性丈夫观看,而存在于画布上的妻子可以为整个男权的凝视目标出现,妻子被作为向男权献媚的牺牲品了,在画作完成的刹那,妻子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在男性对女性的空间表征中,男性定义了所谓完美女性的标准,即按照男权要求存在的女性。如在《丽姬娅》中,丽姬娅成为了完美女性的象征。她的长相是古典美的代表,她的头发像风信子,眼睛像星座那样明亮、像德谟克利特的井那样神秘。此外,她还求真。小说中她熟知天文、地理,学识广博;其写的诗表达了对人性的关怀。[2]但在小说中的开篇,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叙述者称自己不记得自己在何时与丽姬娅第一次见面,甚至不记得她的姓氏,这种不可靠的叙述策略显示丽姬娅是“叙述者”虚构的一个人物,因为深爱一个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何时与女性第一次接触,还有她的姓名呢?因此可以认为丽姬娅只是叙述者想象的结果,他在想象中罗列了男性对女性完美的定义。
男性定义的完美女性标准用其唯一性、权威性抵制任何女性个性化美的追求。男性希望现实空间中的女性都像自己想象空间中的女性那样完美。想象空间的美的标准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尺。一旦这个标尺树立,则拒绝所有个性化的、或有缺陷的美的表达。所以丽姬娅死后,“我”虽然娶了罗维娜为妻子,但因其在审美趣味、知识水平上的缺陷,而受到丈夫的无情虐待,连正常的夫妻之事也被“我”觉得恶心。最终等待罗维娜的只有死亡。罗维娜就是女性美的标准的牺牲品。
男性定义的完美女性标准对所有女性有强制性的规训要求,达不到则会遭受惩罚。在《贝雷尼丝》中,“我”一开始是喜欢贝雷尼丝健康美丽的形象,喜欢“梦中的贝雷尼丝”,她是男性“分析的对象,深奥思考的对象”;而一俟疾病衰老改变了女性,女性便被男权贴上丑的标签,得到男权极端的惩罚——被活埋。厄舍府主人的妹妹,同样逃不过被活埋的命运,原因也是不知名的疾病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特征,使其不再具有女性的活力。男权只接受以完美标准存在的女性,这种标准对女性的残害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女性的表征空间:为空间、生存而抗争
表征空间不仅指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用的物理的空间,而且指女性可以感知的抽象社会空间、生存空间。在男权社会,女性的社会空间、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然而,女性也逐渐意识到只有自己抗争,才能确保自己的社会空间和生存空间。
女性的反抗开始于对自己命运的清醒认识。然而,女性在男权社会基本是无法发声的,历史听到的女性的声音少之又少。男权社会把诸如《椭圆形画像》这类的画像放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下,让女性受压迫的事实变成男性社会秘而不宣的阴影。而且,男权社会还通过叙述来加强对女性的压迫。在《椭圆形画像》画作的旁边,附有小册子介绍的成画过程,本意是宣扬男性画家的专业性,通过宣扬成画过程中的异事来增加画作的价值。但男权的叙事也为颠覆自己埋下了伏笔。“我”通过把蜡烛移动位置,使光明照见了处于阴影中的画像,象征着寻求光明的理性究竟会把深藏在阴影中的女性命运展示出来;关于成画过程的叙述也让女性命运大白于天下,让女性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里得以现身,从而达到教育女性的目的。
生命和死亡是自然界不可违抗的秩序,女性通过打破这个线性秩序宣示女性的反抗能力。女性争取自身空间的战斗开始了,她们的武器之一就是她们的坚强意志。在《丽姬娅》中,丽姬娅临死时说:“只有意志薄弱者才会死去”。宣告女性意志作为反抗武器的诞生。丽姬娅的第一个身体虽然消逝了,但她强烈的求生意志,让她从罗维娜的身体中复活。让代表男权的“我”大感惊骇,女性凭借强力意志,反抗男性社会为自己设定的命运和秩序,通过颠覆时间的线性秩序达到了颠覆男权的统治的目的。
女性通过对身体的夺取,来宣告对男权的反抗的开始。勒菲弗尔指出:“身体是空间的起点。有了对身体的支配的前提,才有对空间的掌控的可能”。[4](P405)身体是空间坐标的起点,没了身体,对空间的掌控也不可能。丽姬娅正是通过对罗维娜身体的夺取,发表了自己对空间夺取的宣言。
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从丽姬娅复活开始,在厄舍府的倒塌中达到顶峰。厄舍府是个古老的城堡,是封建男权的象征,这里女性的空间处于受监视的地位,女主人的社会空间受到挤压——玛德琳不知道有来客,也不出面招呼来客。作为女主人的玛德琳被男性活着放进了棺材,放在了象征男权大厦的奠基处——地下室,放上了男权的祭坛,但她凭自己顽强的意志,打碎了棺材的盖子,勇敢地冲上楼,敲开了男权中心的大门。从表征空间上看,玛德琳从地基处开始破坏整个男权大厦,具有足够的震撼力。象征男权大厦在玛德琳的反戈一击中轰然倒塌。把厄舍府连同周边的池塘和绿地都一起撼动了。男权的表征空间被彻底破坏了。
五、结语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空间实践方面,在男权社会,男性主宰了空间占有和支配,女性被当成物件分配到固定的位置,方便男权的管理;女性的空间是脆弱的,缺乏安全感。而男性则在空间表征里为女性树立了美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确立,就对女性产生压倒性的规训作用,凡不符合该标准的女性便受到男权无情的放逐。男权的压迫激起了女性的反抗,女性从身体的夺取,开始了空间的夺取,整个象征男权的城堡被女性从根基处摧毁。
空间从来就不是仅仅作为事件发生的容器而出现的,空间的中立性也只是幻觉,同质化、空洞化的空间是不存在的。从马克思宣布只存在人化的自然,纯粹的自然已经消亡开始,作为权力、意识形态生产对象的空间就进入人的视野,一部空间史就是就是权力、意识形态角逐的历史。[6]
[1]Weekes,Karen.Poe's feminine ideal[A].In Kevin J.Hayes(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gar Allan Po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48-162.
[2]李显文,刘立辉.爱伦·坡小说中“美女”的多元身份解析[J].外语教学,2014,(6):7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131).
[4]H.Lefebvre.The ProductionofSpace[M].Oxford:Blackwell Press,1991.
[5]Jones,Daryl.E Poe's Siren:Character and meaning in Ligeia[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83,(20):33-77.
[6]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与权力.夏铸九主编: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M].台北:明文书局,1998.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