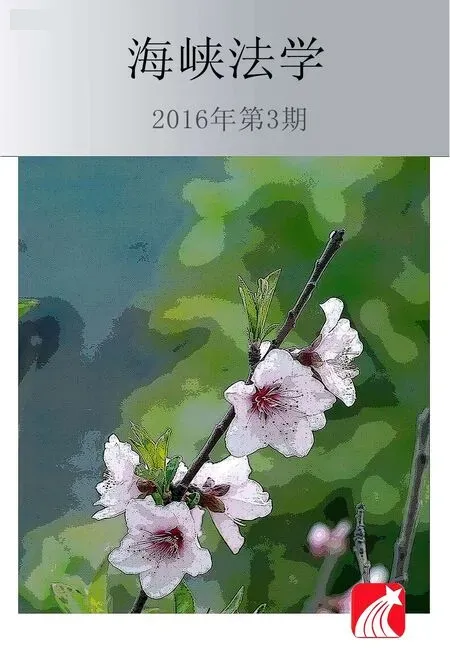连带债务成立规范之逻辑结构
2016-03-15游进发
游进发
连带债务成立规范之逻辑结构
游进发
数债务是否基于同一原因而发生?数债务人中之一人是否负有最终责任,均无法用以区别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反而将应是连带债务者评价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在连带债务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规定为发生要件之脉络下,这项评价矛盾,将显得更尖锐。不仅当事人出于担保债权的目的,而约定连带债务,立法者亦考量到,的确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而制定法定连带责任。连带债务成立规范逻辑结构,乃数债务间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是以规范设计上,势必以同一给付目的、各付全部给付之责作为连带债务之发生要件;以债权人得向各债务人请求全部给付作为法律效果。如此之规范设计,方处在理性之结构之中。
连带债务;连带保证;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不真正连带
一、问题提出与背景
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这条规定之逻辑结构,包括命令(Imperativtheorie)结构与规定(Bestimmungstheorie)结构,①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1975, S. 235 f.; Karl Engisch,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n Denken, 1997, S. 19.简要说明如下:其一,立法者以损害作为构成要件,以损害赔偿义务作为法律效果,不仅合于逻辑,亦合于理性:损害既然发生,则填补损害,不仅可避免损害继续扩大,亦只是恢复原来之状态而已;其二,以行为人之侵权行为作为构成要件,以行为人作为损害赔偿责任主体,是合逻辑与理性:谁行为,便由谁负责,是行为责任之表现;以具有过失之行为人作为构成要件,以行为人作为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不仅合逻辑,亦是理性之要求:任何人只对能预见之自己行为之结果负责。
对任何法律人而言,以上关于“民法”第184条第1项前段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逻辑结构之说明,乃再当然且熟悉不过者。至于连带债务成立规范呈现出如何之逻辑结构?对一些法律人而言,这项问题恐怕显得有点陌生或不太容易掌握。既然于人民法律生活中常发生连带债务,许多重要之法定责任,同时亦是连带责任,例如“民法”第28条所规定之法人与代表人连带侵权责任,以第188条所规定之受雇人与雇佣人连带侵权责任,②林诚二著:《债法总论新解:体系化解说(下)》,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47页。则连带债务成立规范逻辑结构之呈现,恐怕并非只是纯粹理论上之想象而已,而是尚迎合实务之现况与发展。
台湾地区“民法”第272条第1项规定:“数人负同一债务,明示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为连带债务。”同条第2项规定:“无前项之明示时,连带债务之成立,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但《德国民法》第421条第1项第1句规定:“数人负一债务,且各应为全部给付,但债权人仅享有一给付债权者(连带债务人),债权人得依己意,请求各债务人为全部或一部之给付(Schulden mehrere eine Leistung in der Weise, dass jeder die ganze Leistung zu bewirken verpflichtet, der Gläubiger aber die Leistung nur einmal zu fordern berechtigt ist(Gesamtschuldner), so kann der Gläubiger die Leistung nach seinem Belieben von jedem der Schuldner ganz oder zu einem Teil fordern)。”比较以上两条条文后可知,《德国民法》前揭规定“负一给付义务(Schulden eine Leistung)”之文义,①MünchKomm/Bydlinski, § 421 BGB, Rn. 5.与“民法”第272条规定“同一债务”之文义,两者明显不同。这两条法条之歧异恰恰说明,至少从比较法的观点而言,连带债务成立规范逻辑结构之呈现,乃有必要从事之活动。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56年台上字第 1426号判例:“保证债务之所谓连带,系指保证人与主债务人负同一债务,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连带债务之文义参照观之甚明。故连带保证与普通保证不同,纵使无“民法”第七百四十六条所揭之情形,亦不得主张同法第七百四十五条关于检索抗辩之权利。”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66年度第7次民刑庭总会会议决议(二):“某甲由某乙为连带保证人,向某丙借贷新台币数万元,未定返还期限,某丙未向某甲催告,迳向某乙诉请返还本金及利息,按某乙为连带保证人,即属‘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所称之连带债务人,某丙自得直接对之为返还之请求,且某丙既已对其起诉,亦应认其起诉为催告,且截至第二审言词辩论之日止为时又逾一月以上,是其请求核与‘民法’第四百七十八条之规定,并无不合。”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于上开则判例与决议中均认为,连带保证不仅是保证,亦是连带债务,即连带保证人无论如何均无先诉抗辩权。②刘春堂著:《民法债编各论(下)(修订版)》,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88页。尽管保证债务与主债务的发生原因并不相同,即前者发生原因是保证契约,后者发生原因是主契约,但两者给付利益却具有同一性,亦即保证债务与主债务内容相同。既然连带保证亦是保证,③台湾地区“高等法院”2006年上易字第131号民事判决:“查连带保证系指保证人对于债权人约定与主债务人连带负担债务履行而为之保证,即无补充性之保证,台湾地区‘民法’保证契约为不要式,则连带保证之约定,亦为不要式,然须有明示之意思表示,即准用‘民法’第272条连带债务之规定,本件上诉人既未明示表示其负连带保证之责,即不得以其未否认,而推断其应负连带保证之责。”则由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上开见解可推论出,“民法”第272条关于连带债务成立要件之规定,其所指之同一债务,包括同一内容,但不同原因之债务。但从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以上说明似乎无法认知到,数人基于不同原因,负有同一内容之债务,仍然可成立连带债务之理由。这则问题之答案,关键点在于连带债务成立规范之逻辑结构。基于以上种种理由,本文研究连带债务成立规范之逻辑结构。
二、“同一债务”取代“一债务”
如同前面说明,“民法”第272条第1项规定的“负同一债务”文义,不同于《德国民法》第421条第1项第1句规定“负一给付义务”文义。单从字义上来看,“民法”第272条第1项规定的适用范围,较《德国民法》第421条第1项第1句规定为广。但德国法律人在此间,并未贯彻其总是遵守文义之态度。以下首先说明德国法文献现况,包括德国通说见解,以及《德国民法》第421条规定选择以“数人负同一债务”取代“数人负一债务”,作为连带债务成立规范要件之理由。
(一)共同目的观作为连带债务成立的判断标准
依德国学界通说④MünchKomm/Bydlinski, § 421 BGB, Rn. 5; Bamberger/Roth, § 421 BGB, Rn. 5, 7. Stam, NJW 2003, 2940.与德国联邦法院见解,⑤BGH, NJW 1965, 1175; 2003, 2980.纵使数人并非负有一给付义务,而是基于不同原因,各负有一给付义务,但其中任何一项给付义务之履行,均满足债权人之给付利益者,亦成立连带债务。换句话说,是否成立连带债务?这则问题之答案,不再仅限于数人负一项给付义务,而是取决于能否满足同一给付利益。依通说见解,是否成立连带债务,因此与数人所负债务是否出于同一原因,并无关联。①MünchKomm/Bydlinski, § 421 BGB, Rn. 5; Bamberger/Roth, § 421 BGB, Rn. 4.判断满足债权人同一给付利益与否的标准,乃数人各自债务于目的上是否共同(Zweckgemeinschaft)。
但也有从目的共同的判断标准中再区别出同一位阶(Gleichstuftigkeit)②Stam, NJW 2003, 2940, 2941.之判断标准。德国联邦法院实则并不兼采两项判断标准,而是只采目的共同之判断标准,同一位阶在其判决中顶多只具有辅助的判断标准意义③BGH, NJW 2003, 2980.:“部份文献与判决否认成立连带债务关系,其考量在于,依据不同之建筑契约,并不存在着共同目的。在排除瑕疵义务方面,亦无法确认存在这项关系。其他部份文献则基于指向任何一方当事人之瑕疵担保请求权,乃为实现同一目的,而肯认成立连带债务关系;它们乃同位阶。后者正确(Ein Teil der Rechtsprechung und Literatur verneint ein Gesamtschuldverhältnis mit der Erwägung, es fehle angesichts der unterschiedlichen Bauverträge an einer Zweckgemeinschaft. Diese lasse sich auch nicht im Hinblick auf die Verpflichtung zur Beseitigung der Mängel feststellen. Ein anderer Teil bejaht ein Gesamtschuldverhältnis mit der Begründung, die gegen jeden der beiden Unternehmer gerichteten Gewährleistungsansprüche dienten demselben Zweck; sie seien gleichstufig. Letzteres trifft zu)。”
将二则德国联邦法院判决涉及到的事实简化如下:其一,建筑师甲与乙订定关于A屋建筑蓝图与监工之承揽契约,建商丙与乙订定建造A屋承揽契约,建造完成后之A屋具有瑕疵,甲之建筑蓝图或监工工作与丙之建筑工作,均是这项瑕疵之发生原因,甲与丙就瑕疵亦均有过失,因此对乙各负有瑕疵损害赔偿义务,德国联邦法院将这两项出于不同承揽契约之赔偿义务,观察成具有共同目的,④BGH, NJW 1965, 1175.均满足定作人之同一给付利益(赔偿建物瑕疵),应成立连带债务;其二,甲建商与乙订定建造A毛坯屋(粗坯屋)之承揽契约,丙与乙订定A毛坯屋之抹灰工程,A毛坯屋具有瑕疵,甲与丙之工作实施亦是这项瑕疵之发生原因,甲与丙就此均有过失,因此对乙各负有损害赔偿义务。德国联邦法院将这两项出于不同承揽契约之赔偿义务,观察为出于共同目的(填补定作人之瑕疵损害),均是瑕疵损害赔偿义务,处在同一位阶上,两项义务应具有连带义务。⑤BGH, NJW 2003, 2980.
关于作为连带债务成立要件之一的“同一债务”要件,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度台上字第2003号民事判决:“‘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数人负同一债务,明示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为连带债务。无前项之明示时,连带债务之成立,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连带债务之成立,以明示或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又连带债务,系指数债务人以共同目的,负同一给付之债务,而其各债务人对债权人,均各负为全部给付义务者而言。”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这则判决中认为,“同一债务”乃指数债务人各自之给付义务,具有共同目的,明显受到德国通说见解(共同目的说)影响。实际上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不仅在这则判决中,以共同目的说理解“同一债务”要件,在其早期判决中,亦采这项理论。⑥同样采共同目的说者,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16焱页;孙森著:《民法债编总论(下)》,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864页;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600页;杨淑文:《论连带保证与连带债务——“最高法院”1999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一五号民事判决评释》,载台湾地区《法学杂志》第25期,第30页;王千维:《论可分债务、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上)》,载《“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2年第7期,第41页。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90年台上字第 1617号判决即谓:“连带债务,系指数债务人以共同目的,负同一给付之债务,而其各债务人对债权人,均各负为全部给付义务者而言。而不真正连带债务,系指数债务人,以单一目的,本于各别之发生原因,负其债务,并因其中一债务之履行,而他债务亦同归消灭者而言。两者并不相同。”学界通说亦以作为德国通说的共同目的理论,判断连带债务之“同一债务”成立要件。但德国联邦法院当初为何采取如此偏离文义之见解?通说基于何等理由,赞成这项明显偏离法条文义之结构?文献上并未有任何详细说明。实则解决这项问题,关键点在于“民法”第421条规定之中,拟于以下说明之。
(二)担保债权实现的需求作为规范脉络
越多债务人对同一债务负责,亦即以全部财产供强制执行,债权的实现便显得越容易。连带债务的成立,具有担保债权的作用。“民法”第272条的立法理由明白表示,相较于单数债务,连带债务是以数人的全部财产来担保债权的制度,更能实现债权,其谓:“查《大清民律草案》第四百八十三条理由谓连带债务者,使各债务人各独立负有清债全部债务之义务,使债权人易于实行其权利也。此项债务,只须债务人中之一人富有资产,其他债务人虽系无资产者,亦得受全部之清偿,便利实甚。各国立法例皆公认之,故本法亦采用焉。”不仅当事人往往出于担保债权的目的,而约定连带债务,立法者亦考量到,的确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而制定法定连带责任。例如立法者考量到,一般而言,未成年人与受雇人较无资力,实际上往往无法填补全部损害,于是分别将其法定代理人与雇佣人规范成连带损害赔偿债务人,使损害较能获得全部填补。
依台湾地区“民法”第748条规定,数人保证同一债务者,除契约另有订定外,应连带负保证责任。这条规定的立法理由:“查《大清民律草案》第八百七十一条理由谓保证债务人有数人时,其保证人有分别之利益,即非其担负之部分,不任其责,此多数之立法例也。然本条为巩固保证之效力起见,保证人有数人时,均使其为连带债务人而任其责,排除分别利益之抗辩,只保护债权人之利益。但契约另有订定者,仍应从其所订定,此又不易之理也。故设本条以明示其旨。”从这条规定的立法理由可以了解到,立法者确实着眼于强化担保债权之需求,而将共同保证人之保证债务规定成连带债务。
台湾地区“民法”第187条规定之立法理由:“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之经济状况,少有能力足以赔偿被害人之损害。若不及其法定代理人,实难达到本条立法之目的。为期更周延保障被害人之权利,爰修正第三项增列‘法定代理人’,使其经济状况亦为法院得斟酌并令负损害赔偿之对象。”这项立法理由虽然是针对同条第3项而设,但在其中明白提到的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通常较无资力,难以全部填补被害人之损害。况且同条第3项之设定,原即在于顾及未成年人通常无资力之情形。“民法”第188条规定之立法理由:“谨按受雇人因执行职务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雇佣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盖因故意或过失加害于人者,其损害不问其因自己之行为,抑他人之行为故也。然若雇佣人对于受雇人之选任及监督,已尽相当之注意,或虽加以相当之注意,而其损害仍不免发生者,则不应使雇佣人再负赔偿之责任。故设第一项以明其旨。雇佣人对于受雇人之选任及监督,已尽相当之注意,或纵加以相当之注意,其损害仍不免发生者,得免赔偿之责任固矣,然若应负责赔偿之受雇人,绝对无赔偿之资力时,则是被害人之损失,将完全无所取偿,殊非事理之平,此时应斟酌雇佣人与被害人。故设第二项以明其旨。雇佣人赔偿损害时,不问其赔偿情形如何,均得于赔偿后向受雇人行使求偿权,盖以加害行为,究系出于受雇人,当然不能免除责任也。故设第三项以明其旨。”本条第3项规定,亦是为妥当评价受雇人通常无资力赔偿之状况而设。其立法理由即明白表示出这点。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56年台上字第 1426号判例:“保证债务之所谓连带,系指保证人与主债务人负同一债务,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连带债务之文义参照观之甚明。故连带保证与普通保证不同,纵使无‘民法’第七百四十六条所揭之情形,亦不得主张同法第七百四十五条关于检索抗辩之权利。”连带保证不仅是保证,亦是保证债务与主债务连带之债务,只是保证人并无先诉抗辩权。保证具有担保债权实现之结构,其与主债务连带之结果,乃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保证的担保作用因此更加受到强化。而这点亦可证明,连带债务担保债权实现之功能,不仅发挥在数人以其全部财产供强制执行,当其与保证相结合时,还表现在保证人不得主张先诉抗辩权。
从以上说明可以了解到:其一,无论是依法律规定或依当事人意思成立连带债务,其目的通常在于,透过连带债务的产生,以全部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担保债务的履行,换句话说,不论是在法定或约定连带债务中,都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的需求;其二,在前揭法定连带债务与连带保证等情形,均是“数人负同一债务”,而不是“数人负一债务”,其目的均在满足债权人的同一给付利益,是以不仅数人因同一契约负一债务时,才可能存在着担保债权的需求,数人因不同原因各负有一债务,但目的均在满足债权人同一给付利益时,亦通常存在着这项需求。
德国立法者在其《民法》第421条规定使用“数人负同一债务”,而不使用“数人负一债务”的文义,以及德国通说选择偏离《德国民法》第421条第1项第1句规定“负一给付义务”文义,而采取满足债权人同一给付利益的标准,均是考量到,在数人因同一契约负一债务,以及数人因不同原因各负有一债务,但目的均在满足债权人同一给付利益的情形,都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的需求。“数人负一债务”文义的适用范围过于狭隘,根本无法顾及在后之情形存在着这项需求,只有“数人负同一债务”的文义,才能兼顾这两种情形。
三、全部给付之责的双重角色——要件与法律效果
如前所述,台湾地区“民法”第272条第1项规定与《德国民法》上关于连带债务之成立,均以“数人负同一债务”为要件。依命令理论,连结这项要件之法律效果,必须以义务之形式呈现出来。依规定理论,一旦某条规定之要件实现,即适用该条规定,发生法律效果。但并非以任一项义务作为法律效果,并非以任一项要件连结任一项法律效果,即符合命令理论与规定理论之要求。解决以何等义务作为法律效果,以及以何等法律效果连结何等要件之问题,如同前面说明,必须在合乎逻辑与理性之前提下为之。
数人无论基于同一原因或不同原因——或依法律规定或依约定——而负同一债务之情形,通常发生在担保债权实现需求之脉络底下。既然如此,立法者必须选择具担保债权实现作用之义务作为法律效果,否则无法达到这项目的,否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理。进一步有待解决之问题,乃何为具有担保债权实现作用之义务?数人负有同一债务时,规范设计上可能使其负全部给付之责,亦可能使其只负有比例之责,若以比例之责作为要件与法律效果,则无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产生担保债权实现之作用,因为这项作法无异使各债务人只负一部分给付责任,从而债权人是否取得全部给付利益,反将因此陷于更不确定之环境中,债权人此时将必须承担更多位债务人之信用风险,但却不一定更能取得全部之给付利益。于是,其他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选择,只能是且应是数人各负全部给付责任。
以全部给付义务同时作为要件与法律效果,并不致加重债务人的责任,其理由在于:只要连带债务的成立以全部给付义务为要件,债务人只负一部分给付义务的情形,便不可能落在连带债务成立规范的适用范围内;债务人原本就负全部给付义务,使债权人得向债务人中之一人或数人或全体,请求一部或全部给付,亦不致在此间发生不当得利;不论是单数之债的债权人,抑或是复数之债的债权人,原本便得向债务人请求一部分给付(“民法”第318条)。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度台上字第511号判决即谓:“为一部请求者,就实体法而言固得自由行使该一部债权,惟在诉讼法上乃为可分之诉讼标的,其既判力之客观范围仍以该起诉之声明为限度,且只就该已起诉部分有中断时效之效果。从而因一部请求而起诉之中断时效,并不当然及于嗣后将其余残额扩张请求之部分。”
连带债务成立规范的每一项要件与法律效果,莫不是以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作为内涵。数人负同一债务、各负全部给付之责(要件),以及债权人得向债务人一人、数人或全体,请求一部或全部的给付(法律效果)。这些要件与这项法律效果均承载着担保债权实现之意旨。于是,数人负同一债务这项要件,必须配合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之要件,而这两项要件则必须以请求全部给付为法律效果,也唯有如此,始能达到担保债权实现之目的,始是合理之立法。
四、连带债务之成立
依台湾地区“民法”第272条第2项规定,连带债务之成立,限于当事人明示与法律规定之情形。但《德国民法》并未以当事人明示与法律规定,作为连带债务之成立要件。而且如前所述,德国通说选择偏离《德国民法》第421条第1项第1句规定“负一给付义务”文义,而采取满足债权人同一给付利益之判断标准。是以德国联邦法院在涉及连带债务之裁判中,往往必须进行是否构成同一给付利益之判断活动。至于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关于连带债务之裁判活动,大多集中在解决当事人间是否与如何成立明示连带债务等问题。以下研究之重点首先在于,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关于是否成立与如何成立明示连带债务之裁判,其次则是最高法院在“同一债务”之前提下所承认之连带债务。
(一)明示连带
德国联邦法院与学界通说肯认成立连带债务的情形,并不在少数①MünchKomm/Bydlinski, § 421 BGB, Rn. 5.。其原因或许在于,《德国民法》并未将连带债务之成立,限定在以法律规定或当事人明示作为发生原因。基于这项比较法上之差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于类似上开德国联邦法院判决所涉事实之事实中,作出仅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判断。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台上字第1402号判决:“学说上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指数债务人以单一目的,本于各别之发生原因负其债务,因其中一债务之履行,他债务亦同归消灭。故若不真正连带债务人中之一人所为之清偿,已满足债权之全部,对债权人即应发生债绝对消灭效力,债权人自不得再向他债务人请求清偿。故系争工程之监造虽有因投标厂商未尽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造成承包商未依图说施工,并溢领工程款,应依委任法律关系负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责任,惟应受两造最高赔偿总额约定之限制。”于是,亦即因台湾地区“民法”第272条第2项规定,将连带债务的成立限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明示之情形,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关于连带债务成立与否之裁判活动,便只可能集中在探求当事人间是否有成立连带债务之明示意思。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98年度台上字第1322号判决:“数人负同一债务,明示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为连带债务。‘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项定有明文。故只须数债务人就同一债务明白表示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即为连带债务人,至契约当事人之称谓有无表明为‘连带债务人’,与连带债务是否成立无关。”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这则判决中表示,当事人间是否成立连带债务,并不须明白表示出“连带债务”四字②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台南分院2004年度上易字第96号民事判决。,但无论如何必须明白表示出,数债务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之意义。这项当事人意思之解释结果,实属妥当,其理由在于:其一,人民并不见有精确使用法律语言之能力;其二,既然数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同时具有连带债务成立要件与法律效果之双重意义,当事人单以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之明示表示,即已完全带出连带债务之意思。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3年度台上字第1262号判决:“‘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数人负同一债务,明示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为连带债务。无前项之明示时,连带债务之成立,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是以,和解同意书并未记载债务人应就债务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意旨,则能否谓债务人应对之负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应叙明债务人就该债务应负连带清偿责任之法律上依据,若未叙明而遽维持第一审所为命债务人连带给付债权人债务之判决,已有可议。”“最高法院”在这则判决中表示,当事人亦可透过和解而负有连带债务,至于和解明示出连带清偿责任之方式,乃记载债务人应就债务各负全部给付责任之意旨。“最高法院”在这则判决中,贯彻在其上开判决中所表示之意旨,即当事人无须明示连带债务之意思,只须明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便可认为在其间成立连带债务。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4年度台上字第1800号判决:“‘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债权人依第一项或第二项之规定声请法院撤销时,得并声请命受益人或转得人恢复原状。但转得人于转得时不知有撤销原因者,不在此限。此外,连带保证者,即指保证人与主债务人负同一债务,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而言,‘最高法院’1956年台上字第1426号判例可资参照,债权人得对连带保证人随时为全部或一部之请求,‘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百七十三条亦定有明文。”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一再在其裁判中明确表示,连带保证是连带债务,而在这则判决中更是明确指出,若保证人欲与主债务人连带负责,须在保证契约中明示其与主债务人对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最高法院”同样在这则判决中,贯彻其向来对是否成立明示连带债务所采之判断标准,即当事人不必明示连带债务之意思,而只须明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便成立连带债务。法院一再贯彻、维持在其先前判决中所表明之见解,不仅具有使其判决具有可预测之意义,亦有教育人民如何塑造其法律生活,从而降低纷争发生可能性之意义,乃成功的法院裁判活动。
(二)“最高法院”承认之连带债务
如前所述,德国联邦法院广泛承认成立连带债务,甚至包括两位承揽人瑕疵损害赔偿债务之连带。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亦采取德国法上之共同目的理论,理解同一债务这项要件。尽管如此,在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众多裁判中,迄今仅发现到一项连带债务类型,即连带保证。关于是否成立连带债务之认定活动,与德国联邦法院相较而言,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显得十分保守,其原因谅应在于,“民法”第272条第2项规定以明示或法律规定作为连带债务之成立要件,而德国民法上连带债务之发生,则并无这类限制。以下说明几则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裁判,其涉及连带保证成立连带债务,以及涉及共同保证人之连带明示约定。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4年度台上字第1710号裁定①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7年台上字第2830号民事判决、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度台上字第2372号民事判决。:“连带债务之债权人,得对于债务人中之一人或数人或其全体,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之给付,‘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一项定有明文。连带保证人既不得对债权人主张其应先向主债务人为请求,则同法第七百五十三条保证未定期间者,保证人于主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得定一个月以上之相当期限,催告债权人于其期限内,向主债务人为审判上之请求,债权人不于前项期限内向主债务人为审判上之请求者,保证人免其责任之规定,于连带保证自不适用。”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这则裁定中明确指出两点:其一,连带保证不仅是保证,亦是连带债务,即保证人并无先诉抗辩权;其二,“民法”关于保证之规定,如何适用于连带保证,亦即基于连带之约定,“民法”保证契约法上关于先诉抗辩权之规定,于连带债务并无适用之余地。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56年台上字第1426号判例①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66年度第7次民、刑庭总会会议决议(二)。:“保证债务之所谓连带,系指保证人与主债务人负同一债务,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连带债务之文义参照观之甚明。故连带保证与普通保证不同,纵使无‘民法’第七百四十六条所揭之情形,亦不得主张同法第七百四十五条关于检索抗辩之权利。”实际上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早在1960年代,就已在人民之法律生活中发现,连带保证作为明示连带债务的类型,而且早已表明连带保证同时是保证与连带债务,以及在其中并无先诉抗辩权之特征。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82年度台上字第5054号判决②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58年度台上字第1758号民事判决、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98年度台上字第522号民事判决。:“民事两造及诉外人陈某雄既同为诉外人谢某霞之连带保证人,以保证债权人台湾省合作金库之参拾万元借款债权,则对于债权人言,保证人固与债务人连带负履行债务之责任;于共同保证人间则依‘民法’第七百四十八条规定连带负保证责任,故连带债务之规定,于保证人间当亦有其适用。”若共同保证人与债权人未明示成立连带债务,亦即未成立保证连带,则依“民法”第748条规定,虽仍成立连带债务,但此时乃法定连带债务之性质,而非明示连带债务之性质。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其裁判活动中,除早已发现到存在于人民法律生活中之明示连带债务,尚发现共同保证人之连带明示约定。其实从“民法”第748条规定即可得知,共同保证人不仅得以其约定排除“民法”第748条所规定之法定连带责任,亦可以约定共同保证人负连带之责。
五、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区别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台上字第2003号判决③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1年台上字第848号判决、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台上字第1402号判决;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42页。:“‘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数人负同一债务,明示对于债权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任者,为连带债务。无前项之明示时,连带债务之成立,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连带债务之成立,以明示或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又连带债务,系指数债务人以共同目的,负同一给付之债务,而其各债务人对债权人,均各负为全部给付义务者而言。而不真正连带债务,系指数债务人,以单一目的,本于各别之发生原因,负其债务,并因其中一债务之履行,而他债务亦同归消灭者而言,两者并不相同。”观诸“民法”第272条关于连带债务发生要件规定中“同一债务”与“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之文义,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这则判决似指出,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区别基准之一,乃数债务之发生是否基于同一原因:数债务本于不同发生原因时,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本于相同发生原因时,成立连带债务。这项见解似乎也是学界多数见解④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42焱页:孙森著:《民法债编总论(下)》,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891页。。在此间所分析者,乃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区别。
(一)不同之债务发生原因?充分之定义?
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有两项共同点:其一,数债务人对债权人均各负全部给付之责;其二,各债务人中之给付,均满足债权人之给付利益(同一给付利益),均使其他债务人同免责任。由此以观,在前揭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见解中,真正算得上是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区别基准,似只剩下数债务是否本于不同之发生原因这项标准。
于分析“不同之债务发生原因”判断标准前,先再说明一次二则德国联邦法院判决所涉及之事实:其一,建筑师甲与乙订定关于A屋建筑蓝图与监工之承揽契约,建商丙与乙订定建造A屋承揽契约,建造完成后之A屋具有瑕疵,甲之建筑蓝图或监工工作与丙之建筑工作,均是这项瑕疵之发生原因,甲与丙就瑕疵亦均有过失,因此对乙各负有瑕疵损害赔偿义务,德国联邦法院将这两项出于不同承揽契约之赔偿义务,观察成具有共同目的,均在满足定作人之同一给付利益,亦即赔偿建物瑕疵,应成立连带债务①BGH, NJW 1965, 1175.;其二,甲建商与乙订定建造A毛坯屋(粗坯屋)之承揽契约,丙与乙订定A毛坯屋之抹灰工程A毛坯屋具有瑕疵,甲与丙之工作实施亦是这项瑕疵之发生原因,甲与丙就此均有过失,因此对乙各负有损害赔偿义务。德国联邦法院将这两项出于不同承揽契约之赔偿义务观察为出于共同目的,亦即填补定作人之瑕疵损害,均是瑕疵损害赔偿义务,处在同一位阶上,两项义务应是连带义务②BGH, NJW 2003, 2980.。
若依上开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与学界多数所提出之区别标准,于德国联邦法院前揭关于成立连带债务之判决之案例事实中,却因两项债务均本于各自、不同之发生原因,反而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造就同一则案例事实,于德国法上成立连带债务,于台湾地区“民法”上却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之现象。
更有甚者,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一般肯认,债务人(主债务契约)与保证人(保证契约)对主债权人负有连带债务。但若依这项由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所提出之区别标准,却因两项债务均本于各自不同之发生原因,反而亦应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在这两则案例中,数债务人之债务发生原因均不同,但却均应成立连带债务。从比较法之角度以观,这项由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与学界多数所提出之区别基准(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定义),实在颇有疑问。而且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似未意识到其见解前后自相矛盾: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向来肯认连带保证乃连带债务,但若依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这项判断标准,连带保证反而非连带债务。
台湾地区文献上之所以存在着这三项判断标准(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定义),尤其是以债务发生原因是否相同作为标准,其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将债务发生原因与连带发生原因混为一谈。数债务人可能基于不同之原因,而与同一位债权人发生债务关系,但亦可能与该债权人约定该数债务连带,以连带保证为例说明如下:债权人与主债务人间发生债之关系,是基于某一契约或某一条法律规定,债权人与连带保证人间发生保证关系,则是基于保证契约,两项债务之发生原因并不相同,但连带保证人保证债务与主债务人债务之连带,则是基于债权人、主债务人与保证人之连带约定,这两项债务之连带,乃基于同一原因。从以上现象观察亦可得知,纵使数债务之发生原因不同,但数债务人与债权人亦可透过连带之约定,使这些债务成为连带债务,乃契约自由之本质。
综上所述,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与学界多数,似尚未充分掌握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连带债务,而无法命中不真正连带债务之核心。但接下来之问题,乃如何充分定义不真正连带债务?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与学界多数提出之定义,究竟还缺少哪些因素?对其进行补充,均是以下分析之客体。
(二)连带债务担保债权实现之理性结构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与学界向来似均未充分认知到,连带债务之逻辑结构。如前所述,“民法”第272条关于连带债务成立之规定,乃在更加满足债权人给付利益需求之结构中展开:不仅其要件立基于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之上,其法律效果亦建构在这项理性结构之上。当认知到连带债务成立规范这项理性结构时,关于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区别轮廓,似可以被更清晰地呈现出来。于连带保证之例子里,毫无疑问地,可以从连带之约定中充分解读到,担保债权人债权实现之需求。是以连带保证亦是连带债务,而非不真正连带债务。更何况,只有将连带保证解释成其亦是连带债务,始符合当事人意思。
在前揭二则德国联邦法院判决之案例事实中,德国联邦法院肯认成立连带债务之理由,不仅是因两位承揽人赔偿损害,均能满足定作人之给付利益,亦因两位承揽人各自完成之工作,乃造成损害之共同原因,而存在着担保损害赔偿债权实现之需求。台湾地区“民法”若干关于数行为人负连带侵权损害赔偿债务之规定,例如受雇人与雇佣人、未成年人与法定代理人与共同行为人之连带侵权责任,其连带责任之正当性基础,大抵在于行为是造成损害之共同原因或与有助力,是以相应地更应使受害人所蒙受之损害获得全部填补。换句话说,立法者认为在如此出于共同原因或与有助力造成损害之情形,存在着更加担保损害赔偿义务获得满足之需求。德国联邦法院在前揭两则判决中,分别均使两位承揽人负连带债务,不仅符合这项由民法相关规定中所导出的关联性,亦即依法(条之关联)裁判,亦吻合连带债务规范本身之理性结构。
如前所述,在类似上开德国联邦法院判决事实之案例中,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仅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良以“民法”第272条规定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规定作为连带债务之成立要件。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度台上字第1402号判决:“学说上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指数债务人以单一目的,本于各别之发生原因负其债务,因其中一债务之履行,他债务亦同归消灭。故若不真正连带债务人中之一人所为之清偿,已满足债权之全部,对债权人即应发生债绝对消灭效力,债权人自不得再向他债务人请求清偿。故系争工程之监造虽有因投标厂商未尽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造成承包商未依图说施工,并溢领工程款,应依委任法律关系负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责任,惟应受两造最高赔偿总额约定之限制。”基于比较法上之不同,并不能认为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上开判决即不当。“民法”第272条规定既然表明,连带债务成立上之明示与法律规定之限制,法官自应受其拘束。在上开事实里,不仅当事人并无明示成立连带债务,亦无法律规定其间成立连带债务,法官因此无论如何并无法认定成立连带债务。这项连带债务成立之限制,无法对应连带债务之理性结构,且可能因此将应成为连带债务者评价为不真正连带债务,亦即劣化其法律地位。立法论上似应废除这项限制。
从以上分析可推论出,数债务是否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关键点在于在其间是否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若其间并不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则不成立连带债务,而始有可能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尽管如此,应在此间再次强调者,乃依“民法”第280条规定,连带债务之发生,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规定为要件。较诸于德国法而言,台湾地区“民法”上连带债务之发生,明显困难许多,连带债务成立规范之适用余地,显得欠缺弹性,而无法充分顾及,当事人并无明示且法律亦未规定成立连带债务,但当事人间却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需求之情形。
(三)债务人中之一人负最终责任?
文献上有认为,①杨立新:《论不真正连带责任类型体系及规则》,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第58页;李中原:《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的反思与更新》,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53页。相反见解,参见王千维:《论可分债务、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下)》,载《“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2年第8期,第46页以下。若数债务人中之一人对其他债务人而言,应负最终或全部责任时,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准此而论,在上开二则德国联邦法院判决所涉及之案例事实中,两位承揽人彼此间并无何人负有全部责任或最终责任可言,是以应成立连带债务;于连带保证中,若债务人与保证人并无约定何人负有全部责任或最终责任或多少比例之责任时,则亦无人负有全部责任或最终责任,而是应平均负担(“民法”第280条)。
“民法”第280条规定:“连带债务人相互间,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平均分担义务。但因债务人中之一人应单独负责之事由所致之损害及支付之费用,由该债务人负担。”从这条法条但书可知,即便在连带债务中,债务人在对内求偿关系中,亦可能负有最终或全部责任。既然如此,可见以债务人中之一人对内是否负有最终或全部责任,亦无法解决系争数债务是否为不真正连带债务。而且采行这项区别标准,恐将造成在规范上有着担保债权实现需求之情形,却被评价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债务人中之一人对其他债务人而言,负有最终责任或全部责任,不应是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区别标准。而且,连带债务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规定为发生要件,其发生因此更显得困难。在如此之脉络底下,上开评价矛盾将更显得尖锐。
六、结论
台湾地区“民法”主要继受德国民法,主要继受德国民法法条。但从本文研究便可发现到,台湾地区“民法”继受德国民法时,亦可能偏离德国民法法条文义,而继受德国学说。台湾地区“民法”第272条第1项规定是连带债务之成立规范,其要件与法律效果均立身在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或必要性之脉络之中。换句话说,数人负同一债务(数债务具有共同给付目的),出于满足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者,立法者只有透过数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作为要件,以及以数人负全部给付之责作为法律效果,始能满足这项需求。立法者以如此内容之规定关系与命令关系,而且也只能以如此之方式,共同架构出连带债务的逻辑结构。
依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见解,连带债务之明示成立,并不须当事人明示“连带”二字,而只须明示负同一债务的数人各负“全部给付”之责。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所承认之连带债务,只有连带保证与共同保证人之明示连带。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与通说均采取作为德国通说之共同目的观,理解“民法”第272条第1项规定所指之“同一债务”要件。亦即纵使数人各自所负之给付义务出于不同原因,但只要均以满足债权人给付利益为目的,亦成立连带债务。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虽以数债务是否基于同一原因而发生,作为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区别基准:基于同一原因者,乃连带债务;非基于同一原因者,乃不真正连带债务。但其同时却认为,在连带保证,尽管主债务与保证债务基于不同原因而发生,但连带保证仍是连带债务。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这两项见解明显前后矛盾。数债务是否基于同一原因而发生,不应是区别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基准。区别两者之关键点,乃数债务间否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若其间并不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则不成立连带债务,而始有可能成立不真正连带债务。
即便在连带债务中,债务人在对内求偿关系中,亦可能负有最终或全部责任。既然如此,对其他债务人而言,债务人中之一人是否负有最终或全部责任,亦无法解决系争数债务是否为不真正连带债务。以数债务间是否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始能妥当区别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倘若以数债务是否基于同一原因而发生,决定债务人中之一人是否负有最终责任,区别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则恐将造成在规范上有着担保债权实现需求之情形,却被评价成不真正连带债务。而且,连带债务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规定为发生要件,其发生因此更显得困难。在如此之脉络底下,上开评价矛盾将更显得尖锐。保守而言,立法论上应废除这项当事人明示与法律规定之限制,从而至少可避免前揭尖锐之评价矛盾。
(责任编辑:苏婷)
D927.583.3
A
1674-8557(2016)03-0071-11
2016-08-18
游进发(1974-),男,台湾台北人,台北大学法律学系专任副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