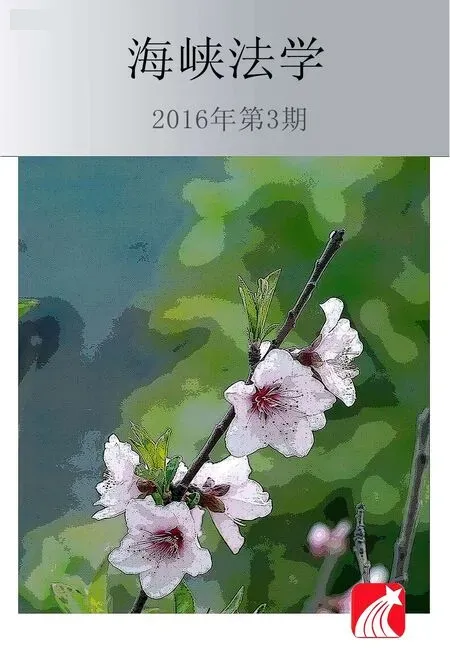财产权属于人权吗?
2016-03-15王晨
王 晨
财产权属于人权吗?
王 晨
财产权是否属于人权,此疑难关涉政治社会的基础,简单地给出肯定和否定的断言将无法看清两者的内在联系。启蒙思想家们试图在人权基础上推导财产权,进而为一种保障个体自由的法治国家奠定理论基础,但从先验哲学的立场上看,这些方案都有内在的困难。在批判这些方案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一种始于阿奎那的解释模式,康德论证了财产权的道德必然性,并从人权推出了财产权。它展示了康德最后的原创力,并帮助人们抵抗那些针对财产权的古老怀疑。
康德;人权;财产权;自然权利;源始共有;许可法
“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当1789年《人权宣言》作此断言时,“神圣”这个字眼已经有点不合时宜,更恰当的表达是,财产权属于“人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如今,就连“自然”这个字眼也已经不合时宜,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的权利虽被视为人权,但它们既不神圣也不自然。在当今的人权话语中,自然除了意味着公理性和不假思索之外,没有其他的意义。存在自然的人权,也存在自然的财产权,而财产权属于人权,似乎再没有比这一点更加自然。为了证明它,可以像法学家援引宪法一样援引《人权宣言》或者《世界人权宣言》,但如果自然就意味着公理性,而财产权属于人权又是自然的,那么两者的一致性却需要通过援引来加以证明,这岂非多此一举?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财产权属于人权,它并没有看上去那样自然。
财产权是什么?“财产权就是盗窃。”①[法]蒲鲁东著:《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页。对财产权自然性的攻击,这仅仅是一个极端的现代版本,它的源头是那位孤独的散步者,②“谁第一个圈出第一块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奠基人。”[法]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而卢梭复活的不过是一个古老的怀疑。为了抵抗这个怀疑,西塞罗的“剧场”常常被视为最好的隐喻。③See. 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Richard Tuck ed., Book II,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2005. p.421.对财产的先占取得,这就像剧场的座位被先到的人占用那样自然而然,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比喻却恰恰包含着对财产权自然性的怀疑。通过先占取得的仅仅是对剧场中一个座位的使用权,而有权使用先占的座位,这和把它宣布为自己的财产显然是两码事,更遑论试图通过先占去占领许多座位。对提出如此非分要求的人,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的权利,那就只能把他轰出剧场。人的权利是自然的,自由、安全和反抗压迫属于人权,这也是自然的,但财产权的自然性却大有可疑。任何把财产权归于人权的观点,除非得到严格的论证,否则就不能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得到辩护,而康德正是要做出这一辩护。
一、人的权利
与其现代先驱一样,康德也把人的权利称为自然权利。①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237.康德正式出版著作之中译文,三大批判参考邓晓芒译本,其余参考[德]康德著:《康德全集》,李秋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部分译文有改动。“自然”不再具有传统的含义,而是仅仅意味着“与生俱来”(angeboren)。②a. a. O.然而,“与生俱来”与出生这一经验事实却并无直接关系,它更准确的表达是“源始的”(ursprünglich)。③a. a. O. S.258, 237.与派生的相反,说一种权利是源始的,这就等于是说它绝非派生,而只有基于“人性”(Menschheit)的权利才堪称源始,④a. a. O. S.237.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⑤a. a. O. S.238.人因其本性(Natur)而拥有自然权利,这是现代先贤们最基本的主张,但当康德谈论人性时,他想到的并非通常意义上人的本性。人性是一种独特禀赋(Anlage),⑥a. a. O. S.26.没有这种禀赋,人就不会是悬在超人和动物之间的绳索,不会是一张瞄向远方的满弓。当自然欲望产生时,动物会受其支配并采取行动,饥饿促使动物寻找食物并立刻把它吃掉,但人能推迟自然欲望的满足,他能控制自己不受饥饿的支配,他存储食物而不是把它全部吃光。这种能力通常被称为有理性,古希腊人因此把人称为“有逻各斯的动物”,它使人区分于地球上的其他一切生命形式。人能够推迟欲望的满足,这一简单的现象揭示了最复杂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现代经济学最感兴趣的市场行为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人全都立刻消费掉他的所得,市场就会不复存在;没有对货币的存储,金融这根经济的支柱就会崩溃。追求利益最大化使人克制当下欲望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富有的人同时也是最节制的人。这种理性就是霍布斯所谓“斟酌中的欲望”,⑦[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6页。也是休谟笔下“激情的奴隶”,⑧[英]休谟著:《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3页。更是韦伯眼中的“资本主义精神”。⑨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当这种理性统治世界,未来的主宰就会是一群没有灵魂的专家,或是一群没有心肝的纵欲者。⑩同上,第106页。
康德所谓的人性绝非单纯意指这样的理性。为满足欲望寻找合适的手段,这只是人有理性的一种不充分体现,而延迟欲望的满足,这也只是理性对感性独立性的初级形式。康德承认这一切都是有理性,但却坚决反对这就是理性全部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在帮助现代人抵抗“理性的毁灭”。如果工具性就是理性的全部能力,那么人和动物就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因为工具理性的目的是被感性所设定,因此从根本上说,人和动物一样受到感性欲望的支配,其区别仅仅在于,人比动物更懂得如何才能谄媚这个暴君。但这并非事实,人性在本质上有别于动物性,理性确实能够完全独立于感性为自己设定目的,这意味着它有能力做感性的主人而不是奴隶。11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3对于康德来说,这绝非夸大其辞,理性有独立设定目的的能力,这恰恰证明了人事实上是自由的。12a. a. O.这种独立于自然必然性的自由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就此而言,有理性绝不等同于有实践理性。一个“魔鬼的民族”确实是有理性的,但无疑没有实践理性。①Vgl. 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II, Berlin und Leipizig:Walter de Gruyter, 1923. S.366.一个卡拉赞式的资本家,无论其自私具有多么开明的外观,也终究掩盖不了他对人的不尊重。②Vgl. 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Band I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0. S.209.人性不仅意味着有理性,也意味着有实践理性,不仅意味着人能够通过满足欲望来获得幸福,也意味人能够按照实践理性所设定的客观目的去行动。这一目的之所以是客观的,是因为对它的保存和促进,这被一切有理性存在者所必然追求,就此而言,客观目的区别于那些被个体所偏好和追求的主观目的。③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IV,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1. S.428.
理性追求的客观目的只能是人自身,康德对道德法则的推演虽然复杂难解,但其基本论断却简单明了。想要某个目的,但不想要实现它的手段,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想要某个目的,却不想要它得以存在的条件,这就会是一种自相矛盾。④a. a. O.因为那就等于说:我想要又不想要这个目的。人为自己设定的一切目的(价值),其存在的先决条件无非是设定目的的能力本身,这种能力就是人性,没有人性,无论追求幸福还是道德行为都将不再可能,因此人性作为一切目的得以可能的条件,就是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必然希望保存和促进的客观目的。⑤a. a. O. S.437.要求人始终把人性作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这是实践理性所颁布的道德法则。⑥a. a. O. S.429.“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单纯当作手段来使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个人作为有人性的存在者都具有人权,因而必须得到他人的尊重。⑦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237.人是目的,他因此和世上的一切事物区别开来。事物没有自由,它们不能对抗人的使用,每个人都可以把事物用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人不是物,道德法则禁止把人当作事物,从而被仅仅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无论这是私人目的还是公共利益。就此而言,奴隶制有悖于人权,因为奴隶被仅仅当作物品;酷刑有悖于人权,拷打者遗忘了敌人也是人这一事实;溯及既往或功利性的刑法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仅仅被当作统治的工具。
人基于人性就应该被作为目的加以对待,这论证了每个人平等地具有人权(内在法权),⑧a. a. O.也蕴含着每个人都能独立于他人的任意强制,自主地决定和追求自己的幸福。从人权的这种平等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特征,很容易把财产权也视为一种人权,后者不仅体现了上述基本特征,而且似乎是人生存于世的前提条件。就人无法自足的本性而言,若没有对外在事物的使用,人将无法生活,更无法活得美好。既然生存权是基本人权,那么作为生存的前提条件,财产就必须同时被理性所要求,再没有比这一点更加自然。然而,这个看似自然的推论却隐藏着一个混淆词义的逻辑错误:生存的前提固然是对外在事物的使用,但这种使用权却并非财产权,没人会把租客称为房屋的所有者。所有权不仅意味着能够使用外在事物,它的本质更在于排他性占有。因此,一个卢梭笔下的自然人离开洞穴觅食,当他再次返回洞穴时,他的小窝或许已被另一个自然人占据,而如果一个文明人离家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那就会有法律和警察出面解决问题。当文明人对外在事物主张财产权时,他主张的不仅是使用,更是排他性占有,这种占有不以对物品的有形持有为条件。然而,文明人的这一主张对一个自然人来说却根本不可思议,在那个后到的自然人看来,洞穴并无主人,他看不出自己为什么不能使用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这些公平馈赠。
二、对传统的批判和修正
把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对立起来,这是霍布斯的发明,康德曾高度评价这一发明,①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XXVII,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74. S.590.卢梭则进一步教会康德把这种自然状态推到极端。②参见[法]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还有一个缺陷,即这些定义来自许多并非人们自然就有的观念,而是从脱离了自然状态后才想到的一些利益关系中得出的。”译文略有改动。当自然状态被推到极端,财产权就随之消失不见。文明人眼中那些理所当然之事,对自然人来说却毫无意义,它们是柏拉图式洞穴墙上晃动着的阴影,自然人无法理解这些人为物的含义。财产权就是如此,其自然性似乎一目了然,但一经思考就成为问题。当一颗豆子被播种下去,“它是我的”这一观念就深入人心,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他人铲除,爱弥儿懂得了什么是不正义。③参见[法]卢梭著:《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4~107页。我付出劳动的果实就是我的,似乎再没有比这更加自然,但它要求下述前提条件,我劳动加工的对象首先必须要是我的。因此,平息爱弥儿义愤的有效办法就是让他认识到,他在其上付出劳动的土地实际上早已属于他人。爱弥儿尚未被哲学败坏,否则他必定会问:土地为什么是你的?因为你付出了劳动吗?但劳动加工的对象必须首先已经是你的。在你耕作之前,土地为什么是你的?一切土地不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吗?每个人不是都有权利使用这些馈赠吗?是什么让你排除了我和其他人的这种自然权利呢?是先占吗?可是难道你看不到,先占取得使用和先占取得财产是根本不同的吗?
哲学追寻自然,正是在这一追寻中,财产权的自然性成为了问题。作为现实政治的基础,财产权被法律所承认和捍卫,而哲学却通过对其自然性的怀疑动摇着这个基础。一个人坚定地主张人权,但同时又坚定地反对财产权,这并不必然是一种自相矛盾,而对于那些没有土地和豆子的人来说,哲学的这一怀疑便如同塞壬之歌,充满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对现实政治基础的怀疑,这和颠覆现实的狂热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而以真理的名义打碎枷锁,这总是最能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合乎正义的东西一定是有用的,有用的东西一定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一定是可能的。”④[法]蒲鲁东著:《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3页。然而,正如罗伯斯庇尔不是卢梭的好学生,蒲鲁东显然也不是。他们忘记了,就在普罗米修斯把火种交给人时,萨图尔也跑上前去拥抱它。“萨图尔,你要为你下巴上的胡须哭泣的。”⑤参见[德]迈尔著:《论哲学生活的幸福》,陈敏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作为卢梭的学生,康德当然明白怀疑的界限。早年的康德对政治和历史毫无兴趣,但它们却是其晚年关注的焦点,这当然绝非偶然。谁若停留在普遍性和必然性中,谁就会对政治和历史漠不关心,后者属于特殊性的领域。只有当其下降至普遍与特殊之间,他才能理解政治和历史。判断力恰好位于理性普遍性和感性特殊性之间,正是《判断力批判》给予康德一个立足点,使之能够下降于太阳和洞穴之间来反思人事,但哲人的旅程这时也已经走到了最后的阶段。当一个人历经艰辛变得成熟,老年却让他变得迟钝,自然则要他去死。⑥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II, Berlin und Leipzig:Walter de Gruyter, 1923. S.118.任何一个熟悉康德法权论的读者都很难不认同叔本华的评论,⑦参见[美]阿伦特著:《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曹明、苏婉儿译,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6页。《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最糟的作品,它重复啰嗦,结构混乱,像一个老人冗长乏味的唠叨。可是读者却也不能否认,《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原创力的最后展现,恰恰在这里,康德帮助人们跨越那个动摇政治基础的怀疑,填平那个横亘于人权和财产权之间的鸿沟。
法权论的基本难题显然已不再是对人权的论证,它已经通过前两个批判得到完成。摆在康德面前的难题是如何从人权推出财产权,以便对付那些对财产权的古老怀疑,并进一步为公民社会奠定基础。从哲学的视角看,即便人权已被启蒙思想家反复论证,但以人权为基础对财产权的论证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这些论证要么把财产权提升到自然的高度,以修辞的夸张替代真理,要么把财产权贬为单纯的人为物,并因此对它的道德必然性视而不见。考虑到财产权是一种不以有形持有为条件的占有,康德用“理知占有”来强调它的这一本质,因而财产问题也就相应地转化为:理知占有如何可能?①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249.对此,最古老也最符合直觉的解释是先占获得。对于无人占有的事物,谁在时间上最先占有,谁就取得了它的所有权,这也是罗马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先占者有福(beati possidentes)。②a. a. O. S.257.然而,这一解释若要成立,它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被取得的是无主物,但正是这个前提根本无法被满足。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看,世界是上帝的作品,而创造者之于被造物乃是无可争议的主宰,因此,世界原始地属于上帝而并非无主物的聚集,人作为被造物之一,在根本的意义上并不能通过先占取得任何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点,托马斯主义传统否定了先占能够取得财产权。③See,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I. II. Q66. A1. Public Domain, 2000.作为哲人,康德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神学论证,然而从哲学的立场上看,先占取得同样大有可疑。由于人权是一种平等和独立的法权,它保障了每个人对他人强制的独立性,而先占取得似乎恰恰有悖于人权,因为先占纯粹是一个单方意志行为,它试图施加给每个人他们原本没有的一种义务。④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247, 261.当我们走进剧场,座位的使用权可以通过先占取得,但如果某人通过先占宣布,从此以后这就是他的专属座位,那他就提出了一个狂妄的要求。他正通过自己单方的意志发布一条命令,要求进入剧场的每一个人服从,即使在剧终人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这位观众的荒谬主张,人们或许能一笑了之,然而先占取得却是法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它的荒谬性若不能被彻底消除,怀疑论就可能适时爆发,从而颠覆财产权的正当性,进而威胁政治社会。正如剧场并非无主物而是共有物,在财产权产生之前的状态也不是无主状态,人权保障了人们能够平等地使用事物,因此世界的源始状态和剧场在下述特征上完全一致:它们对每一个人的使用保持开放,但这种使用权受限于有形持有,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
另一种符合直觉的解释是诉诸劳动。正如创造者对创造物享有自然的所有权,劳动者在某种意义上制造了劳动产品,从而自然地对劳动产品享有所有权。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却必须同时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首先,人的劳动是制造而不是创造,他只能改造既存的质料,并不能通过劳动无中生有地创造实体,因此人的劳动并不能类比上帝的创造,并借此宣布财产权的自然取得。用康德的话说:“偶性的占有不能充当实体的法权占有的一个根据。”⑤a. a. O. S.268.此外,正如爱弥儿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劳动取得的前提是,被劳动改造的事物首先必须属于劳动者。谁在他人的土地上耕作,谁就不能抱怨他的劳动被他人占有。劳动的对象必须被先占取得,而先占取得的仅仅是使用权而不是财产权,因此劳动并没有解释财产权的起源,它顶多是对源始共有的一种分配方式。
先占和劳动都属于单方意志行为,但单方意志行为并不能给他人施加义务,这是因为每个人平等地享有人权,这就排斥了个体随意给他人下命令,从而给他人施加义务的可能性,只有作为创造者的上帝才能通过单方意志直接给每个人施加义务。既然人的单方意志不能施加义务,那么似乎只能求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意志才能做到,这种共同意志的表现形式就是契约。有鉴于此,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财产权才被解释为一种人为契约的产物,它起源于约定而并非自然,这一解释符合《圣经》描述的神圣历史,并天然地带有对财产权的敌视。①See, Carlyle R. W. and Carlyle A. J.,A History of Mediaeval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vol.1,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Ltd., 1981. p.23, p.99, p.133.缓解这种敌视的工作最开始由12世纪教会法学家们做出,随后由阿奎那发展为一个经典模式。根据阿奎那的解释,财产权虽然起源于契约,但并非与自然法相悖,因为自然法并未禁止私有。②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I. II. Q66. A2. Public Domain, 2000.“财物的共有被归于自然法,不是在于自然法命令一切事物应该共有,并且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被人作为自己的来拥有,而是因为占有的划分不是根据自然法,毋宁是来自属于实证法的人的同意。”这一解释框架途经萨拉曼卡学派和格劳秀斯,被普芬道夫所继承,并通过普芬道夫被康德所熟悉。③See, Brian Tierney, Permissive Natural Law and Property: Gratian to Ka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62. No.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然而,这一框架虽然通过契约解释了对世义务的起源,但从哲学的立场看却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首先,财产权产生之前的那种状态,其作为“初始共有”(communio primaeva),④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262.仅仅是一个来自《圣经》文本和神学的虚构;其次,把财产权诉诸于一个全人类的契约,这同样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虚构。
三、从“位置”到“驻地”
哲学不能将虚构的事实作为开端,因此当财产权问题轮到康德来接手时,法权论的关键任务就成为如何修正上述解释,使之在脱离《圣经》支持的前提下与批判哲学相契合。为此,康德的第一步是取消传统“初始共有”(communio primaeva)的概念,并代之以“源始共有”(communio originaria),⑤a. a. O.后者不再是一个时间开端,而是法权推导的逻辑条件。人权使每个人都能独立于他人意志,平等地使用外在事物,因而事物与人的源始关系就如同剧场和观众,剧场中的座位向每个人的使用保持开放,这种基于人权的使用权以有形持有为条件。要生存于世,人必须能够在大地,而不是在海洋或太空中获得一个立足之地(位置)(Platz),⑥a. a. O. S.261.对照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XXIII, Berlin und Leipizig:Walter de Gruyter, 1955. S.323.因此对事物的第一次使用必然只能是针对土地。把人带到大地上任何位置的偶然事件,都足以使他立刻获得一个立足之地,无论这种事件是出生还是风暴,或是其他什么力量。⑦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XXIII, Berlin und Leipizig:Walter de Gruyter, 1955. S.322.如果大地是一个无限延展的平面,那么人就可以在其上走散而不必有交互联系,然而事实却是,大地是一个有限的球面,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互交往,⑧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262.在这一条件下,人所处的源始状态就必须被设想为人类对大地的源始共有,⑨a. a. O.但这种共有与法学意义上的共有财产却有本质区别。⑩参见[澳]斯蒂芬·巴克勒著:《自然法与财产权理论》,周清林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7~88页。[英]詹姆斯·塔利著:《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王涛译,商务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首先,共有财产虽然在内部为共有人共同所有,但在其外部却具有财产权的排他性;而在源始共有中,土地属于整个人类,因此上述排他性特征消失不见。两者的第二个区别更为重要,在共有财产的情况下,共有物的分割需要共有人一致同意,它以契约作为条件;而在源始共有中,某人通过对事物的有形持有获得其使用权,这无需现实契约。鉴于源始共有的上述特征,普芬道夫曾将其称为“消极的”,①Samuel Pufendorf, On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Book IV, trans. by B. Kennett, London: MDCC XXIX. p.366.从而区分于“积极共有”,也即通常意义上的共有财产。从本质上说,积极共有只是私有财产的一种类型,而消极共有则根本不是财产权。
既然与人权对应的是大地的源始共有,因此对财产权起源的解释就必然要求解释这种共有如何失落,以便看出财产权如何从这一过程中诞生。鉴于源始共有状态是最初的自然状态,因此考察财产权的产生发展,也就是在考察政治社会如何从自然状态中产生。在异教诗人眼中,这一过程与黄金时代的消逝一致,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它与失乐园的神圣历史一致。②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19.传统满怀伤感地看待这一失落,它与一种历史感相互交织难解难分。神圣的历史从善发端,人的历史则从恶开始。开端并不神圣,它只是蕴含着完善的种子,而完善只能在终点而非开端被发现。这种完善并非个体的完善,而是作为一个类的人类的完善,这一完善的实现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甚至是战争来作为手段。③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II, Berlin und Leipizig:Walter de Gruyter, 1923.S.21.人类若一直停留于源始自然状态,人性就会永远沉睡,其自然禀赋将无法得到发展。④a. a. O. S.115.自然希望人类走出源始状态,为此它在人性中撒下自爱的种子,它使得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总是倾向于秘密地把自己排除在外,⑤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27, S.32, S.45.他在要求别人不要侵犯自己“位置”的同时,却允许自己背道而驰。这一自然倾向使人在彼此面前充满危险性,是故仅仅他人与我共在这一事实,就足以让我把他人看作敌人,而不必等到现实敌对的行动发生。⑥a. a. O. S.307, S.312.源始共有状态势必发展为霍布斯笔下的战争状态。若思考人的危险性根源,那就只能追溯到人性,恰恰是人性使人能够给自己设定目的,从而偏离自然或理性所设立的普遍目的,就此而言,人的危险性与其尊严性同源同宗。这是否意味着,若要消除人的危险性就必须消除人性?是否意味着必须把古典城邦视为典范?古典城邦最光荣的那一个,它首先发现了公民的价值,其消灭僭主的同时也消灭了家庭和财产,⑦参见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17页。它压制私人领域,更不用说它多么轻视文化。它的正义止步于城邦边界,其行动和言辞的矛盾性并不比它的死敌更少一些。⑧同上,第21页,第245页。理解修昔底德笔下人物言辞及行动中的自相矛盾,这是揭示修昔底德教诲的一把钥匙。康德关于正义的唯一检验标准就是不可自相矛盾。某些事情阻止人们践行正义,而一旦正义被严格践行,政治也将不复存在。然而,仅仅对爱弥儿豆子危机的解决就足以说明,人与人的和平共存并不需要付出消除自爱的代价,而只需要人们学会承认并尊重“你的”和“我的”。⑨参见[法]卢梭著:《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6页。
传统对正义最经典的表达是“给予每个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但若什么是“他自己的”没有事先得到说明,那么这个表达就毫无意义。法权论需要从人权出发对什么是“我的”“你的”加以界定,而伴随着对“我的”“你的”的确认和保障,从源始共有到公民社会(公开的正义状态)的过渡便水到渠成。从根本上说,“必须走出自然状态”(exeundum esse ex statu naturali),⑩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XXVII,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74. S.590.这是理性对人类颁布的一个命令。谁愿意保持在自然状态中,谁就会使正义状态成为泡影,因而这一准则及其行动本身就成为最严重的不正义。11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S.307.与这一过渡相应,人对大地上一个“位置”的获得,必须发展为对大地上一个“驻地”(sedes)的占有,①a. a. O. S.251.后者是一种无需有形持有的理知占有,因而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我的”。作为对世权利,财产权对应着不特定他人的普遍义务,但正如前文所言,任何单方意志都无法设定这种义务。鲁滨逊要把荒岛上的一个立足之地变为驻地,仅靠其单方行动无法办到。他能将这一地方据为己有,凭借的固然是拳头和武器,但暴力只能充当维护财产的手段,却无法冒充为它的源泉。谁把暴力和权利混为一谈,谁就等于宣称“圆的方”存在,它们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能够将位置转变为驻地的只能是全人类“统一的意志”(der vereinigte Wille),②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XXIII, Berlin und Leipizig:Walter de Gruyter, 1955. S.320.因为只有通过契约人们才能交互约定,我放弃你最先占有的土地,即使你离开了它,但前提是你也做出同样的保证。③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255.财产权对应的普遍义务来自统一的意志,康德的解释与阿奎那创立那种经典模式几乎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普遍意志并非历史性产物,它作为发源于理性的一个理念,只是论证财产权的逻辑前提而非事实证据。试图通过经验对理念做出理论证明的努力终将徒劳无益,理念的客观实在性只能在实践必然性中得到论证,④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V,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132.而统一的意志这一理念的实践必然性就在于,基于人性和人不可避免的共存,如果没有清楚地划分“你的”“我的”,从而由人权对应的源始共有过渡到财产权,那么任何现实的法权状态都将是一种幻想。⑤“如果他不想放弃所有的法权概念,那么,他必须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下原理:人们必须走出每个人都按自己想法行事的自然状态,并与所有他人(他不可避免地与他们彼此影响)联合起来,服从一种外在的公开的法律强制”。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and VI,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3. S.312.
至此还剩下一个疑惑需要得到解释。单方意志行为不能为他人设定义务,这个困难似乎已经被普遍意志的引入加以解决。当每一个进入剧场的观众都同意,先占能够取得一个专属的座位,那么这一原本僭妄的行为就取得了合法性。然而在法权论中,真正授予人理知占有权能(Befugniß)的却是一个实践理性的公设,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的许可法”(lex permissiva),⑥a. a. O. S.247.正是这一公设允许人们仅凭单方意志就取得财产。令人困惑的是,既然通过统一的意志已经能够使先占行为设定义务,从而解释了财产的合法性,为什么又需要一个实践理性的许可法呢?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在统一的意志之外又设定许可法,这似乎很难得到一个合理解释。⑦See, Brain Tierney, Liberty and Law, the Idea of Permissive Natural Law, 1100-1800.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2014. p.339.然而从逻辑上看,实践理性的许可法确实应该独立并且先于统一意志。因为如果一种行为违背理性法则,因而就其自身而言是恶的,那么任何意志,哪怕是全人类的普遍意志,也不能使之变成善。如果先占取得财产权,这本身就被理性自然法所禁止,那么即使是人类的普遍意志也无法使之正当化。换而言之,如果财产权本身就是恶的,因而根本没有道德可能性,那就没有提出统一意志这个理念的道德空间。普遍意志能够使先占合法化的前提是,这种行为自身并不被自然法所禁止,而从逻辑上讲,不禁止也就等同于许可。由此可见,许可法在功能上是要为提出普遍意志理念创造一个道德可能性空间,它无法被普遍意志所替换,因而从根源上讲,做出许可的其实并不是普遍意志,而是实践理性本身。
(责任编辑:林贵文)
D913.2;D082
A
1674-8557(2016)03-0082-08
2016-05-13
本文系教育部2014年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项目课题《中国大众民生观念调查》(课题编号:14JJD82002 4)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晨(1981-),男,贵州遵义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法理学2011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