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
2016-03-14李安安
江 春 李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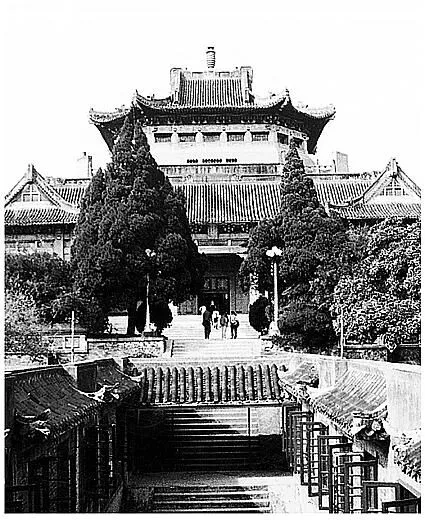
法治、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
江春李安安
摘要:立法回应不足、执法公正缺失与司法独立弱化分别构成了金融抑制、金融排斥和金融分割的法律诱因,造成企业家精神的消沉、低迷和式微,并进而导致金融发展未能通过支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来促进经济增长。以回应型立法助推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以监管治理诱导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以司法独立引领金融分割走向金融一体化,以此弘扬企业家精神和促进经济增长,打造“良法善治、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是未来中国金融治道变革的重心所在。
关键词:金融包容; 金融发展; 司法独立; 企业家精神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正在华夏大地席卷而来。无论创业还是创新,都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更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弘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金融在支持创业、创新方面的作用乏善可陈,金融激励企业家精神的功能未能彰显,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生成。如何通过法治推动金融发展和释放企业家精神,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法治新常态”下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 理论迷思与现实悖论:金融发展的法律追问
目前,国外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最新进展当属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创新理论的复兴。早在1912年,熊彼特就预见性地指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金融的本质或核心功能就是筛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并为他们提供信贷资金,以帮助企业家重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或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进行创新活动,从而实现革命性的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颇有戏剧性的是,这一论断在沉寂了80年之后才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其标志性事件是King和Levine于1993年发表的论文《金融、企业家和增长》以及《金融与增长:熊彼特可能是对的》。在这两篇经典文献中,作者通过对全球各国的金融改革及金融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的反思以后,重新认识到熊彼特在80年之前所提出的金融的核心功能是筛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以帮助企业家重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活动,从而促成经济增长的思想也许是金融发展的本质所在(King & Levine,1993:513-542,717-738)。时至今日,学界普遍认为,金融通过支持拥有新思想或新技术并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既是实现金融内生发展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刺激生产力不断上升及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尽管这一学理共识对金融发展本质的揭示精准而深刻,但与中国金融发展的理论及实践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金融理论往往将金融解释为“资金的融通”,而不是解释为“通过动员储蓄并将储蓄转移到掌握最有利投资机会的投资者或企业家手中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中国传统的金融理论将金融机构定义为经营货币或资金的机构,而不是视为筛选具有创新思想及精神的企业家,以帮助企业家重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活动的金融中介,这是导致中国金融的“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金融的“质量”却十分低下,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创新能力及就业机会仍然不足进而不利于实现普惠式金融增长的根源。
鉴于金融发展的理论迷思与现实悖论,如何变革金融发展模式以强化其时代适应性与面向实践的解释力,无疑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命题。笔者从法学角度深入研究中国金融发展没有着眼于大力支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进行创业或创新活动的原因,从而力求为推动中国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及金融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丰富并扩展“法与金融”的研究内容,进而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今天,如何通过法治支持企业家的创新及创业活动,将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培育企业家精神相结合,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了本文的立足点。笔者的论证逻辑在于: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检视现行的法律制度对金融发展的消极影响及由此造成的对企业家精神的贬损效应,厘清法治、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制度关联,为面向企业家精神的金融发展治道变革提出法律建议,为下个阶段的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扫除法律的观念及制度障碍并提供法治的动力源泉。
二、 立法回应不足、金融抑制与企业家精神的消沉
改革开放以来,在摆脱了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桎梏后,我国金融市场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立法高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金融法律的渐次出台反映出金融市场转轨过程中的“立法饥渴”,金融法律规则的供不应求暗含着通过金融法治为金融改革保驾护航的美好期待。这是因为,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而法治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区分“改革试错”与“权力滥用”的界限,确保改革的目的正当、规则合理与程序正义。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法律不代表有法治,金融法律的不断供给并不意味着金融法治秩序的持续增长。一个悖论在于,在以金融抑制为特征的经济中,加强法治可能阻碍金融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言,加强法治有助于提高私人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份额,推动银行业的竞争,但抑制私人投资,并对金融深化没有显著影响(卢峰、姚洋,2004:42)。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金融抑制,源于政府主动地、有意识地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介入,特别是通过人为地干预金融市场的交易,扭曲利率、汇率等金融市场价格,来实现国家的“经济赶超战略”。对于我国而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决定了政府干预的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广度与深度较之其他转型国家更为突出,如金融机构超高的国有股权比重、金融机构高管的“国家干部”身份、股票发行的严格控制、金融监管部门掌握金融创新的主导权、地方政府将金融市场稳定与风险控制作为维稳工作的一部分等(黄韬,2013:2)。
不断增长的法律制度供给与积重难返的金融抑制构成了鲜明对比,说明法律制度只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通过金融法治实现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法则同样需要借助于相关的配套条件才能获得本土性证成。这里的“配套条件”,最重要的莫过于对金融立法本身的要求,即金融立法必须具有社会回应性与时代适应性,既能够积极回应社会成员的权利诉求,又能够适应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的制度变革需要。有学者将法律分为三类,即作为压制性权力的工具的法律——压制型法,作为能够控制压制并维护自身完整性的一种特别制度的法律——自治型法,作为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回应型法(诺内特、塞尔兹尼克,2004:16)。从应然意义上,金融立法惟有立足于回应型法才能获得正当性,进而成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助推剂。但在实然意义上,受制于信息能力不足、认知能力有限、知识资源贫乏等因素,立法总是难以充分回应社会成员和制度变革的诉求,时常沦为压制性权力的工具。反映在金融领域,国家干预金融市场并由此出台的压制型立法,难以秉持一种审慎的整体主义制度观,也难以作出公平合理和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我国之所以走上压制型金融立法的路径,源于金融的特殊地位以及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背景。众所周知,晚近30余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计划经济体制的隐性税收机制逐渐解体,国民收入结构从“集财于国”向“藏富于民”转变。为了获取日益分散的金融资源与金融剩余,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显性)税收制度,二是金融制度。相对于税收工具,金融工具更容易得到执行。有学者指出,国家为了降低金融动员成本,通过对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开放及国有金融机构等进行金融控制,依托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地位对居民部门金融剩余进行动员,再利用利率管制、信贷倾斜、资金供给及证券市场准入等手段为公有经济部门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与租金补贴(武志,2014:3)。还有学者指出,政府通过金融组织体系的控制和对金融市场、金融对外开放的控制及对利率的干预管理,实现国有金融体系的信用垄断,确保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大多进入国有银行和国家控制下的资本市场而为国家所掌握,弥补财政收入不足,这是中国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控制的核心与实质(杨旭,2012:31)。国家对金融的控制过程,实质上主要就是通过立法对金融进行政府干预的过程。政府干预一方面是基于克服金融市场失灵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政治人”自利性考量的结果。在规则生成的政治维度下,政府培育市场与发展市场的双重任务演化为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金融抑制可以说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交织进化的结果。
金融立法的回应性不足给企业家精神带来了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及其功能的实现,一个必备的前置要件在于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存在良性关系。对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为企业家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与企业家建立一种友好的伙伴关系,尽量减少企业家的投资风险,提供更多的利润激励,帮助企业家筹措资金,开拓市场,同时在企业家力所不及的地方填补空缺。然而,在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下,政府不仅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还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企业家的角色,由此产生的一个弊端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创新机制、竞争机制和组织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企业家精神在管制中走向消沉。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立法回应不足与金融抑制对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家而言,国有企业家反而是受益者,这并非纯粹来自理论的推演,更有着实证上的依据。例如,有学者通过检索和追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网络媒体公开报道的企业家犯罪信息,共搜集了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家的涉案罪名主要集中在受贿罪、贪污罪等贪利型犯罪,而民营企业家的涉案罪名主要集中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融资型犯罪(张远煌、张逸,2014:12)。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即国有企业家往往握有特殊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反映出民营企业融资的制度性瓶颈以及民营企业家在压制型立法供给下的窘迫状态。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一个能有效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金融发展和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同样需要以公民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安排为前置条件。在以金融抑制为结构性特征的融资环境中,企业家的融资性权利受到限制,这压抑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进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三、 执法公正缺失、金融排斥与企业家精神的低迷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难以实施或实施效果不佳的法律无异于“没有牙齿的老虎”。执法作为最广泛而普遍的法律实施活动,在分配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信用和契约为核心的金融法治规则是金融市场赖以维系的根基,低成本和富有效率的执法活动则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如Pistor(2000)研究发现,执法效率是解释一国证券市场发展规模的一个重要变量,制约转型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执法效率的低下,执法效率比法律条文的质量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有更强的解释力。这是因为在这些转型国家,法律体系往往很不发达,执法机构经验又十分欠缺,导致正式的法律治理机制难以因应复杂的社会需求,执法失灵的问题多发常见。具体到我国,纸面上的法与金融市场中实际运行的法往往存在巨大反差,大量起实际作用的金融法律制度以“隐性规则”的形式存在,正式的金融法律制度供给面临被虚置或“空心化”的危险。这种有违契约精神的“金融潜规则”可能诱发运动式执法、“钓鱼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乱象,极大地恶化了本已脆弱的金融法治生态。其中,选择性执法对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最为显著和复杂。
有学者认为,国家根据情势需要什么时候严格执行哪部法律、采取什么执法手段、什么时候放松哪部法律的执行、什么时候严格执行哪个具体的案件、采取什么执法手段、什么时候对哪个案件执行特别对待的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执法方式,均可以称为选择性执法(戴治勇,2008:30)。在社会转型与法制转轨时期的当下,法律的不完备性、执法者信息能力的局限性以及执法资源的稀缺性交织在一起,使得选择性执法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选择性执法会使法律制度的公信力荡然无存,甚至成为投机取巧者可资利用的排他性工具。在金融领域,分业监管的权力配置格局决定了金融法律规则制定和实施的“部门化”倾向,作为执法者的“一行三会”充当着各自行业的“主管部门”角色,它们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写进法律文本,以至于《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础法律的修改很大程度上是银监会、证监会、保险会等金融监管机构扩充其权力空间的过程。金融执法涉及行政权力运作、经济资源调整和法律规范配置,在执法动机、执法任务以及执法考核方面容易被打上政治化的烙印,造成非理性与理性的冲突。事实上,我国金融执法领域由于行政权的非规范性引发的选择性执法现象屡屡发生,监管层次、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监管俘获等“选择性监管”无非是选择性执法在金融领域的投射而已。以证券监管执法为例,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承担着帮助国有企业融资解困的政策性任务,由此面临一个难以消解的悖论,即培育公平、公正、有序、有效的市场和“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的内在冲突,导致政府在证券市场上既充当执法者和监管者角色,又充当市场参与者角色,弱化了其作为监管者的市场监管职能。尤其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证券监管在不同情势下也表现出很强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执法行为如果任凭其蔓延下去,则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势必泛滥成灾,证券市场的法治化将遥不可及。
选择性执法现象频发的背后,隐含着金融监管对民营企业金融排斥的制度逻辑。在本文语境下,金融排斥指涉的是民营企业在金融市场中受到的制度性压制情形。这种制度性压制既存在于直接融资市场也存在于间接融资市场,一方面导致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在金融市场获得满足,另一方面导致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与融资权利遭到了严重限制。在直接融资方面,证券市场作为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场所,本应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企业,但却基于所有制的界分对民营企业上市融资设置了层层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在:(1)主板市场曾长期实行额度审批制,民营企业因难以从地方政府或证券监管部门获取额度而遭到排斥;(2)政府对国有企业上市提供了一定的隐性担保,可以将国有企业部分融资成本转嫁到国家信用上去,民营企业由于缺乏国家隐性担保造成退市风险增加,这种体制性安排造成的“政策租金”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排斥效应;(3)对公司盈利能力、成长性和净资产规模等指标的强调等门槛要求导致IPO程序繁琐、排队时间冗长,进而形成“优中选优”、“好中选好”的饥饿营销效应,“等不起”成为民营企业望A股而却步的重要制度诱因。在间接融资方面,民营企业遭遇的金融排斥现象更为突出,“惜贷”与信贷歧视为其主要表征,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融资机会。国内外的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严重不足。如有学者调查发现,国有企业的营运资本有36%~38%来源于当地银行,而私营企业只能从银行获得22%的营运资本,这说明中国的国有企业相对而言更加容易进入正式金融体系,而私有企业往往受到正规金融的歧视,这就严重压抑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Dollar & Wei,2007)。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内外交困之下,民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在此背景下,民间金融顺势兴起并在事实上发展成为与法定金融两轨并存的格局。然而,民间金融的正当性并不能缓释其合法性困境。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包容性不足。对民营企业的排斥意味着对国有企业的宽容,国有企业利用政府保护和政策红利不仅在垄断性行业坐享其成,而且在竞争性行业“与民争利”,进一步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支持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性金融是我国金融的本质特征(黄嵩,2007:128-151)。民营企业本来承载着培育企业家精神的使命,但在金融排斥等因素的影响下,民营企业家长期游刃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在违法与合法之间艰难地保持着平衡。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民营企业家只能蹒跚前行,处于“跪拜式生存”状态,难以有独立的人格,更不可能有高贵的风骨与精神。从思想根源上讲,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的排斥源于政治生态为其预设的两条原罪:一是民营企业家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二是民营企业家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在这两条原罪的阴影中,民营企业家独立人格的塑造与创新精神的培育都是不可能的。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国家,新教伦理赦免了企业家的贪婪罪,消除了人们的精神障碍,为经商和致富绕上了神圣的光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金融监管与执法机构有使命打破束缚在民营企业家身上的精神枷锁,通过公正执法为其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通过权利赋能释放自由、平等、法治、创新的价值观,使孕育着强大能量的企业家精神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四、 司法独立弱化、金融分割与企业家精神的式微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发挥着保障权利和控制权力、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捍卫人的尊严和维持社会公正等功能。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对于金融投资者与消费者权利保护、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均意义重大,构成了金融发展的坚强后盾。这主要表现在:(1)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与金融有关的纠纷日趋增多,司法介入金融纠纷能够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事实上承担起金融法律资源的配置功能。(2)法院承担着将纸面上的法律转换为运行中的法律的重要功能,司法介入金融纠纷能够弥补成文法的局限,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进而通过维护金融个案正义实现整体的金融公平。(3)法院作为宏观经济的“审查者”、微观经济的“校正器”和制度经济的“助推器”,通过司法审查、法律适用和司法决策构成了金融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4)现代国家的最高法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共政策法院,在规制经济方面具有“规则治理”的意义,不仅涉及与其他国家机关在规制金融领域的权力界定,更会影响到金融市场主体的利益(侯猛,2006:22)。当然,司法对于金融发展价值的彰显,是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这既是司法本质的需要,也是控制权力的需要,诚如有学者所言,提升地方司法的独立性,不仅有助于打破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市场分割,而且也不会破坏现有的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制度均衡,并促使地方政府做出保护私人财产和契约自由的可信承诺,进而有益于长期的经济增长(陈刚、李树,2013:31)。在任何地区,政治和法律的统一都是市场经济的福音,因为只有国家法制的统一才能保证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最佳配置,但这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地方法院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利益的压力和影响。在既有的体制安排下,我国的司法部门一直缺乏事实上的独立性:一方面,由于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的高度重合,人、财、物高度依赖于地方,因此法院被习惯看成地方政府的机构,导致法院的审判权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个案独立受到很大程度的牵制,这就是所谓的“司法地方化”;另一方面,法院系统内部在审判活动和法官人事管理中借用行政管理模式,将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混同,从而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就是所谓的“司法行政化”。司法的地方化与行政化背离了司法本性,是司法独立的制度顽疾,成为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可喜的进展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迈出了司法“去地方化”的步伐,但如何推进及效果如何,仍存在不确定性。
在我国金融市场的权力版图中,“强行政、弱司法”构成了权力配置格局的基本图景,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依附性体现得非常明显。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关于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问题上,各级人民法院发出通知,对已进入行政处置阶段的金融机构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受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正在执行的中止执行。这种司法权自动收缩的行为,显示出司法权在面对行政权扩张时的弱势心态,诱发了行政权力的软约束、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被漠视、道德风险的滋生等问题。面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严重的欺诈行为,司法常常难以作为。如通过“前置程序”设置制度障碍,这不仅直接违背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法律原则,还变相剥夺了受害人的诉权,将投资者置于一种极为被动的状态。即使被告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受理了案件,由于法院在人事、财政和住房等福利上都由本地政府支配,而上市公司又是当地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可想而知。可以说,我国司法机制的运作对于投资者保护的贡献有限,普通投资者经常面临无法通过司法渠道有效救济权利的困境。与投资者保护的“司法失灵”相对应,民营企业的司法保护同样不容乐观,相信“关系”不相信司法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的“无奈选择”。尤其是近年来,民营企业的融资纠纷趋于增多,但“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的司法乱象压抑了民营企业寻求司法保护的冲动。即使正常进入了审判环节,法院对民营企业融资行为的司法审查也不是基于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和鼓励交易的原则,而是遵循“法条主义”的管制逻辑,这在“对赌协议第一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潘林,2014:174)。在吴英案中,法院更是逾越司法谦抑性的边界,主动性地承担起政策性的社会治理功能,充当了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规制与行政监管“替代品”的角色。
司法权的地方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较为微妙,往往通过上市公司反映出来。上市公司作为一种稀缺的金融资源,既可以为地方政府增加税收,又能够为地方官员提供利益输送的通道,所以地方政府习惯于通过土地划拨、税收减免、政府补贴或奖励等手段推动本地企业上市。当这些企业涉案时,地方政府会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要求减免相应的处罚。以绿大地公司造假上市为例,调查人员在整个调查取证过程中面临着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公安部门对绿大地董事长的批捕方案曾数次被地方驳回,证监会把绿大地欺诈发行事件移交司法机关后,当地法院一审却从轻发落,后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地方检察院和法院才被迫提起再审。事实上,地方法院在案件受理、审理和执行等环节都明显地存在偏袒本地当事人并损害外地当事人的情况,当地企业的胜诉率也远远高于外地企业(刘作翔,2003:90-92)。司法权的地方化严重侵蚀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使得司法的统一性在地方政府保护主义下被肢解,由此导致的“法治割据”进一步固化了金融分割的现实格局。金融分割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资本的匮乏必然导致金融管制,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长期以来,在金融管制及地方保护主义下,公司的跨地区投资、银行体系的跨地区借贷、资本通过股票与债券市场的跨地区发行均是不自由的,金融市场被人为割裂为不同的区块,深刻阻碍了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形成(王迪明,2006:51)。司法对于改善金融分割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因为金融分割的本质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引起的金融管制,而司法权作为制衡行政权力的重要力量,能够起到抑制地方政府过度管制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但在司法权地方化的语境下,地方法院在人、财、物的牵制下沦为了地方利益的维护者,难以起到制衡地方行政权力的作用。金融分割意味着土地、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难以通过市场进行最优配置,进而会加剧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失衡与断裂,这样的制度环境不适宜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而正是这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外部制度环境阻碍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五、 面向企业家精神的金融发展法治化变革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善治的制度空间涵盖立法、执法与司法,能够为金融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由于立法回应不足、选择性执法、司法独立弱化均与良法善治背道而驰,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制度重构以促进金融发展和彰显企业家精神,这也在事实上构成了金融发展法治化变革的路径。
首先,以回应型立法助推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为此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在金融刑法方面,修改或废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融资型犯罪,制定“放贷人条例”,特别是要区分金融诈骗和正常的投资行为;在人民银行法方面,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商业银行法方面,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引入差异化监管,通过发展竞争性金融市场使具有竞争能力的金融家和金融机构成长起来;在证券法方面,扩大证券范围,引入股票发行注册制,真正发挥资本市场在资产定价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民间金融立法方面,要制定“民间金融机构法”、“社区再投资法”等法律,保障企业、个人多元化融资权利的实现。这些回应型的立法制度供给,将终结金融抑制的历史,开辟金融深化的新纪元。
其次,以监管治理诱导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鉴于选择性执法对法治的破坏以及对人权的侵犯,强化对选择性执法的治理显得异常重要。由于金融监管机构是金融市场的执法者,选择性执法治理主要指向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治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2年发布的《监管的独立性和金融稳定》和《危机防范和危机管理:监管治理的角色》,监管治理强调的是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问责性、透明性、监管操守。独立性是指监管机构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的牵制而做出客观和理性的判断;问责性是指监管机构不仅要对政府和立法机构负责,还要对被监管机构和公众负责;透明性是指杜绝暗箱操作与监管寻租,使决策阳光化,确保公众对监管信息的可获得性;监管操守是指监管人员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确保其执行善治的制度目标而不是向他们的自利行为妥协。监管治理意味着金融监管机构秉持客观公正的价值立场,通过公开透明的监管执法程序,为金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由于不再受制于金融排斥的困扰,民营企业获得了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法律地位及融资权利,这种包容性或者普惠性的金融体系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最后,以司法独立引领金融分割走向金融一体化。司法权的地方化与行政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性难题,当前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可视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最新努力。为了不让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再次沦为制度试错的牺牲品,必须在法官的遴选、任免与薪金保障以及司法经费等方面作出实质性改革,削弱甚至断绝地方政府对地方司法权的实际支配能力。与此相配套,改变现行的官员考核制度,重塑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司法审查保护私人产权进而制衡地方保护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冯兴元,2010:166)。基于路径依赖的影响,司法权的“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均困难重重,但并非不可能实现。事实上,美国曾在19世纪通过积极的司法干预克服了国内市场分割的问题,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程金华,2010:74)。我国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通过自上而下的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倒逼形成司法改革合力,将“顶层设计”与“地方试点”有机结合,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由于司法独立有助于保护私人产权和契约自由,促进民间投资和市场繁荣,它完全可以成为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源泉。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司法独立的渐进实现,金融分割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多层次金融市场将实现互联互通,金融的“深化”与“宽化”将得到显著改进,全国金融市场一体化以及普惠金融体系的实现亦不再遥不可期。
六、 结语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金融的本质或核心功能就是筛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重温熊彼特一百多年前的这一论断,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思辨力依然历久弥新。然而,学界在探讨“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论题时,几乎都是置于经济学或者金融学的语境和立场加以展开,未能跳出观念藩篱与学科壁垒,以至于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思维怪圈。笔者试图打通法学与金融学之间的知识谱系沟壑,提出并证成这样一种观点:立法回应不足、执法公正缺失与司法独立弱化分别诱致了金融抑制、金融排斥与金融分割,致使企业家精神的消沉、低迷与式微,这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通过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逻辑。这一论断的提出与证立,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在理论层面上,现有的“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范式对法律的作用认识不足,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虽然强调法律对金融发展的作用但没有深刻意识到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应是金融发展的本质所在,因此从法律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补缺意义,体现出一种科际整合的方法论上的自觉。在实践层面上,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成为决策者与公众关注的核心话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了当下主导性的社会话语,而企业家作为创新的主力军和“经济增长的国王”,天生是一个破坏者——破坏旧的秩序、旧的规范、旧的习惯,同时创造新的经济生活、新的经济体制、新的价值观念,如果能够为企业家精神进行法律松绑,则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找到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本文事实上为此描绘了一张“路线图”。总之,通过法治助推金融发展并重振企业家精神,是一项必要、可行且无可回避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刚、李树(2013).司法独立与市场分割——以法官异地交流为实验的研究.经济研究,9.
[2]程金华(2008).地方政府、国家法院与市场建设——美国经验与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3]戴治勇(2008).选择性执法.法学研究,4.
[4]冯兴元(2010).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北京:译林出版社.
[5]黄韬(2013).“金融抑制”的法律镜像及其变革——中国金融市场现实问题的制度思考.财经科学,8.
[6]黄韬(2012).“金融抑制”与中国金融法治的逻辑.北京:法律出版社.
[7]黄嵩(2007).金融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解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8]侯猛(2006).美国最高法院对经济的影响力:一个述评.法律适用,8.
[9]刘作翔(2003).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法学研究,1.
[10] 卢峰、姚洋(2004).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1.
[11] 潘林(2014).“对赌协议第一案”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4.
[12] [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2004).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 王迪明(2006).中国金融市场分割问题探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3.
[14] 武志(2014).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15] 杨旭(2012).中国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控制——基于金融史视角.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6] 张远煌、张逸(2014).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河南警察学院学报,1.
[17] Dollar D.,Wei S.J(2007).Das (Wasted) Kapital: Firm Ownership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IMFWorkingPaper,WP/07/9.
[18] Katharina Pistor(2000).The Standardization of Law and Its Effect on Developing Economies.G-24DiscussionPaperSeries,No.4.
[19] King,R.& Levine,R(1993).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8.
[20] King R.G.,Levine R(1993).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World-BankConference.
■作者地址:江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jiachun@whu.edu.cn。
李安安,武汉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李媛
◆
Rule of Law,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JiangChun(Wuhan University)LiAnan(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Inadequate legislative response,missing impartial law enforcement and weak independence of judicature are the legal incentives for financial repression,financial exclusion and financial division,which leads to depression,downturn and decline of entrepreneurship,and they are the reasons for financial development not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by supporting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In order to foster entrepreneurship and encourage economic growth,the key reform of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 should promote financial repression towards financial deepening by responsive legislation,induce financial exclusion towards financial inclusion by regulatory governance,conduct financial division towards financial integration by judicial independence,and create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financial development,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financial inclus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ependence of judicature; entrepreneurship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309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4M550403)
DOI:10.14086/j.cnki.wujss.2016.0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