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原则的法治思维析论
2016-03-14祝捷
祝 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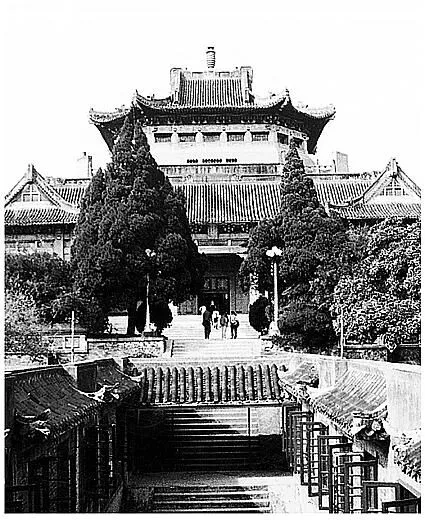
“一个中国”原则的法治思维析论
祝捷
摘要:将法治思维运用于两岸关系研究,不应仅将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复现政治立场的工具,更应是为解决两岸间的棘手问题提供可资适用的法治策略,继而使法律规范实现从“法理立场”到“法治策略”的功能嬗变。在法治思维下,“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内涵可从法律发生意义和法律实施的角度两方面加以理解,而解决“承认争议”则构成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意识。通过构造和运用“宪制-治理”框架,为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提供了可能路径。
关键词:两岸关系; “一个中国”原则; “宪制-治理”框架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为我国现行《宪法》所确认。自《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政界和学界共识。目前,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两岸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抵御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常态化”趋势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和现实之需。与需求相比较,学理层面的研究相对滞后,原因在于:两岸关系研究长期未能落入法学研究的论域内,相关知识储备和理论工具不足;法律规范、法律方法等法治资源在两岸关系中经常扮演的是“立场确认”或“立场复现”角色,法治资源的策略性功能未获得足够重视。为此,笔者拟从梳理法律规范在两岸关系中的功能嬗变入手,挖掘“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内涵,特别是借助两岸各自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宪制性规定和两岸都已经接受的“治理”思维这两大法治资源,构造“宪制-治理”框架,探讨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的方法与路径。
一、 从“法理立场”到“法治策略”:法律规范在两岸关系中的功能嬗变
(一) 当前两岸关系中法律规范的功能:“法理立场”的供给及其窘境
由于台湾问题长期执拗于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议题,中国大陆的台湾问题研究因而一般落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学科论域。法治思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占据台湾问题的话语主流,难以发挥法治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拉动作用。
然而,这并不表明法律规范缺位于台湾问题论域。早在1954年,台湾当局通过“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就开始运用规范方式对两岸关系进行定位与调整(周叶中、祝捷,2007:20)。1990年起,台湾当局在“宪法增修条文”中专列“两岸条款”,并在稍后制定的“台湾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细化台湾地区居民与大陆居民交往的具体规范。2005年,中国大陆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再次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2008年后,两岸签署的多项两岸协议,也被认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法治化成果(杜力夫,2011:6)。可以说,法律规范已广泛存在于两岸交往的各个层次。
对于两岸关系而言,法律规范有着三重功能:第一,用权威化的语言确认大陆和台湾地区各自确定的两岸政策,以及两岸借由商谈机制形成的共识,增强政策和共识的规范性与权威性;第二,利用法律规范的公开性特征,将两岸政策和共识予以公示,增强两岸政策和共识的透明度,也借此汲取两岸事务的民意正当性;第三,借助法律的规范形式,为两岸各交往主体提供行为指引,确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功能的实现,都必须立基于两岸既存的政治立场、政治决策和政治共识,即法律规范所供给之内容,是具备法律规范外观的政治立场,其功能毋宁是为两岸关系提供“法理立场”。法律规范为两岸关系提供“法理立场”的功能,在台湾当局法务部门有关《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说帖中获得了充分地展示。该说帖认为,前述协议“相关之合作内容,系在我方现行的法令架构及既有的合作基础上,以签订书面协议之方式,强化司法合作之互惠意愿,同时律定合作之程序及相关细节,提升合作之效率及质量。”按此说帖,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并非是两岸协议所创设的新合作事项,而是已经存在于两岸各自规定和合作实践中,两岸协议的功能仅限于确认两岸已经形成之合作立场和基础。
由此,法律规范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而是单向度地映射政治场域已经形成的立场,在两岸关系中面临着实践窘境:第一,透过法律规范呈现之“法理立场”,仅仅是对特定政治立场的“规范美化”,对政治力无实际影响力和约束力,政治立场一旦改变,体现特定政治立场之法律规范有遭政治力修改、虚置乃至破弃之虞;第二,法律规范仅仅是回溯性地确认政治立场,对于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缺乏构造力,导致法律规范的型塑功能无法在两岸场域内获得实现,限缩了法律规范的适用余地。法律规范实践窘境的肇因,仍是法治思维在两岸论域内未获得充分发挥,法律规范仅仅被视为确认政治立场的工具。推动法律规范摆脱在两岸论域的尴尬地位,必须摆脱工具主义的法律观,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等法治资源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推动法律规范在两岸关系中的功能嬗变。
(二) “策略定位”范式与法治思维的融合:作为“法治策略”的法律规范
当前从法学角度研究台湾问题,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对台湾地区或者两岸间的某个具体制度、重要案例的研究;第二,将法律规范作为研究线索或支撑结论的论据,目的是补强政治观点或政策言说;第三,引入若干法学概念,用以解释两岸关系中的某些现象。这三类研究对于法治思维在台湾问题论域的推展虽有助力,但距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求仍有距离。从法学角度研究台湾问题,应当为解决两岸间的现实问题提供可资适用的法治策略。
法治策略是“策略定位”范式和法治思维相结合的产物。“策略定位”范式源于台湾地区学者对于两岸谈判的研究,其逻辑起点是两岸的“不对称博弈”。台湾地区学者认为,由于两岸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影响力上的巨大落差,两者构成了“不对称博弈”。但是,两者实力上的“不对称”,只是“总和造构权力”的不对称,即两岸总体实力的“不对称”,并不必然决定谈判的最终胜负。台湾地区可通过选择合适的议题策略和行为策略,扳回两岸在“总和构造权力”上的“不对称”(初国华,2007:13、62)。对于“策略定位”范式,大陆学者多以不变之“一中”立场应对之,并针锋相对地形成了“立场定位”的范式。前述法律规范所承担的“法理立场”复现功能,亦是“立场定位”范式的产物。“立场定位”范式当然是符合两岸历史与现实的,其优势是能够从学理上强化研究所持之立场,但仅使用“立场定位”范式的缺陷也十分明显:“立场定位”范式本质上是对特定政治立场的理论复现,对支撑立场所需的制度构建和实现途径关照不足;“立场定位”范式所得结论的正当性有赖于政治立场本身的认受性,一旦支撑研究结论的立场被质疑或否定,则研究结论的正当性亦将遭受质疑或否定。因此,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立场不动摇的前提下,台湾问题研究可引入“策略定位”的范式,使台湾问题研究的成果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透过“策略定位”的研究范式,法律规范可以作为法治策略(而非单纯用于表述特定政治立场的规范语句)引入台湾问题论域。对此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1)法律规范为形成特定政治立场提供法治资源,法律规范虽仍用规范语言表述特定政治立场,但并非是透过规范语句对政治立场进行单向度复现,相反,政治立场之形成应充分体现法律规范的意旨,受法律规范约束;2)法律规范为衡量两岸关系和两岸各自的政治立场提供法治标准,将两岸为达成政治妥协而形成的各种“建设性模糊”表述,用“合规范性”予以界定,防止本已模糊的政治共识空洞化,两岸在选择各自的政治立场时,至少应当符合各自的规定以及两岸业已形成的制度性共识,将“合规范性”作为政治立场选择的重要考量;3)实施法律规范为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法治路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诸类事项以两岸各自规定和两岸制度性共识的方式固定下来,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就是实施相应法律规范的过程,从而将特定的政治过程转化为法律实施的过程,既降低了政治过程的敏感性,也提升了两岸民众对于特定政治立场的认受度。
法治思维在台湾问题论域内的展开,绝非是对法律规范的附带性、佐证性地运用,而是将一种全新的策略思维引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法律规范也在从“法理立场”到“法治策略”的功能嬗变中,成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最为根本的理据,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框架提供了规范支撑。
二、 “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内涵及问题意识
(一) “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内涵:基于客观事实与认识论统一的透视
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内涵,是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从两岸现实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逻辑谱系而言,“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原则,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认识论基础。
当前文献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论述主要分为两股(黄嘉树,2001:1-5;李松林、祝志男,2012:176-180):第一股从两岸互动的史实出发,论证“台湾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命题,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在历史维度的正确性;第二股从认同心理、文化属性、经济关联、国际承认等现实维度,论述“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两股文献论述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逻辑起点都是将“一个中国”视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使用各种历史材料和现实证据论证这一事实的成立。这一逻辑起点、论证思路和论证材料当然是正确的,构成对“一个中国”原则最为有力的支撑,但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于历史材料和现实证据的解读,存在着多视角性,同一材料既可以从“一个中国”的角度解读,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解读,特别是“以台湾为中心”的历史观,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按“政治反抗文化”理论重新解读台湾历史的说辞(王泰升,2001:13),前述论证的有效性受到冲击;其二,来自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性只能覆盖曾经的历史时空和既存的现实时空,而无法对尚未发生的未来时空进行有效覆盖,亦即以客观事实解读“一个中国”原则,虽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溯性充分论证,但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后及性的关照不足。
虑及此,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应当更加丰富和多元,除需继续坚持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展开论证外,还需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在透过认识论解释“一个中国”原则的过程中,法律规范成为承载两岸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认识和认知的主要载体,“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内涵因而能从认识论的角度获致澄清。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两岸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既存客观事实,而且是两岸的共同认知,亦即“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也投射在两岸各自的主观认识上,为两岸所认可。对此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两岸在主观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认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对于历史材料和现实证据按照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方向进行解读,应避免有意误读或歪曲之;第二,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两岸存在着差异,但两岸能够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对各种差异化的认识进行统合与容纳,“九二共识”因而成为两岸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在认识论层面的替代性表述;第三,两岸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认识具有持续性和连续性,不仅存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也覆盖尚未发生的未来时空,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都形成有效约束。
“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岸各自主观上的投射,并非只是构成一种观念意识,而且对于两岸各自的立法产生直接影响。两岸各自规定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不仅是确认客观事实的事实性原则,而且是体现两岸各自主观上立法意图的法律原则。据此,“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从立法意义或法律发生意义而言,两岸各自规定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规定,是对客观现实的法律确认,亦即法律规范是确认“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客观事实的载体;第二,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而言,“一个中国”原则对于两岸后续发生的行为和事件形成具有规范意义的约束,亦即法律规范是两岸各自对“一个中国”原则认知的建制化,也构成了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存续的制度性保障。
(二) 解决“承认争议”: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意识
吊诡的是,两岸虽均在法律规范层面将“一个中国”原则确认为法律原则,甚至形成“九二共识”的认识论表述,以包容差异化的“一个中国”认知。但两岸至今未能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形成政治互信,“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地区甚至迭遭质疑和抨击。更有甚者,“一个中国”原则已经被台湾地区现行“宪法”确认为一项具有根本性的法律原则,却屡次因台湾地区“政党轮替”遭受冲击。一项本应十分稳固的法律原则,却遭遇种种冲击和动摇,原因自然是多元且复杂的。制度层面的原因,是两岸至今存在着严重的“承认争议”,导致两岸虽有“一个中国”的共识,但因“承认争议”的阻隔而无法获致融通,政治区隔因而无法消弭。“承认争议”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治领域,“承认争议”体现为大陆和台湾是否承认对方拥有“主权”和是否为“国家”的争议;在国际关系上,“承认争议”体现为大陆和台湾是否承认对方为国际法主体以及是否有权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争议;在经济上,“承认争议”主要体现为台湾方面对大陆资本采取的限制性经贸政策,特别是对于大陆国有资本的各种制度限制。在法理上,“承认争议”则主要体现为大陆和台湾是否承认对方的宪制性规定(即大陆的1982年宪法和台湾地区现行“宪法”),以及根据宪制性规定建立的公权力机构的争议,包括:两岸互相否认对方作为“国家”和“政权”的“正当性”;两岸互不承认对方宪制性规定和具有公法性质的规定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两岸互不承认对方公权力机构和政治职位的“合法性”。
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意识,不限于论证两岸在“国家”、“主权”等政治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更不在于臆造各种无可能性的“政治新形态”去包容两岸,而是如何解决横亘在两岸间的“承认争议”。从发生意义上讲,“承认争议”的产生机理是:第一,两岸虽形成“九二共识”,但“九二共识”并未消除两岸各自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差异化认知,相反,“九二共识”是以尊重此种差异化认知为基础的;第二,两岸对于“一个中国”的差异化认知,在两岸交往中或许能够通过“九二共识”予以包容,但在两岸各自实际控制的区域内,“九二共识”的包容性呈现出递减效应,两岸各自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内,因而依然保留着各自的“中国论述”;第三,两岸各自保留的“中国论述”又影响着各自的立法,特别是宪制性规定的创制;第四,而宪制性规定对于各自“一个中国”认知的规定,又运用建制化的力量,确认和保障了各自对“一个中国”认知的差异化。在略显繁琐和缠绕的逻辑基础上,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差异化对立格局,由两岸各自的法律规范所确认并保障,成为两岸各自建立公权力体系的基本法理。
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目的并不是解构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差异化对立格局——这是另一个更加庞大和复杂的政治工程——而是尽力地借助法律规范这一法治资源,运用法治方法,将两岸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差异化认知,在法治框架内予以融合,扫除此种差异化认知对于两岸关系的阻滞,提升两岸关系的抗压能力。
三、 “宪制-治理”框架的机理与运用
(一) “宪制-治理”框架的构造机理
两岸学界对“一个中国”原则及两岸相互关系的解释,依然无法跳脱出“主权-治权”的论述框架。“主权-治权”框架的基本思路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因而在主权上是统一的,但两岸实际上处于“分治”的状态,因而在“治权”上是分离的,这种“主权统一而治权分离”的状态,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也是“一个中国”原则的现状。“主权-治权”框架是目前两岸学界居于主流地位的解释框架,但也存在着明显缺陷:第一,“主权”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确定性和约束性不足,偏向“台独”的学者亦可论证所谓“台湾主权”;第二,“治权”概念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两岸“承认争议”未能解决的情况下,“治权”概念能否在两岸间使用仍存争议;第三,“主权-治权”框架重在描述和解释两岸政治现状,对于“承认争议”之解决不仅欠缺助益,反而以两岸的差异化对立格局为基础。
“主权-治权”框架是政治思维在两岸关系上的经典运用,其间虽涉及法律规范,但法律规范主要是运用于表征两岸在“主权”、“治权”问题上的立场。法律规范的功能仍是将政治立场表述为“法理立场”,法治策略层面的功能供给不足。因此,有必要运用法治思维补足政治思维在合规范性和可接受性上的缺憾,选择两岸都能接受的法治话语,借助两岸共同肯定“一中”的法律规范,超越“主权-治权”框架,形成足以消弭“承认争议”,在法理上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的新理论框架。这种新理论框架的选择,对应法律规范作为法治策略的三个面向,即法治资源、法治标准和法治路径,应当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新理论框架应当充分运用法律、司法解释、裁判等法治资源,尤其是选择两岸各自规定的交叠部分,表征“一个中国”的两岸共识,同时借助法律规范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的约束性和有效性,目的是借助法治资源夯实两岸对于“一个中国”的认知基础;第二,新理论框架应当为判别两岸相关主体(如公权力机构、政党、民间团体、政治人物和民众等)的行为是否符合“一个中国”原则,提供具有拘束力和可操作性的规范,目的是形成判别“一个中国”原则是否获得维护的法治标准;第三,新理论框架应当为两岸解决“承认争议”提供可行的法治路径,推动两岸的差异化认知在两岸都可接受的法治框架内获致融合,最终提升两岸关系的抗压能力。
为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笔者对两岸既有的“主权-治权”框架予以改造,构造更具法治意蕴的“宪制-治理”框架:第一,“主权”在法理层次上首先体现在两岸各自的宪制性规定上,两岸各自的宪制性规定都包含对“一个中国”“主权”的宣示和规定,为避免使用两岸间仍具争议的“宪法”一词,本文使用相对中性和技术化的“宪制”代替“主权”,将在两岸各自范围内具备最高法律效力的宪制性规定所体现的“一中性”,作为巩固“一个中国”原则最可倚重、也是具备最高约束力的法治资源;第二,两岸都确认了宪制性规定在法治社会的普遍约束力和最高法律效力,因此,两岸各自宪制性规定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规定,不仅是一种“法理立场”的表征,也是制约两岸各自域内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相关主体行为的根本规范,构成判别上述行为是否与“一个中国”原则相抵触的法治标准;第三,两岸在各自实际控制区域内,都形成了以法治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体系,“治理”非专指公权力机构,也包含两岸各层次主体在内,因而较之“治权”更具可接受性,因此,笔者使用“治理”代替“治权”,将两岸各自规定视为治理依据,将两岸各自的公权力机构视为治理主体,用具备多元特质和开放特质的治理理论,为解决“承认争议”提供法治路径。
综上所述,“宪制-治理”框架实际上借助了“宪制”的法治资源优势和法治标准特征,“治理”在法治话语和法治路径上的中立性和可接受性,是法治思维在巩固“一个中国”原则中具体运用的切入点。
(二) “宪制-治理”框架在巩固“一个中国”原则中的运用
“宪制-治理”框架在巩固“一个中国”原则、消弭两岸“承认争议”问题上的基本思路,是寻求并能动地构造两岸对于“一中”的法治公约数,构建两岸治理结构,为解决“承认争议”、不断深化两岸共识以及提升两岸抗压能力提供法治框架。
第一,两岸签署具有宪制性地位的协议,推动“九二共识”的宪制化,夯实两岸解决“承认争议”的法理基础。“九二共识”是两岸解决“承认争议”的认识论基础,但“九二共识”至今仍是一项“口头协议”,岛内部分政治势力对“九二共识”的性质、效力甚至是否真实存有质疑之声。推动“九二共识”的成文化、法理化甚至是宪制化,使之从一项基于两岸共同认知的认识论原则,上升为两岸间具有根本性的法理原则,有着重大意义。“宪制-治理”框架不仅依托两岸各自宪制性规定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规定,也推动形成能够包容两岸的宪制性协议。2007年10月,大陆方面已经提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构想,台湾方面予以了积极回应。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对于和平协议这一构想的共同认可,彰显了这一构想的可接受性,也为和平协议作为两岸的宪制性协议提供了可能性。两岸在和平协议中对“九二共识”予以成文化和宪制化,确立和巩固“九二共识”的法理地位,使之不仅能够继续为两岸交往提供政策引导,而且能够在法理层面增进两岸互信、解决“承认争议”提供依据。
第二,深挖两岸各自宪制性规定的“一中性”资源,拓展“一个中国”原则作为法治标准的适用空间。从法治策略的角度出发,“宪制-治理”框架所倚重者,不仅是两岸各自宪制性规定所提供的法理立场根据,还包括宪制性规定在巩固“一个中国”原则上的能动作用。两岸各自宪制性规定中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规定,在学理上可归类为“基本国策”条款(陈慈阳,2005:80),对两岸各自的公权力机构设定了根本层次的授权与委托,两岸各自的公权力机构因而有义务采取各种措施推进“一个中国”原则的巩固与实现。衡判两岸公权力机构和其他相关主体是否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标准,因而从是否认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相对消极的标准,向更加积极的是否维护、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标准拓展。
第三,构建两岸治理结构,以之为核心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框架,为两岸对于“一中”的差异化认知在两岸治理的过程中不断融合,从而为解决“承认争议”提供法治路径。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归根到底是推动两岸对于“一个中国”的差异化认知不断融合。这就需要一个足以包容两岸的框架,让两岸的差异化认知能够在这一框架内进行交流、妥协,最终获致融合的效果。当前两岸虽建立了多层次的交往管道,也形成了由授权民间团体构成的事务性商谈机制和两岸事务部门负责人直接对话机制,但公权力机构、民间团体、政党、城市以及民众等各层次的交往,都呈现出孤立、零散的状态,并未真正形成有序、统一的框架。“宪制-治理”框架运用两岸都能接受的治理思维,建构两岸多元主体共同参加的两岸治理结构,形成足以包容两岸、推进两岸相关规定适用和鼓励两岸公权力机构互动的制度框架。通过治理思维的引入,两岸可以借助社会参与、多元共治、民意主导、平等协商等治理因素,深化两岸互信和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减弱以至消弭两岸在一中问题上的差异性认知。
四、 结语
巩固“一个中国”原则,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框架,既需要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也需要法律学人的法律智慧。运用法治思维巩固“一个中国”原则,运用法治策略缓和两岸因政治对立造成的紧张关系,将两岸对于“一中”的共识宪制化,推动两岸交往的治理转向,有助于提高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法规范理性和法技术理性。在此方面,本文所提出的“宪制-治理”框架为法治思维的运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路径,也为从宪制的高度巩固“一个中国”原则提供了一种可能。
参考文献:
[1]陈慈阳(2005).宪法学.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2]初国华(2007).不对称权力结构下的两岸谈判:辜汪会谈个案分析.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3]杜力夫(2011).论两岸和平发展的法治化形式.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4]黄嘉树(2001).“一个中国”内涵与两岸关系.台湾研究,6.
[5]李松林、祝志男(2012).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九州出版社.
[6]王泰升(2001).台湾法律史概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7]周叶中、祝捷(2007).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地址:祝捷,武汉大学法学院、201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Email:fxyzjie@whu.edu.cn。
■责任编辑:李媛
◆
Consolidation of “One China” Princi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Thinking
ZhuJie(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Applying legal thinking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researches means that legal norms are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political stand,but also a rule of law strategy that deals with tricky cross-Strait issues which may later contribute to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legal norms from “judicial stand” to “rule of law strateg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thinking,the judicial connotations of “One China” policy could be comprehended through the aspects of law occurrence and law enforcement.Meanwhile,solving “recognition dispute” serves as the problematic consciousness of “One China” principle.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nstitution-Governance” framework contributes to possible way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One China” principle with legal thinking.
Key words:cross-strait relations; “One China” principle; “Constitution-Governance” framework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CZZ013)
DOI:10.14086/j.cnki.wujss.2016.0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