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价值的融合:伊斯顿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
2016-03-14张涵之
张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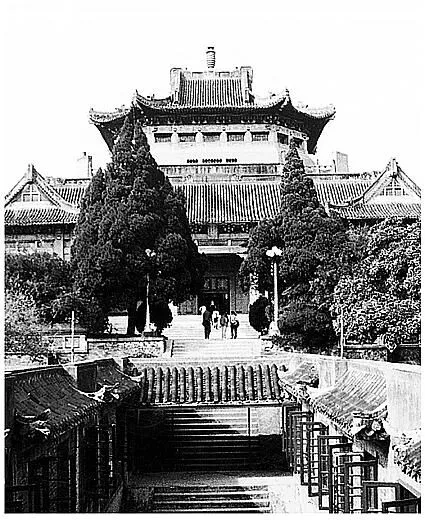
事实与价值的融合:伊斯顿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
张涵之
摘要: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政治学方法论争论的焦点。行为主义政治学倡导的“价值中立”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遭遇了现实困境,致使行为主义方法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研究丧失了效力。针对政治学的这一研究现状,伊斯顿对实证主义的观察方法与历史主义的解释方法进行了批判,并倡导价值的回归与重塑,主张把事实与价值统一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中。事实与价值的融合,正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伊斯顿遵循这一逻辑而创立了政治系统论,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开创了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戴维·伊斯顿; 政治学方法论; 行为主义政治学; 后行为主义; 政治系统
休谟问题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个纯哲学问题,也是政治科学方法论研究所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采用和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在政治学研究中对事实和价值的不同偏好是造成传统主义政治学派、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之间分野的根本原因。传统主义政治学派在研究中“兼具历史性和规范性”(格雷斯比,2013:21),对事实作出解释,同时也兼顾价值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则强调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即祛除价值,这种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实证做法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叶行为主义的兴盛和政治哲学的衰落。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行为主义无法对当时的政治现象作出解释,美国的政治学界爆发了一场旨在修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革命,即后行为主义革命。后行为主义者批判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研究立足点,而倡导价值回归,力图实现事实与价值的融通。由此看来,对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解直接影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并构成后者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
自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以来,韦伯继承和发展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分立说,波普尔、罗尔斯等也在自己的思想中贯彻了事实与价值分立的原则。而事实与价值的分立,在实用主义学派那里遭到了批判。杜威指出,科学判断的逻辑价值不仅取决于“实践的考虑”,还取决于价值方面的“道德的考虑”(Dewey,1903:115)。普特南也认为,“没有我们的价值的人类多样性,其中就不会有表达规范”(普特南,2006:148)。实用主义学派虽然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消解事实与价值的裂痕。相对于实用主义学派,与伊斯顿同一时期的多元民主理论家达尔并没有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进行专门的批判,但他在确立民主体制的标准时把“民主的理想或目标与民主的现实”(达尔,2012:25)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对如何消解价值与事实之间裂痕的具体分析。与之不同的是,伊斯顿不但反对事实与价值的对立,而且把事实与价值的和解与统一作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政治系统理论的研究中。伊斯顿于1953年发表的著作《政治系统:政治学现状研究》奠定了他作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创者”的地位。他于1965年出版的《政治分析的框架》和《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则明确表明了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后行为主义倾向。1969年伊斯顿在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时发表了题为《政治学的新革命》的就职演说,该文成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作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伊斯顿是如何倡导价值重塑的?事实与价值的和解与统一又是如何在他的系统论思想中得到体现和运用的?伊斯顿的思想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有着怎样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考察与探讨。
一、 价值的回归与重塑:伊斯顿对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批判
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是“令人不安和失望的”(伊斯顿,1993:38),在伊斯顿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的政治理论知识严重匮乏,而政治理论知识的匮乏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研究所采取的方法造成的。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观察方法与历史主义的解释方法对事实与经验的重视以及对价值的忽略导致了现代政治理论的衰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普遍采取实证主义的观察方法。以实证研究著称的典型代表芝加哥学派注重社会观察,强调解决实际社会问题,这对美国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政治研究工作很少超越它本身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伊斯顿,1993:42)。伊斯顿自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起一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因此,他对芝加哥的实证之风对政治学的影响深有体悟。伊斯顿尽管赞成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但也看到了这种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时的弊端,认为“不能再指望全盘科学论证作为帮助我们了解社会问题的手段了”(伊斯顿,1993:5)。伊斯顿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特征:把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运用于政治研究中;把价值观念同因果理论对立起来。
政治学领域的实证主义吸收了经济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把经验作为一项指导方针,以期通过观察和记录资料以及“整理和检查那些资料或数据”(伊斯顿,1993:45)来研究政治。伊斯顿指出这种机械式的研究方法忽略了政治上的变化。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断地、纵然有时是不知不觉地变化着。”(伊斯顿,1993:41)然而,自然科学的观察法要求研究的状况或者条件是固定不变的,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研究变化着的政治现实,不可避免地致使政治研究工作仅仅停留在最初的发现阶段,无法上升到“阐述命题的严格状态或表达概念所含意义的确切程度”(伊斯顿,1993:43),也即是说,这种方法使政治学研究只能停留在“是什么”的实然阶段,无法到达“应该怎么办”的应然阶段。这种状况反映在政治实践领域,也即是,我们尽管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发现现行政治体系的缺点,但由于我们缺乏克服这个缺陷的应然知识和价值判断,只能采取保守的态度,仍然把现行政治体系当作“一切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的世界的最佳政治体系”(伊斯顿,1993:42),而不对其进行改善。这种做法在伊斯顿看来一如希腊哲学思想探求稳定状况的行径一样是危险和有害的。
政治学研究中单纯的观察方法对政治条件变化的忽略易于导致政治发展的停滞,而因果理论对价值观念的屏蔽则使我们不能“以起码的逻辑关联性建构一个理论”(伊斯顿,2012:10)。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力求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旨在指出政治事实之间的联系,由这种方法形成的理论被伊斯顿称之为“因果理论”。而伊斯顿认为在政治研究中祛除价值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果理论中往往包含着既定的价值观念。任何一种理论主张都不可能“发现一种只表示情绪或只说明事实关联的主张”(伊斯顿,1993:210)。政治事实之间的关联,往往取决于价值观念。对于理论而言,若是没有价值判断,就失去了深远意义,理论中的逻辑关联正是基于事实与价值观念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建构起来的。而且,“推动政治学发展的力量显然是属于道德性质的”(伊斯顿,1993:210)。
在伊斯顿看来,行为主义力图排除价值,采取严密的科学方法对政治学进行实验式的研究。这种对政治生活研究的科学论证不仅是无益的也是徒劳的,因为大部分的政治学著作是“不难为未经政治学专业训练但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所理解”(伊斯顿,1993:45)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即使没有政治知识,也是可以理解政治的。如此一来,科学的论证反倒多此一举。
伊斯顿不但对行为主义的实证研究表达了不满,同时也批判了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伊斯顿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邓宁、麦基尔韦恩和萨宾等人的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在伊斯顿看来,邓宁对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是纯粹的历史主义的,即使是在历史的范围内邓宁也完全拒绝价值观念。邓宁认为,政治理论和政治意识都始于希腊人,他们已经“探索了人类政治能力的所有方面,并总结出任何时代政治生活的一般特征和规律”(Dunning,1920:416)。伊斯顿据此批判地认为,政治理论对于邓宁而言只是一项历史记载。麦基尔韦恩虽然指出政治理论史是为了说明“我们关于国家和政府思想的发展”(Mcilwain,1932:201),但伊斯顿认为即便麦基尔韦恩承认道德判断的意义,然而这种道德判断只能根据某项历史条件来对理论进行解释。相对于邓宁、麦基尔韦恩,伊斯顿指出萨宾不仅仅对理论进行阐述,还作出了价值评判。然而,伊斯顿认为“萨宾关于理论研究对道德思考的效用并不那么乐观”(伊斯顿,1993:236),萨宾的道德思考对于理论的发展仍然是缺乏建设性作用的。
从伊斯顿的批判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性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是欧洲传统政治学研究的遗留物,它与实证主义的共同之处就是:努力避免价值判断在研究中的运用。它注重对过去的政治实践、政治制度等作出解释性说明。伊斯顿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已设法从价值观念理论中扑灭了活力”(伊斯顿,1993:221)。正因如此,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一些政治理论已经失去了政治理论本应该具有的建设性作用。如伊斯顿所言,20世纪60年代以后,政治科学研究面临着一些紧迫的新的社会问题,如“现代世界迅速而不正常发展的工业化”、“世界性贫困”、“核战争危险”(伊斯顿,1984:73)等,对于这些新问题,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它不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帮助。
伊斯顿对观察方法以及解释方法的批判让我们看到,在政治学研究中祛除价值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缺乏研究意义的。这也表明了伊斯顿后行为主义思想的一个倾向:在政治学研究中,回归价值关注,并根据现实需要而重塑价值。价值的重塑并不是说在研究中要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而是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结合与互补,这正是伊斯顿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
二、 事实与价值的方法论融合:政治系统论的应用
伊斯顿不仅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创者,也是一般政治系统理论的创立者。他的政治系统论思想正是在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创立的,也即是说,伊斯顿将其后行为主义方法论运用到他的政治系统论研究上。
伊斯顿在反思和批判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论断,在其政治系统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应用。建立政治系统所依赖的基本前提,也就是伊斯顿所说的政治系统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为鉴别所有政治系统中需要研究的重要变量(variables)确定标准;其二,详细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三,以较为严密的逻辑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把一系列通则有机地构为一体。”(伊斯顿,2012:8)简要地来说也即是,构成政治系统的变量、变量间的关联以及变量间关联建立所遵循的通则。而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就是这些前提成立的方法论基础。
构成政治系统的变量也就是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政治研究中,伊斯顿认为,“难以逾越的重要障碍并不是仅仅缺乏经验研究的技术,而是极难寻求分析单元”(伊斯顿,2012:10),而“缺少合适的分析单元表明,人们把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用来争论概念及其含义了”(伊斯顿,2012:11)。美国当时的研究状况就是如此。因此,为了改变美国政治学的这种研究状况,必须确立内涵明确、外延清楚的分析单元。而分析单元是借助于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伊斯顿主张,创建政治系统,首要的是明晰相关的概念,这是理论发展“迈出的必然而重要的一步”(伊斯顿,2012:11)。如果概念含糊不清,“那就谈不上考虑什么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也就必然限于概念差异上的纠缠不休。”(伊斯顿,2012:11)政治体系定向概念的确立尽管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伊斯顿,2012:93),但在给一个概念下定义的时候,若是仅仅动用人类储存的经验知识,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描述性的事实,它只能用来解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现象。若是一个概念仅仅涉及价值判断,那么在用它来分析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偏见,我们的分析将会变成纯粹的推测和没有意义的空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的帮助。政治系统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论而非因果理论,所依赖的概念也相应要对现实问题有普遍性的解释力。这样一个概念在伊斯顿看来是要借助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综合运用的,如此建立起来的概念结构,才能有效地识别“解释政治活动并表明其相互关系所必须的重要变动事项”(伊斯顿,1993:88)。
除了在定义概念时要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综合,在概念间关联的建立上,也是如此。概念之间的关联是构成概念框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于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而言,“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抽象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伊斯顿,2012:11)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系列的概念,它们或许存在着事实上的某种联系,但若是没有价值判断做鉴别,我们是无法从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抽出一般性的原则,将其上升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框架而形成理论。正如伊斯顿所言,“高踞于理论之特权等级巅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严格的经验世界的分析。”(伊斯顿,2012:11)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伊斯顿对待描述性理论的批判态度中得到证明。然而,伊斯顿虽然批判描述性理论对价值的忽略,但并不认为立足于价值基础之上的传统理论就是没有缺陷的。纯粹建构性的传统理论过于依赖思想家个人的价值判断,每一个思想家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对自己理论前提的假设往往都是不同于他人的。在伊斯顿看来,理论阐述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不能受到质疑的,否则,执着于传统理论追求“必然要以方向的含糊迷沌和动摇不定为代价”(伊斯顿,2012:4)。也正因如此,伊斯顿声称,他要构建的政治系统理论是不同于建构性理论与描述性理论的兼顾事实与价值统一的“一般性理论”(伊斯顿,2012:6)。至于建立变量间关联所遵循的通则,更是由“努力建立一整套对经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逻辑标准带来的”,也就是说通则的形成是综合运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结果。
事实与价值冲突的和解,是伊斯顿建立政治系统论的前提和基础,为政治系统论的概念及概念结构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政治系统论尽管遭到了一些激烈的批判,如“系统分析事事都关注,但也正由于此,它什么也没关注”(Beardsley,1977:103),但仍然撼动不了它的影响力。伊斯顿正是凭借着基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和解与统一建立起来的“政治系统论”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并由此被誉为1945年以后美国政治学界的十大杰出政治学家之一。
三、 伊斯顿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贡献和影响
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占据主流的一个重要学派。行为主义学派极力倡导排除价值的定量研究,而且对政治行为的研究取代了对古典政治学的根本性问题的研究。这导致了该时期政治哲学的黯然失色,致使政治学的研究限定于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到了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已经不能对当时出现的新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一状况引起了美国学界一些学者对行为主义学派的激烈反思与批判。而反思与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前提——价值中立。
在反思与批判者中,施特劳斯和伊斯顿最具代表性。施特劳斯(1899-1973)与伊斯顿(1917-2014)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热衷于“实证研究”的做法及其“价值中立”的弊端,引起了施特劳斯和伊斯顿对美国政治学的忧虑。他们都对行为主义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与批判。施特劳斯对行为主义的反思主要是通过对古典哲学的回归来进行的。他于1963年著就的《政治哲学史》,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对经典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阐释,旨在引起人们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他认为,对于政治学,历史研究是必要的,“排除掉自身历史的政治科学”(施特劳斯,2009:序言)就不再是科学。从施特劳斯的这一做法可以看出,他完全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研究。相对于施特劳斯,伊斯顿对行为主义的批判虽更为直接,但仍然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行为主义的实证研究,指出了祛除价值做法的种种弊端。同时对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也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研究同样排除了价值,缺乏建构性作用,对实际问题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这实际上间接地表达了对施特劳斯研究的不满。因此,在伊斯顿那里,施特劳斯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不免落下历史主义研究的嫌疑。从伊斯顿对实证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当时的政治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政治学研究中,摆脱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状态而实现事实与价值的方法论综合。
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争论,是引起政治学方法论革命的根本原因。以伊斯顿为代表的学者以美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杂志为理论阵地,对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前提——“价值中立”的批判以及对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倡导,引发了后行为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在政治学领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利用它,排斥它,或者修正它,但忽略它是不可能的。”(Easton,1969:1061)在这场革命当中,伊斯顿的影响在当时的美国政治科学界是不同凡响的。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而言,行为主义单一的、纯粹的定量研究方法逐渐被复合的研究方法所取代。伊斯顿与施特劳斯不一样地方就是,伊斯顿没有丢弃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力图在行为主义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哲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伊斯顿主张把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统一于政治学方法论中。继伊斯顿后,达尔也明确地表明了这一主张,“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达尔,1987:181)因此,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是能够相互取长补短的。“实证方法不是科学方法的唯一选择,它在政治学领域,并不如在自然科学领域那样所向披靡。”(叶娟丽,2005:158)“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齐斯克,1985:10)面对新的危机,我们只有以问题为导向,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价值分析,才能够化解危机。事实与价值的和解与统一,保持了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之间的“连续性”(continuity)(Kirn,1977:84),丰富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为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伊斯顿的思想拓展和丰富了行为主义的研究内容。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西方努力把政治学科学化的产物,它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研究方法对个人或政治团体的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伊斯顿在其思想中提出了著名的“关联原则”(Easton,1969:1054),这个原则意指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时最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如环境污染、歧视、贫困和战争等)相联系,这实际上是表明了伊斯顿的主张,即在政治学研究中应当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由于问题是复杂多样的,所以研究的范围自然也就扩大。以方法为导向,只能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研究,其范围是狭隘的,行为主义的方法只能针对政治行为进行研究,而对其它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伊斯顿并没有放弃行为主义的研究,也就是说他依然坚持对政治行为的关注,但同时他也唤起人们对政治学传统研究内容的重视,只不过以“政治体系”的形式替换了国家或政治团体及其结构的概念。因此,伊斯顿倡导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研究内容上相较于行为主义得到了拓展和丰富。
伊斯顿尽管对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进行了种种指责,但他并没有深入分析“价值中立”形成的深层原因及其带来的更加严重的弊端。行为主义是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的,因此它力图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追求对政治问题的确定性解决。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只是使研究在既定的研究条件下进行,致使研究者很难突破既有意识形态的拘囿。因此,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是根本不起作用的,而后行为主义对价值的重塑,恰恰克服了行为主义的这一困难。
伊斯顿对行为主义“价值中立”做法的反思,以及对事实与价值综合运用于政治学系统理论的倡导,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对政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 结论
伊斯顿通过反思行为主义学派“价值祛除”所造成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后果及其危害,主张在政治学研究中综合运用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方法。伊斯顿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重新认识,纠正了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度重视倾向,促使“方法”导向研究向“问题”导向研究的转变,从而开辟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途径,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思路,增强了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回应力。由此,可以说伊斯顿是当之无愧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创者”。
以事后的眼光察之,伊斯顿所倡导的后行为主义的确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再度繁荣注入了强心剂。无论是理性选择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盛行,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生物学、生态学、精神病学等学科手段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再度复兴,我们都可以很轻易地从中觉出后行为主义的影响和贡献。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来说,伊斯顿的后行为主义思想其及包含的研究思路也是有诸多启发和借鉴的。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恢复虽然已经有30多年,但就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以及学科的美誉度而言,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还有很大差距。大体来说,前20年的中国政治学主要是以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的规范分析见长,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实证主义热潮的兴起,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经验研究也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方法融合的强调、对“问题”导向的重视启示我们必须立足中国,以中国政治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综合哲学分析、历史考察、个案呈现、量化统计等多种路径进行研究,从而真正拓宽政治学研究的现有格局。
参考文献:
[1]罗伯特·A.达尔(1987).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罗伯特·A.达尔(2012).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埃伦·格雷斯比(2013).政治分析:政治科学概论.姜志达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4]希拉里·普特南(2006).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5]贝蒂·H.齐斯克(1985).政治学方法举偶.沈明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2009).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7]叶娟丽(2005).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8]戴维·伊斯顿(1984).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阶段.徐步衡译.政治与法律,3.
[9]戴维·伊斯顿(1993).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0] 戴维·伊斯顿(2012).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1] Philip L.Beardsley(1977).A critique of Post-Behavioralism.PoliticalTheory,5(1).
[12] John Dewey(1903).Logical Conditions of a Scientific Treatment of Morality.InvestigationsRepresentingtheDepartments,PartII:PhilosophyEduc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 William A.Dunning(1920).AHistoryofPoliticalTheories:FormRousseautoSpencer.New York:Macmillam.
[14] David Easton(1969).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63(4).
[15] Michael E.Kirn(1977).Behavioralism,Post-Behavioralism,and the philosophy:Two houses,One plague.TheReviewofPolitics,39(1).
[16] Charles H.Mcilwain(1932).TheGrowthofPoliticalThoughintheWest.New York:Macmillan.
■作者地址:张涵之,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rayzhz@whu.edu.cn。
■责任编辑:叶娟丽
◆
The Unity of Fact and Value:The Internal Logic of David Easton’s Post-behavioralist Methods
ZhangHanzh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 and value are the focu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debate.Value-neutrality of behavioralist research suffered a real dilemma in the late 1960s,leading that behavioralist approach lost effectiveness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at that time.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Easton criticized the method of empirical observation and historicist interpretation.He advocated value return and rebuild,and the unity of fact and value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And that unity,which is the internal logic of post-behavioralist political science.Easton founded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form this internal logic.His theory enriched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ent of political science,and created a basic idea of the study of the post-behavioralist political science.
Key words:David Easton; political methodology; behavioralism; post-behavioralism; political syste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AZZ002)
DOI:10.14086/j.cnki.wujss.2016.0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