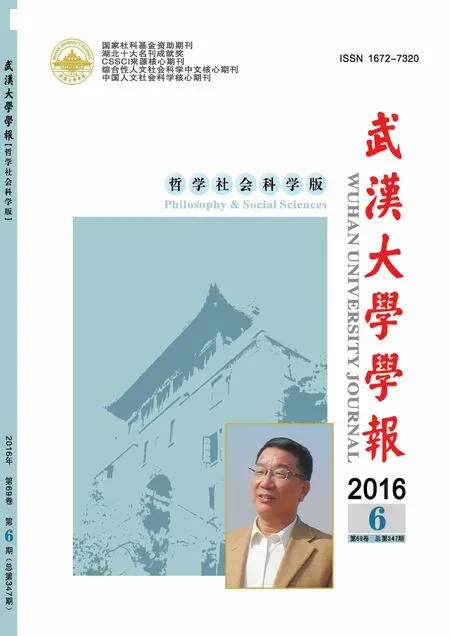论我国移动医疗服务法律监管制度之完善
2016-03-13涂永前
涂永前
论我国移动医疗服务法律监管制度之完善
涂永前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应用和普及,新兴移动医疗应用软件随之逐步得到推广。我国对于移动医疗领域的研究仍处于酝酿阶段,相关法律规定还十分薄弱,难以保障患者、医院以及第三方移动医疗应用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在借鉴美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升立法层次,实行实质性审查原则,明确监管主体、客体及其责任,在此基础上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移动医疗服务监管法律体系。关键词: 移动医疗服务; 移动医疗应用; 法律监管
一、 我国移动医疗服务现状及问题
在“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重背景下,基于O2O(线上—线下)、物联网的交易模式悄然兴起的网络公司通过移动互联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有效纾解。但是,在法律实施差强人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失信者惩戒不力的当下,移动网络线下服务问题并非如线上宣传的那么好,诚如2016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的“饿了么”的问题,就反映了这种交易模式线下监管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不断渗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健保体系的逐步完善,个体寿命大幅延长,但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慢性病发病率的增加,“互联网+医疗”作为其中一种医疗服务模式逐渐被广泛采用,并使医院、医生和医疗服务消费者享受到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便利。截至2015年,世界范围内已经有5亿名智能手机用户使用了移动医疗服务;预计到2018年,使用移动医疗服务的医生与患者人数将超过17亿*See J.Shuren,The FDA’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Mobile Applications,Clinical Pharmacology &Therapeutics,5(95).pp.485-488.而根据欧盟在2015 年发布的《移动医疗绿皮书》中预测,到2017年,全球将有34亿人拥有智能手机,其中50%将使用移动应用。。可以想见,在未来移动医疗服务以及相关App的应用将成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大帮手,对移动医疗服务展开研究势在必行。面对老龄化日趋逼近以及人口众多的现实国情,要解决我国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的一系列棘手问题,需要大力推动以移动医疗为引擎的“互联网+医疗”技术的应用研究。但是,如何规范移动医疗服务及其可能涉及的一些法律难题更需要展开一些前瞻性的研究。
(一) 移动医疗服务概述
移动医疗服务是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而衍生出来,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国际医疗卫生会员组织(HIMSS)对移动医疗(mHealth)界定,我们可以将其归
纳为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See definition of mHealth,http://www.himss.org/ResourceLibrary/GenResourceDetail.aspx?ItemNumber=20221,http://devpolicy.org/2015-Australasian-aid-conference/presentations/1a/Anthony-Huszar.pdf及百度百科。从mhealth的英文表述来看,应该是移动健康较为准确,相关的表述还有远程医疗(Telemedicine,偶尔也有用Telehealth),其上位概念还有数字健康(Digital health)及电子健康(eHealth),而移动健康(mHealth)与远程医疗(Telemedicine)之间存在交叉,不过它们二者都属于电子健康(ehealth)的属范畴。 通常情况下,远程医疗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ICT)、遥感、遥测、遥控技术为依托,给特定人群提供医疗服务。如今,远程医疗技术已经从当初的视频监护、远程电话诊断发展到今天充分利用网络进行高速数字、图像、语音综合传输服务,并且实现了语音和高清图像的实时交流,为现代医学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美国乔治亚州教育医学系统(CSAMS)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网络,可进行有线、无线和卫星通信活动,远程医疗网是其中的一部分。从以上解释来看定义来看,移动医疗(mHealth)服务与远程医疗服务都涉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在技术上肯定是互联互通相互融合,很难精细区分。对于远程医疗服务,《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51号)是这样定义的,“远程医疗服务是一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邀请方)邀请其他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以下简称信息化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医疗机构运用信息化技术,向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的诊疗服务,属于远程医疗服务。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含影像、超声、核医学、心电图、肌电图、脑电图等)诊断、远程监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及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项目。”很明显,这种远程医疗服务属于广义移动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只不过远程医疗服务更加集中在提供远程诊断服务和医疗病例的研讨活动。,例如PDA、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来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移动医疗服务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双边性以及外部性将服务提供方、需求方、各个移动医疗服务主体进行去中介化的高效连接,利用现有的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连接行业参与者。移动医疗服务具体包括远程视频监控、移动看护、药品管理、病患电子标识带的应用、无线音频及视频会议,等等。病人在医院经历过就医的所有流程,从住院登记、发放药品、输液、配液/配药中心、标本采集及处理、急救室/手术室,到出院结账,都可以能动移动技术予以优化。移动医疗已引发医疗保健服务模式的变革,在配合医疗护理改革方面潜力巨大,其允许医生在传统健康护理模式之外,为患者诊断出潜在威胁生命的病症,同时能够帮助医疗服务的消费者统筹规划他们自己的医疗和健康情况,及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这一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医疗各环节相互独立的状况,而且突破了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的限制,通过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大大缓解目前看病难、繁、慢等窘境(王蕾、赵国光,2016:45)。
目前,我国移动医疗领域仍处于萌芽阶段,并且主要依托于电子医疗这个相对完善的领域,此二者具有诸多相似点。因此,移动医疗的研究还须以电子医疗作为载体展开。概括来说,电子医疗主要分为两类:1.平台类。以资源与内容为导向构建B2C、B2B和C2B平台,沿市场需求链而形成平台生态。针对患者与健康人群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主要体现在医疗服务类和健康信息类,满足用户自诊问诊、预约挂号、健康和慢病管理、医-患、患-患间的沟通;针对医生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包括行业关系与信息类和学术与教育类,满足医生类群体以增加合法收入、提升业内知名度、提高医术、晋升职称等需求。2.工具和硬件类。以技术为入口切入细分用户群获取数据,数据流入医-药-研产业链,探索第三方付费的盈利模式。从其服务的对象来划分有:患者类,其服务内容包括医疗类和健康类,满足该类人群病情监测与健康管理、社群交流、获取专业指导与解决方案等需求;医生类,服务内容包括诊疗过程和患者管理,满足该类人群以准确专业诊疗、提高工作与诊疗效率、收集病例以提高医术等需求。
(二) 我国移动医疗服务现状
我国的移动医疗近几年才逐步兴起。2014年5月22日,工业与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共同发布了《中美移动医疗健康研究报告》(mHealth in China and the US:How Mobile Technologies Transforming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该报告指出我国移动医疗健康服务尚处在起步阶段,诸多方面正面临挑战。政府需从各方面积极推进移动医疗的健康发展(伊文,2014:36)。因此,2014年被称为中国移动医疗元年:这一年,资本大量涌入该领域,“未来医院”、“智慧医疗”等概念兴起,医疗类应用程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医院争先恐后加入移动互联网医院的行列。
在此情形下,我国相继出台了移动医疗服务相关政策。2014 年8 月,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就医疗机构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内容、流程及其监督管理等进行了规范。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将“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升为国家战略,该战略的提出也为移动医疗的发展创造了良机。此后不久,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指出要积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来转变卫生服务模式,普惠百姓。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更进一步指出要大力推广在线医疗服务新模式,发展互联网医疗卫生服务,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网络医疗信息平台,加强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工具,提高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能力。可以说,我国移动医疗服务的发展正逢其时,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当然也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条件的支持密不可分。其中,这些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法规政策的促进。近几年,在移动医疗服务领域颁布若干法规和政策,为移动医疗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例如,2009年卫生部《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9年卫生部《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2012年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2012年工信部《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2012年科技部《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十二五”专项规划》、2014年卫计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等等。
2.社会现实的需要。我国中国老龄化人口比重近十年逐年增加,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以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病正危害国民健康;而公共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且分配不均,在东部、城镇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优质医疗资源明显优于中西部和农村,地方政府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导致医疗行业资源配置严重失序,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明显弱化。
3.经济发展的保障。我国GDP保持较快增长,城乡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在近十年增长迅速,并且中国互联网行业融投状况向好发展。
4.技术创新的推动。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医疗移动化发展提供了便利;可穿戴智能医疗器械、云存储和大数据技术连接移动互联网,大力推动了移动医疗的崛起;再加上传感技术与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端+云”模式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易观智库,2015:2)。
据易观智库的预计,移动医疗占在线医疗和移动医疗总体结构规模比例从2015年的31%,2016年增长到43%,到2017年将超过50%,增至55%;而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在2014年达到30亿元,预计到2017年移动医疗将达到200亿元,以128%的增长率高速发展(易观智库,2015:3)。总之,我国移动医疗服务领域发展前景广阔,发展和完善我国移动医疗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我国移动医疗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其监管不足
虽然移动医疗服务在我国发展速度迅猛,但相应制度规范尚不健全,需逐步解决。
首先,我国医疗服务资源配置问题依然存在,广大基层医院设备落后尚不具备开展移动医疗的软硬件设施。其次,我国医疗资源有限,完全模仿国外的医疗模式不符合我国国情*国外的移动医疗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建立一对一的私人医生的医疗模式,这种模式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都非常流行,私人医生模式是一种提供上门的、个性化的医疗服务模式。,且资历较高的医生中能熟练掌握相应互联网技术的屈指可数,但矛盾之外在于资深医生更受大众欢迎,这就导致“老大夫”门庭若市,而懂得移动医疗技术的“小大夫”却门可罗雀,移动医疗实施的意义荡然无存,因此全面开展移动医疗服务有局限性。再次,我国一直存在就医难的问题,且医疗支出已超过大多数人的承受范围,若简单地将医疗服务从线下移至线上,并不会明显降低其成本,无法根本解决就医难的问题。最后,我国移动医疗服务还未达到问诊阶段,当患者得重病,网络平台上的医生不敢轻易诊断,患者也不会轻易相信其结论(严佳婧,2015:53)。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曾就此指出,网络上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的,只能从事健康咨询(徐爱芳,2015)。简言之,移动医疗目前只有“咨询”功能,尚无法实现“诊疗”。
总之,在我国移动医疗服务无论是从规范上还是在技术上仍不成熟,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尽管移动医疗服务有着“互联网+”的迷人之处,一直方兴未艾,但对其进行监管的制度供给却严重不足。例如:首先,刚刚兴起的移动医疗服务缺乏相关标准。没有标准指引,移动医疗发展就会呈现无序状态。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因为准入门槛低,缺乏监督机制,市场上的移动医疗相关产品虽种类繁多,但良莠不齐,不利于用户甄别。因此在这一领域亟须就其准入条件、监管者、监管对象及监管手段等进行明确。进言之,由于缺乏相应的器械、服务、流程标准,移动医疗器械的精确性将难以保证,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也因此更难规范。其次,移动医疗服务涉及诸多平台和商业主体,一旦发生纠纷,这些主体间的责任无法明确,导致追责困难。当前的移动医疗投资主要集中在网络问诊平台或App上,定位于在线健康咨询,在健康咨询与医疗诊治间尚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再者,网络平台及健康App是否具有行医资格等,用户一旦遭遇误诊或用药问题,责任主体不确定,维权困难。再次就是个人隐私存在泄露风险。2014年初国家卫计委印发了《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但该文件未明确移动医疗实施过程中该如何就采集到的与个人隐私、健康信息相关的保护及管理手段。
综上所述,有鉴于我国目前移动医疗服务监管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实有必要。
(四) 移动医疗法律监管国内外研究综述
学界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对移动医疗服务进行概括论述,其中有大量研究是针对移动医疗服务的概念、发展需要、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的,多数研究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在规范及法律制度供给方面的深入研究鲜见。目前,对移动医疗法律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完善移动医疗法律法规的必要性。有学者指出,现有的《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只是简单地对远程医疗活动中当地与远程端医疗和机构的法律关系作了限定和划分,仍缺少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蔡佳慧、田国栋、张涛等,2011:29)。
2.建立健全应用开发者的审核机制。如有学者指出针对目前某些不正规的第三方应用商店和开放平台在对非官方应用的管理、审核中仍存在较多弊端和漏洞,需要加强对应用开发者身份信息的核查和备案,通过借鉴国外对手机健康软件的审核经验,在我国设立相关机构审查手机健康软件(王姝淼、郑秋莹,2013:82-83)。不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管理局(FDA)的规定值得借鉴,对于大多数非医疗器械应用(nonmedical device apps)是不纳入监管范围的(United States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2015)。
3.制定科学的监管标准,加强人才和机构建设。有学者建议,首先要明确监管标准,规定监管机构对监管的产品是采用原先的分析结果抑或重新审查;其次,面对医疗应用软件这样的新兴事物,监管机构的设置、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硬件设施的装备(乔羽、褚淑贞,2014:2704)。在英国,有专家建议决策者及有影响的机构应该考虑对一些健康相关的应用进行评估和审查,并且建议参照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所采用的标准化的评估标准(standardized evaluation criteria)(Edwin D Boudreaux etc,2014:363-371)。
4.移动医疗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了如下几点不足:其一,执法动力不足;其次,被动的“选择性执法”;其三,个人信息保护适用规则缺失;最后,执法机制“部门割据”。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建立各类主管部门间的合作执法机制、案件协作机制及联合执法机制共同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建议(孙平、李国炜,2013:35-43)。
5.建立社会监督渠道。有学者认为:在监管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建立通畅的社会监督反馈渠道。建议借鉴英国经验,通过官方网站向病患及医疗专业人士推荐移动应用库,对入库应用实施安全审查准入,用户可以对这些应用进行点评,实现有效监督(宗文红、陈晓,2015:343)。
纵观以上研究,大体上是从监管制度的构建、机制的形成等方面进行宏观上的论述,其中也不乏对欧美等成熟法律制度的借鉴,这些研究为我国移动医疗发展及其规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以上研究不同,本文主要是从移动医疗相关立法的完善、移动医疗的监管主体的认定、监管对象与责任主体的明确、监管机构审查的原则角度阐述移动医疗的法律监管问题,从而形成协调统一的移动医疗监管体系和机制,为移动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 移动医疗应用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
移动医疗应用是移动医疗服务的载体。规范它就需要定位其性质,明确其调整规范及监管手段。
(一) 移动医疗应用平台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有如下表述:“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积极推广在线租房等新业态,着力破除准入门槛高、服务规范难、个人征信缺失等瓶颈制约”。因此,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又名“分享经济”,与我国有学者提出的平台经济接近,在“互联网+”的新模式下这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将会得到充分发展(徐晋,2013:15-19)。
分享经济理论是产业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该理论的产生是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几年平台型企业发展很快,平台型企业重视客户的培养和召集,通过调整双边客户的价格来招揽和维护价格敏感度高、数量较少的一方。近几年的商业发展表明,从门户网站、网络游戏、电子商务到网上社区、第三方支付等不断创新,平台型企业演化出平台产业,平台经济发展迅猛。自Rochet、Armstrong等学者对双边市场做出了奠基性的研究以来,双边市场和平台经济理论也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平台经济实质实现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三大趋势的集成与融合。
与传统经济中市场简单分为买卖双方单边市场不同,平台经济是以双边市场为载体,双边市场以“平台”为核心,通过实现两种或多种类型顾客之间的博弈获取利润。Rochet & Tirole就双边市场进行了定义:如果通过提高向一边的收费,同时同等程度地降低向另一边的收费,平台可以改变交易量,则称这一市场是双边市场,也即,在双边市场中,价格结构影响交易量,平台应该设计合理的价格结构以吸引双边参与者,同时提升其竞争力。已有文献一般将双边市场分为四类:交易中介、媒体、支付工具和软件平台(J.Rochet & J.Tirole,2006;李允尧、海运、黄少坚,2013:123)。
分享经济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即外部性(externality)和多属行为(multi-attribute action)。
1.网络外部性是指一边终端用户的规模会显著影响另一边终端用户使用该平台的效用或价值。比如,银行卡持卡的消费者越多,POS机对于商户的价值就越大;而安装POS机的商户越多,银行卡对于消费者的价值也越大。这种消费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通常所说的消费“正外部性”。早在1974年,J.Rohlfs在有关电信服务的研究中便已发现这种现象。后来,许多学者称之为“网络外部性”。Evans(M.L.Katz & C.Shapiro,1985:24-440)以及Rochet & Tirole还专门对“成员外部性”(Membership Externality)和“用途外部性”(Usage Externality)进行了区分(Jean 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2010:233-260)。
2.多属行为。现实中存在着多边平台市场结构。主要有:(1)相似性平台(Coincident Platforms)。几个功能相似的双边平台为市场同一方提供同质化的市场服务,包括电子游戏、操作系统、银行卡、电信以及网络门户网站等,这些平台之间显然存在竞争关系。(2)交叉性平台(Intersecting Platforms)。多边平台为多个市场方提供可相互替代的产品或服务,平台之间也存在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如众多中小型网站或专业性网站经常在网页上相互链接,显然这些交叉性平台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3)垄断性平台(Monopoly Platforms)。多边市场的任一方都不存在竞争对手的平台。这种垄断性平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很鲜见,但在我国确实曾经存在或仍现实存在,例如中国银联、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加油站等(李允尧、海运、黄少坚,2013:124-125)。
以上对分享经济理论的分析为我们对移动医疗服务市场经济中如何运作提供了准确定位。
(二) 移动医疗应用的法理定位
在经济法理论中,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是两个相异的概念,医疗服务是典型的私人产品,而公共卫生则属于纯粹的公共服务。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上具有竞争性,在收益上具有排他性”。公共卫生服务,如瘟疫防控、传染病预防,等等,因无法排除第三方受益,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私营医疗机构不会提供,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而医疗服务,患者自己受益,不具有社会公共性,且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本质上属私人服务。因此,医疗服务在逻辑上应当由市场提供,供方需方自由选择(陈云良,2014:74)。
此外,移动医疗应用本质上是通过移动端向受众提供医疗服务的一种模式。因此,移动医疗应用的目的是提供医疗服务,具有营利性,应受到市场规则约束。但有学者认为此类服务可能属于公共服务,因为医疗服务具有正外部性,患者得良治能降低其他人患病的概率,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但正外部性不是移动医疗应用划归为公共服务的充分条件,且公共产品的划定也不利于移动医疗应用的发展。在市场竞争前提下,政府适当规制,才是符合我国国情,促进移动医疗发展的最佳路径。
三、 美国移动医疗监管法律制度
完善移动医疗法律监管的首要问题是监管机构责任的划分和监管对象的确定。因此,本文将从这一方面借鉴美国相关法律制度,探讨我国移动医疗监管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一) 美国移动医疗法律制度发展的背景
1989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了指导性文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计算机产品监管指引》(下称“《指引》”),开始将医疗软件作为医疗器械进行监管。但200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撤销了1989年的《指引》。2008年2月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指导性规则,将之前未作规定的“医疗器械数据系统”纳入分类I中。201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移动医疗应用指南草案》(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the Draft Guidance)中总结了两类具有潜在风险的应用:一类是把移动平台变成医疗器械。如通过传感器将移动装置变成听诊器的应用,又如能测量血糖和心电图并将其结果呈现在智能终端上的应用;另一类是控制既有医疗器械使用的应用。例如通过胰岛素泵控制胰岛素的输送(宗文红、陈晓,2015:34)。2012年7月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和创新法案》(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afety and Innovation Act)从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移动医疗应用(mobile medical apps)的监管职责*See Section 618 of FDASIA.。2011年7月21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移动医疗应用指南草案》,并于2013年9月23日出台《移动医疗应用最终指南》(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the Final Guidance,下称《最终指南》),该《最终指南》成为第一部旨在对移动医疗应用进行监管的指导性操作文件。2015年2月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更新了2013年9月25日的《FDA内部员工移动医疗应用指南》(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Guidance fo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并与2015年同日发布的《医疗器械数据系统、医疗影像存储器械及医疗影响交流器械指导性文件》(Medical Devices Data Systems,Medical Image Storage Devices,and Medical Image Communications Devices)保持一致。该《最终指南》虽不具强制性,但已然成为美国监管机构在移动医疗应用市场准入及相关监管领域的重要依据*More details see http://www.fda.gov/downloads/MedicalDevices/.../UCM263366.pdf.。
(二) 《最终指南》中相关监管规定
在《最终指南》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移动医疗应用纳入其监管范围内。《最终指南》解决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否具有对移动医疗应用的管辖权问题,它明确当对患者造成极小的风险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样对其具有适当的监管权。《最终指南》把强制执行自由裁量纳入应用范围,但该局未明确规定其监管活动的范围仅限哪些存在高危风险的移动应用。
通过与2011年《移动医疗应用指南草案》比较发现,《最终指南》在组织和内容方面与《移动医疗应用指南草案》十分相似,但在强制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和不受监管对象的范围进行了扩张解释。
首先,《最终指南》确定了移动医疗应用的概念。与指导意见草案相类似,最终指南把“移动医疗应用”定义为如下的一种移动应用:(1)符合《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ederal Food,Drug,and Cosmetic Act,FD&C Act)第201(h)条关于“器械(device)”的定义;(2)被认定为“法定医疗器械”的附属品或者转变为“法定医疗器械”的移动平台。尽管“移动医疗应用”的定义依然没有改变,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扩展了“法定医疗器械”的外延,把具有创新性的医疗器械纳入其中,即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事先未对之明确、批准或界定。
其次,《最终指南》详细规定了被监管对象。其中指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将对移动医疗应用的生产者进行监管,规定如下:(1)包括任何制定移动医疗应用的规格说明或者创造、设计、标示、再加工或调整修改一款移动医疗应用的组织机构,但这些制造商标示或推广其产品具有医疗器械的功能的除外;(2)为移动医疗应用制定详细说明或要求规范或者从其他个人或机构购买产品研发/制造服务以便之后的商业销售的组织机构;(3)为移动平台设计的一款移动医疗应用和硬件器械,且移动平台与移动医疗应用、硬件器械相结合,用作医疗器械的组织机构;(4)设计一款移动医疗应用或者软件系统,通过订阅网址、软件的服务或其他类似的方式提供给用户连接医疗器械功能的路径的组织机构。《最终指南》规定了不受FDA监管的对象:单纯经销或销售移动医疗应用的机构没有监管的权力(比如,应用商店);一般用途的移动平台的生产者(比如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用于移动医疗应用的研发、销售或者使用的工具、服务或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仅为自己业务工作而设计移动医疗应用的执业医师;仅以搜索、教学或分析为目的,而不用于商业销售的移动医疗应用的制造商。因为这些应用故障不会给病患造成风险,对其监管力度也就最小。此类移动医疗应用包括:测量体重指数等,且可传至智能手机App等移动终端,但此类应用进入市场需进行售前告知。在2015年《FDA内部员工移动医疗应用指南》中则明确规定健身追踪等健康相关产品基本免于审查。2015年《医疗器械数据系统、医疗影像存储器械及医疗影响交流器械指导性文件》当中则再次明确对医疗设备数据的接受、传输、存储以及展示不加强监管,其目的旨在促进移动医疗技术更好地发展和创新。
最后,《最终指南》明确了受监管的移动医疗应用范围。《最终指南》通过列举的方式,在主要条款和附属条款中区分并明确了以下几类受主动监管的一般应用程序:(1)以控制其操作、运转或者能量来源为目的,连接现有的医疗器械的移动应用程序;(2)从一台已连接的医疗器械中,展现、传输、存储或更改特定病患的数据的移动应用程序;(3)用于从移动平台向法定医疗器械传输的移动应用程序;(4)用作特定病患数据分析和提供特定病患诊断或治疗建议的移动应用程序。概括来说就是CLASS II(II类)及CLASS III(III类)移动医疗应用,CLASS II应用发生故障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风险的移动医疗应用。在移动医疗中,该类应用程序通常附带硬件部分,例如需插入iPhone中的便携式听诊器,并附有相关应用程序。此类应用进入市场前也需进行售前信息披露。而CLASS III应用如发生故障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损伤,因此对这类产品监管力度最严。此类医疗设备必须获得FDA的售前许可而不是售前通知。在201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内部员工移动医疗应用指南》中也明确规定用于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技术将进行严格监管。然而,对不符合《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201(h)条“器械(device)”定义和仅存在较低风险的移动医疗应用不进行监管(Joseph Goedert,2014:17)。
(三) 《最终指南》中所监管的移动医疗应用规定
通过对《最终指南》中相关问题的论述可发现,医疗器械监管的规定值得借鉴。在对医疗器械的规定方面,从美国器械与辐射健康中心(CDRH)*该机构的英文全称是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隶属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下属的医疗产品与烟草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Medical Products and Tobacco)管辖的研究机构。类似的FDA研究机构还有6家,分别是食品及营养应用中心(Center for Food Safety & Applied Nutrition,CFSAN),生物学评价及研究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CBER),药物评估及研究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CDER),兽药中心(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CVM),国家毒理学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oxicological Research,NCTR) 及烟草制品研究中心(Center for Tobacco Products,CTP)。美国作为世界上在监管技术、医疗器械创新及制造、辐射产品安全方面的领军者,对于如何快速检测医疗器械的质量如何、精确识别其功能,以及方便器械的许可和退出市场都有一整套的制度规范及组织机构来实施这些职能。承担这个重任的机构就是器械与辐射健康中心。 该研究机构服务于与FDA一致,致力于保障和促进公共健康,但是其使命不同,其主要是致力于为病患及有医疗服务需求者持续提供及时、安全、有效、高质量的医疗器械及安全的医用辐射产品,并为消费者、病患及有医疗服务需求者提供其力所能及的科学信息服务和医疗产品。该机构通过推动监管科技促进医疗器械创新,为医疗产品行业提供可预测的、持续的、透明的及有效的监管路径,维护消费者对医疗器械市场的信心。参见http://www.fda.gov/aboutfda/centersoffices/officeofmedicalproductsandtobacco/cdrh/default.htm。的规定来看,创新性和安全性间并无矛盾。因此,通过确保医疗设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通过促进创新来提升公共健康保障成为该机构的目标和任务。
为了实现保障和提升公共健康目的,我们需要摆脱传统意义上安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不能兼容的错误认识。如美国抛开扩大或减少立法之争,将关注点主要放在提高立法的质量上,例如,如何有效完成作为监管机构和协调机构的双重任务。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正在协助建立一种监管环境,通过消除不合理的监管阻碍,为创新发展提供便利,并向消费者保证医疗技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但是,目前美国民众获得安全和有效的移动应用的目标尚未实现。为此,近几年,移动应用的开发者一直在寻求相关的指导意见,以明确哪些移动应用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监管,哪些不受监管。明确相关分歧对吸引投资和促进创新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美国器械与辐射健康中心(CDRH)应对此提供相关指导意见。关于移动应用《最终指南》规定大致如下:
尽管很多移动应用适用于医疗服务,而且部分可能作为医疗设备,美国器械与辐射健康中心(CDRH)与以往一样对属于医疗设备的移动应用的特定部分进行监管,并认为这种针对性监管将会促进创新发展,同时又能通过加强对患者风险更大的移动应用的监管,来保障患者的安全。
美国对作为医疗设备的应用软件的法律规定是基于其风险和功能性的。基本原则是功能性应被同等对待,但应用程序所属的平台除外。例如,无论大小,用于测心率的心电图设备是心电图设备,其对患者造成的风险和对医疗从业及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保证的重要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以上就是《最终指南》颁布的意义所在。但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一款移动应用被视为医疗设备,而且使移动平台转换为医疗器械(例如心电图设备)或者医疗器械的配件(例如远程控制电脑断层扫瞄器的应用程序),该中心就将对这种技术进行法律规范。毕竟,无论其是通过移动还是非移动平台进行操作,它仍属于医疗器械。而且,移动应用不是与平台相关的,而是与其功能性相关。
美国器械与辐射健康中心(CDRH)在此之前已对移动应用有过规定。从1989年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开始关注以电脑及软件应用为基础的医疗设备并制定相关政策草案,拟进行监管。之后还陆续将多款移动应用器械纳入其监管列表中*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DA Staff-Implementation of Medical Device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and Device Listing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mendments Act of 2007,http://www.fda.gov/MedicalDevices/DeviceRegulationandGuidance/GuidanceDocuments/ucm185871.htm.。后来因诸多原因,该草案于2005年被撤销。不过,应澄清的是,近年来美国一直着手对移动应用软件进行规范,包括属于医疗器械的移动应用等。而在《最终指南》中,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特定范围的、给患者带来较大风险的移动应用上。
(四) 《最终指南》中的强制执行自由裁量权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尝试对可能符合《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规定的“器械”的定义的移动应用程序,采用强制执行自由裁量,但没能如预期运转而对病患来说造成较低的风险的应用程序除外。与我们对法定应用程序的分析一样,《最终指南》中除受制于强制执行自由裁量的应用程序的一般分类,还包括一些特定实例,如:通过指南或激励,提供或者改善辅助性临床治疗,用于帮助患者在日常护理中安排健康计划;为患者提供简易的工具以管理和追踪其健康信息;提供患者获取健康状况或治疗情况相关信息的简易途径;用于特定销售,来帮助患者记录、展示或向提供者传达潜在的医疗状况;执行用于临床实践的常规简单计算;使个人与个人健康档案系统或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建立交流与联系。
尽管指南扩张性规定应用程序受制于自由裁量的强制执行权,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受制于强制执行权自由裁量的应用程序与积极规定的应用程序之间的划分依旧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应用的开发者可能面对困境,不能决定他们的应用程序被认为是执行“用于临床实践的常规简单计算”(由强制执行的自由裁量权规定调整),还是被认为是执行特定病患数据分析和提供特定病患诊断或治疗的建议。除此之外,这些基本上由该局提供的分类和实例将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移动医疗应用程序。因此,尽管《最终指南》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但某些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其中部分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美国移动医疗应用监管规范依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参众两院议员已经起草了相关提案,并试图彻底修改现有的移动医疗应用监管规定。众议院两党联盟于2013年10月提出了《使用合理的监督技术以提高监管效率法案》(Sensible Oversight for Technology which Advances Regulatory Efficiency Act),而参议院中共和党与独立派的联盟则于2014年2月提出了《防止监管过度以促进医疗技术法案》(Preventing Regulatory Overreach to Enhance Care Technology Act)。这两个法案均旨在限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移动医疗领域的监管范围。两提案均明确了临床类、健康类和医疗类应用软件之间的差异。提出临床类和健康类应用软件将不受该局监管。该局关注焦点应重新转移到那些可以对特定病人进行诊断的应用软件身上。这两份法案均已被提交到相关下属专业委员会,且国会也表示会围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该领域的监管继续展开辩论。从该局之前在该领域的监管历史来看,未来其不太可能完全放弃对移动健康领域的监管权限。。
无疑,服务现实需求、与移动医疗应用紧密相关的法律框架是推进医疗仪器审查创新和智能化的根本保障。通过关注功能性而非平台的相关资料,并且通过更多聚焦对患者存在更大风险的技术,我们能够通过提升和支持新技术的发展来平衡患者健康医疗中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
四、 域外移动医疗服务监管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美国移动医疗应用监管制度的考察,反观我国该领域发展所存在的监管问题,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法律和实践对我国移动医疗服务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有借鉴意义的。其实,在移动医疗服务领域,欧盟的系列监管措施也值得借鉴。以移动医疗服务的科学认证为例,欧盟的认证过程比美国更开放、更高效。对于新的移动医疗器械,相关制造商根据欧盟的医疗器械判定流程自行判定是否属于医疗器械,如若属于医疗器械,一般将会归为I类。在英国药监机构——药品与健康产品监管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注册备案的制造商可自行对移动设备进行宣传。与此同时,欧盟有超70家欧洲统一(Conformite Europeenne,EC)认证机构,遍布其成员国。一旦医疗设备被其中一个机构认可,该设备在整个欧盟成员国都准许销售。首先,欧盟对医疗设备的认证首先依据的是 ISO/IEC 2382-1标准,判定软件是否为一个电脑程序;其次,欧盟注重的是软件对医疗数据的处理方式,是否有区别于存储、压缩、归档、交换以及检索的其他数据处理方式是判定的关键;最后,依据欧盟医疗器械的 1993年 6月14 日理事会指令 93/42/EEC(Medical Devices Directive)第1.2a条规定判定软件是否为医疗设备。欧盟对移动医疗软件的监管分级沿用了医疗器械的分级系统,同时明确规定了各类移动医疗设备的监管级别。对于移动医疗设备而言:有积极治疗功能和出于诊断目的的设备一般归为IIa类,有潜在危险的归为IIb类;用于避孕和阻止性传播疾病传播的移动医疗设备归为IIb类;此外,所有其他移动医疗设备均归为I类(庹兵兵、沈丽宁、徐彪,2016:78-80)。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完善互联网融合标准规范和法律法规,……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方式,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保护公平竞争,防止形成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因此, “互联网+”的移动医疗服务的法律监管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促进互联网发展必需的后盾。
(一) 完善移动医疗服务的相关立法
反观我国相关立法情况,1999年1月4日,我国原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2014年8月21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该《意见》对医疗机构远程医疗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监督管理等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并明确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含影像、超声、核医学、心电图、肌电图、脑电图等)诊断、远程监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及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所规定的其他项目。总体上,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移动医疗服务的法律体系,相应的制度框架也没有建立起来,相关规定较少且仅停留在效力层次较低的政府部门规章。为此,应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移动的医疗法律体系。
首先,应当从实际出发,通过立法形成移动医疗服务的顶层制度框架。第一要务是明确移动医疗监管的主体机构,并且要让监管更加具有执行力。其次明确移动医疗服务的有条件准入领域、限制性开发领域,设置涵盖生命健康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运用以及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强移动医疗服务的信息安全管理,确保医疗信息在发送、传输和传递过程中的安全性。但此项立法不宜过细,应当保持立法的概括性和灵活性。因为我国移动医疗甚至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不像美欧等国有雄厚的财政资金保障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支撑,而且立法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诸多规则在制定时便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因此,当务之急是将移动医疗法律监管的框架搭建起来。其关键在于监管主体、客体、原则等总括性的规定,而相应的细则、解释和技术标准则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跟进。同时出台相关配套规范,明确对移动医疗主体资格审查备案、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安全保护、纠纷解决、消费者维权等问题的解决办法。
其次,关于移动医疗领域是单独立法还是纳入基本医疗卫生立法,笔者认为,移动医疗服务领域不宜单独立法。原因在于,“互联网+”是国务院提出的指导意见和大政方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指引,其并不能取代传统的制度体系。法律具有普适性,移动医疗服务仍为医疗卫生体系的组成部分,为兼顾普遍适用性和特殊性,将其归于医疗卫生立法,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进行规定较为适宜。
最后,移动医疗的发展需修订《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障医院及医生从事移动医疗服务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推动医生多点执业,促进医疗资源均等化(王蕾、赵国光,2016:46)。
(二) 明确移动医疗服务监管主体以及强化实质性审查原则
移动医疗领域的监管归属于市场监管的范畴之内。由于市场自身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从而需要监管主体的设立及运行予以解决。但监管主体自身也有缺陷,监管主体的行为并不能保证始终与设计初衷相吻合,因此,对监管主体进行法律上的规制十分必要。
移动医疗服务领域并没有相关系统性的立法,相关的零散规定只现于各种法规规章之中,而监管制度更是十分薄弱。对此,在制定和完善相关立法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监管主体的确定问题。在我国,已经设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和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此外,还有中央和地方各级卫生行政机关,负责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环境工作。其下属负责行政执法的卫生监督局/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前称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还有各级医院也有一定的监管职权。这些监管主体如何分配职责及协作配合是问题之所在。
移动医疗服务涉及互联网、物联网、医疗机构、消费者、第三方平台等各类法律问题,因此,若这些部门之间的职责范围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及相关机构的协调管理,是无法形成促进我国移动医疗深入发展长效机制的。2012年7月颁布的美国《FDA安全和创新法案》首次从法律层面正式明确了该局对移动医疗的监管职责。而在我国单独设立新的机构专门执行移动医疗监管不符合我国国情,在财政资金、人员编制、与现有机关的协调配合等方面都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关立法在明确划分移动医疗法律监管责任的同时,形成移动医疗服务方面的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对移动医疗服务领域发生的法律问题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或没有规定时,进行评估与认定,分配职责、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关于监管主体的审查原则,依照我国国情,宜粗不宜细,细则需逐步实现,稳中求发展。因此,为解决现阶段移动医疗领域产生的监管问题,可借鉴美国的实质审查原则,对移动医疗应用软件进行功能性和风险评估管理,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既要保证审查和监管的合法性,也要有合理性的要求。实质审查也可认为是监管主体行使的一种自由裁量权,裁量时须兼顾安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虽然三者间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协调和统一是实质审查考量的原则之一,同时也是监管追求的目标。同时,还应确立实质审查的例外情形。如前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将移动应用分为诊断治疗类、辅助治疗类和医疗系统外围类,对三者监管力度有别。第1类需重点监管,第2类风险较低可行使自由裁量权,而第3类不在该局的监管范围内。《最终指南》中还列举了强制执行自由裁量权的6种例外情形,但仍显粗略。我国可借鉴美国及欧盟在这些领域的既有经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移动医疗服务审查原则。我国也可结合自身国情,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移动医疗服务法律制度。
(三) 明确监管对象
这里的监管对象特指移动医疗应用软件。在这方面,美国有着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美国移动医疗应用的监管对象涉及面较窄,只对存在较高风险的应用进行监管,其合理性上文已有论述。我国可借鉴其经验,确定合理的监管对象,对不涉及生命危险的应用放宽监管,而对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的应用进行严格监管,力求对移动医疗的监管在保护病人安全的同时又不打击该领域的创新。随之,对移动医疗应用涉及的监管对象进行合理分类,并针对每类对象制定监管细则。可能的监管对象包括器械、应用、服务以及医生。针对器械和应用,需要制定发布前审查机制,并从临床、公共卫生、自我健康管理等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监管。针对在线提供的服务也应当建立相应的监管规范,以便让后台提供服务的人员明晰服务界限。针对在各种咨询平台工作的医生,急需对其资质制定监管细则,或者通过医生多点执业政策及医疗纠纷保险的不断完善,以使医生的监管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宗文红、陈晓萍,2015:345)。
对于如何认定较高风险,这就需要建立风险认知及风险评估体系。所谓风险认知,是指人们对可能存在潜在伤害情况的感知;而风险评估,是指通过量化等可计算的方式来测评风险的大小(乌尔里希·贝克,2003:29)。移动医疗应用软件的安全性是与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价值判断相关的属性。风险评估和风险关系具有社会关系属性,对移动医疗应用软件具有监管责任的主体对应用软件的安全性负有说明责任,而且移动医疗应用软件的发展具有可变性,它要求各监管主体及时履行危险防控义务,对风险管理制度、方法、手段进行定期再审查、再评估,通过不断完善的过程化管理达到防控目标。
(四) 明确被监管主体的责任
目前我国从事移动医疗服务的主体鱼龙混杂,通常涉及提供医疗服务链条上的多个服务提供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3条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是连带责任人,销售者(包括服务提供者)在承担产品损害责任后,可以向生产者追偿相应经济损失(陈协平,2015:87-93)。但是,移动医疗领域是特殊的领域,需要特别规定予以规范。根据美国2013年《最终指南》的相关规定,对于如何认定责任主体,主要根据如下原则来判定:关联性,即责任主体应当与医疗服务有一定关联;公共性,即移动医疗应用应当在市场环境下运行,由不确定的主体参与其中;营利性,主体行为具有营利性目的,教学或研究使用的应用不在此列。所以,我国亟须出台相应规范,确定移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性质和责任,明确移动医疗产品侵权责任。
针对移动医疗应用软件的监管,有必要建立 “开发—审查—准入—运行”层层推进的监管机制。一方面由相应职权的行政监管机关进行日常、定期、抽查等形式的监督管理,发现违法情况,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移动医疗开发商、平台运营商、分销商等在医患关系之外,间接参与移动医疗服务的各方主体也有一定的监管义务和责任。这些主体扮演着检验移动医疗应用软件质量的前线监察员的角色。各主体对移动医疗应用软件质量并未制订专门的审核标准(王姝淼、郑秋莹,2013:81),因此,完善相关审核标准迫在眉睫。首先,由于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商鱼龙混杂,应当出台相关规范加强其自律监管,并定期核查;其次,加强对平台运营商、分销商的监管力度,在其内部建立质量评级体系,对应用软件技术力量不足、产品质量不高的开发进行重点监管;最后,各方主体将用于医疗服务的应用软件上报至有关行政监管机关进行备案,对明显质量缺陷的应用软件,马上予以淘汰;对无法界定的,应予以暂停使用,待有资质的鉴定机构给出鉴定意见后,再做决定是否再启用,从而做到预防性监管,防患于未然,避免损害的发生(乔羽、褚淑贞,2014:2704)。如果违反监管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致谢: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得到了辽宁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生王晓天的协助,论文的前期修改及投稿后的修改得到了辽宁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建及两位双向匿名评审专家的指点,特此致谢。。
[1]蔡佳慧、田国栋、张涛等(2011).我国远程医疗法律与政策保障现状分析与建议.中国卫生信息理杂志,4.
[2]陈云良(2014).基本医疗服务法制化研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
[3]陈协平(2015).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纯粹经济损失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4.
[4]李允尧、海运、黄少坚(2013).平台经济理论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7.
[5]卢意光(2015).“互联网+医疗”所涉法律风险探析.医学与法律,6.
[6]乔羽、褚淑贞(2014).国外移动医疗应用监管对我国的启示.中国药房,29.
[7]屈梦珂(2015).互联网医疗领域监管问题研究.湖南工程学院学报,4.
[8]孙平、李国炜(2013).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以网络预约诊疗服务为例.法学,9.
[9]谭相东、张俊华(2015).美国医疗卫生发展改革新趋势及其启示.中国卫生经济,11.
[10] 庹兵兵、沈丽宁、徐彪(2016).美欧移动医疗项目推进与监管措施探析.中国医院管理,2.
[11] 王蕾、赵国光(2016).“互联网+医疗”的困境及政策解析.中国医院,2.
[12] 王姝淼、郑秋莹(2013).手机健康软件Apps的监管问题研究.管理观察,22.
[13] [德]乌尔里希·贝克(2013).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4] 徐爱芳(2015).国家卫计委:不允许开展互联网医疗诊治.环球网,http://health.huanqiu.com/health_news/2015-04/6155558.html?referer=huanqiu.
[15] 徐晋(2013).平台经济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6] 徐倩、赵文国(2014).国内外移动医疗应用现状及启示.检验医学与临床,9.
[17] 严佳婧(2015).移动医疗“这块蛋糕”并不甜?.华东科技,2.
[18] 易观智库(2015).中国移动医疗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5.易观,http://www.analysys.cn/report/detail/11843.html.
[19] 伊文(2014).我国移动医疗健康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需从四方面推动.健康管理,8.
[20] 翟运开、谢锡飞、孙东等(2014).我国远程医疗发展的法律与医疗伦理的限制及其化解.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1.
[21] 宗文红、陈晓(2015).国外移动医疗监管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4.
[22] 左秀柒(2010).网络时代远程医疗法律问题论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35.
[23] Edwin D Boudreaux,PhD,Molly E Waring,PhD,Rashelle B Hayes,PhD,Rajani S S-adasivam,PhD,Sean Mullen,PhD,Sherry Pagoto,PhD(2014).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mobile health apps:strategies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PracticeTool,4.
[24] Goedert J.(2014) MOBILITY:FDA Issues Final Guidance on Medical Mobile Applications.HealthDataManagement,1.
[25] Jean Charles Rochet,Jean Tirole(2010).Two-Sided Markets:An Overview.Toulouse,11.
[26] J.Rochet & J.Tirole(2006).Must-Take Cards and the Tourist Test,Working Paper,IDEI,University of Toulouse.http://idei.fr/doc/conf/tsm/papers_ 2006/rochet.Pdf.
[27] J.Shuren(2014).The FDA’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mobile applications.ClinicalPharmacology&Therapeutics,5(95).
[28] M.L.Katz,C.Shapiro(1985).Net-work externalities,competition,and compatibility.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75.
[29] United States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2015).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http://www.fda.gov/medicaldevices/digitalhealth/mobilemedicalapplications/default.htm.
■责任编辑:李媛
◆
China’s mHealth Service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ts Legal Supervision
TuYongqia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smart phones,the emerging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 are gradually spreading world-wide.The domest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obile medical is still in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problems concerning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the protection of the patients,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hospitals,as well as the providers of the third-party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App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obile medical concepts,the research of the domestic status in this fiel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s some investigat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mhealth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oncerning systematic regulations and laws matching China’s status quo in this brand new field.
mobile health service;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 law enforcement
10.14086/j.cnki.wujss.2016.06.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D02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009);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4ZD11)
■作者地址:涂永前,南京审计大学润泽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Email:tuyongqi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