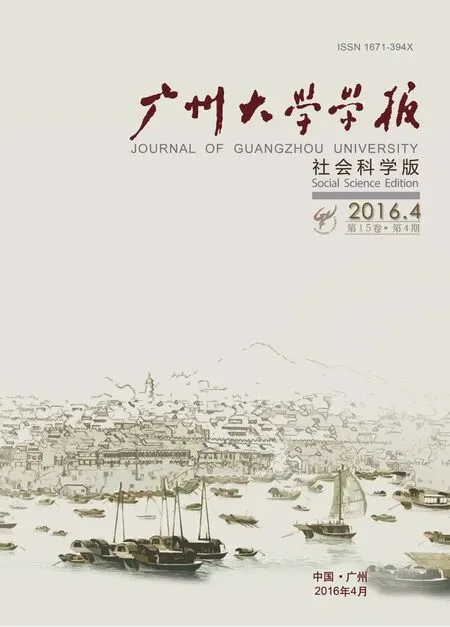康德论道德教育中的叙事应用
2016-03-09郑晓绵黄泰轲
郑晓绵,黄泰轲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湖南长沙 410081)
康德论道德教育中的叙事应用
郑晓绵,黄泰轲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作为证明道德法则和进行道德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叙事通过故事、小说、传记、辩难、道德问答等具体形式在康德伦理学中得以应用。在向“德性伦理”回归之呼声愈加强烈的背景下,通过对康德论道德教育中的叙事应用及其注意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对加深康德伦理学的理解,深化对叙事伦理的认识,走向德性伦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康德;道德教育;叙事;叙事伦理;德性伦理
叙事是当下学术研究中使用较为频繁的一个概念。按照一般的解释,叙事就是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真实或虚构事件的叙述,说得简单和通俗点,叙事就是“讲故事”。作为人类一项古老而基本的文化活动,叙事的表现形式多样,“不仅早期的神话、寓言、传说有这样明显的叙述类型,甚至历史与哲学也都是以叙事知识的方式存在的。先秦的哲学著作也可以视为某一个人物(哲学家)的所言、所思、所为的故事。”[1]叙事与伦理学的结合早已有之,亚里士多德《诗论》中对“卡塔西斯”概念的分析“既符合以悲剧和喜剧为代表的文艺中情感的平衡和协调要求,也符合以德性(virtue)为对象的伦理学中情感的平衡和协调要求。”[2]在当代,将伦理学运用于叙事批评或在叙事中阐释伦理学意蕴已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叙事伦理”也因之成为一个时髦的学术词汇。
仅从西方道德教育史看,叙事在古希腊时期便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在古希腊,道德在神话、史诗、戏剧、哲学等诸多的叙事形式中才得以保存、展示、理解和教育。“一般来说,对美德采取一种姿态也就会对人类生活的叙事特征采取一种姿态。”[3]182比如雅典的孩子们,正是在吟诵、倾听和阅读《荷马史诗》中才对正义等道德概念有所理解的。所以麦金太尔才说,讲故事在从英雄社会到中世纪后的那一道德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具有关键作用。[3]274麦金太尔同时认为,正是斯多葛主义这一“希腊罗马文化插曲”的出现,为西方伦理学开启了一个迥异于“德性传统”的“规则传统”并渐成伦理学之主流。“规则传统”主导下的道德教育,因强调和凸显理性对规则的认知、理解和遵从,也就相应地导致了叙事在道德教育中地位的弱化。
康德的伦理学是规范伦理的典型。康德将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提到了首要地位,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必然性。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理性指引下,排除一切外在的干扰,发自内心地“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规范伦理强调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必然性,这势必与带有个体性、偶然性特征的叙事伦理相抵牾。是故,在康德那里,我们很少见到他对叙事的论述或运用叙事去论述——比如,像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那样,大篇幅乃至大部头地通过阐释小说来分析、说明道德问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说康德对叙事没有作出思考。事实上,作为一种证明道德法则和进行道德教育的辅助手段,康德深刻认识到叙事的作用和局限,他提倡叙事应用并同时说明了注意问题。我们从应用例举、注意问题、评价等三个方面来看康德道德教育中的叙事应用。这对加深康德伦理学的理解,深化对叙事伦理的认识,走向德性伦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教育中叙事应用的例举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康德并没有直接运用也不可能去运用“叙事”这一现代痕迹明显的术语。在他那里,叙事是通过故事、小说、传记、辩难、道德问答等具体叙事形式体现出来的。康德以人物传记为例,详细介绍了道德教育中的叙事应用。他认为,在理性为我们确立了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则之后,教师应重视利用人物传记给学生证明普遍的道德法则的正确性,使学生真正理解法则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康德陈述了具体应用步骤:第一,搜索古今人物传记,现成地证明教师们对学生宣明的义务(职责);第二,比较不同环境中的类似行为,让学生判断行为或大或小的含义;第三,激发学生的兴趣,训练其判断力以促其进步;第四,练习认识和赞扬纯粹理性的良好举止,同样练习怀着遗憾和蔑视之情注意对纯粹理性行为的偏离。[4]通过这几步,学生不仅在情感上更是在理性判断力上有所收获。康德认为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这些判断力通过把这些行为看作值得赞扬的或值得谴责的单纯习惯,会为将来生活作风中的端正品行构成一个良好的基础。”[5]168-169
介绍完这些步骤后,康德举了“一个正直人”的例子对叙事应用作了示范说明。比如,教师给学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正直人被要求参与诬告一个无辜且无权无势的人,这个正直人先是被诸多的好处如高官厚禄所引诱,后又被诸多的损失如被迫与朋友断绝友谊、剥夺财产继承权、遭受迫害甚至性命不保等相要挟,最后甚至他那处于极度穷困之中的家庭都恳求他顺从,但不管怎样,他都坚守节气,不为所动。康德说,在听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学生必定会经历一系列的情感变化,“逐步从单纯的嘉许上升到景仰,从景仰上升到惊异,最终上升到极大的崇敬,上升到一种甚至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强烈愿望”[5]170。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认为,通过选择一个故事,我们给学生提供一个榜样,通过这个榜样,我们能激起学生心中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会变成学生的道德动力,有了道德动力,学生便有一种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人的内在冲动。康德看到了正面的道德榜样给学生带来的道德力量。这一点,也是被很多思想家所肯定并强调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甚至认为道德英雄的感召力所启发下的抱负或热望是人类道德和宗教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6]从实际教育效果看,通过叙事,我们把这些道德榜样的故事讲给学生听,这种简单直观的方法远比那些苍白繁琐的说教更能激起学生的道德情感,进而塑造学生良好的道德品格。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说:“如果你曾经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像乃至实践的行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7]
但是,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康德引导我们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上述这个“一个正直的人”的例子中,最终使我们作出正确道德行为并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其关键与其说是“情”还不如说是“理”。按康德伦理学理论,这个“理”就是理性确立的普遍的道德法则。康德亦明确指出,孩子最终被征服的不是故事主人公的“生命的内在激情”而是对“法则的敬重”,即这个主人公将纯粹而不混杂任何意图的法则安置在心灵上。康德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没有理解它,仅仅停留在情绪被感染之上,只能算是心血来潮,心血来潮并不能裁成个人的道德价值。康德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人们喜欢用情感调校心灵而不是用严肃的职责调校心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要被叙事所展现出来的柔软、强健、狂妄的情感牵着走。因此,在康德那里,在道德教育时,叙事可以用,但要注意许多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下面我们来详细解析。
二、道德教育中叙事应用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看到,康德注意到了叙事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康德这里,这种作用和应用均是有限的。在康德看来,叙事只是道德法则证明和道德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它多用在理性能力尚不成熟的儿童和青年身上,它不能代替学生的理性培养,相反,它的应用还要以学生的理性培养为前提。康德认为叙事应用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叙事要以“义务”(职责)为范本
康德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是在他努力地排除一切外在的诱惑、目的、干扰后发自内心的只按照理性的普遍道德法则行事而体现出来的。理性给我们颁布与外在目的无关的“定言命令”,这些命令即是我们的“义务”,按照这些“义务”行事才能表现和成就道德。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并不是任意一个故事都适合当作范本来讲给学生听的。我们给学生讲的故事,也应该以“义务”(职责)为范本,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范本中,纯粹的、高尚的道德才能得以展现。前面所讲的“一个正直人”故事中,主人公不为外界的任何利诱、威逼、恐吓、恳求所动,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不诬陷别人的义务,这便是一个好的道德教育叙事范本。康德这样总结这个事例:“倘若道德的法则,神圣性和德行的形象要对我们的心灵处处施加某种影响的话,那么它们只有在作为纯粹而不混杂任何福乐意图的动力被安置在心灵上时,才能够实施这种影响。”[5]170这也就是说,只有仅仅是出于“义务”而不夹杂其他功利目的的道德才有自身的庄严和崇高。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也讲到,我们在每一次的道德教育的课堂上应努力引导学生关注我们如何通过灵魂的升华来战胜诸种困难和冲突从而仅遵从我们的“义务”。“灵魂受到的诱惑越多,这种升华就只会越强烈地鼓舞灵魂去尊崇自己的义务。”[8]493“强烈地鼓舞灵魂去尊崇自己的义务”这正是道德教育中叙事应用的作用和直接目的。
基于这种考虑,康德严厉反对那些以功业为叙事范本而对学生进行的道德教育。康德认为,这样的道德参杂着各种目的,是不纯粹的,它难以激起学生心中对纯粹道德的庄严感和崇敬感。这种教育方式如果不是有害的话最少也是没有任何真正作用。康德告诫教师:“把所谓高贵的、慷慨的和求功业的行为树立为孩子们的范本,而其意旨在于通过灌输对于这类行为的热情来收复他们,这全然是南其辕而北其辄。”“如果行为所由从出的动机是对他职责的高度尊重,那么正是对法则的这种敬重,而非自命的内在的慷慨和高贵的功业思想,恰好对旁观者的心灵具有最大的力量。”[5]171
熙攘天下,名来利往。毋庸讳言,受社会以功业标准衡量人之价值的风气影响,在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功利叙事范本(充斥于图书市场的各种“成功学”图书即是一例)。通过对“一个正直的人”叙事范本的详细分析,康德启发我们:人之价值和尊严只有在自己所承担的无条件的“义务”(职责)中才能得以体现,功利教育并不是真正的德育,它最终也无助于学生高尚道德的养成。
(二)叙事要以理性能力的培养为目标
教师讲给学生听的故事是他人的故事,故事讲述的也是他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他人能否成为我们行为的依据?康德明确指出说:“他人给予我们的东西,不能确立德性准则。因为这种准则恰恰在于每个人的实践理性的主观自律,因此不是其他人的举止,而是法则必须充当我的动机……好的样板(示范性的转变)不应该充当典范,而只应当充当合乎义务的东西的可行性证明。因此,并非与某个他人的比较(他是怎样的),而是与他应当怎样的理念(人性)的比较,因此是与法则的比较,必须给教师提供其教育的绝不可少的准绳。”[8]489-490在康德看来,榜样虽然能激发我们的道德情感,但这毕竟只对我们的行为起辅助作用,榜样本身不能给我们提供行为的法则,只有我们自己的理性才能为我们的行为立法。在进行道德教育时,教师应让学生理解,不是别人教会你行为的准则,而是理性直截了当地教导你并命令你应当去做。因此,在叙事应用中,应该以学生理性能力的培养为教学目标。对于儿童和青年的道德教育而言,因其理性能力尚未成熟,故而更要加大其培养力度。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提供了“一部道德问答手册的片段”,详细描述了一个教师如何通过问答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在这一片段中,康德强调了对学生理性能力的培养问题。他说:“在这种问答的道德课程中,对道德教化来说具有很大用处的会是:在每次剖析义务时提出一些决疑论问题,并且让孩子们聚集起来尝试自己的理智,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打算如何解决摆在他面前的棘手课题。——不只是因为这是对理性的一种与未受教育者能力最相适宜的培养(因为这种培养在涉及什么是义务的问题上能够比就思辨问题而言远为容易得多地作出决定),并且是一般而言使青年的理智更加敏锐的最合适的方式,而主要是因为人的本性就爱这么做,在这件事中和在对它的处理中,人一直形成了一门科学(借此他如今就明白了),而这样,学生就通过这类练习不知不觉地被引入到对道德事务的关切之中。”[8]493-494决疑是人的本性,也是培养理性的一种极好的方法。下文中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谈这点。
(三)叙事要实事求是,切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理性对教师提供的叙事进行决疑
在道德教育的叙事中,有些教师追求榜样的“全部德性价值”,唯恐不这样做,就会减损榜样的真实性和道德感召力。康德对这个不良倾向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过分追求榜样的道德完满性,或让我们觉得榜样遥不可及,或让我们耽于单纯的幻想,结果只会让我们放弃普通和平凡地走向德行的努力。康德意在告诫教师,在叙事应用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切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俗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全人”,道德上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教师竭尽全力地维护所予榜样的“全部德性价值”的努力最终也只能是徒劳的。
退回来想一想,为什么不能允许榜样有一些瑕疵呢?榜样的瑕疵有助于学生的决疑从而也有助于他们理性能力的培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在道德教育中的叙事应用时,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理性对榜样进行评判。
然而,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教师自身对学生的评判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态度。教师不能认为学生的决疑是恶意的非难和有意地论证德性只是空名,相反,教师要耐心地引导学生找到一条对榜样进行评判的准绳,这条准绳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普遍的理性道德法则。因此,学生依照普遍的理性法则对榜样进行评判其实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一种道德上的严格追求。
康德这样阐明学生决疑的实质:“其实这常常只是在依照不容情的法则规定真正德行含义时的善意的严格,在与这个法则而不是与榜样比较时,道德事务中的自负大为降低,谦卑不但得以教授,而且也为每个人在其深刻的反省中感受到。”[5]168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普遍理性的道德法则对榜样的德行进行检验,既可以看到榜样之难能可贵的地方也可以发现榜样之不足的地方,对于榜样之难能可贵的地方,我们应加强学习,对于榜样之不足的地方,我们须深入反思。这种学习和反思能让我们免于道德自负从而时刻保持一颗道德上的谦卑之心。
顺着康德的论述,再反思一下我们的道德教育。我们为道德典型隐讳瑕疵不仅屡见不鲜,而且还是一个传统。《荀子·成相》中便提到了当时社会的“隐讳疾贤”现象,唐代杨絫为《荀子》一书作注时说:“隐讳过恶,疾害贤良,长用奸诈,少无灾也。”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更是说:“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道德典型往往被塑造得完美无缺,有的甚至是从小就德性不凡,在做出道德行为选择时,很少面临道德心理冲突,完全是见在良知,当下即是。很明显,这样的道德典型是“可望不可即”的,最终,难逃被戏谑、被消解乃至被消费的命运。《中庸》有言:“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也就是说,道不远人,即便是匹夫匹妇,也能知晓与践行。康德不提倡叙事范本的十全十美,为的就是给学生自身的理性判断和道德践行留下得以锻炼的空间。
(四)叙事要注意叙事者本身的榜样作用
在道德教育的课堂上,教师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作者,因为在学生的眼里,教师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对学生而言,在由教师这一作者撰写的故事中,教师本身即是一个榜样。这也就意味着,学生们不仅仅模仿教师所讲故事中的榜样,他们往往还把教师本身当作榜样来模仿。康德对这一点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德性教育的实验手段(技术手段)是以教师本人为模范实例(具有示范性的表现),以他人为告诫实例,因为仿效是对于还未受教育的人来说是接受他今后采取的准则的第一次意志规定。”[8]489因此,在道德教育的叙事应用中,教师应注意自己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之作者的双重角色,按照这一双重角色,他在提供榜样的同时亦在塑造自身为榜样。所以,在道德教育中,教师自身的言行举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教师本身就应努力成为一个标准的叙事范本。康德在此处其实对教师这一职业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禁为康德伦理思想的周全和深刻击案叫绝。在他的伦理学说中,道德的功利性、道德的虚假、道德的自负、道德的矫揉造作、道德的幻想、道德上无法攀及的完满、道德的狂热等均无立足之地。康德批判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道德之纯粹。在康德那里,“纯粹”两字有其发轫和终结之点,任何对此点的偏离都难免会走向道德上的不纯粹。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听听康德是怎么说的吧:“道德学发轫于道德本性的高贵性质,这种性质的发展和教化指向一种无穷的益处,终结于——狂热或迷信。”[5]178
三、道德教育中叙事应用的评价
在康德的道德著作中,谈道德教育的篇幅虽不大,但道德教育作为道德认知的重要一环,还是引起了康德的重视。康德意识到,作为一种证明道德法则和激发学生道德情感的辅助手段,叙事在道德教育中可以得到应用,当然,其应用也应注意诸多的受限制的问题。如果把这些限制放到康德的整个伦理学体系中去理解,我们便发现它合乎康德的理论逻辑且对现实问题有着重大启发意义。康德的伦理学体系凸显了道德的自律性、纯洁性和崇高性,在排除了功利的、幸福的、人性的、神学的基础后,康德牢牢地将道德规律奠基在普遍理性之上。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因自身的可普遍性及无条件性而受到尊重和向往,这是道德法则的绝对价值,也是我们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因此,就道德教育而言,应该注意叙事范本的选择,它应该能体现道德的“绝对命令”,应该能有助于训练且提高学生的理性判断能力,应该能有效反对道德功利、道德虚伪与道德狂热。康德所提示的上述注意问题,在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中仍未能得到很好注意,这也是我们今天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原因。
当然,康德的伦理学说仍然带有空想性。正如有学者所说,康德的伦理学“宛如一束断了线的气球,高入云端,五彩斑斓,熠煌耀眼,但永远落不到实处。它对一切时代有效,对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效,对一切人有效,对任何一个人都无效。它要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因而永远也得不到任何可能得到的东西。”[9]译序38-39究其原因,康德排除一切经验杂质之后纯形式的道德法则在具体的道德实践和具体的道德境遇中根本不能得到普遍地遵守。牟宗三借用“云门三句”来评价康德的伦理学,说康德的伦理学只做到了“截断众流”,还没有做到“涵盖乾坤”,更没有做到“随波逐流”。[10]也就是说,康德的伦理学做到了“源头”干净,但在沟通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上,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康德的理论便显示出了它的窘境。牟宗三的这种概括是新颖而深刻的。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局限,康德的这种以培养理性以确立和理解普遍化的道德规则为目标的道德教育方式便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理查德·罗蒂便认为,普遍理性是一种形而上的不诚实的假设和言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法则,我们的道德法则都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即道德法则处于某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体中才能得以理解。罗蒂进一步认为,与其说是因服从普遍道德法则而做出道德行为,不如说是我们受到伤害时对痛楚的敏感而促使我们做出道德行为,而这样的道德敏感性只有小说、电影、戏剧、报纸报道等才能提供给我们,所以,未来社会的道德指引者是擅长讲故事的作家、记者等人而不是像康德那样的哲学启蒙者。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持,罗蒂直接提出了“抛弃论证,转向叙事”的口号。我们也可看到,在康德那里尚作为辅助手段的叙事在罗蒂那里得到了肆意地使用。与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寥寥几页谈叙事应用不同,罗蒂则大篇幅乃至大部头地谈叙事应用,这样仍不过瘾,最后罗蒂干脆从哲学系转到比较文学系,通过阐释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如何在叙事中成就美德。罗蒂的这种做法让我们想到海德格尔。他通过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来阐明“存在”。海德格尔亦反对康德式的理性确立的普遍法则。他认为,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只有在对本质的寻求中,我们才能获得理性,因此,哲学静思是理性获得的一个主要途径。海德格尔将这种在对现存事物的沉思中达到理性顶点的过程称作“视的隐喻”,他认为,除此之外,在我们理性的逻辑空间外面,存在着改变一个人语言和生活的召唤,这种召唤是“听的隐喻”,对一个人德性的成就而言,具有开放性的“听的隐约”显然比具有封闭性的“视的隐喻”更好。[11]很明显,“听的隐喻”要求的是来自叙事的启示而不是来自理性论证的确定。
叙事的开放性使我们有着更多的道德选择和参照标准,这会不会带来道德失范乃至价值虚无呢?这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家所忧惧的,他们认为,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性而言,道德参照标准的模糊性和多元性是一种亟待校对的“不健康状态”。正是有这样的忧惧,康德才对叙事在道德教育中的应用采取谨慎的态度。有必要这样裹着小脚走路么?“道德之不确定性”真的是一种可怕的状态么?齐格蒙特·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对康德的忧惧作了回应。从上文分析中我们知道,康德的谨慎是为了保证道德能牢固地建立在人类的普遍理性之上。但鲍曼认为,康德所积极维护的普遍理性是“难以捕捉”的,是哲学家“个人制作”的神话性名词。鲍曼进一步认为,普遍理性抹杀了实际生活中道德选择的两难,在它的审视和监控下,我们的道德感情越来越麻木,道德成长的冲动越来越丧失,德性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因此,在没有根基的后现代,康德所忧俱的价值多元恰恰是鲍曼所欢迎的。在鲍曼看来,在后现代,没有普遍伦理规范的状态会成为一种“新常态”,我们应该学会生活并且可以生活在这样的新常态中。鲍曼援引戴维斯的话说,把人类想象成一只善变的蜥蜴,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主题。[12]26鲍曼的意思是说,人类自由与可变的天性使他们向往道德的多元标准,这种多元虽然有不稳定特征,但恰是这种不稳定给我们带来了开放与活力,刺激我们的德性成长。鲍曼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我们不是接近普遍理性或本质这一目标的“朝圣者”,而是没有预定目的和固定路线的流浪者、观光客,我们的快乐和好奇之心促使我们从一个点移向另一个点。鲍曼说,促使我们不停前行的动力“在于他对上一次旅居地的醒悟和他对尚未参观的地方那种永远潜藏的希望,也许下个地方没有像他以前参观的地点一样拒斥他的缺点”[12]282。对某一个预设目标的接近不是我们不断前行的理由,相反,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看不同的风俗、风景,满足我们的好奇、快乐、希望之心,是我们不断前行的理由。“知识来源于惊异”,同样地,被一种我们所期待和所感惊异的人所召唤并想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也是我们道德成长的源动力。我们不仅不恐惧于道德多元反而乐意看到并维护道德多元。
在古希腊,德性的内涵之一就是卓越。人不是神,人永远不能达到卓越的顶点。我们只有在对自己不断的否定中不断地走向卓越。所以,我们需要有关走向卓越的各种开放式而不是一种标准式的故事,我们渴望听到的下一个故事,能启发我们走向卓越。叙事能给我们提供各种卓越的范本。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的论述告诉我们,叙事伦理在回归德性伦理传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3]
【参考文献】
[1] 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15-16.
[2] 李志雄,季水河.卡塔西斯——一种亚里斯多德式的伦理批评原则[J].外国文学研究,2007(3):110-117.
[3] 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戴兆国.西方道德哲学著作解读[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165.
[5]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735.
[7]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8]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郑家栋,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97.
[11]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7.
[12]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林雪漫]
Kant's Theory on Application of Narration in Moral Education
ZHENG Xiaomian,HUANG Taik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thic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Abstract:As a supplementary means of proving the moral law and moral education,narration is applied in Kant's ethics with specific forms,such as stories,novels,biographies,debates,Moral questions and answer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rong voice of virtue ethics,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application of narration in the moral education of Kant,We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Kant's ethics,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rrative ethics,and go to the virtue ethics.
Key words:Kant;moral education;narrative;narrative ethics;virtue ethics
作者简介:郑晓绵,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研究生,从事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黄泰轲,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博士研究生,从事中、西伦理史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学校德育创新项目(2015DYYB064)
收稿日期:2015-12-15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6)04-00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