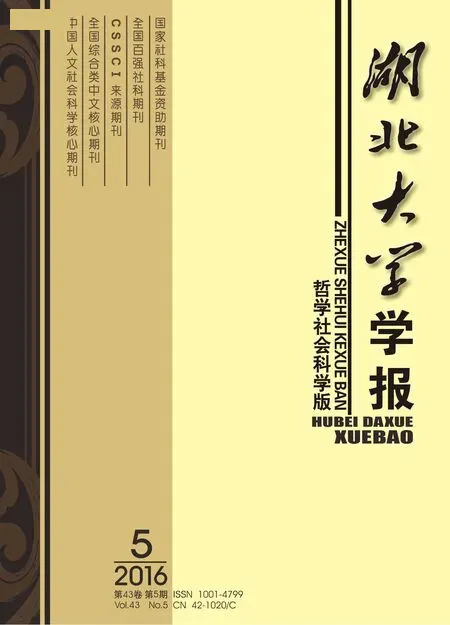民国女性作家群的文学史书写
2016-03-09余蔷薇
余蔷薇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民国女性作家群的文学史书写
余蔷薇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民国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当时的文学史编纂者将这些女性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来叙述已渐成一种风气;1940年代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各种文学史著中,这个性别“群体”不复存在;19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女性作家群”这个概念再次出现,但已呈现出别样面貌。究其原因,民国时期的女性创作、读者接受和文学批评的繁盛,促成了民国文学史书写突破既有体例开始突出述者主体性,也因此留下了不成熟的痕迹;1980年代以后的主流文学史中,有成就的女作家个人得到了合理的文学史安排,性别意识在具体的作家论中也彰显有致,但“女性作家群”却在这种更显“成熟”的文学史叙述逻辑中遭遇切分与消解。
女性作家群;民国时期;文学史书写
民国女性作家群的文学史书写是指民国时期编纂的文学史著对一批女性作家给予的一种群落性关照。“五四”以降涌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女性作为一支特殊的、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进入文学舞台和民国史家的视野。从史著层面看,中国文学史开始自觉叙述女性作家群,而且这种书写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倾向;但到194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各文学史著中,这批作家作为一个女性文学“群体”不复存在;19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女性作家群”这个概念在文学史著的描述中再次出现,但已呈现出别样的叙述面貌。在这样的文学史书写变迁中,民国女性作家群的文学史叙述或型塑,是值得专门考察的。
一
自1922年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叙述新文学的发生历史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论及新文学的文学史著。最早对女性作家予以介绍的是1928年光华书局先后出版的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和赵祖抃的《中国文学沿革一瞥》。前者在小说中提及冰心的《超人》、庐隐的《海滨故人》;后者对冰心女士的诗作给予“谓极一时之难能,树新诗之壁”[1]124的高评。但两者均只是提及个别女性作家创作。
最早将女性作家创作作为一个群体现象来观察的文学史著是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版)。在“鸟瞰中的新文学”这个章节中,著者集中论述了冰心、绿漪(苏雪林)、沅君(冯淑兰)的作品:“冰心女士的作风也恰如她的小说集的名字《超人》,同派的像绿漪(苏雪林)女士的《绿天》与《棘心》,沅君(冯淑兰)女士的《卷葹》、《劫灰》及《春痕》,都能表现出她们超于肉爱的伟大精神,和非尘俗所有的自然之情和美。”[2]360并罗列其他女作家陈学昭、庐隐、凌叔华、吴曙天、陈衡哲、露丝、吕云沁、张近芬、蒋逸霄、白薇等及其作品[2]370。其中所列举的露丝的《星夜》、吕云沁的《漫云》、张近芬的《浪花》、蒋逸霄的《绿笺》,已经完全消失在后来的文学史书写和新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谭著视苏雪林、冯沅君与冰心同派,显然,“派”在此处蕴含着强烈的性别意识,谭氏虽未及以“女性作家群”或“女性文学”界定诸位女士的创作,但这里依女性性别将这个群体独立出来的意图已然明显。
将女性创作作为独立的现象来观察并不始于文学史著。早在1928年,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以严苛的眼光挑选新文学运动的杰作,以期“列入世界作家之林”,“很自负”地让外国学者去研究,其挑选乃依据思想、学术、短篇小说、白话诗、戏剧、长篇小说以及女作家分类,虽然这几个层面之间缺乏科学的分类逻辑,但就其专门类列女作家这一点来说,足见其对女性创作这个现象的重视程度。陈源选取了冰心的小说和白薇的戏剧:“一位是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一位是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3]345此论述颇见1928年文坛女作家兴起时的状况,冰心的风靡自是不用多说,白薇刚展露头角,这种描述一方面可见陈源精准的判断力——在白薇还“几乎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推举其作品列入“十部著作”,不能不说大胆而有见识。更重要的是,能将此二位女性并列,以“女作家”与诸种文体相并列,虽然缺乏一定的分类逻辑,但确实能见出对“女性创作”这个新兴现象敏锐的嗅觉。果不其然,之后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出版社1930年版)中就依样抄录陈氏的论述;此后的文学史著,尤其是1930年代大规模的“造史”高潮中,无论编纂者身处何种阵营,受到何种思想影响,均开辟专节或至少用专门的文字论述女性作家。
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著,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是第一部系统的新文学专史。王著在新文学第一期中重点论述了冰心、庐隐、冯沅君,第二期集中论述了丁玲、陈衡哲、绿漪、凌叔华、谢冰莹。尤其是介绍第二期作家时,王氏专门指出:“在这一期中有几位女作家,是应该提到的。她们的创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在技术上,都显示了很大的成就,并不下于男子的。从此重男轻女的观念,可以完全打破,使她们的天才自然发展,而在文艺的园地里,得到相当的地位。现在可以择几位很有希望的女作家论列于左……”[4]227在按时期、文体、派别的分类体例中,“女性作家群”已经独占一席之地,这意味着女性作家群体的创作在专门且系统的新文学史著中正式得到了醒目的标举。
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著如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武汉大学图书馆复制1931年版)、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徐扬的《中国文学史纲》(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许啸天的《中国文学史解题》(群学社1932年版)、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年版)、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1935年版)、霍衣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广州北新书局1936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等,这些文学史有的是著述千年中国文学史,有的是新文学专史;编纂者身份不一,有的从事文学创作,有的专事学术研究,有的从事革命活动,不一而足,但均花费了专门的笔墨来论述女性作家群。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在新文学的小说部分,论述“女作家”冰心、庐隐、沅君、丁玲、陈衡哲、凌叔华;在散文部分,则论述冰心、陈学昭、绿漪。胡著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皆为“不可多得的女性文学”[5]307,这里的“女性文学”虽然与1980年代后兴起的“女性文学”概念不尽相同,没有后者那样清晰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却是编纂者在自觉的性别视野下对“女性作家群”的群体文学特征的体认。霍衣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更是将女性作家群的小说分为了两派:一派“如冯沅君的大胆敢言,和凌叔华充分表示旧家庭婉顺女性的人格,和同以秀丽文字震动文坛的绿漪,她们是终于沉默在幸福里,与苦闷的象征绝缘,以后也就再听不到她们的歌唱”;另一派“是庐隐和谢冰莹、丁玲、白薇。她们始终脱不掉生活的苦网,所以和文学缘也就归结较深”[6]86。分派之后再细致论述各派之异同点。霍氏在散文部分又专论女性作家群的散文特点,他不仅将女性放到一个群体、流派来论述,还同中现异,深入论述女性作家群在群体特征背后各自的风姿仪态,如认为苏雪林的散文如“小阳春天气,有些醉人”,“有时又似春天,使人觉得世上无处不甜美可爱”;而陈学昭的散文则“带着秋天肃杀的气氛”,有时“又带着北风怒吼的哀怨”[6]115。徐扬的《中国文学史纲》与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均为左翼文学史,二者也极其重视女性作家群。徐著较为粗糙,新文学作为尾巴附在最后的论述中显得非常简略,但在结束该著简单列举“现代文学的几个方面代表作家”时,徐氏的分类标准是小说、诗歌、戏曲、散文、文学批评、文学史、女作家、翻译,并专门罗列出女作家的姓名:冰心、庐隐、绿漪、沅君、陈衡哲、陆晶清、蔡慕晖、凌叔华、冰莹等[7]55~54。贺著被誉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国现代文学”①贺凯是早期共产党员、革命家,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1953年,周扬视察山西大学时,在大会上赞扬:“贺教授在30年代师大读书时,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本书是我们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具有划时代的价值。”详见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第三十九卷《社会科学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25页。的文学史著,它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冰心与庐隐的作品,随后也列出“不少的女作家”:冯沅君、白薇、凌叔华、绿漪、丁玲等[8]372~373。
在这些民国时期编纂的文学史著中,“女性作家群”受到了充分重视,可以想见当时女性创作的繁荣。然而,在建国后一个时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女性作家群”这一概念伴随性别意识的淡化而不复存在。
二
1970年代后期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作家群”呈现出了与民国时期不同的景观。一方面,在少部分文学史的叙述中,“女性作家群”再次进入史家视野。如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即重现了“女性作家群”——该著在叙述女性作家的创作时均将之处理为群体来论述。例如,在成长期(1921~1928)“短篇小说欣欣向荣”中,列“庐隐·冰莹·冯沅君”为专节,著者专门指出:“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八这个期间,女作家可分三批来介绍,第一批的女作家是陈衡哲、冰心和庐隐,第二批是冯沅君、苏梅(雪林),第三批则是丁玲、谢冰莹和白薇。”[9]168~169在收获期(1929~1937)“散文的泥淖与花朵”中列“陈衡哲·冰心·丁玲”为专节,此节结束时,著者强调:“女作家中还有袁昌英、凌叔华、黄庐隐、林徽音、萧红、苏雪林、沉樱、白薇等在收获期留下可观的散文作品,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介;有些则因限于资料,找不到代表性的作品;有些则因为没有值得特别品鉴的作品。”[10]144在凋零期(1938~1949)“诗歌的歧途和彷徨”中列“陈敬容·赵令仪”为专节,在此节开篇,司马氏即言:“中国新文学史上女诗人不多,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仅有冰心、白薇,三十年代有林徽因、方令孺、陈学昭、陆晶清,作品都很有限,到了战时战后,就更寥寥可数了。”[11]234后半部分言“赵令仪经历不详”而未对其生平作任何介绍,根据前两卷的体例安排,想必此处也是依性别将两者并列。如果说司马氏的文学史著因远离新中国意识形态而在异域追求“文学非政治化”而走向一种“诗意与唯情”的文学史观,还不足以说明女性作家群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命运的话,那么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则代表中国大陆在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去蔽后“女性作家群”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某些端倪。该著在“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一章后,紧接着设置“在妇女解放思潮中出现的女作家群”专章,叙述了“女作家群出现的历史意义及其特点”,以冰心、庐隐、其他女作家(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为重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章节安排与设置上看,女作家群仅次于鲁迅之后,可见著者的重视程度。在论述中,著者给“女性作家群”以这样明确的界定:以作家性别区分出来的群体,而不是以社团、流派区分出来的群体[12]214。可见,性别意识超越了流派、社团,其意图在于凸显那个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崭新历史现象。
虽然上述两部影响颇大的著作都重现了“女性作家群”,但一个是海外的文学史,一个是小说专史,两者并不代表大陆这个时期文学史尤其是广泛用于教学的文学史编纂的主流,此期更多的文学史著是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散置于各时期、各流派之中。如1980年代最早个人编纂的文学史著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将冰心和庐隐置于文学研究会作家群,将丁玲置于左翼作家群,将萧红置于东北作家群,将郑敏、陈敬容置于九叶诗人群。这样,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女性作家被分散于各流派中。这一体例在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得到了强化。钱著中,冰心分别出现在第一个十年“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小诗体”、“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各节中;庐隐、冯沅君出现在第一个十年“‘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型叙述小说”中;白薇出现在第一个十年“‘小剧场’培育的田汉、丁西林等话剧文学的开创者及其创作”中;丁玲分别出现在第二个十年“‘左联’和左翼小说”、第三个十年小说“现实与民间”中;萧红分别出现在第二个十年的“东北作家群”小说和“左翼作家的‘鲁迅风’杂文和风格多样的散文”、第三个十年“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部分;林徽因出现在第二个十年“京派小说和其他独立作家的小说”中;张爱玲、苏青、梅娘出现在第三个十年小说“通俗与先锋”中,张爱玲还在“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中又被提及。钱著是19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以来影响最大的文学史著,其编写体例影响广泛,其他文学史著基本上沿用之。这样的处理实则取消了性别视野下的“女性作家群”的概念。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女性文学专史。198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著作大量引介,加之新时代中国妇女的思想进一步觉醒,女性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女性文学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198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开始出现研究现代女性文学的专著。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些著作有的虽冠以“研究”之名,实则梳理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并总结其特点和规律,具备女性文学专史的性质。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女性作家群在文学史的编纂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同于民国时期的别样面貌。
三
民国时期编纂的文学史著出现的“女性作家群”,经历了阶段性的中断后,虽然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但已然不再拥有原初的那些特点。需要追问的是,在文学史的书写变迁中,这样一个作家群何以曾被民国文学史所着力书写?
一定时期某个作家群的出现,必然说明这个时期的这群创作者具有某些相似的类的特征,如阵容整齐,人数众多,作品独特,在文坛形成一道亮丽出彩的风景。五四时期,西方世界所带来的“现代认同”,冲击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形成了“现代视野”的“个体自我”之发现[13],其中包涵着女性独立和个性解放思想,“新旧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体现在对女性的态度上”,封建文化压制女性意识、身体与权力,“现代文明是一种尊重女性、欣赏女性的文明”[14],女性“个体自我”的发现与阐扬为女性作家群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契机。这种空前的文化启蒙与文化滋养使众多女性走出家庭,以文学创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介入社会。到了文化走向多元的30年代,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出版业的日益发达,催生了大量女性阅读者与创作者,使女性作家的创作从量到质都走向深化。
从量上来看,此期有各种报刊发表大量女性文学,还有各种结集成书的女性文学作品。比如在诗歌方面,1930年代出版的女性诗集就有冰痕的《苦诉》(中国印刷局1930年版)、荪荃的《生命的火焰》(北平孤星社1930年版)、虞琰的《湖风》(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版)等15部之多。此外,除了诗集,这一时期还有女性诗歌选集,如《女朋友们的诗》(新时代书局1932年版)、《女作家诗歌选》(上海开华书局1934年版)、《暴风雨的一夕》(女子书店1935年版)、《现代女作家诗歌选》(仿古书店1936年版)等等。
在小说方面,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梅、白薇等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外,还有大批在今天看来名不见经传但在当初却受到欢迎的女作家的创作。比如,1940年代,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仍然大有销路,谭正璧曾编选过《当代女作家小说选》,遴选出在当时受大众欢迎的16篇作品,作者分别为张爱玲、苏青、杨琇珍、曾文强、程育真、邢禾丽、汪丽玲、严文娟、汤雪华、陈以淡、施济美、俞昭明、吴克勤、周錬霞、张憬、燕雪雯。谭正璧在序言中对作者的创作风格给予了细致深入的评析,他强调自己并非以一个文学批评家而是以文艺欣赏者的资格来编选,“我们并不是读文学史,我也不是在写作家评传”[15]3。编者强调的乃是一种大众读者的欣赏眼光,这说明这些女作家的被选,并不来自专家视野,而是一般文学读者的阅读价值观。它颇能说明民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女性作家群意识,在当时的读书界,是有社会基础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创作的繁荣,也带来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繁荣。30年代曾经出版过多部对女性作家的批评专著,如黄英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对冰心、庐隐、陈衡哲、袁昌英、冯沅君、凌叔华、绿漪、白薇、丁玲10位女作家予以批评。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现代书局1932年版)对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绿漪、冯沅君、沉樱、陈学昭、白薇、陈衡哲10位女作家予以批评,此书还于1946年由四合出版社再版。黄人影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光华书局1933年版)是女作家论的合集,其中收录了对丁玲、白薇、谢冰莹、冯沅君、绿漪、冰心、庐隐、陈衡哲、凌叔华9位女作家的21篇评论,包括对当时以及后来都影响深远的毅真的《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此外,还有专门的女性文学史问世,如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版)、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开明书店1932年版)、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31年版)。前两部均以编年方式,“主辞赋,述诗词,不以小说戏曲弹词为文学”而“殊多编窄”,谭著则“以时代文学为主”,兼顾小说、戏曲、弹词等各种文体[16]自序,但遗憾的是,兴起不久的现代女性创作尚未纳入其视野。尽管如此,中国女性文学专史的出现,意味着文学史家已经开始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千年中国文学史,这无疑具有全新的意义。
一种文学现象的蓬勃发展,以及各种各样多声复义的书写姿态和立场,可以让文学史书写者们重新审视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文学[17]。正是女性创作、读者接受和文学批评的这样一个基础,使得这个群体的创作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码规则,形成了一种新的书写范式。
传统文学史的书写范式往往以文体为中心,中国最初的几本文学史著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10),虽借鉴日本学者,但其著主体部分是以文体流变为线索,如第七篇至第十六篇分别以群经文体、周秦传记杂史文体、周秦诸子文体、史汉三国四史文体、诸史文体、汉魏文体、南北朝至隋文体、唐宋至今文体、骈散古合今分之渐、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为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1914)是分体断代史,以时代和戏剧体裁为线索,而非以戏剧家为章节的中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8]文学史这种以体分野的范式源自中国传统文学“文章辨体”、“历代诗踪”的研究方法。无论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体裁的划分,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文体的搜集,抑或是钟嵘的《诗品》为诗体演进确立评价标准,无不重视文体的寻根探源,以此建构某种前后传承的学统谱系。
很显然,在既有文学史以文体流变为中心的叙述范式中,当时“女性作家群”这样一种主体之凸显现象是无法被完整呈现的。它的可能的处理方式只能是,将她们化整为零地纳入到文体流变的叙述框架中去,但这无疑是把当时的一个文学兴奋区、一个崭新的性别视野中的独特文学风景牺牲给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体制了。这一时代性的文学史书写难题促成了民国文学史书写突破文体范式向主体范式开放的格局。但这种突破与开放,留下的是体例上的混杂、分类上的不讲逻辑,明显呈现出一种不成熟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变革的过渡性状态。
1980年代以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代表的一批大陆主流文学史教材,在叙述体制上将时代、文体、作家主体(群体和个体)给予了一种总分式的具有较好的逻辑自洽性的安排。它继承并发扬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所构建的文学史叙述体制。在这样一种叙述体制中,作为有成就的女作家个人得到了应有的叙述,虽然作家群的概念也获得了文学史的位置,比如流派的叙述得到了凸显,甚至像“东北作家群”的整体性叙述也被兼顾到了,但民国时期那样一批文学史所着意凸显的“女性作家群”,还是被一定程度地化整为零了。这时的性别意识可能已经在具体的作家创作剖析中变得更深刻,但它却随着这样一个“女性作家群”的分割化安排而显得平淡多了。
[1]赵祖抃.中国文学沿革一瞥[M].上海:光华书局,1928.
[2]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M].上海:光明书局,1929.
[3]陈源.西滢闲话[M].上海:新月书店,1928.
[4]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
[5]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M].上海:北新书局,1932.
[6]霍衣仙.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M].广州:北新书局,1936.
[7]徐扬.中国文学史纲:下[M].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
[8]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M].北京:新兴文学研究会,1933.
[9]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
[10]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
[1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1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3]戴景贤.中国现代哲学建构与宗教思惟发展中之儒释交涉[J].长江学术,2014,(3).
[14]方长安.对新诗建构与发展问题的思考[J].文学评论,2015,(2).
[15]谭正璧.当代女作家小说选[M].上海:太平书局,1944.
[16]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M].上海:光明书局,1931.
[17]王德威.我的文学研究之路[J].长江学术,2014,(1).
[18]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M]//王国维戏曲论著——宋元戏曲考等八种.台北:纯真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熊显长]
I206.6
A
1001-4799(2016)05-0084-05
2015-12-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ZW04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5T80825
余蔷薇(1980-),女,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