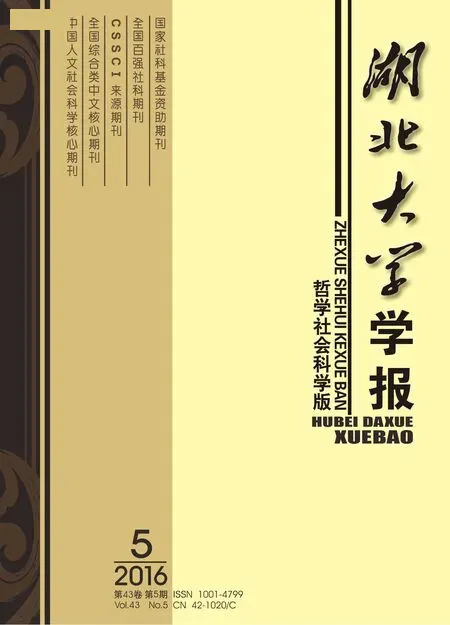现代小城镇小说:基层社会转型初期的历史文化反思
2016-03-09李莉
李 莉
(湖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现代小城镇小说:基层社会转型初期的历史文化反思
李莉
(湖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由都市向乡土基层社会的持续推进,地处“城”之尾、“村”之首的小城镇开始接受西方工业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影响,在器物技术、典章制度和思想意识等层面逐步突破传统束缚,进入艰难的蜕变,整体上却呈现出“破”之初而未“立”的特殊的历史状态,经济破败、政体混乱、“价值失范”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城镇题材小说以“小城镇”为窗口,形象地展示了传统乡土基层社会在异质文明初步撞击下的历史面貌,同时,大多数作品以双向、辩证的视角探讨其文化根源,结合小城镇这一特定区域的社会属性和结构特征,揭示畸形、病态的现代物质文明和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化在小城镇初期蜕变中的消极作用或负面影响。部分小说缺乏必要的理性意识,对于乡土社会转型初期出现的诸多现象缺乏冷静、客观的审美观照。
小城镇小说;社会转型;文化反思
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工业文化和商业文明的持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都市向乡土基层社会渐次推进。小城镇①这里的“小城镇”,特指20世纪上半叶介于大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城小镇,包括通常意义上的乡镇、市镇、县城,以及部分规模不大的州府和都会的卫星城。地处“城”之尾、“村”之首,是一种别于“都会”又高于“农村社区”的“社会实体”[1]326。作为我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建制县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小城镇在基层社会转型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既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对话的重要窗口,又是这场异质文明冲撞的交火地带,显示出乡土社会在异质文明初步波及中的特殊状态。小城镇是现代小说重要的题材类型[2]。现代作家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鲜活的生命体验,刻写出一幅幅生动的小城镇画卷,为我们触摸那个遥远的社会人生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艺术资料,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破”:外来文明的传播与接受
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大致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洋务运动为开端,对“坚船利炮”等器物、技术的学习与吸收;二是以“变法维新”为开端的典章制度层面的改变;三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思想意识层面的变革。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传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化,作为连接城、乡的咽喉要道和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在器物技术、典章制度和思想意识等层面也逐步突破传统束缚,进入艰难的蜕变。
器物技术本是一种文明最外露的物质形态,由于西方的器物技术并不侵害到中国文化的内部价值,所受的阻力最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突破传统文化防线的先锋,对小城镇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只是相对都市,实用又直观的外来物资在这里更受欢迎,技术的引进则要少得多,接受状态也更为复杂。小城镇是城乡交通和物流的枢纽区域,“市镇”、“县城”等多是乡土基层社会的物资集散地和重要的消费市场。相对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多种外来物资进入小城镇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衣食住行的一部分,民众的物质生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3]。偏远的四川小镇的市摊上,出现洋灯、洋布、洋线和洋针(李劼人《死水微澜》)。东北小城,有来自俄罗斯的饼干、糖果、蛋糕、面包、圣诞老人(骆宾基《混沌》),以及手风琴和钢琴等新型乐器(萧红《小城三月》)。纸烟、罐头、太阳镜和白金手表等“都市文明的奢侈品”也已经到了遥远的湘西(沈从文《长河》)。在沿海、沿江地区,有直接从上海进货的花露水、毛巾、香皂。电灯、洋火、洋米、洋油,甚至洋楼等,已由都市传入小城小镇,悄然走进了寻常人家(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相伴而来的,是外来技术的引进。由沿海到内陆地区,火车、汽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电话、电报等通讯设施已经遍布小城小镇(《霜叶红似二月花》、施蛰存《公路》及《洋油》、师陀《果园城记》、何其芳《县城风光》等),即使是最小的乡镇也不多不少地设置了一家邮局(沙汀《某镇纪事》)。电影这一现代化的娱乐样态走进了僻远的乡镇(沙汀《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新型传播媒体——报刊,已深入县城、市镇,成为联系城乡的重要手段之一。民国以后的十年间,僻远的湘西水码头“吕家坪”也一直传阅着上海的《申报》(《长河》)。新型的机械化生产、新式的农业技术也经由唐子嘉(茅盾《多角关系》)、葛天民(《果园城记》)等新式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传入小城镇。同时,这些外来的器物技术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人情风貌等方面的变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葛天民们将新型物种和技术引入中原小城,在祖祖辈辈传承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方法中加入新的元素。机械化生产冲击传统的手工作坊,新型劳资、债务纠纷应运而生。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改变了人们“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古老的花园已经关不住少年人的心了”,钱良才一年之中,往外跑的日子远多于在家的时日(《霜叶红似二月花》)。相对于单纯的生活物资,外来技术(或部分夹杂外来技术的物资)的引入,更容易触及或渗透到其他文化层面,只是因为受到知识和资金等条件的制约,在小城镇的传播和接受是有限的。
如果说器物只是一种文化之“用”,典章制度则是一个文化之“体”,触及文化内核。自维新变法运动以来,涉及传统章制、圣典的众多变革大多与小城镇有着直接的联系,最明显的,是基层社会政权和教育体制的转型。“新”的政权推翻了封建的官僚体制,党部和“委员”代替“知县”、衙门,成为基层社会的政治权力中心,在县政府之外,逐级设立区公所、镇公所,配备县、区议会等机构,沿袭数千年的绅权、族权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从茅盾、叶圣陶笔下的沿海县城、江南市镇,到穷山僻壤的沙汀故里川西北乡镇,县、乡级议员“选举”紧锣密鼓地进行,革命者方罗兰(《动摇》)、世家子弟黄和光(《霜叶红似二月花》)、混迹官场的龚老发团(沙汀《龚老发团》)、传统士绅蒋士镳(叶圣陶《倪焕之》)和胡国光(茅盾《动摇》)等各种身份的人一并活跃于不断迭更的政制变革中。与此同时,新式学堂取代传统私塾,从乡镇到县城,出现小学、中学和多种职业技术学校。蒋冰如、倪焕之等新式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办农场,大张旗鼓地致力于教育变革(《倪焕之》)。此外,晚清民初以来的“敦风化俗”运动(《霜叶红似二月花》),三四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长河》)对礼俗规范的冲击同样值得关注。
由于牵涉到信仰、价值等深层因素,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变最深刻,也最艰难。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西方观念意识层面所遭到的抗拒最强,穿透力也最弱。相对都市,小城镇显然是一个文化防线更为坚固的所在,然而,思想意识层面仍然出现了“有限”的变革。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观念在这里萌芽。女性的处境和地位得到改善,江南小城镇里,金佩章(《倪焕之》)、陶慕兰(柔石《二月》)、许静英(《霜叶红似二月花》)等步入新式学校,在保守的内地小镇,翠姨也呼吸到男女平等的新气息(《小城三月》),王民治、张恂如“默默”地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霜叶红似二月花》)。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使得金钱逐步替代从前的“身份”,冲击传统的价值标准。“轻商”意识逐步淡化,商人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曾经“上不得台面”的商人王伯申开始尝试与缙绅赵守义一争高下(《霜叶红似二月花》),相对举人和秀才,弃儒从商、经商供职者的声势明显提升(许钦文《回家》)。
二、“破”而未“立”:转型初期的历史状态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民族面对异质文化的侵入都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蜕变更新,一是崩溃覆灭。现代文明初期撞击下的小城镇社会里,虽然各个层面日渐突破传统束缚,整体上却呈现出“破”之初而未“立”的特殊的历史状态,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呈现出陈腐、没落的气息,新的合理的秩序又尚未建立。在大多数现代小城镇小说中,所谓的“转型”或“蜕变”给这里带来的尚不是发展和希望,而是愁苦和迷茫。
衰败、没落是这一时期小城镇的整体形象。最明显的,是经济的普遍衰败。费孝通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经济瘫痪”已成为三四十年代包括小城镇在内的乡土社会的普遍危机[1]303。何其芳惊叹四川县城的市面竟失去了昔日军阀统治下的“繁荣”,萧条的市面述说着商业的“凋敝”,小市民们无不“带着愁苦的脸,悲伤的叹息”[4]84~86。茅盾为乌镇的凋敝和破败而扼腕叹息:
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5]89
……
……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乡镇无论如何不可与从前等量齐观了。农村经济的加速度崩溃,一定要在“剪发旗袍的女郎”之外使这市镇涂染了新的时代的记号。
而最最表面的现象是这市镇的“繁荣”竟意外地较前时差得多了。[5]113
王鲁彦、许钦文、郁达夫、茅盾、师陀、施蛰存等人纷纷撰文描写故乡小城小镇的破败,抒写“今不如昔”的感喟。无论是社会学家的研究,还是小城镇作家的小说创作,均在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之外,将这一普遍“破败”的根源指向外来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冲击下传统手工业的没落和自然经济的日益凋敝。火车的到来改变了中原小城的商业格局,二十年前汇聚七十二行、“车水马龙,灯耀如昼”、热闹“非凡”的古城老街形同改道的河床,日益见得空阔,若幺宾们的生意一落千丈(《酒徒》)。江浙沿海小城镇里,轧米船穿行在柴船、冬瓜船和小划船之间,夺走了手工砻米的生意。伊新叔做了二十多年的南货买卖,生意兴旺,然而,拥有洋机器且资金雄厚的永泰商行的出现,使他迅速陷入低效率、高价格的困窘之境,货物滞销,只能蚀本贱卖(王鲁彦《桥上》)。牛奶公司用“科学方法炼过的”、“维他命顶多”的“卫生”牛奶抢走了财生的生意,主顾们认为从前的牛奶全是“豆浆”,“吃了不补”(《牛奶》)。由于外货倾销、白银外溢、民族工业大量倒闭,林老板(茅盾《林家铺子》)、李惠康(《多角关系》)等小城镇商人、新兴民族资本家纷纷破产。
基层社会新旧权力频繁交替,政制迭更,政局混乱。县长、区长、镇长、乡长、党部委员、保安队长、议员、巡官等各种名目的新官僚纷纷登上小城镇这一方小小的舞台;革命者、军阀、新士绅、传统豪绅等各种地方势力走马换灯一般,以至于省当局一年一换,县当局则“平均半年一换”(《动摇》)。革命者摇摆不定,蒋士镳(《倪焕之》)、胡国光(《动摇》)等“土豪劣绅”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操纵舆论、左右各级各类“选举”,真正在政治、教育等方面有志于社会变革的黄和光(《霜叶红似二月花》)、蒋冰如(《倪焕之》)们受强权势力的打压,或成为他们的替死鬼,或被卑劣的手段挤出所谓的“竞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地方政权之腐败、权势者之残暴、基层行政之“僵化”,达到极其罕见的程度[1]380。
混乱的政治格局与萧条的经济相呼应,构成破败而又混乱的社会面貌。文本中的小城镇社会道德严重堕落,传统伦理纲常、习俗制度日益瓦解,人心不古,人欲横流。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相伴而生的淫逸、势利之气腐蚀传统的风俗人情,改变小城的世态观念,拜金主义冲击传统以“诚信义”为代表的商业文化。勤劳节俭的吉顺因步入“建筑有些仿效上海,带着八分乡村化的洋气”的县城,金钱便成为他惟一信奉的上帝,他毫不掩饰自己这种心理:“对呀!人生行乐耳!有了钱就是幸福,有了钱就是名誉;物质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精神不过是变化无常、骗人愚人的幻影罢了”(许杰《赌徒吉顺》)。“旧有的恶习和从滨海城市最新熏陶而来的贪欲”使阿卓成为一个“坐吃山空”的蛀虫(王鲁彦《阿卓呆子》)。金牙、手表、眼镜、上等纸烟、罐头等“奢侈品”日日唤醒并满足刘卓然、胡凤梧的“享受欲望”,使他们“学会比人家消耗一生还多的经历”,吃、喝、嫖、赌样样在行(《果园城记》)。面对遭受灭顶之灾的伊新叔(王鲁彦《桥上》)、林老板(《林家铺子》)、李惠康(《多角关系》),从前敬重他们的信用、与他们长期保持各种生意往来的人纷纷落井下石、谢幕拆台,或乘机挖货,或抽走款项。如史伯伯因为没有接到儿子寄回的钱,便遭到人们的冷嘲、奚落(王鲁彦《黄金》)。在原本民风古朴的湘西,新的普通教育造成一种“无个性无特征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6]389,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已经被常识所摧毁,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7]339。
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价值失范。所谓“价值失范”,既是一种价值规范的崩溃、瓦解,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心理现象,一种人的道德根基被动摇或被连根拨起的特殊心理状态,“传统的以及尚未确立的权威的现代价值秩序,一并失却对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规范导引作用”[8]367。戊戌政变以来如白云苍狗般变幻莫测的世事,尤其是“人欲横流”、世风日下、子辈“荒谬混沌”的社会现实,让以陆三爹为代表的传统读书人深感“危邦不居”,旧有的思想信仰都“起了动摇,失了根据”,感叹“天道”、“性理”成了“一句空话”;面对混乱的社会局面和畸形、倒退的历史演进,新式知识分子也陷入同样的痛苦与迷茫,感慨“这世界虽然变得太快,太复杂,却也常常变出过去的老把戏,旧历史再上台来演一回。不过重复再演的,只是过去的坏事,不是好事”(《动摇》)。对于在文化价值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承担着特殊职责的小城镇知识分子来说,转型初期“破”而未“立”的文化状态,使他们失却了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陷入了难以名状的心灵阵痛与精神焦虑之中。强烈的危机意识同样渗透在普通人的生命感受之中。《新与旧》(沈从文)以湘西“最后”一个刽子手的命运,在新与旧的落差中揭示普遍的信仰危机。在“朝廷”已然改称“政府”、用枪毙代替斩首的民国18年,军部心血来潮,要求已经变成守门士兵的昔日“刽子手”杨金标去砍两个犯人的头。“刑罚”结束后,杨金标照几十年前的规矩逃到城隍庙,等待“神人合作”的审判,却被当成见了鬼、撞了邪气的“疯子”。经历三十年的社会“进步”,围观者与官府都不再需要神的庇护,无法禳除“罪过”的杨金标眼中的世界变得鬼影憧憧,在文明的裂缝中惊恐而死。
三、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双向反思
面对小城镇转型初期这种复杂、特殊的历史现象,大多数作家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理性意识。在他们笔下,“现代”物质文明的畸形、病态,传统文化的腐朽、没落,同是导致20世纪上半叶乡土基层社会畸形演进的重要因素。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享受,展现了人类的理性力量与尊严,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剧烈的心灵阵痛。意义迷失、精神颓废、道德堕落日甚一日,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迷雾四处弥漫,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与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极不协调的精神画卷。20世纪上半叶,技术文明的进步与道德价值的失落之间的这种二律悖反不仅没有随着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成熟得到缓解,反而愈加广泛地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现代文明对乡土中国的浸淫方式、小城镇特定的社会属性和结构特征、小城镇人面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状态,使得这一问题更趋复杂、醒目。
20世纪上半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西洋文化在以小城镇为代表的乡土基层社会“并没有全盘输入,只是输入了它的上层或表面的一层”。这所谓的“上层或表面的一层”,除了“部分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便是“享受欲望”[1]361。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奢侈品的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种罐头在各阶层间的广泛消费,以及“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7]339。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遭受旧势力的强力打压,资本主义的享乐意识、商业文明的金钱价值观念却迅速蔓延。原本朴实的吉顺(《赌徒吉顺》)们变为一批被物质欲支配的“危疑扰乱”的人物;琳琅满目的现代“奢侈品”将刘卓然、胡凤梧(《果园城记》)、阿卓(《阿卓呆子》)们“全副武装”,“贪欲”随之如火焰般生长,推动他们快速滑向堕落的深渊;金钱观念动摇传统的道德规范,打破古朴的民风习俗,将古老的“名誉”观和以“诚信义”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践踏在脚下,在改变如史伯伯(《黄金》)、杨金标(《新与旧》)、陆三爹(《动摇》)等传统小城镇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的同时,却又尚未建立新的更为合理的文明秩序。
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其一开始便处在与传统手工业和自然经济体系异常尖锐的对峙中。受区域经济结构和形式的影响,小城镇是传统手工业和自然经济的重要载体,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初级市场和城乡经济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同时承受着由都市金融危机和乡村破产转嫁过来的多重损失,自然成为这一特定历史进程的“重灾区”。沉重的半殖民地枷锁使资本积累的全部负担落到了仍处在自然经济体系中的广大小生产者身上。伊新叔(《桥上》)、财生(《牛奶》)为代表的小生产者是这种不平等的经济体系的直接受害者,他们非但没有从中获利,反而在所承受的旧的压迫与剥削之外,又背负了新的负荷与灾难。李惠康(《多角关系》)、林老板(《林家铺子》)等小城镇商人在外货倾销、外来资本竞争、机器工业影响下挣扎以至最终“破产”的命运显示,西方机械化工业和商业文明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带给小城镇的,确实是危害大于所得,不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达和现代化的明显进程在这里尚了无踪影,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也面临崩溃的命运。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小城镇社会,现代化进程还处在萌芽阶段,作家实际感受并予以批判的并非纯粹的现代文明,其中掺杂着大量的传统因素。面对这样的混合物,作家批判的力量更多地落在腐化、没落的传统文化上。
在大多数作家的笔下,畸形的物质文明无疑有其致命的毒素,陈腐的宗法常态也未尝不是培植罪恶的温床,影响并决定小城镇“衰落”命运的直接因素是现代工业文明,内在的根源却在于已经熟透以至于腐烂到极致的传统文化。师陀、黎锦明、许杰等作家着力暴露封建文化的腐朽、堕落与现代物质文明中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之间的深层联系,揭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欲横流”背后的传统文化的根源。“祖传的豪奢”、酗酒的恶习早已浸入若幺宾(《酒徒》)们的骨髓,腐蚀人物意志与活力,旧迷信与新贪欲的相互杂糅、渗透,将吉顺(《赌徒吉顺》)、阿卓(《阿卓呆子》)所代表的老中国儿女引入歧途。由于缺乏吸纳异质文化的健全心态,刘卓然、胡凤梧(《果园城记》)等世家子弟也不可能真正接受现代文明中健康、有价值的元素。他们身上具有纨绔子弟挥霍、堕落的本性,有着很多的“恶”,这种“恶”与他们的身份一样,与生俱来。刘卓然生来就背负着父辈勾心斗角的阴影,胡凤梧是那位善于计算的布政使以及那些善于挥霍的布政子孙的后裔,他承袭了“凡我们能想到的破落主子的全部德行,而同时,他也承袭下祖宗们遗留的罪孽”(《果园城记》)。正是这种种“德行”与“罪孽”,使他们沉醉并迷失在畸形、病态的物质文明之中,快速滑向堕落的深渊。相对而言,茅盾、叶圣陶、沙汀的小城镇系列小说则聚焦于典章制度,揭示了传统的等级观念、特权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在政体、教育变革中的巨大的腐蚀性和破坏力。作为传统绅权的代表,绅士在基层社会的地位根深蒂固,近现代化的低度发展和社会结构分化的不足,并不足以动摇其在基层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民国以来,中央名义上以“集权”替代地方“自治”,表面上“筑下了直达民间户内的轨道”,实际上却“半身不遂”[1]380,给了各种地方势力争权夺利的空间。蒋士镳(《倪焕之》)、赵守义(《霜叶红似二月花》)、胡国光(《动摇》)们依然掌控主要行政事务,所谓的新生力量或被“排斥于外”,或依附、寄生于封建宗法业已腐烂的肌体之中。结果,无论是方罗兰(《动摇》)、黄和光(《霜叶红似二月花》)投身其中的大革命运动和议会选举,还是倪焕之、蒋冰如(《倪焕之》)积极推进的教育变革,并无“实质性”进展,不过是“旧有人等,改换名称”而已。
崇古、拒变,甚至以变为不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之一。对于传统的中国人,往往“新”即是“乱”,“变”则往往与“乱”同义,对新事物缺少尝试的心意,对一切违反传统的事物更持怀疑和拒斥的态度。20世纪上半叶,小城镇的新式教育相对都市尚处于萌芽阶段,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了解也多半流于肤浅。认知的不足加剧了小城镇人对外来文明的疑虑和排斥。这种小农意识所特有的文化心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为转型初期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另一重要障碍。在描写小城镇萧条、破败面影的同时,小城镇小说着力展示了人们对新兴事物的拒绝和排斥,强调这种“拒斥”态度的普遍性、盲目性。对于当时的小城镇而言,拆城墙修马路、建公园和图书馆、设置政治训练学校等维新之举均属“变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对此都“蹙着眉头唉声叹气”,这不仅仅是因为“毒莽一样”的马路吞噬了穷人的家,加重了他们的捐税,他们还有一种“心理上的负担”,即“对于那修马路一类新设施的顽固的仇视”(《县城风光》)。无论是新式学堂,还是洋学堂的学生,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人们的非议或排斥(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对于整顿风化习俗的“新生活运动”,仅仅就因为其“新”,便引起满满们(《长河》)的惶恐和不安。即使在现代工商业相对发达的沿海城镇,人们也几乎是本能地排斥外来事物。洋油、公路、火轮在他们眼中成为异端,甚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洋油》、《公路》、《霜叶红似二月花》)。火轮被“砸”、公路被“挖”,外来文化和新兴事物的命运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费正清等人曾经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至普遍衰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自身“明显的惰性”,对于外来挑战的“回应无力”[9]334。正是这种普遍的、近乎无意识的“守常”、“排外”意识形成可怕的惰性心理,久之,则无心变革,也无力变革。正因为此,商人的直觉虽也偶尔令若幺宾(《酒徒》)们萌生到新的集市“碰碰运气”、改变现状的想法,却从来不会付诸行动,伊新叔(《桥上》)、财生(《牛奶》)们也只能哀叹“生不逢时”,在时代的变更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失去自我更新的可能。
四、历史理性:问题与局限
异质文化初期撞击下“破”而未“立”的社会面貌、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双向反思,赋予大多数小城镇小说以深厚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理性批判品格。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状态,部分作家作品缺乏必要的历史理性,对于以小城镇为代表的乡土社会由古典向现代转型初期出现的诸多现象缺乏冷静、客观的审美观照。
现代化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自足的体系,它的构成要素的每一次伸展、存在空间的每一次开拓,都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突破或否定。然而,面对“常”与“变”的更替,部分作品流露出疑虑和不安。自辛亥革命前后到30年代,为了从根本上改良社会风气,加快、加大变革的力度,政府自上而下多次推行一系列改良社会风俗的法令,出现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该运动从大都市蔓延到全国各中小城市,甚至波及一部分村镇,内容广泛,从日常的衣食住行,涉及到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方式、思维结果和价值取向。虽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但这一运动在整体上对于改良社会风貌、推动思想意识层面的革新起到了积极作用。废名、沈从文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新生活运动”对小城小镇的冲击。在他们的笔下,由于对古风习俗的巨大冲击,这一运动遭到人们普遍的排斥与抵制。废名《河上柳》借古风人物之口,称之为“反变”。《长河》全篇笼罩在即将到来的“新生活运动”的阴影之中,并以满满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古风人物对该运动的疑惧与不满,表现了“新生活运动”在小镇引起的恐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对古风人物的同情、尤其是与人物几乎同样的焦虑意识,使作品对这一运动表现出明显的质疑。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沦丧、价值失范等现象,部分作家表现出过度的忧虑和恐慌,甚至以单一的道德标准衡量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表现出较明显的“泛道德主义”倾向。所谓“泛道德主义”,是指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时,偏向道德伦理的判断而缺少冷静的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属于道德文化,现代文明在伦理道德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严重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泛道德主义倾向成为可能。部分作家因此赞美传统伦理道德和古老的诗礼传统,为其没落感叹、哀伤,质疑、诅咒现代文明,并以此作为衡量社会常与变、进与退的标准。《长河》所表现的三四十年代,“现代”二字已到了吕家坪之类的湘西市镇,古朴、自然的民情民性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迅速瓦解,农业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作者因此感慨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勤俭治生”、“忠厚待人”的品格被外来洋布煤油“逐渐破坏”,质疑所谓的历史“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并由此得出变化中的“堕落趋势”这一历史性的结论[7]339。与此同时,部分小说将一切萧条与衰败、罪恶与堕落皆归根于外来文明,缺乏双向、辩证的审美观照。施蛰存《上海来的客人》、《渔人何长庆》中,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成为“诱惑人的恶魔”,侵蚀小城小镇古朴的民风,引诱、欺骗菊贞似的“纯真”男女,使人“不能防备”。小说强调了现代文明的“恶”和古镇男女的“纯真”,而忽视了人物所因袭的历史重负在其悲剧人生中的影响和作用。
恩格斯谈到文明发展时指出:“数千年的文明制度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淳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10]179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种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一定的代价。以“价值失范”为例,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现象,只是“现代化的进程却使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8]368。审视20世纪上半叶处在现代化发展初期的中国小城镇,需要客观、辩证的理性意识,也应防范以道德尺度代替历史眼光,否则可能被种种民族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束缚发展的手脚,永远在转型期痛苦地徘徊。
[1]费孝通.费孝通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2]易竹贤,李莉.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J].江汉论坛,2003,(11).
[3]朱汉国.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及其特征[J].史学月刊,2003,(11).
[4]何其芳.县城风光[M]//何其芳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茅盾.乡土杂记[M]//茅盾全集(1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6]沈从文.湘西·沅水上游几个县份[M]//沈从文文集(9).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7]沈从文.长河·题记[M]//沈从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8]何显明,等.漂泊的心灵: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价值失范现象[M]//方克立.走向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9]费正清,赖肖尔,等.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责任编辑:熊显长]
I206.6
A
1001-4799(2016)05-0078-06
2016-01-07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资助项目:16D029
李莉(1968-),女,湖北荆州人,湖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