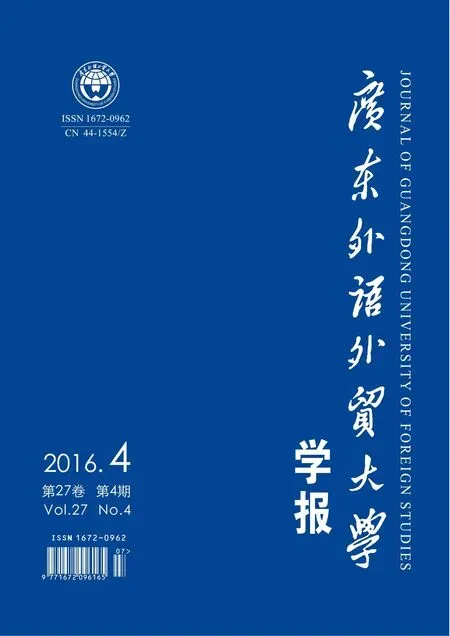虚构作品的秘密生活
2016-03-09丽萨詹塞恩
丽萨·詹塞恩
(肯塔基大学 英语系, 美国 列克星敦 40506)
虚构作品的秘密生活
丽萨·詹塞恩
(肯塔基大学英语系, 美国列克星敦40506)
发展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孩子的词汇量与他们的“思维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虚构作品对读者的思维理论提出了各种要求,阅读虚构作品构筑了一条通往丰富词汇量的康庄大道,对学生的整体学业表现具有长期有利的影响。虚构思维阅读强化了我们日常社交活动所呈现的思维阅读的某些模式,比如,三层套叠式思维状况内在于虚构作品中,在阅读体验中无处不在,文学文本总是比信息文本在更高层面的套叠中运作。如果少教虚构作品,那么只有那些受到父母鼓励而大量阅读虚构作品的学生仍然可以做到学业出色;其他学生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最终的词汇量会比较少,成绩也比较差。
思维理论; 三层叠套式思维状况; 虚构作品; 词汇量
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名为“共同核心标准方案”(The Common Core Standards Initiative)的全国中小学教育改革。尽管这个方案在许多方面可能存在教益,但在其他方面却有问题。具体而言,当涉及英语语言与文学的教学时,这项改革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认识到虚构作品可以激发学生的复杂思考(complex thinking)。支持这项改革的人士认为:为使“所有学生将来在大学、职场、以及人生中取得成功而做好准备”,这些小孩必须阅读比“故事和文学”“更为复杂”的文本。①这种认为“故事”不如非虚构作品的论调在西方文化中具有久远传统;利用这一偏见是容易的,似乎不需要给出任何证据加以论证。
然而,发出这一论调,甚至更糟糕的是,把这一论调作为一项将影响到几代在校生的教育政策基础的人士理应给出证据。考虑一下这个方案所指定的百分比。假如四年级时英语课的阅读分配比例是“文学”文本与“信息”文本各占50%,那么到八年级时,文学文本的比重只占到学生所有阅读材料的45%,而到十二年级时,这个百分比会降至30%。重复一下,“英语语言艺术”下属的所有课程中,70%的阅读材料将会是非虚构类的。戏剧、小说以及诗歌只占剩下的30%。支撑如此大的改动的理由是信息文本能够丰富孩子的词汇量,丰富的词汇量能够带来学业成功。我们认为指定这些百分比的人士至少应该了解孩子的词汇习得研究,这些研究理应表明信息文本比起 “故事和文学” 确实能更好地累积词汇。
然而,这些研究从未被这项改革的设计者提起,原因是这些研究根本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发展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孩子的词汇量与他们的“思维理论”(theory of mind)的发展息息相关。“思维理论”也称作“思维阅读”,即孩子们解释自己和他人由诸如想法、欲望、情感等思维状况所引起行为的能力。②即使粗略瞄一眼发展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也会质疑信息文本读得多将有诸多益处的肤浅论断。对这些研究的持续关注表明:阅读虚构作品构筑了一条通往丰富词汇量的康庄大道,因为虚构作品对读者的思维理论提出了各种要求。因此,改革者应该建议多读文学,而非少读。
请注意,我所说的持续关注不仅仅是呼吁对认知科学家的研究发现进行报道。尽管其中一些发现认为阅读虚构作品有利于孩子的思维理论发展,但是它们对于什么使得虚构作品独具这种效果的思考还是相当笼统。我们也不敢有别的指望。大多数认知科学家对于研究文学文本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来自机构方面的激励。文学学者则拥有这两者,这就是为什么理应由我们来把认知科学的研究和课堂上应该阅读什么的建议这两者的连接进行理论化。
我们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列出阅读清单,而是让大家认识到另一个学科的数据开始在“我们的”领地——我们胜任且致力于探究的领地——的边界上堆积的那些时刻。
首先,我们快速看一下(主要)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把词汇习得与思维理论发展联系起来研究的历史。对孩子的词汇量进行研究始于1891年,但是由于方法论方面的缺陷,这些研究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都不够可靠。1982年,Michael Graves和他的同事发现:“一年级结束时,中产阶级的学生比起下层阶级的学生[阅读并且理解了]大约多出百分之五十的词汇量”(Graves、Brunetti、Slater,1982:102)。后续研究显示:尽管这个差距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而缩小,但是到高中毕业时,社会、经济背景处于劣势的学生所掌握的词汇量仍然比社会、经济背景处于优势的学生要少至少四分之一(White、Graves、Slater,1990)。
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许多关于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理论发展的研究。研究显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出身工人阶级的孩子在所有领域都明显做得更好”,包括对错误信念(false belief) 的认识(即,认识到别人有可能相信你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是真实的)以及情感(Cutting、Dunn, 1999)[注意:这些研究有意使用狭义的思维理论。联系到那个使用“缺乏”(deficit) 方法对下层阶级人口进行测试的不光彩历史,我们应该警惕从这个具有局限性的定义作出关于受试者的思维理论的宽泛论断所潜在的危险。]③后来关于思维理论与词汇相关联的研究给社会经济因素添加了一层重要意思。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比较常跟自己的子女讨论思维状况。那些鼓励出身社会底层的孩子建构关于自己以及他人的思维状况的介入项目(intervention program),当把父母也包括进来时是成功的,而当目标只对准课堂交流时,则是失败的(Peterson、Jesso、McCabe, 1999)。“那些谈论心理话题”的父母 “提高了孩子对思维状况的理解水平”(Harris、Rosnay、Pons, 2005)。
尽管词汇与思维理论看上去相互交织,但是认知科学家并没有就因果关系流(flow of causality)达成共识。这一状况反映了语言习得与思维理论发展两者关系的更大问题。语言与思维理论均为有争议的宽泛术语,关于“谁先存在”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有些科学家认为语言“在思维理论的发展中起着根本性的、因果关系的作用”,其他科学家则认为“语言的作用只不过是为孩子提供建构思维理论所需要的信息的一种自然方式”(Astington、Baird, 2005:4)。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没有达成共识看成是给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包括我们自己,提供了一个良机。
Joan Peskin 和Janet Wilde Astington(2004:254)研究听故事对幼儿园儿童的词汇增加所具有的作用之后,继而研究故事中出现的明确的元认知术语,如认为(think)、相信(believe)、猜测(guess)对儿童的思维理论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可能性。发展心理学家对元认知词汇特别感兴趣,因为撇开其他东西不说,这些词汇与学业表现紧密相关,在初中与高中,这些词汇包括推断(infer)、 暗示(imply)、 预测(predict)、 怀疑(doubt)、 估计(estimate)、 承认(concede)、 断定(assume)和确认(confirm)等用于科学思考以及历史思考的词语。
Peskin 和Astington 改写了幼儿园儿童的图画书,比如Pat Hutchins的《萝西的散步》(Rosie’sWalk):“这样做,文本便具明确的元认知词汇,诸如认为(think)、知道(know)、想知道(wonder)、弄清楚(figure out)以及猜测(guess)”(2004:255)。《萝西的散步》于1968年初次出版,讲述了一只小鸡到谷仓旁的场地去散步,浑然不知有只饥肠辘辘的狐狸紧跟在她身后,随时会扑上来。小读者得根据图片自己建构故事,因为故事包含的文字非常少。Peskin 和Astington比较了两组儿童,一组读了这些书,另一实验对照组也读了这些书,但是没有附上元认知词汇。比较结果是:“听具有许多元认知词汇的故事,不如从那些暗中吸引思维注意的图片和文字中积极建构自己的解读来得重要” (2004:253)。那些听到明确的元认知词汇的儿童的确开始使用这些词汇,但是用得并不正确(2004:267)。
一方面,该研究支持了心理学家的发现,即父母与孩子互动时说的话不如他们如何说这些话来得重要。正如Paul Harris、Mark de Rosnay以及Francisco Pons(2005:72)所观察到的:“父母与孩子交谈时解释了许多不同的思维状况。这些解释并没有跟特定的词汇或者句法结构捆绑在一起,而是反映了对不同视角的广泛敏感性,与此同时培养了孩子同样的敏感性”。
另一方面,该研究发现,在故事中明确使用元认知词汇似乎并不利于儿童的思维理论发展,这让Peskin 和 Astington 接着关注读者应该会暗地进行的思维化活动(implicit mentalizing)。她们这样做也是受到了Letitia Naigles早前一个研究的推动,Naigles 发现:“那些在电视节目中听到更多表示肯定的元认知词汇(认为、知道、以及猜测)的儿童,后来对肯定的区分却不如那些所看的电视节目比较少用这些词汇的儿童”。她们的研究也受到Deepthi Kamawar的研究 (Peskin、Astington, 2004:265)以及Elizabeth Richner与Ageliki Nicolopoulou研究的推动。他们“比较了两组儿童,其中一组的老师使用了更多元认知词汇,另一组的老师使用较少”,“结果发现,老师使用较少认知词汇的那组儿童在完成思维理论任务时表现得更为出色”。
正如Peskin 和Astington(2004:266)所注意到的:“教信息不会自动导向学会”。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 “建构性、努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积极重新组织觉察和作出推断……这些推断可能导向更为深刻的理解,因为孩子得努力去推导出意思。具反讽意味的是,清楚明了的语境可能导致较少思维发展,这正是因为它是明确的缘故”。从这个角度看,阅读虚构作品便呈现为一个建构性学习的范例过程:
当故事里的不同人物对同一行为具有不同认识时,便产生戏剧性冲突。这可以通过失误产生:读者知道罗密欧不知道朱丽叶因服药睡着了、而不是死了。或者可以通过欺骗产生:汤姆·索亚假装姑妈要求他做的杂务是一个冒险活动,从而把他的朋友一个个骗来为他粉刷篱笆(2004:267)。
我认为文学学者应该从这里开始进入讨论。关于阅读虚构作品时读者应该会经历暗地思维化活动的会话是我们应该参与的会话(尤其当利害攸关时,因为Peskin 和Astington暗示,阅读虚构作品可能对学生的整体学业表现具有长期有利的影响。)
思维理论被批评家纳入关注范畴已经接近十个年头了,在许多领域均取得进展(Abbott, 2013; Palmer, 2004; Rabinowitz, 2015; Rabinowitz、 Bancroft, 2014; Polvinen, 2014; Vermeule, 2010; Zunshine, 2006),包括历史主义(Richardson, 2010; Spolsky, 2010)、电影与媒体理论(Plantinga, 2015; Smith, 2015)、戏剧研究(Lyne, 2014)和酷儿理论(Vincent, 2015)。我们仍然不清楚阅读虚构作品时头脑/思维的运作,认知科学家也不清楚。此外,文学学者与认知科学家近来一系列的合作研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所做的有理有据的思考(得到我们学科长期以来对虚构作品的意识的兴趣的支撑)对这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具有一定的贡献(Phillips, 2015; Whalen、Zunshine、Holquist, 2012;Vessel、Starr、Rubin, 2013)。
接下来,我将谈论文学批评对思维理论所做探讨的其中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似乎与Peskin、Astington、Naigles以及他们的同事的发现最为相关。我的出发点是:虚构作品与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认知机制相同,即把想法和情感归因于他人和自己(归因,并不意味着正确地归因。考虑到我们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理解常常出错,也许更为准确地概述我们日常思维阅读的词语是思维误读。)阅读虚构作品是思维阅读的观点,Alan Palmer在《虚构的思维》(FictionalMinds) 以及我在《我们为什么阅读虚构作品》(WhyWeReadFiction) 分别作出了阐释。Palmer主要把该观点运用于小说这个文类,我则关注虚构作品中的思维状况,虚构作品是个宽泛的概念,包括散文、戏剧、叙事诗以及关注想象和意识的回忆录(例如,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Speak,Memory))。
虚构思维阅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化了我们日常社交活动所呈现的思维阅读的某些模式。比如,用三层套叠式思维状况(triply nested mental states)来思考我们建构复杂社会场景时的经历。这种三层套叠就是一个思维状况套在另一个思维状况里面,这个思维状况又套在另一个思维状况里面。与一个朋友交谈之后,我担心她会以为我有意说反我真正表达的意思。我的同伴告诉我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希望我儿子明天会记得他今天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相信你们都能回忆起最近自己的一些三套叠例子,虽然我们经历这些这些例子时并不会对自己明确地表述出来。
虽然三套叠从人际关系上看扣人心弦,并且充满情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偶然出现。在虚构作品中它们则无处不在。更确切地说,相对于它们在文本中的内在性,在阅读体验中则无处不在。虚构作品推动我们建构三套叠以弄懂我们所读的东西,但是这些三套叠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则因处于不同历史语境的读者而不尽相同(Zunshine, 2015)。保持不变的是套叠本身:虚构作品的意义的基本单位是不同思维状况之间的关系。
复杂套叠在段落层面开始累积(Zunshine, 2014),虽然单个句子也可能展现这种套叠。复杂套叠也可以组织起所有章节。思维状况在章节层面和行为层面套叠的现成例子便是Peskin 和Astington 上面所举的例子,我们不妨再次看看:汤姆·索亚不想让他的朋友意识到他讨厌粉刷篱笆;罗密欧不知道朱丽叶只是想让一些人认为她死了。
要把想法和情感套叠起来的话,作者可以主要聚焦人物的思维状况或者人物、叙述者和隐含读者的思维状况(Zunshine, 2014)。此外,她可以选择详细说明这些思维状况,也可以选择只字不提,从而迫使我们做出推断以弄懂我们所读的东西。
同一个文本可能结合了不同的方式。例如,E.M.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End) 是这样开头的:“事情不妨从海伦给她姐姐的几封信说起”(1921:3),小说里面也有这样的句子:“玛格丽特应该知道海伦知道巴斯特夫妇所知道的情况吗”(1921:254)。后者详细说明了人物的套叠式思维状况,前者则要求有一个隐含作者,该隐含作者要她的读者知道行为将通过一个自反式叙述者(reflective narrator)的意识进行过滤——一个隐含的套叠式思维状况。
另一个例子来自20世纪初一本俄国小说,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We),在这里用以展示一本小说可以自我定位为不涉及思维状况(小说设置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在那里,情感被数学公式取代,甚至人们的名字都以数字命名),然而,该小说仍然完全依赖套叠式思维状况:
所有这些都毫无微笑。我甚至可以带着某种尊重说(也许她知道我是Integral的一名建造者)。但是我不确定——她的眼睛或者眉毛里——有种奇怪恼人的x,而我不太能够捕捉到,无法用一个数字表述出来。
这里充满套叠。例如,D-530想知道I-330是否印象深刻,因为她知道他做了什么。还有,他被激怒了,他无法弄清楚她的确切态度。此外,隐含读者知道D-503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爱上I-330。
我最喜欢的一个隐含套叠式思维状况来自曹雪芹的《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套叠式思维状况是通过在人物的名字前面策略性地使用“一个”而产生:
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 (《红楼梦》, 第五回)
我们在理解这个句子时,可以这样来详细说明我们推断出的思维状况:叙述者要他的读者意识到黛玉觉得比平时更没有安全感,因为她确信身边的每个人都认为她比不上宝钗。这里至少有四个套叠式思维状况,但是为了表述清楚,我们得觉察到一些细微提示,比如黛玉用来指她表姐的不高兴语气(“一个薛宝钗”),以及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黛玉具有的近乎偏执狂的自我意识 (Zunshine, 2014)。
我在使用明显是“认知主义”的术语抛出我的观点(例如,“套叠式思维状况”、“思维理论”),但是不应该被遮蔽的事实是:首先开始讨论这些问题的并不是认知科学家,而是文学学者,中国古典诗词研究者Haun Saussy(2006:428)注意到:“思想即使不被言说,也可以被再现,这是所有文学的普遍现象”。在探讨反讽时,叙事学理论家也预料到会出现关于套叠式思维状况的讨论,指出 “宽泛地说,所有叙事艺术的例子都存在三个视角——人物的、叙述者的和观众的。当叙述变得更加复杂时,第四种视角会随着叙述者与作者的明确区分而出现(Scholes、Phelan、Kellog, 2006:240)。
我想通过两点来进一步探讨这些洞见。第一,三套叠思维状况——隐含的和明确的——均构成虚构作品的基本意义单位。因此,叙事理论家所假定的每一个不同视角均表现为一个套叠式思维状况。例如,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1749)。读者知道他们比奥尔华绥先生更了解屠瓦孔先生。然而,为了不使读者谴责“奥尔华绥先生的智慧和洞察力”,叙述者提醒读者,他们之所以知道这一切,唯一的原因是叙述者本人“告诉了” 他们“这些事情”(Fielding,1996:117)。第二,虚构作品里的套叠模仿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交际模式,获得了思维理论的支撑,但是又远远超越它们,这些套叠是用具体文类和作者所独有的文体手段创作出来的,因此不能简化为社会认知(社会认知本身是复杂的)(Zunshine,2011)。
因为从《萝西的散步》到《霍华德庄园》的途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学龄前儿童快乐阅读Hutchins所写的故事时,她的思维阅读经历颇为复杂:这个孩子高兴自己知道萝西这只小鸡并不知道有只饥肠辘辘的狐狸想要吞食她,她也高兴自己知道萝西会一次次地逃离危险。《霍华德庄园》的读者通过这个早前的阅读以及之后逐渐搭建起来的大型文化认知脚手架而构筑了自己的思维阅读。她把破译虚构作品的代码带进了福斯特的小说,④这些代码包括对文类和异质语言(heteroglot)的认识,这种认识伴随着阅读更多的虚构思维而获得。
例如,一个9岁儿童在原则上可能知道“玛格丽特是否应该知道海伦知道巴斯特夫妇所知道的情况”这句话的含义,但是她听不出其中的戏仿语气。因此,她不会质疑福斯特的叙述者,以为是他吐出来这么一句粗糙的套叠句,⑤也不会认真查阅这句话在文本里的出处,该出处其实来自蒂比这个厌烦“个人关系”的年轻小伙子(当然,一个留意句子出处的学生与不留意的学生是有很大区别的,任何科学老师或者历史老师都能证明这一点)。
所有这些思考是如何跟当前教育改革的捍卫者所坚持的观点——信息文本能够促进学生词汇习得,因此在“英语语言艺术”中应该占据比文学文本更大的比重——相关的呢?问题的答案要看你到底如何看待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第一,是元认知词汇(即关于思考的思考)促进了学业成功;第二,如果只是在文本和课堂讨论中接触元认知词汇,那么不会有助于词汇的习得。
如果你重视这些研究,那么虚构作品中的套叠式思维状况值得再次细看。文学文本总是比信息文本在更高层面的套叠中运作。而且,它们不用通过明确使用元认知词语来获得这个更高层面。通过暗示套叠式思维状况,虚构作品示范了 “建构性、努力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学习者积极地重新觉察和推断”(Peskin、Astington,2004)。
当然,信息文本偶尔也能够把思维状况套叠至第三甚至第四个层面,教这些文本的教员偶尔也有可能不堆砌认知词汇,从而不帮助学生完成这个艰苦工作(Zunshine, 2013)。但是,如果我们想找寻一个与持续积极地重新觉察和推断同时进行高层次的套叠式思维状况,那么只有虚构作品可以做到。如果少教虚构作品,那么只有那些受到父母鼓励而大量阅读虚构作品的学生仍然可以做到学业出色;其他学生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最终的词汇量会比较少,成绩也比较差。
注释:
①http://www.corestandards.org/ELA-Literacy/.“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for English Language Arts and Literacy in History/Social Studies, Science, and Technical Subjects.”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 June 2, 2010.
②思维理论的研究在心理学各个分支均呈现指数性增长,包括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认知文学研究等。不过,在本文,我聚焦的是发展心理学与教学,然后是认知文学理论。
③感谢Ernest Morrell 和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Sherian Blau所主持的英语教育课程项目参与的学生提出了这个洞见。
④对Evelyne Ender 和Deidre Shauna Lynch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出的洞见和建议,我深表感谢。
⑤关于虚构作品的出处,参见Zunshine 的著作WhyWeRead。
ABBOT H P. 2013. Real Mysteries: Narrative and the Unknowable[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STINGTON J W, BAIRD J A. 2005. Introduction: Why Language Matters[C]∥ASTINGTON J W, BAIRD J A (eds.). Why Language Matters for Theory of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O XUEQIN. 红楼梦[M][2014-09-29].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body.ASP?CHNO=005.
CUTTIN A L, DUNN J. 1999. Theory of Mi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Language and Family Backgrou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Interrelations[J]. Child Development, 70(4): 853-865.
FIELDIN H. 1996. Tom Jones[M].BENDER J, STERN S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STER E M. 1921. Howards End[M]. New York: Vintage.
GRAVES M F, BRUNETTI G J, SLATER W H. 1982. The Reading Vocabularies of Primary Grade Children of Varying Geographic and Social Backgrounds[C]∥NILES J A, HARRIS L A (eds.). New Inquiries in Reading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Rochester: Natl. Reading Conf.
HARRIS P L, DEROSNAY M, PONS F. 2005. Language and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State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2): 69-73.
HUGHES C, WHITE N, ENSOR R. 2014. How Does Talking about Thoughts, Desires, and Feelings Foster Children’s Socio-cognitive Development?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C]∥LAGATTUTA K H (eds.). Children and Emotion: New In-sights into Developmental Affective Science. Basel: Karger.
LYNE R. 2014. Shakespeare, Perception and Theory of Mind[J]. Paragraph, 37(1): 79-95.
NAIGLES L R. 2000. Manipulating the Input: Studies in Mental Verb Acquisition[C]∥LANDAU B, SABINI J, JONIDES J, ELISSA L (eds.).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Language: Essays in Honor of Henry and Lila Gleitman. Newport. Cambridge: MIT Press.
PALMER A. 2004. Fictional Mind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ESKIN J, ASTINGTON J W. 2004. The Effects of Adding Metacognitive Language to Story Texts[J]. Cognitive Development (19): 253-273.
PETERSON C, JESSO C, MCCABE A. 1999. Encouraging Narratives in Preschoolers: An Intervention Study[J].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6): 49-67.
PHILLIPS N M. 2015. Literary Neuroscience and History of Mind: An Interdisciplinary MRI Study of Attention and Jane Austen[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LANTINGA C. Facing Others: Close-Ups of Faces in Narrative Film and in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LVINEN M. 2014. Engaged Reading as Mental Work: Reflections on Teaching Cognitive Narratology[J].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16(1): 145-159.
RABINOWITZ P J. 2015. Toward a Narratology of Cognitive Flavor[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ITZ P J, BANCROFT C. 2014.Euclid at the Core: Recentering Literary Education[J]. Style, 48(1): 1-34.
RICHARDSON A. 2010. The Neural Sublime: Cognitive Theories and Romantic Text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ICHNER E S, NICOLOPOULOU A. 2003.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al Styles and Their Impact on Peer Interaction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Understanding[C]∥Bienni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Tampa, Florida.
ROBBINS C, EHRI L C. 1994. Reading Story-books to Kindergartners Helps Them Learn New Vocabulary Word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6): 54-64.
DE ROSNAY M, PONS F, HARRIS P L, MORRELL J M B. 2004. A Lag between Understanding False Belief and Emotion Attribution in Young Children: Relationships with Linguistic Ability and Mothers’ Mental State Language[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 197-218.
SAUSSY H. 2006. Unspoken Sentences: A Thought- Sequence in Chapter 32 of Honglou Meng 红楼梦[C]∥ANDERL C, EIFRING H (eds.).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Honour of Christoph Harbsmeier. Oslo: Hermes.
SCHOLES R, PHELAN J, KELLOG R. 2006.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Revised and Expanded[M].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J. Filmmakers as Folk Psychologists: How Filmmakers Exploit Cognitive Biases as an Aspect of Cinematic Nar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Spectatorship[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POLSKY E. 2010. Narrative as Nourishment[C]∥ALDAMA F L (eds.). Toward a Cognitive Theory of Narrative Act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VERMEULE B. 2010. Why Do We Care about Literary Character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ESSEL E A, STARR G, RUBIN N. 2013. Art Reaches Within: Aesthetic Experience, the Self, and the Default Mode Network[J].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7):258.
VINCENT J K. Sex on the Mind: Queer Theory Meets Cognitive Theory[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ALEN D H, ZUNSHINE L, HOLQUIST M. 2012. Theory of Mind and Embedding of Perspective: A Psychological Test of a Literary ‘Sweet Spot’[J]. Scientific Study of Literature, 22(2): 301-315.
WHITE T G, GRAVES M F, SLATER W H. 1990. Growth of Reading Vocabulary in Diverse Elementary Schools: Decoding and Word Meaning[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2 (2): 281-290.
ZAMJATIN E. 2008. Мы[We][M]. Moscow: АСТ.
ZUNSHINE L. 2015.From the Social to the Literary: Approaching Cao Xueqi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onglou Meng 红楼梦)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UNSHINE L. 2015.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UNSHINE L. 2011. Style Brings In Mental States: A Response to Alan Palmer’s ‘Social Minds’[J]. Style, 45(2): 349-356.
ZUNSHINE L. 2014. Theory of Mind as a Pedagogical Tool[J].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16(1): 89-109.
ZUNSHINE L. 2013-12-09.Why Fiction Does It Better[J].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B4-5).
ZUNSHINE L. 2006. 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许莲华]
The Secret Life of Fiction
ZUNSHINE LISA
(EnglishDepartment,UniversityofKentucky,LexingtonKentucky, 40065,USA)
A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has yielded the finding that children’s vocabulary is cor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theory of mind”. Reading fiction may have long-term beneficial effects on students’ overall academic performanc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theory of mind and the broadening of their vocabulary. Fictional mind reading intensifies certain patterns of mind reading present in our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For instance, triply nested mental states are omnipresent in the experience of reading and they constitute fundamental units of meaning in fiction. Literary texts always function on a higher level of nesting than do informational texts. Teach less of it, and only students whose parents encourage them to read a lot of fiction on their own will still do well. The less fortunate others will end with poorer vocabularies and grades.
theory of mind; triply nested mental state; fiction; vocabulary
2016-03-14
Lisa Zunshine(丽萨·詹塞恩),女,肯塔基大学Bush-Holbrook(布什-霍尔布鲁克)英语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认知诗学。
译者简介:邱小轻(1973-),女,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和叙事学。
I313
A
1672-0962(2016)04-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