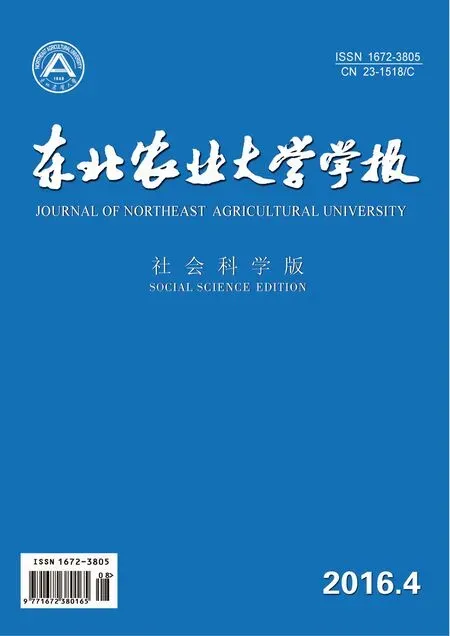从空间角度解读《舍巴日》中的性别叙事
2016-03-07汪立珍
谭 婷 汪立珍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从空间角度解读《舍巴日》中的性别叙事
谭婷汪立珍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根据福柯等人的观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基点,更是一个包含复杂权力秩序的集合体。《舍巴日》作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创作转型的代表作,揭示了土家族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深刻变化。小说中时间被淡化,突出空间特征,包括地理空间、神圣空间和文化权力空间等,呈现出湘西土家族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身份。小说中的不同空间在对话时反复呈现出传统性别秩序,地理空间的性别化体现出女性的“他者”地位,神圣空间的消解与重置体现出女性感性与男性理性的对立,文化权力空间内的两性关系则体现出男性的主导力量。从性别叙事角度考查两性关系在小说不同空间内的反复叠现,有助于了解叙事中作家对土家族内部传统性别秩序的态度,以及土家族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两性关系的变与不变。
空间;性别叙事;《舍巴日》
20世纪中叶,“空间转向”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态势。列斐伏尔认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他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知识直接介入物质生产的结果。列斐伏尔提出空间具有社会性,不仅包含生物—生理关系,还牵涉到生产关系,他将空间分成自然空间、神圣空间、历史空间、矛盾性空间、差异性空间等。福柯认为,空间并不是静止的、死亡的,相反,它是活跃的、具有思辨性的。在他看来,空间之间不是单纯二元对立的,我们不是生活在虚空中,“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2]”,也就是说,空间是多种关系的集合。索亚不断发展“第三空间”理论,他提出,第一空间是物质空间,第二空间是构想的精神空间,第三空间强调“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它具有潜意识的神秘性和有限的可知性,它彻底开放并且充满了想象。[3]”所以,第三空间既是真实空间又是想象空间,它将第一和第二空间中的二元对立关系解构后再重构。本文在综合几位学者关于空间认识的基础上认为,空间不仅是地理存在的基点,还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空间是权力秩序的体现,具有多重性、异质性、富有生命力等特征。“空间转向”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与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索,在许多作品中,“空间已成为现代小说叙事中的一种重要元素。[4]”作家们不仅将空间作为故事发生场所,还用空间表现时间、压缩时间,甚至用空间谋篇布局或推进故事发展,空间角度对了解作家作品中的权力关系极为重要。
《舍巴日》是土家族作家孙健忠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舍巴日”在土家语中是“摆手舞”的意思。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来自原始部落的女人掐普在现代社会里的种种不适,农村老惹在面对商品经济发展时的不断抵抗,年轻人不满父辈的固执,在城市文明的诱惑下不断“出走”的故事。孙健忠以前瞻性的思考深刻描绘了土家族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与外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揭示了土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刻变化,传递了他对民族发展的焦虑与希冀。
小说《舍巴日》具有明显的空间化特征,不仅展示了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地理空间,还将土家族人的文化、历史融入小说中,呈现出湘西土家族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身份。孙健忠通过《舍巴日》探索身处地域和文化“杂居”地带的湘西土家族人的历史命运,不断挖掘不同“层级”文明碰撞下土家族人的心路历程。小说中的时间被淡化,突出了空间的发展、变化,使得空间承载了更多的信息与内容。《舍巴日》中的空间化书写涉及地理空间、神圣空间、文化权力空间等,四种不同地理空间的人在对话时出现的悖谬与荒唐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将地域空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并置呈现,性别叙事在这种多重视域的空间化写作中贯穿始终,作家将地理位置性别化,让女性角色承担“返魅”的意味,使得传统性别秩序在不同空间中反复呈现。从小说的空间化角度探索贯穿文本的性别叙事,有助于了解叙事中作家对民族内部传统性别秩序的态度,以及土家族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两性关系的变与不变。
一、地理空间
小说里的人物与现实存在的人一样,必须在具体存在的地理环境中相互交往。因此,生存空间具体表现为个体存在的地理空间,地理空间的物理属性表现为小说中的空间场景。地理空间是人物活动的现实场所,也是文本叙事中开展的基点。《舍巴日》中的地理空间是十必恰壳—里也—马蹄街—港口,孙健忠将不同形态的土家族文明并行搁置,既没有单纯否定现代理性社会中另一个原始的“我”的存在,也没有单纯肯定势不可挡的现代文明。“十必恰壳”是原始巴人居住的地方,十必是小野兽,恰壳是大森林,那里的人们说着古老的巴语,跳着“撒忧尔嗬”和“舍巴日”举行古老的仪式,恪守古老的传统,他们“欢乐多于痛苦”。“里也”是“可耕种的土地”,即农村。在这里,土家族人靠以土地为生,大瓦房在村子里错落有致,一派宁静、自足的景象。以独眼老惹为代表的里也人是转变狩猎采集方式后的生产力代表。马蹄街是农产品聚集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农村高。但马蹄街上有些人心术不正,买卖中出现欺诈行为。港口即大城市,是孙健忠笔下土家族人要面对的必然发展趋势。老惹的儿子宝光、宝明去大城市打拼,在金钱的诱惑下逐渐“异化”,将自己看作不断生产的机器,逐渐忘却土家族人的历史与传统。作家通过人物在这四个地理空间的转换,不断审视土家族历史发展过程,指出一种明显的文化悖论。
十必恰壳—里也—马蹄街—港口转换成小说中的主人公,即:掐普—老惹、宝亮—岩耳—宝明、宝光,实质上即:女—男—女—男。可以看出,地理空间实际上被性别化了,而地理空间的性别化又反过来指涉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地理空间与主人公的性格十分贴切。大森林是茂密的、神秘的、多产的、感性的,正如女性性格中的柔软及拥有神秘的生殖力量。农耕土地是坚硬的,正如老惹性格固执一样。马蹄街界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虽已发展但水平还不太高,如岩耳一样虽已商品化、为人精明,但她依然无法摆脱旧习俗的桎梏。宝光和宝明的雄心勃勃象征着城市的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异化”。两名女性分别代表十必恰壳和马蹄街这两个空间,一个是原始、愚昧的地方,另一个是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地方,而男性则代表里也和港口城市这两个地方,里也拥有人赖以存活的土地,而城市则象征着为人向往的更高级的生活,男性总体上象征更好的生活、更先进的生产力,而女性则更多代表原始的、未开化的力量,其实是指代了女性的“他者地位”。
此外,地理空间的流动与选择体现出女性的“第二性”特征。掐普和宝光、宝明都是从一个地理空间到另一个地理空间,地理空间的错置不仅使他们的身体流浪,文化的“错位”感更使得他们的心灵经受了流浪。掐普从原始部落来到农耕社会并触摸到商品经济,她的流浪富有强烈的隐喻意味,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流浪。掐普来到农耕社会后,发现这里的巴人已经失掉了很多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不跳舍巴日,不敬白虎神,“不得了,白虎是老祖宗,我们子孙怎么能赶他、射杀他?掐普开始发现里也人的不善了。[5]”她的丈夫不亲近她,她也不用像在大森林里一样守着部落的火堆,只是不断地耕作、耕作,最后她发出了感叹,“啊,亲爱的十必掐壳,多么叫人怀念,掐普好悔啊,她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部落,跑到里也这个痛苦的地方来呢?[5]”这是掐普对以前生活的怀念,也是作者发出的感叹,民族的传统和历史多么令人怀念!掐普,这一十必恰壳的代表,在经历了排斥、融合的过程后最终因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又找不回自己的家园,真正成为了流浪者。宝光和宝明在大城市的流浪导致了其“异化”,他们回到家乡后,一句话也不说便倒床睡了七天七夜,“唉,我累,我累,累……[5]”“我怕,怕,怕……那火车叫得好吓人啊!还有汽车,满街来来去去的汽车……[5]”“‘真不知道,当初我们为什么要跑到这个鬼地方来?’‘你后悔了?’‘我想回去,我们家乡多清静啊,多安逸啊!’…[5]”宝光和宝明在梦中说的话真实反映了他们的处境:在大城市里像机器一样工作、生活。然而他们醒来后听说自己睡了七天七夜,便慌张地背起行李要再次出门,他们把金钱看得比土家族人最重要的节日——赶年更重要。“阿妈,如今世界上的事,我和你老人家难说清楚。外边是不清静,我和宝明是去吃苦、受罪。可是我们会慢慢惯势的,会喜欢过外边那种生活的。阿妈,这是‘时代’……[5]”这是土家族人面对现代工业文明时的向往与焦虑,他们纵然在大城市中艰难打拼,也要义无反顾地拥抱它,这是不可抑制的现代化潮流的巨大诱惑力。掐普、宝光两兄弟的不同选择显示出理性男性与感性女性之间的差异,掐普抛弃自己在文明社会打下的基础,“后退”回去寻找自己的原始部落,这是女性更念旧、更感性的体现,原始部落在这里像母亲一样可以给予掐普温暖。宝光和宝明在遭受心灵的磨难与流浪后,理性地选择继续“出走”,去习惯大城市的生活与节奏,城市像父亲一样给与他们力量。他们奔赴象征男性的城市,又成为城市象征中坚硬的一部分。
《舍巴日》中的地理空间是有性别的,男性如老惹的三个儿子奋力冲向马蹄街、港口城市,男性的拼搏、理性象征着城市与发展,掐普的蒙昧、神秘象征着森林与落后,岩耳的小精明正如商品经济刚起步的马蹄街。男性在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富有活力的部分,他们代表的空间是坚硬的、理性的,女性要么趋于原始、尚未开化,要么理性程度不如男性,她们代表的空间是神秘的、柔弱的,作家利用性别化的地理空间,叙述了土家族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他者”的位置。
二、神圣空间
神圣空间是指“某些空间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赋予了‘圣’的特性。[6]”,“在世俗空间中有时也能体验到能够唤起空间的宗教体验所特有的非均质的神圣价值。[6]”《舍巴日》中多处描写掐普跳舍巴日、敬白虎神、叙述洪水神话的场景,她虽已脱离十必恰壳这个原初语境,但每当这些场面出现时,这些空间对她有着神圣意味,构成了她在里也的神圣空间。小说在神圣空间内也不断推动传统性别秩序的呈现,在不断“祛魅”的现代社会,掐普身上的“魅”一部分被认可一部分被排斥。
查乞在土家语里是锦鸡的意思,她儿时便从十必恰壳来到里也,早已习惯里也人的生活。当独眼老惹想给宝亮定门亲事时,他“急忙去找那位一胎生出五男二女、又会捉鬼弄神的查乞,求她给老三宝亮找个合适的女人。[5]”可以推测,查乞在里也的生活里有部分是与“神鬼”有关的。或者,她从十必恰壳来的这一身份使得她身上带有某种神秘意味。当掐普想要寻找祖先白虎神的帮助时,“她去找同是从十必掐壳部落来的查乞。一升米,两颗鸡蛋,钱纸和香,使查乞变成神的信使。她骑着走马,嘀嘀嗒嗒回到遥远的武离钟落山,又把老祖宗廪君白虎神请来。[5]”这种古老的巫术有着神秘的力量,查乞的身体作为白虎神与人们沟通的媒介,逢请必应。掐普是查乞从原始部落带到里也来的,她身上也充分体现了“魅”的特点。当查乞叫她挑选一个人作为她的丈夫时,“她不敢挑,只在心里默默数着,数到十五(这是个吉祥的数字)的时候,随手抽出一张。就是这个了。这不是她的意思,是天的意思,是白虎神的意思。[5]”她的命运像古老的部落一样遵从保护神的意愿,将命运的决定权交给白虎神。当掐普踏入现代社会后,她依然遵从古老的信仰,曾前后两次寻求过白虎神的帮助。一次是当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对她不理不睬时,白虎神在查乞身上附身后告诉了她原因,她请求白虎神将岩耳吃掉。还有一次是当宝亮被关进监狱后,她请求白虎神将自己的丈夫带回来。在掐普的眼中,丈夫的无爱是因为其魂魄被其他女人“勾走了”,于是她跑去猫记饭铺找岩耳要求比试投剑、采野果、打野猪、跳舍巴日,要求她归还宝亮的“魂”。像掐普这样想依靠神灵杀死情敌、到情敌面前“索魂”等做法在现代文明中是不可理喻的,体现出其原始、蒙昧的特点。白虎神从头到尾都没有帮助掐普任何事,她用自戕的极端手段换得了宝亮的同情,宝亮实际上主导了她的命运、爱情与婚姻。在掐普的神圣空间里,白虎神的力量受到了质疑,她的命运也不由神来决定,而是由她现实中的丈夫来决定。
掐普是原始文明的象征。谢友祥认为,土家语称呼祖父为“阿谱”、“爬谱”等,与“掐普”音近,所以掐普还有比“花儿”更深的含义——老祖宗[7]。他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掐普不仅来自原始森林,她还将民族的历史带了回来,她像老祖宗一样了解民族的过去。舍巴日最初用于祭祀等仪式场合,古老的仪式歌成为原始文明的标志,传播舍巴日的掐普也就成了原始文明的载体。不仅如此,掐普还告诉里也人人死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事情,应跳“撒忧尔嗬”,她将阻挡白虎进门的弓箭拔掉,提醒人们白虎神是巴人的祖先,应该欢迎等等。掐普是“魅”的代表,她代表民族的过去,她身上体现出在现代社会不受欢迎的“原始”“野蛮”与“落后”,然而也正是这个来自原始部落的野人带回了民族传统,恢复了某些已被“祛魅”社会遗忘的民族文化。
《舍巴日》中的洪水神话作为隐喻贯穿小说的整个谋篇布局,隐喻了土家族的发展。“滔天的洪水退了,世间上没有人了,只剩下葫芦船上的两兄妹,阿哥叫布所,阿妹叫雍尼。[5]”在孙健忠看来,现代化就像一场洪水,是对土家族文化的一次重大考验,但土家族文化的根脉会像洪水神话中的布所和雍尼一样存活下来并继续繁衍生息。洪水神话与文中多处内容相互照应,小说最后部分有一场大雨下了三天,鸡、猪等都患了瘟病,掐普说:“阿爸老祖宗,只怕要涨齐天大水了,老祖宗,世间上就会没得人了,救救我男人吧,只剩下葫芦船上的两兄妹了。[5]”掐普内心深深地恐惧着洪水,她甚至认为应该杀一个人去敬白虎神。里也社会里法律规定连牛都不准随意杀,更何况用人祭祀这种野蛮的仪式?掐普总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小说中的岩耳与木瓜丈夫是表姐弟,她受娘家胁迫嫁给表弟,就像洪水神话中的“兄妹婚”一样。洪水神话中的“兄妹婚”有着神圣意味,是民族繁衍生息的力量,但孙健忠有意打破这个空间,将“兄妹婚”看作是愚昧的、阻碍民族发展的。这场大雨就像一场仪式,古老的神话提供前车之鉴:洪水会冲走必然要被冲走的人,即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比如木瓜表弟和野人掐普;洪水最终留下了宝亮与岩耳,一个美丽、精明,一个踏实、肯干,他们的结合承载了民族的希望与繁衍生息的力量。
小说在“返魅”与“祛魅”的叙事中往来穿梭,查乞和掐普都是“魅”的代表,岩耳虽想彻底“祛魅”,却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宝亮不断对掐普进行“祛魅”改造,他掌控了掐普的感情,他也成为掐普神性空间运行的中心。宝亮出狱后与岩耳终成眷属,既是打破了“兄妹婚”的神性空间,又寄托了作家对新神话的期待,期待他们的结合能带来新的力量。
三、文化权力空间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ϗ[8]”“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9]”即:空间不是静止的、死亡的,是一种权力表征的方式,在一个空间内,不同的人被赋予不同话语,产生不同权力。文化权力空间在小说中的呈现寓于人物关系中,人物的刻画与人物关系体现出不同话语的较量。《舍巴日》在文化权力空间内通过两性之间的位置、两性关系等方面指涉了女性的“他者”身份。
从女性特征来看,掐普与岩耳代表了女性的两个极端。掐普是从大森林里走出来的,身上拥有与理性文明不同的特征,她不洗脸、不洗澡、不梳头,一身骚臭,是野人模样。她不懂文明的法则,把跑出去的家猪打死后扛回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她身上原始、蒙昧的特征不讨男性喜欢。而岩耳则积聚了为男性激赏的所有条件,她为人精明、风情万种,“加上她完全照一个城里女人最新派的打扮,哒哒响的高跟靴,屁股包得紧紧的裤子,米黄色毛线开胸衣,在手腕上和手指上闪闪发亮的手表和金戒指,浑身散发出的捉摸不定的异香,使她显得无比华丽和高贵。[5]”岩耳是一个迷人的精灵,是猫记饭铺里的“摇钱树”,是颠倒众多男人心魄的女人,她是“现代物质文明的样品”。无论是野蛮的掐普还是柔情似水的岩耳,她们都被“物化”,被标签化、被反复观看。掐普的“原始人”装扮、生活习惯被人嘲笑、戏弄,岩耳的美则被物化成城市的复制品,高跟靴、包紧的屁股、毛线开胸衣、手表和金戒指、异香,城市文明的包装更加突出她的女性特征,岩耳成为城市物质的消费者,而她也成为男性的消费对象,满足男性的欲望与窥视。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概括出:“女人既是夏娃又是圣母玛利亚。[10]”无论将女性看作天使或者恶魔,其实质都是将女性作为不平等主体对待。岩耳既是“迷人的精灵”,又是害宝亮进监狱的间接推手,她美,但也有“毒”,男人必须当心。当掐普第一次闻到岩耳身上的香味时,她认为正是这香气勾走了宝亮的“魂”,于是她回里也后摘了很多野花戴在身上,希望这样的香味能吸引男人。在这里,岩耳已被当作包括掐普在内的许多女性的“样板”,她们观察她,模仿她。男性设下的刻板印象将女性同化为带有香气的、温柔的、有鲜明女性特质的。所以当掐普长久地纠缠着宝亮,跳舍巴日想讨得他的喜欢时,宝亮并没有从她身上找寻到任何“女人”的愉悦感,不惜用暴力拒绝她的要求。“她要,她要……她受不了哪,就会死哪!让那个该死的岩耳,把宝亮的魂魄退回来……老祖宗,老祖宗……[5]”掐普体内不断萌动的生命力催发了“我要,我要”的乞求,向男性乞求。不仅在男性的眼中,掐普不受人喜欢,甚至在女性的观念里,像掐普这样的野人算不上“真正”的女人。“真正”的女人应该像岩耳一样有娇嫩的脸庞和丰腴的身体,可以抚慰男子的身体和心灵。宝亮的身体和心都属于岩耳,而掐普一样都没有,与其说掐普败给了岩耳,不如说她败给了先进的“文明”。
掐普与岩耳的特征被孙健忠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她们与男性的关系更体现出男性的主导地位。掐普原先所在的部落里,分工极为明确,“男人进山打猎,下河捕鱼,女人或出去摘野果子,或留下带孩子,烤兽肉和守火堆。[5]”这说明男性在掐普所在的部落里已经占据经济主导地位。掐普来到里也后,认独眼老惹为阿爸,跟他学做阳春,老惹总是一种包容的、指导的姿态管理掐普的生活、劳作,因为他认为掐普是需要被管教的“野人”,潜意识里将她放在比现代人低的位置上。岩耳虽美丽、精明,但也没能逃过“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的传统习俗,被猫家当“续骨种”接过来成为一个傻子的媳妇,平日里要忍受像西尼嘎这样的男性客人的调戏,“让这个风骚女人给自己端饭送菜,高兴时调笑几句,把眼睛勾着她那最诱人的部位看,甚至乘人多拥挤时,故意贴近那个柔软的身体,伸手随便在什么地方捏一把,以不多几个钱,买来一种享受,实在不算吃亏。[5]”而一有风吹草动就被猫老板收回所有的钥匙,失去经济大权。岩耳没有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她需要不断牺牲自己的身体为猫家打理好饭铺,即使是明知道遇见了想占她便宜的人,“故意扭扭迷人的腰肢和屁股,回头给西尼嘎一个极其妩媚的笑脸,仿佛给他一种暗示,一种鼓舞,一种幻想。[5]”将一个来自原始部落的女人与一个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女人联系起来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男人。宝亮迫于老惹自杀的压力而将掐普娶进门,但他却不爱她,他爱的是精明美丽的老板娘岩耳。小说中有两段分别关于宝亮与岩耳、掐普亲热过程的描写:
“她快活得发着抖,又去热烈地吻他,不停地长久地吻,将一个舌头伸进他的嘴里。她还狼一样用牙齿咬他,用舌头舔他……一张娇嫩的脸盘与一张粗糙的脸盘相互摩挲,如牛挨痒。后来他们倒下了,在草地上胡乱翻滚半天,终于联结成一体,直到彼此将对方捏得粉碎。[5]”
“这晚上,是掐普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晚上。她发了疯似的,大声哼着,呻吟着,哭着,喊叫着。宝亮用手捂她的嘴。她又像母狼一样,残忍地撕咬宝亮,露着尖利的牙齿,伸出长满小刺的舌头,还伸出一对锋利的前爪……若不是宝亮奋力反抗,说不定已被她撕个粉碎。吃进肚子里了。她还唱起歌来,大声大声唱,像狼的嚎哭。[5]”
仔细对比这两段描写,掐普更具有“原始”的特点,她像只野兽或动物一样,而岩耳的“娇嫩”则让宝亮非常享受。同样是用舌头、“像狼一样”舔宝亮,然而宝亮所倾注的情感完全不一样。他对岩耳是出于真心喜欢,而对掐普则是同情。用性来满足一个女人的需求,让女人臣服,宝亮似乎已经占据一个更高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无论是原始女性,还是现代女性,她们身体的欲望都需要他来满足。“她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劣等性才把自己交给男人,而是因为她把自己这样交给男人,她才接受了她是劣等的这个观念,才建立了关于这种劣等性的真理[10]。”就是这样两个女人,在宝亮进监狱的时候,岩耳“厚起脸皮来闯乡政府”为宝亮伸冤,当她被挡回来后,她倒在床上直流眼泪。岩耳是极度伤心的,既为牢里的宝亮哭,也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哭。掐普并不知道宝亮去了哪里,她满山遍野地去找寻宝亮,把屋里屋外的地方都找遍了,她甚至用手去扒开每一座坟墓,看看里面有没有她的丈夫,她野蛮却情真意切!岩耳与掐普这两个女人都如此坚定地爱着宝亮。最有趣的是结局设定,真相澄清后宝亮回到里也,掐普和岩耳和睦得如同亲姐妹。掐普与岩耳在宝亮进监狱后开始和解,等宝亮回来后,掐普选择了悄悄离开回到自己的世界,成全宝亮与岩耳的爱情。在这段三角关系里,掐普与岩耳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姐妹,而这个农村男人完全成了中心。
《舍巴日》中的女性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两性关系呈现出拯救与改造的态势。因为男性的需求,查乞将掐普从原始部落里带出来,独眼老惹不断改变她劳作的方式,教她如何适应农耕生活——比采集渔猎更稳定的生活方式。而掐普的男人——宝亮,则传输给掐普现代人关于婚姻的观念:婚姻要基于爱才能幸福。宝亮按照现代女性的模样改造掐普,送她香粉、新胶鞋和起花涤确良衬衣,叮嘱她“拖鞋落雨天穿。衣服等夜边洗过澡就穿。[5]”宝亮用男人的眼光改造着这个从原始森林来的女人,一步步改变她对自我的认知,并将自己逐渐同化成“商品化”的女人。岩耳表面上虽是风光的饭铺老板娘,但她是迫于舅家压力嫁给了一个傻子,她一辈子都被限制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没有爱,没有性,只有唯利是图的舅舅、只会呵呵的傻子和一帮占她便宜的男人。当她遇到宝亮时,她像遇到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住,但她的命运依然跟这个男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宝亮进监狱,猫老板便没收她的钥匙,使她失去权力;当宝亮出狱后,她便同时获得了自由,恢复饭铺老板娘的身份。宝亮实际上拯救了岩耳的爱情与生活。
《舍巴日》里的男性与女性处于“看”与“被看”的位置,男性在两性关系中体现出其主导位置,他们掌控着女性的命运,这种不对等关系突出了男性的力量与中心位置,并将女性置于“他者”的位置上。
四、结语
《舍巴日》中的地理空间是有性别的,从十必恰壳—里也—马蹄街—港口,小说中的男性占据城市与土地,女性占据森林与小镇,而女性倾向于原始、愚昧、感性、软弱,男性则倾向于现代、文明、理性、精明强干,所以男性和女性代表的地理空间带有不同特点。在神圣空间里是“魅”与“祛魅”的博弈,查乞和掐普这两个从十必恰壳来的女人在文明社会里充当“魅”的角色,宝亮成为掐普神圣空间的中心,为了他,掐普多次请求祖先白虎神的帮助。以宝亮为代表的男人则是现代社会中“祛魅”的象征,他按照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断改造掐普,不断祛除她身上的“野性”。小说中的女性与男性处于不对等的位置,女性特征被极端化,要么野性如掐普,要么可爱如岩耳,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是被改造、被拯救的关系。通过考查《舍巴日》中性别叙事在不同空间中的呈现,可看出小说中不同空间的叠合呈现出传统性别秩序,体现男性的主导力量,女性仍处于“他者”位置。
[1]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王志弘,译//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和上下文[M].陈志梧,译//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龙迪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3(10).
[5]孙健忠.猖鬼[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6]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7]谢友祥.土家族文化寻根中的未来关怀——重读孙健忠的《舍巴日》[J].民族文学研究,2001(3).
[8]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M].陈志梧,译//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9]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M].陈志梧,译//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10]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I247
A
1672-3805(2016)04-0066-06
2016-04-24
谭婷(1992-),女,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