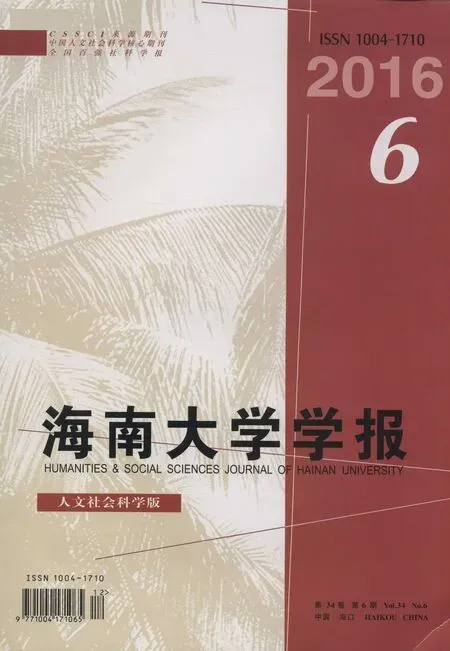直播
——视觉消费与权力隐喻
2016-03-07刘汉波
刘汉波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直播
——视觉消费与权力隐喻
刘汉波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继2015年中国互联网关键词“网红”之后,2016年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无疑是作为视觉消费的“直播”。越来越低的视频传输门槛、爆炸式增长的用户基数、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资本涌入,以及“网红”和明星的助阵,使得直播在改变着互联网格局的同时,还直接影响着“网红文化”共同体下的文化生态。现场化、真实化、互动化巧妙地置换了“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使虚拟身份兑现成现实资本,甚至改变着网民身份确认的模式。
直播;亚文化;视觉消费;权力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经历了以网站门户为代表的“互联网1.0”时代和以论坛社区为代表的“互联网2.0”时代,并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狂潮下进入了“互联网3.0”时代。这意味着互联网的运作逻辑由网站向用户提供单向图文信息输出,转变为网民与网站、网民与网民间的双向互动,最终进化为图文声影全方位的互动。“真实—虚拟”这套二元对立关系的壁垒因此就显得越具游移性和渗透性,真实所涵盖的现实经验往往被具有存在效果但并不一定能或曾直接见证的视觉经验所代言。而作为生产视觉经验的“直播”,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异军突起。
如果说2015年的网络年谱里,“网红”是引人注目的关键词,那么2016年刚过一半,“直播”就以互联网新宠的角色高频率地进入公众视野,甚至一度改写着互联网的运营格局和资本运作。它反映了“互联网3.0”时代之后的一个转向:个体经验分享代替了部门内容输出,泛平台传播代替定向发布,观众需求主导着制作人的内容投放。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内容的可视性越来越强,在场性、互动性、实时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视频制作、传输、储存和分享的门槛全面降低,在传统的电脑终端直播炙手可热的时候,手机端的移动直播迎来大爆发,正在成为新世代的互联网社交平台和超级入口。这不但是资本与市场迎来新一轮角逐的前奏,还是数字时代中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视觉内容成为消费对象的象征,更是互联网文化生态的微妙转向:在现实符号化、影像化的消费社会①中,人们可以通过视觉生产和符号消费来重塑社会角色甚至改变社会地位。
一、视觉生产与符号消费
2005年,中国国内出现了第一个专门的视频聊天室,以交友聊天和演艺秀场作为主要内容。2008年投入运营的六间房和2012年的YY接着成为综合直播的主要公司。2014年随着斗鱼、虎牙等细分直播类别的垂直直播网站的出现,直播迎来了一个高潮。2015年,网易、阿里、腾讯等大型知名互联网公司纷纷开辟直播业务。2016年,随着映客和一直播的崛起,中国正式进入移动直播时期,直播也随着“互联网3.0”时期的白热化迎来了新一轮高潮。直播能在2014年到2016年密集地暴露在公众视野内,并非偶然发生的,也不是简单的市场现象,它从萌芽、发展到成熟,同样也是逐渐发达的消费社会在视觉生产和符号消费上的形态更替。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入轨道后,丰裕(Affluence)、共识(Consensus)和中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从不同的层面共同改变着社会的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简而言之,丰裕和共识促成了具备可观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的生成,这就促生了一些新的社会人物类型、社会行为安排和价值观,消费社会逐渐形成。消费社会步入轨道后不断发展,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娱乐业全方位兴起,世俗文化成为“文化产业”,消费文化也开始以不同的面相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态里。而视觉消费,便是消费文化下的一种多变又普遍的面相。
视觉消费,本质上属于符号消费的一种。消费社会的兴起和消费文化的渗透,迫使人们置身于鲍德里亚所描述的“物体系”的差异结构当中,消费过程在某个意义上形成了人参与“符号—物”的符号活动并从中获得一种幻象满足的过程。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事物都是可被消费的“商品”,所有“商品”都是符号,所有的符号也都是“商品”[1]。视觉形象,自然也被纳入消费的范畴。如此一来,身体、行为和空间都被纳入这场符号活动中,不仅成为主体幻象的载体,而且成为符号价值的载体。而直播这种以传递动态视觉形象为运作机制的互联网行为,实质上也是一种符号消费。在消费社会里,它存在着一套有迹可循的演绎逻辑。布尔迪厄曾通过场域、资本、惯习和趣味这四个要素去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消费现象。一定的场域意味着主客体关系之间的网络和构造,这是实现某种同质化的语境前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便在不同场域中寄存并相互转换。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置身不同的位置从而对应地影响人们的认知、评价和鉴赏,这些惯习最终产生了趣味[2]。相似地,直播也由场域、资本到惯习、趣味支撑着运作。
直播作为这种互联网时代的视觉消费行为,其所处的场域是数字视觉技术所制造的虚实渗透,即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改变。丹尼尔·贝尔曾在探讨“视觉”在现代生活的位置的时候,提到当代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强化视觉成分。他认为,当代世界是一个城市世界,大城市生活刺激并限定了社交能力的方式,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3]。这便制造了人群同质化的前提。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网络提速的成本下降、便携移动设备的高度智能,视频传播的门槛降低,动态的视像成为每个人都可以生产、传播与消费的经验载体。从早期网页的静态图片到后来的gif动图展示,从需要跳转的视频超链接到在当前网页便捷播放的窗口,从微博支持Live Photo*Live Photos是在照片拍摄前后录制一段1.5秒的动态视频,当用户在照片上深按一下,照片就会自动播放动态效果。到微信朋友圈的小视频功能,视觉作为载体的“虚拟”不再简单地作为由数字传递、程序驱动的方式所创造的真实物的感知,更成为了基于二手经验的真实判断,转换成一种通过视讯终端确认自我并生产形象的新型社会关系结构。在这样的场域下,拥有经济资本的投资方和融资人、各个领域中携同文化资本的草根名人或明星甚至一些具有社会资本的机构组织便一拥而入。从老牌直播间YY、斗鱼、虎牙等到网易、腾讯、360等各大知名互联网公司,从Papi酱这样的“2016年第一网红”到范冰冰、杨颖、周迅、甄子丹等当红明星,都以各自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场域的角逐中。根据新浪官方的《微舆情》分析数据,截至2016年4月,国内已知直播平台共有116家,其中2016年4月前成立13家、2015年出现27家、2014年出现29家、2013年出现11家、2012年出现11家、2012年以前出现25家。可见,直播平台在近三年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占直播平台总数的60%。在场域和资本都做好铺垫的前提下,“读图时代”所带来的视觉经验和感官享受更迅速地跟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接轨,并与大众对视觉形象的需求紧密结合,视觉消费由手段转换成目的。
可以说,直播的盛行,尤其是2016年来移动直播的爆发,是当今消费社会的新一轮狂欢。它不仅成功地背向实体经济实现了虚拟形象兑现财富的“符号消费神话”,还在这样的符号消费中通过权力的转换重构着人们的阶级属性,改变着人们的阶层差别。
二、“网红文化”:想象性关联中的亚文化
如果说消费文化是当今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那么“网红文化”*“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曾被列入《咬文嚼字》2015年12月发布的“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当中。他们是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皆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成为“网络红人”。“网红”也跟互联网一样,经历了“文字网红”、“图文网红”和“宽频网红”等不同的代际。“网红文化”也就是通过“网红”的运作模式在公众视野内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亚文化。则成了与之相对应的亚文化。直播作为新兴的视觉群宴和符号狂欢,依托着“网红文化”来进入公众视野,或者说,直播是“网红文化”这种亚文化里其中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消费文化(主流文化)—‘网红文化’(主流文化对应的亚文化)—直播(具体表现)”的脉络可谓清晰可寻。
“网红文化”与网民的审美、娱乐、窥私等心理高度契合,通过人气聚集而实现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转换。它一度以亚文化的角色充斥着公众视野,甚至直接影响着互联网经济和网络社交生态的运作。亚文化是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是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4]。作为消费文化下的亚文化,“网红文化”的独特价值和观念在于,它试图打破市场经济早期“勤劳致富”这种传统的资本积累模式和消解“劳动光荣”、“实干精神”这些价值判断,通过将主体塑造成大众视野内的符号消费对象,实现知名度、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三位一体跃升。这种“一夜暴发”式的跃升,其实现前提其实就是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的体现:想象性关联,也就是把事物纳入符号指述当中的功能[5]133。它直接致使生产消费让位于符号消费。
直播作为一种视频传输形态,通过真实、生动的传播,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吸引眼球,实现了即时化、现场化、生动化的传播效果。早期的秀场直播脱胎于视频聊天室,主播们往往都是有一定才艺、衣着性感的美女,消费“颜值”成为一项可盈利的生意。随着直播内容延伸至游戏、泛生活等领域,现场感和社交性也越来越强[6]。直播平台就像一个结构庞大而操作灵活的欲望(需求)分拣器,将社会公众的窥私欲望、发泄欲望、身体欲望、猎奇欲望、表达欲望、认知欲望、共鸣欲望等分门别类地安置到不同类别的直播当中。观众在观看直播的时候,直播画面中的电子竞技游戏、美食或商品甚至人的肉体,无不成为视觉经验载体,对应着观众的想象。而直播的视频本身,则把观众的想象(能指)与直观动态的视觉经验(所指)关联起来。直播凭借动态的视觉内容,更为直观地把那些从一个意义系统中借来的事物,结合到一个由亚文化自身产生并通过亚文化的用法生成的不同的代码当中,以此来转变它们“既定的”意义。2015年以来,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下,“陪伴”与“分享”成为直播的新主题。直播的内容从美女秀场、游戏延伸到美食、美妆、购物等日常生活内容。2016年,随着“移动直播元年”的开启,化妆、美容、旅行、逛街、吃饭、宠物等移动直播日常生活内容,惊人地与已有十年积累的歌舞才艺、恶搞吐槽、游戏讲解等传统直播内容平分秋色。2016年7月11日,“2016年第一网红”papi酱在1小时25分的直播中,创造了2 000万人在线、1.13亿个赞、8家平台同步直播的纪录,而她直播的内容,仅仅是一边吃夜宵一边与观众互动并回答一些问题。
随时随地可进行、可互动的移动直播,使得观众在直播过程中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而是转变为可以与播主实时互动的主体。因为在移动直播中,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需求与播主互动,甚至通过打赏可以兑现为现实财富的虚拟礼物来引导播主满足自己的想象和需求。这意味着一场权力的转换:观众与播主的关系,不再是“看”与“被看”的关系,而是“陪伴”与“分享”的关系,是“引导”和“应和”的关系,是相互需求的关系。想象性关联所指涉的窥私欲望、想象代入、情绪发泄、感官猎奇等,在移动终端直播这里获得了新的升华,它们不再是在被动或隐秘状态下捕获播主感官形象的潜在行径,而是主动参与到视觉输出的公开演绎。这意味着任何可以进入直播的人都获得了以主体的身份直接观看甚至干涉客体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仅包含着间接支配播主身体与行为的能力,还意味着空间关系的改写。
褔柯在《另类空间》中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他认为空间是不能与人类活动分离的,它不是一个空的容器,而是具体的人的空间实践形式。因此,空间也不是现成给予的东西,而是通过实践和关系创造的。理解空间就是理解人类实践本身[7]。移动终端直播是信息传播高度发达和社交平台高度普及后,人类制造视觉内容的生产行为。移动终端直播所产生的或正在进行的具体位置,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坐标,或者一个客观的房间、草地、海滩或旅游景点,它成为了对应于直播行为的“可书写文本”。主播以既定的主题展开直播,观众或粉丝则通过流量与之互动,见证并参与到空间这个“可书写文本”的改写和赋意的过程当中。当直播结束后,整个互动过程被保存下来,生成一个可读取的视频文件,空间也就实现了即时性的现场还原到无限循环的永久符号的转换。在播主与观众的互动过程里,时间关系已经不再是人们把握现实、进行事件的衡量尺度和核心范畴,取而代之的是空间关系。“空间不是抽象的同一的秩序,而是由多元的、异质的关系构成的。在现实中存在着这样的场所,它既是现实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挑战、质疑、改写着现实。”[8]在这里,观众用添加意义的方式对播主所展示的空间进行改造,实现了重新赋意的权力。
三、身份建构与自我超越:“同源性”关系中的权力转换
在传统直播奠定10多年基础后,移动直播依托着“网红文化”在互联网上一路高歌,并改变着互联网经济产业的格局和互联网的文化生态。直播之所以能够在视觉消费的外衣下裹藏诸多权力隐喻,除了上述亚文化所提供的想象性关联之外,还因为作为一种亚文化,“网红文化”在群体中实现着“同源性” (homologous)关系。“同源性”关系是指人在群体中的价值确认,本质上是一种达成了想象性关联之后进一步的权力运作。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被用来进行想象性关联的事物反映、表达和呼应着群体生活的面相,一个亚文化群体所关联的那些对象,总是与他们的关切焦点、群体结构和集体自我形象有着“同源性”的关系,因为通过所关联的对象,他们可以发现自身的核心价值并加以保持[5]138。换言之,“网红文化”下的直播行为,它关涉的不仅是个体欲求的实现、感官想象的表述,还有身份转换和阶级差别。如果说亚文化所提供的想象性关联实现了大众的窥私欲望、猎奇心理、快感体验、情绪宣泄等表层需求,那么“同源性”关系则意味着社会身份的自我建构和社会身份的自我超越。
消费文化的定义者迈克·费瑟斯通在谈到符号消费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建构时候,提到人们通过符号消费来表现和维持不同的社会地位。为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表达,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消费,利用消费对象的符号属性强调生活方式对社会地位的区分,它激起人们对现代化城市的体验与生活方式的兴趣[9]。在直播这场盛大的视觉消费中,人们可以跨越所在地区、现实角色、社会阶层来主持或观看直播。作为视觉消费者的观众在直播的过程中几乎零门槛获得进入消费社会进行视觉消费的权力。鲍德里亚在描述消费者的某种微妙心理的时候指出:当消费成为社会的普遍标准时,没有消费就是没有进入消费社会的标志,这构成了现代人的深层负罪感,消费成了消除这种负罪感的必然方式[10]。如此一来,那些在直播中参与视觉消费的观众,便在相同的关切焦点中获得一种群体的归属,代入到消费文化的主流角色中,确认“同源性”关系。极光数据服务的统计结果显示,移动直播终端的用户群中,三线城市占了56.8%,华北、华东、西南和华南四个地区加起来占了超过一半。如果说区域划分或一线、二线、三线城市这样的层级划分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城市建设规模的大小、经济水平的高低、政治位置的远近和文化认同的强弱,那么直播这种视觉消费行为则为每个只要拥有电脑/手机并连上网络的人提供了高度现场感、还原化和参与度的视觉消费权力,这种权力是直接通往消费文化的文化现场的权力。
而作为视觉内容输出者的播主,只要在互联网社群中创造一定数量的能够引起用户活跃度的视像内容,被自身所感兴趣的内容所刺激的沉默用户(普通看客)就会变成活跃粉丝,从而帮助建立更广泛的内容传播和用户联接,为播主带来知名度、现实财富和社会地位。1992年出生的女主播沈曼在2013年之前是一位护士,通过“网红文化”发酵并成为大型直播平台YY的知名主播后,至今已经吸引了4亿名用户,年收入百万元。1990年出生的曹安娜在成为优酷来疯女主播之前是家乡的一名房产中介,月薪1 500元,转行做直播并在经纪公司安排的游戏代言、演艺和主持等活动后成为知名“网红”,曾在3小时的单场直播中收入26万元[6]。类似的“网红”主播在近年可以说是雨后春笋般出现。主播通过生产大众需求的视觉内容,演绎粉丝想象的感官形象,配合着社会情绪的走向脉络,这一切都反映、表达和呼应了大量视频直播用户乃至整个互联网生态圈群体生活的诸多面相、欲望和需求。相应地,作为反馈,主播受到更多粉丝的关注,获得粉丝所赠与的财富尊重。虚拟身份不仅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获得青睐、尊重和膜拜,还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切实的经济资本和循环运作的文化资本。在“同源性”关系中,互联网生态圈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的价值体系、道德法则、审美判断和群体认同的共同体。这种“同源性”关系下聚合的视觉消费共同体,曾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被齐格蒙特·鲍曼探讨过。鲍曼称之为“衣帽间式的共同体”,人们暂时放下现实生活的角色,怀着自己的兴趣在某个空间中寻找共同的意义,当他们在这个空间里被满足了需求、实现了想象或捕获了快感,他们便又返回现实角色[11]。主播在共同体里既充当着虚拟身份的偶像角色又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切实的资本,因而直播为这些“网红”主播们带来了社会身份的建构和自我超越。这也意味着,在当今消费社会里,传统的劳动不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以“网红文化”为代表的亚文化使符号的无限增值产生新的循环,每一样事物都有机会获得新生。移动直播的普及将这种“重获新生”的身份建构和超越变得更简单,更多人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成为“网红”或明星。换言之,视觉消费使得普通人可以用最普通的设备获得身份建构和自我超越的权力。
作为一个关键的社会学概念,“权力”的定义一度存在着争议。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控制他人、事件或资源的能力,马克思则将权力放置在社会阶级和制度去考量。通过梳理直播的起源、运作模式以及分析它背后的想象性关联和“同源性”关系,笔者认为,对于直播这个社会现象而言,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权力更趋向于褔柯所说的“权力是一种势力关系,一切势力关系都是权力关系”[12]。这种聚焦在势力关系的权力,在消费文化运作的时候又主要表现为符号权力。对于直播这样的视觉消费而言,“看”与“被看”是产生关系中的两股势力,“看者”的需求与“被看者”的视觉表达构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看者”获得想象性关联,并在最大化的互动中支配“被看者”的行为模式、身体走向和空间意义,最终获得进入消费文化(主流文化)的权力,在群体认同中确认“同源性”关系。而“被看者”则密切配合“看者”的需求,将他们的欲望结合自己的才艺兑现为可视化的视觉景观或视觉形象,从而产生经济利益,循环文化资本,最终获得身份建构和自我超越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同质化的、向心的聚合力量,维持着这套符号体系的中心地位。
四、结语
对于大众而言,公共领域不再是关切的焦点,私人空间成为大众可以投射欲望的场地。在事件、身体、形象等所有事物都可能被建立想象性关联的消费社会中,公共领域难以进行某种固定的、长久的、以时间为资本的宏大叙事,取而代之的是流动的、暂时的、以空间为基础的消费狂欢。而在视频的传输门槛急剧降低的今天,直播(尤其是移动直播)以其制造的现场感、逼真感和互动感,深化着上述的消费狂欢。这反映了在劳动分工精细化和社会角色定型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体作为劳动者的现实角色被嵌入到实体社会运行的每个组织结构中,个体必须与实体社会的运行节奏同步,于是,个体的时间很大程度上被“公共化”、机械化。时空关系也因而变得流程化,空间成了价值,时间则成了手段和工具。诚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新沟通系统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时间与空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象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13]如此一来,对时间的极度渴求和对空间的强烈占有,迫使实体社会中的个体重新审视程序化的固定劳作,并在碎片化的虚拟空间寻找补偿。当这种补偿不仅能够在虚拟空间中获得尊重和地位,还能兑现为实在的资本,能实现权力转换的时候,“虚拟”便进一步介入现实。直播的产生、运作和发展,无不体现着这份介入的力量。
可以说,这种“虚拟”介入现实的转向,是市场经济下社会实践所不可避免的遭遇,也是消费社会中个体所置身的境况。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不断形成视觉消费的时候,无论是将虚拟空间视为欲望投射对象的用户,还是将视觉消费视为权力转换和自我超越的主播,都将面临新一轮的自我身份确认的问题。因为,虚拟现实是一种具有无限接近现实体验的可能性的“他在”,如果它改变了自我身份赖以形成的条件,那么当个体依靠这样的“他在”确认自我的时候,视觉消费便不再是简单的行为方式,而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虚拟现实可以成为改变现实的资本,却无法从本质上代替现实。
[1] 让·鲍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
[2] 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引论[M].李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7.
[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33.
[4] 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1-136.
[5] 斯图亚特·霍尔.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M].孟登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6] 方正传媒.视频产业演进史[EB/OL]. [2016-05-15].http:∥www.199it.com/archives/456778.html.
[7] 米歇尔·褔柯.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2006(6):24-28.
[8] 汪行福.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与批判[J].天津社会科学,2009(3):41-47.
[9]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64.
[10]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3.
[11]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78.
[12] 吉尔·德勒兹.褔柯·褶子[M].于奇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66.
[13]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07.
[责任编辑:吴晓珉]
Live Webcast: Visual Consumption and Metaphor of Power
LIU Han-bo
(School of Humanit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Since “Internet celebrity” as a keyword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in 2015, “live webcast” as a style of visual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nother one in 2016. The increasingly low threshold for visual transmission, the explosive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users, the capital influx of a few Internet firms as well as the help of “Internet celebrity” and stars all make live webcast chang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 while directly affecting the cultural ecology under the community of “Internet celebrity culture”. Live field, authenticity and interaction skillfully displace the power relations of “seeing” and “being seen”, which exchange virtual identity for real capital and even change the modes of confirming the netizens’ identities.
live webcast; subculture; visual consumption; power
2016-08-26
① 迈克·费瑟斯通第一次将“消费者”与“文化”放在一起,创造出“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一词。他认为消费文化就是指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它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消费伴有符号生产、日常体验与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
G206
A
1004-1710(2016)06-0108-06